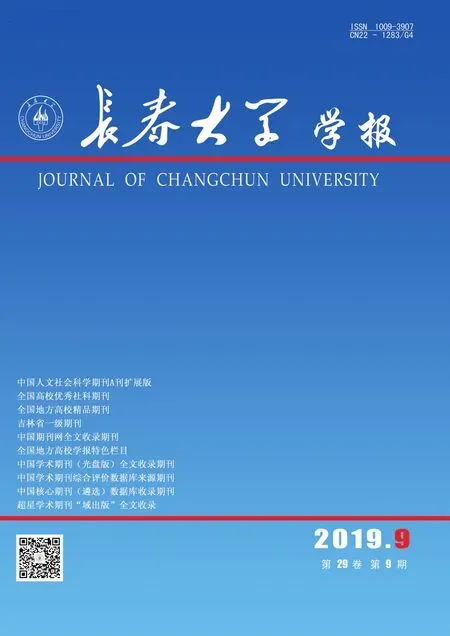文学翻译:还“陌生”以“陌生”?
刘为洁
(厦门理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4)
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是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什克罗夫斯基(Shklovskij)在《艺术作为手法》一文中对语言进行变形之后所具有的文学性作出的非常著名的解释。它的要义在于,文学文本要在语言和情节设计上“陌生化”于惯常做法,“使事物变得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1]。这里的“形式”不是与“内容”相对的,不是通常所认为的“思想的外壳”,而是指艺术作品的创造方式。这种创作方式往往直接体现作者的陌生化意图。陌生化的翻译过程因“异”而起,无“异”则无“译”;此处的“异”不仅体现在陌生化语言形式上的偏离,还体现于文化意义上的偏离。因此,陌生化可谓是作者在形式层面对相关常规语言有动因的偏离的一种逻辑活动。而由于翻译与译者的文化熏染息息相关,那么陌生化翻译作为文化问题便是对译者的一大考验,即对“异”的处理方法如何。
本文结合陌生化翻译的具体实例分析,试以类比的翻译策略从实现层、形式层和语义层三方面来探讨陌生化语言在跨文化语境下实现文学性对等的根本路径。
1 陌生化语言的英汉偏离形式
就文学性而言,陌生化最鲜明的特征就是挑战常规,但并非指晦涩难懂,而是让原来熟悉的事物变得新奇,是一种去除熟悉感、打破认知惯性的艺术手法。也就是说,陌生化是对常规的一种偏离。陌生化语言的关键在于常规语言和偏离语言所构成的互文张力。互文源自以往常规搭配所提供的关联性,张力来源于常规与偏离之间在当下所构成的不连贯性,因此,常规和偏离之间的张力是一种特殊的平衡关系。
实现这种关系的平衡需要译者寻求形意关系的最佳平衡点,否则就会稀释陌生化的作用力,危及译语文本的诗学价值和连贯性。译者想要再现陌生化意图,就必须在译语文本中生成偏离式语言以仿造互文张力,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学者主张还“陌生”以“陌生”的原因所在。然而,译语文本的偏离虽从文化意义上可呈现多样性,但在具体实现中又离不开现实特殊的语言形式,可以说,偏离的具体方式取决于语言形式的具体特点。
语言形式是制约译者再现陌生化意图的因素之一。进而言之,陌生化语言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文本系统的一部分,构成文本连贯的一环,只不过它所构成的连贯是特殊的连贯,或者说“有标记连贯”。有标记连贯的标记性源自偏离,而偏离以常规为背景,常规语言就是属于文本系统中的“无标记连贯”,没有常规就没有偏离之说。因此,按照常规的语言特征划分,英语可用于创造偏离的方法大致可分为五类:语音书写层面的韵律、谐音、叠词、拟声词等;词汇层面的同音异形词、双关语、字谜、仿拟等;语义层面的非常规搭配等;句法层面的倒装结构、违反语法常规的句法、排比重复等;篇章层面的回文、嵌字句、歇后语等。
本文将以上五类划分归纳为实现语言偏离形式的三个层面:实现层、形式层、语义层。其中,实现层包括语音偏离和书写偏离;形式层包括词汇偏离和语法偏离;语义层包括语义偏离。译者翻译陌生化语言时,首先就需要参照三个层面的语言特征对陌生化语言的偏离方式有所把握,然后在此基础上解读其文化意义,实现跨文化交流。
回顾陌生化的翻译研究,文学翻译中的陌生化形式、意义及其翻译策略引起许多研究者的关注。学者们讨论文学性的对等时主要关注的往往是文学语言的“形式”。然而,翻译范畴中的陌生化概念远比形式主义学派的复杂,具有双重文本性和跨文化性[2]。因此,不少翻译学者认为陌生化语言是不可译的。就文本类型而言,文学性越高的文本就越具有更高的抗译性,难以用另一种语言完全再现;就翻译主体而言,由于受其文体和诗学意识的限制,译者难以充分表现源语的陌生化手法。陌生化语言的可译性归根结底都归因于语言的不完备性[3]79。而语言的不完备性决定了语言的意义潜势这一命题,所以文本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开放性的,这才给读者提供了“见仁见智”的思考空间。
其实,不管文本和文化语境如何多变,语言自身就有一个不断丰富更新的过程,唯有如此,它才能推动不断涌现的“异质”的表达形式和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不管语际之间的语言差异有多大,任何一种语言系统都是自足的、具有表征性的,译语和源语之间虽然不可能“完全对等”,却可以最大程度地向“对等”趋同;译者不能保证将源语中所有的偏离形式加以体现,却可以恰当的翻译补偿策略最大化地再现源语的陌生化手法。换句话说,语言符号是有限的,但语言符号的组合可以表达无限的意义,在语言的转换过程中造成的意义上的偏离都能在另一语言系统中得到补偿[3]104。
2 陌生化翻译的类比策略
上述的分类对研究文学作品语言形式及其中所展现的陌生化特征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那么,在翻译过程中,汉语是否有与英语相对应的偏离方法呢?如果没有,汉语是否为译者提供其他方法作为补偿?以往研究者在研究陌生化翻译时提出的策略不是异化就是归化。然而,理想的译文应该是归化、异化适度,归化和异化并不截然对立,乃至译语读者既看不出“归”也看不出“异”来,悄然入于钱钟书先生所说的“化境”。因此,具有敏锐诗学意识的译者往往需要在“同”和“异”之间把握尺度,方能在二者之间游刃穿梭,把握互文张力的最佳平衡点。
过分归化,将掩盖源语语篇所蕴含的异域性特征,导致文学性的流失;过分异化,陌生化往往被陌生性所覆盖,而陌生性可能触发读者对他者的排斥,压缩读者的阐释空间和减少阅读的趣味。无论何种形式,都将导致诗学价值的不连贯,难以让译语读者产生相应的文化联想。因而,以类比的翻译策略恰恰是遇到文学性较强的文学文本时在特殊语境中所采用的动态、辩证的处理方法,不能把它简单地归结为归化或异化。
从性质上来说,类比就是根据两种语言在形式或功能上的相似以一种语言的表现手段表征或象征另一种语言的表现手段。它是基于两种语篇的形式对应而不是语义等值[3]223。从具体操作上来说,类比就是译者选用译语本土语言文化材料在译语文本中仿造陌生化形式的翻译策略,通过以“相似”为向度的类比法可以消除微观层面“遣词造句”等方面的“不可译”,彰显源语的“形”、“意”特色,使陌生化手法“现形”,通过手法的灵活调变寻求陌生化意图的“不变”。
下文旨在弄清在跨语言文化转换的过程中,译者能否在实现层、形式层和语义层三个层面以类比的翻译策略在译语文本中生成偏离、仿造陌生化形式的同时,将作者的陌生化意图明确传达给译语读者。这些问题对于想仿造陌生化形式的译者和研究者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1 实现层的类比
实现层的陌生化包括语音和书写偏离。当然,语音偏离与书写偏离经常有重叠之处。语音偏离指文本中某个或某些词语的发音违反语言系统的发音规则。现实生活中,由于情绪、受教育背景、方言背景或者仿讽他人等原因,人们在发音上有时会表现出与规范发音相距甚远的个人色彩。但译者仍旧可以利用错音字来进行类比翻译。错音字即用近似音来标示“不标准”的普通话读音,如我们网络用语中就常用“赶脚”表示“感觉”,“酱紫”表示“这样子”等。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中,译者在翻译AdventuresofHuckleberryFinn时就使用了这种方法突显老黑奴吉姆的种族和方言背景,如用“陀旧”代替“多久”,“史什摸人”替代“是什么人”。各地方言不同,因而在声母、韵母、声调等方面各有各的“不标准”,因此,声母、韵母、声调等都可用于变形,声母如“f-h”“r-l”“z-zh”“c-ch” “s-sh”“n-l”“d-t”“j-z”,韵母如前后鼻音之分,声调如一个调到尾。
书写偏离指的是对书写规范的违反,这种违反既可以在字/词之内表现为误拼误写某个或某些字/词,也可以在字/词之间则表现为违反正常的排列规范,文学创作者便泛化这些形式规则,把原来不组合在一起的语素组合起来,构成新词。这些新词作为对现有词汇的扩展,形式上的张力非常引人注目,而汉译也同样可以类比的方式让读者耳目一新。如SnowWhite中的一例:
原文:I am tired of being just ahorsewife.[4]
译1:我厌倦了仅仅做一个家庭主驸。[5]
译2:只当个家庭煮妇我已经感到厌烦。[6]
小说中,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同住,组合成一个现代“家庭”,她日复一日地为他们做家务,成了他们的家庭“煮”妇,她厌烦了自己的家庭角色,对歧视女性的社会忿忿不满,希望改变现状从平庸中得到解脱。不难看出,原文horsewife是housewife在形、音上的变异。在文学创作中,作者有时候会对某个符号进行变异,使它在形或声上临摹符号所描写对象的某种特征。这些形/声偏离符号原本并无拟声/拟像理据,但是特殊语境和作者的陌生化意图赋予了它们临时理据。在这里,作者就凸显词的理据,表达了她的言外之力。从符号上看,horsewife是一个偏离符号,能指是其音响形式或书写形式,所指是家庭主妇。当相关的horse及其引申义被激活时,这一能指就派生出另一能指,即“做牛做马”的主妇。在特殊的语境下,当双关语指向后一种能指所表达的意义时,用字面直译成“家庭主妇”的常规译法会使译语和源语发生冲突,不能再现作者的陌生化动因,此时,译者就应该用新的表征方法将其透明的文化意义陌生化,突显动因。
译1中,“家庭主驸”的译法虽然在“音”的偏离形式上看似保留了,尽管译者在语音层面下了功夫,但没处理好译语的形和义传递的最佳语境关联信息,普通读者不可能在horsewife和“主驸”之间找到关联。也就是,源语是双关语而译语不是,没有让译语最大限度地折射出说话人的陌生化意图。如果译语读者不能辨别译者的陌生化形式仿造的意图,那么这种形式的仿造就是失败的。译2的“家庭煮妇”虽与“马”不对应,但“煮妇”和“主妇”音似,在形式上相关,且在语义上暗涉“女人只限于厨房‘做煮(主)’”,将“主妇”概念陌生化了,可类比horsewife蕴含的“做牛做马”之义,与“主驸”相比,文化批判意味更加明显。horsewife之于housewife自然不同于“家庭煮妇”之于“家庭主驸”,正因其间既存在相似性又有相异性,我们才称作类比。所描写对象的相关文化特点是译语读者所熟悉的,读者可以把陌生化语言中的偏离特征和被描写对象联系起来,从而把握两者之间的临时像似性。英汉两套语音和书写特征都是在各自文化里才能表达它的本土文化意义的。因此,即使译者以译语本土的语音、书写偏离去对应源语文本的语音、书写偏离,它引起的是本土联想,而非源语的文化意义,所以译者只能诉诸于类比在本土文化语境中构建临时像似性。但这种像似性应为译语读者所识解,如“家庭煮妇”;而不能让偏离形式成为一种陌生性,如“家庭主驸”。
2.2 形式层的类比
形式层包括词汇偏离和语法偏离。词汇是作者或译者通过灵活运用现有构词规则,创造出现有词汇中不存在的词语。不过,新词虽新,却是依据原有规则创造出来的,或者至少与现有词汇存在某种联想关系,读者结合上下文语境基本可以理解这些新词。在新词创造方面,不仅“词”在英语和汉语中的地位不同,而且两种语言造新词的方法也不同,因而两种语言的新词表现出来的张力在程度和方式上有所区别。如:
原文:He went to India with his capital, and there, according to a wild legend in our family, he was once seen riding on an elephant, in company with aBaboon;but I think it must have been aBaboo——or aBegum.[7]
译1:他带着我姨婆给他的这笔钱,到印度去了。据我们家里一种荒乎其唐的传闻,说在印度,有一次有人看见他和一个马猴,一块儿骑在大象身上。不过,据我想,和他一块儿骑在大象身上的,决不会是马猴,而一定是公侯之类,再不就是母后什么的。[8]
译2:他拿着钱到印度去了。我们在家里听到的传说简直神了,说有人在印度看见他和一只狒狒骑在大象身上,不过我想那一定不是狒狒,而是位绅士,或者公主。[9]
《大卫·科波菲尔》本就是一部儿童文学名著,狄更斯在此精心挑选了3个博得孩子一笑的俏皮词汇,Baboon、Baboo和Bagum。它们在词汇形式的创作上不仅形式相近,而且音韵相似,整个句子因为词汇的偏离尽显童趣。译1为了传达这种俏皮的韵味,也用了3个发音相近的汉语词,但语义却与原文发生了偏离。原文中的Baboon指的是狒狒,这里却译为“马猴”,语义上虽有出入,译者的陌生化意图却不难被读者识解;而“公侯”“母后”的词汇偏离形式看似“无稽之谈”,却和“马猴”在音、形、义的创造上产生了语用关联的连续性,在字面意义上虽谈不上等值,但类比的语用效果却是对等的,源语的趣味性及形意之间的张力完全可以让读者“心领神会”。译2将这几个词直译为“狒狒”“绅士”“公主”,语义虽然准确无误地译出了,但读者很难在词汇的音、形、义上找出其间的关联性。其实,英语中并没有Baboo和Bagum,但前文提及“拿钱去了印度”,所以这两词应是仿造印度语发音的英语仿拟词,作者独具匠心,将两种语言和文化杂合以创造语篇的陌生化效果,实乃文豪手笔。在印度语中,Baboo指的是印度穆斯林土邦的公主,Bagum则是印度人对尊贵人士的称呼。如果译者没有从上下文识别出作者的陌生化意图,就不可能仿造偏离,那么源语幽默的陌生化意趣荡然无存,更谈不上文学性的对等;而如果译者采用译语词汇偏离去对应源语词汇偏离,首先就必须将语义逻辑本土化,即替换源语文本的语义内容,译语读者才能辨识和把握形式上的偏离意图。
语法偏离是指对语法规则的违反和扰乱,以致在词句组合上显得不合语法。“汉语的语法不像英语那样有显露的外在形式,……它不是通过形式(form)或形态(morphology)来表示语言成分之间的关系,而是让语义本身来体现这种关系的”[10]。英语语法的“刚柔并济”恰恰为偏离提供了条件和参照,使偏离的语言形式获得明显的对比张力。相比之下,隐性且弹性的汉语语法则无硬性语法形式要求,所以作者或译者难以用它来塑造形式上的对比和张力。一般情况下,英语语法形式只是语言使用的基本规则,文体价值不大,译者无须过多理会。但有时候,作者会违反语法规则,在形式上与上下文形成对比、联动和互动,表达特殊含义,此时扭曲的语法形式成为临时的新符号,参与文本主题意义的表达,对译者构成挑战。如:
原文:Next came an angry voice——the Rabbit’s——“Pat! Pat! Where are you?” And then a voice she had never heard before, “Sure then I’m here!Digging for apples,yerhonour!”
译1:再一会儿,就听见很发怒的声音——那兔子的声音——“八升!八升!你在哪里?”她听见一个先前没有听见的口音问道:“我在这儿,老爷您哪!我在这儿地底下掘苹果,老爷您哪!”[11]36
译2:接着传来的是一阵生气的叫声,那是兔子的声音:“派德!派德!你在哪里?”接着是一个她从没听过的声音:“是啊,我在这里!在挖苹的果,老的爷!”[12]93
每种语言都有独特的择句选词、修辞、话语标记等语言形式,其自身的形式特点从根本上限定偏离的可能方式。而上文中的Digging for apples是典型的语法偏离,dig和apple这两词完全搭配不当,这样源语的陌生化手法给读者就注入了新鲜、意外的感受。语言形式承载意义,甚至是文化意义,读者完全可以从上下文找出一些线索,还原作者的陌生化意图。Digging for apples的前面出现了一个人名Pat,相信源语读者肯定能辨识Pat是典型的爱尔兰名字。所以,Pat提到的yerhonour是your honour的语音书写偏离形式,同时杂糅了英语和爱尔兰语言的文化。而Pat口中的apples实际上是指“爱尔兰苹果”(Irish apple),意为“马铃薯”。擅长语言逻辑游戏的卡罗尔故意为之,以dig搭配apples。译1把Pat翻译成“八升”,“升”是中国式的计量单位,这种过度的归化翻译钝化了读者对源语中蕴含的异域文化的认知,更难以联想到“八升”与“掘苹果”之间有何关联性,偏离形式的仿造没有深化文本主题意义,也未能让读者产生相应的文化联想,因此就难以收获与源语读者类似的陌生化效果。译2中“苹的果”、“老的爷”是对语法偏离形式的翻译的一种创新性挑战,属于类比式的仿拟,体现于“苹的果”与“苹果”的差异,“苹的果”与“爱尔兰苹果”的共现。尽管“在挖苹的果”与“digging for apples”,“老的爷”与“yerhonour”在语法、语义上都不能对等,但陌生化的语用效果是等值的,读者能体会到译者仿造语言游戏的乐趣。可见,抽象的、主观的动因都可以落实和体现为具体的、客观的上下文符号关系。可以说,上下文符号介于偏离式语言和作者的动因之间,既是作者或译者向读者传达意图的桥梁,也是读者用于阐释偏离式语言为何被设计成如其所是的线索和依据。因此,译语既要体现偏离形式,又要体现作者的偏离动因,这就决定了以“相似”为向度的类比法的“呼之欲出”,因为类比既依赖于本土常规,同时又要打破本土常规的惯性,这无疑构成对译者的一种挑战。
2.3 语义层的类比
语义偏离是词语的基本义与当下意义的类比关系。语义类比属于语义相似性。常规语言和陌生化语言的区别就在于,常规语言或者是无此相似性,或者是有,但该相似性已被熟知而石化,在阅读过程中成为认知背景;而陌生化语言的语义相似性则是独特新颖的,其相似关系由文本语境临时获得,具有突出的陌生化效果。请看Alice’sAdventuresinWonderland第11章的1例:
原文:“——and the twinkling of the tea——”
“The twinkling ofwhat?”said the King.
“Itbeganwiththe tea,” the Hatter replied.
“Of coursetwinklingbeginswith a T!...”
译1:“……而且那个茶又要查夜——”那皇帝道:“什么东西查夜?”
那帽匠道:“查夜先从茶起头。”
那皇帝厉声道:“自然茶叶是茶字起头!……”[11]128
译2:“……还有一闪一闪的茶……”
国王问:“什么东西一闪一闪?”
帽匠回答:“我说从一开始——”
那国王厉声说道:“‘一闪一闪’当然是
从‘一’开始!……”[12]235
双关语属于特殊的陌生化语言,在这本儿童名著里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如果双关语按字面翻译,作者的陌生化意图就会在跨文化语境中立刻被阻断,获得的陌生化效果与常规翻译无异。原文“Of course twinkling begins with a T!”中的twinkle的第一个字母是t,又和前文的tea(茶)同音,成为一个纠缠不清的双关语。译1和译2都没有按照字面直译,都用了类比的方法。译1从一开始就没有把“twinkling”译成“一闪一闪”,而译成“那个茶又要查夜——”,读者不管从前文还是后文,除了“茶”和“查”是同音字,难以联想到“查夜”与“茶”之间到底有何关联,可以看出译者并没有识别出作者的陌生化意图,以致译者仿造陌生化手法的动因难以被读者所识别,偏离便难以获得陌生化效果,也稀释了陌生化语言的幽默感。实际上,源语中看似“满纸荒唐言”的陌生化语言的背后蕴含着卡罗尔严密的思维逻辑,都是有着很强的互文张力和关联的“逻辑游戏”。在这里,帽匠想到的是在第7章疯茶会中提到的歌“一闪一闪傻乎乎……好像茶盘飞四处”。所以,帽匠未说完的句子,可能是“……还有一闪一闪的茶盘”。因此,这种互文关联让译2的译者领会了作者的陌生化意图,从而在twinkling上下足了功夫,译者使用“‘一闪一闪’当然是从‘一’开始”的译法类比于“twinkling begins with a T”。“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这首童谣对中国读者并不陌生,读者应该容易识别译者翻译成“一闪一闪”的动因。这样一来,加上译者灵活利用tea和T的谐音特点,巧妙地在twinkling和tea之间建立起关联性。因此,语篇翻译的质量归根到底取决于源语与译语之间最佳的语言和文化的关联度。当译文难以直接传达语篇在音、形、义、修辞等方面的特质时,译者需要有敏锐的文体和诗学意识,体现源语的常规和偏离之间的张力连贯,有效地传达作者的陌生化意图或意蕴。类比式的仿拟可以有效地保持文体连贯性,其语义虽然不能够等值,却同样能达到“妙趣横生”的奇特效果。总之,陌生化的翻译属于文学性较强的翻译,因此在语际转换时,首先应对源语的文体偏离作出积极的诗学反应,然后诉诸于超越语言单位但保留陌生化意图的类比策略,这种意图无形中打上了译者作为文化“摆渡人”的烙印。
3 结语
如果说,实现文学性翻译的途径是还“陌生”以“陌生”的形式仿造,那这种观点只探讨了偏离形式本身,忽视了偏离形式的文本语境和文化语境,更忽视了翻译具有转化诗学价值和构建翻译文学性的施为力量。因此,决定陌生化“文学翻译”的关键要素不在于陌生化形式本身,“文学翻译”的实现途径也不在于陌生化形式仿造,“文学翻译”行为的决定性要素在于:译者需要在译语文本“异质文化形式”与译语文化本土文学形式之间突出相似性还是相异性。因此,陌生化翻译的悖论属性决定了译者进行还“陌生”以“陌生”仿造形式的同时,还需要译者具备敏锐的文体和诗学意识,在陌生化语言的三个层面——实现层、词汇层和语义层上以类比的翻译策略在跨文化语境下转移诗学价值并构建其翻译文学性。类比的翻译策略是具有动态属性、辩证的翻译艺术的处理手段,又是翻译认识论的科学方法[13],同时也是实现文学性对等的根本途径。类比的翻译策略可以让译者站在译语文化的角度,向读者呈现其观察源语文化的视角,将“异质”文化转化为“本土”文化的逻辑,在特殊文本语境中构建临时像似性,引发译语读者对源语文学文化的联想。当世界进入全球和本土相杂合的时代,我们以陌生化语言的翻译为旨来思考译者如何对待“异质”的问题就显得非常重要和必要,它不单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陌生化语言的翻译方法,而且有助于进一步认识文化审美活动的需求,并借此重审我们对文学性对等的既有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