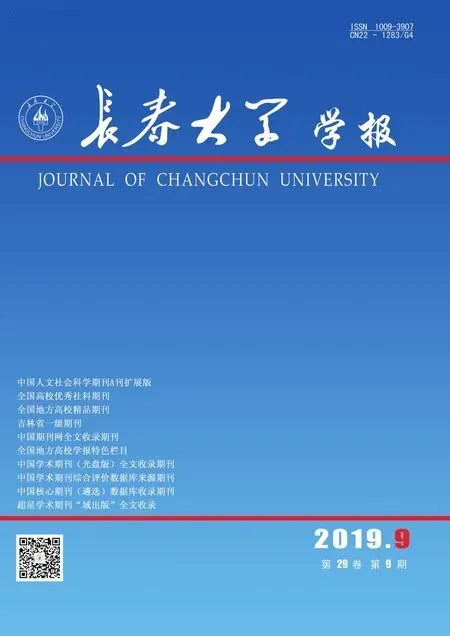翻译他者的文化动因
李慧芳,林 夏
(1.皖江工学院 基础部,安徽 马鞍山 243031;2.武汉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武汉 430072)
翻译与文化场的自我建构密切相关,中西方莫不如此。趋于稳定的文化场也会影响翻译对象和策略的选择。德国浪漫主义阐释学大师施莱尔马赫(F.Schleiermacher)主张“将读者带往作者”的翻译路径。鲁迅奉行“宁信而不顺”的“硬译”论。受德国浪漫主义存异翻译思想的影响,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L.Venuti)提出了异化翻译思想。翻译中保存的他者异质性,会对目的语的语言、文化和社会造成深远的影响,必须予以适当的调处。若在“传递性的掩饰下,对原作异质性系统的否定”[1]5,则只会是糟糕的翻译。翻译什么、如何翻译,应与文化场提升和完善文化量的内在需要相契合。本文拟从文化场、文化量与翻译动因的关系谈起,对比施莱尔马赫、鲁迅和韦努蒂的存异翻译思想的理论内涵和终极目标,以期厘清文化场自我建构与翻译中他者异质性调处方式的内在联系。
1 翻译与文化场的双人舞
文化场的形成、发展和走向强盛,翻译始终如影随形。众所周知,古希腊罗马文化和希伯来基督教传统是西方文化的主脉。古希腊文化,发轫于受古埃及文明影响的克里特岛,后为罗马所继承并发扬光大。公元5世纪初,哲罗姆完成了《通俗拉丁文本圣经》的翻译,16世纪的宗教改革期间,民族语译本的《圣经》也相继诞生。
1.1 文化场与文化量的概念厘定
文化场是一个较为宽泛的跨学科概念,专门对其进行界定的研究尚不多见。场的概念最初取自物理学中的磁场。人类很早就发现了磁性的奥妙,《古矿录》就有战国时期赵国磁山一带使用司南辨别方向的记载。磁场虽然不是由物理粒子所构成,不能为人们所目见,却客观地存在于磁性物质周围。本文定义的西方文化场,指的是以古希腊罗马文化为背景,以基督教各教派教义为传统,交织着近现代自然、人文科学成就的场域。文化场既是抽象的概念,又是具体的物质和区域存在。不但有类似于物理学磁场的无形控制力和影响力,也有建筑、服饰、饮食、交通、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等具体形式。文化场经过历史沉淀,往往以城市为中心,主导着自我场域中主体的行为和意识形态,并向四周辐射其影响力。
文化场在众多领域里拥有的历史积淀和发展水平必定有所不同。我们把文化场在相关领域历史积淀的数量和发展的质量称作文化量,用以表征文化场的整体属性。文化量又可分为有形的量和无形的量。有形量包括建筑、工具、书籍、服饰、饮食等摸得着、看得见的有形存在;无形量则包括历史名人、科技知识、人文思想等无形影响力,或曰软实力。文化场总有自身文化量薄弱的领域向该领域具有较高文化量的其他文化场借鉴学习、自我提升的内在需要。而文化量相对较高的文化场,也有向外传播其成就的欲望。文化场在全部领域的文化量都很弱或都强大的情况很少出现,因此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的互译总是存在的。文化翻译清晰地显示出文化场自我建构的艰辛和漫长的历程。
1.2 翻译与西方文化场
翻译,勾画出欧洲文化场的基本面貌。“希腊是欧洲人心目中的精神家园和文化故乡”[2]。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病逝,希腊帝国坍塌,崛起的罗马取而代之。随着罗马文化对希腊文化的翻译和改造,希腊文明的火种在罗马帝国得到传递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恩尼乌斯将希腊的六音步诗歌拉丁化,他与安德罗尼斯、涅维乌斯一道,改编、翻译了大量的希腊戏剧和诗歌,被誉为罗马文学的三大鼻祖。维吉尔摹仿荷马《欧德赛》的风格,创作出了罗马史诗《埃涅阿斯纪》(Aeneid)。“把古希腊文学特别是戏剧介绍到罗马,促进了罗马文学的诞生和发展,对于罗马以至后世西方继承古希腊文学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3]2。希腊文化通过翻译汇入了罗马文化,西方文化场的轮廓由此初现。
392年,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主导了欧洲人的信仰和意识形态。405年,哲罗姆译成了《通俗拉丁文本圣经》,希伯来基督教文化逐渐成为西方文化的传统思想。16世纪中叶的宗教改革中,各民族采用方言翻译《圣经》,确立了各自方言的母语地位。在德国,路德不仅开启了宗教改革和理性启蒙之门,他所翻译的《圣经》还草创了书面德语,并且建议其他译者在翻译时用方言的习语和表达[4]54。“路德译本《圣经》中所有的成语和句式都是德语的,是作家可以一直使用下去的”[5]。翻译为德国的民族统一奠定了语言层面的基础。在这一时期的法国,阿米欧翻译了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以下简称《名人传》),成为西方翻译史和文学史上的不朽之作。英国的诺斯也在1579年翻译了《名人传》,查普曼在1616年完成了《荷马史诗》的翻译,蒙田的《散文集》也在1603年由佛罗里欧译入英语。1611年《钦定本圣经》的出版被称为“英语中最伟大的译作”,更是奠定了现代英语的基本风格。同样是在翻译的驱动下,“在法兰西,侵入的法兰克人、哥特人、勃艮第人和诺曼人都已与原来的凯尔特人和巴斯克人融合在一起”[6]402。翻译促进了欧洲各民族亚文化场的崛起,民族语言间的翻译逐渐成为了必要。
17至18世纪的启蒙运动,民族意识进一步觉醒,民族语言更加受到重视,亚文化场也愈发显现出各自的独特性。此时的“翻译家们不仅继续翻译古典著作,而且对近代的和当代的作品也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赛瓦提斯、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歌德等大文豪的作品都被一再译成各国文学”[3]4。18世纪后半叶兴起的工业革命,使得科技进步一日千里,人文领域大师辈出,灿若星辰。历经2000多年的沧桑岁月,古希腊罗马文化、希伯来基督教传统、近现代自然/人文成就汇聚、交融,西方文化场渐趋繁盛。西方文化场自我建构的历程中,翻译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正是翻译,让荷马所描绘的特洛伊战争、赫西俄德所刻画的诸神之战扎根于各个民族的语言文化之中,成为了西方人的集体无意识。
1.3 翻译与中华文化场
中华文化场的形成,同样是一部民族融合史。
黄帝败炎帝,经尧舜禹、夏商周,中原民族逐渐融合,中华文化场雏形初现。东周王室暗弱,诸侯纷争,烽烟四起。“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使得各亚文化场隐约可见,其影响至今犹存。一统天下的秦始皇,推行“书同文、车同轨”,消解了各亚文化场的方言演化为独立语言的可能性。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奉儒家为主导思想。然而,“东汉后期的党锢之祸以及随之而来的魏晋禅让易代,使得两汉经学赖以生存的根基彻底动摇……名教成为窃权弄柄的旗号”[7]。玄学家们索性隐居于青山竹林间,专心于“三玄”的阐释,儒家思想已不能唯我独尊。正是释经这一语内翻译的形式,让儒道思想共同搭建起了中华文化的坚实基座。
季羡林先生视翻译为中华文化青春永驻的万应灵药。“倘若拿河流来作比,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水依靠的就是翻译。”[8]佛教东来,翻译居功甚伟。三国支谦的“因循本旨”,东晋道安的“案本而传”,不免还有些“过分追求实质,必然致使义理隐晦,不易了解”[9]70。六朝的鸠摩罗什“对于原本,有增有损,求达求雅,属于意译一派”[10]。唐朝的玄奘又有“五不翻”之说。面对文化他者,代代译者冥想苦思,笔耕不辍,化“异”为“己”,为中华文化场引来了清泉活水。佛教在佛经翻译的过程中,也在逐渐本土化,禅宗最终成为中土流传最广的宗派。宋明以后,佛经翻译的规模,已不能与两晋南北朝时期相提并论。然而,无论是回到孔孟之道的宋明理学,还是倡导“知行合一”的陆王心学,都已明显地打上了佛教思想的烙印。历经千年,阐释和翻译中,儒、道、释思想不断交融,成为中华传统思想的内核。
16世纪以降,悄然崛起的西方文化场开始向东方播撒文化量,翻译就是重要的途径之一。“明末清初来华的外国传教士,知名的有70余位,共成书400余种,其中有关科学的占130种左右”[9]307。当时所译的众多学科术语,至今仍在使用的也不在少数,客观上为中国的近代化做出了一定的贡献。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从迷梦中惊醒的士大夫阶层,开始向西方寻找民族自强的良方。新旧文化交替之际,严复、林纾等人翻译大量西方人文著作,产生出诸多重要的翻译思想。瞿秋白等人提倡用中国人口头上讲得出的语言来翻译,鲁迅则强调“保留洋气”,“宁信而不顺”的硬译论,反映出彼时的译者们渴望借鉴他者、革新民族语言文化的赤子之心。然而,历经坎坷的中华文化从来没有中断过,更没有消失。事实上,传统思想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通过外译散发着持久的魅力。德国的康德、谢林、黑格尔,美国的爱默生等人,都是中国古代哲学的读者。海德格尔还曾对“道”(Tao)、“逻各斯”(Logos),以及他的“自身的缘发生”(Ereignis)等观念作过对比研究。而在海德格尔看来,“他本人、荷尔德林与老子都是‘诗性的思想者’”[11]。
翻译就是如此,携带着文化量,穿梭在文化场域之间。
2 自我与他者的浪漫邂逅
倾慕他者,翻译居中传情。清代的陈澧曾说:“盖时有古今,犹地有东西,有南北,相隔远则言语不通矣。地远则有翻译,时远则有训诂。有翻译则能使别国如乡邻,有训诂则能使古今如旦暮,所谓通之矣。”[12]地远时遥,语俗各异,阐释与翻译可弥合之。
2.1 异质性调处与翻译动因
毫无疑问,谁翻译谁就必须面对如何适当地调处他者异质性的难题。
实际上,他者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跨学科术语。“‘异’可以用来表示自己所不了解的一切,与‘异’相对的乃是自己。”[13]翻译中的他者,表现为差别性、异域性和陌生性。语言、文化的异质性,在翻译中以他者的面貌呈现在译者的面前。翻译必须珍视他者的异质性。狄尔泰认为,“如果生活表现完全是陌生的,阐释就不可能。如果这类表现中没有任何陌生的东西,阐释就无必要”[14]。法国翻译理论家乔治·穆南在《翻译的理论问题》一书中也曾指出,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共性,构成了翻译的可行性,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个性即差异性,构成了翻译的必要性[15]。也就是说,正是他者与自我的差异性,翻译才是必要的。了无新意的完全归化之作,也就失去了对目的语文化场提升自我文化量的效用。
如前所述,文化场总有向相关领域文化量较高的文化场借鉴学习、提升自我文化量的倾向。文化场提升自我文化量的内在需要,就是翻译的动因所在。每个领域都拥有较高文化量的文化场是很少的,所以强弱文化场之间在不同领域的互译现象十分常见。翻译他者文化,无论采用何种方法策略,最终都是为了化“异”为“己”。译者的任务就是要解放寓于源语中的语义,让其在译入语中再次绽放出生命力[4]5。异质性不会也不可能永远以陌生的形式在目的语文化场中存在。随着时间的流逝,异质性要么不被接受而被淘汰或遗忘,要么逐渐被熟悉,最终融入文化场的自我文化。
翻译的目的在于融会贯通,化解文化场域间的交际冲突。因此,为适应读者接受的需要,翻译中他者的形变在所难免。文化场间的地域越是区隔,渊源越是疏离,译者就越有可能采取更为深度的归化,他者的形变也就会更加严重。不然的话,过于陌生的异质性就会伤及目的语文化场语言的完整性和文化的延续性,不利于译作的读者接受,更有损于文化场的自我建构。但归化并不等于彻底的同化,“同化是把外语文本转化为本土主流价值观的一种极为保守的方式”[16]24。在鲁迅看来,“……不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倘有,就是貌合神离,从严辨别起来,它算不得翻译”,翻译就要有异国情调,也就是洋气[17]。刘英凯赞同鲁迅“保留洋气”的翻译思想,极为反对《飘》的译者在翻译《飘》时把原属“客籍”的人名、地名都改“入”了中国“籍”的做法[18]。实际上,刘英凯所反对的“归化”,就是韦努蒂所反对的归化的极端状况——“同化”。文化场提升自我文化量的内在需要促成了翻译之实,唯有适当保留他者异质性的存异翻译,才能真正契合取“他者”之长补“自我”之不足的翻译动因。
2.2 文化场自我建构与存异翻译
文化场处在形成、发展或相对落后的时候,必然倾向于采用保留更多的他者异质性的翻译路径,以提升自我的文化量。德国浪漫主义存异翻译思想就产生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中。18世纪至19世纪初的英法等国,已发展为资本主义强国,而此时的德国却尚未统一,语言文化也相对落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甚至讽刺德语只配用来跟马交谈。“法语成了时髦的语言,法国思想方式和观点之崇高不亚于共和时代的最后半个世纪希腊思想观点之在罗马”[6]418。在这种境况之下,“德国需要的是从希腊语、拉丁语输入新的表现方式,重新丰富德国语言文化,来对抗大兵压境的法国扩张主义的语言文化,构建德意志民族身份建构,摆脱法国文化的霸权控制”[19]。
翻译他者文化,取其所长,构建自我文化,凝聚民族精神,成为此时德国文化精英的历史使命。事实上,在浪漫主义时期的德国,赫尔德、席勒、歌德、施莱格尔两兄弟、施莱尔马赫等人,都主张保留文本异质性的翻译路径。在赫尔德看来,“在从其他语言翻译优秀作品时,乃是语言或富有或贫乏的试金石。它拥有什么、缺少什么就会变得了然”[1]37。1813年,施莱尔马赫在柏林皇家科学院发表了《论翻译的不同方法》的著名演讲,系统地阐释了两种翻译路径:“译者要么尽可能的不打扰作者,把读者带往作者;要么不打扰读者,把作者带往读者。”[20]而他在实际翻译柏拉图的作品时,明确采用了“把读者带往作者”的存异路径。
存异翻译思想是浪漫主义时期德国文化精英的普遍观念,他们之所以翻译荷马、索福克勒斯、但丁、赛瓦提斯、莎士比亚,就是要改革德语,使其成为适合文化精英创作民族文化产品的“更为高雅”的语言,从而培育出强盛的德意志亚文化场。如果说是路德让德语书面化,那么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化精英对古希腊罗马经典和欧洲其他民族文学的翻译,则彻底地改变了德语“笨拙、僵硬”(A.W.施莱格尔语)的面貌,确立了德语与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同样重要的文化语言地位。德国人从此考虑的都是翻译外语,而不再是说外语了[1]148。存异翻译让德国迈出了民族统一、文化强盛的坚定步伐。
2.3 存异翻译思想之嬗变
存异翻译思想在不同的文化场有着迥异的翻译效果和理论境遇。
如上文所述,施莱尔马赫“把读者带往作者”的存异思想,有着特定的历史和人文背景。日耳曼人一直认为自己才是古希腊罗马精神的真正继承者。“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21]800年,查理在罗马城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直到1806年,弗朗兹二世才被迫放弃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尊号。虽然在伏尔泰看来,神圣罗马帝国“既不神圣,也非罗马,更不是帝国”,但是日耳曼人毕竟拥有罗马帝国皇帝的头衔达一千余年之久。F.施莱格尔和诺瓦里斯就不无自豪地宣称,他们古代的民族才是正统的罗马民族,德国就是罗马[1]51。
浪漫主义时期的德意志亚文化场还没有真正形成,德语相对还很落后,但毕竟是在“家”一般熟悉的欧洲文化场之内,继承的是身在其中且自认为是其正统继承者的文化,所以基本上不存在文化上的陌生感,更多的只是对语言异质性的调处。而欧洲的民族语言,与拉丁语都有着或近或远的亲缘关系。这些重要的历史人文因素,使得德语和德国文化能够通过存异翻译成功革新。而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中国,鲁迅等人的“硬译”之作,似乎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鲁迅与施莱尔马赫的存异之作的接受效果之所以迥异,主要就是因为两人身处文化场的具体情况不同,翻译的源出场和译入场之间的渊源也不同。与浪漫主义时期语言文化相对落后的德国完全不同,尽管鲁迅身处的中华文化场,当时在经济、军事、科学等领域已经被西方文化场超越,但毕竟在众多领域依然拥有深厚的文化量,尤其是五千年文明史所凝结出的浩瀚的文言典籍、宗法制度。另外,施莱尔马赫主要是在西方文化场之内实施的翻译,而鲁迅从事的主要是跨越中西文化场的翻译,不但要克服语言层面的异质性,还要越过差异巨大的文化鸿沟。“硬译”之作自然也就显得过于突兀,一时难以为国人所接受。
鲁迅主张“宁信而不顺”的翻译,也是想要借鉴外语的词汇和句式,“输入新的表现法”。实际上,当时甚至有人提出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的激进主张。鲁迅等人试图通过革新语言再造文化、让中华民族摆脱贫穷落后现状的赤子之心令人动容,但是语言进化毕竟是渐进的过程,思想传统也不可能在朝夕间推倒重来。所以,鲁迅的硬译翻译很难达到施莱尔马赫的存异翻译那样的文化效果。又过了半个多世纪,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提出了异化翻译理论。
韦努蒂的异化论,一定程度上是继承并发展了德国浪漫主义存异翻译的思想,但两者在理论内涵和终极目标等方面,有着根本的不同。在韦努蒂看来,“译者通过恪守当下的用法,维持一直以来的句法来呈现的语义,努力确保可读性,从而产生一种透明的假象”[22]。透明、通顺的译文导致译者隐形,遮蔽了译者的劳动付出[16]1,使得翻译和译者的地位边缘化,同时也“加剧了对英语译者的经济剥削”[16]17。韦努蒂认为,翻译处在一种无法自拔的窘境之中。一方面,翻译在各个领域都发挥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译者却没有出版商或其他赞助人那样的话语权,显示出翻译在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所处的尴尬境地[23]。于是韦努蒂想要构建一种全新的理论,采用“语言剩余”来呈现边缘性的原作,使译作不被视为原作,实现让翻译和译者显身的目的。
虽然韦努蒂在之后的论著中声称,自己“并非是要抛弃流畅的翻译,更多的是要拓展译者被允许使用的受到限制的词汇和句法”[24],但是他所推崇的异化之作,必然造成不通顺、不易懂的实际效果。在韦努蒂看来,译者显身是打破翻译窘境的有效方式。事实上是混淆了在译作的接受和评判层面的译者,与为翻译付出了劳动应获得相应酬劳或精神尊重层面的译者之间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后者是前者的归宿。刻意用不透明、不易懂的译文让翻译和译者显身,译作就会可能因文学性不佳而失去读者。不但不能实现其提高翻译和译者地位的初衷,甚至会给译者和译作带来被读者和目的语社会彻底抛弃的灭顶之灾。换句话说,翻译和译者地位的提高,不能指望由读者无法接受的译作来实现。
韦努蒂身处英美亚文化场,关注的主要是将相对弱势的非英美文化译入强势的英美文化的翻译现象,没能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场提升自我文化量的翻译动因,也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德国浪漫主义存异翻译旨在革新民族语言、构建强大文化场的初衷。施莱尔马赫、鲁迅、韦努蒂等三人所提出的翻译理论,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共同的存异思想,然而三人各自身处的文化场不同,翻译实践涉及文化场域的渊源也不同,语言的差异性也不同,导致三种存异翻译思想迥异的理论境遇。
2.4 品味他者的异质性
“五方之民,言语不同,嗜欲不同”,翻译则可“达其志,通其欲”。他者的异质性带来的新鲜体验,正是翻译的妙处所在。因此,如果完全将他者的异质性同化,也就从根本上消解了翻译的必要性。适当地保留他者文化的异质性,可以弥补目的语文化场在相关领域文化量的不足,促进文化场的自我建构。然而,翻译本身就是一个化“异”为“己”的过程,归化他者在所难免。译者对原作的确负有伦理的责任,然而译者有权在翻译过程中对原作进行调整,以便向译入语读者呈现符合译入语句法和表达规范的译作[4]117。目的语文化场所处发展阶段不同,与所译文化场的地域区隔,渊源疏离的不同,译者对他者异质性的归化程度也就会有所不同。
翻译中,他者与自我逐渐趋近,界限慢慢模糊,最终必然就会处于一种类似于文本意义踪迹若隐若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文性”状态。在洪堡看来,翻译的最高目标是,既要感受他者又不让人感到陌生性[1]154。过于激进,就会超出目的语的接受限度,语言也会变得难以界定。在德国,福斯(Voss)所译的《伊利亚特》与路德所译的《圣经》拥有同样的历史地位。即便如此,A.W.施莱格尔还是认为,福斯的翻译险些创造了一种新的俚语,而不再是讲一种正式语言[1]140。从中西方翻译史来看,多数时期,透明和通顺的准则,主导着翻译的批评和接受。翻译是要让无法阅读原作的读者,对译作产生如原作般的真实感、本土感,强烈到能够依靠译作“行走”或逾越艰难[25]。翻译之难就在于,既要让读者在翻译中品味出他者的异质性,又不能超出读者的接受限度。
3 结语
文化场的自我建构与完善,翻译功不可没。德国浪漫主义时期“把读者带往作者”的存异翻译,成功地革新了德语,继承了古希腊罗马文化,构建了强大的德意志亚文化场。与浪漫主义时期的德国不同,鲁迅所处的中华文化场,拥有五千年文明史,在诸多领域都积淀了厚重的文化量,不会也不可能在顷刻间抛却重来。忽略了语言演化的时间性和文化革新渐进性的“硬译”之作,自然也就难以为国人所接受。施莱尔马赫从事的翻译主要都在西方文化场内,基本上没有文化层面的陌生感,需要调处的主要是语言层面的异质性。鲁迅的翻译大多是在差异巨大的中西文化场之间进行的,语言与文化异质性都要理顺,才有可能满足读者的接受期待。
韦努蒂身处西方文化场中强盛的英美亚文化场,主张以语言剩余呈现边缘性原作,制造不流畅、不透明的阅读体验,让译者显身,以便提高翻译和译者的地位,却忽视了文化场自我建构和提升自我文化场的翻译动因,也偏离了德国浪漫主义存异翻译培育强大文化场的初衷。韦努蒂所推崇的异化之作,不但不能实现他提高翻译和译者地位的目标,反而可能会因译作的文学性欠佳,而给译者和译作带来被读者和目的语社会彻底抛弃的灭顶之灾。翻译,既不能消极地抹杀他者的异质性,也不能让其永远处于不被自我理解的陌生状态。译者必须以读者期待的接受方式呈现他者、消融异质性,方能实现取“他者”之长补“自我”之不足并最终实现化“异”为“己”的翻译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