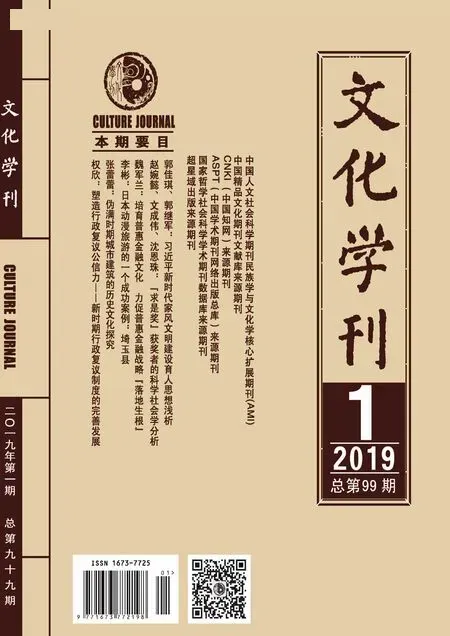认知隐喻学视野中“草”的惯用表现的汉日对比
段静宜
近年来,学者对隐喻的研究已经从单纯的修辞学角度发展到对于认知方式的探求,其研究对象也拓展到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中存在的万事万物。汉语中存在大量的植物词汇,这些词汇的应用也从植物范畴扩展到更多的范畴,形成了更广泛的隐喻表现。植物隐喻的产生是以人们对植物各种特征及功能的熟悉和体验为基础[1],反映了认知主体的“身体性”。植物中的草虽不如花朵艳丽,也不如树木挺拔。然而,草却无处不在,与“草”有关的语言表现也十分丰富。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语言文化的交流源远流长。孙毅[2]提到:“隐喻既根植于语言,又根植于文化,隐喻是一个语言社团文化和经验的积淀,是文化在语言中的集中体现”。明确了语言和文化之间难以分割的特点。本文主要以《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3]、『動植物のことば辞典』[4]、『動植物のことわざ辞典』[5]、『大辞泉』[6]中收录的与“草”有关的惯用表现、古典文学作品以及CCL语料库[7]、日本少纳言语料库[8]中收录的诗句、例句为语料进行对比分析,以探求中日两国在植物语言文化方面的异同。
一、“草”的意象形成及意义扩张
在汉字的不断发展中,“艸”作为偏旁部首,成为汉字构成的重要部件,并衍生出大量与“草”相关的汉字。由此也可以看出“草”在早期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日语中同样使用「草」字,假名表记有「くさ」和「そう」,其中「そう」保留了汉字传入日本时原本的发音特点。
草是对茎秆柔软的植物的统称,广义上也包括部分庄稼和蔬菜,如青草、野草、水草等。日语中,草被定义为「植物で、地上部が柔軟で、木質の部分が発達しないもの。」[10]从以上定义中可以看出,“柔软”是草的典型特征,是基于认知主体在对草的利用和认识过程中形成的经验基础。随后,草的意义也不断扩张,形成了“柔软”“不起眼”“娇嫩”“坚韧”“生机”等丰富的隐喻义。
二、汉日语言中“草”的隐喻表现
(一)以人为目标域的“草”隐喻
1.人自身即为“草”
20世纪80年代,电影《芳草心》的插曲《小草》凭借“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的歌词红遍我国大江南北,花花世界中毫不起眼的小草也引起了芸芸众生的共鸣。古时的人们早已将自己比作“小草”,以草的渺小来喻自己的渺小。“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孟郊以“寸草”自比,表达对母亲的感念,“寸草心”也被赋予了对父母的感恩之意。例如,“悠悠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何家庆执著的回报精神,体现着一种崇高与纯粹。”
日语中用「根無草」(无根之草)来表示漂泊不定的人,用「浮草稼業」表示没有稳定工作、四处辗转的人。例如,「浮草稼業はいい加減にやめて、郷里へ帰って身を固めろ」父にいわれたのは一九七六…(笔者译:“不要再去四处打工了,快回来安身立业”,被父亲这样说的时候是在1976(年)……)
Lakoff G & Johnson M[11]提到的“地位高为上,地位低为下”也体现在“人是草”的隐喻中。以自上而下的视角来看,小草贴近于地面,并不能轻易引起注意。在高高在上的古代统治阶层眼中,平民即是微不足道的“小草”,“草民”“草芥”成为平民阶层的隐喻。现在常用的“草根文化”“草根交流”中的“草根”一词源自英语的“grassroots”,用于表示政治上的弱势阶层和平民阶层,日语中也使用「草の根活動」一词表示政治范畴的民众运动。
2.人的品行是“草”
《楚辞》中出现了川穹、白芷、泽兰、蛇床、款冬等植物[12],如“扈江离与辟芷兮”“揽茹蕙以掩涕兮”,这些香草生长于广阔的田野,诗人将其置于室内或随身携带,香草淡而清幽的芬芳成为君子高尚人格的象征,形成了“香草”意象。香草之中的“兰”以其生长于幽谷、气味幽香而受到文人雅士的钟爱。韩愈诗云“兰之猗猗,扬扬其香”,李白也写过“为草当作兰”。“兰”喻义高洁淡泊,是中华民族精神内涵的象征。现代著名思想家胡适也以“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表明自己的心志。香草所在之地象征着纯粹的理想之地,香草也用来比喻人美好的品行。
此外,小草因其在自然界中旺盛的生命力也常被用于象征“坚韧”“拼搏”的性格,如“疾风知劲草”便是对坚毅品格的赞美。小草在春天蓬勃而出,春季同样带给人以温暖、明媚的感觉,以这样的身体经验为基础,白居易发出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感叹。草是茎干柔软的植物,当“柔软”的特性映射到精神域,有时也被赋予了负面的评价,对于意志不坚定、没有主见、随波逐流的人则可以用“墙头草”来形容,如“墙头草,两边倒”。

“杂草”在汉语中可以用于表示多余、不需要的、不合群的人或事物,日语中则以“杂草”顽强生长的特性为焦点,用「雑草」来表示有韧性。例如,「政治家になりたくてなったタイプ」も、自己愛は強い。でも、その自己愛には、もっと雑草のようなしぶとさがあるように思う。(笔者译:“因为想成为政治家而从政”的类型的人也十分自爱。但是,我认为这种自爱中更有一种杂草般的韧性)。
3.人的情感是“草”
草的“绵长”“细柔”可以映射到人的情感域,尤其是秋草更容易引发不舍、惜别、惆怅等情感。《诗经》中以“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来渲染暮秋的景色,折射出诗人内心的怅惘。唐代的边塞诗中也多有“大漠”“秋草”的描写,用来突出戍边将士孤苦悲凉的心境。
日语里,秋季生长在野外的七种代表性植物被称为「秋の七草」[13](秋之七草)。七草常用作表示秋天的季语,最早出现于日本古典著作《万叶集》中,「秋の野に咲きたる花を 指折りかき数ふれば七種の花」(笔者译:盛开在秋季田野中的花,细数当以这七种为美)、「萩の花尾花葛花瞿麦の花女郎花また藤袴朝貌の花」(笔者译:胡枝子,芒草,葛花,抚子花,女郎花,兰草和桔梗花)[14],七草被看作是日本文学中“物哀”的表现之一。“物哀”中的“哀”并不仅仅指悲哀、伤感,更多的是指对自然的感悟,是人和自然的交融合一,是一种超然的境界,这也是日本文学审美的核心所在。
(二)以自然为目标域的“草”隐喻
草生长于大自然,在季节变化中呈现出不同的姿态,是自然界的符号之一。草木的变化用于表示季节的更替和时间的流逝,“春草”是“希望”与“活力”;“秋草”是“萧瑟”与“衰落”;日语中的「若草」意为春天新生的幼草,是春这个季节的寄语。
草木茂盛的地方也就是人迹罕至的地方,汉语中的“草木深”是破败的隐喻。日语中的「草葉の陰」(草叶深处)用来表示墓地的所在;「草深い」(草深)则是农村、田野的代名词。
(三)“草”的词性扩张与转喻现象
草字词性的扩张与转换也与隐喻密切相关。有人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提出汉字本身就是一种隐喻的观点,草字的形成基于认知主体对草最为基础的认知:植物初长出地面、娇小而茂盛的样子。汉字能够直接引发对于其所表示的事物的具体的、动态的联想,这也为词性的扩张提供了重要的身体经验。草肆意生长的样子引发“凌乱”“不正式”等联想,草也作为副词、形容词来使用,如草草了事、草书、草稿、草案。
日语中也有相似的用法,除「起草」「草書」「草々」,「詠草」最初用来表示和歌、俳句的歌稿,后来发展成为一种专门的书写方式。此外,用草作为接头词来表示非正式的意思,如「草芝居」「草競馬」「草野球」表示地方举办的、非官方的、非专业的戏剧表演、赛马、棒球比赛等,汉语中也有“草台班子”的说法,这里的“草”可以看作是基于场地、设施的转喻用法。草也用作接尾词,「言い草」「語り草」表示谈话的素材,「お笑い草」表示笑料。接尾词中的“草”在这里引申出了“种子”的意思,用以表示来源,这也可以理解为是基于空间相邻性的转喻现象。
三、“草”隐喻中的文化要因
(一)“草”和古代信仰
植物是人类衣食住行的重要来源,一些植物被赋予了神圣的力量,形成了早期人类的植物崇拜。草在中国古代曾用于占卜,“蓍草占卜”是最古老的占卜方法,以蓍草的形状来判断吉凶,草也被看作人与神之间的特殊连接。
日本认为自然界中的一草一木皆有神灵居住,万物皆有灵。古代日本有“结草”的习俗,将草和草结在一起,诚心祈求两个人永不分离,也用于祈求旅途安全和好运。位于京都市北区的上贺茂神社,以「双葉葵」(双叶细辛)作为神社的纹饰,「葵」被看作是连接天神和人间的神草,是神的象征。
(二)“春之七草”和草之神
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是创造日本的男神和女神,在生下了风神、木神、山神之后,诞下了草之女神「カヤノヒメ」,「カヤ」的汉字写作「萱」,即是草的意思。草神诞生之后,世上便长出了各种草类。农历正月,春风拂过,小草初生被看作是草之女神对人间的恩惠,因此便有了正月采摘野菜的习俗[15]。
季节的更迭在日语中被称为「節句」,由冬至春更替的时间点被定为1月7日,称为「人日の節句」。“人日”的说法源于中国,传说女娲造人,前六日创造了各种牲畜,直至第七日才创造了人,因此,农历正月初七被叫做“人日”。这个习俗传入日本后与采摘野菜的习俗相结合,形成了“人日”要喝七草粥的风俗:取芹菜、荠菜、母子草、繁缕、佛之座、芜菁和萝卜七种春天常见的野草配粥食用,以祈求新的一年无病无灾、健康平安。
(三)“仙草”意象
秦始皇派术士徐福去海中仙山求取仙草的传说家喻户晓,古人认为吃了“仙草”便能健康长寿乃至长生不老。我国古典文学作品中不乏对“仙草”的描述,“尔去掇仙草,菖蒲花紫茸”(唐·李白《送杨山人归嵩山》)是李白赠与友人杨山人的诗,“仙草”表达了诗人对友人归居山野的向往。杜甫也在其《赠李白》中有“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之句,表达了和李白同游去求仙草的期待。“仙草”生长于深山幽谷,诗人对“仙草”的追求反映了对纯粹精神家园的追求。
及至明清时代,话本、小说盛行,广为人知的《白蛇传》中蛇仙白素贞盗取仙草、《红楼梦》中绛珠仙草的前世今生,“仙草”是神话传说和民间信仰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象征。“仙草”意象的形成与草旺盛的生命力有关,也是基于草的药用价值而形成,是长久以来人与植物共生共存的见证。
(四)“唐草”到“和草”
唐草纹是一种以蔓草形象为基础,采用忍冬、兰草、牡丹、荷花的茎叶形状作为纹样的传统图案。唐草纹起源于古埃及,因盛行于中国唐代而得名。受时代背景和审美观念的影响,各个朝代所使用的唐草纹不尽相同,但唐草纹的植物卷曲的茎叶形象,富有生命力,寓意吉祥,已经成为建筑、服饰和艺术领域的中国元素。唐草纹于奈良时代传入日本,日本人在此纹的基础上进行了艺术再创作,之后又基于日本人喜爱的泡桐、紫藤、松竹梅等植物形象形成了和风唐草纹样。唐草纹是中日文化交流、继承和发展的重要文化元素,其流传至今也因为草旺盛的生命力能够引发对于繁荣、长寿的联想,是吉祥的象征。
四、结语
隐喻是存在于认知主体思维深处的重要认知方式。与人类生活形影不离的草是人们感知世界、理解世界的途径之一。本文从认知隐喻学的角度,通过对“草”相关语言表现的解读,分析了“草”隐喻的认知机制和产生过程。以对于草的形状大小、气味特征、生长时间与地点等植物特性的经验为认知基础,研究了人们对于人体、品行、精神及季节等方面的联想。语言与文化是不可分离的关系,草的隐喻义的形成也受到植物信仰、神话传说、民俗习惯的影响,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汉日语言文化中“草”的惯用表现的对比反映出中日两国关于草的认知的异同,也体现了中日文化交流的悠久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