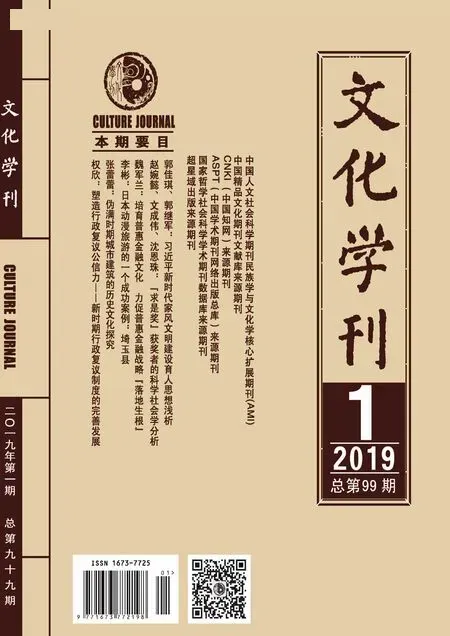《漳州方言语法》相关研究评述
陈 越
16世纪初,欧洲海上强国开辟了通往亚洲的航路,西方传教士、商人、使节等陆续东来,中西文化之间开始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接触与交流,也由此拉开了西人对汉语第一次大规模接触和认识的序幕。期间,传教士们将所接触的语言记录下来、写成的语言学著作,成为今天汉语研究的宝贵资料。
自1565年开始,西班牙人开始到漳州招募唐人协助开发菲律宾马尼拉。在历史记载中多明我会传教士最先对菲律宾马尼拉的海外华人群体进行传教。在多明我会开展的“华语活动”中,“华语”指的并非汉语普通话,而是专门指在我国台湾和福建传教区范围内的闽南方言。当时,西班牙人开始了与漳州方言使用者的语言接触,并对当时的漳州方言作了记录。西班牙传教士所著的《漳州方言语法》(Artedelenguachiochiu)这一语法著作,便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传教士对闽方言的记载是与该语言进行语言接触的产物。游汝杰[1]提到,外来人与方言使用者的语言接触主要通过口头交流的途径来实现(pp.164-166)。而传教士们所著的当地方言语法著作,则是将口头交流进行整理、记录而得。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对17世纪西班牙多明尼加(Dominican)传教士Melchior de Mancano所作《漳州方言语法》这一手稿语法文献进行分析。通过对比书中所记载的语法点与当前学界对闽方言语法的分析与研究,评述当时西方传教士在漳州方言语法时的优点与不足。在研究方法上,将共时性的田野调查和历时性的文献语料相结合,是本文对17世纪传教士闽方言研究进行分析所基于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
一、研究背景
(一)16—19世纪初西人汉语研究
自17世纪中叶开始,来华传教士开始编撰汉语语法书,并且出版了一系列汉语语法论著。比如,罗明坚、利玛窦于1583年到1588年之间合作编写的《葡汉字典》,被认为是“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的最早尝试”;利玛窦在1606年所著的《西字奇迹》,是“第一部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的注音读物”;金尼阁于1626年所著《西儒耳目资》一书,被评价为是“西人撰写的、最早的一部分析汉语语音的韵书”;卫匡国在1652年所作的《中国文法》,被称为是“耶稣会士最早撰写的汉语语法书”等[2]。这些论著大多是关于西方传教士对当时中国上层社会使用的语言,即“官话”的记录和研究。
20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对传教士汉语语法著作展开了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一是关于原始资料的目录汇编,二是对原始文献资料的译介,三是专题专书的研究概况,四是多学科视角的研究概况[3]。从中可以发现,原始资料、文献对还原当时方言语法研究概况、发现与当前研究的侧重差异,有重要的意义。
(二)传教士闽方言文献研究概况
在16到18世纪期间,至少有18本关于福建方言语法的研究著作问世[4]。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叶,在西班牙人统治菲律宾的初期,天主教派传教士编纂了记录当地语言的几种词典和语法书。这些以手稿或者说写本形式保存至今的资料,多数是以拉丁字母标记的,为了解约400年前闽南语的面貌提供了珍贵的研究资料。然而,这些珍贵的资料在现代学者对闽方言进行研究的初期没有受到重视。在对汉语语言多样性的分析方面,许多历史学家或者史料编纂者,甚至是语言学家们,往往都只会把中国语言和三个符号联系在一起——汉语官话即普通话、汉语文言文、汉字;然而,记载汉语方言语法文献的重要性也是不可忽视的。
二、《漳州方言语法》及其相关研究
(一)《漳州方言语法》概述
西班牙人在菲律宾的传教活动中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语言学资料。传教士们一边学习唐人语言,一边把所听到的语言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记录下来。根据洪惟仁[5]先生的观点,该时期所编写的语言学资料主要包括四个种类:词汇集(Bocabulario)、词典(Diccionario)、语法书(Grammatica)或虚词典(Arte)。这些资料在传教士之间流传,也成为他们学习汉语的资料或教科书。编纂词典和虚词典相互参照是传教学习语言的方法。根据韩可龙[6]先生的观点,该手稿的作者可推测为17世纪在菲律宾马尼拉的多明尼加传教士Melchior de Mancano神父。手稿上并没有明确标记成书年代,但在手稿中所记载的一个词条是“Bang lèg' s chàp' pê' n | ? ‘48th year of the Wànlì emperor.”由此可以推测,该手稿编于1620年,共33页,目前流传下来的仅有两本,其中一本藏于西班牙Bacelona大学,另一本藏于伦敦图书馆。在文题中,“chio chiu”最有可能指的是位于福建省的漳州地区,这样的推测可以从一本同样出自17世纪一位传教士之手的词典DICTIONARIO,其中有一个词条写到“chio chiu: probincia 漳州”。根据分析考证,在《漳州方言语法》这本书中所记载的方言词条,和包括厦门、漳州和泉州地区在内的闽南地区方言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漳州方言语法》一书的编纂所基于的田野调查的方言区系菲律宾地区的漳州方言,因此,手稿中所记载的方言普遍具有闽南方言漳州地区的词汇、音韵和语法特征。这与当时西班牙的殖民背景是息息相关的。当然,从共时研究的角度来看,漳州方言从明朝至今受到社会历史等方面的影响,与明朝时所表现出来的语言特征存在诸多不同。也不排除从传教士本人的角度、基于印欧语系基础之上的语言架构使得所记录的漳州方言带有一定印欧语系的印记以及在抄录和翻译时不可避免的一些笔误。韩可龙[7]先生在其著作中提及,对《漳州方言语法》一书的早期研究已有许多,例如Theophilus Siegfried Bayer对《漳州方言语法》的翻译,以及台湾元智大学对该书的扫描,此后便是韩可龙先生对此书的翻译和研究。可以发现,在语言学研究领域,基于传教士文献而开展的语言研究受到的关注在近几年来并不是很多。
(二)《漳州方言语法》研究评述
应该说明的问题是,《漳州方言语法》这份手稿究竟如韩可龙所说是一本语法书,还是如洪惟仁所说是一本“虚词典”。这两种看法均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均存在探讨的价值。
从词典编纂方面来看,或者从一本语法分析著作中对词汇部分的分析来看,其可取的地方是与同时期的其他闽南方言词典和汉语方言词典相比,词语的选择不再只局限于单音节词。这与多明我会的西班牙传教士们认为官话并非当时中国唯一语言是相吻合的。多音节词的记载是方言存在的标志之一。不足之处在于,词条的记载顺序是杂乱无章的。约1620年,虽然拉丁字母早已出现,但尚未实现国际化,且英文字母尚未对其进行借用,故无法期待当时一本西洋传教士所编写的词典能够像当今国际化汉语和英文词典一样按照26个英文字母的顺序从A到Z进行编排;并且,对比同时期其他闽方言词典诸如《词典》(DICTIONARIUM)等,也无法做到按照西文字母的编排顺序对词条进行编排。但正如一些早期传教士文献词典一样,词条的记载是毫无规律的;甚至可以推测,这是传教士们每天进行方言调查
工作时、在交流的过程中记载下来的一些语言片段和用法,因而没有任何规律可循。比如,手稿中开头记载的三个字分别是“尊”“船”“准”,它们的漳州话读音相近、音调调值不同,且均以辅音/ch/开头;然而,在五个字遵循这样的规律之后,作者又转向以辅音/k/开头的单音节词。词典编纂上单双音节的编排是任意的。
在词典总体编写上,传教士语言学家在对汉语方言进行记录时使用到基于传统欧洲语法分析基础之上的词型范例和方法论,如被欧洲语言学语法学家们所广泛使用的“Greco-Latin”模式[注]Greco-Latin模式:即古希腊-拉丁式语法。。十分肯定的是,Greco-Latin模式的语法范例如词型变化等方面明显不适合分析与印欧语系在形态上存在差别的语言。也以为理论框架明显的不适合性,被记录下来的语言和它实际的读音意义等方面仍然存在差别。比如:在《漳州方言语法》中,“是”的闽南语读音被标记为/sy/,正确的标记应该是/si/。也就是说,《漳州方言语法》这份手稿中的语法内容,很可能只是与语言学事实相分离的理论构想。如图1所示,《漳州方言语法》一书对由“人”这个词引申而来的对语法成分的分析。从这里也可以看出Arte列举词条的任意性,在此处则表现为在列举词条的同时用词语扩展进行语法分析。图1中“人”是主格用法,“人个”是所有格用法,以下除了“僚氏”无法得知其与这组带有“人”字的词语的关系之外,“惜人”等词语似乎都是词语的宾格用法。根据韩可龙[8]的观点,《漳州方言语法》的作者还提到了“呼格”(vocative)、“与格”(dative)和“离格”(ablative)这样的形式区别。从这一点出发可以分析,首先,在汉语语法学的分析中,少有提到“与格”“离格”“呼格”这样的用法,或者说汉语对词语属性的划分并没有如此细化,如在“宾格”和“与格”之间进行区分。其次,对“主格”“宾格”“所有格”这样句子成分的分析,从16—17世纪或者当前的汉语语法研究的著作来看,这样的分析落脚点显然不是汉语语法对词语属性和句子成分分析的重点。由此可见,该手稿作者的语法分析是基于印欧语系的语法分析框架来进行的。

图1 《漳州方言语法》中“人”的语法结构
同时,书中还出现了词条重复出现的情况,如图2中“写字”和“念经”两个词语,虽然从西班牙语释义的角度上看会略有差别,但是从漳州方言音和义结合的角度来看,二者的词义是相同的。

图2 《漳州方言语法》中词条重复一例
关于声调,闽南语的音调在《漳州方言语法》中没有被作为重点进行解释。现在学界认同的闽南语语法是存在“七声调”,然而在手稿中只能看到五个声调的描述。
在词条的背景方面,有些词条的收录或许带有西方文化的背景,而不符合当时中国文化的背景。比如,“查暮日”是否可以翻译成“妇女节”?在古代中国,由于男尊女卑,所以当时并不像现在一样有专门属于女子的节日。
《漳州方言语法》还存在解释不够清楚的情况。解释一个语法现象时所举的例子不够充分,且没有提出一些反例来帮助理解。
要充分理解这部词典,需要考虑到这种材料直接反映了当时教师和学生的学习现状。这部词典的编订想必不是经过充裕时间的整理而创立的,因此有许多原封不动的错误出现了,给词语的注音也未必标出忠实于汉字的读音。比如,给“萤火虫”的“萤”字标上“hue quim chee”的读音,表示“火金星”的意思,这个被考证为是西班牙语”luciernega”的音译。《漳州方言语法》的作者在手稿中提到发掘出八个漳州方言的声调,这与现代漳州方言中七个声调[注]正常发音;嘴巴比平时张得更开、影响上颚而产生的发音,如“家”“枷”“假”;送气;鼻化不送气;鼻化送气;更加鼻化;更加鼻化且送气。的事实不符。
此外,该书还存在没有区分单音节词与合成词(在手稿中的多字词是短语而非复合词);没有使用福建方言独特的记录方式,等等。
三、总结与讨论
事实上,在早期的传教士汉语研究当中,曾一度出现了“单一语言制”的问题。“单一语言制”,是指当时有许多学者认为所谓的“汉语”指的就是一种语言,方言在中国境内的存在被大大忽视了。虽然产生这样的结果与没有足够的数据库,语言学先行者的井底之蛙思想,以及当时的背景环境对“语法”这一语言学范畴的局限性认知等原因相关,但无论如何导致的结果就是方言在传教士语言学研究中出现得越来越晚了。值得一提的是,天主教在早期就有对中国的当地话即方言的研究。
正如作者在《漳州方言语法》这本手稿的前言中写道:“普通话是整个中国通行的语言,在漳州这个地方也是如此……但是漳州话(chio chiu)却是漳州这个地方最普遍的语言。”可见作者充分认识到了中国境内语言的多样性,并非仅仅只关注官方使用的“普通话”。根据不同的参考文献,在16—18世纪至少有18本记录福建方言的语言学文献产生,但许多资料都已经亡佚或者失传。对于记载闽南方言的手稿,被广为提及的文本主要有《漳州方言语法》、《汉语西班牙语词典》(DictionariumSinoHispanicum)及《闽南话词典语法》(Bocabulariodelenguasangleya)等。总而言之,虽然传教士的方言研究的资源在数量上并没有优势,但是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早期中国的语言学研究并不像大多数人所认为的是以普通话为导向的,方言应该被置于更加重要的研究地位。
可以说,包括《漳州方言语法》在内的传教士语言学研究文献在语言学研究中是十分重要且珍贵的。为了寻找这些资料特别是尚未编辑的手稿资料,研究者们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即使为出发寻找这样的资料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也不能确保一定能找到某个特定的手稿;并且,这样长时间且大量经费的投入却也未必能够保证研究必然产生成果。
四、结语
传教士语言学研究对汉语研究有重大的意义与作用。本文通过对西班牙传教士所作《漳州方言语法》进行分析,肯定传教士语言学文献的积极作用,并且通过对比当今对汉语方言中漳州方言的研究,分析西人对漳州方言研究中的优势与不足。不足之处产生的原因主要是西人与我国在语言习得方面基于不同的语系,不过也应当考虑手稿的阅读对象等其他因素。当然,这些优点与不足对国际社会上的汉语语法研究都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总之,早期西洋传教士的方言学著作具有诸多重要意义,其中一方面意义在于其提供的自然口语的精确度;另一方面,对西人研究汉语并且撰写的汉语及汉语语法方言的著作进行研究和分析,这不仅能够进一步丰富对外汉语理论研究,还能直接推进对外汉语本体的研究,更能够促进海外汉学史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