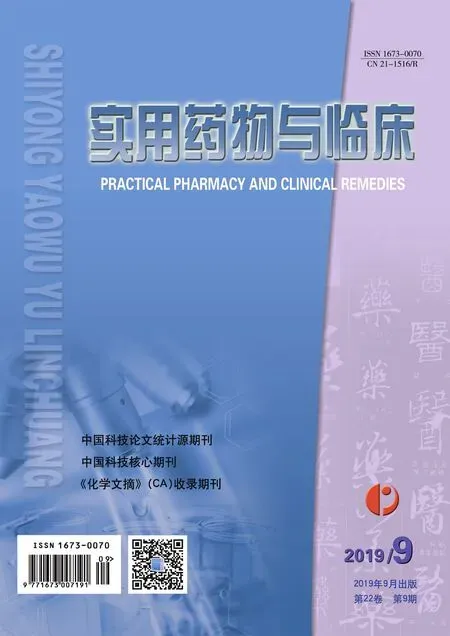PD-1/PD-L1抑制剂治疗肺癌的疗效预测因素
吴笑驰,倪 磊
0 引言
肺癌是世界上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每年确诊160万例新病例,也是全世界癌症死亡的主要原因,每年造成140万例死亡[1]。尽管在肺癌的治疗方面已有一系列方法,包括手术治疗、放化疗和分子靶向治疗等,但晚期肺癌的5年生存率不足5%。研究表明,肿瘤的生成不仅依赖于癌细胞的特性,还与免疫系统的相互作用有关[2]。T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受到刺激信号和抑制信号的调节。在肿瘤细胞中,调节因子蛋白的功能紊乱会导致肿瘤的免疫耐受,最终导致肿瘤的免疫逃逸。
免疫疗法是治疗肺癌的一种很有前途的方法。目前,针对程序性死亡分子1(Programmed death-1,PD-1)及其配体PD-L1的相关药物已被批准用于肺癌的治疗,抗PD-1单抗的代表性药物有Nivolumab和Pembrolizumab(MK-3475)。2015年10月,美国FDA批准了Nivolumab作为二线药物用于治疗转移性鳞状细胞癌或者非鳞状细胞非小细胞肺癌(NSCLC),Pembrolizumab作为二线药物用于治疗肿瘤细胞高表达PD-L1的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2016年10月又批准Pembrolizumab用于无EGFR、ALK突变且PD-L1表达超过50%的NSCLC治疗。抗PD-L1单抗的药物有MPDL3280A和MEDI-4736,现已进入Ⅲ期临床研究阶段。但目前治疗的客观缓解率(Overall response rate,ORR)较低(在非选定的肺癌患者中平均不到20%),而且这些抗体的成本很高。因此,探索抗PD-1/PD-L1治疗的有效性预测因素对于更有效地确定最有可能受益的患者,而不排除可能受益的患者显得尤为重要。
1 PD-L1的组织表达
PD-1又称为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1),主要在T细胞、原始B细胞、单核细胞和NK细胞中表达,在正常人体中,其与配体结合后可以促进活化的淋巴细胞凋亡,从而中止免疫活化作用,避免了免疫系统的过度活化而产生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在免疫调节中发挥重要作用。PD-L1或程序性死亡配体-1,主要表达在淋巴细胞的抗原提呈细胞中,也常在各种恶性肿瘤中表达,可以通过抑制T细胞相关激酶来阻止细胞毒性T细胞对肿瘤的反应[3-5]。PD-L1可以在肿瘤细胞中表达,也可以作为一种获得性、适应性免疫抵抗机制表达。在NSCLC中,有27%的患者表达了PD-L1,其表达主要位于细胞膜或细胞质中[6-8]。抗PD-L1或抗PD-1免疫治疗使固有免疫系统对肿瘤生长发挥作用。一项包括了155例NSCLC患者的MEDI-4736临床研究中[9],其中58例可评估的NSCLC患者,客观缓解率(ORR)为16%,PD-L1阳性与PD-L1阴性的肿瘤相比ORR更高(25%vs.3%),疾病控制率(Disease control rate,DCR)总体35%,PD-L1阳性患者与PD-L1阴性患者相比DCR更高(45%vs.24%)。在一项包括194例晚期NSCLC患者的Pembrolizumab研究[10]表明,在未筛选PD-L1状态的患者中,ORR为20%,而在PD-L1阳性患者中ORR为23%,PD-L1阴性患者中ORR为9%。PD-L1表达似乎可以预测治疗反应,但是许多PD-L1阳性的肿瘤患者对治疗没有反应,而一些PD-L1阴性的肿瘤患者对治疗显示出临床反应[11-12]。因此,PD-L1表达与临床反应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是治疗反应的辅助预测因子,但作为单一的生物预测标志物来选择治疗方法仍有较大的局限性。
免疫系统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系统,受多种机制的调节,PD-1/PD-L1阻断治疗的临床反应并不完全依赖于PD-L1表达,其他影响因素包括:其他的免疫调节机制,包括PD-L2、LAG1等;其他免疫调节细胞的存在和作用;细胞因子的环境。另外,由于PD-L1表达的异质性并且可以由于时间及既往的治疗而发生动态性变化,多种细胞因子、靶向治疗等均可诱导PD-L1表达,因此,对PD-L1的组织表达进行抗PD-1/PD-L1治疗前大样本的评估比较困难。进一步的研究必须明确最佳的IHC分析方法,验证和规范PD-L1阳性的定义,并探讨PD-L1蛋白不同表达水平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水平对肺癌患者预后的影响。
2 肿瘤突变负荷(Tumor mutation burden,TMB)和新抗原瘤内异质性(Intratumoral heterogeneity,ITH)
已经证实大量突变的肿瘤更有可能对抗PD-1药物。一些肿瘤突变被转译为新抗原,从而使肿瘤细胞被免疫细胞识别[13]。在肿瘤如NSCLC的治疗中,对T细胞检查点封锁的一种解释是促进T细胞对新抗原的反应,新抗原是T细胞的抗原决定簇,是肿瘤特异性突变的结果[14]。在NSCLC中,暴露于烟草会增加肿瘤的突变负荷,除此之外,DNA修复机制的缺陷也可能是基因突变的原因。随着突变数量的增加,高突变负荷和对检查点封锁的反应将会增加新抗原的数量。在Rizivi等[15]的关于NSCLC的抗PD-1治疗的报告中,确定了T细胞对许多预测的新抗原的反应,新抗原反应的CD8+T细胞的水平与肿瘤的突变负荷有关。在16个发现队列患者和18个验证队列患者中,由全外显组测序确定的NSCLC突变景观和对pembrolizumab的反应的研究显示,在发现队列中,有高非同义突变负荷的患者(高于中值)的ORR组高于低突变负荷(低于中值)者(63%vs.0,P=0.003)。在高非同义突变负荷的患者中,疾病控制率(DCR)的比例高于低突变负荷的患者(73%vs.13%,P=0.004),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的时间也更长(平均14.5个月 vs.3.7个月,P=0.01)。验证队列中在高非同义突变负荷的患者中,DCR更高(83%vs.22%,P=0.04),PFS的时间明显更长(未达中值 vs.3.4个月,P=0.006)。较高的非同义突变负荷与Pembrolizumab的临床疗效及预后改善显著相关,非同义突变负荷和DCR之间有很高的一致性。临床中仍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具有较高的突变负荷而无法获得理想的免疫疗效。低的肿瘤新抗原ITH也可能是影响免疫治疗反应的重要因素。McGranahan等[16]发现,PD-L1在具有较高的新抗原负荷和较低的新抗原异质性的肿瘤中表达较多,在7个原发性NSCLC肿瘤中,新抗原异质性的差异很大,平均只有44%的新抗原在肿瘤区域的亚群中发现。此外,癌症基因组图谱(TCGA)NSCLC腺癌数据显示,高突变负荷且低ITH(<1%)联合与单一的突变负荷相比,与长生存时间更具有相关性,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关联在NSCLC鳞状细胞群没有被观察到。在具有高突变负荷且低ITH(<1%)的肿瘤患者中,患者的临床效果比单一高突变负荷的患者更持久(P=006),且无进展生存率(P=0.001 7)和整体生存率(P=0.008)更高。与单一的突变负荷相比,这些特征似乎与持久的临床受益更具有相关性。
分析表明,与突变相关的新抗原识别是内源性抗肿瘤免疫反应的重要组成部分,免疫相关的新抗原可以通过计算方法识别,肿瘤突变负荷联合新抗原瘤内异质性能更好地预测PD-1/PD-L1的阻断效果。
3 肺癌组织亚型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国际肺癌研究协会(IASLC)分类标准,肺癌可分为2种主要的亚型:小细胞肺癌(Small cell lung cancee,SCLC)和非小细胞肺癌(NSCLC)。NSCLC被进一步划分为几个子组,最常见的是鳞状细胞癌、腺癌、大细胞癌和肉瘤样肿瘤。目前不同的免疫阻断药物在肺癌的不同组织亚型中研究结果尚不统一。在一项有关Nivolumab(抗PD-1药物)的多中心Ⅰ期临床研究[17]中,收集了129例晚期NSCLC患者,结果表明,在NSCLC的不同组织亚型中(鳞状细胞癌17%,非鳞状细胞癌18%)和EGRF突变型、KRAS突变型或野生型中,ORR(客观缓解率)相似。抗PD-1或抗PD-L1药物在鳞状细胞癌中活性更高,可能与鳞状细胞癌中肿瘤浸润T细胞更丰富有关,但在临床试验中没有显示这种相关性[18]。PD-1/PD-L1表达与EGFR表达之间的相关性是有争议的,可能由于EGFR与样本年龄有关[19]。在一项对125例NSCLC患者的回顾性分析研究[20]中发现,PD-1阳性和KRAS突变存在显著相关性(P=0.006),没有发现和EGFR突变或ALK转位存在相关性;PD-L1阳性和EGFR突变存在显著相关性(P=0.002),与腺癌之间存在显著联系(P=0.005)。另一种具有显著表达PD-L1的组织学亚型是肉瘤样NSCLC,在69%的病例中表达PD-L1,而非肉瘤样的NSCLC为27%[21]。分析表明,Nivolumab在野生型EGFR/KRAS突变患者中,在PFS和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方面表现出更大的受益[22]。在KEYNOTE-010亚组分析中显示,Pembrolizumab在野生型EGFR患者中,在OS方面显示更大的受益[23]。
现在对SCLC的研究较少,一些研究也显示出了可行性。PD-1和PD-L1分子是在SCLC细胞系中共同表达的,研究者认为,PD-1及其配体在细胞毒性T细胞上的生长抑制可能会参与肿瘤细胞的生长抑制,但仍需进一步的证实[24]。一项针对广泛期SCLCⅠb期的临床试验(KEYNOTE-028)中报告了Pembrolizumab对表达PD-L1阳性SCLC的ORR为31%,安全性和其他肿瘤类型的安全性一致[25]。在一项针对SCLC的多中心开放性Ⅰ期及Ⅱ期临床试验中,Nivolumab单一疗法和Nivolumab联合Ipilimumab治疗,对既往接受过治疗的SCLC患者,显示出抗肿瘤活性,并具有持久的反应和较好的安全性[26]。目前很多相关研究仍在进行中。
4 吸烟的分子标记
烟草烟雾中的致癌物质是导致NSCLC中突变的重要原因[27]。与吸烟相关的肺癌比从不吸烟患者的肺癌有更大的突变负荷[28]。烟草烟雾致癌物质与DNA相互作用,导致产生癌症发展的基因变化,以及许多可产生免疫原性的新抗原[29-30]。一些对PD-1和PD-L1药物的研究表明,有吸烟史的肺癌患者反应率较高。在236例Pembrolizumab治疗肺癌患者的研究[31]中,结果显示ORR为21%,然而,大多数患者都有吸烟史,在有吸烟史或现在吸烟者中ORR是27%,而从不吸烟者的ORR是9%。另外,在1个MPDL3280A治疗晚期NSCLC患者的1期临床试验[32-33]中,ORR是23%,其中,有吸烟史或现在吸烟的患者中ORR是26%,而从不吸烟患者中ORR是10%。在对Nivolumab的Ⅰ期研究[34-35]中,结果表明,在有吸烟史或现有的吸烟者中ORR(20/75,27%)高于轻度/从不吸烟者(0/13,0%)(P=0.034),与无反应的患者相比,有应答反应患者的烟草暴露量显著增加(P=0.036)。根据碱基C到A的转换频率,一个已被证实的分子标志可用来区分是否吸烟[36],吸烟患者标记为TH(Transversion-high)、不吸烟患者标记为TL(Transversion-low)。Rizivi等[15]研究发现,在TH患者中ORR为56%,而在TL患者中ORR为17%(P=0.03);持续临床获益(Durable clinical benefit,DCB)的比率分别为77%和22%(P=0.004);在TH患者中,PFS的时间更长(P=0.000 1),自我报告的吸烟史并没有显著区别,DCB和PFS在吸烟者和从不吸烟者之间(P=0.66和P=0.29)或重度吸烟者与轻度/从不吸烟者(P=0.08和P=0.15)之间无明显差异。与吸烟史相比,吸烟分子标志与DCB、PFS有更显著的相关性。而且,突变的吸烟分子标志可能具有更广泛的应用,不仅对肺癌,对其他吸烟相关性的肿瘤,作为PD-1/PD-L1阻断的预测生物标志具有临床价值。
5 肿瘤浸润性T淋巴细胞(Tumor infiltrating T-lymphocytes,TIL-T)
T细胞活化并浸润是肿瘤免疫中的重要环节,部分对PD-1阻断治疗无反应的患者中缺乏T细胞浸润[37]。新抗原特异性T细胞可以调节与PD-1阻断相对应的临床反应。与来自于外周血的CD8+T细胞或健康志愿者的CD8+T细胞相比,从NSCLC中分离出来的CD8+TILs表达的PD-1增加。此外,PD-L1抗体阻断PD-1/PD-L1途径,增加细胞因子的产生,提高了CD8+TILs的增殖能力,并在体外产生干扰素[38]。T细胞的反应只有在开始治疗后才会被检测出来,最初会迅速增加,然后达到稳定。新抗原特异性T细胞反应是在使用PD-1阻断治疗患者的外周血淋巴细胞中发现的,外周血的新抗原特异性T细胞检测有希望作为比较简易、快速的手段对PD-1阻断治疗的反应进行监测。
6 结语
免疫疗法,尤其是免疫检查点抑制,已经改变了肿瘤治疗的范式,PD-1/PD-L1阻断剂已经作为临床治疗肺癌的一线药物。为了在肺癌患者中应用更精确和更有效的免疫疗法,从而使更多的肺癌患者获益,迫切需要在临床应用中确定更好的预测生物标志,而动态变化的免疫系统对PD-1/PD-L1阻断治疗的预测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联合应用多种预测标志物或多种手段综合评估可能是一个有效途径。本文综述了目前对肺癌PD-1/PD-L1阻断治疗的可能影响因素,并评估它们是否具有潜在的诊断、治疗或预后价值。此外,肿瘤免疫原性、协同刺激/抑制、肿瘤微环境的免疫细胞、系统免疫等,都可能影响PD-1/PD-L1阻断的疗效,进一步研发精确预测阻断疗效的生物学标志,对于提高免疫阻断治疗应答率、建立合理有效的联合治疗方案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