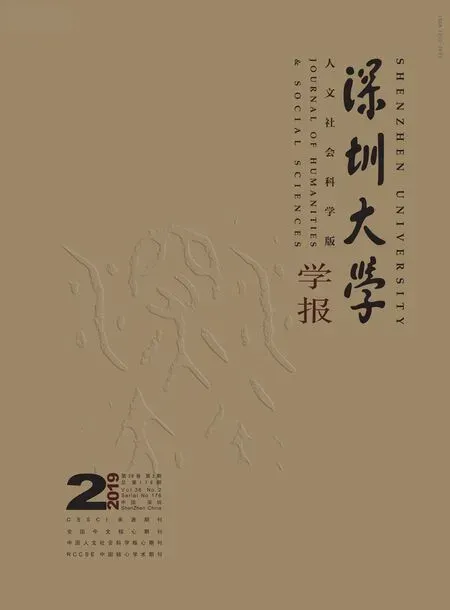“春秋大义”的形上过程及其学理化
张甲子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春秋》万余言中,并无一个“义”字,后世所谓的“春秋大义”“微言大义”实际是在对《春秋》的解释中形成的①。左氏学、公羊学、谷梁学的确立及发展,使得经学家舍经求传,将《春秋》之“义”演变为“三传”之“义”。有侧重政治哲学之思辨,据“仁义”之“义”演为“大义”,引申出道义之论者,如董仲舒、胡安国、廖平②;也有侧重历史表述之考察,以“经义”之“义”演为“微言”,归纳出义例之说者,如杜预、孔颖达、刘师培③。《春秋》及“三传”成书虽前后有别,但都在《春秋》之“义”的基础上,对“义”不断进行阐释。我们可以从孔子作《春秋》之“义”的历史动因入手,进而考察“三传”之“义”的演变脉络,观察“义”如何通过形而上的演进,完成了学理化的建构。
一、孔子依“礼义”制《春秋》
孔子作《春秋》,绳尺二百多年间之史事,评骘公卿大夫数百人,其评判的基本原则,后世学者言之为“义”。如司马迁论“《春秋》以道义”,又言《尚书》“以道事”,指出二者的差别在于《春秋》中蕴含有“义”。杜预亦将《春秋》与其他史书相较,“以明国史皆承告据实而书时事,仲尼修《春秋》,以义而制异文也。”[1](P1721)认为孔子以“义”断史事,目的不在评判史实,而是建构新史观。以此为标志,后世学者皆强调“诸史无义而《春秋》有义也”[2]。然因孔子对“义”未加明言,后世揣测甚多,“《春秋》,义海也。以义达之,而各有至焉。”[3]各有解说,分歧恰在对“义”的理解之中。
《春秋》常事不书,但在事关“义”的大节上,有美必著,有恶必显。孔子彰显合“义”之事,如《春秋·定公五年》:“夏,归粟于蔡。”此处未记归之者,究竟是哪国帮助蔡国渡过了难关?一是“专辞也”,为鲁国;二是“义迩也”[4](P324),倡导诸侯国要行道义。春秋盟国间订有盟约,“救灾患,恤祸乱”[1](P898),战时出兵援助,共同抗敌;战后会合财货,相补兵灾;平时存恤救灾、抑强辅弱。这些要履行的责任与义务,可视为盟国公约。在盟国之外有灾,“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救灾恤邻,道也。行道有福。”[1](P368)自愿周济它国,行的也是通行于世的道义,在孔子看来,合乎“义”便不必详述。
《春秋》所记更多的是不合“义”之事,显然是孔子以此表明立场。《春秋·僖公十九年》:“冬,梁亡。”《春秋》书灭国的通例是“某国灭某”,如《庄公十三年》“齐人灭遂”,《僖公十二年》“楚人灭黄”,此处仅记“梁亡”二字。梁国实由秦所灭,《左传·僖公十九年》记有“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处,民罢而弗堪”;《昭公二十三年》又记有“伯沟其公宫而民溃。民弃其上,不亡何待”;《谷梁传·僖公十九年》则言:“梁国,自亡也。”《春秋》如此记载,突出了梁国灭国的根本原因,是梁君倒行逆施,不尚义而自取其咎。
《春秋·庄公三年》又载:“冬,公次于滑。”纪国灭亡在即,鲁庄公前往滑地,想与郑伯商议联合救纪之事,郑伯未应。鲁国军队驻扎于近郊,畏惧齐国兵力,只是做出了救纪的姿态,实质上并未行动。胡安国《春秋胡氏传》释为:“鲁纪有婚姻之好,当恤其志;于齐有父之仇目,不共戴天。苟能救纪抑齐,一举而两善并矣。见义不为而有畏也,《春秋》之所恶。”吕本中《吕氏春秋集解》也认为:“见义不为而有畏也,《春秋》之所恶,故书公次于滑以讥之也。”《春秋》记载此事,在于讥刺鲁庄公与郑伯见义不为,不出义兵。
孔子据《鲁春秋》作《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6](P509),其“义”绝不是简单就几则史事而发。孔子自言《春秋》之“义”为“窃取之”,虽为谦词,亦表明“义”并非其首创,乃承袭自旧有的史官系统。“义”是早期史官政治判断力与历史感知力的体现,常见于其他史书中[7]。董狐在《晋乘》中直书“赵盾弑其君”,杀晋灵公者为赵穿,赵盾身为相国未加阻止,难辞其咎。董狐并未详尽记录经过,而是突出了此事的警诫意义,贬斥赵盾之意显而易见。还有他国《春秋》,申叔时曾对楚庄王言,“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8](P485),此《春秋》应为楚《梼杌》,与“世”“令”“语”“故志”“训典”并列,用之以教国子要有扬善抑恶之心;晋悼王也曾“召叔向使傅大子彪”,因他“习于《春秋》”,可以“日在君侧,以其善行,以其恶戒”[8](P415)。当时列国皆有史官,不仅记本国之事,亦记他国之事,对同一事件的记载与评判却未必相同,这些“义”显然缺乏系统性。
孔子在吸收史官之“义”的同时,又将其改造升华为带有客观评骘意味的“义”。史官之“义”基于史官的职事传统,史官既掌司藏书,多识前言往行;又写作册命,记录时政,故其“义”多为具体的褒贬之“义”。孔子在《春秋》中寓予的史学之“义”,综合原史及商周的文化传统,不仅将褒贬之“义”发展为垂鉴史观,用以警诫后世,更能在“义”中赋予历史理想,以“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6](P3297),使天下知之,使后世尚之。孔子裁断《鲁春秋》纪年时限,笔削《鲁春秋》记事详略,乃“因义而见其所载之当否。其义有关于天下之故者,则书而存之。……其义无关于天下之故者,则削而去之”[9]。欲以一国之春秋,包举百国之春秋,欲举鲁国史为天下史。
孔子曾感叹:“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何时“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不得而知[6](P509)。但诸侯国记事须上报周王室,孔子观列国之史,欲作《春秋》超越旧史,以史为鉴,对天下进行监督与约束,是其认为后人“知我者”之所在。孔子又以匹夫之身,担当史官职守,褒贬议论列国诸侯,“窃礼乐、赏罚之权以自任”[11],行社会裁决与社会审判,有私人僭越周天子行事之嫌,是其认为后人“罪我者”之所在。
在孔子的新史观中,史书的最终目的不是记述史实,而是指陈史义。梁启超就认为:“旧史官纪事实而无目的,孔子作《春秋》,时或为目的而牺牲事实。”[12]如《春秋·定公八年》:“盗窃宝玉、大弓。”阳虎私自拿走了鲁定公宫中的宝玉、大弓等礼器,在孔子看来,这如同强盗之举,但阳虎并非强盗,孔子书其为“窃”,是直接对阳虎的行为进行批评。有论曰:“《春秋》之作,非以存王迹,以著王迹之所以熄。”[13]“存王迹”只有历史记录的功能,“著王迹”则是对基于史实形成的家国理想、政治认知、社会秩序的表达,前者强调的是借鉴过去的历史经验,即史官之“义”,后者强调的是凝聚当下及未来的历史共识,即史学之“义”。当孔子《春秋》作成,便具有旧史未有的哲学高度,其成为了历史评判是非的标准,而这种是非评判的标准,也是古代中国历史共识的立足点。
孔子作《春秋》还有一契机,即“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孙奭疏:“孟子言自周之王者风化之迹熄灭而《诗》亡,歌咏于是乎衰亡;歌咏既以衰亡,然后《春秋》褒贬之书于是乎作。”[10](P226)这个时间点并非孔子始作《春秋》之时,而是《春秋》的纪年之始。《鲁春秋》应“起自伯禽之封,以洎于中世”[14],孔子断在鲁隐公元年,正处平王末期,周道渐绝,周王室号令无所束,赏罚无所加,天下被列国诸侯裂之。此时《诗》亡的不是文本,不是乐制,而是《诗》的礼义精神。“礼”是形式,“义”是精神,是从礼中体现出的社会秩序、社会责任和社会义务,可用之于评价所有人的行为[15]。司马迁言“《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孔子继《诗》亡而笔削《春秋》,就是要继承诗乐之“礼义”,将史官褒贬之“义”用“礼义”来重新评断。
北京市门站的上空,1985年10月21日下午3时,点燃了耀眼的天然气火把,北京输气工程试输气一次成功。这条长达70千米的巨蟒,跨越河渠、铁路、公路,带着石油工人对首都人民的深情厚意,把华北油田的天然气引进了北京,日输气40万立方米。它像一条彩练,把石油工人的心与伟大的首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礼义”由乐官通过乐教,教化使天下人知,礼是行为的共识,乐是情感的共通。但乐官需要歌舞表演,局限性很强,当外界条件不能满足时,走向衰亡难以避免;而史官即使失官,若能把可知的史事记述下来,史学的传承系统便不会崩塌。《鲁春秋》本以《周礼》为旨归,《左传·昭公二年》记韩宣子见《鲁春秋》:“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杜预注:“《鲁春秋》,史记之策书。《春秋》尊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礼尽在鲁矣。”苏轼认为“孔子因鲁史为《春秋》,一断以礼。”[16]指出了《春秋》以礼义评骘人事。毛奇龄《春秋属辞比事记》也认为:“鲁史记事全以周礼为表志,而策书相传谓之礼经。凡其事其文一准乎礼,从此比之属之,虽前后所书偶有同异,而义无不同。……以礼为志,而其事其文以次比属,而其义即行乎礼与事与文之中。”明确“礼义”是《春秋》记事属文的准绳,也是孔子衡量《春秋》所载人事得失成败的标准。
在礼义难明的春秋时代,“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10](P178)。在此之前,诸侯君臣行事不合“义”,史官可以口诛笔伐,但这种外力对那些不介意的乱臣贼子无济于事,后世僭越之事依然史不绝书。孔子强调的“义”,是以“礼义”精神确立社会制度,整合社会关系,并通过观察历史进程、评价历史人物,借对错、是非、兴衰成败进行“义”的审判,以之规划出新的历史秩序,使得“义”成为历史行为评价的尺度。
二、左氏学以“德义”建构史评准则
孔子以《春秋》授徒,并不以《春秋》为纲传讲史实,而以古今之事为引,着重对《春秋》之“义”的解读。后有七十子口传,至左丘明时,“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6](P509-510)可见《左传》重史事叙述,其评骘史事之依据,亦本《春秋》之义。张大亨《春秋通训后叙》引苏轼言:“依经以比事,即事以显义。”目的在于通过更加详实的事件叙述,彰显孔子所蕴含之义。姜炳璋《读左补义》称:“作之者即事而为经,述之者论本事而为传,事举而义存焉。”确定《左传》以史事明《春秋》之义,正是遵从了孔子“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的用心[6](P3297)。皮锡瑞《经学通论》总结为“借事明义”,“《左传》并不传义,特以记事详赡有可以证《春秋》之义者”,是以事明义,如《春秋》借宋襄公之事,以明仁义行师之义;借齐襄王之事,以明复仇之义,借祭仲之事,以明知权之义。《左传》剪裁运化更多的史料,以史事发展的走向、记述的详略异同,继续彰显孔子所辨的是非、所著的得失、所寄的褒贬。
与《春秋》全书无“义”字不同,《左传》中“义”字出现的很频繁,多用于评断历史事件之走向,或评点人物之品行。《春秋》的“礼义”,可以理解为制度共识,而《左传》在记史事时将其具体化,作为制度共识的“礼义”进一步抽象为社会共识的“德义”,以之评价人与事的得失。鲁桓公将受贿的器物放于太庙,庄公去齐国观看祭祀社神,文公六年闰月不告朔,十五年日食击鼓,又在土地庙里用牺牲祭祀,或不合礼仪、礼制,或超出礼度[17],也就是违背了制度共识。《左传·桓公二年》载师服“义以出礼”之言,认为“义”是制定“礼”的理论根据,更强调礼的精神是约束人的行为时的基础法则;《僖公二十八年》又言“礼以行义”,认为遵“礼”实际是“义”的体现,在“义以处之,礼以行之”的互动关系中[1](P903),作为道德共识的“义”与作为制度共识的“礼”合而并用,“义”开始独立于“礼”,被作为衡量行为的另一个准则。
《左传》明确出现“德义”之论,正是将制度共识抽象后,对蕴含在法则之内的道德共识进行总结,形成新的社会共识。《哀公二年》讲“顺天明,从君命,经德义,除诟耻”,主张国君要顺从天命,推行德义。《宣公十五年》又言“将敬奉德义以事神人”,敬奉德义来奉事神灵,才能“申固其命”,使国运继续,政令通行。《昭公二十八年》有“苟非德义,则必有祸”,若无德义,必有祸患临头。《成公元年》记载叔服劝谏刘康公不要伐戎,原因是“背盟不祥,欺大国不义,神人弗助,将何以胜”?“德义”有神秘的约束力,绝不能忽视其存在与影响。
《左传》所强调的德义,实际是礼的精神抽象化后所形成的新的社会共识。西周立国之初,以当时的道德认知制礼作乐,试图通过礼乐规则来巩固道德共识。随着礼崩乐坏,原本蕴含在礼乐制度中的道德共识被忽略了,礼乐演变成了徒具形式的仪式,天子与诸侯、诸侯与诸侯及诸侯与大夫之间的礼制尚且存在,但礼的内在约束性的德义,却被视而不见。孔子试图依礼义的标准,重新叙述春秋时期的人事,以是否合礼来褒贬人事。而《左传》进一步抽象,将“礼义”升华为“德义”,以之为道德共识,视为天子、诸侯、大夫、士必须遵守的社会法则,从而将附着于“礼”的制度共识,转化为人之能群的道德共识,即非礼的行为,不简单是违背规则的问题,而是违背道德共识的问题。《左传·庄公二十七年》有“天子非展义不巡守”,周天子视察诸侯国的目的,就是为了宣扬天授予的德义,以之规范社会秩序,诸侯皆应从之。《成公二年》载晋人之言:“反先王则不义,何以为盟主?”违反先王的制度是不义,即违背了天子建德以分封的道德共识,怎么能做诸侯国的盟主呢?晋、齐这样的大国,应“大国制义以为盟主”,才能“小国所望而怀也”。《僖公七年》又载管仲劝齐桓公不要答应太子华的要求;《僖公二十五年》记载狐偃劝晋文公勤王,送周襄王回王城;《文公七年》记载郤缺劝赵宣子归还卫国的土地,都强调做事要符合德义。反之,《僖公十四年》记秦有饥荒,求助于晋,晋却不伸援手,庆郑以“怒邻不义”叱骂之,晋国不行义,必致亡国。《左传》以有德、有义为准绳,记述诸侯之事,侧重体现了诸侯国的政治驾驭能力与权威影响力。
《左传》所言的“德义”,亦落实到了个人对道德共识的认同,是为个人美德。《左传·宣公十五年》载解扬之言:“君能制命为义,臣能承命为信,信载义而行之为利。”君臣皆承义而行,才能有利于国家;《昭公四年》又记郑子产进行赋税改革,《昭公六年》记郑人铸刑书,都以合德义为前提。《襄公二十三年》记“庆氏不义”,庆氏无德,在陈国专权、叛军、虐民,最终不保;《昭公元年》记楚令尹公子围篡权夺位,“强以克弱而安之,强不义也。不义而强,其毙必速。”尽管公子围登基为楚灵王,但几年后,还是因众叛亲离而自杀。《昭公二十四年》中有苌弘对王子朝乱事的评语:“何害?同德度义。”孔颖达正义引孔安国云:“德钧则秉义者强。”唯有同德,才能谋义。《僖公二十四年》有“心不则德义之经为顽”,心中时刻要有德义,耳目听闻、言谈举止都必须按照德义进行。
史书在记叙史事时,蕴含有对史事的评判,这些评判的依据是基本的道德共识,《左传》《国语》皆言之为“德义”。后世有论《国语》亦为左丘明所作,是为《春秋外传》,从“德义”作为记言、记事的标准来看,二者体现出了高度的共识。《国语·晋语四》载赵衰言:“夫先王之法志,德义之府也。夫德义,生民之本也。”德义被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法则。《晋语七》又载司马侯言:“诸侯之为,日在君侧,以其善行,以其恶戒,可谓德义矣。”认为诸侯的弃恶从善,正是合乎“德义”的要求。其中所言的“德义”,已不再局限于合乎制度要求,而是从更高的道德层面,对人的行为提出了要求。
由此来看,《左传》通过叙事,强化了道德共识在历史评判中的基础性地位,与《春秋》更关注制度共识对人事的褒贬相比,体现了史学认知的深化,不再关注于特定历史阶段的制度性视角,更关注这些行为是否合乎人类基本的道德要求。作为制度的“礼”是可以不断调整的,“礼义”在长时段内也是不断演进的,但作为价值共识的“德义”,却更为恒定,以“德义”的标准衡量历史人物和事件,从而为历史叙述寻找到了足以洞穿千年的基本标准,确立了史书的客观性。
三、谷梁学对《春秋》“经义”的建构
《春秋》记事简略,《左传》以史事增嬗,做的是叠加的加法;《春秋》明事辨理,《谷梁传》挖掘深意所在,做的是交错的乘法。《左传》将自身与《春秋》视为一体,通过“君子曰”,评价《春秋》与《左传》所记的史实;《谷梁传》将《春秋》陌生化处理,试图解开《春秋》谜团,又将《春秋》作为第三人称,直接总结《春秋》之“义”。《左传》叠加的“义”,多针对史事,《谷梁传》交错而出的“义”,多针对《春秋》文本进行的阐释。通过对《春秋》笔法的解读,形成了《春秋》经义的基本建构。
《谷梁传》以解经阐释《春秋》之“义”,先确定《春秋》之“义”的必然存在,然后开始解决问题:“义”如何在《春秋》中得以体现?“义”与《春秋》哪些史事相关?“义”的原则是什么?这三个问题分别是对语法语义的理解、对事实的理解、对精神的理解[18]。如《谷梁传·隐公元年》:“《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又言:“《春秋》贵义不贵惠,信道不信邪。”以美恶有别,指出《春秋》之“义”的道德标准,即美者美之,恶者恶之。美之者,《春秋》有“善救陈也”“善救许也”“善救徐也”“善救邢也”,称赞诸侯国援手相救的美德;恶之者,《成公十八年》“称国以弑其君,君恶甚矣”,《春秋》记载以国家名义杀了国君,说明国君可恶至极;《襄公十年》“称盗以杀大夫,弗以上下道,恶上也”,憎恶郑国国君乱杀臣属。这些美、恶评价的依据,是《春秋》依据礼义而发,《左传》依据德义进行过评判,《谷梁传》的阐释,是对孔子蕴含在《春秋》之中的“义”进行文本上的解读,将其中的“微言”发微,使“大义”明白,从而使得《春秋》不再作为史书,而成为可资评判、可供参考、可以阅读的经典范本。
《谷梁传》的这种解读,发微了诸多《春秋》未明言的史实,以之作为阐释其政治理想的载体。如《庄公六年》中认为《春秋》为职位卑微的“王人”称名,是赞许他救助卫国的举动而“贵之也”,“救者善,伐者不正”,贬斥诸侯的不义之师,以正为美。《庄公四年》记“纪侯大去其国”,因“纪侯贤而齐侯灭之,不言灭,而曰大去其国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齐国灭纪,纪侯有贤,从纪侯的角度记“去”,褒奖贤君;《襄公二十九年》记“吴子使札来聘”,因其“身贤,贤也”,故称为子,褒奖贤臣。《宣公十七年》称公弟叔肸“贤之也”,故记其卒,“以取贵乎《春秋》”,行为之正,合乎道义;人品之贤,合乎德义。《谷梁传》以春秋间人事为依据,发微出诸多其未明言然却为学界关注的道义、德义,以之作为阐释儒家学说和寄托政治理想的学理来源,使得《春秋》成为儒家学说的基本典籍,形成了最早的经义。
经义是据经立义,是对经典文本的阐释。《谷梁传》以《春秋》为重王道、尊君父、讨乱贼、辟邪说、正人心之作,除以彰美惩恶为《春秋》之“义”的道德共识外,还以贵贱之别为《春秋》之“义”的秩序共识,其实是对《春秋》之义的引申与阐发。《桓公二年》:“书尊及卑,《春秋》之义也。”《文公二年》:“不以亲亲害尊尊,此《春秋》之义也。”《昭公四年》:“《春秋》之义,用贵治贱。”孔子提倡的克己复礼,正是要恢复维系“亲亲”关系的周礼,而《谷梁传》所言的“不以亲亲害尊尊”,恰恰体现的是战国时期学者对亲亲尊尊关系的新思考,即诸侯维系社会秩序和国际秩序,不再依靠西周时期确定的伯仲叔季之类的宗族关系维系高下,而是新形成的以社会关系来区分尊卑。这一阐释显然是借经典而立义。
《谷梁传》对五伦关系的讨论,最能看出其借《春秋》而立新义的用意。在夫妻关系中,《隐公二年》:“夫人之义,从君者也。”以夫为贵;《成公十五年》:“夫人之义,不逾君也,为贤者崇也。”夫为尊者,妇为卑者,夫妇有上下之分。在长幼关系中,“《春秋》之义,诸侯与正而不与贤也”[4](P19),卫桓公去世后,对杀州吁改立公子晋的看法不一,《谷梁传》理解为以嫡长为贵;《桓公十五年》记有“讥夺正也”“反正也”,公子忽出奔又复归,其为嫡长,《春秋》便肯定重登君位的行为;在君臣关系中,以君为贵,所以《桓公二年》调换时间顺序,先记宋殇公被弑,再记大夫孔父被杀,而实际上,孔父是在宋殇公之前被害的;《僖公十年》“以尊及卑”,将国君卓子置于大夫荀息前;《成公十七年》将鲁成公伐郑后归国,写在公孙婴齐去世前,都是《春秋》表达的“臣子之义”。在夷夏关系中,“礼:诸侯无外归之义,外归,非正也”[4](P90),诸侯是不能依附夷狄的,“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国也”,听从夷狄之国的指挥,来攻打中原国家的行为是不正义的。
《谷梁传》在对《春秋》之“义”的解释中,附益了诸多《春秋》所载人事中涉及却未必为孔子所关注的社会秩序、道德认知和价值共识,《谷梁传》尽最大可能地进行了发微和解读,这些解读是从《春秋》的字里行间考证、推演出来的,从而使得《春秋》成为一本可无穷诠释、无限解读的经典。《谷梁传》在对其进行解读时,意在建构一个更为理想的、更为具体的道德阐释文本和历史经验文本,以合乎日益增长的学说要求。这就使得《春秋》的经典性日渐强化,成为学者日益关注、学界日益阐释的“经”。《谷梁传》依《春秋》解“义”,使《春秋》之“义”呈几何倍数增长,形成了复杂的“经义”系统。需要补充的是,《谷梁传》促成《春秋》“经义”的形成,还在于其对《春秋》笔法的解读。如《谷梁传·桓公五年》:“《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庄公七年》:“《春秋》著以传著,疑以传疑。”指出《春秋》用清楚的语句记载清楚的史事,用有疑问的语句记载有疑问的史事,《春秋》客观著史的态度进行赞扬并对《春秋》中大量的实词、虚词,并分析词序、句读、歧义等进行了训解,如《昭公二十九年》:“溃之为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则恶矣,亦讥公也。”释“溃”的言外之意,指出《春秋》讽刺鲁昭公不行德义,失去民心;《哀公四年》:“《春秋》有三盗:微杀大夫谓之盗,非所取而取之谓之盗,辟中国之正道以袭利谓之盗。”这些训解,强化了《春秋》作为“经”的文本性特征,使得《春秋》不仅作为学理的载体,还成为著作的范本。
四、公羊学与“春秋大义”的学理生成
从成书时间看,《公羊传》在“三传”中成书最晚,且与《左传》基本以左丘明一人之力整理史料成书不同,《公羊传》是“及末世口说流行”[19],经过几代的口传之义,最终誊写成书,其内容不出于一时,亦不出于一人,故学理驳杂。《公羊传》短小零碎,明显有从口传到记录成文的痕迹,且多自问自答,包含了许多战国后期士人对治国理政的新思考。如何从乱世到治世,是战国后期学者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公羊传·哀公十四年》:“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认为《春秋》是孔子出于拨乱反正而作,其中寄托的“义”正是为后人立法。战国后期的儒生面对由兼并而走向一统的国家如何治理,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一是以荀子为代表的儒生,试图通过礼法并治重建王制,并进行了制度性的设计,是为立制派。二是以公羊学者为代表的儒生,试图从前代经典中找到国家治理的经验,并对之进行理论阐释,形成服务于现实的理论架构,是为尊王派。
荀子对王制的设计和建构,并没有得到其弟子李斯和韩非子的认同,秦汉之际的儒生也只是继承了荀子所传的经典而对其尊礼重法的学说进行了剥离。而《春秋》则被固守经典的儒生视为孔子亲传的“六经”之一,依据《春秋》之义推演治国理政之策,成为秦汉之际儒生们服务现实进行理论建构的出路。《公羊传》中多次论及“诸侯之义,不得专封也”“大夫之义,不得专废置君也”“诸侯之义,不得专讨也”“大夫之义,不得专执也”。周天子势微,诸侯大夫也不能代行天子之“义”。公羊学者在《僖公元年》批评齐桓公不经过周天子,擅自在陈仪之地安置被狄逐出故土的邢国,又将被狄打败的卫国安置在楚丘;《僖公十四年》批评了齐桓公使杞国迁都营陵,以避徐、莒威胁。继承了孔子寄托的“礼义”,强调诸侯应该尊重天下共主的周天子。这一标志的认知,体现出公羊学在战国乃至秦汉之际面对现实重大关切的勇气。那就是天下只能有一个共主,其他诸侯必须臣服于他,这不是取决于军事实力的大小,而是取决于道义的有无、取决于天下秩序的维持。
公羊学面对秦汉之际的地缘政治,强调了华夷之辨,认为夷之所以不能与华对等,不在其种族,而在其缺少“义”,即缺少对天下秩序的基本认同,缺少彼此相互责任的承担。《公羊传·庄公十年》有“不与夷狄之获中国也”,不赞许夷狄之国俘虏中原国家的国君。《庄公二十四年》论“戎众以无义”,直接贬斥戎族无义,《庄公三十年》记有“《春秋》敌者言战,桓公之与戎狄,驱之尔”,齐国不是与戎狄交战,而是驱逐之,对夷狄有所鄙视。《僖公二十一年》记楚成王与宋襄公之战,也有“楚,夷国也,强而无义”的说法。“夷狄无义”的认知,为秦之备胡、汉之备匈奴提供了学理的支撑,汉初对匈奴的指责和讨伐,也是以其“无义”为借口[20]。
董仲舒是公羊学说的集大成者,其做《春秋繁露》数十篇,是对《春秋》及《公羊传》的系统解读,吸收了其他经传的观点,形成了一个能服务于时代所需的理论体系,对《春秋》《公羊传》中未及诠释的诸多细节进行了全面阐释。其《春秋繁露·楚庄王》:“《春秋》贤而举之,以为天下法,曰礼而信。”强调《春秋》是国家治理的经典法则。《观德》:“《春秋》常辞,夷狄不得与中国为礼。”认为《春秋》言明了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王道》:“《春秋》立义,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有天子在,诸侯不得专地,不得专执天子之大夫,不得舞天子之乐,不得致天子之赋,不得适天子之贵。”推崇《春秋》中蕴含的尊卑秩序,将之作为政治伦理的基础。《阳尊阴卑》:“《春秋》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强调君臣秩序中的主次地位,是《公羊传》尊王学说的具体化。在董仲舒的认知中,《春秋》为汉代的治国理政提供了基础性的文本,其中既有经验的借鉴,也有学理的阐释。
在这样的视角下,董仲舒竭力发明《春秋》中的“微言大义”,将之言之为“春秋大义”。《春秋繁露·楚庄王》:“《春秋》,义之大者也。”《正贯》:“《春秋》,大义之所本耶?”其所言的大义,便是《春秋》中寄寓了治国理政的全部要义,对其经验进行借鉴,对其学理进行阐发,可以为汉建制,更可以为汉立义。《楚庄王》:“得一端而博达之,观其是非,可以得其正法。”《精华》:“《春秋》者,得一端而多连之,见一空而博贯之,则天下尽矣。”《玉英》:“《春秋》之道,博而要,详而反一也。”这些一以贯之的“大义”便是要尊王攘夷。尊王的要义,是维系天下一统;而攘夷的要义,是举国备胡,而不能轻易苟合。
景帝、武帝时期,汉王朝面临的内忧在于诸侯坐大,外患在于匈奴入侵。如何保证汉家天下的一统,尊王为汉王室提供了经验的借鉴和理论的阐释,为武帝削藩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汉王朝削弱诸侯而行郡县提供了学理支撑。攘夷的阐释使得汉王室逐渐走出了与匈奴和亲的传统,转而采用更为积极的策略,按照“义”的准则与匈奴展开国际道义上的战与和,从而使得匈奴最终承认“义”的准则,并按照“义”的要求与汉王朝展开交往,形成了新的地缘政治观,为此后解决华夷关系问题做了实践性的示范。
董仲舒以尊王、攘夷的现实需求为视角,将《春秋》中的“微言大义”进行了全新的阐释与建构,不仅将《春秋》的经验推广到汉代行政秩序之中,而且将“春秋大义”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法则,不断发微,“《春秋》举世事之道,夫有书天,之尽与不尽,王者之任也。”[21](P467)使得《春秋》及《公羊传》成为常读常新、寓义无穷之书,成为体现恒常之理的经典,确立了“春秋大义”的经典型。如其言“《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21](P14),强调继承传统经验。又言“《春秋》固有常义,又有应变。……《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21](P89-95),主张世上万变不离其宗,是为人之为人的价值共识。明确提出孔子作《春秋》是为万世立法:“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万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贤才,以待后圣。”[21](P158-159)将《春秋》所谓为汉立法的依据。汉王室要想长治久安,必须依据《春秋》改制,“今所谓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变其理,受命于天,易姓更王,非继前王而王也。……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21](P17-19)摆脱秦制的传统,建立起一个合乎《春秋》学理的新王朝,从而为宣帝、昭帝之后的改制思潮提供了学理依据。
由此来看,“春秋大义”的形成,是春秋学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对其学理进行形而上的抽象化过程,从而使得《春秋》从史书逐渐演化成为经书,史书侧重于史实,而经书侧重于学理。谷梁学和公羊学在阐释的过程中,将《春秋》作为经验的借鉴和学理的来源,对其中蕴含的道德共识、价值共识和秩序认知进行了深入而详切的阐释,将战国乃至秦汉学者的政治理想、社会理想寄托其中,使之成为治国理政的经典文本,成为汉改制的理论依据,从学理上完成了“春秋大义”的理论建构,《春秋》及其三传也因为这些形而上的学理阐释,完成了从史到经的转化。
注:
①“义”之所以成为阐释《春秋》的核心,根本原因在于《春秋》的文本性质与功能具有“义”的原始发生内涵与指代功能,故《春秋》中无“义”字,却能以“大义”精神独领群经。(参见谭佳《<春秋>与“义”:“义”的文化渊源及内涵之探》,《百色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这种从《春秋》三传对“义”的建构的角度分析,不无道理。回到《春秋》文本,《春秋》是记事史书,在行文中并无论辩,故没有使用“义”之涵义的语境。不独于此,《春秋》中也无“仁”字,可为旁证。
②参见(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北宋)胡安国《春秋胡氏传》,(清)廖平《榖梁古义疏》等。
③参见(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刘师培《春秋左氏传例略》《春秋左氏传古例诠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