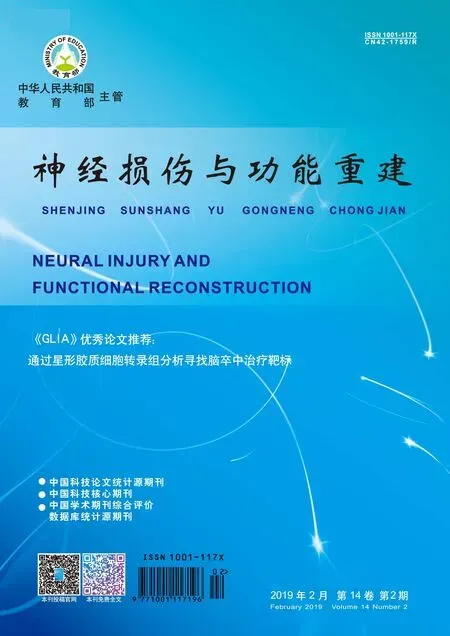脑出血后免疫炎症反应及相关临床研究进展
马阳,张萍,唐洲平
脑出血(intracerebral hemorrhage,ICH)是脑卒中第二大类型,致残率和死亡率高,目前针对ICH后神经功能恢复的治疗非常有限[1]。继发性脑损伤在ICH患者的神经功能损伤中起着重要作用,其中,免疫炎症反应在ICH后脑水肿及脑损伤的形成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2,3]。本综述旨在讨论近年来ICH的免疫炎症机制的研究进展,总结ICH后的病理生理变化和主要炎症细胞及炎症介质在病程中的变化及作用,最后介绍与ICH的免疫炎症治疗相关药物的临床试验进展。
1 ICH损伤机制
ICH后脑损伤主要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两种。原发性脑损伤主要为血肿的占位效应,机械压力引起钙内流和兴奋性毒性神经递质分泌,引起细胞毒性水肿和坏死。继发性脑损伤是由于血液成分进入脑组织,和受损的脑细胞一起引发了多种有害机制,导致血脑屏障破坏和血管源性水肿。
继发性脑损伤的病理生理过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首先,ICH后血凝块和血液释放大量凝血酶,激活补体途径及蛋白酶激活受体,引发细胞毒性和细胞裂解。ICH后红细胞溶解释放出大量血红蛋白和珠蛋白,血红素加氧酶-1在出血周边区域激活的小胶质细胞中高度表达,可分解血红素产生胆红素、一氧化碳和铁。铁通过氧化还原反应中产生的自由基增加氧化应激,引起组织损伤、DNA损伤,血脑屏障破坏和炎症。而一氧化碳可抑制细胞呼吸,限制氧的释放,增加线粒体中的自由基。实验动物模型也表明铁螯合剂--去铁胺能改善ICH损伤模型的神经功能结局及减轻脑水肿[4]。因此ICH后及时清除血肿是治疗中重要的一环。其次,ICH后往往伴随着炎症指标的变化,外周血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率(neutrophil-to-lymphocyte ratio,NLR)与血肿周围水肿独立相关,NLR与ICH后30 d的死亡率和发病率也相关,因此对预后有一定的提示作用[5,6]。转录组学研究显示,ICH和脑缺血具有差异表达的T细胞受体和CD36基因、Toll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s,TLR)、巨噬细胞和T辅助细胞途径等[7]。此外,ICH后炎症条件下基质金属蛋白酶(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MMPs)的激活也可导致血脑屏障破坏,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和脑水肿形成。
2 ICH后免疫炎症反应
2.1 小胶质细胞和巨噬细胞
ICH后小胶质细胞首先应答,ICH的损伤刺激作用于不同的小胶质细胞表面受体,包括TLR和晚期糖基化终产物的受体。小胶质细胞和巨噬细胞活化后分为2个主要亚型:传统活化表型即M1和选择性活化表型即M2。活化的M2小胶质细胞分3种亚型:M2a、M2b和M2。M2a亚型有助于细胞再生,M2b和M2c亚型参与吞噬和去除组织碎片。确定M1/M2小胶质细胞和巨噬细胞的比例可以提示病理生理环境,M1/M2高意味着高氧化的苛性炎症环境,而低M1/M2意味着修复、再生环境[8]。小胶质细胞M1样表型的激活主要发生在ICH急性期后,对M2样小胶质细胞反应发生在亚急性和慢性期,可能有助于吞噬细胞碎片和血肿清除[9]。推测ICH的免疫炎症治疗应该通过调节不同时期小胶质细胞功能,促进组织修复和功能恢复。
ICH后小胶质细胞和巨噬细胞的活化机制,大概归纳为以下几方面[10]。④损伤相关分子模式分子(damage-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 molecules,DAMPs):ICH后,血红素刺激小胶质细胞释放高迁移 率 族 蛋 白 B1(high mobility group protein,HMGB1),HMGB1可以激活TLR4诱导炎性损伤,也可在ICH晚期激活RAGE促进血管生成。动物实验表明,通过减少血肿周围HMGB1和激活的小胶质细胞的数量,可减轻脑水肿和神经元凋亡[11]。④TLR:血红素可通过TLR4增强小胶质细胞活化,随后诱导NF-κB活化,最终增加ICH后的炎症细胞因子表达和炎性损伤。临床研究表明,TLR2和TLR4表达显著升高与ICH患者的不良结局相关[12]。Wang等[13]发现,ICH后由血红蛋白诱导的新型TLR2/TLR4异源二聚体引发了ICH的炎性损伤,增加了TLR2和TLR4的有害作用。④Notch信号通路:Notch信号通路参与神经炎症性疾病中小胶质细胞激活和炎症过程,有动物研究证实Notch-1信号传导是ICH诱导的反应性星形胶质细胞增生的关键调节因子,在ICH大鼠模型中使用特异性抑制剂阻断Notch-1信号传导,可抑制由ICH引起的星形胶质细胞增殖和胶质纤维酸性蛋白水平,改善ICH后神经功能[14]。阻断Notch-1信号通路可能是ICH的潜在治疗策略之一。④炎症小体:炎症小体是细胞内先天性免疫应答典型的模式识别受体之一,在调节半胱天冬氨酸酶1(caspase-1)活性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小胶质细胞表达Nod样受体(NOD-like receptor,NLR),NLRP3炎症小体通过释放白细胞介素-1β(interleukin-1β,IL-1β)及促进ICH后中性粒细胞浸润来扩增炎症反应,在ICH模型小鼠中抑制NLRP3炎症小体可有效减少ICH后炎症反应[15]。嘌呤能2X7受体(P2X7R)在NLRP3激活的上游,P2X7R的基因沉默可抑制NLRP3炎症小体活化和IL-1β/IL-18释放,并显著减轻脑水肿和神经功能缺损[16]。研究证实,ICH后补体介导的神经炎症依赖于NLRP3的激活且NLRP3是ICH后神经炎症所必需的[17],抑制NLRP3可以减轻ICH后脑损伤及炎症[18]。这些发现均支持炎症小体在促炎细胞因子的产生和释放,以及加剧ICH诱发的继发性脑损伤中的作用。
2.2 淋巴细胞
ICH患者血肿周围存在T辅助淋巴细胞,CD4+T细胞是ICH后24 h的主要脑浸润白细胞群,其数量在第5天达到顶峰。调节性T细胞可抑制ICH模型的炎症损伤[19],尽管缺乏临床前证据,但它可以介导ICH后延迟免疫应答,可能是部分通过加强炎症来氧化微环境。芬戈莫德是一种鞘氨醇-1-磷酸受体调节剂,具有调节免疫功能,可有效抑制T细胞迁移进入神经中枢系统,减少局部免疫反应。已有临床前实验表明,芬戈莫德可减轻ICH啮齿动物的脑水肿、神经元凋亡和脑萎缩,改善神经功能缺损[20]。ICH后B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的低渗透率表明在ICH中可能作用不大[21]。
2.3 单核细胞
单核细胞在ICH后12 h内就已迁入大脑,ICH后第5天数量达到顶峰[21],ICH后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及受体CC趋化因子受体2(CCr2)参与单核细胞向脑的迁移[22]。研究表明,有少量循环炎性单核细胞的Ccr2(-/-)小鼠在ICH后较对照组运动功能更好[23]。具有野生型中枢神经系统细胞和Ccr2(-/-)造血细胞的嵌合小鼠也显示运动功能的早期改善。这表明减少血源性炎症性单核细胞有助于急性神经功能障碍的恢复。有2家医院前瞻性收集了85例ICH患者的血清样品,发现患者24 h时较高的CCr2水平与1周后的神经功能不良结局独立相关[23]。一项包含115例ICH患者的前瞻性队列研究发现,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指标升高的患者90 d的mRS评分较差,发病后24和72 h,人干扰素诱导蛋白10(CXCL10)的升高与较差的90 d mRS评分独立相关[24]。总之,炎症性单核细胞在ICH后提示恶化早期神经功能缺损,可能为治疗靶点。
2.4 中性粒细胞
中性粒细胞是脑损伤后首先进入大脑的白细胞群体。胶原酶诱导的小鼠ICH后4 h,在血肿及其周围就发现浸润性中性粒细胞,其数量在ICH后3~5 d达到峰值[2]。在它们凋亡后,释放的分子可能会进一步刺激小神经胶质细胞/巨噬细胞,加剧神经炎症过程。多形核中性粒细胞可协助清除脑卒中的细胞碎片,加重血脑屏障的降解,引起ICH后继发性损伤,脑水肿,再出血和神经功能恢复不良[25]。促炎性N1中性粒细胞已被证明在脑水肿和神经毒性中的作用,而抗炎N2中性粒细胞可抑制这种过度的免疫反应,促进神经元存活。
2.5 炎性介质
与ICH相关的炎性介质很多,包括趋化因子、炎性细胞因子、转录因子、补体系统等。在ICH后用TNF-α抗体治疗可减少小胶质细胞/巨噬细胞活化,并减轻脑水肿和改善神经功能[26]。研究发现外周血TNF-α可用于预测ICH患者不良预后风险[27]。来自啮齿动物模型的数据表明IL-27可修饰骨髓中的中性粒细胞成熟,抑制其产生促炎/细胞毒性产物,同时增加其有益的铁清除分子(包括乳铁蛋白)的产生,最终减轻脑水肿及血肿,改善神经学评分结果[28]。IL-17A则可促进小胶质细胞自噬和小胶质细胞炎症,从而降低脑水含量并改善ICH小鼠的神经功能[29]。
3 关于ICH免疫炎症治疗的临床研究进展
3.1 芬戈莫德(Fingolimod,FTY720)
2014年,进行了一项以口服芬戈莫德是否安全有效地缓解ICH患者的血肿周围水肿和神经功能缺损的临床研究。将ICH患者23例随机分为实验组(标准ICH治疗+芬戈莫德0.5 mg/d,连续口服3 d,首剂在发作72 h内服用)和对照组(标准ICH治疗),结果表明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患者神经功能改善程度较大,血肿周围水肿较轻,且药物安全性高[30]。芬戈莫德治疗可显著降低ICH小鼠模型脑的T淋巴细胞浸润并促进血脑屏障完整性[31]。也有动物实验表明在胶原酶诱导的ICH小鼠模型中给予芬戈莫德(ICH后1 h腹腔注射)对于急性期(ICH后24 h和72 h)的小鼠的死亡率和神经功能改善没有影响[32]。接下来仍需大规模的临床研究来验证芬戈莫德治疗ICH的效果,如给药时间及有效干预时间窗等。
3.2 塞来昔布(Celecoxib)
塞来昔布是一种选择性环氧合酶2抑制剂,在胶原酶诱导的大鼠ICH模型中,塞来昔布治疗可减轻脑水肿、炎症和血肿周围细胞死亡,促进功能恢复[33]。2009年一项回顾性分析纳入ICH发病48 h内入院的患者34例,分为治疗组(发作48 h内服用塞来昔布,400 mg/d,≥7 d)和对照组(未服用塞来昔布),发现塞来昔布治疗显着降低了脑水肿体积且不良事件发生率无差异,表明塞来昔布可能是安全有效的治疗ICH药物[34]。2013年一项包括了44例患者的多中心试验也表明,ICH急性期给予塞来昔布与减轻脑水肿有关[35]。后续仍然需要大型的前瞻性临床试验来确定塞来昔布能否改善ICH患者的短期与长期功能结局。
3.3 米诺环素(Minocycline)
四环素类抗生素米诺环素是一种小胶质细胞活化的抑制剂。米诺环素可通过降低ICH后的铁负荷,减轻铁诱导的血脑屏障破坏和脑水肿[36],也可通过抗自噬、抗凋亡来减轻继发性脑损伤[37]。最近一项双盲、随机对照临床试验评估了米诺环素对于ICH患者的安全性和可行性,共纳入20例受试者,结果显示米诺环素治疗与第1天至第5天的MMP-9水平的降低相关,且安全性高[38]。
3.4 罗格列酮(Rosiglitazone)和吡格列酮(Pioglitazone)
PPAR-γ是调节CD36表达的配体依赖性转录因子,其本身是对吞噬活性重要的清道夫受体。在ICH小鼠模型中,用PPAR-γ激动剂如罗格列酮治疗增加了CD36表达,并促进了小胶质细胞和/或吞噬细胞对红细胞的吞噬作用,对于血肿吸收有有益作用[39]。PPAR-γ激动剂罗格列酮和吡格列酮经FDA批准用于2型糖尿病血糖控制,正在进行的II期剂量递增试验,以评估吡格列酮用于ICH患者的安全性[40]。
4 结论及未来方向
炎症反应越来越被认为是ICH后继发性脑损伤病理生理学的重要参与者。证据表明,对于炎症和免疫应答的靶向治疗是一种可行的方法,然而,需要更进一步研究ICH后免疫系统的变化及其与大脑的相互作用,来帮助开发新的免疫干预手段。未来的研究方向分为2部分:机制方面要重在阐明各种炎症细胞因子随时间变化起的具体作用及找到有效调节免疫系统的方法,使之在ICH后不同阶段发挥相应的作用,抑制氧化炎性环境的同时促进神经修复与再生,改善ICH后神经功能结局;临床方面需要探索免疫炎症调节的时机、患者选择、剂量调控及安全性[41]。目前关于ICH免疫炎症调节的临床试验还不多,需要一些大型前瞻性试验来确定某些药物的效果。明确免疫炎症治疗的机制及方法,对于ICH治疗及预后具有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