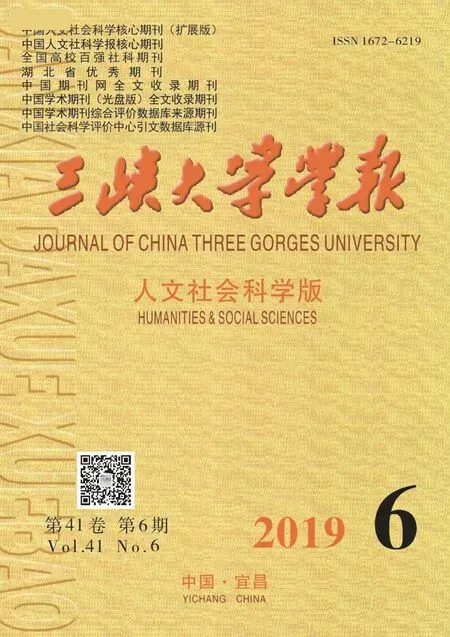受贿罪共犯的规则适用与实践认定
李丁涛
(西南政法大学 法学院, 重庆 401120)
为规范受贿罪共犯的实践认定,近年来,我国共有三部司法解释直接或间接地对受贿罪共犯问题作出了规定,分别是2003年的《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2007年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和2016年《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总体来讲,在受贿罪共犯问题上,相关司法解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均是以共同犯罪的一般性理论为指导,均明确了成立受贿罪共犯所应具备的相关构成要素。但同时也应注意到,有些规定与共同犯罪的理论并不相一致。基于此,本文通过对受贿罪共犯的相关规定进行分析,得出成立受贿罪共犯的一般性规则,同时结合典型性案例,对如何在实践中认定受贿罪的共犯进行探讨。
一、受贿罪共犯的相关规范梳理
涉及受贿罪共犯问题的相关司法解释,虽然在受贿罪共犯的具体认定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但却各有侧重。其中,《纪要》主要就近亲属及近亲属以外的人与国家工作人员成立受贿罪共犯问题作出了规定。该文件在明确了成立受贿罪共犯取决于行为人双方有无共同受贿的故意和行为这一总则性规定之后,规定了两种典型的近亲属构成受贿罪共犯的情形,即近亲属代为转达请托事项,收受财物后告知国家工作人员的,以及国家工作人员明知近亲属收受请托人财物,仍按照近亲属要求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此时,该国家工作人员成立受贿罪,其近亲属成立受贿罪的共犯。针对近亲属以外的其他人成立受贿罪共犯的情形,《纪要》规定,近亲属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构成受贿罪共犯。
《意见》主要就特定关系人及特定关系人以外的人与国家工作人员成立受贿罪共犯问题作出了规定。该文件认为,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实施相关受贿行为的,应认定国家工作人员成立受贿罪,特定关系人以受贿罪的共犯论。针对特定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成立受贿罪共犯的问题,《意见》明确指出,特定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与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占有的,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
《解释》关于受贿罪共犯的规定,实际上是对特定关系人成立受贿罪共犯的一种特殊认定。即在国家工作人员知道特定关系人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因未履行监督、退还义务而推定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受贿故意,进而间接认定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成立受贿罪的共犯。
不难看出,在上述三部司法解释中,《解释》关于受贿罪共犯的(间接)规定,实际上是对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一种延伸性规定,是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成立受贿罪共犯的一种特殊情形,不具有一般性的指导意义。因此,对成立受贿罪共犯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司法解释实际上只有《纪要》和《意见》两部。而通过对两部文件所涉及受贿罪共犯的内容分析可得,二者在认定受贿罪共犯问题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均是以共同犯罪一般性理论为指导,均明确了成立受贿罪共犯所应具备的主客观要件。如《纪要》和《意见》均从实质上要求成立受贿罪共犯需行为人双方在主观上具备“通谋”,在客观上分别实施了受贿罪的相关实行行为。同时,两部解释在认定近亲属以外的人和特定关系人以外的人与国家工作人员成立受贿罪共犯时,均明确二者需共同占有财物[1]。
由于《纪要》和《意见》关于受贿罪共犯的规定所规范的主体外延不同①,因此,在运用不同司法解释认定受贿罪共犯时,必然存在某些认定差异,如关于近亲属以外的特定关系人(如情妇)构成受贿罪共犯的认定不同、向第三人行贿的认定不同等[2]。但本文认为,上述认定差异是近亲属和特定关系人外延不同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据此不能否认两规范在认定受贿罪共犯时所具有的内在一致性。当然,由于《纪要》和《意见》关于受贿罪共犯的规定不可能完全一致,在具体认定中,如果存在法条竞合,应以“新法”《意见》的规定为准。
二、受贿罪共犯成立的一般性规则
《纪要》和《意见》对于认定受贿罪共犯具有一般性的指导意义,《解释》则是针对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成立受贿罪共犯所作出的一种特别规定。因此,在规范层面对受贿罪共犯成立的认定,应以《纪要》和《意见》的规定为主,同时兼顾《解释》的特别规定。
1.主观上须具备“通谋”要件
在受贿罪共犯主观要件的认定上,《意见》明确规定了“通谋”要件。但《纪要》在对近亲属与国家工作人员成立受贿罪共犯进行认定时,并未使用“通谋”一词,仅是规定了两种典型的近亲属构成受贿罪共犯的类型(代为转达请托事项型和明知近亲属收受财物型)。基于此,有学者认为,按照《纪要》的规定,近亲属收受财物后,国家工作人员明知此种事实而仍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就可以认定国家工作人员与近亲属构成受贿罪的共犯,而不需要双方具有通谋[3]。这是否表明《纪要》和《意见》在认定受贿罪共犯时的标准不同了?其实不然。首先,《纪要》关于近亲属成立受贿罪共犯的两种类型性规定,主要针对的是当时司法实践中较为突出的情形,为了统一认识,才予以例示性写入《纪要》,属于注意规定而非创设新的共犯认定标准②。对受贿罪共犯的认定仍应以相关总则性规定为准,即应以是否具有共同受贿的故意和行为为准。其次,相关学者之所以认为《纪要》与《意见》关于受贿罪共犯主观要件的认定标准不同,很大程度上是对“通谋”进行了限缩解释,将“通谋”仅限于“事前通谋”的类型。其实,“通谋”除“事前通谋”的类型外,还包括“事中通谋”。所谓“事中通谋”,是指行为人一方在实施了受贿罪的某个实行行为之后,另一方基于对先前行为的认可,而继续实施受贿罪的其他实行行为的情形。而《纪要》中关于“近亲属收受财物后,国家工作人员明知此种事实而仍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的情形,便属于“事中通谋”的类型。再次,《纪要》在认定近亲属成立受贿罪共犯时,虽未使用“通谋”一词,但在对近亲属以外的人成立受贿罪共犯的认定中,却明确了双方必须具备“通谋”要件。由此可见,“通谋”实质上是在坚持共同犯罪一般性原理的基础上,结合受贿罪的复合性特征,对成立受贿罪共犯所应具备的主观要件内容的(共同受贿故意)一种表述。《纪要》和《意见》关于受贿罪共犯的相关规定,并未脱离“通谋”的范畴。
那么,《解释》关于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成立受贿罪共犯的特别规定,是否仍延续了行为人双方以“通谋”为构成要件呢?本文认为,《解释》的相关规定,在推定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成立受贿罪共犯时,实质上仍是以“通谋”为构成要件的。作为具有共同利益关系的一个整体,国家工作人员对特定关系人利用其影响力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应具有监督义务。同时,作为共同利益人,国家工作人员对特定关系人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应负有责令其退还或上交的义务,否则,即表明国家工作人员对特定关系人收受财物的行为持认可或放任态度。据此,国家工作人员便应当对特定关系人这种未退还财物的不法后果承担共同责任[4]。这种以国家工作人员不履行特定的监督、退还义务为前提,进而推定其与特定关系人具有共同的受贿故意,实际上仍属间接承认了双方具备“通谋”要件。
2.受贿罪共犯的成立仅限于共同的实行犯
我国刑法学界多将“实行犯”等同于德、日等国家刑法理论中的“正犯”来适用③。而受贿罪作为一种真正身份犯,无身份者能否与国家工作人员共同成立受贿罪的实行犯(正犯)呢?对此,我国刑法学界主要有肯定说、否定说和折中说三种观点[5]。肯定说”和“否定说”的观点,要么未排除自首犯等不能由无身份者构成真正身份犯实行犯的情形,不当扩大了其成立范围;要么无视某些真正身份犯中,无身份者可以参与实施部分实行行为的情形,进而缩小了其成立范围。两种观点均有不周延之处,故而不可取。“折中说”是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该说认为,在判断无身份者能否构成真正身份犯的共同实行犯时,应视具体情况而定。对于有些真正的身份犯,由于其身份和犯罪性质具有不可替代性,进而决定了无身份者不可能参与其实行行为。如脱逃罪、遗弃罪等。但在某些真正身份犯中,由于实行行为具有复合性且部分实行行为具有可替代性,无身份者可以参与实施部分实行行为,在这种情形下,无身份者便可以构成真正身份犯的共同实行犯,如受贿罪等。
基于该理论通说,收受财物行为作为符合受贿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即实行行为)④,具有可替代性,非国家工作人员实施该行为的,便可以与国家工作人员成立共同的实行犯。但有学者基于义务犯理论,认为无身份者实施的行为虽然符合构成要件行为,但由于欠缺义务违反性或者能力实现性,只能被认定属于非实行性的帮助行为[6]。对此,笔者不赞同。其一,非国家工作人员实施收受财物行为被认为是帮助行为的理论基础是义务犯理论,而义务犯理论本身在我国就未贯彻或者说争议很大;其二,根据受贿罪实行行为的学说,不论从形式的立场认为行为是否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还是从实质的立场认为行为是否造成了法益侵犯的紧迫性,收受财物的行为都应当是受贿罪的实行行为。
在明确了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可以成立受贿罪的共同实行犯之后,反观《纪要》和《意见》关于受贿罪共犯的相关规定,无论是特定关系人(《纪要》规定为“近亲属”)⑤与国家工作人员成立受贿罪共犯,还是非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成立受贿罪的共犯,均明确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包括特定关系人和非特定关系人)收受请托人财物为内容,相当于明确限定了受贿罪共犯的成立条件,即受贿罪共犯的成立仅限于共同的实行犯。据此,非国家工作人员教唆或帮助国家工作人员实施受贿犯罪的,在规范上均不成立受贿罪的共犯。
受贿罪作为真正的身份犯,其共犯认定的实质是解决非国家工作人员参与受贿行为的罪责问题。依据共犯与身份理论,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相互串通⑥、以及二者共同实施受贿犯罪的,均可能成立受贿罪的共犯。但我国关于受贿罪共犯的相关规定却只将成立受贿罪共犯的类型限定为共同的实行犯。如此规定,很大程度上是刑事政策对刑事立法的指引在个罪中的体现。我国历来重视对国家工作人员实施受贿犯罪的打击,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的参与行为则较为容忍,反映在受贿罪共犯的认定上,便是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参与实施了受贿罪的部分实行行为作为认定其成立受贿罪共犯的条件。
3.非特定关系人成立受贿罪的共犯必须与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占有财物
《纪要》和《意见》在对受贿罪共犯进行规定时,均依据行为人与国家工作人员的关系密切程度,对不同主体成立受贿罪共犯分别作出了规定,其中,在认定国家工作人员与非特定关系人成立受贿罪共犯时,除具备“通谋”要件外,还要求双方共同占有所收受的财物。之所以如此规定,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工作人员的解释,主要是出于主客观相一致原则与刑事打击面的考虑,鉴于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已有共同利益关系,故不再要求“共同占有”要件[7],而非特定关系人和国家工作人员不是天然的利益共同体,故需要对所收受的财物“共同占有”。也有学者认为,非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有共同占有请托人提供财物的事实,则在实践操作层面可以比较方便地认定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和存在受贿犯罪的共同故意问题[8],如此,以受贿罪共犯论处也就顺理成章了。
其实,在笔者看来,上述关于“共同占有财物”的规定是值得商榷的。按照共同犯罪的原理,非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的共犯,取决于双方有无共同受贿的故意和行为,而具备“通谋”即表明双方有共同受贿的故意;国家工作人员和非特定关系人分别实施了为他人谋利和收受财物的行为,即表明双方有共同受贿的行为。据此认定二者成立受贿罪的共犯在理论上已足,不需要在客观上对财物共同占有。
另外,对“共同占有财物”所作出的相关解释也较牵强。首先,认为“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已有共同利益关系,故不再要求‘共同占有’财物”的观点,实际上犯了一种预设前提的错误,即认为受贿罪的共犯必须以共同占有财物为前提,特定关系人由于和国家工作人员已有共同利益关系,而不需要共同占有财物,非特定关系人由于和国家工作人员没有共同利益关系,而需要共同占有财物,此明显不合理;其次,认为“‘共同占有财物’便于认定存在受贿罪共同故意”的观点,同样经不起推敲。对受贿罪共同故意的认定应以对“通谋”的认定为准,“共同占有财物”对于办案机关从侧面认定国家工作人员与非特定关系人是否具有共同的受贿故意虽有助益,但该行为绝不是认定受贿罪共犯的必要条件。
“共同占有财物”要件实质上是立法者出于从严认定非特定关系人成立受贿罪共犯,缩小刑事打击面这一刑事政策的要求而作出的一种特别规定,与我国的共同犯罪理论并不必然一致。基于此,在理论上成立受贿罪共犯的情形,依据相关司法解释并不必然成立,而在具体认定中则应以相关解释的规定为准。
三、受贿罪共犯的实践认定
基于上文的论证,在对受贿罪共犯主客观要件进行认定的过程中,由于客观要件是实实在在表露于外的结果,是一种事实判断,较容易认定。但对主观要件的认定,却是一种价值判断,在实践中较难把握。事实上,实践中认定受贿罪共犯的疑难点均表现为对受贿罪共犯主观要件的认定,即对“通谋”的认定。基于此,本文对受贿罪共犯的实践考察,将侧重于对受贿罪共犯主观要件的考察。
1.受贿罪共犯实践认定的疑难点
依据刑法理论,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成立受贿罪的共犯需具有共同的受贿故意,在规范上即表现为二者应具备“通谋”。受贿罪作为复行为犯,“为他人谋利”和“收受财物”均为其实行行为,按照上文对成立受贿罪共犯的规范分析,“为他人谋利”和“收受财物”须由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分别实施。那么,行为人在实施受贿罪相关实行行为的过程中,需要何种程度的意思联络⑦才能认定二者具有共同的受贿故意?此问题也是认定受贿罪共犯主观要件的核心。一般来讲,国家工作人员实施“为他人谋利”的实行行为,同时对于非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物”的行为也应当是明知的⑧。因此,对受贿罪共犯主观要件的认定,主要是针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对国家工作人员实施的“为他人谋利”行为是否具有意思联络的认定。为对此问题进行准确论证,本文以特定关系人参与实施受贿犯罪为例进行阐述。
(1)事前联络型。对于此种类型,实践中认定成立受贿罪共犯基本无异议。例如:国家工作人员甲与妻子乙商定,在甲利用职权为某房地产开发商丙拿到市中心区附近的一块商业用地之后,由妻子乙出面收受丙送予的好处费10万元。此种类型,特定关系人(妻子)与国家工作人员对实施受贿罪“为他人谋利”和“收受财物”的实行行为均具有事前的沟通和联络,属于典型的事前通谋,应认定二者具有共同的受贿故意,成立受贿罪的共犯。
(2)事中明知型。此种类型要求特定关系人在收受他人财物时,对国家工作人员为他人谋利的事实明确知晓。此时,特定关系人收受请托人财物的行为是基于对受贿罪另一实行行为(为他人谋利)的认可,属于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对受贿罪“为他人谋利”和“收受财物”两个实行行为均具有意思联络的情形,应认定为二者具有共同的受贿故意。如上例中,如果国家工作人员甲利用职权为丙拿到市区某商业用地后,将此事告知妻子乙,并安排乙收受了丙送予的10万元好处费,此时,妻子乙明知甲为丙谋利的事实,仍收受请托人丙送予的好处费,属于典型的事中通谋类型,应认定妻子乙与甲具有共同的受贿故意,进而认定二者成立受贿罪的共犯。
(3)事中不明知型。所谓“事中不明知”是指在特定关系人收受请托人财物时,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对他人谋利的事实不明知,对此,是否应认定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共同的受贿故意,即是否属于“事中通谋”。如上例,如果妻子乙在收受请托人丙送予的10万元好处费时,对国家工作人员甲是否为请托人丙谋利并不知情,甚至说,妻子乙仅是按照国家工作人员的安排收受了请托人送予的财物,或者被动的接受请托人送予的财物,这种情况下,是否仍要认定妻子乙与国家工作人员甲具有共同的受贿故意?对此,我国刑法学界及实务部门有不同观点(下文详述)。
(4)事后推定型。此种类型主要是针对《解释》关于受贿罪共犯的特别规定所做的一种界分。上文论述了成立此种类型的受贿罪共犯,是因国家工作人员未履行特定的监督、退还义务,而推定其具有受贿的故意,进而与特定关系人成立受贿罪共犯。该种类型是以国家工作人员对特定关系人实施的收受财物行为具有事后明知(意思联络)为内容,此有别于上述以特定关系人对国家工作人员为他人谋利的行为是否具有意思联络的类型。虽然该种类型将认定“通谋”(共同受贿的故意)的时间进一步延伸了⑨,但在具体认定中却不存在多大疑问。
不难发现,上述对受贿罪共犯主观要件的认定,除“事中不明知型”在实践认定中可能存在不同观点,其他几种类型在认定中均不存在多少疑难。对“事中不明知型”受贿罪共犯主观要件的认定,实际上是对“事中通谋”成立范围的界定,所要解决的是实践中常见的“特定关系人单纯收受请托人财物是否可认定具有共同的受贿故意,进而成立受贿罪共犯”这一类型性问题。在理论上对该问题进行释清,对于实践中准确认定此类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2.受贿罪共犯疑难点的争议分析
特定关系人单纯实施了收受请托人财物的行为,但对国家工作人员是否为他人谋利不知情,对于此种类型应如何认定,我国刑法学界和实务部门有不同观点。张明楷教授认为,虽然(国家工作人员与第三者)没有事先通谋,也非同时在场,但第三者接受财物时,明知请托人提供的是某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正当报酬,对此应以受贿罪共犯论处(即具有共同的受贿故意)[9];林雪标副教授认为,(特定关系人知道是不正当报酬而收受的)从实质上来看,该特定关系人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接受贿赂物,而是作为工具被使用,仅仅是代为收受[10],因此不能认定其具有共同的受贿故意;熊选国教授认为,配偶、子女明知他人所送财物系国家工作人员为他人谋取利益所得而代为收受,但事先没有教唆或帮助行为,或者明知系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所得而与其共享的,属于知情不举,不能以受贿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责任(即不具有共同的受贿故意)[11]。
张明楷教授基于承继的共犯理论,认为在国家工作人员实施了为他人谋利的实行行为之后,因受贿犯罪未终了,特地关系人明知请托人送予的财物系贿赂物而收受的,属于以共同犯罪的意思参与实行的行为,因而在理论上属于承继的共犯类型,应当认定特地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共同的受贿故意,进而成立受贿罪的共犯。张明楷教授的论述是对受贿罪共犯理论层面的一种论证,但理论上对受贿罪共犯的认定并不必然与我国关于受贿罪共犯的规范性规定相一致。上述类型在理论上构成承继的共犯无疑,但在规范层面成立受贿罪的共犯需要具备“通谋”要件,而对“通谋”的认定不仅需要特定关系人明知其所收受的财物系国家工作人员的不正当所得,而且还需要对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利的事项具有一定意思联络。
而依据林雪标副教授的观点,上述类型中,特定关系人之所以不构成受贿罪的共犯,其理由是特定关系人收受贿赂物的行为实质上属于代为收受的行为。何为代为收受的行为?乍听有理,实则难以认定。本文认为不存在所谓代为收受的行为。因为,第一,如果从贿赂物的本质来看,贿赂物系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正当报酬,那么,不论特定关系人是主动收受还是被动收受都可以认为是代为收受,不能作为认定双方是否具有共同受贿故意的依据;第二,特定关系人只要收受了贿赂物,便完成了收受财物的实行行为,即已说明收受财物是个人所实施的自愿的行为,因为在收受贿赂物的过程中,其并未受到胁迫,完全可以拒绝。因此,对于特定关系人来讲,只有收受或者不收受贿赂物的问题,不存在个人收受或者代为收受贿赂物的问题。相关学者抛出“代为收受”的观点,无外乎是想从侧面对行为人是否具有共同的受贿故意进行认定,但该观点只能说明行为人收受贿赂物是否具有主动性,并不能以此对受贿罪共犯成立的主观要件进行认定。
另外,依据熊选国教授的观点,在实践中对受贿罪共犯的认定则过于严苛且不符合受贿罪共犯的相关规定。首先,特定关系人如果明知他人所送的财物系国家工作人员为他人谋利所得而代为收受的,即表明特定关系人不仅明知其所收受的财物系国家工作人员的不正当所得,还对国家工作人员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事项知晓。据此,即已说明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具备成立受贿罪共犯的主观要件,应成为受贿罪的共犯,而非论者说所说的不成立受贿的共犯;其次,依照上述观点,则基本排除了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成立“事中通谋”的情形,如此,实践中大多数特定关系人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事例,便不成立受贿罪的共犯。如上例中,妻子乙明知国家工作人员甲为请托人丙谋取利益的事实之后,仍按照甲的安排收受了丙送予的财物,本属于典型的“事中通谋”而构成受贿罪共犯的情形。但依照上述观点,该事例亦可归入“配偶、子女明知他人所送财物系国家工作人员为他人谋取利益所得而代为收受(且没有教唆或帮助的行为)”的情形,而不能认定妻子乙构成受贿罪的共犯。如此明显不妥;再次,依据相关规范,对受贿罪共犯的认定,以成立共同的实行犯为基准,特定关系人是否事先有教唆或者帮助行为,不是成立受贿罪共犯的必要条件。
3.受贿罪共犯疑难点的释清
上文分析了受贿罪共犯主观要件认定的疑难点,即在特定关系人单纯收受财物,而对国家工作人员为他人谋利的事实不明知的情况下,是否可认定其与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共同的受贿故意,进而成立受贿罪的共犯。对该问题的认定,所要解决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对“事中通谋”范围的界定。笔者认为,需要在现有规范的基础上,通过对相关典型性案例进行分析,得出认定“事中通谋”的一般性规则。
实践中,办案机关对“事中通谋”进行认定,往往仅以对特定关系人收受请托人财物的行为具有认识为必要,进而推定其与国家工作人员在为他人谋利的事项上具有意思联络,而成立“通谋”。如上例中,只要妻子乙实施了收受请托人财物的行为,在实践中一般会倾向于认定妻子乙与国家工作人员甲构成“通谋”而成立受贿罪的共犯。推定的一般逻辑为:在妻子乙收受请托人丙送予的10万元好处费时,其应当能够认识到所收受的财物系国家工作人员甲职务行为的不正当报酬,同时结合丙的身份(房地产老板),也应当能够认识到国家工作人员甲为请托人丙谋取了利益或者请托人丙对国家工作人员甲职务行为有所请求(因为请托人不可能无缘无故地送予如此大额财物)。按照此种认证逻辑,办案机关便可推定妻子乙是在明知国家工作人员甲为请托人丙谋利的情况下而收受的财物。上述对“事中通谋”的认定方式,必然会不当扩大特定关系人成立受贿罪共犯的范围。
为更好地指导实践办案,将办案机关认定“事中通谋”的逻辑思路限定在规范可控的范围之内,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刑事审判参考》第1143号案例(罗菲受贿案),对“事中通谋”作出了界定:虽然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事先未就为请托人谋利并收受财物形成共同的犯意联络,但其对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的事实明知的情况下仍代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物,应认定与国家工作人员具有通谋。应当说,该指导性案例对“事中通谋”的认定具有合理性,是对“通谋”实质性解释的一种规范性认可。依据该解释,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构成“事中通谋”,必须以其对国家工作人员为他人谋利的事实明知为内容。按文理解释,这里所要求特定关系人“明知”的内容(即“为他人谋利的事实”),应是一种具体的事实、特定的谋利事项。据此,不论办案机关如何推定,只要特定关系人对相关谋利的事实不明确知晓,便不能认定其与国家工作人员构成“通谋”。如此界定,的确能够规避实践中对“事中通谋”随意进行认定的风险。但据此能否作为办案机关认定“事中通谋”的可行性规则,进而恰当处理“特定关系人收受请托人财物是否构成受贿罪共犯”这一类型性问题呢?笔者认为,仍有不妥当之处。
其一,与相关典型性案例的认定不一致。《刑事审判参考》第1143号案(罗菲受贿案)的解析明确指出,(之所以认定罗菲和张曙光具有“通谋”是因为)罗菲对于请托人杨建宇与张曙光(罗菲情夫)之间具有请托谋利关系知情⑩,结合案情可知,在罗菲收受请托人杨建宇送予的相关财物时,其并不知晓张曙光具体为杨建宇谋取了哪些利益,对张曙光为杨建宇谋利也仅能推定其大概知晓。该案的一审判决更是明确指出,虽然现有证据不能认定作为特定关系人的罗菲除收受财物外,还向张某(张曙光)转达请托,或者帮助杨某(杨建宇)从张某处获得利益……也不能认定罗菲对杨某直接向张某请托的事项及张某实际为杨某提供帮助的事项知情,但认定特定关系人罗菲构成受贿罪共犯不以此为必要。其二,对于解决“特定关系人收受请托人财物是否构成受贿罪共犯”这一类型性问题不具有指导意义。如果将特定关系人“明知”的内容限定为一种具体的事实、特定的谋利事项的话,则相关典型性案例对“事中通谋”并无解释的必要,因为按照共同犯罪的原理及对相关规范的解释,在特定关系人明知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利的具体事实后,仍收受请托人财物的,可当然的成立受贿罪的共犯。依此界定,便将“事中通谋”的成立仅限定为双方均对谋利事项明确知晓的情形(上文“事中明知型”),而对于一些特定关系人收受请托人财物,但对谋利事项不明确知晓的情形,即便是能够合理地推定其对谋利事项明知,亦不能认定特定关系人构成“通谋”而成立受贿罪的共犯。其三,实践中大多数案例,特定关系人仅对所收受财物性质的非法性有所认识,对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具体谋取了哪些利益是不明知的。要求特定关系人对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利的具体事项明知,不具有现实性意义。
因此,在实践中对特定关系人是否构成“事中通谋”进行认定时,应作实质性把握,即以特定关系人对国家工作人员为他人谋利的事实具有明知作为认定其二者构成“事中通谋”的必要内容,但在对“明知”内容的界定上,应将“为他人谋利的事实”解释为一种概括性事实,并以此作为特定关系人“明知”内容的最低限度。所谓“概括性事实”,是指该事实具备部分构成要素,并能够通过所具备的构成要素对事实的内容进行合理性地推定,其强调对相关事实进行推定必须具备合理的依据,而合理的依据又必须是指特定关系人对国家工作人员为他人谋利的部分事实要素知晓,如对国家工作人员在哪些领域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知晓、对请托人所请托的事项大概知晓等。如上例中,在妻子乙收受请托人丙送予的10万元财物时,如果其大概知晓国家工作人员甲在商业用地领域关照过丙,或者丙曾在某次宴请甲、乙一起吃饭的时候,说过希望国家工作人员甲对其在商业用地领域给予关照等,如此,便可推定乙对国家工作人员甲为丙谋利的事实具有明知,进而认定其与国家工作人员构成“通谋”。相反,如果妻子乙在收受请托人丙送予的财物时,对请托人丙的基本情况、请托及谋利的相关事项均一无所知,仅能够推定其所收受的大额财物是国家工作人员的不正当报酬,但无法通过既有事实来推定国家工作人员是否为请托人谋取了利益,如此,便不能认定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构成“通谋”。
四、结语
受贿罪共犯问题历来是理论界和实务部门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学者们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受贿罪共犯问题作出理论阐释和实践论证,但相关研究必须以受贿罪共犯的既有规定为依据,并以指导实践办案为目标。我国关于受贿罪共犯的相关解释规定与受贿罪共犯的传统理论界定并不严格类同,对受贿罪共犯理论界定的范围要宽于规范认定的范围。因此,在实践办案中,要避免单纯以共犯理论来指导对受贿罪共犯的认定,而是要依据受贿罪共犯的既有规定,明确受贿罪共犯的成立范围。
受贿罪共犯实践认定的疑难点是对其主观要件的认定,即对“通谋”的认定。受贿罪作为复行为犯,对“通谋”的认定应突出行为人在“为他人谋利”和“收受财物”两方面的意思联络。据此,在处理“特定关系人收受请托人财物是否构成受贿罪共犯”类型性问题上,明确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具备“通谋”的条件是特定关系人对国家工作人员为他人谋利的事实明知,是符合刑法理论和规范要求的。但在对“明知”内容的具体认定上,既不能是毫无事实根据地凭空推定,也不能苛刻地将认定标准限定为具体的事实、特定的事项,而是应该以特定关系人对国家工作人员为他人谋利的“概括性事实”具有明知为依据。当然对“概括性事实”的认定最终仍需结合具体案件事实来把握。
注 释:
① 《纪要》所规范的主体是近亲属及近亲属以外的人;《意见》所规范的主体是特定关系人及特定关系人以外的人。而特定关系人的外延要明显大于近亲属。
②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刑事审判参考》,总第106集,法律出版社2017版,第50页。
③ 如马克昌教授认为,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实行某一具体犯罪客观要件的行为,在刑法理论上叫共同正犯(共同实行犯)。参见马克昌《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25页。
④ 我国理论通说认为,所谓实行行为,是指实施符合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某种具体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参见马克昌《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0页。
⑤ 由于《意见》中所规定的“特定关系人”的范围要大于《纪要》中所规定的“近亲属”的范围,且更具合理性,为下文论述方便,统一以“特定关系人”指称。
⑥ 国外立法及刑法理论一般将共犯参与正犯实施犯罪的行为称为“加功”,包括教唆、帮助行为。
⑦ “意思联络”作为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具有“通谋”的认定内容,在具体认定中(尤其是对“事中通谋”的认定),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行为人双方对彼此所实施的受贿罪实行行为的一种明知和认可。
⑧ 如果国家工作人员对于非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物的行为不明知,则国家工作人员便不具有受贿的故意,即不成立受贿罪。如此,认定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成立受贿罪共犯的前提便不复存在了。
⑨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刑事审判参考》,总第106集,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52页。
⑩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参考》,总第106集,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