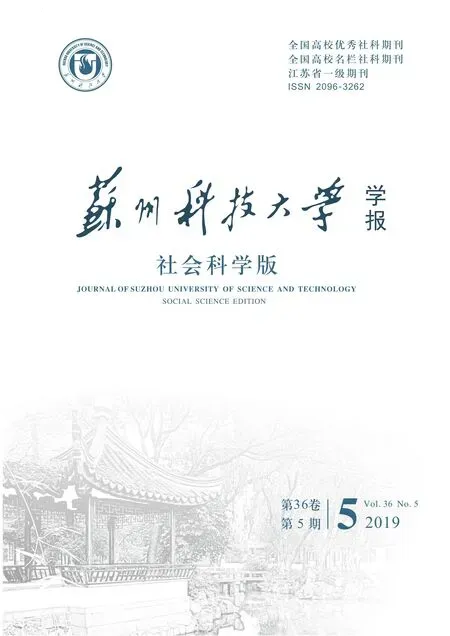如何建立跨学科知识培养体系*
——以PPE教育为例
马翰林(苏州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近年来中国教育界在如何培养实践型人才、跨学科人才以及有专业性的领导人才等问题上多有讨论。这三类人才往往相互关联,其中实践型人才为现实问题服务,复杂的现实问题往往涉及多个学科,而统合多个学科需要有跨专业背景的领导力,由此这三类人才实际上可以统合为一种人才。而具备这三种能力的人才正是创新力量的核心,也是影响我国产业转型的决定性力量,所以笔者称之为“创新型人才”。如何通过系统的教育体系培养这样的人才呢?目前看来问题多多,有的人只注重创新性的某一个方面(如跨专业性),忽略了创新的复杂多维;有的人或许注重了创新的各个方面,但在如何统合多维的问题上却缺乏有学科发展历史经验的研究根据,只是凭借所谓的知识结构关系来判断学科的关系。笔者以一个恰恰旨在同时培养这三项能力为目标的人文社科领域的综合性学科——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简称PPE)的教育发展史为例进行探索:该学科如何通过科学知识结构的磨合以及制度的建设致力于保障所培养人才的多学科综合性、博雅情操(领导力)以及问题意识。
PPE最早由牛津大学于1920年代创办,目前是牛津很受欢迎的专业之一。PPE由三个学科支撑而成,立足于培养学生广博而深入的认识世界、思考问题的能力和一定的解决问题的能力。于这个属性,PPE培养了大量政治领袖、企业家、主编、优秀学者和教师等。而在通识教育、博雅教育的春风之中,我国的高校也开始引进PPE概念,构建有着中国特色的PPE教育。PPE教育理念的引入或许会成为中国高等教育通识化改革的突破口。同很多教育界的研究者不同,笔者认为国内在通识教育或跨学科人才培养方面最欠缺的不是制度建设(虽然这个也非常重要),而是对具体的跨专业性质的学科知识结构与学科间相互作用缺乏高屋建瓴的认知框架——笔者称之为“内涵分析”。而PPE教育在这个问题上非常明确,那就是“博雅为本,通识为体,哲学为导,‘异质创新’”。所谓“异质创新”指的是它更能容纳被具体的某个专业性学科(如经济学)的保守势力所不容的异质性人才或理论,这种创新往往是跨范式的[1],因而是带有哲学性的。
一、 PPE的内涵
只有深刻理解一个学科教育的内涵性,才可能真正有效地推行一种有深刻内在价值的高等教育,而这恰恰是很多人在建构高等教育学科设置时所忽视的。PPE教育对这一点(理解内涵)的要求尤其高,所以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范例来对待。PPE的内涵分析着重讨论:一是PPE教育的宗旨和性质;二是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三大学科在PPE教育理念下是如何建立相互之间的有机联系的。
(一)PPE教育的宗旨:情操、能力与知识
从历史上来看,PPE缘自博雅教育或古典教育或经学教育。1920年,在牛津大学,林赛(Lindsay,当时牛津的副校长、贝列尔学院的院长)等校董委员会成员推动了PPE的建立。建立PPE的原因大概有三个:一是原先的古典哲学教育的师生数量因战争缘故急剧下降;二是各种社会科学如经济学开始在大学中崭露头角;三是一战之后英国的国情要求出现新型的政治人才。原因二和三导致战后回归校园的学生和学者都倾向于进入时兴的新学科,如经济学领域。[2]30由于被哲学和古典学领衔,PPE最初建立时的基本格调还是博雅教育。博雅教育主要以学习古典人文学(literae humaniores)和哲学经典(统称经学)为主,要求学生具备较强的古典语言、文法和古典思维功底。此外,它还有帮助学习者修身之用,如《西塞罗三论》就一直是英国中上流社会青年的必读书目,被认为可培养青年的崇高情操。PPE开始时被称作“现代经学”(Modern Greats),因为它的底色是古雅智慧与道德情操。
PPE的诞生还来源于其他一些原因。在当时,牛津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有各自的诉求。哲学和政治学希望能够摆脱古典学的束缚,成为一种更加现代的学科,而经济学希望提升自己的地位和市场,如此便一拍即合。此外,PPE的定位是一个优等学位课(Honour School),毕业者将会获得荣誉学位(Honours Degree)。这是牛津本科教育六个等级中的最高等级,也是培养精英学员和提升学科实力的一个重要途径,所以PPE各领域的教育者都很重视这个机会。由此可见,PPE的起源是牛津哲学做的一次哲学教育现代性转向实验:由传统的博雅教育平稳转向现代的通识教育。但当时的哲学家将经济学和政治学当作哲学自身的一种当代经验路径来对待,而不是与哲学不同的学科。[2]36所以在他们看来,PPE并不是旨在建立一个联合三大社科专业的跨专业学科,而是在建立一个由哲学统摄的新型(现代)哲学性学科。经济学家们对此颇为不满,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著名的LSE经济学系领导者)曾在一次经济学讲座中评论道:
(现代经学)已经趋向于陷入泥沼,就是因为它被一帮哲学家把持,他们中的一类人过于自信于自己的学科(被)赋予了一种统摄一切(或近乎一切)的精神统摄力,而从来不顾及他们自己的水平或者技术资格。例如,听说J. A. 史密斯,一个道德哲学教授,却在司职经济学方法论的教学,而他对这方面一无所知!还有比这更荒谬的吗?[3]35
之所以经济学家会产生这样的感觉,是因为相比哲学,经济学是一门更加专门化的知识性科学学科;相比博雅教育,经济学更加注重经验性知识与数理分析技能训练。在PPE的开始阶段,经济学就已经力图为自己争取利益。1920年牛津就有经济学家提出使用“科学经学”(Science Greats)而不是“现代经学”作为PPE的别称,但是反响平平。牛津大学1917—1918年的学术年鉴显示,当时经济与政治科学的学位委员会已经开始提议将经济学作为所有学生的必修专业。[4]9所以,牛津经济学家自然反对哲学方面关于PPE的建设理念。以哲学家为主导的人文学委员会提议的考核论文要求(9篇)中有6篇是关于近代(1760年以后)哲学的,经济学(4篇)并没有被安排到核心位置,而政治由于同道德和政治哲学有很大的交集,所以也具有很强的覆盖性。[2]33这个提案遭到牛津经济学家的反对。经过反复讨论,联合委员会以95票对58票通过了PPE的终极优等学位课(Final Honour School)规则,获得PPE的学位至少要完成以下方向的论文:(1)道德与政治哲学;(2)1760年以来的英国政治与宪政史;(3)1760年以来的英国社会与经济史;(4)笛卡尔以来的哲学史;(5)政治经济学;(6)以下领域专著研究三选二,形而上学与道德哲学、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7)一个进阶的哲学、政治或政治经济学研究;(8)至少从英、法、意中三选二,能够做到无准备翻译。[2]38
由此可见,哲学家们关于PPE的设想目的基本达到,拉丁文从毕业要求中被排除(到1933年不再做语言要求)[2]39,标志着博雅教育中颇占时间的语言修养教育被排除在外,这无疑为平民子弟入学PPE提供了更好的条件。由于学业的工作量极大且涉及领域广泛,对学员的读写能力提出非常高的要求,所以在客观上PPE至少是一个高度重视现代语文功夫的能力教育——这对博雅哲学教育也很有利。此外,经济学论文的比重也增加到5篇左右。所以,这是一个对哲学更有利且相对平衡的课程设计。虽然这个宗旨的出台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一直沿用到现在。当下PPE的设计者沿用该思路的理由是,希望利用哲学的博雅元素来制衡功能化学科对人的异化。因此,虽然存在大量的例外,但在目前看来世界上大多数的PPE依然是由哲学领衔(我国也是如此)。
随着不同学科要求的能力越来越专业化,这个早期的PPE教育课程设计必须做出修改,由此,通识教育的选修制度开始同PPE结合起来。例如,牛津PPE对经济学的要求越来越多,而且紧跟时代。起初是以教授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为主,还有如纪德(Gide)的《原则》(Principle)、尼克尔森(Nicholson)的《原理》(Elements),以及之后加入的亨德森(Henderson)的《供给与需求》(DemandandSupply)、莱费尔特(Lehfeldt)的《金融》(Money)、道尔顿的《财政学》(PublicFinance)。经济学的专业化加强意味着平均主义的教育无法在PPE继续贯彻下去,当时有批评认为这种教育会使学员成为泛泛而谈的空乏之辈。于是,1931年牛津不得不再次做出调整,允许学生在PPE的三个族群中选取两个方向进行研究,而不是全面发展。今天的牛津也只要求学生在众多主题中选取一个作为毕业论文的主攻方向。从这个角度来看,PPE被动地成为一种泛艾略特教育。后来在美国建立PPE的大学往往直接将PPE同艾略特选课制度相对接。PPE教育由此开始成为一种“自由教育”,也就是所谓的通识教育。自由教育的自由性正是来自选课制度。
一般而言,人们往往认为直接在PPE的不同学科之间建立知识上严格的逻辑关系是不可能的。而有些人或许不这么认为,因为后来诸如哈耶克这样横跨哲政经的大师或者诺斯的法经济学的出现,似乎可以证明厚重的经典性学术力量对于经济学发展的反哺。然而这未必是因为这些大师受到了类似PPE这样的学科体系的培养。首先,这些人和PPE的关系并不密切——尽管邀请哈耶克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的罗宾斯曾经在牛津教授过PPE的课程,但他对PPE颇有微词[3]111,127-130。显然,哈耶克与经济学的关联要比同PPE的关联大得多——虽然他是一个集哲学、政治和经济学三系为一体的大学者。所以,后来的这些交叉理论与PPE的关系只是间接的。其次,早期的PPE对经济学界发展的影响不是直接的(培养经济学家),而是间接的(为“异质性”创新力量提供空间)。其实早在1936年凯恩斯出版《通论》的时候,PPE就已俨然成为一个经济学学科教学与知识发展的直接助力。1936—1939年,牛津PPE最早将《通论》加入研读书目,牛津的经济学家反而比剑桥更加迅速地接受了凯恩斯的“新经济学”[4]87。这与PPE始终强调对经济学的理论性研究与思想性的侧重是分不开的。综上,即便期许PPE直接出产哈耶克那样的综合型大师未必是一个必然的诉求,PPE对经济学的间接影响确是实实在在的。PPE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与它同时强调博雅与通识教育有关:没有博雅追求的一般专业往往不会有足够的宽容性接纳新范式下的经济学理论,只有通识教育的选课制度才能保障学科教学的实施以及相对稳固的专业性。
通过PPE在牛津前20年的发展史介绍,我们可以看到PPE内部三种力量的相互制约与相互促进。这三方力量,人们通常以政、经、哲三方为单位来划分,而笔者建议以博雅教育(培养情操与思想)、能力培养教育和知识技能教育来划分。很少有学科会像PPE一样试图在一个学历中平衡并同时实现这三种教育。我们可以看到,思想性教育(如哲学教育)与知识专业化教育(如经济学)在一定的条件下是有矛盾的:思想性学科会陷入理性的自负,妄图凌驾于知识性学科之上,很容易成为空中楼阁;而知识性学科教育如果不注重思想就会沦为培养知识工匠的低等学科。能力培养教育则可能为双方中的一方服务,它会是一个放大镜,将一方的优势或劣势放大——不同的学生对不同能力(如数理计算、逻辑推理与语文写作)的重视和掌握程度不一样,会导致他们走向不同的学科偏向。从凯恩斯主义在牛津的传播来看,虽然PPE经历了阵痛,但是坚持知识与思想结合的理念保证了PPE的某种统一性与建设性。
(二)PPE与哲政经学科交叉
首先要明确一个问题,即“学科交叉”与“交叉学科”的区别。所谓的学科交叉,在这里主要指建立PPE三个学科之间的公理化或知识性的普遍联系,这种联系往往是在学科有共同重叠点的前提下建立的。所谓的交叉学科——比如政治经济学——却很难澄清这样一种联系。换句话说,所谓的交叉学科的“交叉”往往只是一种模糊的说法,因为我们无法给出明确的标准来说明一个学科是否与别的学科“交叉”了。
根据当代著名的PPE研究者与设计者杰拉德·高斯(Gerald Gaus)等人的观点,自杰文斯(Jevons )和瓦拉尔(Walras )将微积分引入经济学分析之后,经济学和哲学、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就分道扬镳了。这直接导致了经济学同哲学、政治的研究对象会有差别,因为很多政治上的价值是无法进行量化分析的,而由于研究模型的局限,经济学关于人类社会的很多模型也过于理想化。[5]2-3此外,放弃寻找PPE三科的重合点已经成为PPE界同仁的共识,由此可以推断建立严格的三科联系是不可能的。但是一些“家族相似”性的联系(源自维特根斯坦的一个哲学概念)却存在,比如现在被绝大多数学校的PPE强调的博弈论就同时被哲政经三科重视,只不过它们各自的侧重点和方式不同。
关于如何理解PPE三科的关系,至少有三种观点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观点一:高斯提出的“收敛式”,即在不同的学科之间建立一种“家族式”的关系,将它们收敛在一起。家族中成员之间的关系并不需要总是和谐的,我们可以从某种系统的观点来看待它们这个整体,建立它们之间复杂的有机性关系。这一点从他和一些PPE或哲政经学者共同撰写的一本PPE论文集的各部分主题之间的关系就可以看出来。该论文集从内容上分六个部分,它们分别处理六个问题:(1)人类价值和理性在经济分析中地位;(2)经济应得与我们对于经济收入的评价的关系;(3)经济的效率标准如何与其他价值建立联系;(4)作为选举人的基本经济模型与自主性、共识性的道德观念之间的关系;(5)当我们不只是简单地考虑当下而是也要考虑后代人的时候,我们的道德标准要如何被动态地应用;(6)来自经济学和伦理学的洞见如何帮助我们更好地规划公共政治。[5]4
观点二:来自经济哲学家乔佛里·布雷南(Geoffrey Brennan)的“统分式”。布雷南是杜克和北卡教堂山大学的联合PPE项目(简称Duke/UNC PPE)的缔造者,他认为:“政治学作为一种研究,而哲学和经济学则提供工具,帮助我们在不同的政治体系之下来说明、预测和评价人的行为。”[6]可见,布雷南并没有将哲政经当作平行的三个学科,而是将它们进行了分层处理,视政治为PPE的核心研究内容,而将(道德)哲学和经济学当作方法论来对待。
观点三:来自笔者所称的“批判式”。这个名称受到法理学理论中将马克思的理论称为“批判理论”的启发。所谓的批判理论,其特点是以解构为主,而不是建构。换句话说,笔者认为,PPE三科之间可以互相构成批判关系。这种关系的主要作用是帮助学习者认清其中任何一科的局限性。这种观念有一定的局限,它往往比较适用于那种“主辅模式”的PPE,即学生会选择以某个方向为自己的主攻方向,其他方向只是充当辅助性知识。而这里的辅助性就是帮助学习者认清主修科目的缺陷所在,从而能有更加广阔的视野来面对它。
以上三个观点并不完全互相抵触,在建设一个PPE学科的时候完全可以将它们综合运用。在PPE的另外一个重头戏——上文提到的所谓“交叉学科”中,这三个观念更是容易被杂糅在一起,分不清你我。这里所谓的交叉学科在更多的时候也指一些“具体的学科领域”。乔纳森·诺姆利(Jonathan Anomaly,Duke/UNC PPE的核心成员)和乔佛里·布雷南等人在2016年出版了名为《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一本选集》[7]的教材,这是市面上唯一一本PPE专业选集读物。该书第十三章“边缘地带的市场”广泛讨论了“性服务”“毒品”“器官移植”“哄抬物价”“血汗工厂”等交叉学科课题。美国大学最新的PPE项目往往会开设两种核心课程:引路课程(Gateway Course)和顶点课程(Capstone Courses)。著名的宾夕法尼亚大学PPE项目的顶点课程,除了有“公平与利他”之外,还有“关于腐败和犯罪的经济学”这样的专门性领域研究[8]。这种交叉学科在PPE的研究生教育中更加多见。例如,德国维藤/黑尔德克大学(Witten/Herdecke Universit)的PPE研究生教育提出,他们并不注重各自单独的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传统教学,而是把教学重点放到“全球化”“气候变化”“贫困问题”“世界公民”“未来世界社会”等主题上。
PPE看上去是一门被设计出来的学科,而不是直接由知识部门衍生出来的学科。其实,我们应将其看作一门在知识部门的蜕变过程中由种种因素促成的学科,而不应简单地将其看作一个跨专业学科。它试图始终保持对知识源头性的尊重,同时希望这一点能够对知识本身的历史变革起到本质性的启示作用。鉴于这一点,PPE培养过的人成为质量惊人的哲学家也就不令人惊奇了[9]。
二、PPE的外延
英美大学学科教育的成功往往要依靠大学的制度性条件,PPE也是如此。我们关注的是,PPE旨在同时适应西方的博雅精神与现有的通识教育制度的课程设置。所谓的通识教育又称“自由教育”,其实古典的博雅教育本质上是(另)一种自由教育,只不过通识教育更加注重所谓的“现代人的自由”,而博雅教育更加重视“古代人的自由”。艾略特改革之前,在博雅教育中学生所学的只是古代的人文经典以及古典语言等少数经典。古人并没有选课的自由,但是由于这些经典精深广博、格调高雅,使得学生获得了一些自信的德者和强者意识,这种自信对于责任感和荣誉感的培养是至关重要的。现代通识教育则建立在自主培养和自主选课的基础上,鼓励学生根据兴趣来培养自己。如果说前者是培养一种“荣誉意识”,那么后者则是在培养一种“民主意识”。PPE试图同时强调这两者,尽管PPE不再强调古典语言的研习,但是从来没有轻视过对古典文献的研究。当代PPE研究者牛津大学的伊丽莎白·弗雷泽(Elizabeth Frazer)与约克大学的马丁·奥尼尔(Martin O’Neill )于2016年着重强调了博雅教育对PPE的重要性,认为“不能向技术官僚和技术人员退缩”[10]。PPE被认为是用来平衡过于功能化的现代自由精神和有可能产生非理性激情的古代自由精神的学科。
关于PPE的课程设计,在牛津大学PPE官网上可以找到一本100页的学生手册[11],其中有详细的对应信息。牛津大学PPE大概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不同学校对这两个阶段的解释不一样,但是功能性质是一样的。第一阶段是在入学的第一年,学生将学习一些核心基础课程,哲政经三门都必修,其中:哲学课程为概论、道德哲学、逻辑学;政治学课程为政治学理论、政治学实践、政治分析;经济学课程为宏观和微观经济学。在PPE的第二年会进入第二阶段,学生可以在三门核心课程中选择两门,或者继续选择三门兼修。此外,必须在牛津各个学院开设的选修课程中选修一定数量的更加专业的课程。第一阶段学生的学习会以博雅教育为主,需要阅读大量古典文献,这个阶段最终会以一次预备考试作为检验,以确定学生是否有资格进入下个阶段的学习,从而最终获得终极优等学位;第二阶段的学习被要求聚焦于某个具体的研究领域,不可空泛。这种学制安排很好地兼顾了博雅教育与专业教育。
三、 PPE在中国
由于PPE属于广义的通识教育,而且同其他专业相比更加依赖通识教育制度的建立,所以,PPE目前最大的困难自然来自通识教育推动中遇到的难题。甘阳在《大学通识教育的两个中心环节》中提到,中国通识教育进程的两个阻碍依然存在:一个是共同核心课程制度,另一个是助教制度。[12]核心课程的问题可以分为两点:一是我国高校除了专业核心课程之外,还有一些非知识导向的公共必修课程占据了大量的课程比例;二是通识教育课程被理解成一种“素质教育”而不是知识教育,成为“第二课堂”。这些以“概论”形式构建起来的趣味性简单课程成为“饭后的小甜点”[12]。关于助教制度,则直接同中国大学的师生人员比例以及助教系统建设等问题相关。后者是更加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师生比的条件差距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弥补,而助教系统的建设问题却始于理念。中国的985高校和211高校中,多数学校的师生比往往可以达到兴办通识教育的要求,却依然办不好通识教育,这或许就与此有关。有观点认为,中国的研究生生源水平往往要低于本科生。然而,这并不构成不设立助教制度的理由,在基本能力具备的情况下,助教的效力往往取决于助教督导(往往是研究生的导师)的辅导设计和安排。一般而言,研究生的导师应将辅导内容同助教自己的研究方向结合,让助教与学生平等对话、教学相长。综上,助教制度、公选课的制度设置、知识质量的评估、教学的薪酬激励机制等等,这些看似都是一些“外延”的问题。
然而笔者认为,在我国推行通识教育以及PPE教育的最大困难还是在对于“内涵”的理解层面。虽然外延很重要,但是中国高教界并不是没有条件去逐步改善环境和制度,提高办学条件。过去十年是中国通识教育大兴土木的十年,中国高教界在该问题的推行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是存在着大量的问题。中国著名的高校,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等,都建立了博雅型的教育学院,这种模式被各地方高校争相模仿,风潮一时间席卷全国。可是这种方式是否真的适合通识教育在中国的发展?人们对此依然有不少质疑。因为这些学院并没有受到广大人文社科界师生的欢迎。
问题主要有两点:一是很多博雅学院过于重视经典教育,而忽视了人文学科的当代转型——人文学科也出现了专业壁垒;二是来自各个学院的任课教师很难建立一个准确的理念来理解这些通识类的教育,也很难将这种通识教育看作自身专业的另外一种可能的存在形式。北京大学陈向明在2006年发表的《从北大元培计划看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一文中,详细阐述了北大通识教育在各个方面的问题,其中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观点:从“第一年通识,而后进入专业”的模式来看,这只是人为地划分了通识和专业的时间区间,进入大二之后,学生又开始了专业教育,这导致很多学生进入元培实际上是为了选择自己想去的专业,而并不重视大一的通识教育。[13]
摆脱这一困境的方法是存在的。仅仅就PPE这个专业来看,北卡和杜克的PPE教育或许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模板:开学的时候开设PPE的引路课程(人民大学PPE已经开设了这门课程),在PPE后期开设一些PPE顶点课程,这些交叉学科的课程一直贯穿PPE教育的始终,在维持专业性的同时,依然保持它的通识性。其实很多所谓的专业性学科到后期都会进入一些交叉领域,而传统专业主义会导致在这些领域中产生专业中心主义的风气——过于强调某个专业的方法和原则,而忽视其他专业,从而缺乏宽容性。而PPE培养的学员或许会避免这一心理。此外,这还要求人文社会科学的教育者在学习理工科专业化的同时,也应该学习理工科以问题为导向(无论是现实还是理论问题)的联合创新意识,通过真正有价值且有反思性的项目来推动PPE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