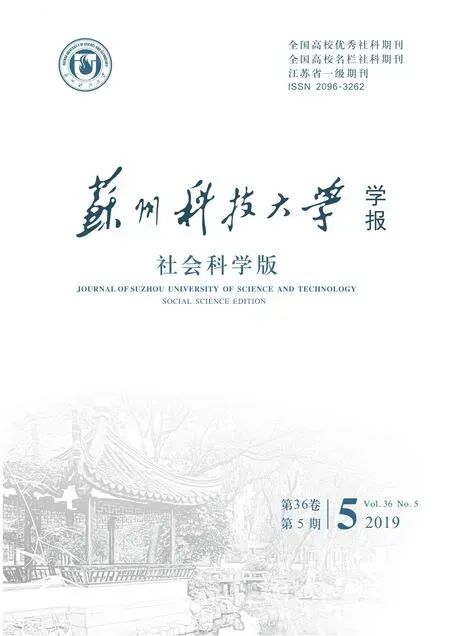都市背景下的他者想象*
——伍尔夫《岁月》中的“英格兰性”建构
綦 亮(苏州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相较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 1882-1941)的现代主义小说,国内学界对她的现实主义风格作品《岁月》(TheYears)的研究明显不足,不仅数量有限,而且视角比较单一,主要集中在女性形象塑造和女性成长主题等方面。(1)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可参见:梁雪霞《从〈岁月〉看伍尔夫的女性职业观》,《赤峰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第117~119页;徐晗、吕洪灵《弗吉尼亚·伍尔夫〈岁月〉对传统成长小说的继承与超越》,《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第127~132页。事实上,作为一部描绘英格兰半个世纪世事变迁的作品,《岁月》具有十分丰富的政治和文化内涵,而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它对英格兰民族身份,或曰“英格兰性”的再现。所谓“英格兰性”,就是英格兰作为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性,是英格兰民族身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表达。《贝奥武甫》《大宪章》、君主立宪制、工业革命、莎士比亚、白金汉宫、大本钟、板球,这些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其实都是英格兰民族身份的文化符码,是英格兰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标识。当然,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但从更加宏观的角度看,贯穿英格兰历史,同时也最能体现英格兰民族特性的恐怕还是英格兰的殖民主义传统。海外扩张和殖民征服是英格兰作为一个岛国生存和发达的重要保障,英格兰曾经创建了世界上最为庞大的殖民帝国,其民族意识的萌芽、确立和发展都与殖民主义密切相关。作为英格兰民族身份的集中表述和高度概括,“英格兰性”渗透着英格兰作为一个帝国的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意识。
大英帝国的由盛转衰是英国现代主义文学产生和演变的重要背景,因此大部分英国现代主义作家“都与帝国,以及与帝国相关的‘英格兰性’有密切的关联”[1],伍尔夫就是一个典型。伍尔夫的一生恰逢大英帝国从辉煌走向衰败的历史转型期,这种时代背景深刻影响了伍尔夫的文学创作,使其创作与帝国紧密勾连。恰如苏珊·斯坦福·弗里德曼(Susan Stanford Friedman)所言,对于伍尔夫这样“在大英帝国全盛期降生,在帝国衰退期死去的英国作家来说,帝国的故事自然占据其创作的中心”[2]。作为一名女性作家,伍尔夫竭力抨击基于男权思想的帝国和殖民意识形态,但作为一名来自中上层社会的宗主国白人作家,伍尔夫对帝国又有一种内在和自发的认同,有意识地在创作中彰显与帝国存续相依的“英格兰性”。本文意在解读《岁月》的民族身份认同主题,探讨在大英帝国由盛转衰的时代背景下,伍尔夫如何借助以伦敦为中心、吸纳爱尔兰和犹太人等民族和文化他者的权力关系网络,构建作为一种殖民主义话语的“英格兰性”。
一
作为首屈一指的世界级城市和国家首都,伦敦是大英帝国重要的文化地理符号之一,是英格兰民族形象的重要象征。从乔叟到莎士比亚再到狄更斯,一代又一代文学巨擘在对伦敦的艺术再现中抒写英格兰风貌,探微英格兰国民性,对英格兰民族特性进行了深层和多元的文化表达。伍尔夫生于伦敦的书香之家,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在伦敦度过,她的许多作品都围绕伦敦架构,“无论作为现代性宏大叙事的背景,还是作为故事细节描写的场景,无论是作为外在形象,还是作为潜在符号,伦敦都是伍尔夫城市文学叙述的一个重要依据”[3]。伍尔夫曾为《好管家》(GoodHousekeeping)杂志撰写介绍伦敦的系列随笔,后以《伦敦风景》(TheLondonScene)之名结集出版。从川流的伦敦码头到静穆的圣保罗大教堂,从繁华的牛津街到幽静的卡莱尔故居,伍尔夫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将整个伦敦的历史文化风貌勾勒得细致入微,钟爱之情溢于言表:
最刺激的事情莫过于观看船只沿着泰晤士河溯流而上——大船小船,黯然失色的,光彩照人的,来自印度的,来自俄国的,来自南美的,来自澳洲的,在经历寂寞、危险、孤独的煎熬之后,竞相从我们眼前鱼贯而行,前往港湾安家落户。[4]
在伍尔夫所有以伦敦为背景的小说中,最为人熟知和称道的无疑是素有“伦敦小说”之称的《达洛维夫人》(Mrs.Dalloway),这部作品深入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以全新的现代主义时空观赋予都市景观丰富的精神内涵。事实上,《岁月》对伦敦的再现力度是丝毫不亚于《达洛维夫人》的。如果说《达洛维夫人》是对伦敦的“共时”呈现,那么《岁月》则是对伦敦的“历时”书写,“小说以抒情怀旧的笔调娓娓讲述了这座城市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变迁,塑造了一个兼具精神质感和历史深度的都市形象”[5]。虽然再现角度不同,但就神韵和气质而言,《岁月》和《达洛维夫人》中的伦敦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岁月》中的叙事者对春夏之交伦敦的描写就非常有代表性:
在伦敦,已经可以感受到季节的脚步和压力了,特别是在西区,那里彩旗飘扬,手杖敲打着地面,各种款式的衣服粉墨登场;粉刷一新的房屋撑开了遮篷,盛有红色天竺葵的篮子随风摇摆。公园——圣詹姆斯公园、格林公园、海德公园——也都准备就绪。……往下来到公园巷和皮卡迪利大街,货车、小汽车和公共汽车沿街道行驶,街道好像狭槽一般,车辆开开停停,就像谜语破了又立一样,在这个时节,街道就是这样拥堵。[6]118
不难看出,这其实就是对《达洛维夫人》中那个达洛维夫人沉醉其中、沃尔什引以为傲的伦敦的重现。和《达洛维夫人》一样,《岁月》中的伦敦也是一个对英格兰人有巨大吸引力、能够刺激他们的官能、恢复他们的活力、使其产生认同和归属感的帝都。呼吸着伦敦柔和的空气,在穿行的巴士和熙攘的人流中,埃莉诺感到无比的自在和惬意:
这是她的世界;她在这里感觉如鱼得水。街道熙熙攘攘;商店里成群的女人拎着购物袋挤进挤出。她感觉有种习惯性和韵律性的东西在里面,就像在田头俯冲的乌鸦,起起落落。[6]68
《岁月》不仅纵览伦敦的城市风貌,还把“镜头”拉近,细致描摹那些镌刻着大英帝国历史文化记忆的著名景观,突出它们在伦敦城市空间中的位置。海德公园的祥和气氛让徜徉在其中的马丁和萨拉心旷神怡,“似乎一切都是新鲜甜美的。微风轻拂着他们的面庞,空气中弥漫着喃喃细语,可以感受到枝叶的颤抖和车轮的快速转动,还有犬吠声和不时传来的断断续续的画眉的歌声”[6]175。来到肯辛顿宫,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如名画一般的优美景色:
整幅画面的构图非常出色。在绿色的岸边矗立着维多利亚女王白色的雕像;远处是那座古老宫殿的红色砖瓦;幽灵般教堂的塔尖高耸入云,圆塘里荡漾着蓝色的涟漪。……怡人的微风轻轻吹过。[6]179
在马丁眼中,安妮女王的雕像巍然耸立、气度非凡,“就像轮子的轴心一样”[6]165,赋予原本混乱的街道以秩序。而雕像后面的圣保罗大教堂则更让马丁折服,这座伟大建筑的宏大雄伟深深地震撼着他的神经:
他体内的所有重量似乎都开始变动。他有种奇怪的感觉,好像他体内有什么东西在和着这座建筑的韵律移动;它纠正着自己:它停了下来。真叫人兴奋——这种比重的变化。他觉得自己应该当一名建筑师。[6]166
作为英格兰第一大教堂,圣保罗教堂在英格兰民族身份认同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对伍尔夫来说,这个高大建筑既是压迫性的,又能给人以安慰;既是专制教会的符号,也是‘英格兰性’的标志”[7]166。《岁月》虽然讲述五十余载的世事变迁,但小说中伦敦的地理坐标仿佛独立于年轮的转动,像是一种稳定剂,无论何时何地都能给熟悉它的人以精神上的慰藉,成为他们身份认同的参照,发挥一种文化坐标的功能。进一步说,“这些文化人工制品对那些不适应大都市巨变的人来说是一种保护性的安慰,同时也提醒人们注意,英格兰仍然拥有庞大的海外帝国”[8]。通过表现英格兰人与城市空间的精神维系,并由此对其进行文化和具有意识形态导向的透视,伍尔夫表达了“一种对英格兰的强烈和非理性的忠诚,就像孩子对父母那样”[9]。
深度聚焦大英帝国的心脏伦敦是伍尔夫构建“英格兰性”的重要策略。城市对帝国来说具有非凡的象征意义,“它们既保护帝国的认同,也作为一种服务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帝国的权威和勋章得以传递给继任者”[10]。卡利尼(Peter J. Kalliney)在评价《达洛维夫人》时指出:“现代主义对城市的兴趣,就像《达洛维夫人》对伦敦的描写所表现的那样,让都市环境可以被更加广泛地用作一种英格兰民族身份的语言。”[11]《岁月》也有类似的特点,相比《达洛维夫人》的意识流风格,它以更加写实的手法聚焦城市空间,通过创造一种“能强烈引起人们集体认同和文化记忆的‘传统’氛围”[12],使伦敦成为承载和彰显“英格兰性”的重要场域。
二
《岁月》对伦敦景物的精心雕琢说明,“就创造一个独特的英格兰身份而言,地理和空间在有关英格兰的文学创作中自始至终都是常用的修辞”[7]179。《岁月》中除了英格兰国内空间,还有一个重要的海外空间——爱尔兰。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指出,空间关涉意识形态,是政治性和策略性的。[13]就想象和书写民族身份而言,海外空间在某种程度上比国内空间更加重要,因为“‘民族’是一个关系词;一个民族的存在在于它不同于其他的民族。……民族没有本质的或内在的特征;每个民族都是一种话语构成,它的身份在于它与他者的不同”[14]。作为英格兰的殖民地,爱尔兰对构想英格兰民族身份是不可或缺的。
爱尔兰的反殖运动是《岁月》的重要背景。在爱尔兰反殖民史上,有一位领袖人物的名字不得不提,那就是查尔斯·斯图尔特·帕内尔(Charles Stuart Parnell)。帕内尔对于爱尔兰的意义,就如同甘地之于印度,纳赛尔之于埃及。在他的卓越领导下,爱尔兰的民族解放事业在19世纪末取得实质性进展,形成与英格兰分庭抗礼的局面。19世纪80年代,帕内尔“支配了英国议会的议事议程。任何一位英国首相在行使权力时都不会不考虑帕内尔的反应。……他强化了爱尔兰民众的民族主义诉求,要求在整个爱尔兰实现英国君主治下的自治”[15]132。《岁月》故事的起始时间是1880年,正是在此前后,帕内尔“开始在爱尔兰发表战斗性越来越强的演讲,从各方面谴责格莱斯顿和英国政府,要他们正视爱尔兰民族主义的热潮”[15]139。帕内尔领导下的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迸发出的巨大能量,有力地冲击了英格兰人的自我认知,影响乃至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迪莉娅是帕内尔的忠实信徒,被帕内尔的英雄形象和领袖气质深深感染,视其为偶像。在母亲的病榻前,望着病重的母亲,年少无知的迪莉娅感觉无聊透顶,于是开始兴奋地想象自己与帕内尔并肩演讲的场景:
她站在台上,台下人头攒动,每个人都在叫喊,挥舞着方巾,嘘声和口哨声不绝于耳。然后她站了起来。她身着白衣从台子的中央立起;帕内尔先生就在她身旁。[6]17
在母亲的葬礼上,迪莉娅依然对帕内尔念念不忘,不得不告诫自己要等仪式结束后再去想他。
1891年,受私生活问题负面影响的长期困扰,心力交瘁的帕内尔在一片争议声中死去,这一突发和轰动性事件是《岁月》“1891”一章的主要背景。但和“1880”一章主要表现爱尔兰局势对作为个体的英格兰人的影响不同,这一部分重点突出殖民地事件对作为一个群体的英格兰人的渗透;或者说,它要说明的是英格兰人如何借助爱尔兰想象一种集体和公共身份。小说首先呈现的是一个阅读群体,“报童在门口飞快地分发着报纸。人们路过时一把抓过来,一边走一边翻阅”[6]82。埃莉诺恰巧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看到帕内尔的死讯时,她一开始感到难以置信,甚至有些不知所措,但当注意到“一个男人用食指指着这个消息”时,她开始相信报道的真实性,而后马上想到要去找妹妹迪莉娅,因为她知道迪莉娅看到这个新闻后会非常伤心:
迪莉娅在乎,迪莉娅比谁都在乎。她之前经常说什么来着——要为那个事业,为那个男人离家出走?正义,自由?这下可好,她所有的梦想都要破灭了。[6]82-83
就在此时,帕吉特上校也在报纸上看到了这个消息,无独有偶,他也想到了迪莉娅,“他有种感受,这种感受和他的女儿有关;说不清到底是什么,但让他皱起了眉头”[6]84。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指出,印刷资本主义(print-capitalism)“让快速增长的人群能够以全新的方式思考自我,并且将自己与他人关联起来”[16]。“埃莉诺和上校在同一天,在伦敦这一帝国中心阅读同样的新闻,这将他们联成一个整体。对新闻的共时接收让各种人物发生关联,从而产生一种共同体的感觉。”[17]121《岁月》通过突出帕内尔的死讯以报纸为载体在伦敦散播开来的过程,直观展现了一种共同体身份的生成。
当然,这种共同体毫无疑问是排他性的。在《岁月》中,“爱尔兰是处于文本边缘的想象性空间”[17]127。这在英格兰人对帕内尔死讯的反应中表露无遗。在大英帝国的忠实拥护者帕吉特上校眼中,帕内尔是一个“毫无廉耻的投机者”,一个“干尽所有坏事的煽动家”,所以当他看到帕内尔的死讯时,“一种强烈的欣慰感,一种强烈的带有一点胜利味道的感觉涌过他全身”[6]84。虽然因为女儿的缘故,他在庆幸的同时也感到几分遗憾,甚至对帕内尔产生敬意,但这种暂时性的认同感没有太多实质意义,因为“只有当帕内尔的死消除了他对英格兰霸权的威胁后,帕吉特才对他产生几分同情”[17]122-123。帕吉特上校的弟妹尤金妮同情帕内尔的遭遇,特别是奥谢对帕内尔的感情,更让她深感惋惜,消息传来,她非常难过。但在帕吉特看来,尤金妮是庸人自扰,表达的情感“与对象完全不成比例”[6]87。
在经过了“1917”和“1918”两章的“空白”之后,《岁月》在讲述20世纪30年代的“当代”一章中再次将爱尔兰拉回读者的视线。这一章的故事围绕家庭聚会展开,主人是迪莉娅和她的丈夫——爱尔兰人帕特里克。帕内尔的死对迪莉娅造成很大触动,可以说是她成年后嫁给一个爱尔兰人的重要动因。但帕特里克并不是迪莉娅原本想找的像帕内尔一样的反叛者,而是个不折不扣的亲英派,“她原本想找一个疯狂的反政府人士,却嫁给了一个最尊敬国王、最崇拜帝国的乡绅”[6]292。帕特里克来自一个为帝国服务了三百多年的英爱(Anglo-Irish)家族,祖上是十六七世纪来爱尔兰拓殖的英格兰人,所以尽管帕特里克是爱尔兰人,但他真正认同的是英格兰。在帕特里克看来,英格兰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国家;他还认为,正如女性获得选举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她们的生存状况一样,爱尔兰来之不易的自由也并不比受人欺压好多少,甚至更糟,所以爱尔兰人还是愿意重新加入帝国。帕特里克的亲英立场暴露了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两面性。在爱尔兰寻求独立的过程中,非理性的打砸抢烧和对平民赤裸裸的血腥杀戮时有发生,给爱尔兰的社会稳定和爱尔兰人的正常生活造成极大危害,使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常常陷入不得民心的尴尬处境。1916年的都柏林起义和1922年的爱尔兰内战是比较典型的例子,其中的一些细节很能说明问题。都柏林起义爆发后,英军赶来增援,当他们往城里进发时,“他们遇到的第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就是好几十个爱尔兰妇女给他们送来了茶、甜饼和饼干”[15]195。内战中,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领袖迈克尔·柯林斯被射杀后,“有一个都柏林妇女,她在一年前曾情愿为柯林斯献出自己的生命,但在事发的第二天看到报上的这则新闻时两眼放光,高声喊道:‘这消息不是太棒了吗?’”[15]233。伍尔夫对爱尔兰的混乱状态是有一定了解的,她在1921年的一则日记中写道:“在爱尔兰不断有人被射杀和绞死……因为某个可怜的男孩在礼拜一早上被杀,都柏林一直在举行群众游行。”[18]这些信息是伍尔夫塑造帕特里克的现实依据。作为一名爱尔兰人,帕特里克的亲英姿态及其现实指涉无疑是对爱尔兰最有力的边缘化。
进一步结合小说的创作背景和伍尔夫的个人旅行经历来看,帕特里克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伍尔夫本人对爱尔兰的文化偏见。《岁月》创作于1932年,发表于1937年,而伍尔夫曾于1934年出游爱尔兰,这段经历对她创作《岁月》起到关键作用。从伍尔夫的日记和通信中,我们可以明确感受到她——一位来自宗主国中上层社会的游客,在面对爱尔兰这样一个殖民他者时的文化优越感。伍尔夫眼中的爱尔兰几乎是一片不毛之地,这让习惯了大都市生活的伍尔夫很不适应,不止一次地感叹和抱怨“爱尔兰的生活是多么破败和肮脏,多么空洞无物和一贫如洗”[19]210,直言“没法在爱尔兰生活,……心跳在那里都会慢下来”[19]216。虽然身在爱尔兰,但伍尔夫时刻想到的是英格兰,英格兰是她衡量和评价爱尔兰的唯一标准:爱尔兰的村庄“像是从西肯辛顿切割下来的街道交汇区”,都柏林的圣斯蒂芬格林公园是“对林肯律师学院广场的爱尔兰式模仿,就像梅里恩广场是对贝德福德广场等建筑的模仿一样”[19]215。在伍尔夫“英格兰中心主义”眼光的注视下,爱尔兰失去了文化、历史和美学特性,被降格为英格兰的附属,只是因为英格兰的存在才有意义。也正是因为爱尔兰这样的殖民他者,为伍尔夫与作为帝国的英格兰产生认同提供了参照,正如她在日记中所言:
我终于明白了,如果我是爱尔兰人,我也想要归属大英帝国,因为这里没有享受,没有创造,没有刺激,只有伦敦的残渣,太贫乏无味,好像来到乡下一样。[19]215
这充分说明“伍尔夫的爱尔兰之旅使她自己的‘英格兰性’意识浮出水面”[17]126。在《岁月》里,伍尔夫也将这种意识融入对爱尔兰的虚构之中,使爱尔兰成为烘托英格兰身份的陪衬。
三
《岁月》中除了爱尔兰的异域形象,还涉及印度、非洲、埃及和澳大利亚等殖民空间。帕吉特上校一家三代都有殖民地工作和生活的经历:他本人是一名帝国军官,曾在印度、非洲和埃及服役;儿子马丁和孙子诺思分别在印度和非洲当过兵;女儿埃莉诺也曾去印度旅行。“所有文化都在一定程度上因为帝国的存在交错在一起,没有一个是单一和单纯的,所有的都是混杂、异质、明显被区分开来和多样的。”[20]《岁月》展现了帝国语境中的文化混杂性,说明“英格兰性”并不是对英格兰本土文化特征的单向定义,而是英格兰人“与来自其他民族文化背景的人遭遇中逐渐形成的一整套话语体系或集体文化意识”[21]。除了爱尔兰人,小说中另外一类重要的异域民族文化形象是犹太人。
犹太人的历史是一部苦难史和血泪史。公元1世纪,古罗马人占领耶路撒冷,犹太人从此背井离乡,开始了长达千年的流亡生活。由于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巨大差异,犹太人长期受西方主流社会的排挤和压迫,是后者文化、种族和民族意义上的他者。在众多西方国家中,英国的反犹传统是比较深厚的。早在13世纪,英国就开始驱逐犹太人,拉开了反犹的序幕。“在文学领域,英国作家受到欧洲传统反犹主义的影响和波及,在社会背景和民族偏见的固有视界下,他们秉承了一贯的反犹主义传统,难以排除潜在的丑化犹太人的先在视阈,文本中流露出较为明显的排犹倾向。”[22]的确,英国文学中不乏自私、贪婪、唯利是图、阴险狡诈的犹太人形象,《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和《雾都孤儿》中的伐金就是其中的典型。
进入20世纪,对犹太人的负面再现继续上演,并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强化,因为“20世纪的英格兰民族身份……是以对外来者的排斥为基础的——就是那些‘种族’,或更加宽泛地说,文化意义上的外来者”[23]。英布战争中的溃败是大英帝国由盛转衰的重要标志,而犹太人被认为是这场战争的幕后操纵者,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英国法西斯势力的抬头,这种观点更被广泛接受。[24]279对于这一时期的英国文学,特别是现代主义文学来说,“犹太性”是“可以被塑造和再塑造的材料”[24]277,与前代相比,其处理犹太问题的方式和视角更加灵活和多元,但反犹的基本立场没有太大变动。
伍尔夫从不掩饰自己的反犹立场,虽然丈夫伦纳德·伍尔夫是犹太人,但这并没有弱化她对犹太人的敌对情绪。从伍尔夫的日记和书信中可见,她对犹太人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抵触和排斥。与丈夫的妹妹见面后,伍尔夫直言“不喜欢犹太人的声音,不喜欢犹太人的笑声”[25]。不仅如此,她对丈夫的全家都抱有成见:
我开始看清楚他们是多么丑陋、多么爱管闲事(nosey)、多么无可救药的中产阶级。真的,我的审美发出的抗议声音最响——他们让我的房屋和花园变得廉价——他们仿佛让我们置身伯爵宫和酒店里,站在门廊里,夹在苹果树、青菜和鲜花中间,他们看上去是那么的突兀、呆板、土气、花里胡哨、俗不可耐![26]
甚至对丈夫的犹太身份,伍尔夫也是颇有微词:
我真恨自己嫁给了犹太人——我讨厌他们的鼻音、他们东方式的珠宝,还有他们的鼻子和赘肉——我是一个十足的势利眼:他们有旺盛的生命力,而正是这点最吸引我。他们死不了——他们可以靠一把米和一滴水活下来——就算皮包骨头他们照样能繁衍、交配,还能赚……大钱。[27]
显然,伍尔夫表面上自嘲,实则在婉转地挖苦和嘲讽犹太人。伍尔夫刻意突出犹太人的鼻子,这是一种明显的脸谱化,说明她对犹太人的反感“多从身体的厌恶开始,进而转入对犹太人思想情操、性格品质、层次趣味的鄙夷,并且矛头往往指向整个族群而非个人”[28]78。伍尔夫在《岁月》中对犹太人的塑造和对“犹太性”的暗示,与她的非虚构作品中的犹太人形象有很强的关联性。埃莉诺年少时曾在伦敦贫困区做义工,为贫困者提供慈善服务,服务对象中就有犹太人。她描述一个叫莉莉的犹太人时说:“她走进来时浑身珠光宝气。他们确实喜欢华丽的装扮——犹太人。”[6]23在姬蒂的聚会上有一位特雷尔夫人,“一个东方长相的女人,一根羽毛从她的后脑勺浮出来,和她的犹太鼻子相映成趣”[6]188。
小说对犹太人的集中描写出现在最后一章。一日,诺思去拜访租住在一所简陋公寓里的姑姑萨拉,准备一同去参加迪莉娅的聚会。萨拉不想去,为了逼迫自己下决心,就拿起一本书让诺思读,读到他们必须走为止。由于灯光昏暗,诺思看不清书的内容,为了打发时间,转而吟诵起了英国玄学派诗人安德鲁·马弗尔的名作《花园》。当背到“对这甜美的独处来说/众生是过于粗鄙了”这句时,门外传来脚步声,接下来就是他们关于犹太人的对话:
“犹太人。”她小声说。
“犹太人?”他说。他们听着。他现在听得非常清楚。有人打开了水龙头;有人正在隔壁洗澡。
“犹太人在洗澡。”她说。
“犹太人在洗澡?”他重复道。
“明早浴缸里会有一圈油腻。”她说。
“该死的犹太人!”他愤愤地说。一想到隔壁的浴缸沾染了一个陌生男人的油腻就让他恶心。
“继续——”萨拉说,“对这甜美的独处来说,”她重复着最后一行,“众生是过于粗鄙了。”
……
“这个犹太人是谁?”他问道。
“亚伯拉罕森,做油脂生意的。”她说。
……
“他会把毛发留在浴缸里。”她总结说。
诺思不自觉地抖了一下。食物里有毛发,盆里有毛发,还是别人的毛发,他感觉浑身不舒服。
“你和他共用一个浴缸吗?”他问道。
她点点头。
他扯开嗓门说了声:“天哪!”[6]248-249
诺思的惊讶引出了萨拉的回忆,因为这也是她当初发现浴缸里的污垢后的第一反应。犹太人的存在给萨拉带来了极大的不适,她甚至到报社求职,想找份工作,赚了钱后换一个地方住。但倔强、叛逆、追求精神独立的萨拉又不愿为了一个犹太人而委身于体制内,寄人篱下,为某个主人服务。由此观照上述对话就会发现,通过突出犹太人肮脏的身体,“伍尔夫把‘犹太性’和一种对精神独立的威胁关联在一起”[29]。这种关联在萨拉对马弗尔诗句的重复中进一步凸显出来,这句诗暗示犹太人对萨拉个人私密空间的冒犯和入侵,同时又从形式上直观地以英格兰人的高雅反衬了犹太人的粗俗,象征“英格兰性”对“犹太性”的文化优势。诺思的追问暂时扰乱了这种势力对比,但他的问题又牵引出了犹太人与金钱、财富的密切关联,也没有逃脱出对犹太人的程式化再现。实际上,小说并没有明确交代亚伯拉罕森的职业,只说他是in the tallow trade(做油脂生意的),trade既可以表示“生意”,也可以指“一种技能”,因此in the tallow trade也可译为“是一位油脂工”。结合语境看,这种译法更加符合逻辑。那么,亚伯拉罕森的工人身份是否为对其脸谱化的反驳呢?应该肯定,这种模棱两可是具有一定颠覆性的,在工人运动浪潮和工人维权意识空前的年代,这至少说明伍尔夫在有意识地尝试对犹太人进行多元再现;但也正是这种游移不定表明伍尔夫在这个问题上的固有观念和妥协,因为“安排一个崇尚高雅文化与独立精神的外邦女子与一个彻底物质的犹太男工同住,也一样体现一种厚此薄彼的价值判断”[28]81。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岁月》对犹太人的再现都是在反犹主义框架内进行的,“犹太性”也由此被赋予了一种他者性,与“爱尔兰性”一道构成小说想象和书写“英格兰性”的参照系。
四
伍尔夫在《岁月》中遵循了借助他者彰显自我的身份认同逻辑,她“对‘英格兰性’的描写是通过……一种反射性高光的形式完成的,也就说,通过命名他者来隐性地命名自我。换言之,自我的种族和民族性完全是借助中介体现出来的,反映为一种当他者被标记和命名时的隐性反差”[30]。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认为“现世性”(worldliness)是文本的主要存在方式,无论怎样的文本,“即使以最精致化的形式出现,也总是羁绊于境况、时间、空间和社会之中——简言之,它们是在世的,因而是现世性的”[31]。在“现世性”概念的观照下,追求艺术自觉、极具先锋和精英倾向的伍尔夫的文学创作显示出与特定历史文化语境的紧密关联。“先锋时代是……一个帝国民族国家已经成为国际秩序和心理共同体主导范畴的时刻。……尽管他们致力于改变既有的艺术和政治体制,尽管他们有一种世界性的旨趣,参与国际层面上的美学和社会革命,但欧洲先锋艺术群体尤其注重提升他们自己民族的声望。”[32]这正是伍尔夫的写作语境,而对于一位生活在走向没落的大英帝国的现代主义作家来说,通过文学想象重建帝国权威,进而获得身份认同和归属感便成为一种必然。伍尔夫作品中表露出的殖民心态和种族主义思想揭示出她作为“意识流小说家”和“女权主义者”的复杂性,也为重新审视其经典性提供了一种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