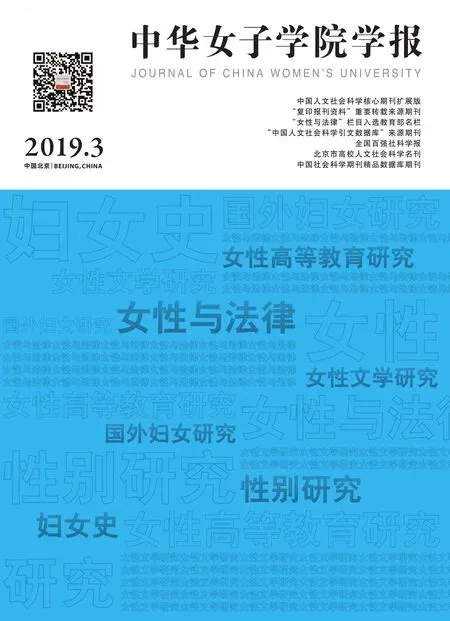女性连坐的社会性别分析:从长沙尚德街东汉简牍的一条律文说起
夏增民
2011年,长沙市尚德街某建筑工地出土一批东汉简牍,总计有300 余枚,被命名为“长沙尚德街东汉简牍”。概括言之,这批简牍的内容可以分为公文、私信、药方、杂文书、习字简等五大类。其中J482 中的一些简牍,被认为是“公文”的摘录。但整理小组把J482 中的木牍084(2011CSCJ482②:1-1)、212(2011CSCJ482②:25-2)、254(2011C SCJ482②:3-5)统一归类为诏书,似有商榷之处。木牍084(2011CSCJ482②:1-1)每行文字均以“诏书”二字开头,其内容当是诏书的内容摘引无疑。而木牍212 和254 的简文并未以“诏书”二字开头,从其内容看,更像是对法律条文的摘抄。所以,J482 中的简牍应该是诏书和法律条文的杂抄,而且所抄录的诏书与法令条文是按内容相关性条列的,但是都不完整。其中法律条文按刑名进行了归类,以类相从。从内容的编排来看,木牍的持有人对法令条文的抄录基本是按罪名由大到小、处罚由重到轻来排列的,先是要斩、弃市等死刑,然后依次是髡钳、完城旦、司寇、鬼薪白粲等。其目的可能是便于分类掌握,以备平时翻检、查阅,供学习法律或审理案件时使用。
同时,这些公文类简牍的内容也涉及当时社会对家庭、性别的规定,不仅足以验证、补充传世文献以及此前出土的秦汉法令的相关内容,还可以对秦汉时期的刑罚制度和性别议题提供新的认识。以下试以其中“嫁为人妻减死罪一等完城旦”一语为例解释之。
一、“减死罪一等”与东汉刑罚制度的规范化发展
在汉代,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以及应对社会危机、平衡政治斗争和缓和社会矛盾等原因,对于死刑,皇帝往往进行一些赦免。当然赦免是有条件的,本处于“殊死”及以上刑罚的,往往不在赦免之列。因此,在皇帝的诏书中,往往有“自殊死以下”等语,这在简牍资料中也有反映。
赦免在汉代成为常设的制度,在践祚、改元、祥瑞、灾异等特定的场合会按照惯例进行赦免。除此之外,得以减死的具体原因还可以是“以钱赎”,其目的是为了增加政府收入。如《汉书·武帝纪》曾记载,天汉四年“秋九月,令死罪入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另《外戚传上·孝昭上官皇后传》也记:“盖主为充国入马二十匹赎罪,乃得减死论。”
同时,也有因“积功”而被赦免的情况,如《汉书·萧何传》载:“传子至孙获,坐使奴杀人减死论。”或因“才干”得免,如同书《刘向传》:“上亦奇其材,得逾冬减死论。”总之,在汉代,对死刑的赦免虽然有固定的程序,但就其原因而言,却是较为随意。
死刑赦免,往往称“减死罪一等”或“减死一等”。①也有“减死二等”者,如《汉书·哀帝纪》中御史大夫赵玄即才“死二等论”,同书《朱博传》还作“减玄死罪三等”,记载并不统一。减等之后的处罚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尤其在死刑免除减一等处罚的问题上,西汉与东汉相比已经有很大的差异。西汉减死,多再处以劳役刑(徒刑),有髠钳为城旦、髡为城旦、完为城旦(完城旦、城)、鬼薪。此外还有髡钳、髡等刑罚。例如:
《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永始元年,坐使奴杀人,减死,完为城旦。”
《汉书·贾捐之传》:“长安令杨兴减死罪一等,髠钳为城旦。”
《汉书·陈咸传》:“减死,髠为城旦,因废。”
《汉书·鲍宣传》:“上遂抵(鲍)宣罪减死一等,髡钳。”
《汉书·刘辅传》:“上乃徙系(刘)辅共工狱,减死罪一等,论为鬼薪。”
《汉书·李寻传》:“(李)寻及解光减死一等,徙敦煌郡。”
以上具体案例中,减死一等大多是劳役刑,以“髡为城旦”为主,刑期仅四年。②闫晓君认为,汉初“城旦舂”尚无明确刑期,文帝十三年刑制改革之后开始明确,即应劭所说的“四岁刑”。参见闫晓君:《汉初的刑罚体系》,载于《法律科学》2006年第4 期。唯李寻处以迁徙刑。③陶安认为,因为减死之后剩下的“髡钳城旦舂”刑很容易被赎罪制度蚕食,所以从成帝时开始对减死的刑徒加以“徙边”的附加刑。参见陶安:《秦漢刑罰體系の研究》,东京创文社,2009年版,第213—281 页。
这种情况在东汉得到了很大的改变。东汉死刑赦免之后,主要是处以迁徙刑,劳役刑则成为次要。遍历《后汉书》之“帝纪”,如《后汉书·显宗孝明帝纪》载,永平十六年,“诏令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死罪一等,勿笞,诣军营,屯朔方、敦煌;妻子自随,父母同产欲求从者,恣听之;女子嫁为人妻,勿与俱。谋反大逆无道不用此书。”相类似的诏令也出现在《后汉书》之《肃宗孝章帝纪》《孝和帝纪》《孝安帝纪》《孝顺帝纪》《孝冲帝纪》《孝桓帝纪》以及《皇后纪下·安思阎皇后纪》中。也就是说,东汉时期,几乎每朝都申明了死刑减免后另要处以迁徙刑的处罚。
不过,另检之《后汉书》之“列传”,则减死之后的处罚略显多元化。择其主要罗列于后。例如:
《后汉书·耿夔传》:“(耿夔)坐征下狱,以减死论,笞二百。”
《后汉书·杜茂传》:“(杜元)坐与东平王等谋反,减死一等,国除。”
《后汉书·郅寿传》:“(郅)寿得减死,论徙合浦。未行,自杀,家属得归乡里。”
《后汉书·胡广传》:“大将军梁冀诛,(胡)广与司徒韩縯、司空孙朗坐不卫宫,皆减死一等,夺爵土,免为庶人。”
《后汉书·史弼传》:“(史弼)得减死罪一等,论输左校。”
《后汉书·党锢传·苑康传》:“征(苑)康诣廷尉狱,减死罪一等,徙日南。”
综合以上《后汉书》“纪传”中的相关资料显示,在东汉时期,“减死一等”之后,除三次未说明另施以何种刑罚之外,归乡里、归本郡、归家三次;国除、夺爵土两次;输左校、髡钳、笞二百各一次;余皆徙(戍)边。相对照来看,两汉在死刑减免后的处理上有明显的差异,由以劳役刑为主演变成以迁徙刑为主。
秦代,迁徙刑轻于劳役刑。[1]79而且一直至西汉文景时期,都是“列于徒刑之下,是刑罚体系的末端”。而在文景时期刑制改革以后,由于劳役刑的惩罚力度大大降低,迁徙刑与劳役刑的等级差距变小,迁徙刑式微。[2]49-50到元成时期,在轻刑之风背景下,大量减死犯产生,为了避免“赎死”减刑而产生逃避处罚的弊端,便采取了以徙边的迁徙刑加重减死后的髡钳城旦刑。因此,迁徙刑又成为一种常用之刑。“最晚至东汉,非殊死罪名均徙边。”[3]159从此,迁徙刑也渐成为仅次死刑的刑罚,直至西魏时期,演变成为传统中国五刑体系中的流刑。
西汉后期对相关罪犯“减死”后的处置,可以看作是自西汉文景时期刑制改革初步形成以笞刑、徒刑、死刑为主体的刑罚体系之后[4]75,中国传统刑罚体系的又一变化。这使得迁徙刑成为重刑,也是迁徙刑成为正刑的第一步。这一变化过程虽然比较缓慢,但是笞、杖、徒、流、死五刑体系最终形成的不可缺少的环节,可看作是中国传统刑罚制度规范化发展史上的重要一步。
二、“嫁为人妻”与女性权利
如前所论,减死一等降为迁徙刑,意味着在刑罚力度上要大于减死一等降为劳役刑,因为死刑减免以后的“徙边”是迁徙刑和劳役刑结合的复合刑。在这个前提下,女性如果连坐,长沙尚德街东汉简牍中所摘录的“嫁为人妻减死罪一等完城旦”,则是对女性进一步恤刑的表现。
连坐,尤其重视家族的连坐责任,是中国古代刑罚体系的重要特点。[5]在汉代,刑事连坐制度已经较为完备[6]8,在司法实践中较为普遍。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收律》曾载:“罪人完城旦、鬼薪以上,及坐奸府(腐)者,皆收其妻、子、财、田宅。其子有妻、夫,若为户、有爵,及年十七以上,若为人妻而弃、寡者,皆勿收。坐奸、略妻及伤其妻以收,毋收其妻。”从中可以看出,在汉初,普通的轻型犯罪,家属也要负连带责任,从坐的比例相当高。高敏曾指出,《二年律令·收律》有可能制定于汉高祖五年(前202年)前,而在文帝二年(前178年)被废除。[7]在此之后的西汉,缘坐之刑虽不在律令之列,但对于诸如“大逆无道”“谋反”等严重罪行的处罚,还是经常临时使用。这在《史记》《汉书》和《后汉书》的记述中并不鲜见,比如郭解案、灌夫案、梁冀案等。
然而,在汉代的刑事连坐责任中,家族中的女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获得某种程度的减免。这说明在秦汉时期的司法实践中,的确存在针对女性的宽宥之法。①王辉认为,汉代连坐制度有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个基本原则是连坐犯适用的刑罚比照正犯来减等,而且存在着老、幼、妇减免刑责的规定。参见王辉:《汉代家庭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堀毅通过对云梦秦简的考察,认为在秦以至汉,妇女都是被作为宽刑的对象给予各种特别保护,国家权力科罚于妇女身上的负担总是比较轻的。[8]198,210同时,在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也不乏针对女性减刑、免役的规定。[9]关于此,《汉书》《后汉书》也有相关的记载,比如“女徒复作”“女徒顾(雇)山”,都可以称得上“施惠政于妇人”。②《汉书·宣帝纪》注引李奇曰:“复作者,女徒也。谓轻罪,男子守边一岁,女子软弱不任守,复令作于官,亦一岁,故谓之复作徙也。”孟康曰:弛刑徒也。见中华书局标点本《汉书》第235 页。《汉书·平帝纪》:天下女徒已论,归家,顾山钱月三百。师古曰:“谓女徒论罪已定,并放归家,不亲役之,但令一月出钱三百,以顾人也。为此恩者,所以行太皇太后之德,施惠政于妇人。”见第351 页。
自西汉后期起,尤其是到东汉,皇帝多次“议省刑罚”,实行删除繁苛、修明法律的政策。如西汉元帝、哀帝以后,“手杀人皆减死罪一等,著为常法”。[10]918东汉章帝“决罪行刑,务于宽厚”。[10]919从整体上而言,刑律有所约减,刑罚趋于宽缓,对女性犯法也多蠲免。《汉书·平帝纪》记载:“明敕百寮,妇女非身犯法,及男子年八十以上七岁以下,家非坐不道,诏所名捕,它皆无得系。”《后汉书·光武帝纪上》也记载:“男子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妇人从坐者,自非不道,诏所名捕,皆不得系。当验问者即就验。女徒雇山归家。”对从坐的女性,汉代都特别下诏书,给予释放。一般认为,汉代存在着“女性恤刑制度”,其表现在施刑的照顾、减刑的优待和囚禁的宽待等三个方面。③参见林红:《汉代女性犯罪问题初探》,载于《南都学坛》2008年第1 期。另外,学界对于女性的“恤刑”,凡涉及女性犯罪问题的论述都有提及,如翟麦玲、张荣芳:《秦汉法律的性别特征》,载于《南都学坛》2005年第4 期;贾丽英:《汉代有关女性犯罪问题论考:读张家山汉简札记》,载于《河北法学》2005年第11 期。而在长沙尚德街东汉简牍中所摘录的“嫁为人妻减死罪一等完城旦”法令的出台,也昭示着女性从坐范围较以前得以缩小。
汉代法律的这一特点,与儒家思想和政治实践的结合有极大的关系。儒家提倡“慎德明罚”,主张“恤刑”,虽然在其法律思想中,并没有直接体现专门针对女性的优待。然而,《周礼·秋官·司刺》记有“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三赦乃指“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憃愚”,针对的是幼、弱、老、疾,女性可归入弱者之列。《左传·襄公十九年》记有:“妇人无刑。虽有刑,不在朝市。”根据杜预注,此无刑应该是“无黥、刖之刑”,也可以说是对女性处罚的减免。
然而,在这种对女性“恤刑”的背后,隐含着女性地位从属性的玄机,即女性的人格并不独立,而是依附于男性。这在社会性别史上是一个公论,而在这里又得到了明确的体现。当然,在儒家文献中,这一立场始终是得到强调的。《礼记·杂记》载:“凡妇人从其夫之爵位。”郑玄注曰:“妇人无专制,生礼死事,以夫为尊卑。”《礼记·效特牲》也载:“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妇人无爵,从夫之爵。坐以夫之齿。”另,《春秋繁露·基义》则明确指明了社会的性别秩序:“夫为阳,妻为阴”,“妻兼功于夫”,“丈夫虽贱皆为阳,妇人虽贵皆为阴”。《白虎通义》之《爵论》和《三纲六纪》则说得更为明白:“妇人无爵何?阴卑无外事,是以有‘三从’之义: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故夫尊于朝,妻荣于室,随夫之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对女性的“恤刑”,并不是对女性的权利维护,很大程度上是视女性为弱势群体,体现的是法律对弱势群体在施刑和量刑上的照顾。另外,更大的可能,这是对女性生育功能的重视,视女性为生育的工具,保护女性的生育抚育功能。①参见翟麦玲、张荣芳:《秦汉法律的性别特征》,载于《南都学坛》2005年第4 期;田小梅:《在“照顾”的历史表象背后:中国古代法律“照顾”女性的内在原因剖析》,载于《妇女研究论丛》2008年第5 期。
事实上,儒家思想的流行以及汉代“引经决狱”“以礼入法”,开启了法律的儒家化进程,使法律发生了由法治向礼教的变化。[11]具体到东汉的法律,其维护男性利益和特权的性别特征更加明显,因此对于女性而言,法律的儒家法也可以称为法律的父权化。②法律“父权化”似系由李贞德在讨论北魏“刘辉案”时提出。参见李贞德:《公主之死:你所不知道的中国法律史》,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5 页。李贞德在该书中重点分析了法律中的夫家认同问题。女性从属于男性和夫家的理论原则,在司法实践上也得到了体现。无论生父母本家,还是夫家家族中有人犯罪,女性都要受到株连,负刑事连带责任。这是中国古代法律的法律家族主义的特征决定的。③瞿同祖认为,中国古代法律的主要特征表现在法律的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上。参见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导论”,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2 页。
这种情况发生改变的转折点,一般认为是曹魏正元二年(255年)的毌丘俭案。根据当时魏国的法律,“犯大逆者诛及已出之女”。毌丘俭的儿媳荀氏为司马师姻亲荀顗的族妹、荀氏的生女毌丘芝,已嫁为颍川太守刘子元为妻,按照法律应从坐处死,因怀孕暂时系狱。荀顗请托司隶校尉何曾为毌丘芝求以“没为官婢”的赎死刑。何曾乃使主簿程咸上议,建议改变“父母有罪,追刑已出之女;夫党见诛,又有随姓之戮;一人之身,内外受辟”的不合理现象。当然,这个提议不是为了维护女性的权益,而是“男不得罪于他族,而女独婴戮于二门,非所以哀矜女弱,蠲明法制之本分也”,从而达到“法贵得中,刑慎过制”的目的。[10]926可以说,程咸虽然是为荀氏请求免死,但在客观上从法律上界定了女性司法权益的边界,同时也进一步规定了女性从身份到权利上对夫家的归属。
程咸提出的“宜改旧科,以为永制”得到允许,“有诏改定律令”。至司马昭时,又令贾充修订法律,其中又有“减枭斩族诛从坐之条,除谋反适养母出女嫁皆不复还坐父母弃市”的新规定[10]927,进一步明确了女子出嫁不再受生父母本家的牵连。④到了西晋永康年间,女生对于父母本家的连坐也被取消。司马伦、孙秀政变,解系、解结兄弟被害,解结女已聘裴氏,原定祸起次日出嫁,裴氏本欲按礼制使解结女免刑,“解结女曰:‘家既如此,我何活为。’亦坐死。”但此事引发朝廷改革旧制,从此,“女不从坐,由(解)结女始也”。详见《晋书·解结传》,第1633 页。以后即使族刑临时恢复,也往往对女性有所蠲免,如《晋书·肃宗明帝纪》:“(太宁)三年春二月戊辰,复三族刑,惟不及妇人。”从此,就女性的连坐责任而言,法律的父权化得到了巩固,这也正是北魏“刘辉案”争议的大背景。⑤北魏“刘辉案”始末,详见李贞德:《公主之死:你所不知道的中国法律史》,三联书店2008年版。
现在看来,这一制度的创制并非始于曹魏,而是在东汉即有先声。《后汉书·显宗孝明帝纪》记永平十六年九月丁卯诏:“令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死罪一等,勿笞,诣军营,屯朔方、敦煌;妻子自随,父母同产欲求从者,恣听之;女子嫁为人妻,勿与俱。谋反大逆无道不用此书。”此诏即表明,除谋反、大逆无道等重罪之外,出嫁的女子无须连坐徙边。东汉明帝时,寒朗曾上言曰:“旧制大罪祸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于身,天下幸甚。”[12]1417可能即是指此。这是西汉后期以来刑罚趋向宽缓的持续。
三、“嫁为人妻减死一等完城旦”试释
经过以上的讨论,我们再来看长沙尚德街东汉简牍J482 木牍212 所摘录的“嫁为人妻减死一等完城旦”。
这一条应该是节文,我们推测其本意应该是,若不是谋反、大逆不道等重罪,已出嫁的女子在本家有人犯罪应连坐处以死刑的时候,可免除死刑,但仍要受到“完城旦”的处罚。鉴于“城旦”一般是男性刑名,此处当是缺抄一“舂”字,应为“嫁为人妻,减死一等,完城旦舂”。《汉书·刑法志》载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奏言:“诸当完者,完为城旦舂。”又曰:“罪人狱已决,完为城旦舂,满三岁为鬼薪白粲。”“前令之刑城旦舂岁而非禁锢者,如完为城旦舂岁数以免。”而《后汉书·显宗孝明帝纪》诏举赎刑之时,也有“完城旦舂至司寇作三匹”之语。以上记载皆为“完城旦舂”,可是为其证。
对于一般犯罪,在某种条件下对连坐的人员减刑,可以说从汉初就开始了。《二年律令·收律》规定了对犯罪者家族成员实施的条件及范围,其中有:“罪人完城旦、鬼薪以上,及坐奸府者,皆收其妻、子、财、田宅。其子有妻、夫,若为户、有爵,及年十七以上,若为人妻而弃、寡者,皆勿收。”据此,王辉认为这就明确了如果仅是父家的一般犯罪,出嫁女不必缘坐。[13]89
事实上,至于身犯谋反、大逆不道者,汉代也有不连坐的先例。汉昭帝时,鄂邑长公主、燕王旦谋反事败,善后时“赦王太子建、公主子文信及宗室子与燕王、上官桀等谋反父母同产当坐者,皆免为庶人”;[14]227杨恽先犯“大逆不道”,后以《报孙会宗书》再犯之,处以“要斩”之刑,而妻子不过徙酒泉郡。[14]2898但这都是个案,不能以法律论之。对鄂邑长公主和燕王旦的谋乱,要考虑到当时的政治形势,为稳定政局计,不得已而缩小诛杀范围。而杨恽案也是杨恽本人为宣帝“所信任”,“不忍加诛”之故。所以,在东汉时期,凡谋反减死之诏下,对连坐者皆注明类似“谋反大逆,不用此令”之语。
但是,至三国时期的“毌丘俭案”,谋反等重罪“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14]2302或“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姊妹女子之适人者皆杀之”[10]20的连坐刑罚,开始在律令层面发生重大变更,此后,凡涉“谋反大逆”罪之处罚,一般来说,似已不可以再有减刑。
总之,汉魏时期,对一般犯罪的家属连坐,可以酌情减刑。前此已有论述,从西汉到东汉,减死一等之后的处罚已有以“髡为城旦”变为以“徙(戍)边”为主,即由劳役刑变为迁徙刑。但木牍212所记的“嫁为人妻,减死一等,完城旦”却仍不是“徙(戍)边”,而是与西汉的规定更相近。同时,除此之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东汉其他减死“完城旦”的记载。仅有安帝时史宓、樊严减死“髡钳”,桓帝时史弼减死“论输左校”,与“完城旦”的处罚相近。不过,史宓、樊严在“阎显诬耿宝案”中算是从犯;“史弼案”则是魏劭与同郡人行贿于权宦侯览,加之“平原吏人奔走诣阙讼之”,属于在舆论压力之下的轻判。与此相类似的,还有曹魏文帝时“大女刘朱殴打子妇致前后三妇自杀”案,刘朱最后竟只判“减死输作尚方”[10]922,而这也是依长辈殴打晚辈会得到减刑原则的判决。所以,我们可以推测,在东汉,出嫁女基于父母本家的连坐责任会更减免一等。如《后汉书·显宗孝明帝纪》所载,永平十六年“诏令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死罪一等,勿笞,诣军营,屯朔方、敦煌;妻子自随,父母同产欲求从者,恣听之;女子嫁为人妻,勿与俱”,以及“女子嫁为人妻,勿与俱”。女儿已出嫁,无须徙边;但不意味着不处罚,或许就是处以“完城旦”。上文提及,西汉到东汉这一时期中国古代刑罚体系的规范化发展,新的五刑体系“笞、杖、徒、流、死”正在形成中,“完城旦”的徒刑是轻于“徙边”的流刑的。这也就表明,出嫁女子对本家的连坐责任更小了。
“嫁为人妻,减死一等,完城旦”也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律发展的连续性。既然这一法条是刑罚轻省的表现,那就意味着它是法律儒家化或法律父权化过程的一环。这一过程自西汉时起,中经“毌丘俭案”和西晋《泰始律》,直至《唐律疏议》最终完成。比如《唐律疏议·贼盗》规定:“若女许嫁已定,归其夫。”又有,“《疏议》曰:‘女许嫁已定’,谓有许婚之书及私约,或已纳娉财,虽未成,皆归其夫。”至此,本文所提及的自汉晋以来所有的争议案例都落实成了成文法律。另外,木牍254 正面所摘录“伤兄姊,加罪二等”的法条,与魏文帝时“欧(殴)兄姊加至五岁刑,以明教化也”[10]925可谓一脉相传,这也正是法律发展连续性的例证。
以上讨论表明,东汉时期针对女性的从坐范围已在缩小,处罚程度也在逐步轻省。正是在这样的司法实践之下,曹魏正元二年程咸上议以后,一般情况下,出嫁女性不再受生父母本家株连。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重大进步。
当然,如前所述,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固化了女性在法律上对丈夫和夫家的依附,女性的权利不是女性个人独立的权利,而是作为丈夫和夫家权利的一部分。因此,女性不仅要随从夫家坐罪,而且对女性个人权利的侵害,也往往被认作是对丈夫和夫家权利的侵害。
这在简牍法律资料里面同样可以得到印证。例如,《二年律令·杂律》曾规定:“诸与人妻和奸,及其所与皆完为城旦舂。其吏也,以强奸论之。”此律条亦见敦煌悬泉置汉简,其载:“诸与人和奸,及所与□为通者,皆完为城旦舂;其吏也以强奸论之。其夫居官……”从中可以看到,在汉代,对“和奸”的处罚是针对男女双方的,都要处于“完为城旦舂”的处罚。如果男方为官吏,则以强奸罪重处。但是必须要指出的是,这一条规定适用于已婚女性而非未婚女性;而且对未婚女性的“和奸”量刑目前尚没有发现,是否处罚以及如何处罚也不得而知。从出土的《二年律令》法律条文顺序来看,此段条文前后较为完整,或许汉律对此没有规定,亦即未婚女性与人“和奸”,不予处罚。果真如此的话,那么汉律只处罚人妻的“和奸”,其实是对男性权利的保护,因为法律认为对已婚女性的侵犯就是对其丈夫权利的侵犯,这反映出秦代以至西汉初女性对男性的依附关系。
另外,《二年律令·贼律》规定:“斗殴变人,耐为隶臣妾。(怀)子而敢与人争斗,人虽殴变之,罚为人变者金四两。”如果殴打孕妇致人流产,“耐为隶臣妾”,即判处一年徒刑;而怀孕女性若挑动斗殴而致自己流产,自己也要“罚金四两”,相当于判处六年徒刑,所受处罚要远重于施暴者。因为女性的身体不完全属于自己,还同时属于丈夫和夫家,自己挑起斗殴而致自己流产,最重要的不是使自己的身体受损,而是使丈夫和夫家的权益受到了侵害,所以要被施以重罚。类似的判决也在云梦秦简《封诊式》中曾经出现,可见这一司法精神前后一脉相承,体现了当时两性关系中既定的价值判断。
综上所述,长沙尚德街东汉简牍J482 公文木牍中“嫁为人妇减死一等完城旦”一语,显示了女性从坐刑罚的演变过程,同时也体现了女性在法律上对男性和男性家庭的从属性和依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