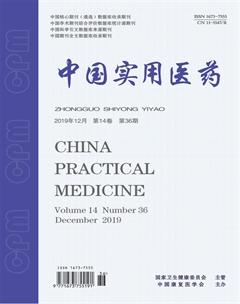HDFN的诊断方法研究进展
廖忠 陈宇南
【摘要】 胎儿和新生儿溶血性疾病(HDFN)基本原因是指某些妇女在怀孕期间暴露于父系衍生的红细胞抗原或在其既往输血史中暴露于非自体抗原, 红细胞致敏。一旦被致敏, 未来怀孕可能导致HDFN。近几十年来, HEAs检测是重要输血试验组成部分[1]。传统上, 这种检测是在患者或供体单位红细胞(RBCs)上进行的, 使用的试剂抗血清具有明确的抗原特异性和凝集点。多种血型抗原的同种异体抗体与HDFN有关联, 可见于ABO、RH及MN等血型系统。HDFN可能导致严重的溶血、黄疸和核黄疸。在我国, ABO相关HDFN比例最多, 而RH(-)人群仅占0.4%, 低于白种人15%[2]。其他血型系统则更为罕见。一旦发病, 病后预后极差, 所以先期诊断则显得尤为关键。需要适当的诊断工具来区分HDFN与其他红细胞相关原因的妊娠免疫和黄疸的肝或感染性病因。HDFN由于其高发病率和严重的临床症状, 应确保早发现、早治疗。
【关键词】 溶血性疾病;血型系统;胎儿;新生儿;抗原;抗体
DOI:10.14163/j.cnki.11-5547/r.2019.36.107
1 血清学方法
关于产前诊断, 如果发现有临床意义上的同种异体抗体, 或者有前一个胎儿或新生儿受到HDFN的影响, 最初是通过确定胎儿RBCs中相应抗原的存在与否来确定HDFN的胎儿风险[3]。
为预防及避免HDFN的发生, 妊娠妇女除行常规的产前检查外, 还应包括妊娠史、流产史、HDFN史及夫妻双方的ABO和Rh血型的鉴定、不规则抗体筛选。而目前临床检测血型最为常用的方法, 其原理是让待测样本红细胞和标准血清中血型抗原和抗体在液体介质中发生凝集反应, 通过肉眼识别判断血型表型。常用的方法有玻片法、试管法等。在此基础上改良的微柱凝胶法[4], 进一步提高了检测的准确性, 且具有所需样本少、抗干扰能力强等优势。尽管有研究表明[5], HDFN的发病率随母体内抗-A/B或抗-RhD水平的升高而递增, 但仍有一些高抗体水平的个体并没有发生HDFN, 而一些低抗体水平的个体发生了中至重度的HDFN。对那些有过流产史、HDFN史的孕妇, 应该密切注意其体内的血清抗体水平。
血清学方法可用于孕妇在怀孕早期的弱抗体检测, 血清学分析的优势来自于其敏感性和灵活性, 这使得在妊娠早期抗体滴度较低时即可发现和鉴定。但其局限性在于实验须在标准化条件下进行, 且检测出来的抗体滴度与HDFN疾病严重程度之间的相关关系仍然欠缺。另外, 对HEAs进行血清学检测还有其他局限性。例如, 需要抗原特异性抗原。在某种程度上, 这大概是因为滴定法结果本身就是一种不精确的抗体浓度测量方法。同时, 对于许多临床相关的HEAs, 也没有商用的抗血清(如V抗原)。如果单个样本必须检测多个抗原, 那么特定的抗血清的成本依然比较昂贵。血清学检测是人力成本较高, 需要有经验的技术人员才能获得与凝集测试的主观终点一致的结果。
血清学类型的方法可能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时间, 并且需要穩定可靠的抗血清。如前所述, 如果血液样本中含有来自最近输液的持续供体细胞, 或者通过间接凝集作用在样本上使用阳性的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DAT)进行输入, 就不能在不修改的情况下使用它们。改良的血清学方法并不总是成功的, 它们不能用于某些常见的抗原。近年来, 分子分型(基因型测试)已成为一种替代方法, 可以克服血清型分型的许多缺点, 同时也能增加与输血管理相关的新信息。
2 分子分型方法
在许多情况下, 这种血清学检测有严重的局限性。而分子诊断测试方面的进展, 克服了血清学检测的局限性, 使实验室能够检测特定位点的编码序列, 从而可以推断出抗原的状态。在分子水平上, 抗原变异是基于对HEA基因编码的DNA序列变异, 如单核苷酸多态性(SNPs)、插入或缺失。例如, RHCE基因(676G>C) 密码子226的单核苷酸变化是E/e等位基因的基础[6]。
因此在分子生物学基础上, 开发了多种血型基因分型方法[7], 常见的有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法、单链构象多态性PCR法、扩增产物长度多态性PCR法、等位基因特异性引物消耗法、突变位点分离PCR法以及DNA芯片法、直接测序法等。当父亲为杂合或父系接合性未知时, 胎儿红细胞抗原决定需要通过胎儿血型基因分型来进行进一步的管理。运用PCR-序列特异性引物(SSP)、PCR-限制片段长度多态性(RFLP)等[8]分子生物学技术可从怀孕16周的孕妇羊水细胞中检测出胎儿的血型基因, 对于有 HDFN 史或流产史的妇女, 其丈夫基因为杂合型者, 用分子生物学技术可以更早、更准确地预测胎儿的血型基因型, 可有选择性终止RhD阳性胎儿的妊娠, 避免对RhD阴性胎儿的一些侵入性损害检查[9]。可检测的血型基因型有RhD、c、E、Cw、K、Fya、Fyb、Jka、Jkb 等。在 ABO HDFN 的预测中, 如母亲为O型, 父亲为AO /BO型的夫妇, 检测其胎儿ABO血型基因型, 如胎儿为O型, 完全可以排除HDFN发生的可能, 避免其他不必要的检测。如胎儿为AO/BO基因型, 则提示有发生HDFN的可能, 从而指导临床在必要时进行其他检测。
尽管分子遗传学在未来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但与所有的方法一样, 分子抗原类型有其优点, 但也有其局限性。因为技术、医学和遗传缺陷导致表型(在红细胞表面上表达的)与基因型(编码基因)不同。大多数基于DNA的扩增都不排除检测中没有表达的基因, 这可能导致抗原检测假阳性。另一方面, 不是所有的血型多态性都可以很容易的分析[10], 例如, 如果大量的等位基因编码一个表型(例如ABO、Rh和null表型);或具有大片段缺失的等位基因(如Ge-)或由混合基因编码的等位基因(例如在Rh和MNS系统中);或者当分子基础未知时(例如Vel、Lan、Jra)。此外, 并不是所有种族的所有等位基因都是已知的[11]。
3 標本采集
胎儿血型基因分型样本来源于几种胎儿DNA。传统上包括羊膜穿刺术、脐带穿刺术和绒毛膜绒毛取样(CVS)和经阴道灌洗获得的子宫颈组织的胎儿细胞。每一种都对胎儿有风险, 而且与样品质量有关。经阴道灌洗获得的宫颈组织则胎儿DNA的丰度低, 而母体DNA、羊膜穿刺术、角膜穿刺术和CVS感染的可能性较高, 并增加了妊娠期出血的风险, 增加了母体致敏的风险。以往, 羊膜细胞是胎儿血型基因分型的首选来源, 因为相对于其他方法, 羊膜穿刺术的安全性较好。然而, 即使是羊膜穿刺术也有0.3%~1.0%的流产风险和3%~17%的胎盘出血[12]。早期产前诊断胎儿DNA的非侵入性产前诊断方法的出现, 已经消除了这些担忧, 并极大地提高了对胎儿组织进行分子检测的能力。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监测胎儿危险的侵入性程序已经被放弃。胎儿血型分型可在妊娠期间孕妇血浆中使用无细胞胎儿DNA。胎儿贫血可通过多普勒超声检查, 以确定需要宫内输血的胎儿。最后, 强化光疗法是一种安全的干预手段, 以降低胆红素水平, 以预防核黄疸。由于母体抗体在这一时期保持活跃, 受感染的新生儿在出生后的几个月可能需要一次或更多的输血。
4 未来趋势
在血型分类中, 最有潜力但依然在实验阶段的新方法是诊断微阵列的发展。DNA以及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微阵列依然处于实验阶段。最大的影响可能来自于目前进行的各种类型的常规化验, 包括血型分型和血液捐献的病原体检测。微阵列有可能改变这些测试算法, 以在单个平台上同时测试所有需要的标记, 减少使用专用操作符和特定试剂的多种仪器的成本, 并大大简化了数据处理方面的操作。
如上所述, 大多数血型抗原都是等位基因, 是SNP的结果。对于DNA微阵列, DNA分离后的多重PCR扩增了含有SNPs的基因片段。然后将PCR产物杂交到一个含有短等位基因寡核苷酸的阵列中。对于每一个血型, 都有不同的寡核苷酸(正义和反义)。然后用自显微镜和图像分析系统对整个阵列进行可视化处理, 阵列信息进行解码, 基因型得分。首次结果表明, 微阵列将提供一个可靠且快速的程序, 可以进一步改进以提高效率。为测定血型, 研制了蛋白质微阵列, 它们是用多种血型抗原特异性抗体标记的。该方法也可用于直接抗球蛋白检测的微阵列中, 在微阵列表面发现单克隆抗免疫球蛋白G(IgG)和抗C3d, 并在荧光素异硫氰酸酯标记的荧光素中, 使敏感的RBCs反应。碳水化合物微阵列包含许多不同的多糖, 以一种小型化的形式固定在固体支架上。在相同的条件下, 可以同时对阵列中的每个组件的蛋白质、病毒或细胞进行绑定。使用含有不同糖蛋白的碳水化合物微阵列, 可以检测出A、B、H和Lewis血型的抗体。
参考文献
[1] Quraishy N, Sapatnekar S. Advances in Blood Typing. Advances in Clinical Chemistry, 2016, 77:221-269.
[2] Malomgré W, Neumeister B. Recent and future trends in blood group typing. Anal Bioanal Chem, 2009, 393(5):1443-1451.
[3] Wilkinson DS. Clinical Utility of Genotyping Human Erythrocyte Antigens. Laboratory Medicine, 2016, 47(3):e28.
[4] Keir A, Agpalo M, Lieberman L, et al. How to use: the direct antiglobulin test in newborns. Archives of Disease in Childhood Education & Practice Edition, 2015, 100(4):198.
[5] Hadley AG. A comparison of in vitro tests for predicting the severity of haemolytic disease of the fetus and newborn. . Vox Sanguinis, 2015, 74(S2):375-383.
[6] Shields JA. Prenatal typing of fetal DNA in cases of potential alloimmune haemolytic disease of the newborn: clinical benefit outweighs disadvantage. . British Journal of Biomedical Science, 1999, 56(1):49.
[7] Daniels G, Finning K, Martin P, et al. Fetal blood group genotyping from DNA from maternal plasma: an important advance in the management and prevention of haemolytic disease of the fetus and newborn. Vox Sanguinis, 2010, 87(4):225-232.
[8] Zhao H, Li B, Li N, et al.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55 twin neonates with haemolytic disease of the newborn. Immunologic Research, 2017, 65(3):699-705.
[9] Denomme GA, Akoury H, Sermer M, et al. RhD status of a fetus at risk for haemolytic disease with a discrepant maternal DNA-based RhD genotype. Prenatal Diagnosis, 2015, 19(5):424-427.
[10] Fasano RM. Hemolytic disease of the fetus and newborn in the molecular era. Seminars in Fetal & Neonatal Medicine, 2016, 21(1):28-34.
[11] Hendrickson JE, Delaney M. Hemolytic Disease of the Fetus and Newborn: Modern Practice and Future Investigations. Transfusion Medicine Reviews, 2016, 30(4):159-164.
[12] Moise KJ. Hemolytic disease of the fetus and newborn. Clinical advances in hematology & oncology, 2013, 11(10):664-666.
[收稿日期:2019-0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