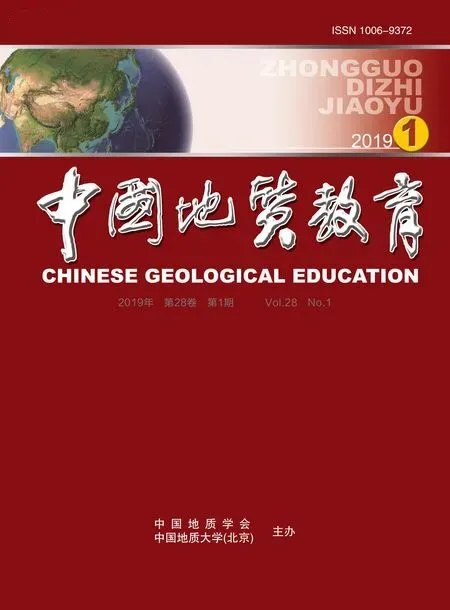矿业类院校资源勘查专业“煤田地质学”课程发展趋势
郭 晨,马东民,彭 涛,陈 跃,鲍 园,付常青,师庆民
西安科技大学 地质与环境学院,陕西 西安 710054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地质学类的课程体系也应与时俱进,紧跟行业发展趋势,适应新时代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其中煤田地质学也不例外。煤田地质学是研究煤的形成演化、基本性质与组成、聚煤规律与地质控制的一门学科。杨起、韩德馨两位院士奠定了我国煤田地质学的学科根基和理论体系。近年来,随着以煤层气为代表的煤系非常规天然气以及煤系共伴生矿产资源的快速发展,煤田地质学的理论体系、学科内涵已广泛延伸,煤系处处有资源的观念已深入人心,研究客体正逐渐从煤层本身拓展到整个含煤岩系,并强调煤炭的生态环境友好性。在分析“煤田地质学”课程的发展趋势之前,有必要了解煤田地质学领域近年来取得的主要进展。
一、 煤田地质学主要进展
1. 煤系非常规天然气
在煤系地层中,除煤炭自身外, 煤层气、煤系暗色泥岩中自生自储的页岩气、以煤层及暗色泥岩为烃源岩储存在致密砂岩中的致密气, 以及与煤层紧密伴生的油页岩等十分富集。煤层气、页岩气、致密砂岩气等煤系非常规天然气(煤系气)共生共存的现象已日趋受到业界的关注[1]。
(1)煤层气。
作为煤田地质学的重要分支,煤层气地质学近年来发展迅速,2007年中国矿业大学傅雪海教授与秦勇教授等人出版了国内第一本煤层气地质学教材[2],首次系统介绍了我国煤层气的地质条件、成藏特征与开采工艺,建立了课程体系。我国煤层气产业发展对世界的主要贡献在于:突破了只有中、低阶煤具有建产条件的认识,实现了以沁水盆地南部为代表的高煤阶煤层气藏的商业开采。近年来煤层气地质的主要进展包括煤层气的多元化成因、煤层气成藏的宏观地质机理、煤层气成藏效应。其中基于原创性思维的煤层气成藏效应研究尤其值得关注,主要涉及含煤层气系统弹性能及其耦合控藏效应、多层叠置独立含煤层气系统、深部煤层气成藏作用的特殊性等方面[3]。中国煤层气勘探开发趋势是由中高煤级向低煤级储层、由浅部向深部、由单一煤层(组)向多煤层(组)、由地面开发向井地立体式开发、由陆地向海洋、由煤层气单采向煤层气与煤成气共采方向发展[4-5]。
(2)煤系致密砂岩气。
煤系致密砂岩气是指以煤层或煤系页岩为烃源岩,以致密砂岩为储集岩,且源储紧邻的非常规天然气。煤系砂岩气具有以下特征:煤系中普遍发育细粒碎屑岩,储集条件相比于常规天然气要差,穿插气源充足,致密砂岩与烃源岩大面积紧密接触,含煤地层旋回性强,可发育多套生储盖组合的非常规天然气藏。煤系致密砂岩气的成藏以源储紧邻、弥漫式充注为特点。我国鄂尔多斯盆地东缘的临兴区块、石楼西、大宁—吉县区块相继取得煤系致密砂岩气的勘探与开发突破,准噶尔盆地准东斜坡带三工河组、头屯河组砂岩气勘探也有不同程度的进展,具备良好的勘探前景[6]。秦勇指出,无论地质认识还是勘探开发技术,未来10年煤系致密砂岩气比煤系页岩气更为现实[7]。戴金星院士认为,与煤层气、页岩气等非常规气相比,中国近期在非常规气勘探开发中应以致密砂岩气为先,同时指出我国目前勘探发现的致密砂岩气全部属于煤成气,即气源都来自于煤系中的Ⅲ型泥岩或腐殖煤[8]。这是由于致密砂岩孔渗极低,只有“全天候”气源岩煤系连续不断供气,才能形成大气藏。可见煤系致密砂岩气研究与勘探开发的意义与重要性。
(3)煤系页岩气。
煤系页岩气是页岩气的重要类型之一。煤系干酪根以腐殖型(Ⅲ型)为主,H/C较低,TOC较高,生烃母质的性质导致煤系泥页岩以生气为主,具有长期缓慢生烃、排烃困难且效率低、残留烃量大等特点[9]。有关专家和机构初步预测结果显示,我国部分盆地或地区煤系气中煤层气、致密砂岩气、页岩气地质资源量平均占比分别为36.61%、23.53%和39.86%[10-11],可见,页岩气占有最高的资源比重。
此外,煤系灰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均被发现,比如在山西霍西煤田太原组发现了煤系灰岩气,在青海聚乎更矿区中侏罗世煤系中发现了天然气水合物。尽管位于不同的储层,但整套含煤岩系在物源类型、沉积环境、构造热演化等方面具有显著的一致性。因此从成藏空间分布来看,煤系非常规天然气具有同盆共生的特征[12]。煤系气勘探开发扩展了原来只考虑煤层气的视野,可有效提升单井产量,煤系气共生共探与共采受到我国天然气界高度关注[5],尤其临兴区块煤系砂岩气的产能突破极大提升了业界信心。傅雪海等设计了煤系“三气”原位分隔合采工艺技术,可有效提升不同类型储层的合采效率[11]。
2. 煤系伴生稀有元素矿产
煤系伴生稀有元素矿产资源的研究在国内外逐渐受到重视与关注,已成为煤地质学领域新的研究热点和前沿方向,对于我国煤炭行业转型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13]。在特定地质条件下,煤中可以富集如锂、镓、锗、铀、稀土元素等金属元素,另外贵金属元素如铂族元素、金、银、铌、铯、钪、铷和锑等也在煤中富集,并达到可利用的程度和规模[14-15]。作为电子工业的重要原料,锂、镓、锗3种战略性矿产在煤中的富集程度与利用前景受到更多关注。我国煤中锂、镓富集区主要分布在华北石炭 — 二叠纪和华南二叠纪两个聚煤期,锗主要分布在东北早白垩世和滇西新近纪聚煤期,含煤盆地物源和区域性断裂的控制使煤中锗、镓、锂金属元素呈区域性分布的特点。在山西宁武煤田平朔矿区和准格尔煤田发现两个超大型伴生锂矿,同时提出了其综合利用品位,这是一种新的成矿类型,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16-18]。煤中的稀土元素同样值得关注,虽然煤中稀土元素含量偏低,难以直接利用,但煤灰中的稀土可以相当富集,并可望得以综合利用[19]。DAI 等指出准格尔煤田官板乌素煤矿煤中稀土元素的含量达到154μg/g,黑岱沟煤矿最高达到255μg/g,可以综合回收利用[20]。
3. 煤中有害元素
相比于有益元素矿产,有害元素的分布与成因更加值得关注,岩浆热液造成煤中微量有害元素富集已有较多报道[21-23]。岩浆热液形成的方解石和黄铁矿脉是河北峰峰矿区无烟煤中Zn、As、Mo、Cu、Ni、Co等微量有害元素富集的主要载体[24]。S是煤中的主要有害元素,在煤炭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含硫气体可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危害。随着环保要求的持续增长,关于煤中含硫量分级也做了修正,目前最新的国家标准“煤炭质量分级”第二部分“硫分”(GB/T15224.2 — 2010)对含硫量进行了重新分级,要求比过往更加严格,比如过去将全硫含量大于4%定为高硫煤,现在则将这一标准降到了3%。相应内容也应在“煤田地质学”课程教学中加以强调。
此外,国内外闻名的黔西地方流行病氟中毒常常归因于黔西晚二叠世煤中高含量的氟以及不科学的燃煤方式。通过代世峰等研究发现,该区煤中氟含量接近于中国大部分煤中氟的含量和美国煤中氟的平均含量。然而,当地居民把黏土作为煤燃烧的添加剂和制作煤球的粘合剂,这种黏土中的氟含量很高,均值为1027.6μg/g,它是造成黔西地方流行病氟中毒的根本原因[25]。另外,西安市2017年开展了大规模治霾行动,市内所有燃煤企业停工整顿,市政供暖方式由燃煤改为燃气,但西安市的雾霾并未得到有效缓解。上述现象给我们启示,不能盲目将煤作为产煤、用煤地区所有污染、健康、生态等问题的罪魁祸首,而应以科学的态度理性分析。
二、“煤田地质学”课程发展趋势
在以上3个领域的发展推动下,煤田地质学的学科内涵被极大延伸,研究领域和关注层次被极大拓展。因此,新时期对“煤田地质学”课程内容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来的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应围绕这些方面强化课程内容建设与教学改革。
1.拓宽思路
煤田地质学绝不仅仅是研究煤层本身,煤系处处皆资源,曹代勇等从经济性、赋存特征、成因机制等方面对煤系矿产资源进行了分类,包括煤—能源矿产、煤—金属矿产、煤—非金属矿产、煤—能源矿产—金属矿产、煤—能源矿产—非金属矿产、煤—非金属矿产—金属矿产等6大类[26]。未来应高度聚焦煤系矿产资源一体化勘查与开发的方向,拓宽教学思路与课程内容。在传统煤田地质学讲授内容的基础上,重点加强煤系非常规天然气、煤系伴生稀有元素矿产两个方面的课程内容与课时安排。当然,这些内容的学习需要油气地质学、矿床学的相关理论支撑,对学生的专业基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学过程中也可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穿插介绍、补充其他相关地质学科的基本原理与方法,这也对授课教师提出了更高要求。
2.学科融合
随着非常规油气地质学的不断发展,传统煤田地质学和石油天然气地质学的界线逐渐模糊,呈现出不断融合的趋势,比如煤属于Ⅲ型干酪根,是重要的油气烃源岩(生气),同时发育复杂的孔裂隙结构,可作为有效储集岩,还可作为天然气的有效封盖层。含煤地层频繁叠置的沉积旋回是煤系气共生的基础,造就了多源、多储、多盖的成藏特点,层序地层学在煤及煤系气地质研究中的重要性日趋显著。煤成油也曾被广泛关注(吐哈盆地),柴北缘地区大煤沟组煤系泥页岩中发育页岩油。石油地质学中标定烃源岩有机质成熟度也是借鉴煤田地质学中的镜质体反射率。同时,我国诸多盆地为煤、油、气共生盆地,比如鄂尔多斯盆地、塔里木盆地等,化石能源一体化勘探开发已成主流趋势,对能源地质勘查人才的知识维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在“煤田地质学”课程中交叉介绍油气地质学、非常规油气地质学的内容势在必行。同时,如前所述,煤系伴生矿产还包括金属矿产和非金属矿产,矿床学也是煤田地质学的重要基础。严格意义来讲,煤田地质学是广义上矿床学的一个分支,即有机矿床学。
3.绿色勘查
随着环境保护的需求越来越高,开发任何矿产资源都不能以牺牲环境和人类健康为代价。作为高碳能源的典型代表,煤的绿色勘查与清洁利用成为必然,谢和平院士提出了未来煤矿“井下无人、井上无煤”的科学构想[27],煤炭地下气化可行性及地质风险日益受到关注。煤地质领域的学者提出了“洁净煤地质”概念,建立了煤炭资源洁净潜力评价体系,查明了煤中有害元素的迁移转化机理和环境效应,建立了有害元素的分级方案[28-30]。西北地区无疑是我国未来煤炭储量、产量新的增长地,煤炭资源勘探开发西移已成为我国的主要能源战略。而西北地区普遍干旱,生态环境脆弱,煤炭开采可能导致的生态问题包括河水断流、泉水干涸、水位下降、地表沉陷等,王双明院士指出,西部煤炭开采应以保护含水层与地表植被为核心,决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并提出了保水采煤的科学构想[31-33]。因此,如何协调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以实现科学探煤、采煤,是西部地区煤炭开采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绿色勘查的理念应运而生并逐渐深入人心,“煤田地质学”课程中急需补充相关课程内容,包括煤的绿色勘查理念、方法与技术,煤中有害元素的分布、成因及清洁利用、西部保水采煤方法与理念等,以顺应煤炭低碳化、洁净化、低(零)生态损伤发展的趋势,并培养学生的环保思维与社会责任感。
4.新内容、新方法
重点围绕煤田地质学近年取得的最新进展,调整、纠正陈旧的、甚至错误的教学内容,明确新认识、新概念。比如,关于断坳盆地的概念,过去教材认为兼具断陷盆地和坳陷盆地的性质,这一概念非常模糊且无实际意义,目前强调时间序列上的变化,即由早期的断陷盆地演化为后期的坳陷盆地,且无沉积间断[34]。类似的内容急需进行修正。另外,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涌现出的新方法、新技术值得关注。比如在煤层气储层表征方面,核磁共振、X-CT扫描等无损测试技术得到广泛应用,在表征储层孔隙结构、流体赋存与运移状态等方面效果良好[35-38]。此外,扫描电镜、傅里叶红外光谱、电子顺磁共振、X射线衍射、X射线光电子能谱、原子力显微镜等技术手段也逐渐被广泛应用于煤的化学结构与组成分析。在教学中适当介绍这些新技术、新方法,可有效提升学生的业务素养,增强就业、深造的潜力以及社会竞争力。
三、结论
煤炭资源的多重价值体现在含煤岩系中多种矿产资源的共生组合与共采潜力,“煤田地质学”课程教学也应与时俱进,紧密结合煤系非常规天然气、煤元素地球化学与矿物学、保水采煤领域取得的最新成果,以及煤系处处有资源与绿色勘查的发展理念,对相关课程内容进行调整与改革,未来应重点聚焦于“拓宽思路”“学科融合”“绿色勘查”与“新内容、新方法”4个方向的发展趋势,推进煤田地质学教学内容与方式方法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