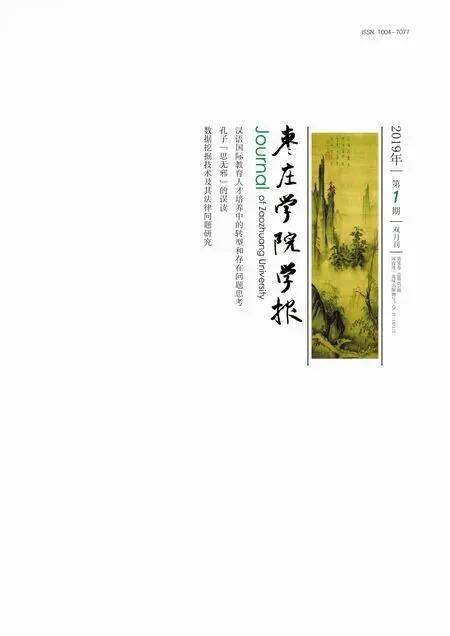中国古代劝进之“稳定”心态论
王承斌
(许昌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河南 许昌 461000)
本文所论劝进,主要指古代臣子在帝王继位前所行的劝即位行为。①在中国古代王朝更替过程中,这类事件较多。一直以来,人们对此一般持否定态度,认为劝进主要是臣子为谋功名富贵而向帝王示忠、阿谀奉承。勿庸讳言这种心态在劝进中时有发生,有时还较为明显。然我们的认识若局限于此,则会失之肤浅。古人劝进思想实较复杂,追求稳定是其中非常重要的方面。客观认识这类事件,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封建社会士大夫之思想和生活态度。
一
中国古代劝进事件中有明显的求稳定目的,表现之一便是劝进言辞中有大量“天下不可一日无君”“帝王不可久旷”“安社稷”“宁海内”等内容的表述。
如两汉之际的混战中,刘秀部下以“帝王不可以久旷,天命不可以谦拒,惟大王以社稷为计,万姓为心”[1](P21)劝进。三国时诸葛亮等在蜀劝进刘备: “愿大王应天顺民,速即洪业,以宁海内。”[2](P888)西晋灭亡后,刘琨、慕容廆等劝进司马睿:“蒸黎不可以无主……社稷靡安,必将有以扶其危;黔首几绝,必将有以继其绪……尊位不可久虚,万机不可久旷。”[3](P146)南朝刘宋太子刘劭弑帝后即皇位,众叛亲离,刘义恭等劝进刘骏:“今罪逆无亲,恶盈釁满,阻兵安忍,戮善崇奸,履地戴天,毕命俄顷,宜早定尊号,以固社稷。”[4](P1646)南朝梁傀儡皇帝萧纲被害后,侯景自立为帝,梁朝灭亡,徐陵、沈炯等人以“万国岂可无君,高祖岂可废祀”[5](P119)来劝进梁元帝。后燕皇帝慕容盛在国内兵变中被杀,群臣以“国多难,宜立长君”[3](P3105)劝进慕容熙。安史之乱暴发后,唐玄宗逃亡四川,无心理政,国家混乱,裴冕等人劝唐肃宗“愿陛下顺其乐推,以安社稷。”[6](P242)五代十国时后唐庄宗李存勖死于兵变,长子李继岌亦亡,国家无主,动荡不安,群臣劝进李嗣源“行监国之仪,以安宗社。”[7](P490)又后唐李从珂起兵击败闵帝,冯道等劝进说:“洪基大宝,危若缀旒,须立长君,以绍丕搆……一日万机,不可以暂旷;九州四海,不可以无归。”[7](P629~630)北宋灭亡后,南逃大臣耿南仲、汪伯彦、张俊等人以“中原不可一日无君”[8](P11347)劝进宋高宗赵构,期盼“中外之协心,同定安危之至计”[9](P107)“亟行天讨,兴复社稷。”[8](P11278)元代蒙哥汗去世后,在激烈的皇位争夺中,赵良弼等人劝进忽必烈:“今中外皆愿大王早进正宸,以安天下,事势如此,岂容中止,社禝安危,间不容发。”[10](P3744)又元成宗去世,成宗次兄之子爱育黎拔力八达等人以“神器不可久虚,宗祧不可乏祀”[10](P479)劝进武宗。明建文帝朱允炆实行削藩,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攻入应天府后建文帝下落不明,臣子以“天下岂可一日无君”[11](P272)劝进朱棣;明英宗被俘后,国家无主,“时议者以时方多故,人心危疑,思得长君以弭祸乱。”[11](P479)在瓦剌大军逼近的生死存亡关头,于谦等大臣忧国忘身,劝新主朱祁钰“早正大位,以安国家。”[11](P479)等等。
这些劝进多发生在局势动荡之时,无论是天下无主、群雄纷争,还是天下有主却不能治国理政而致混乱,臣子们劝进中所说之“安社稷”类绝非虚言,他们劝进新主即位,是渴望在乱世中辅佐君王,君臣同心协力、名正言顺地“安社稷”“弭祸乱”,再建稳定统一大业,实现个人治国、平天下之理想,此乃儒家思想之体现,这在许多劝进言辞中表现明显。如刘秀部下劝进时所说“攀龙鳞,附凤翼,以成其所志耳”[1](P21),“其所志”便是他们心中建功立业之志。南朝梁末徐陵、沈炯等劝进梁元帝:“待陛下昭告后土,虔奉上帝,广发明诏,师出以名”[5](P119),希望与君王一同“廓清函夏”[5](P117),实现其“治平”愿望。北宋灭亡后,耿南仲、汪伯彦、张俊等人劝进宋高宗赵构,期盼“中外之协心,同定安危之至计”,君臣同心协力“亟行天讨,兴复社稷”等,均是此意。有些劝进言辞中还有鲜明的忧国忧民色彩,如两晋之交刘琨等人劝进时说:“自元康以来,艰过繁兴,永嘉之际,氛厉弥昏,宸极失御,登遐丑裔,国家之危,有若缀旒……四海想中兴之美,群生怀来苏之望。”在回顾了元康以来社会动荡不安、国家危在旦夕之后,紧接着指出民众内心的悲愤:“厄运之极,古今未有,苟在食士之毛,含气之类,莫不叩心绝气,行号巷哭。况臣等荷宠三世,位厕鼎司,承问震惶,精爽飞越,且悲且惋,五情无主,举哀朔垂,上下泣血。”“陛下虽欲逡巡,其若宗庙何?其若百姓何?”[3](P146)饱含了对国家、民生的殷切关怀,对新帝登祚稳固社稷、安定万民的殷切期待和深挚的忧世情怀,感人至深。
“治国、平天下”是古代士人的人生理想,是许多人为之奋斗终身的目标。混乱的时局,尤能激起士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劝进那些手握兵权、有声望者“进正宸”“正大统”以定人心,希望君臣共同努力稳定局势,进而再现统一稳定之盛世局面。其中包含的稳定心态、“治平”思想十分明显。这一点较好理解,无须多论。
二
劝进中稳定心态的第二种表现是强调“正名位”。如刘邦统一天下后群臣劝进说:“诛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辄裂地而封为王侯。大王不尊号,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12](P379)诸将“皆疑不信”,主要是因此前周代分土封侯为帝王之权力,刘邦不即帝位,则分封诸将行为名不正、言不顺,故被分封者疑虑不安。南朝刘宋时刘义恭等劝进刘骏“宜早定尊号,以固社稷”,即早称尊号以正名。南朝梁末徐陵、沈炯等人以“待陛下昭告后土,虔奉上帝,广发明诏,师出以名”[5](P119)劝进梁元帝。代国灭亡后,拓跋珪率兵平乱,许谦等以“宜正位居尊,以副天人之望”[13](P2734)劝进。隋末混乱中,裴仁基等劝起义军首领李密即尊位“正位号”[14](P5774),又裴寂等人以同样意思劝进李渊。②两宋之交,南逃臣子以“当天下汹汹,不早正大位,无以称人望”[8](P11470)劝进宋高宗。元泰定帝崩,群臣以“扰攘之际,不正大名,不足以系天下之志”[10](P3328)等劝进图帖睦尔(文宗)。明代靖难之役后,臣子劝进燕王朱棣:“殿下为太祖嫡嗣,徳冠群伦,功在社稷,宜正天位,使太祖万世之洪业,永有所托。”[11](P272)明英宗被俘后,于谦等大臣劝进新主朱祁钰“早正大位,以安国家”等。
有人认为这类“正名”说法只是劝进者为取悦被劝进者、为谋私利而寻的借口。实际上并非如此,正名位是封建社会巩固政权、维持稳定秩序的重要措施和必须手段。
首先,在天下无主而致的混乱纷争中,正了名位,建立合法政权,可获得政治上的主动,最终虽未必能成功,却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民众认同,给士人以归属感,③能增强凝聚力——“系天下心”,更顺利地争夺人才、臣服雄杰等。在古人看来,“是非之正,取之逆顺。逆顺之正,取之名号”[15](P354),“名苟不正”则难以服众,会“事有不从”,而凭“帝命以伐有罪”,“师出以名”,则名正言顺,会更有号召力,更利于巩固现有政权乃至平定混乱、统一天下,正如鲁昌劝进晋元帝时所说:“诸部犹怙众称兵,未遵道化者,盖以官非王命,又自以为强。今宜通使琅邪,劝承大统,然后敷宣帝命,以伐有罪,谁敢不从。”[3](P2806)从中不难看出他们渴望辅佐新主建功立业、实现“治平”的愿望。当然,乱世中不是任何人、任何情况下正名都有此效果,只有被劝进者本身是尚受拥护的已亡政权合法继承人,即旧皇室之后裔,如司马睿之于西晋王朝,赵构之于北宋王朝等;或乱世纷争中功勋显赫而受众多士人拥护者,如汉光武帝刘秀,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等。若两条都不具备而称帝号,则无甚作用甚至适得其反。
这种“正名”作用在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上有较明显体现。曹操挟持汉天子,将“名”控制在自己手中,代表着中央与正统,在四处征伐过程中取得了巨大优势。“汉天子”招牌,对社会上一些中小军阀产生了强烈影响,为曹操赢得了当时重要社会力量——士家大族的支持,赢得了社会舆论的支持、雄才俊杰的依附等。相反,反对曹操便为不义,是悖礼叛逆。名分之“正”的作用在此得到了充分体现。这方面,笔者在《先唐劝进文中正名思想论析》一文中有过论述,可参看。虽此“正名”与本文所论有差别,然无本质不同。劝进中的正名主张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
其次,就禅代而言,当时旧皇虽在,但大权旁落,权臣势大,出现君不君、臣不臣现象。这是“名”之乱,不符合应有秩序与规范,对安定民心、维持统治秩序不利,极易导致政治上的混乱。因权臣长期执政,故禅代之际朝中大臣基本上都是权臣集团成员,他们之劝进虽有谋集团利益、谋个人政治资本之嫌,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包含着通过正名来改变名实不符现状以消除隐患、更好地维持统治秩序之意图。众所周知,历史上因权臣执政引人不满,臣子与失势君王联合夺权,或者借“勤王”、尽忠王室之名行反叛者不在少数,这在曹操、司马昭、武则天等人身上均发生过。④无论是真心维护皇权,让其名至实归,还是别有用心,这种夺权、叛乱主要是由权臣控制朝政、君臣名实不符而起,或者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借口。相反,若权臣在众人拥护下取代旧皇,正名即位建立新政权,则能消弥不少此类祸乱。因此时若有人再行反叛,那便是以下犯上,反而名不正、言不顺,被置于极不利地位。所以说,这种情况下之“正名”,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政权的稳定。
正名思想在中国社会由来已久,其最初产生的目的正是为了稳定政权,消除社会混乱。春秋时期天子失政,社会动荡,当时诸侯既不忠君,也不从君,而是称王称霸,各自为政。面对这种情况,孔子提出为政必先“正名”的主张。他认为“君”“臣”“父”“子”等每一个名,都有其一定意义,即这个名该有的行为规范,它所指事物应该如此的标准。“正名”就是要求处于君、臣、父、子等不同地位的人,所行符合此名应有的标准规范,如“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16](P66),“事君不贰是谓臣”[17](P347)等。君臣各自履行自己的职责,不得逾越,做到名实一致,只有这样才能消除社会动荡。正名思想在后世一直为人们所重视,相关论述甚多,不一一赘述。大体而言,这种思想与儒家礼教关系密切,其政治上的内涵,主要是通过正君臣之名来稳固封建统治,君实施名赋予它的统治权力,臣子无条件服从君主命令。徐复观先生在“名”之作用方面曾有过精辟论述,他说:
在以老子、孔子为中心的文化活动中,可以说原始的咒语,完全由合理的思维和合理的言语所代替了。但名的神秘性虽在宗教中褪色或消失,却在政治上还发生很大的作用。贵族的统治阶级,把自己由地位而来的名,认为即是政治权力的真。有此名,即无条件地应有此统治权力,人民即应无条件地服从他的权力。[18](P208)
封建统治阶级认为,他们由地位而来的“名”本身就是“权力的真”,是权力正当性的来源,代表着在社会上拥有绝对的统治权、处于支配地位,其他人应无条件服从,如“诸侯之义,非天子之命,不得动众起兵诛不义者”,[19](P213)“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15](P386)等等。名位正,且在君无过失、无暴政情况下,诸侯不听命就是对“名”的破坏,是背离“礼”和君臣伦理,为逆天而行、大逆不道,那将遭致众人的反对,天子更可以发号司令、“恭行天罚”以征讨剿灭之。正名之作用实显而易见。
“正名”是合法政权建立时必须重视的。任剑涛先生在探讨中国政治的合法性时,就提到儒家在建立政治合法性过程中礼与正名缺一不可,他说:“‘正名’,即按照伦理道德的规范端正政治行动的名分,就是一个树立政治合法性权威必须重视的事情。”[20](P27~34)也就是说,正名可以较好地解决政治合法性问题和避免政治危机的出现,它在封建社会政治上有着明显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劝进正名的最终目的,或是为便利地稳定局势、实现一统,或是为国家的长治久安。
三
劝进中稳定心态的第三种表现,是“天命”“人心”的表述,此为证明被劝进者进位乃顺天应命、顺人心之举,许多劝进事件中均存在。如刘秀部下劝进时说:“帝王不可以久旷,天命不可以谦拒,惟大王以社稷为计,万姓为心。”诸葛亮等劝进时称刘备:“圣姿硕茂,神武在躬,仁复积德,爱好人士,是以四方归心”。[2](P888)隋末混战中,段达等人以“天命不常,今郑王功徳甚盛,请揖让,用尧、舜故事”[21](P3693)劝进王世充。安史之乱暴发后,裴冕等人以“万姓颙颙,思崇明圣,天意人事,不可固违”等劝进唐肃宗,希望他“即皇帝位以系中外望”。[6](P242)后汉刘知远功勋卓著,张彦威等劝进说:“今远近之心,不谋而同,此天意也。王不乘此际取之,谦让不居,恐人心且移,移则反受其咎矣。”[14](P9340)完颜阿骨达维护女真部落联盟有功,阿里罕普嘉努宗翰等人称:“大功已建,若不称号,无以系天下心。”[22](P26)金攻陷辽都后辽天祚帝逃亡,李处温等劝进耶律淳:“主上蒙尘,中原扰攘,若不立王,百姓何归?”[23](P352)北宋亡臣劝进宋高宗赵构:“大王皇帝亲弟,人心所归,当天下汹汹,不早正大位,无以称人望。”希望赵构“早正大宝,以定人心,以应天意”[8](P11701)等等。
在新旧王朝禅代期间的劝进里,这种“天命”、“人神属望”表述更集中,劝进者同时还列天地祥瑞之出现以证明它。此乃为权臣进位造势。如曹丕称帝前,“侍中刘廙、辛毗、刘晔、桓阶、陈矫、陈群等,争陈符命劝进。”[24](P286)司马伦执政期间,“宗室诸王、群公卿士咸假称符瑞天文以劝进。”[3](P1601)群臣劝进刘裕时说:“‘有命自天’……‘勋格天地’者,必膺大宝之业。”“太史令骆达陈天文符瑞数十条,群臣又固请,王乃从之。”[4](P48)劝进萧衍:“君临万方,式传洪烈,以答上天之休命。”[5](P29)杨坚上位前,百官列举当时出现的“赤雀降祉,玄龟效灵,钟石变音,蛟鱼出穴”[25](P12)等祥瑞劝进,北周静帝禅位诏中也说道:“上则天时,不敢不授,下祗天命,不可不受。”[25](P12)徐知诰被群臣劝进时,认为“人望己归”[26](P767)而即位建国,等等。
这其中的“天命人心”、祥瑞之说,并非如有些人所认为是劝进者自欺欺人之谈。古人多认为,受命于天,其政权便是合法的。如班固就曾说:“受命之君,天之所兴,四方莫敢违。”[19](P349)而祥瑞的出现,正是天意认可的表现。劝进中明言这些,也是意在解决政权合法性问题,是为避免出现政治危机所作的努力。然众所周知的是,汉代董仲舒主张“天人感应”神学理论,他融合先秦儒家“天命论”和阴阳家的五行学说,提出“天”是有意志的至高无上的神,皇帝受命于天,体现天的统治权力,君权神圣不可侵犯;并认为政通人和,得上天认可,天降祥瑞以昭告;而君王失政,致民怨国危,天便降灾难以警示、惩罚——“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异以谴告之。”[15](P318)后来这又与河图、洛书等神话传说相结合,发展出荒诞不经的谶纬之学。此说汉魏之际已不时受人批判,逐渐为人们所抛弃。然劝进中为何一而再地提及天命、祥瑞?其实,此中天命、人心思想及祥瑞意识,非汉代谶纬思想之翻版,更多地是对传统天命、民心思想的继承。
天命思想在夏和西周时代便已产生。《尚书·召诰》有“有夏服天命”[27](P471)之说,即夏王朝受天之命统治万民。商代,天命思想仍和宗教迷信思想有密切关系,但已经有了“天命即人心”观念的萌芽。《尚书·泰誓》中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27](P329),已包含人心即天命思想。《汤誓》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27](P227),谓天命欲亡夏桀,是因其“多罪”,若“有夏无罪”,天命则未必“殛之”。以此而论,天命实际在人而非在天。春秋战国时期,天命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孟子在论天人关系时注意到人的作用,既认为君权天授,又强调君权要“民意”认可,提出了“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28](P194)及“以人为本”等主张。而汉代贾谊在论及王朝兴衰时,也认为人的善恶行为与天命有着直接关系:“知善而弗行,谓之不明;知恶而弗改,必受天殃。天有常福,必与有德;天有常灾,必与夺民时。”(《大政》)[29](P268)等。可见古人认为执政者需受天命、得民心,这样才能长治久安,否则统治难以持久。刘泽华先生研究古代政治思想时认为:“植根于天人之际的权力合法性较之诉诸武功和先祖列宗而言,无疑是一种更为广泛和深厚的传统。”[30](P314)这种传统思想是劝进中天命、人心说的基础。
劝进中与天命相关的祥瑞意识,与其说与谶纬有关,不如说是原始先民祥瑞祈求的表现。祥瑞思想起源甚早,原始部落的图腾已包含有祥瑞意识,它源于先民对灾难、死亡的畏惧,对幸福、美好、平安的追求,体现了趋吉避凶、消灾保平安的本能。徐华龙《中国祥瑞文化》、宁业高《中国祥瑞文化漫谈》等著作对此有详细阐述,此不赘。“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出妖孽”[31](P1693)类思想早有萌芽,如《诗·小雅·十月之交》中写日食、月食、地震等自然现象,并将之与朝廷用人不善联系起来,认为它们是上天对人类的警告——“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32](P845)便是其表现。
传统的天命、祥瑞思想,积淀在人们内心形成受天命、得民心将会天地呈祥、国泰民安观念。劝进中应天命、顺人心内容的陈述,正是这种观念的不自觉体现,表现了劝进者对稳定政治的渴望。也可以说,是用人们对盛世、德世,对和平、稳定生活的期盼,为被劝进者上位寻求稳固的统治基础。
四
稳定心态的第四种表现,是劝进文中功德的陈述。如言刘秀“平定天下,海内蒙恩”,[1](P22)完颜阿骨达维护女真部落联盟有功,抗辽中战功显赫,阿里罕普嘉努宗翰等人说“大功已建,若不称号,无以系天下心。”明代臣子劝进燕王朱棣时强调:“殿下为太祖嫡嗣,徳冠群伦,功在社稷”等。这方面更明显的表现是禅代过程中群臣劝进权臣。如王莽进位过程中,群臣上书称颂其“收复绝属,存亡续废,得比肩首,复为人者,嫔然成行。所以藩汉国、辅汉室”[33](P4083)等功德者比比皆是。赵翼曾说这一过程:“始则颂功德者八千余人,继则诸王公侯议加九锡者九百二人,又吏民上书者前后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34](P71)可见人们对此之重视。其他劝进中都或多或少有这方面内容。
因种种原因,前人对此功德之陈述一直颇有微词,禅代过程中这方面内容尤受诟病,被认为是为进位者歌功颂德,是为求个人名利而阿谀奉承。如赵翼曾说:“盖自汉魏易姓以来,胜国之臣,即为兴朝佐命,久已习为固然。其视国家禅代,一若无与于己,且转藉为迁官受赏之资。”[35](P322)后世人也多持此见。实际上,这种认识有失偏颇。无论禅代还是混乱之际的劝进,这种功业的陈述乃是必须,是新政权稳定之基础,无此则不能服众,易致混乱败亡。就目前所见众多劝进言辞看,这方面陈述或有所夸大,然大多实有所据,非纯粹阿谀奉迎类溢美之词。乱世中功勋显赫者,如刘邦、刘秀、完颜阿骨打、朱元璋等自不用说,禅代时被劝进之权臣也都是有相当声望、有坚实政治基础者,如王莽、曹丕等;许多更是在天下分裂、皇权衰弱之际累建战功而功勋卓著者,刘裕、萧道成、萧衍、陈霸先等无不如此。没有这种声望和功德,没有自己的势力集团,欲受禅绝无可能。传统德治思想是劝进中功德陈述的内在原因。
中国古代儒家一直信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这一点。《左传?僖公三十三年》中便有“德以治民”语。《尚书·尧典》称尧“克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27](P31)认为“克明峻德”可致“协和万邦”,统治稳固,即君主个体道德是政治的基础。孔子则明确提出“为政以德”的政治理念,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16](P15)又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6](P16)将德和礼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为政治民需以德,则大德者当有天下。《中庸》中说道:“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31](P1705)谓只有具仁德者方可治理天下,树立天下之根本法则。禅代过程中旧皇之退位诏,也多有对受位者功德的陈述,如汉献帝退位诏中说:“是以前王既树神武之绩,今王又光裕明德以应其期”[36](P861),魏元帝禅位于西晋诏曰:“惟王乃祖乃父,服膺明哲,輔亮我皇家,勳德光于四海”[3](P50)等等,几乎无有例外。虽其中所说未必是真心之言,然“天命无常,惟归有德”思想却十分明显。
“有德者居天下”之思想影响深远。被劝进者若无功德则无法服众,功高德大者上位,才能得到最大多数人的支持,“协和万邦”,建立稳固的统治。劝进中功德的陈述明显体现出这种德治思想,或者说是劝进者进行的仁德宣扬与劝说,也正是他们渴望国家稳定的表现。
最后须提的是,常被人批判的劝进者谋取个人利益这一点我们并不完全否认,那在一些劝进中客观存在,然这不仅与本文所论其中稳定心态的存在不矛盾,反而更能证明之,因稳定的局势方符合士大夫阶层的利益,进一步说,个人利益本就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二者本为一体,政局不稳,天下混乱,个人、家族、国家利益均将受损。综而言之,无论从哪方面看,谋求稳定都是古代劝进的重要目标之一。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诸多劝进,许多确实在特定历史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维护了国家的统一、稳定。对此,我们应给予客观而全面的评价。
注释
①中国古代劝进有两种类型,一是劝即最高帝位,如侍中刘防等劝曹丕代汉等,这类劝进较多;一是劝权臣接受帝王给予的九锡之礼等赏赐,如郑冲等劝司马昭受礼等,此类较少。两类虽有差别,然无实质的不同,本文侧重论述前一类.
②裴寂等劝进说:“桀、纣之亡,亦各有子,未闻汤、武臣辅之,可为龟镜,无所疑也。寂之茅土、大位,皆受之于唐,陛下不为唐帝,臣当去官耳。”(《旧唐书·裴寂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2287页。)裴寂等人从唐王处得土地、封号,唐王不称帝,则此分封名不正言不顺。这与群臣劝进刘邦时所说“大王不尊号,皆疑不信”情况类似.
③封建时代士人效忠之对象、最终之归属是国家,而国家之代表为皇帝。国亡世乱,天下无主,士人无所归依,内心惶惶,故渴望自己所属集团首脑尽快“正位”,建立合法政权,使自己有归属感.
④武则天情况特殊,她在唐高宗时控制朝政,虽不属权臣执政,实无甚差别,均造成君主名存实亡之结果。故列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