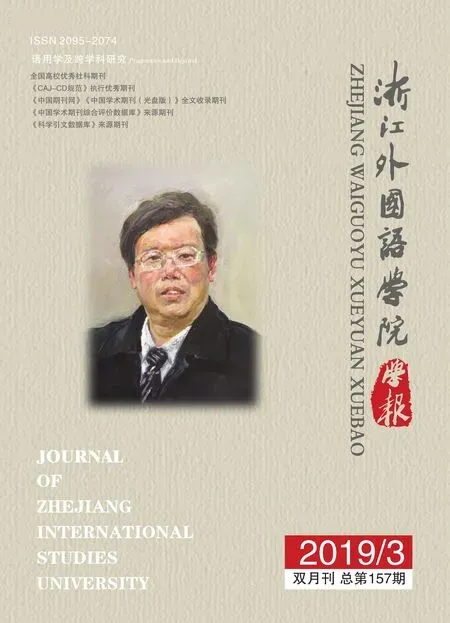《修理匠》中的医学伦理
陆 贇
(江苏理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常州 213001)
一、引言
2010年,美国作家保罗·哈丁(Paul Harding,1967— )凭借处女作《修理匠》(Tinkers)一举夺得普利策小说奖,成为当年美国文坛的黑马。评委会称赞这部小说是“对生命的大力颂扬,新英格兰地区的一对父子,经历苦难和欢欣,超越他们受到束缚的人生,以全新的方式来感知世界、应对死亡”①参见普利策奖官网(https://www.pulitzer.org/winners/paul-harding)。。
《修理匠》的核心主题是医学伦理(medical ethics)。根据世界医学会(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的定义,医学伦理指的是“医学实践中的道德问题”,尤其是患者、家属、医师、医院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处理(Williams 2009:9)。通常认为,公元前5 世纪古希腊医师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倡导的职业誓言是古代医学伦理的雏形,并间接影响到古罗马法律中的相关规定。中世纪之后,现代意义上的医学伦理思想开始萌芽。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和医学实践的发展,到19 世纪时,医学伦理已成为特定的研究对象。1803年,英国医师托马斯·珀西瓦尔(Thomas Percival)以《医学伦理》为题出版专著。这是该术语首次以正式形式出现在医学文献之中(Jonsen 2000:58)。1847年,美国医师艾萨克·海斯(Isaac Hayes)在珀西瓦尔的基础上,提出美国版的医学伦理准则。他用当时流行的社会契约论来描述患者、家属、医师、医院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并且强调患者理应担负起相应义务,配合医师的治疗方案。这套准则历经五次修订,对于美国的医学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Jonsen 2000:69)。
自20 世纪80年代起,随着伦理批评的发展以及叙事医学的兴起,文学作品所涉及的医学伦理问题开始引起关注。阿瑟·弗兰克(Arthur Frank)提出,疾病叙事起到了重要的见证作用,不仅让读者关注人物的“道德选择”,同时也注意到作品中隐含的“社会伦理”(1995:145)。刘小枫则认为,叙事伦理学通过“讲述个人经历的生命故事”,提出“生命感觉”的问题,并探讨其中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1999:4)。研究文学作品的目的并不是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法则,而是借助具体人物的经历来唤起共鸣,反思现实生活中的同类问题。
《修理匠》是一部典型的医学叙事作品。哈丁围绕癫痫、老年痴呆等疾病,不仅塑造了鲜活的人物形象,同时也描写了激烈的家庭冲突和感人的父子亲情。本文拟从伦理秩序的破坏、伦理责任的规避和伦理关系的修复三个方面来分析作品所蕴含的医学伦理思想。
二、污名:伦理秩序的破坏
疾病造成的首要影响是患者的身份变化。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埃尔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所言,患者大多背负污名(stigma),在周围人眼中变得声名狼藉,不值得信任。并且,他们的抗争被当作“自身缺陷的直接表现”,被视为危险的源头,变成周围人排斥他们的“合理理由”(Goffman 1963:5)。
与此同时,背负污名也意味着患者在家庭中的地位直线下降。在原有的家庭伦理秩序中,男性家长通常处于强势位置,是权力的掌控者和家庭的管理者。而一旦罹患精神疾病②在严格的医学意义上,癫痫并不属于精神疾病。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对此缺乏了解,以为霍华德的精神出了问题。本文为求行文顺畅,沿用了这一说法。,不仅他的地位会遭到质疑,沦为被看管的对象,而且整个家庭的伦理秩序也将受到破坏,原先的和谐生活会被矛盾和冲突所取代。
在《修理匠》中,哈丁着重描写了主人公霍华德·克罗斯比的癫痫对于家庭伦理秩序的冲击。霍华德的妻子凯瑟琳对于癫痫缺乏了解,丈夫间歇性的发作让她不堪忍受,因此她骂丈夫是个“蠢货”,“他就是个疯子,一发病就扑腾”。直到老年,凯瑟琳依然没有谅解霍华德,声称后者“在她的心里留下了永远的阴影,让她不得安宁”③本文中小说《修理匠》的引文皆为作者根据同一版本(Harding,P.2009. Tinkers[M].New York:Bellevue Literary Press)自译,下引该书,仅随文标注页码。(Harding 2009:20)。
凯瑟琳的抱怨并非毫无道理,因为癫痫大发作的场景极其吓人。深受其害的俄国作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F.M.Dostoevsky)曾在小说《白痴》中这样写道:
癫痫,也就是羊痫风,往往是突然发作的。在这一瞬间,面孔,特别是眼神,突然扭曲,神色大变。整个身体,整个面孔,都不停地抽搐和痉挛。从胸中迸发出一种可怕的、难以想象的、奇怪的号叫。在这号叫声中,一切带有人味的东西好像一下子全都消失了。(2010:321)
这段描写抓住了癫痫的典型特征,即突发性和可怕性。看似健康的患者在瞬间就失去了正常人的模样,抽搐、痉挛、惨叫,变得更像野兽而不是人类。由于癫痫的这些特征,患者往往遭受周围人的歧视,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癫痫发作时的表象让人联想到疯狂,认为患者已经丧失常态,回归某种动物属性,甚至可能造成伤害;其二,其他人可能会对癫痫患者失去信任,认为后者随时可能发病,无法正常工作和生活。
在《修理匠》中,霍华德出现了类似的状况。1926年的圣诞节晚宴,在全家团聚的欢乐气氛中,霍华德突然癫痫发作,摔倒在地板上,浑身抽搐。他倒下时,头砸到旁边的座椅上,鲜血淋漓,整个场面十分恐怖。当时乔治·华盛顿·克罗斯比只有12 岁,这是他第一次目睹父亲发病的全过程。父亲咬着叉子的样子“像是骷髅”,乔治感到十分惊恐,他觉得“这不是人的嘴巴,不是爸爸的”(85)。随后,神志不清的霍华德紧紧咬住乔治的手,造成大量流血。此时,哈丁切换了叙事角度,从少年乔治的第一人称视角再现了他在那一瞬间的想法:
父亲显出怪异的安宁,仿佛他正凝神思索,又仿佛他正分心于他处。当他几乎咬断我的手指时,他正在微笑,或者是我感觉他在微笑,他笑得很安宁。……当我用雪松棍子撬开他血淋淋的牙齿时,我并没有感觉到,我可能正在伤害一个人,这一事实让我更为难受。到处都是我手上流出来的血,我的手指似乎和手掌分离开来。……父亲满脸是血,嘴里也是,这些都是从我手上流出的血。他的头发上有血迹,地上也有,那些都是他自己头部受伤后流出的血。……我没有感到恐惧。我心想,原来这就是真相。(87)
母亲对待父亲的态度也令乔治感到震惊。她的动作非常粗暴,就像是在制服猛兽。霍华德刚发病,她就“从乔治手中一把夺过勺子,朝丈夫猛扑过去,跨坐在他的胸口”(85)。母亲用力把勺子横着塞进丈夫的嘴里,以免他把自己的舌头咬下来。在乔治被咬住后,她依然冷漠,“一把抓住丈夫的嘴,仿佛那是个装有弹簧的捕熊夹”(87)。随后,她把雪松棍子凶狠地塞进丈夫嘴里,命令乔治用力撬开他血淋淋的牙齿。
这次发病彻底破坏了霍华德一家原有的伦理秩序。故事的背景是20 世纪30年代,霍华德一家居住在美国东北角的缅因州,当时这一地区的经济依赖农牧业和林业,工商业并不发达。霍华德主要以贩卖日用品谋生,兼做各种杂活,收入虽然微薄,却是全家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凯瑟琳是个家庭主妇,几个孩子尚未成年。在这种情况下,霍华德理应成为一家之主,获得家庭成员的尊重。然而,疾病破坏了原有的和谐,霍华德所背负的污名让他无法再管理整个家庭,不仅妻子把他当作废物,孩子们也对他失去了敬畏之心。
对于凯瑟琳来说,霍华德的身体状况日渐糟糕,已经沦为任由她处置的废物。她最终下定决心,要把霍华德送往精神病院,把他彻底禁闭起来。对于乔治来说,这段经历是个沉重打击。曾经敬重的父亲变得如此可怕,所以他先是希望父亲“就此从地球上消失”,随后又希望父亲变成一个像他一样大的孩子,并且被咬上一口,让他也能明白“被野兽般的父亲攻击是什么滋味”(112)。在偶然得知凯瑟琳的计划后,乔治并没有反对,也没有向父亲告密,而是默默支持母亲。在他的心目中,母亲才是这个家庭的支柱和掌权者。
乔治对父亲的敌意不仅源自曾经的伤痛,更在于内心的羞愧,因为一直以来的传言得到了证实,他的父亲真的是个“疯子”。这种耻辱感并没有随着乔治的成长而消失,而是转变为他对自己的精神压抑。罗伯塔·科尔伯森(Roberta Culberson)指出,在创伤性事件中留下的伤口会带给患者某种身体记忆,在他体内“产生特定的神经反应,这些反应作为事件的记忆得以保留——很大程度上保持了经历受伤和作出反应时的感受”(转引自 Frank 1995:174)。在霍华德离家出走之后,乔治手上的伤口不断提醒他过去的噩梦。与此同时,他又努力压抑相关记忆,“从不允许自己想象父亲的样子”(19)。“从不允许”这样的措辞显示出乔治内心的愤恨和恐慌,因为“从不允许”意味着他其实并没有从当初的事件中真正恢复,只不过强迫自己去压抑创伤记忆。
从乔治修理钟表的片段可以看出,父亲发病时的阴影始终困扰着他。在象征意义上,钟表代表着理性和秩序,因此修理钟表意味着用理性力量来消除混乱,重建伦理秩序。潜意识中,乔治将这一过程与关于父亲的记忆联系起来。尤其是当弹簧松脱,弹出来割伤他的手时,乔治似乎又看到“父亲坐在地板上,他的腿正踢着椅子,把地毯都踢得卷起来,灯从桌上掉下来,他的头撞击着地板,他的牙齿紧紧咬住一段木头或是乔治的手指”(20)。这样的记忆表明,乔治重建秩序的尝试并不成功。虽然乔治在自己的家庭中成了说一不二的强势家长,但是他和父亲的关系依然紧张,新的秩序并不能抚平他内心深处的伤痛。
霍华德的癫痫只是偶然发作,却依然给家人带来了莫大的困扰。凯瑟琳始终不肯原谅他,乔治一直强迫自己忘记父亲的存在。这一切的源头就在于精神疾病的污名属性。可以说,正是因为霍华德的家人用歧视的眼光看待他,没有真正体谅他的痛苦,理解他的诉求,才最终导致家庭关系的破裂。通过这样的情节安排,哈丁促使读者注意到,污名只会带来负面作用,我们应当理性对待患者,不仅要尊重他们的生命价值,积极协助其就医,而且要合理调整家庭关系,让他们继续参与家庭管理,维系良好的伦理秩序。
三、隔离:伦理责任的规避
精神疾病造成的另一个影响是患者被剥夺人身自由,以治疗的名义,在精神病院长期遭受监禁。在许多人看来,精神疾病患者属于不正常的人,“必须被隔离,被改造,甚至被彻底拒绝”(Scambler 1989:49)。对于家属来说,隔离是一个诱人的选择,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将照看患者的职责移交给精神病院,从而合理规避自身的伦理责任。
在《修理匠》中,凯瑟琳咨询了医生的意见,打算将霍华德送往缅因州东部医院。在这家医院提供的宣传画册上,她看到了干净的房间、宽敞的户外活动区,还有一幢砖头砌成的高大建筑,看起来像是高档宾馆。整个医院给凯瑟琳留下了良好印象,她觉得这是个温暖安全的庇护所。在那一瞬间,她的心理活动折射出精神病院对于她的特殊意义。她觉得就像是一个饥寒交迫的旅行者,在寒冷的冬日翻过一座山头,突然看到一座小屋,屋子的每个窗户都亮着灯,烟囱里正冒着炊烟,人们聚集在一起,享受梦幻般的快乐时光,所有的陌生人都能在这里得到庇护(102)。
仔细分析这一细节不难发现,打动凯瑟琳的并不是这家医院的治疗水平或效果,而是她把医院的刻意宣传当作精神慰藉,从而不必因为将霍华德送到那里而感到愧疚。事实上,宣传画册的内容表明,这家医院提供的治疗措施并不科学,患者要从事各种劳作,还要接受包括水疗和卧床休息这样的原始疗法。指望这些措施能够治疗精神疾病,显然是异想天开。与其说这里是医院,倒不如称其为用来隔离患者的禁闭所。
历史上,欧美等国在19 世纪大量建造了类似的精神病院。医史学者安德鲁·斯卡尔(Andrew Scull)认为,应该综合看待这些精神病院所起到的作用。一方面,这些机构的确收容了各类患者,并且以较为人性的方式提供保护,避免他们受到他人的攻击和伤害;但另一方面,这种做法实质上是一种“有效且彻底的控制手段”,将患者彻底隔绝,以预防其实施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反讽的是,当时盛行的这种治疗方式又被称为“道德疗法”(moral treatment)。倡导者希望将“道德规训和自我控制”的理念灌输给这些患者,从而帮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秩序”(Scull 2006:116)。然而,实际效果与这些人的设想相去甚远。到了20 世纪初期,随着收容人数的大幅上涨,精神病院的资源极其紧张。为了便于管控,暴力手段开始恢复,部分患者的活动受到限制,形同拘禁(McCandless 2003:188)。
因此,凯瑟琳打算将霍华德送往精神病院的举动,无异于将他投入牢笼。在伦理层面上,这是一个极具争议的决定。不仅因为这家医院本身的性质,更是因为凯瑟琳并没有和霍华德商量,而是打算瞒着他,偷偷将他送过去。事实上,患者拥有病情知情权和治疗选择权。即便是那些不具备充分能力的患者,也要确保他们“根据自身能力在最大程度上参与到决策过程之中”(Williams 2009:49)。不管凯瑟琳是否充分了解医院的实际状况,她的这一做法都侵犯了霍华德本人的权利。
得知凯瑟琳的计划后,霍华德非常失望,因为他发现妻子对他缺乏真正的理解和尊重,只当他是个癫痫病人,是个窝囊废,不愿意认真倾听他的诉求。与此同时,他也发现儿子乔治对他心生嫌恶,想要逃离家庭。家人的一再伤害最终让霍华德下定决心,离开原先的家庭,开启新的人生。
霍华德对于精神病院的抗拒还有另一重原因。在他很小的时候,他亲眼目睹自己的父亲,也就是乔治的爷爷,被家人送走时的情形。当时他的父亲患有严重的老年痴呆,生活难以自理。母亲在教会的帮助下,将父亲送往某个机构安置。对于霍华德来说,那次离别是他最后一次见到父亲。黑色的马车,加上教会成员全身的黑衣打扮和清晨的迷雾天气,都让他有着不祥的预感。对他来说,那“就像是一场梦,关于父亲死亡的梦”(139)。他的预感其实很合理。虽然小说没有明言,但是按照当时的通行看法,老年痴呆也属于疯癫④18 世纪时,法国医师菲利普·皮内尔(Philippe Pinel)将疯癫细分为几种类型,老年痴呆是其中之一(qtd.in Porter 2002:132)。,因此父亲的结局很可能就是被禁闭在精神病院中,悄无声息地离开人世。
此后,霍华德独自出门,想要找寻父亲的踪迹,结果却迷失在黑暗潮湿的森林中,经历了癫痫的第一次发作。回到家后,他浑身湿冷,嘴巴淌血。母亲煮了一锅浓汤,让他慢慢喝下。浓汤很热,从喉咙一路烫到胃里,直到他全身发热。母亲同时告诫他,在知觉恢复正常之前,不要开口说话。于是,霍华德一直默默喝汤,整个过程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
这段情节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口腔作为发声器官,代表着霍华德对于真相的追问。母亲的告诫则代表着社会层面的禁令。在当时,老年痴呆同样是一种污名。因此,父亲被送往精神病院,名为隔离,实为抛弃,母亲实际上规避了自己的伦理责任,这是她希望保守的秘密。而她也利用这次机会,对霍华德提出警告,让他别再寻找父亲的下落。
之后,霍华德不再提起此事,但他始终惦记着父亲,多次梦见父亲回来看望他。癫痫的发作反而加强了他对于父亲的情感认同,因为亲身经历过折磨,所以他对于父亲的痛苦感同身受,同时也更加理解父亲生前所倡导的伦理思想。作为社区牧师,父亲在布道中一直呼吁要关爱各类弱小的生命。长大成人之后,霍华德继承了父亲的思想,并且在推销途中身体力行。他给贫困的农家男孩免费理发,给衰老的森林隐士送去烟草,并且帮他拔牙,他还给家境普通的主妇提供购物建议,避免她们遭受欺骗。这些都体现出霍华德善良的秉性,同时也是他的妻子和孩子不曾了解的另一面。
霍华德父亲被送走的情节呼应了凯瑟琳想要送霍华德去精神病院的片段。通过对比不难发现,两个妻子的做法如出一辙,都是借由隔离的名义规避自身的伦理责任。然而,两个儿子的做法迥然不同:乔治站在母亲那边,默认了她的选择;霍华德却试图追寻父亲的下落,以孩童天真的方式践行自己对于父亲的承诺。童年的这段经历也为霍华德后来的抉择提供了注解。正因为霍华德经历过和父亲永别的痛苦,他才对精神病院和隔离制度深恶痛绝,并最终选择逃离家庭。
诚如研究者所言,照看精神疾病患者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有不少人在历经折磨之后意识到,某些疾病可能无法根治,并且无法掌控,因此他们会“重新估量自己的义务”(Karp 2001:58),进而作出自己所认为的更为合理的选择。这种考量原本是人之常情,只要患者能够得到妥善安置和有效治疗,不失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然而,《修理匠》中两个妻子把丈夫送往精神病院的决定,都是出于自身考虑。尤其是凯瑟琳,她想摆脱霍华德这个包袱,既没有征求他的意见,也没有考虑他的切身利益。因此,哈丁在描写这两段情节时,更多是对患者报以同情,同时也否定了这种做法。隔离制度虽然给家属减轻了负担,却牺牲了患者的自由,这显然有违现代医学伦理的基本准则。
四、共情:伦理关系的修复
所谓共情,指的是以情感为纽带,将自我与他者联系在一起,切身感受其他人的苦难(Slote 2007:13)。和同情有所不同,共情的态度尊重他者的特殊性和差异性,而不是将自我的看法强加于对方。在《修理匠》中,哈丁强调了共情的重要性,尤其是这一态度在修复伦理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
共情的首要前提是摒弃偏见,不再使患者背负污名。德国思想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认为,必须将精神病人看作受难的人类,才能意识到自己对于他们的伦理责任:
我无意识中将她褪去人形,变为事物,变为客体,我必须压制这一态度。我必须透过疾病表象,去发现她未曾改变的基本人性,进入她的世界——但我必须带着理解,而不是怜悯的态度,去关心她的康复……否则,我将无法接触她的内在,无法厘清我对于她的责任。(qtd.in Hollander 1990:194)
在小说中,哈丁充分发挥意识流叙事的优势,细致描摹霍华德的内心意识,引领读者透过疾病表象,感受更为真实的人物内心。哈丁对感官反应的描写生动且详尽,病发过程似乎是被放慢后呈现出来的:
霍华德·克罗斯比的耳朵里同样叮叮作响,声音起初在远处,随后渐渐靠近,最终抵达他的耳朵,并且钻了进去。他的脑袋里发出低沉的响声,就像是击锤在铃铛里敲击。一阵寒意跃上他的脚趾头,随着响声的起伏传遍整个身体,直到他的牙齿嗒嗒作响,膝盖颤抖,直到他蜷缩起来,免得整个人散架。这是他的先兆,每当他遭受癫痫侵袭的时候,他整个人立即被化学电流所形成的冰冷光晕所包围。(15-16)
哈丁通过上述一系列动态描写使原本混沌莫名的先兆感受变得鲜活而细腻:先从听觉开始,声音由远到近,由轻到重;随后又转到触觉,从脚到头。此外,哈丁还使用大量比喻生动地呈现出癫痫发作的全过程,而电击是他使用最多的比喻。霍华德将癫痫的力量之源想象为“太阳系边缘一团不停旋转的电子风暴……一束又一束电光从火花旋涡中分叉出来”。进而,他将发作前的先兆比作“在闪电之前被推着前进的灼热的空气”,而发作的那一瞬间则像是“闪电触及肉体”(46-47)。
哈丁所运用的一系列比喻不仅新颖生动,而且贴合霍华德作为诗歌爱好者的身份。与此同时,这一系列修辞手法也构成了陌生化效果,让读者对癫痫产生全新的认知,从而超越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抽搐和痉挛”的表面印象,深入了解患者,为随后的消除污名埋下伏笔。
共情的另一个要素是关怀。共情并不仅仅是了解对方,同时也意味着自身的付出和关爱。对于患者来说,情感慰藉和医学治疗一样重要。霍华德在离开家庭后的经历证明了这一点。他遇到了第二任妻子梅甘,后者天性乐观大方,和偏执严苛的凯瑟琳完全不同。在霍华德发病后,她没有丝毫歧视和贬低,反而细心护理,扶他到床上躺下,按摩太阳穴,给他端来热茶。梅甘有时还给他读通俗小说,缓解他的紧张心理。让其他人感到畏惧的癫痫症状丝毫没有困扰她,因为她觉得那不过是疾病而已,并不会影响她对于霍华德的感情。不仅如此,梅甘还说服霍华德,积极寻医访药,最终遇到一个高明的医师,对症下药,明显缓解了霍华德的病情。
此外,实现共情的态度还需要主体敞开自我,在心中认可并接纳对方。德里克·阿特里奇(Derek Attridge)指出,“只有当‘我’肯定、欢迎、信任、支持他的时候,他才能(作为他者)存在”(1999:28)。在小说的结尾部分,乔治在临终前经历了伦理意识的觉醒,从压抑回忆转变为渴望见到父亲。这是故事情节的高潮,同时也是共情态度的最终体现。
在描述两人关系时,哈丁明显将乔治置于主导地位。乔治掌控着自己的意识和记忆,控制着自己对于霍华德的认识。但与此同时,乔治也无法将霍华德从意识中完全抹去,留在乔治记忆中的霍华德更像是一种幽灵般的创伤记忆。尽管乔治苦苦压抑自己,不去回想往事,但父亲发病时的样子总会在意想不到的瞬间闯入他的内心意识。唯有当乔治开始逐渐自省,不再将霍华德视为可怕的怪物,而是承受苦难的人时,他才能透过狂乱的疾病表象,去接触霍华德的内心世界。
在小说结构上,乔治对霍华德的认识与接受,体现为围绕两人分别展开的两条叙事线索从泾渭分明到逐渐汇拢,最后合为一体的过程。这一结构具有“复调小说”(polyphonic novel)的特色。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在剖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时认为,他的“艺术视觉展现模式的根本类别不是逐步演进,而是共存和交互作用。他主要是通过空间,而非时间来查看并构想他的世界”(Bakhtin 1984:28)。哈丁采用了类似的叙事结构。他通过拼贴和并置等空间化叙事技巧,呈现出乔治临终意识的若干片段。这些片段并非任意选取,而是围绕乔治对待霍华德的态度转变,记录了他敞开内心世界,与霍华德达成精神联结的整个过程。
在小说结尾,无名氏留下的笔记片段用诗歌般的语言描绘了由共情态度所产生的灵魂交汇:
当死亡的时间来临,我们知道大限将至,走到院子深处躺下,我们的骨头变成黄铜。我们被选中。我们被用来修理钟表和音乐盒……我们的肋骨被用作齿轮上的锯齿,它们轻轻敲击,像象牙般发出嘀嗒的响声。这就是我们最终联结起来的方式。(190)
此时,钟表变成了联结的象征。个人就如同钟表中的齿轮,唯有紧密结合方能整体运行。临终前的记忆浮现成为乔治和父亲修复关系的契机。那一刻,乔治清楚地记起了某一年的圣诞夜,霍华德在失踪多年后突然上门拜访,又匆匆离去。那是两人最后一次相见。正是在这段时空交错的记忆中,父子俩的故事汇集在一起。这个交汇点既是乔治生命的最后时刻,也是他关于父亲的最终印象。
哈丁用霍华德的道别词作为整部小说的收尾:“很高兴再次见到你,乔治。好的,好的,我会的。再见。”(191)死亡在此刻变成了精神上的重生。对于乔治来说,霍华德不再是那个咬伤他的疯子,那个面目可憎、浑身抽搐的癫痫病人,而是暗中关注他、始终支持他的父亲,一个重新开始生活的强者。对霍华德的重新认识也将乔治从怨恨和压抑中解脱出来,带着对父亲的思念安详离世。
结尾部分的巧妙处理将各个叙事片段串联起来,同时也深化了这部作品的伦理意义。在故事开场时,乔治躺在病床上,拼命压抑着自己关于父亲的记忆。这样的悬念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兴趣。随着叙事进程的深入,读者得以了解更多往事,并对父子俩的遭遇报以同情,期盼着两人能够修复关系。在多次延宕之后,小说在结尾部分达到了高潮,同时也迎来了圆满的结局。这样的叙事处理在形式上呼应了作品的伦理寓意,那就是共情态度的重要性。只有放下偏见,增进交流,才能透过疾病表象,真正了解并接受患者。
五、结语
《修理匠》是新世纪美国文坛同类作品中难得一见的佳作。哈丁围绕克罗斯比一家的疾病,书写了一段令人难忘的家庭往事,不仅塑造了霍华德和乔治这两个鲜活的人物,而且也勾勒出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冲突。哈丁对意识流叙事和拼贴手法的娴熟运用,对复调结构的巧妙安排,都增添了这部作品的魅力。
与此同时,《修理匠》中的医学伦理主题也促使读者反思,重新审视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对待类似患者的态度。这些患者并非失去人性的怪物,而是需要我们理解和同情的病人。倾听患者的故事,尝试了解他们的内心,以共情的态度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心灵沟通,这就是哈丁所要传递的伦理意义。
本研究得到江苏理工学院2018年度人才引进项目“美国后现代金融小说研究”(KYY18549)的资助,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