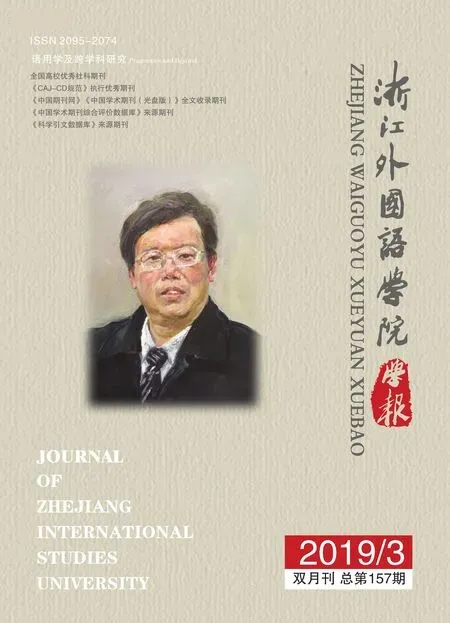文学自译中的翻译暴力
邹常勇,朱湘军
(1.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广东 广州 510900;2.暨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619)
一、引言
作为一门综合学科,翻译学越来越多地被置于文化研究的视域之中。尽管文本在翻译研究中仍然处于中心和基础地位,但在文化视角的观照下,译者却拥有了更多阐释文本的权力。当译者将自身的主体意识或其所代表的主流文化意识加诸翻译之上,便会造成译文与原文的偏差,这种行为可视为一种“暴力”操控。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认为,按照目标语价值观、信念和表达方式对源语进行重构的翻译暴力存在于翻译的意图和行为之中(2008:13-15)。植根于西方的强势文化语境,韦努蒂声称翻译暴力主要体现在欧美译者翻译亚非拉文本的过程中,其突出表现为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文本的归化翻译,即翻译中的“我族中心主义暴力”。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又进一步提出,“翻译暴力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是翻译过程中所固有的”(2008:15)。李小均(2006)认为,翻译暴力有显性和隐性之分。栗长江(2006:61)拓展了翻译暴力的内涵和外延,认为“翻译的暴力具体体现在对原文的任意删节,改写,扭曲;源语塑造形象在译语中的变形或身份的‘易位’;翻译流向的落差等等”。孙艺风(2014)则进一步从翻译暴力的性质出发,将其划分为危害暴力和柔性暴力,并分析了两类翻译暴力的形成动因及其对翻译行为的影响。
综观前人的研究,大多数研究者聚焦于译者与原作者不为同一人之时所发生的翻译暴力现象。那么,当两者合一时,是否也还会发生此种现象?如有,其动因和具体体现又是什么?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本文拟在华文文学自译范围内加以探究。
二、文学自译与翻译暴力
文学自译古今中外都有,不少名作家都曾将自己的得意之作翻译成他国语言。比如,泰戈尔凭借其自译的英文版《吉檀迦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从此跻身世界文坛;再如,我国的林语堂、张爱玲、萧乾等人也曾将自己的作品翻译成英语,取得了不小的成就。这些成功的自译者都拥有绝佳的双语能力,对源语和目标语文化理解通透,对自己的作品有着准确的把握,且能通过自身的翻译将作品内涵准确地传达给目标语读者。翻译学家普遍认为,自译可以弥合翻译中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之间的差距,给目标语读者以身临其境之感,从而收获理想的翻译效果。“翻译中的艺术性,要求译者对原文从形式到内容的统一体有全面而又细微的理解和感受,真正做到和原作者心灵相通,然后调动译入语中最适宜的手段,用恰如其分的译文,使读者也获得同样全面而细致的理解和感受。”(金隄 1998:8)就这一角度而言,自译作品最能酣畅淋漓地表现出原作的思想情感、语态、语气甚至节奏韵律,最能还原原作的美感,还有谁能比原作者更了解自己的作品呢?
既然如此,那么自译作品是否一定能严格忠实于原文?是否也存在翻译暴力?为了检视自译中的对等情况,吴波用案例分析法研究了白先勇对《台北人》的自译,他发现即使译者和原作者为同一人,仍然无法确保译本完全忠实于原作,译者会因为某些需要而有意地对原作的内容或风格作出调整,“译者的任务远比‘忠实于作者和原作’这一要求深刻复杂得多”(2004:68)。林克难(2005:44)在仔细研读了萧乾的自译作品后发现,译者并未采用传统的全译加注方式,而是进行了大量的删节和增益,这些做法无法用传统的翻译理论来解释。因此,林克难提出,文学翻译的译者“应该而且可以根据不同的文本、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读者等诸多因素而采取不同的译法”。北塔(2006:24)在分析了卞之琳的诗歌自译后认为,卞之琳并没有对原作亦步亦趋,而是“更多地显示了他的诗人本色”,随意洒脱、灵活多变、俯仰由心。上述研究表明,即使译者与原作者为同一人也无法保证译文与原文在语言和风格方面的完全一致,自译似乎反而给了译者更大的自由空间来操控原文。这些操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对原文的“僭越”(孙艺风 2014:8),亦属于翻译暴力的范畴。
事实上,自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除了需要克服语言的差异,还要面临文化传递方面的冲突和交锋。自译者在原作的创作过程中往往会立足于本族文化,服务于本族读者的阅读习惯。然而,当其成为翻译者时,则会在文学理念、人生经历及自我完善需求等因素的驱动下,跳脱出源语及其文化背景的限制进而对源文本作出相应的调适处理——增益、删节甚至改头换面。可见,文学自译中的翻译暴力是“一种隐喻,既可以指翻译抹杀了外语文本的语言和文化差异,也可以指译文对目的语语言和文化系统的‘挑战’和‘颠覆’”(张景华 2015:70)。
三、文学自译中翻译暴力的具体体现
一般而言,文学自译中的翻译暴力主要体现在翻译策略、文化塑造和美学诉求三个方面。
(一)翻译策略
翻译策略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解决所遇到问题的程序”(Lörscher 1991:76)。不同于他译者,自译者“更能够将语言象征与所指分离,更注重作者预设的微妙情感和客体的美学意义”(黎昌抱 2011:93)。另外,自译往往是异地、异时而作,自译者对自己的作品大抵会有新的感悟与思考,在自译过程中往往可能产生新的“创作的心理兴奋”(黎昌抱 2011:93)。因而,自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更大胆,也更具多样性。
自译的动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自译者的翻译策略选择,黎昌抱(2011:93-94)将其归结为以下四种:一是跨语境文化交流和自我价值实现;二是不满原作并试图通过自译来弥补;三是战争、政治、婚姻失败、生活窘迫等因素;四是追求新的诗学观念。在这些动因的触发下,自译者或选择贴近源语的翻译策略,或选择贴近目标语的翻译策略。事实上,为了赢得更多、更广泛目标语读者的认同与接纳,自译者有时会倾向于采用贴近目标语的翻译策略,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一些显性或隐性的改写,其中不乏翻译暴力。比如,在萧乾的作品《矮檐》中,乐子的父亲是“一个决心独身而被家庭强迫聘娶的冷酷男人”(2001:172)。他自幼立志独身,对“尘世”没兴趣,性情古怪,一辈子不肯扑哧笑一声,甚至婚后不让自己的妻子靠近,因而是婚姻悲剧的主要责任者。然而,在萧乾的自译作品When Your Eaves Are Low中,乐子父亲的这些古怪行为,以及家族中的一些人际矛盾和家庭琐事,都被作了删节处理。萧乾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描写年幼的孩子和无助的母亲在家族中受到的白眼与欺凌,以及父亲死后母子俩相依为命、孤苦伶仃的生活。萧乾明白,目标语读者的价值观和文化理念决定了他们较难理解乐子父亲的古怪举止,他选择了贴近目标语的翻译策略,对原文施加了一些“暴力”操控。
自译者为了贴近目标语而采用的“暴力”手段具体包括删减(deletion)、改造(alteration)、增加(addition)等形式。从表面上看,这些对原文的“大刀阔斧”式处理大大超出了传统直译与意译的理论范畴,也背离了翻译的忠实性原则,但是实际上,自译者往往使用这些“暴力”手段取得了良好的翻译效果。
(二)文化塑造
近几十年来,翻译中的文化塑造问题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韦努蒂(2001:358)认为:“翻译以巨大的力量构建对异域文化的再现(representation),同时也构建着本土的主体。”丁如伟(2017:113)提出,在跨语际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会再现或者重塑原文文化身份。自译者精通两种不同的语言及其文化,这在一定意义上使其拥有了“上帝的视角”,他们既是原文的创造者,又能用另外一种语言和文化来再现或重新构建自己所创造的文本世界。
萧乾、林语堂、余光中等自译者往往辗转多地,甚至是在异国他乡完成对自己作品的翻译,因而他们对于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会有较为敏锐的感知,并且试图通过自译在两种文化之间寻找平衡。他们并不认同西方文化优于中国文化,进而身体力行地在其自译中塑造积极的中国文化形象,甚至将翻译暴力作为一种武器来抵抗西方文化的“傲慢与偏见”,为本族文化发声。萧乾在20 世纪40年代旅英期间,开展了大量传播中国文化的工作。除了用英语发表著作以外,他还将自己早期的一些文学作品自译为英语。在萧乾看来,“中国文学在那个时代不是用来消遣的,而是用来救亡图存的”(符家钦 1988:267)。为了获得文化之间的平衡,萧乾在自译中大量使用删减的翻译手法,将自己原作中一些不利于中国文化传播的故事情节、场景描述和人物形象一一删除,以此来重塑中国文化形象。萧乾将自己的小说《花子与老黄》翻译为Epidemic。相比于原文,译文的篇幅减少了三分之一左右,所删减的内容主要是老黄在主人家所受的不公正待遇。比如,萧乾将原文结尾处老黄被扫地出门,像野狗一样病死在荒郊野外的情节改造为他最后被送入传染病医院。通过删减和改编,原本描述受尽压迫和欺凌的仆人最后被主人抛弃后悲惨死去的故事转变为体现作为小少爷的“我”、仆人老黄以及小狗花子之间友谊的故事。在《篱下》一文中,萧乾对环哥家的周遭环境描述道,“出门就黑压压一片绿庄稼,要不就一围死寂寂的坟堆子”(2001:20)。然而,在自译作品Under the Fence中,他却将“死寂寂的坟堆子”这一信息删除了。概言之,在萧乾的自译中,原作中关于中国文化的负面信息被大量“暴力”处理掉了,他似乎为负面文化信息设置了“过滤层”,以此来正面建构中国文化形象。自译作品中的文化再现或重塑凸显了译者对源语文化的观照和反思。
(三)美学诉求
在文学自译活动中,自译者往往更清楚自己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及该如何表达,更能以独特的翻译手法、美学志趣和情感体验来满足目标读者的期待视域,因此自译作品往往也更加传情达意。作为审美主体,自译者既是创作者又是翻译者,因此对于他们而言,翻译绝不仅仅是传递信息。如果自译者只关心信息的传递,那么损失和背叛的往往是原作的价值。假如自译者想要保留原作的价值,那就不得不在语言上花些心思,对原作进行创造性的美学阐释。自译者有时会将原作中隐晦的文学线索、文学审美和情感倾向显性化,“通过种种‘明示’,让自己的意图在读者处获得共鸣,展开直接的主体间对话”(黎昌抱 2011:94)。在这个过程中,自译者一边努力提取原来的文本意义,一边调动新的文学、文化体验,建构新的文本意义。就这个意义而言,自译是原作者“用源语言创作时的语言冒险的进一步延伸”(陈义海 2013:16),其艺术情感力、想象力以及审美知觉力就此得以进一步提升。
一些有过海外经历的自译者,往往有着强烈的跨文化交流和作品自我增值的需求,他们渴望在自译过程中与不同诗学发生碰撞,“重新思考、体验与表达”(杨联芬 2006:20),不断打破原作中的美学框架。从翻译美学角度来看,作为审美主体的自译者不再简单地受制于源文本,他们往往倾向于进行“审美重置”,在不同的语言中重新建构自身的美学志趣。
自译者为满足特定时期、特定读者的期待视域,出于自我完善的美学诉求,有时会采用一些“暴力”手段。比如,卞之琳为了突出诗歌的主题意象,将其诗歌《春城》自译为Peking,1934,而非Spring City。此外,在卞之琳的自译中,一些无题诗被“暴力”改造成了有题诗,如《无题三》被译为The Doormat and the Blotting-paper,《无题四》被译为The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and a Running Account,《无题五》被译作The Lover’s Logic。余光中一生徜徉于中英诗歌的阅读、写作与翻译之中,“英诗的意象、节奏、韵律、句法”(2009:171)早已深入感性,成为其诗艺的一大来源。于他而言,诗歌创作和自译相辅相成。在自译过程中,余光中有时也会对原作中的一些意象及韵律进行“暴力”改造,如例(1):
(1)原文:难闻的焦味?我的耳朵应该
听你喘息着爱情或是听榴弹
宣扬真理?格言,勋章,补给
能不能喂饱无餍的死亡?(余光中 2017:30)
译文:The smothering smoke of troubled air?Shall I hear
You gasp lust and love or shall I hear the howitzers
Howl their sermons of truth?Mottoes,medals,widows,
Can these glut the greedy palate of Death?(余光中 2017:163)
例(1)节选自余光中的《如果远方有战争》及其自译作品If There’s a War Raging Afar。在自译过程中,余光中将“宣扬真理”译为“Howl their sermons of truth”,其中“Howl”一词将原诗中简单的“宣扬”变得更加形象化,战争的残暴、嚣张扑面而来,诗歌的张力由此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虽然余光中只改动了个别词汇,但是诗歌中战争的意象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如“补给”被翻译为“widows”。如果说“格言,勋章,补给”使读者联想到战争的荣耀,那么“widows”则让他们体悟到一种直面死亡的肃杀之感。此外,“Mottoes,medals,widows”一气呵成,从韵律、音乐性的角度提升了诗歌的美感。这样的效果,是直译所无法达到的。再看节选自同一诗歌及其自译作品的例(2):
(2)原文:如果有战争煎一个民族,在远方
有战车狠狠地犁过春泥
有婴孩在号啕,向母亲的尸体
号啕一个盲哑的明天(余光中 2017:30)
译文:If far away a war is frying a nation,
And fleets of tanks are ploughing plots in spring,
A child is crying at its mother’s corpse
Of a dumb and blind and deaf tomorrow;(余光中 2017:163)
例(2)中,“盲哑”被增译为“dumb and blind and deaf”,婉转回旋,诗歌的音乐美得到了进一步升华。由此可见,体现在自译美学诉求中的翻译暴力并不一定是危害性的,合理的运用可以使译文还原甚至超越原文的美。
四、结语
创作主体、审美主体及翻译主体的三位一体赋予了文学自译以特殊的意义,自译者的独特翻译经历简化了理解原文的过程,克服了他译中的一些局限性。研究发现,自译注重对原文所蕴含文学性、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再现或重塑,而非字面意义的简单对等。身份重叠使自译者拥有了比他译者更大的自由度和创作空间,有时其会通过较大幅度的“删”“增”“改”等翻译暴力来彰显主体性。自译者的“暴力”操控表面上使译文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原文,实则有助于突破“不可译”的局限性,在不同文化中重新定义自己的作品,进而提升作品的美学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