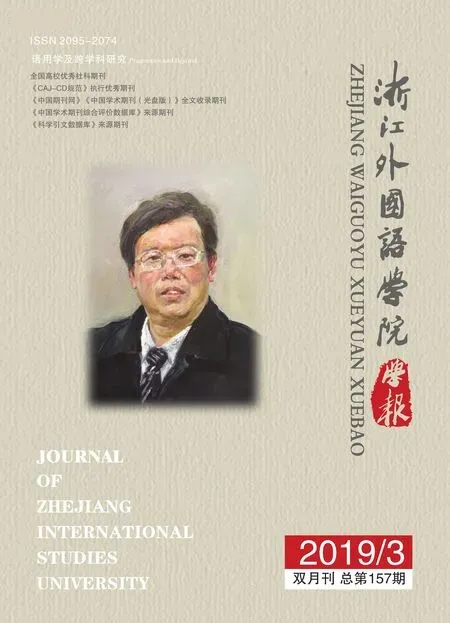中医遗产的本土叙述与文化话语重构
——基于浙江衢州两部方志的考察
高佳燕,侯 松
(1.浙江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1;2.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翻译学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420)
一、引言
中医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命运却几经沉浮,近些年来也遭到了不少质疑,处境颇为尴尬(Fruehauf 1999;张功耀 2006;张爱华、岳少华 2010)。习近平总书记(2017)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中西医并重,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为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中医这一宝贵财富,推动中医走向世界,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医话语体系显得至关重要。
2010年,中医针灸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不少人将此看作中医复兴的契机,国家与地方层面也制定了一系列的中医非遗保护政策与措施。然而,联合国非遗保护的话语框架和运作体系能否真正彰显中医的文化内涵?中医究竟具有什么样的中国传统文化意义?在遗产话语框架中,中医又该如何成为一种连接传统的意义存在?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思考。本文借鉴话语分析的跨学科视角和分析方法,以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刊行的姚宝煃等修、范崇楷等纂的《西安县志》和民国十八年(1929年)郑永禧编纂完稿的《衢县志》①今浙江省衢州市市区及周边所辖一些乡镇,自唐咸通年间至清历称西安县,民国时改名衢县。本文中的《西安县志》《衢县志》《西安怀旧录》(下文提及)均是关于衢州的文献。中关于草药和医家的叙述为例,考察方志中所建构的中医传统文化意义及其话语特征,并思考其对当下传承、复兴中医的启示。
二、非遗保护的话语研究
近年来,话语分析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在遗产学界越来越得到认可(Watertonet al. 2006;侯松、吴宗杰 2013)。随着遗产运动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审视与反思遗产运动中的政治、经济博弈与西方文化霸权,认为遗产并不是简单的历史过往,而是涉及一系列的社会表征与话语建构(Walsh 1992;Waterton & Watson 2010)。国际遗产话语研究领军人物劳拉简·史密斯(Laurajane Smith)率先将批判话语视角引入遗产研究。通过对《世界遗产公约》《威尼斯宪章》《巴拉宪章》等国际遗产保护条约进行话语分析,她提出,现代遗产保护话语强调遗产的物质性、原真性、纪念碑性,凸显的是其史学的、美学的、科学的“普世价值”(Smith 2006)。这套“权威化遗产话语”(Smith 2006:11)体系构建了文化遗产的标准样态与基本表述方式。
2003年,随着UNESCO 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传统手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纳入保护范畴。虽然该公约不再强调遗产的物质性和纪念碑性,但它“把社会实践、技艺和传统等同于物质遗产中的遗产物、遗产地或者遗产景观”(Byrne 2009:229),其运作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复制了物质遗产保护的操作方式,因而仍有诸多学者对其中折射出的话语与文化霸权进行了批判性反思。
首先,通过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的话语表述及话语实践,有学者发现,它依然遵循着西方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和框架(Alivizatou 2011),它所采用的术语都是西方的概念(Houet al. 2016),并没有摆脱其普世性、学科化与文化保存的思维逻辑。比如,在研制之初,它依然在寻找一个“合法的框架”和“普世的”(universally recognized)原则(Bedjaoui 2004:150)。符合这些原则和标准的遗产得以列入保护名录,否则就只能惨遭淘汰。又如,在公约的研制过程中,知识和技艺成为遗产保护的重点(Blake 2001:45)。史密斯由此认为,非遗保护公约并未能完全摆脱“权威化遗产话语”的影响(Smith 2006)。
其次,有学者提出,纵观联合国的非遗名录,它更优待那些五彩的、具有异国情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好符合浪漫化的西方认知,而真正本土的作品则未能得到呈现(Kirshenblatt-Gimblett 2004;Kurin 2004)。对此,国内有学者同样提醒道,要警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东方主义”。如夏敏(2007:7)认为,进入西方视野的东方“非遗”,“是西方的东方主义想象的重要对象物”。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仍然面临着“多重地方的以及超地方的(supra-local)挑战”(Skounti 2009:75)。
总体而言,全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受到西方价值观和话语体系的影响。被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能丢失部分本土的言说方式与文化内涵,甚至被重新予以组装或构建。例如,在考察贝多因文化遗产的多元话语过程中,有学者发现,在申请成为世界非遗的过程中,贝多因文化受到了地方、学术界、国家以及国际四个层面话语的影响,其文化被进行了分类与组装(Bille 2012)。同样,中医在申遗过程中也遭遇了困境和悖论,经历了一个“削足适履”的过程(林敏霞 2014)。
由此可见,不管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还是全世界范围内的非遗保护运动,都存在着文化失语的问题。联合国视域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能充分呈现每一遗产的本土历史文化价值。要真正挖掘遗产的文化内涵,我们仍然要回归到本土的文本与文化话语语境之中。在此方面,中国学者已经做了不少尝试,将话语分析与中国传统历史文本相结合,深入分析方志中的文化遗产观(Hou 2019;侯松、吴宗杰 2012,2015;吴宗杰 2012;吴宗杰、侯松 2012)。本文将延续这样的研究路径,考察遗产话语研究很少涉及的中医。由于中国古文行文的特殊性,通用的话语分析框架对此并不适合,因此本文借鉴话语分析的跨学科视角和分析方法,以两部衢州方志中关于草药和医家的叙述为例,从语料中寻找较为凸显的内容和语言特征作为切入口,着重探究以下问题:
1)方志中的中医记载与非遗申报书中的表述或者说当今主流非遗话语相比,哪些内容没有被提及,哪些内容又有所侧重?
2)方志中的中医叙述体现出什么样的意义建构?
三、多元意义空间与地方文化内涵——作为一方物产的草药
《西安县志》中共记载了黄精、地榆等三十一味衢州当地出产的草药,其叙述范式较为统一,主要涵盖两个方面:其一是引用各类历史语料,对草药的名称(来源)、意义关联、性状功效等予以说明和考证;其二是引用诗歌、散文等素材,进一步彰显其地方文化意义。在记载每一味草药时,通篇很少突出编修者自己的语言,而是通过“裁剪”语料的方式,选取、整合不同维度的文本,通过“述而不作”的话语风格,建构中医(物产)的多元文化意义,并强调其独特的地方内涵。
(一)多维度文本建构的多元意义空间
从《西安县志》的文本选取与裁剪方式来看,该方志的编修者并不局限于记录草药的医学功能,而是通过不同历史维度、不同体裁、不同领域的文本交织,构建草药多元的文化阐释空间,体现中国哲学中自然与人文相照应的审美情趣。我们以该方志对黄精、艾草这两味草药的相关记载为例加以阐发。
《西安县志》对黄精这味草药的记载如下:
黄精:(《五符经》)黄精获天地之精淳,故名为戊巳芝。(舒二生诗)且封丹鼎去,绝岭寻雪苗。
(《西安县志》:761)
从中可见,编修者在开篇裁取了道教经典《五符经》中的一句话,点出了黄精的价值及其与中国传统宗教的关联。该引用告诉读者:自古以来,道家认为黄精吸天地灵气,久服可以成仙,因而将其列为仙品。接着,编修者并未介绍其药理功效,而是附上了一句诗“且封丹鼎去,绝岭寻雪苗”。“丹鼎”为道教用语,指的是道士炼丹的炉子,与前文的《五符经》呼应。而“绝岭”“雪苗”等,读来令人有出尘之感。如此一来,黄精的意义就不再局限于药的层面,似乎也流露出些许古人追求自然、隐逸世外的情致,而这样的情致一直以来也是中医和道教养生的重要精髓。
又如,对于常见的艾草,《西安县志》中作如下描述:
艾:(《尔雅》)艾,冰台。注,今艾蒿。味苦而辛,生则温,熟则热。(徐士敷诗)煮艾亲芝泥。
(《西安县志》:761)
文中先是介绍了艾草的别名,但并非直接说出,而是追溯到了中国的儒家经典《尔雅》,突出了其词义的源头。接着,编修者以一句比较典型的中医话语“味苦而辛,生则温,熟则热”点出艾草的性味。不同于现代科学强调的“精确性”“可证实性”或“二元论”(陈徽 2009),中医语言追寻诠释性、可理解性和辩证互补(吴宗杰、吕庆夏 2005)。而在文末,编修者附上了徐士敷的一句诗“煮艾亲芝泥”。“芝泥”即印泥,是古代文士常用之物,核心原材料之一便是艾(草)。据郑永禧在光绪年间所完成的《西安怀旧录》②《西安怀旧录》为郑永禧所著,手稿现存于衢州博物馆。记载,徐士敷是乾隆年间的儒生。在这样的多元话语记载中,艾草的内涵和意义也是多元的,它既属于中医的范畴,但又不止于此,它同时与儒士、诗书有着密切关联。在传统中医观念中,文与医也是不分家的,比如《针灸大成》的作者——明朝针灸大师杨继洲便是“幼业举子,博学绩文”③参见《〈卫生针灸玄机秘要〉叙》(http://xuewen.cnki.net/R2009030200001311.html)。。
由此可见,在《西安县志》中,草药并未完全成为一个医学知识对象,而是与中国的历史、哲学、文学、宗教以及古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寄托着古人对自身、对世界的人文感怀。通过方志的语料筛选和文本叠加,它的意义丰盈而流动。方志这种“述而不作”“微言大义”的叙述方式与多元的人文意蕴,与非遗保护中的中医遗产表述有较大的差别。
作为对比,我们不妨看一下,同样是关于艾草,中医针灸的非遗申报书④本文所引的中医针灸非遗申报书下载自UNESCO 网站,参见https://ich.unesco.org/doc/download.php?versionID=07331。原文为英文,下文中的相关中文引用均为笔者所译。是如何描述的:
艾灸的原料艾是一种芳香植物,遍布中国,因自古以来中国人相信艾草能够驱病而被广泛应用于艾灸。……中国有俗语称“一根针,一把草,保你健康活到老”,“端午门前挂艾草,一年医生不会找”。
(UNESCO 2010:5)
可以看到,非遗申报书中首先将艾(草)作为一个植物学的知识对象予以定义:芳香植物。这与现代医学话语中对草药进行生物学、化学研究如出一辙。其次,通过“自古以来”“广泛应用”等词将艾(草)的历史内涵与意义关联局限在治病驱病的医学领域。文中虽然也纳入了中国的俗语、谚语,试图建构艾(草)与百姓生活的联系,然而关注的焦点在生命健康范畴,并且通过“健康活到老”“医生不会找”等语句,进一步强化了艾(草)的医学功能。由此,艾(草)作为“艾灸的原材料”,其内涵便主要与植物学及现代医学保健相关了。
中医是文本与阐释的巨大海洋(Kaptchuk 2000)。在传统的书写方式中,通过保留“语言的原真性”(吴宗杰、余华 2011;侯松、吴宗杰 2012)以及选取多元的文本,古人尽力保留了中医及其背后多元的文化思考。而在现代非遗话语中,要理解过去只能经由当下的语言符号来实现,来自于另一个时间和空间的意义就被当下的语言遮蔽了(Duara 1995)。
(二)独特的地方内涵
《西安县志》中关于中医物产叙述的另一个显著特点,便是通过选取衢州当地文人作品或与衢州相关的材料,建构出草药独特的地方文化意义。下文以枳实与茱萸的相关记载为例加以阐述。
《西安县志》对枳实这味草药的记载如下:
枳实:(《本草》)明目益气。西邑春夏间,小儿拾取香橼之未成而小者,售入药肆。(《山叟杂记》)信安多木奴。《水经注·榖水条》:夹溪缘岸悉生芳枳,是古先有枳未有橘也,或以为北人呼橘亦曰芳枳。(陈一夔诗)风吹枳花满溪香。
(《西安县志》:764-765)
方志编修者首先引《本草》点出枳实的医学功效,之后以少量自己的语言简述了衢州当地药肆中的枳实来源,紧接着便引用《山叟杂记》交代了枳树以及枳实在衢州的悠久历史。《山叟杂记》出自何人之手已不可考,然而文中提及的“信安”即为衢州的古称,“木奴”指的便是柑橘。而《水经注》所提及的“榖水”指的就是衢江,又称“瀔水”。由此可见,枳树为当地特产,自古便沿衢江两岸而生。最后,文中以衢州人陈一夔的诗歌“风吹枳花满溪香”结尾。据《西安怀旧录》记载,陈一夔是清代乾隆年间的廪生,此诗是他三月时节泛舟衢州莲花溪而作,描述该地遍生芳枳、花香扑鼻之景象。
又如,茱萸在《西安县志》中是这样记载的:
茱萸:(《本草》)吴茱萸处处有之。(徐日久诗)一家并登高,插头欢伯仲。
(《西安县志》:764)
方志中的这一记载先引《本草》,点出茱萸是当地常见的草药,紧接着便附上明朝衢州籍进士徐日久的一句诗。据《西安县志》(1970:729-730)记载:“重阳,士人挈榼提壶,游鹿鸣山,谒项王庙观菊,采茱萸佩之。”徐日久的诗句“一家并登高,插头欢伯仲”描绘的正是明朝时期,衢州士大夫于重阳佳节携族中兄弟一同登高,采茱萸插头的习俗。
由此可见,方志中所记载的草药带有独特而鲜明的地方文化地理印记。编修者基于衢州历史文化所建构的草药形象呈现出了独具地方特色的文化意义。这种地方性在传统中医哲学中十分重要,因为中医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与情境中孕育而成的(吴彤、张姝艳 2008:541)。《黄帝内经》里有“小者小异,大者大异。故治病者,必明天道地理”(姚春鹏 2010)的说法。《千金方》《小品方》等诸多中医典籍以及各中医流派中,也有“因地制宜”的中医相关理念(郑洪 2017)。
诚然,中医的独特地方内涵在非遗申报书中也有体现,比如其提到了 “天人合一”(the unity between man and nature)、《针灸大成》(The Great Compendium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等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中医典籍。然而,申报书中中医话语体系的建构仍受到了西方话语的影响,例如,在阐述针灸的贡献时,申报书中作了如下描述:
以天人合一的整体观为基础的针灸,通过非药物的物理刺激激发人体自我调节功能而实现健康的目的。将针灸列入代表作名录后,它的自然、绿色健康理念将得到其他社区、民众的更多了解和理解,这一凝聚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知识与实践将为相关群体或个人的生命健康保障增添一种安全有效的选择。
(UNESCO 2010:6)
这两句话出现在申报书第二部分第二段,紧跟着上一段的主旨句“针灸作为中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根植于深厚的传统文化细节之中”(UNESCO 2010:6)。然而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天人合一的整体观”,该段中并未出现更多关于中国深厚传统文化的细节描述,相对而言,“物理刺激”“人体自我调节功能”等西医话语以及“自然”“绿色健康”等现代环保话语使用较多。这样的叙述虽然也体现了中医针灸的基本理念和医学贡献,但对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阐释不足,并没有很好地凸显地域特色。
由此可见,在联合国所主导的非遗保护的话语框架内,中医的表述有时不得不借助现代的、西方的话语,中医的意义是相对单一、凝固而局限的,多数时候停留在医学领域。UNESCO 所提出的“文化多样性”“历史性”和“民族性”等目标,事实上并未得到很好体现。相较之下,在《西安县志》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集文学、史学、哲学、医学等于一体的叙述与审美方式,在这种话语体系之下,中药作为衢州物产,有着很强的文化与地方内涵,其意义是多元、流动而开放的。
四、由技入艺,医以载道——“中医传承人”的人生叙事
除了草药,衢州相关县志还对中医传承人——医家进行了记载。在《衢县志》中,郑永禧通过搜集前朝史料和各地文献,共记录了元朝至清末的十一位医家。以下抄录两则清末医家的传记:
雷丰:(《西安怀旧录》)字松存,号侣菊,又号少逸,其父逸仙,自闽浦来衢即悬壶于市。丰幼承父训,天资聪颖,诗书画皆擅长,时有“三绝”之誉。以医道盛行于时,研究医理益精,有《时病论》及《医家四要》之作,盖所以教其及门江程二生也。
(《衢县志》:2505-2506)
(《衢县志》:2506)
郑永禧引《西安怀旧录》及《棠陵邵氏谱》记载了两位医家的生平。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传统方志中的人物传记并不按照时间顺序记载人物一生中的大小事件,而是取编修者认为重要的部分予以记录(Bretelle-Establet 2009)。我们看到,在上文两篇传记中,郑永禧并没有就两位医家的“医技”或“医术”进行长篇描写。第一则医家叙述先交代了雷丰由外地来衢,在市井中为人治病,并称其“诗书画皆擅长,时有‘三绝’之誉”,向读者展示了一位才子文人的形象。在医学方面,先言其医道“盛行于时”,再说其医理研究益精,然后记录其医学著作,最后交代其授徒教学之功。简而言之,医道第一,医理为次,其后才是著书立说、授徒育人,从而建构起传统中国医家的立体形象。显然,该形象也与中国儒者的立体形象结构相呼应。同样,在记录邵嗣兴的生平时,方志仅用了“善精眼科”四个字来描述其医术,却在有限的篇幅中,以大量细节描写其体恤贫者、为人治病不收医金的仁心善举,从而建构起心地仁厚的儒医形象。综上,在古人的叙述中,医技并不是叙述的主体内容,医者的道德品质才是话语建构的核心。
《衢县志》中对其他医家的叙述都不同程度地遵循了这个价值取向。作为对比,我们不妨看一下中医针灸非遗申报书中对于针灸项目传承人的叙述:
针灸形成了区域、团体或个人学派的不同特点。由程莘农所完善的“三才进针法”以及由贺普仁总结而来的“针刺三通法”对促进针灸的持续生命力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代表性传承人程莘农于2007年成立工作坊,总共招收25 名学徒,并于2009年召开“国医大师程莘农学术研讨会”。贺普仁于2006年向其弟子传授针法,并在北京成立了贺普仁中医诊所用以授业。以这两位大师为代表的相关团体和传承人都在尽力传承针灸,确立保护措施。
(UNESCO 2010:5,9)
按照UNESCO 的申遗标准,“技艺特点和成就” 被作为衡量传承人是否符合标准的必备条件。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上述叙述中,两位中医传承人的“针法”及其医术头衔、医学活动成为了叙述的主要方面。在此叙述范式之下,传承人更多的是成为传授“技艺”的载体,是“技艺”的展示者和传播者。
由此可见,由于“权威化遗产话语”的渗透,目前联合国对于中医价值的认定,似乎更关注“技法”的传承及中医的医药价值。据透露,中医针灸之所以申遗成功,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便是其具有“技艺性、演示性很强的‘可见形式’”,符合“‘单体’项目要求”(张宗明 2011:64)。但是中国传统对中医价值的思考,最终应回归到儒家的济世道德价值取向,即由技入艺、医以载道。事实上,从张仲景的“进则救世,退则救民”,到范仲淹的“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中国传统对“医”的思考远远超越了其技术本身,而这恰恰是中医遗产保护中容易被忽略的。
五、结语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 近年来,我国大力提倡复兴优秀传统文化,并提出“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我们应以怎样的视角介入文化遗产研究,又应该以怎样的话语视角去书写、保护、传承文化遗产,这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本文以浙江衢州两部方志中的草药、医家叙述文本为例,分析了中国传统话语范式下的中医意义建构特征,以求为中医文化遗产保护和复兴提供一个可能的视角。我们无意全盘否定UNESCO 非遗保护策略和运作方式,也无意割裂传统和现代话语,或评判孰优孰劣,而是通过展现传统中医的言说方式及其中包含的文化观、价值观、道德观,呈现被现代话语所遮蔽的意义,从而实现传统与当下、东方与西方的对话,使得中国智慧在当下获得重新认知,进而走向世界,促进世界文化话语的多样性。这也是话语分析研究者所希望达到的目的,因为话语分析,尤其是批判话语分析,强调的就是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形成跨学科甚至超学科的视角(Fairclough 2005),从而促进多元文化话语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