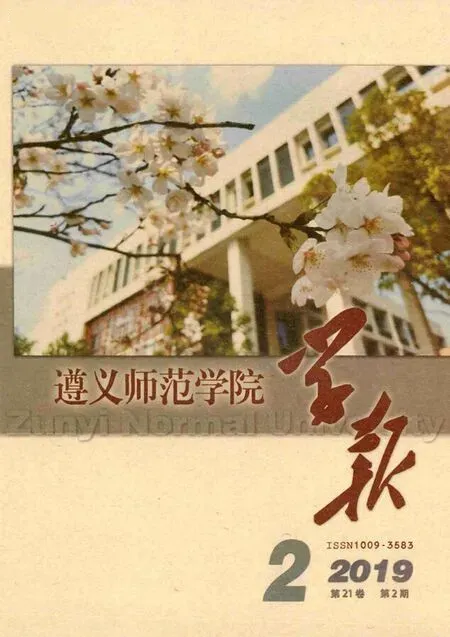邪典艺术:洛氏恐怖文学的审美特质研究
毛彬彬
(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吉首416000)
美国作家霍华德·菲利普斯·洛夫克拉夫特(1890―1937)与爱伦·坡、布尔斯被世人并称为美国三大恐怖小说家。三位小说家的文学创作活动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围绕恐惧这一人类在原始蒙昧中便已具备的天性来开展自己的独特书写,并形成了各有特色的作品体系,因而在世界恐怖文学史上各自占据了一席之地。三者在创作领域上的一致,却不影响在创作风格上的极大差异,也因此形成了三位恐怖小说家的作品中蕴涵的不同的审美意趣。其中洛夫克拉夫特的恐怖文学作品,如《疯狂山脉》《印斯茅斯的阴霾》《超越时间之影》等都具有洛氏自身独特的审美风格,受到部分读者的狂热喜爱,因此成为了小众恐怖文学爱好者们所津津乐道的邪典文学的重要代表作。洛夫克拉夫特将人类对于未知世界的恐惧书写到了一种艺术上的极致,如他曾在作品中写道“人类最古老、最强烈的情绪是恐惧,而最古老、最强烈的恐惧,是对未知的恐惧”。洛氏恐怖文学通常以一种非理性的笔触让故事的主人公随着故事情节逐渐深入,在面对接踵而来的未知恐惧的过程中开始失控乃至陷入疯狂,也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获得了一种建构于神秘主义与非理性倾向上的异质审美体验。这种独特的审美风格不仅在当时受到了一定程度上地关注,也在其后的恐怖文学作家群体中吸引了大量的追随者,如创作了大量同类型作品并整理、完善了克苏鲁神话体系的奥古斯特·威廉·德雷斯等人。虽然是通过后来者的创作与整理才使克苏鲁神话最终汇集成了一个庞大繁杂却又完整的恐怖神话体系并受到大量恐怖文学爱好者的肯定,但这个庞大的恐怖神话体系的奠基者这一荣誉则必须归于洛夫克拉夫特这位克苏鲁神话的先驱。在当前,尽管恐怖文学作为一种具有较大市场的文化产品类型,但在国内的文学研究领域中,恐怖文学的文学研究成果远少于科幻文学等其他题材。通过对相关作品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大量国内外现有的恐怖类文学作品都部分或全部地引用了克苏鲁神话的体系与其观念,并以此作为作品主要的世界观架构素材,这也导致了一种艺术同构和体系化的情况产生。因此将洛夫克拉夫特的创作与随后的克苏鲁神话体系作为学术研究的基质,以艺术审美的视角结合文化创新的要素来展开对恐怖文学的研究,有助于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与认识洛夫克拉夫特的作品的审美特质,更深刻地把握恐怖类文学作品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一、洛夫克拉夫特的惊悚美学
洛夫克拉夫特的作品和创作与他特殊的生活经历有着不可分割地联系,家庭生活的不幸与一生命运的坎坷为洛夫克拉夫特的文学创作始终蒙上了一层阴郁的色彩。由这种阴郁色彩所带来的是其作品中从故事的开始部分便可以令人感受到的压抑与紧张,这种氛围通过洛氏繁复而雅致的叙述手法与人物对白一层层地铺垫开来,使恐惧这种人类在面对危难时与生俱来的心理体验得到了彻底展示。而人类对于未知世界的恐惧,便是洛夫克拉夫特意图想要展现给读者的惊悚美学的出发点,他曾提出:“我认为,人的思维缺乏将已知事物联系起来的能力,这是世上最仁慈的事了。人类居住在幽暗的海洋中一个名为无知的小岛上,这海洋浩淼无垠、蕴藏无穷秘密,但我们并不应该航行过远,探究太深”。[1]洛夫克拉夫特在作品中对人类认知的可能性与真实性提出了质疑,认为人们不应该再对所处的世界那些尚未被人类所认知的部分进行进一步地探究,以免为人类招致祸患。剩余的未知部分对于人类来说应该是浩淼无垠的海洋,其中蕴含的无穷奥秘永远不应该被人类知晓,以保护人类可怜的理性。洛夫克拉夫特对于超自然和宇宙的认知是动态的,在他的一生中这种认知都在不断地演变,并最终趋向于一种感性而非理性的直观。这种思想的源起可能由于其所生活的时代正是现代科学技术飞速进步的时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使洛夫克拉夫特对于人类能否驾驭好这把双刃剑产生了担忧,从而使洛氏的创作哲学在认识论上彻底转向了不可知论。
这种认识论上的转向,为其在作品中营造终极恐惧即人对未知的恐惧创造了有利条件。洛夫克拉夫特写道:“在我看来,世界上最可悲的事情莫过于,人类通过无知的科学把世间万物联系起来”。在否认了人类科学认知世界的可能性与真实性之后,他以人类在面对从群星间降临的旧日支配者时,无法以理性视角与逻辑方法进行合理的解释,只能屈从于超自然的非理性与反逻辑作为了作品的主基调。如在《疯狂山脉》中作者以层层叠叠的叙事铺垫与人物对白来使整个故事情节抽丝剥茧般地向读者展开。伴随着探险中的故事主人公随着探索的逐步深入而渐渐失去理性,开始变得疯狂和怀疑一切,读者也在这种阅读过程中体会到了一种超越寻常现实的新奇,感受到了作者在作品中想要传达的艺术体验。这种体验正是来源于洛夫克拉夫特以人类的认知为界限,划分了人与世界的严密边界,却又通过他的作品让身处于平凡世界中的人们窥见了那一丝隐藏在浩淼无垠的群星与海洋背后的奥秘,由此带来的独特审美感受。
这与康德哲学体系中对现象界与物自体的划分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康德提出人类以及人类所认识的一切无不是处于现象界,可以被认知与评判,但却并非完全的真实。以人类的认知能力为界限,康德在现象界之外划分出了不可认知的物自体,将哲学探讨中的抽象和繁琐的概念皆归之于物自体,使人免于陷入无穷思辨的困扰。洛夫克拉夫特在他的作品中,将其创作中的重要概念即旧日支配者定义为人类不可思议、不可名状的存在,哪怕是其实体并未直接降临于世间,单凭旧神的名便能让人产生难以消退的恐惧并最终陷入疯狂。如在他的重要的、同时也是克苏鲁神话的名称由来的作品《克苏鲁的呼唤》中,故事的主人公由调查一个奇异的陶制艺术品开始,以凡人之身去探索超越人类理解的宇宙真相,经过仔细的调查之后发现藏在其后的恐怖秘密,越知道世界的真实面目,主人公就越失去理智,随着真相的不断揭示而一步步地将自己套入宿命的索套,再也无法挣脱。在这样的世界观架构之下,作者笔下的人类文明只不过是宇宙中小小的沙粒,人类引以为傲的艺术也不过是艺术家与沉睡的恶魔的精神发生感应后陷入癫狂的副产物,在旧日支配者面前甚至连人类的思考都是无意义的。读者在阅读作品的过程中,也随之产生了一种类似于故事主人公面对自身无法抗拒的诡秘存在时的恐惧与绝望的心理体验,在竭力保持着自身的理性以对抗故事世界的荒诞的同时,体会这种异质的审美意趣。这便是洛夫克拉夫特的惊悚美学,他以人类的认知极限作为作为突破口,将惊悚的元素寓于人的认知之外的存在,规避了人的理性对于荒诞世界的抵抗。
为了塑造这种诡秘却又具有诱人的惊悚的审美特质,洛夫克拉夫特在作品的用语方面则选取了一种略微不便于读者接受的、宛若巴洛克风格般繁杂而富丽的语言结构。在叙述过程中层层递进,围绕故事主线用大量的笔触进行环境、氛围的描写,并对主人公的心理状态进行大胆而直白的表述,以此塑造紧张、压抑、惊悚的整体风格。如在《疯狂山脉》中,他花了大量的篇幅来描叙南极的环境,描绘高耸的山脉与空旷无人的恐怖古城,读者的思维被洛氏的笔触带入到惊悚的故事世界,跟随着探险者一步步地探索冰层下的恐怖地道,伴随着对诡异壁画的真相一步步地揭开,主人公开始逐渐地失去理智,也越发地接近隐藏在南极深渊下的终极恐惧。对于这种超乎人类认知的终极恐惧的真实面目作者并没有用大量的篇幅去描写,在读者的思维随着主人公进行探索的过程中,洛氏的惊悚美学已经通过这种对于恐怖氛围的营造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二、崇高与邪恶交织的邪典艺术
如果将洛夫克拉夫特在作品中传递的惊悚美学进一步地拆解,我们可以发现这种令人惊异的艺术美感可以归纳为两个处于核心地位的要素,即疯狂的宏伟与崇高与无理性的神秘与邪恶。正是这两者在洛夫克拉夫特作品中相互交织,才支撑起了洛氏恐怖文学与克苏鲁神话体系的惊悚美学特质。
(一)疯狂的宏伟与崇高
无论是在洛夫克拉夫特的《疯狂山脉》还是在《暗夜呢喃》等其他作品中,亿万年前于群星间降临大地的旧日支配者们都是人类不可思议、不可名状的存在。主人公在面对这样一种超乎于寻常思维定式,违反现有的科学逻辑的存在时,无不为之畏惧和疯狂。对于那些作者笔下虚构的超越时间与空间的诡秘存在来说,人的一切都是无意义的,人类只不过是旧日支配者的玩物,等待着被从沉睡中苏醒的旧神重新纳入统治,主人公在认识到宇宙的黑暗真相之后也不免陷入癫狂。洛夫克拉夫特以一种独特的、站在人类之外的宏大笔触对克苏鲁神话的世界观进行了塑造。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把宇宙看作是一个由天、地,以及在天地之间的自然事物按照一定的等级次序排列而构成的系统。一切生物和生命之母的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诸神所居住的天空位于宇宙的上面区域,由各种永恒运动着的星体构成”,[2]而在洛氏笔下,整个世界都是盲目痴愚的强大旧神阿撒托斯的睡梦中的产物。如果以艺术审美的视角来分析这种宏大的叙写,读者在阅读洛氏恐怖文学作品的过程中,会被不自觉地带入这种宏大的意境,对自身所处的现实环境和原有的思维定式进行了超脱,开始以克苏鲁神话的世界观对人类的社会与文明进行重新地思考,以黑暗诡秘的宏大宇宙来反衬人类文明的渺小,从这种对比中得到一种独特的、似于崇高的感受,这种崇高感受同样属于一种审美体验。以康德的美与崇高的观念来看,这种崇高体验与普通的艺术美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共性,即“二者都是审美判断即反思判断,都是自身令人愉快的并不涉及利害,目的和概念,但又都具有主观的合目的性,必然性和普遍可传达性”。[3]
在阅读洛夫克拉夫特的恐怖文学作品时,读者可以明确感受到面对着无垠而神秘的超自然世界,崇高这种无形式的审美体验无时无刻不在感染我们的阅读心理,洛夫克拉夫特的作品中描绘的克苏鲁神话世界早已超出了在通常情况下读者阅读经验与认知能力的把握。非现实元素构建的克苏鲁世界这一假定性情境对于读者而言,只能视为必须利用整体性的心理体验去把握的对象,读者感受到的只能是一种超越形式的、无限制的、违反理性的审美感受。在宏伟的群星海洋与超自然的旧神之间反现人类文明这沧海一粟般的渺小与卑微,这种宏伟与卑微的落差通常让故事中的主人公逐渐失去理智、陷入疯狂。但这种在渺小中看见宏伟,由恐惧转化为崇高的体验通过作品所传达出的,却是读者在体验虚构出的、无害的崇高之时明显地感受到的艺术审美的愉悦。
(二)无理性的神秘与恶意
与这种欣赏崇高的愉悦体验相伴的则是一种基于神秘主义的氛围与洛夫克拉夫特想要表现的无理性的恶意。在洛氏笔下的故事中,通常都是主人公因为偶然事件或者线索而一步步调查下去,最终触及到某些涉及到旧日支配者的“禁忌的知识”,打破了原有的认知边界,颠覆了对世界的认识。这种充溢着神秘主义氛围的叙述风格很难说没有受到当时盛行的存在主义思潮的影响,尤其是克尔凯郭尔的神秘主义。因自身的信仰问题,克尔凯郭尔的一生是在忧郁中度过,洛夫克拉夫特同样也在一生中饱受精神崩溃的困扰。“在洛夫克拉夫特46年的短暂人生旅途中,他总共创作了65篇小说,以及数10篇记事、散文、诗歌”。[4]在作品中,洛夫克拉夫特否认了现实世界的意义,否认了人类存在的意义,否认了人的思考的意义。洛夫克拉夫特用他的笔触将现实的一切都诉诸于神秘,用认知能力作为界限将认知之外的一切未知都留给了自己虚构出的超自然的存在,以一种非理性的态度来建构独特的克苏鲁神话体系。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普洛丁在美学史上首次驳斥了古希腊罗马以来在形式上关于美的理论,强调人的主观精神,认为美不是事物的属性,感性世界的美总是渗透着精神的东西。”[5]但在古希腊时期的日神与酒神这两种精神的划分中“日神精神是有节制、有度的,摆脱剧烈情感而依靠哲学式的冷静。日神精神构筑事物的表象、美的表象、梦幻或造型艺术,并通过表象摆脱痛苦。而酒神精神则不同,它通过瓦解个体意志,把痛苦转变为普世的存在哲学,带有幻想的方式,使苦难得以释放。”[6]
而依据克尔凯郭尔的哲学思想,在现实世界中真实存在的唯有人内心中的东西,即人的主观意识与非理性的内心体验。在洛夫克拉夫特笔下,这种个人内心中的体验被极大地简化了,克尔凯郭尔认为人在现实生活中体验到的只是痛苦、情欲、含混和荒谬等感受。在洛氏的克苏鲁神话中,这种内心的体验被不可思议地简化到只剩下荒谬的、宿命般的、无理性的恶意,旧日支配者对于人类除了毫无由来的恶意之外别无其他的情感,哪怕是作为同族的人类,也一样充满了恶意。如在《墙中之鼠》这个骇人的故事中,作者先以叙述者的视角展开叙写,通过层层铺垫营造恐怖氛围,最终则通过视角的转换,告诉读者恐怖的情节恰恰是由于主人公自己所致。这种突然的转换让读者感受到的只能是来自外界的毫无理性、难以逃避的恶。而在“《超越时间之影》中,匹斯里一生都生活在可怕的噩梦与恐惧之中,无法再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他的灵魂已经毁灭”。[7]
由令人疯狂的、超越人类认知的宏伟描叙让读者感受到的、异样的崇高与根源于非理性的神秘主义风格和被着重凸显的、源自于人的内心的、无由来的恶意这两者相交织,便是洛夫克拉夫特的邪典美学特质的两大核心所在。
三、克苏鲁神话与文艺创新
毫无疑问,洛夫克拉夫特作为克苏鲁神话体系的先行者,在世界恐怖文学史上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在今天,我们除了阅读、欣赏他的以及受到他的作品影响的追随者所创作的克苏鲁神话体系作品集群之外,更应该注意到这一作品集群在文艺创新中的应用与价值。当前,虽然已经有学者开展了对于克苏鲁神话等其他恐怖文学作品的研究,如史蒂芬·金的创作与作品研究等。但在总体层面上,恐怖文学研究理论的建构还是较为不足的。这不仅导致了相应的恐怖文学作品的研究理论的缺失,也导致了研究者在将其他恐怖文学作家、作品纳入文学研究领域时会遭遇到比针对其他题材的文学研究活动更大的困难。单纯地将恐怖文学提出作为一个文学研究对象,结合当下人们的文艺心理期待与市场反馈来开展学术研究,也是一个具有一定的创新意识、把握了文艺需求的研究新方向。当前有大量的恐怖文学作品都部分或全部地借用了克苏鲁神话体系的世界观,这也显示出洛夫克拉夫特的作品的思想价值:通过作品的世界观与人物对白来展现对荒诞世界的反抗思想,以及以艺术化的方式表达对人类科学探索的担忧。同时,隐藏在其思想价值背后的市场价值也值得我们的注意。
当前“关于洛夫克拉夫特的研究,国内几乎少有关注。在若干个版本的美国文学史中,只有寥寥几本提到了洛夫克拉夫特,也仅仅是一笔带过”。[8]在这样的前提下,以不同的学科和理论视角为基点进行对洛夫克拉夫特的作品与创作和克苏鲁神话体系的研究,对于后来者在创作该类型文学作品时谋求创新有着极大的助益。在讲求文化创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不仅要大胆向前迈步,更要回首看向文学创作者在文学与文化中的积淀,从中寻求创新的思路与方法。
四、结语
综上,我们在将洛夫克拉夫特的作品与创作及以其为先行者的克苏鲁神话体系归于邪典艺术后,通过对其审美特质的分析,得出了构成洛氏恐怖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的两大核心即疯狂的宏伟和崇高与无理性的神秘和恶意,以此对洛夫克拉夫特的恐怖文学作品进行了一次美学层面上的探讨,并分析了洛氏恐怖文学在当前的文学领域中的价值。尽管洛氏作品中的一些特点如繁杂富丽的文风也时常为人所诟病,但这并不影响其在世界恐怖文学史上的地位。在追随者的努力之下,克苏鲁神话现今已经成为流传最为广泛的恐怖文学创作体系之一。“洛夫克拉夫特在穷苦潦倒中离世,现在他终于得以安宁,远离喧嚣,愿旧日支配者的低语不再侵扰洛公的安眠”。[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