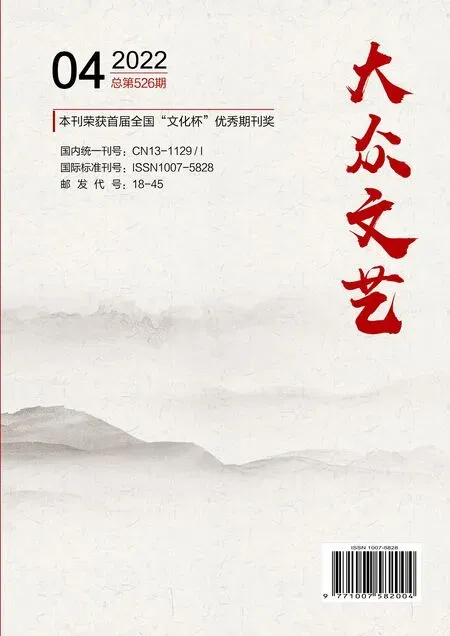从十八线演员熬成悲剧制片人
——解读《金锁记》中曹七巧的悲剧命运
徐珊珊 ( 南京林业大学 210000)
一、外因:局外推手
七巧的哥哥曹大年为了钱把她卖给姜家残疾的二少爷做姨奶奶,在讲究“门当户对”这种传统婚姻观的时代,出身卑微的曹七巧在姜家自然不会太好过。姜家老太太改变主意把七巧扶做正房奶奶,突然拔高了她的身份,但并不待见她的“草鞋亲”。七巧痛恨自己被娘家坑了一辈子,对哥嫂的态度很恶劣,却始终摆脱不了这份拖累她的亲情。在姜家生活的不满将她的性格逐渐导向压抑扭曲。
二、内因
(一)姜家社交圈交际障碍
七巧原是麻油店站台的,日常所接触的都是市井村民,社会阶层低但见多识广,这样的生活环境使她养成了大大咧咧的性格,说话没忌讳,在氏族大家里很容易遭人嫌弃。身份卑微导致她在姜家不受人尊重,三奶奶兰仙不大搭理她,就连丫鬟也敢在背后说三道四。七巧也想通过主动接触姜家人的方式来赢得人际关系的改善,竭尽全力想要融入姜家的社交圈,却总是事与愿违,村妇式的言行举止往往成为别人口中的笑柄。可以说,曹七巧的种种言行表现出了神经症性格倾向。“从具体从层面上说,神经症是由人际关系的紊乱和失调引发的”,这也是她情商低的表现。
(二)性格及思想缺陷
七巧错在不该嫁入姜家,然而换一种门当户对的婚姻,她也不会过得幸福美满,根因在她自己身上:嘴太毒,怨气太重。大事小事都败在她的一张嘴上,文中两次形容她平扁而尖利的喉咙“像剃刀片,四面刮得人生疼”,这张嘴不仅伴随了她悲剧的一生,也双双葬送了儿女的幸福。多年的隐忍化为牢骚抱怨,她成了别人眼中典型的“毒蛇怨妇”形象。但她又不能表现出来,只能幽恨,一个极具表现力的演员最终熬成了制片人,只不过所导向的都是悲剧。
七巧对女儿长安的婚姻有着太过绝对的经验之谈。自己因为钱财卷进了一场没有爱的婚姻事故,就形成了婚姻都是为了钱的思维定势,提亲者家境不如她们的一律否决。即便是小老太太的形象,出场也自带阴森恐怖气息,童世舫第一次见她时竟觉得毛骨悚然。
丈夫和婆婆相继过世,她数十年的忍耐就是为了金钱,终于等到分家的时候,又假装从容不迫,怕被人耻笑,自尊心很强。姜家房产她都调查过,可见其精明与盘算之久,用十年摸清了这个局,把钱作为终极目标,其心理必然经历了极为复杂的积压演变。她就像个演员,当着九老太爷的面精心演了一出“苦情戏”,却还是敌不过封建分家制。
(三)视钱如命
曹七巧对金钱的需求呈现病态。一分到钱就立即跳脱姜家,与之几乎切断来往,守财奴的性子开始显露。姜季泽十年后再来找她,尽管依旧心动,但在爱情与金钱面前,她还是选择了后者。消磨的时间改变了她的金钱观与价值观。她在姜家长期缺乏安全感,没有爱情,没有靠山,也没有可以信任的人。她对钱太过于敏感,一提到钱就精神紧绷,很容易情绪失控,总觉得别人的靠近都是为了她卖掉一生换来的几个钱,令人心酸。她就像个怀抱金钱的刺猬一样,表面锋芒毕露,内心却敏感而脆弱。
(四)情欲的极度压抑
她曾经也有粉红泡泡的梦,渴望被爱,然而丈夫患有软骨症,不能满足她正常的情欲。她也得不到想要的爱,姜季泽故意躲她,碍于世俗眼光,她没有那么强的反抗性,不得已压抑自己的情欲。曹七巧的泼辣、暴戾、变态,都是在欲望长期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产生的,换位思考甚至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她爱姜季泽,但他更看重她手中钱,情欲的她更加痛苦,痛苦则使她的怨恨变本加厉。长时间积累恶念, 那么这样的生命就只能在痛苦和无明当中不断轮回。她成了严重缺爱的“毒蛇怨妇”,她的世界从此失去了色彩。
(五)孤独患者的病态报复心理
七巧对女儿长安的一系列行为尤为矛盾。为了把女儿培养成大家闺秀,在追求放脚的新旧交替时代还给女儿裹小脚;作为单亲妈妈更是要强,为跟大房、三房攀比,送女儿上新学堂,但她对女儿花钱太斤斤计较,毫不顾虑她的自尊心,导致长安羞愧退学。面子、情欲如蔓草的恶滋,使得儿女成了七巧发泄与满足情欲的工具。女儿长安的婚事一直被耽搁着,谈到嫁妆就破口大骂长安,边暗示自己没钱边贬低自己的女儿,只是因为怕别人要嫁妆钱。当女儿终寻觅到一个如意的未婚夫,沉浸于爱情的甜蜜时,七巧源于孤独以及女性的嫉妒,无意之中向准女婿透露长白抽大烟上瘾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仅仅一句话就摧毁了长安所有的希望。长安也怕了七巧,不再想着出嫁,逐渐成为七巧个体悲剧的继承者。
七巧对儿女婚姻的病态心理,不仅表现在对他们婚姻的掌控欲上,还表现在极力外化儿媳妇上。严重的恋子情结、扭曲的母性,对长白占有欲太强,从而产生了根本不把儿媳妇当自家人的外化冲突,觉得儿媳会抢走自己一生最重要的这个男人,便百般羞辱直至其死去。她宁愿将已婚的儿子彻夜守在自己面前烧烟也不愿他和儿媳妇在一起,前后逼死两房儿媳。长白怕了七巧,整日在外厮混,避而不回。
三、结语
制片人是一部片子的主宰,提供资金链,负责统筹指挥,并有权决定一切事物。黄金死死地掌握在七巧手里,只要七巧存在,长白和长安注定逃脱不了她的控制。曹七巧对自己及儿女有着矛盾态度以及矛盾的价值观;对金钱的理解过于偏激,被黄金的枷锁奴役,甚至发展到了精神障碍,成为爱情和婚姻里的双重牺牲品,活生生裂变成了报复者,葬送了好几条人命。她本就是个悲剧制片人。
——曹七巧形象的另一种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