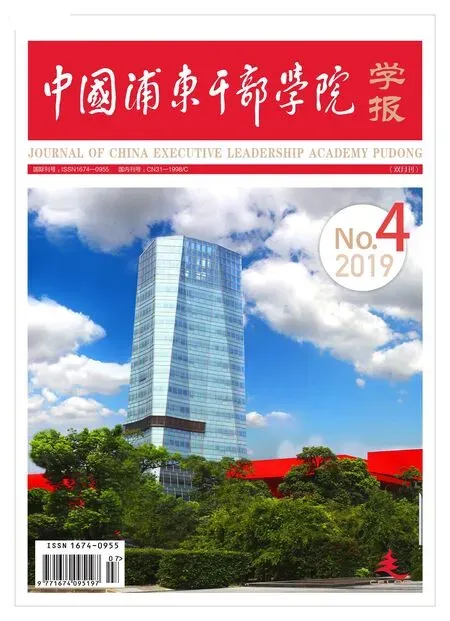“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情感赋义
王清涛
(山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250358)
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以及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主旨演讲的主题和核心就是“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崇高的价值目标,“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1]15
构建自己研究的对象向来是哲学的宿命,因为哲学从来没有自己现成的对象。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指出,哲学与其他科学不同,其他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现成的,而哲学研究的对象则是自己建构的,“哲学是独立自为的,因而自己创造自己的对象,自己提供自己的对象”。[2]59许多学者在使用“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时,通常是将其视为意义自明的概念来使用,并望文生义地臆造了它的内涵,但越是常用的概念其意义往往越是模糊不清,即所谓“熟知非真知”,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指出,“熟知的东西所以不是真正知道了的东西,正因为它是熟知的。有一种最习以为常的自欺欺人的事情,就是在认识的时候先假定某种东西是已经熟知了的,因而就这样地不去管它了”。[3]20“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这样一个概念,它有待于思想的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以现实的经验世界为基础,但它又不就是现实的经验世界,现实的经验世界有很多不尽完美、不尽完善的地方,它有待于按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则进行建设,其目标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当今世界的否定形式。“人类命运共同体”存在于对未来美好世界的期待中,这一概念本身也是一个尚待建构的哲学命题,将其背后的哲学讲清楚,是当代中国哲学的使命。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哲学研究的对象
从巴门尼德开始的形而上学,其所关注的并不是经验对象,而是经验世界背后的“真正”存在,如本源、善本身、理型、真理、本质等,当时哲学研究无非是对这些“真正”存在的理解和界定。唯名论产生以后,认识的对象发生了根本转变,哲学研究从实在论的抽象存在转变为对经验对象的精确描述,经验对象成为认识的唯一对象,这是形而上学研究对象的第一次“乾坤大挪移”。再后来,在走出胡塞尔现象学主体间性困境中诞生了语言分析哲学,在后者那里,维特根斯坦发现,所谓的哲学问题其实是语言问题,于是,所谓的哲学研究其实是语言分析。据此,维特根斯坦实现了哲学研究的语言转向,哲学的对象不再是外部世界,而是人的语言本身。
虽然在哲学史上形而上学的对象有过几次转移,但其对象根本上来讲却都指向现实世界,唯名论以经验世界为研究对象自不必说,所谓的“真正”存在也是针对现实世界而言的,“真正”存在是现实世界背后的“真正”存在;而维特根斯坦所谓的语言学转向,表面看来哲学研究的对象成了语言分析,但维特根斯坦的语言还是对现实世界精确描述的语言。维特根斯坦将世界区分为现实世界和可能世界,现实世界是可以用语言言说的世界,“命题是现实的形象”,[4]38“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逻辑充满着世界;世界的界限也是逻辑的界限”。而可能世界则是不可言说的世界,“我们不能思考的东西,我们就不能思考;因此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思考的东西”,语言到此止步,“世界是我的世界这个事实,表现于此:语言(我所理解的唯一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主体不属于世界,而是世界的一种界限”。[4]79波特兰·罗素在为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一书所作的导论中概述维特根斯坦的意见,“我们的世界对于某些能从世界之上来俯瞰的高级的存在物来说可能是有限的,但是对我们来说,无论它怎样有限,它不可能有界限,因为在它之外一无所有”。[4]12可以言说的世界是现实世界,但不可言说的可能世界只不过是还没有进入人的语言世界中成为思想对象而已,如此看来,以往的哲学,其形而上学研究要么直接以经验世界为对象,要么是研究经验世界背后的“真正”存在,要么是对经验世界的语言描述进行分析,总之,以往形而上学的对象都与经验世界相关,但“人类命运共同体”虽然以经验世界为根据,但它又不在经验世界中,它能否成为形而上学的对象?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预见到人类将要面临“灭亡”这样一个严峻事实基础上提出来的,是人类对自己命运的警醒。人类正面临着一系列威胁,如在冷战时期因美苏争霸所带来的核威慑,它会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人类如同坐在随时可能爆发的火山口上,人类灭绝随时会不期而至。除此之外,环境危机、资源危机、粮食危机、人口危机等等都如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人类头颅之上,随时会终结人类历史,如果不对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空洞等采取措施,人类走上不归之路是实实在在的。这个或将出现于人类面前的对象是实实在在的,它可以用语言进行精确描述,因而可以成为形而上学对象。而人类之所以要预见“人类将要灭亡”这一事实,是为了避免这一事实的出现,因此,人类会采取各种各样的行动,去消除带来这一后果的种种原因,来挽救人类,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对这一思路的精确表达。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作为与“人类将要灭亡”相对立的概念存在的,“人类将要灭亡”的实在性决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在性,那么既然“人类将要灭亡”可以进行精确描述——“人类将要灭亡”已经成为文学、艺术、哲学的重要题材,许多科幻电影,如《2012》《后天》《未来水世界》《天地大冲撞》等都力图对“人类将要灭亡”这一事实进行精确描述,那么,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对立概念得到充分描述之时,“人类命运共同体”当然也应当成为被描述的对象,并且这一对象会在描述中完整呈现出来,即“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形而上学对象。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的哲学研究就是谓词对主词的界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语言赋义是一个形而上学问题。
情感判断在逻辑学上没法进行真值分配,但其开启了人的存在的多种可能性,对其研究在哲学上属于“偶态存在论”或“偶态形而上学”,谢文郁是对此问题关注较多的国内学者,他说:“从亚里士多德关于情态句的分析开始,追踪情态句中的可能性问题,展示其中的模态逻辑问题……模态命题中有情感因素。一方面,模态命题的情感呈现了可能性之实在性;另一方面,它直接引导不同生存方式……这一语境中充分展现了一种完全撇开现实世界来谈论可能性的偶态存在论”,[5]“这里谈论的可能世界是实在的(但不是现实的),因而相关命题是具有真值的(不是在条件句中或假设中)。人们把这个思路称为‘偶态形而上学’”。[6]344如此看来,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属形而上学的一个特殊领域,即属于“偶态存在论”或“偶态形而上学”。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情感对象
语言所赋义的形而上学对象有三类:即经验对象、论证对象和情感对象,这三类对象的意义分别通过经验指称、论证呈现和情感指示完成,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究竟是一个经验对象,还是论证对象,还是情感对象呢?“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个拥有现实基础,是根据现实逻辑推论出来的人类共同体的未来形态,应该是与现实相关联,但这一未来形态必然不被经验,所以,它首先以经验为基础,但又不是一个经验对象;其次,它是在逻辑论证基础上理性推论的结果,但它又具有不确定性,它依赖于人们对未来的态度,因人类对未来态度的不同,人类历史会有不同的发展方向,也就是说,当人们把世界当成是掠夺的对象,如海德格尔所讲的,世界是在我之外的现成物,人与世界相对立,人与世界的关系就是攫取和被攫取的关系,那么,世界的未来将不但不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反而其前途岌岌可危,甚至有可能走向毁灭,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也不是一个论证呈现的对象;“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否到来完全有赖于人的情感,是因为人们之间普遍的爱,人类对世界前途和命运的担忧,人们才投身于对未来世界多种可能性的认识中,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如此,才会呈现“人类命运共同体”。
如果“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情感对象,那么首先必须回答的就是这一对象的实在性问题。情感指向的对象是非经验对象,它的实在性靠什么来保证?虽然情感对象不在人的感觉经验中,但进入人的感觉经验的对象毕竟是有限的,未来的一切都不在感觉经验中,都不是感觉对象,如果仅仅承认感觉经验中的对象的实在性,那么,人的感觉经验的扩大必然是:在横向(空间维度)不断进入未知领域,在纵向(时间维度)不断进入未来,也就是说,我们在不断地进入非实在性之中,即进入虚无之中,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贝克莱将非感觉对象的实在性交给上帝,其实在性因在上帝视野中——“存在于一种永恒精神的心中”[7]22而得到了保证。也只有上帝的承诺,经验主义认识论才不至于将经验有限性推入到虚无中。情感对象的实在性得不到经验的证实,但也不会因为无从经验而被否定。未来的一切和不断拓展的未知领域都存在于人的情感世界。
与不同的感官呈现不同的感觉对象相类似,不同的情感也指向不同的对象,在这一点上,充满情感期待的全球化和以掠夺为目的的全球化,在其视野中所呈现出来的对象是完全不同的。从新航路开辟以来的全球化并不是对世界美好情感期待的产物,而是资本逻辑的结果。哈佛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在其《棉花帝国全球史》(Empire of Cotton: A Global History)一书中将成就现代世界的全球化历史分为从16世纪开始的“战争资本主义”(war capital)和从18世纪末开始的“工业资本主义”(industry capital)两个阶段,欧洲以枪炮开道的战争资本主义以“奴隶制、侵占土著人民、帝国扩张、武装贸易及企业家对人民和土地的主权”为核心,而工业资本主义则指称“我们通常认为的现代世界,即以大规模生产为基础的全球化模式,它大约出现在1780年左右的工业革命中”。[8]6无论是战争资本主义还是工业资本主义,其目的都是通过掠夺而实现发财梦,对全球化的情感期待是负值,如果说有所期待,那也无非是期待被掠夺地区有更珍贵的宝藏,更丰饶的物产——以满足掠夺为目的,中国近现代就因此而陷入无底的深渊和灾难中。无论是第一阶段的全球化还是第二阶段的全球化,它们都以掠夺和牺牲殖民地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民族和人民为代价,全球化的结局必然是失衡的世界,落后国家和人民成为全球化的牺牲品。既往的全球化是资本逻辑的产物,其发财致富的贪婪决定了既往全球化无情掠夺的本性。但“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开显的全球化新时代,是以对世界的美好期待为动力,是以“为世界谋大同”为目的,是以全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对未来世界的美好向往为支撑,充满期望的理念必然带来充满期望的未来。经济学家张维迎《理念的力量》一书的核心观点认为,支配世界的不是既得利益,而是理念,“理念是重要的,人的行为受利益的支配,也受理念的支配;社会的变革和人类的进步基本上都是在新的理念推动下出现的,没有理念的变化就没有制度和政策的改变;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所取得的成就是理念变化的结果”,[9]1而人们笃信的理念就是信念,信念就是一种情感。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情感基础
“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提出基于敬畏、担忧和期待三种基本情感。
其一,敬畏情感。中国人的敬畏情感是在祖先崇拜中逐步确立起来的。哲学上所讲的敬畏主要是对天命的敬畏,孔子敬畏天命,讲君子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10]256对天命的敬畏这种情感包括两部分,即崇敬和畏惧,首先,所崇敬的对象一定是高高在上的,作为天命来讲,它是人命运的主宰,主宰人的吉凶祸福;其次,被崇敬的对象本身就是绝对必然性,此所谓“天之经,地之义”,人只能去遵从它,而不能去改变它;再次,被崇敬的对象一定会根据人的行为对人做出奖惩,正是因为天命可以对人奖惩,因此人类才对天命产生畏惧之心,崇敬与畏惧合起来就是敬畏之心,敬畏之心是处理人与世界关系的基本情感,也是人与世界其他情感关系的基础。孔子敬畏天命是为了从天道观上找到其政治主张合理性的理论依据,天下是天命授受的,“天降丧于殷,殷既坠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终出于不祥”,[11]243因此,君王要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才能基业牢固。敬畏天命,顺天而为,是对人类的共同要求。“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首先在对世界的敬畏中出现的,当代人是人类历史的一个片段,人类历史浩荡前行,其发展有恒定的规律,人必须尊重人类历史规律,如果对人类历史规律不敬,就会遭受其惩罚,这在人类历史上的惨痛教训不胜枚举,承认唯物史观就必须确立对世界的敬畏之心。正是在对世界的敬畏中,人类历史规律的威严才矗立起来,人在其面前不得妄为,其行为必合历史之大道。但纵观当今世界,人类历史大道不显,许多国家、地区、民族的行为仿佛是一次次地向人类历史大道冲击,极端组织、极权政治、国际恐怖主义等正将这一态势愈演愈烈,人类前途与命运岌岌可危。与中国人的敬畏情感不同,基督教文化的基本情感是信念,信念的对象是上帝,因而信念处理的是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而敬畏搭建起来的则是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从敬畏情感中可以生发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
其二,忧惧之心。《列子·天瑞》中就有一个杞人忧天的故事,“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身亡所寄,废寝食者”。[12]23杞人忧天是讽刺那些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而担惊受怕的胆小怕事之人,但也正是这种对未来的担忧,可以使人们反省自己的生活方式,并进一步发展为影响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人类命运共同体”就起因于对未来的忧惧之心,担心人类未来可能的不归之旅。正是因为对此的忧惧,才可能迫使当代人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社会管理方式、社会发展方式以及面对周围世界的态度,正是在对未来的忧惧情感中,一个新的人类生存状态显现出来。
其三,期待情感。人们总是期待事件朝有利于自己生存的方向发展。未来世界总处于多种可能性的变化之中,自从人类诞生以来,人类总是幻想自己同上帝一样具有规划未来的力量,人们用自己的能力和智慧塑造未来,但是,未来从不完全像人类给定的那样单调,未来世界总是处在多种可能性之中,人类在“尽人事”之后,只能“听天命”,然而,人类更期望事件朝有利于自我生存的方向发展,这就是期待情感。当代世界科学技术如此发达,但人类还是不能完全掌控世界的未来,“灰犀牛”“黑天鹅”层出不穷,世界总处于无限的可能性之中,正因如此,人类只好期待美好的未来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人类对世界未来的美好期待。
命运情感会带来人生态度的转变。人类将走上不归路是当代人对于人类未来命运的担忧,那么,在仇恨人类的人那里,他恨不得人类走上不归路,他可能会为人类走上不归之路而谋划,甚至为这一目标而做些什么。反过来,对于那些热爱人类,唯恐人类的将来有所差池,对人类未来担惊受怕的人来说,他也会做一些相反的工作,可以使人类更好地发展,永续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的一个情感对象,作为情感对象,它是在人类对人类命运之不归路的忧惧基础上而产生的,它可能会成为人类的未来,但也可能永远不会成为人类的未来,我们作为哲学问题来思考它,而无关乎其真假,当然,只要全人类都忧惧人类未来的前途和命运,并以此而产生共鸣,走人类命运共同体之路,那么,人类永续发展的可能就会到来。
四、情感赋义基础上的逻辑演算
完成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情感赋义,便可在此基础上进行逻辑演算,即以一旦“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实实在在的形而上学命题,其内涵在情感赋义中被揭示出来,并被人理解和接受,那么,一个人所理解的世界同时也可能是其他人所理解的世界,这在胡塞尔那里就是主体间性问题,一旦人们对世界未来的理解具有共同性,人类就可能采取共同的拯救世界的行动。对人类未来命运的忧惧情感可能是共同的,那么为了避免人类走上不归之路,人们会达成观念上的共识,形成观念共同体,一旦对人类前途命运的担忧情感有了共鸣,那么人类便会在共同的情感基础上认识世界,这样的人对人类未来命运有着共同的看法,继而形成观念共同体,共同观念可以产生一致的行动,来避免断送人类的前途和命运。
首先,是共同情感形成观念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情感对象,凡情感都具有感召力,“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一个具有强烈感召力的情感对象,凡是关注人类未来,关注人类命运的人,都会为人类的前途和命运担忧和着想,他们会逐渐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并形成观念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要旨就是,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13]
其次,共同的观念会带来共同的行动。一致观念的达成是采取共同行动的基础。例如,美苏从核裁军谈判到协议的达成,就是因为预见到了一旦全球爆发核战将给人类带来无情灾难这一可能而采取的行动。20世纪50年代初,随着氢弹爆炸,人类清晰地认识到核武器对人类生死存亡的巨大威胁,因此,从1958年起,美苏开启了核裁军谈判,1991年终于签订了《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虽然跟人们期待的去核还相去甚远,但这一条约的签订无疑是人类要保护世界免受核威胁的共同观念的初步结果。2015年12月12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近200个缔约方一致同意通过的《巴黎协定》又是一例,《巴黎协定》的签署是因为各方预见到了气候变化对地球的威胁,并因此采取一致行动。“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这样,“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综合人类面临的各种威胁前提下提出的架构更加宏观、目标更加远大的概念,一旦达成这样的观念共同体,人类将采取类似的行动,来避免人类所可能面临的各种威胁。
再次,“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下的共同行动会带来整个世界的重大变化。“人类命运共同体”会引导整个世界的社会状况、人的生存方式等都发生实实在在的深刻改变,包括人和自然的关系、人类的生产方式、社会管理方式甚至人的思维方式等都会发生根本改变,也就是说,“人类命运共同体”会带来一个新世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得到了广泛认同,“‘一带一路’构想得到一百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将44亿人口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4]世界对“一带一路”的认同很重要的原因是“一带一路”背后所蕴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带一路”建设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尝试,“一带一路”将贯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全球对“一带一路”的积极响应事实上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同,这种观念上的一致将会带来“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动,而共同的行动将会让人类命运共同体走向现实。
结 语
世界是全世界各国人民共在的世界,这个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建设都不能仅仅以自己国家的发展为唯一目的,而是要以整个世界的发展和进步为目的,一个国家的人民在建设自己美好家园的同时,也在记挂着世界的建设,每一个国家的建设都是世界建设的一部分。国家规划和发展以世界进步为指向,与整个世界的未来融为一体,与世界共同进步。在经济一体化领域,欧盟的政策、制度为欧洲一体化的谋划走在了世界前列,但欧盟的规划以欧洲发达国家一体化的经济为根基,世界的共同进步不在其考量的范围之内,欧盟说到底,是欧洲发达国家如何形成统一市场,并继而保持和提升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优势,从而更有利于其攫取高额利润罢了。而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却是致力于塑造一种新的世界秩序,这一新秩序以人类的共同福祉为考量,中国规划的巨型世界工程(如亚欧铁路大动脉、亚美高铁设想等),这些发展项目均以世界未来为蓝图,因而,中国的“一带一路”带来的全球一体化,将助推一个美丽新世界建设。这个世界,因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间的相互友好而充满意义,一个民族因活在其他民族温情的祝福中,活在其他民族善意的期待的目光中而充满自豪感,而倍增建设新世界的激情。这样的一个世界才是一个各民族共在的世界,一个民族的存在以其他民族的存在为目的,而不是以其他民族的存在为手段——此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应该深刻地检讨自己的历史及其价值观。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人类社会何时不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侵略、奴役和压榨。然而,当代世界再也不允许这一噩梦重演,世界不再给人类这种机会,当代世界再也不允许一个民族的发展以牺牲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为前提了。当代世界是一个合作共生的时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当代世界是一个系统的整体,一个民族的命运与其他民族的命运休戚与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