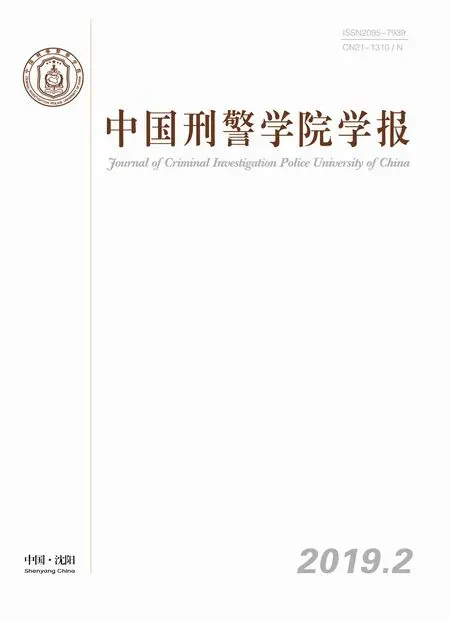微观互动视角下警察执法冲突行为研究
汪开明 沈瑞英
(1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 上海 200444;2 巢湖学院经济与法学学院 安徽 巢湖 238000)
1 引言
除少数例外,警察执法活动中的强制行为大都是在平时的日常生活情境中发生的,因此,这些发生在警察执法中的强制行为往往容易引起社会和大众舆论的关注。由于警察是代表国家行使公权力的一方,他们可以在执法过程中合法地对相对人采取一些强制措施。一方面,实践中确实有一些警察在执法过程中滥用权力,对相对人非法或不适当地使用某种强制措施,而“警察权力与公民权利在一定条件下成反比例关系,即警察权的扩大意味着公民权的缩小,警察权的滥用往往导致公民权化为乌有。由此可见,这里存在一个警察权的悖论:一定限度内的警察权是为保障公民权所必需的,而超出这个限度的警察权,则有侵夺公民权之虞”[2],警察在执法中如果非法使用某种强制措施,会严重侵犯公民合法的权利与自由。另一方面,警察与相对人,特别是那些身为普通社会公众且只是实施了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相对人相比,警察天然处于某种强势地位,这导致即使在警察对这些相对人合法使用某种强制措施的情况下,出于对弱势群体的本能同情,社会和大众舆论也会对警察执法中使用的强制措施大加贬抑,甚至是愤怒申讨,特别是在涉案相对人受伤、致残或死亡的情况下,社会公众的这种愤怒之情更是达到顶点。在传媒高度发达的当代社会中,无论中国还是外国,关于警察执法中对相对人采取的强制措施一直就是社会争议的焦点问题。例如,美国很多警察执法暴力案件甚至引发了较为激烈的社会动荡,典型的如1992年4月29日因“罗德尼·金案”而发生的“洛杉矶骚乱”①1992年4月29日,美国洛杉矶一家地方法院宣判1991年3月3日毒打黑人青年罗德尼·金的4名涉案警察无罪。法院对4名警察的无罪判决引发了美国公众特别是广大黑人的强烈不满。当晚,数千名黑人在洛杉矶街头举行示威游行,示威游行持续数十小时,并引发严重骚乱,共造成50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上千幢房屋被焚毁,经济损失超过10亿美元。、2015年4月27日因“格雷案”发生的“巴尔的摩骚乱”②2015年4月12日,美国巴尔的摩市25岁的黑人青年格雷因逃避警察的盘查,在神志清醒的状态下被警察戴上手铐押上警车,但1小时后格雷从警车里出来时已经神志不清,脊髓几乎断裂,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4月27日,在格雷葬礼举行后,巴尔的摩爆发全市骚乱,彻夜的纵火、抢劫使得市长不得不宣布22点以后在全市进行宵禁,严重的骚乱还使得马里兰州的州长出动国民卫队来维持该市的秩序。,这也正如美国学者柯林斯所言:“在现代国家的日常生活中,国家宣称对暴力拥有垄断性的权力,其他人则应当‘保持和平’。国家机构工作人员也需要将获得授权的暴力保持在最低限度。但是这一理想情况常会被恐慌进攻中的微观情境互动所打破。随之而来的是自警察机构建立以来就一直存在于历史中的残暴行为。自1990年以来,这些行为开始被关注揭发,成为臭名昭著的丑闻”[3] 118。
虽然警察执法是一种代表国家行使公权力的职务行为,警察在特定情况下可以合法地对相对人使用强制措施,但在个案中,特别是警察在与相对人面对面的微观互动情境中,由于各种原因,可能会导致警察非法或不适当地对相对人使用某种强制措施,而相对人也会有意暴力抗法,或者因为某种误解而对执法的警察使用暴力进行攻击。由此,在警察与相对人之间就会爆发激烈的暴力冲突行为。
实践中,警察在执法活动中与相对人之间的冲突行为往往呈现高度的复杂性,警察与相对人在微观互动中各种特定的行为表现、心理及情感的变化等因素相互作用,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对警察执法中与相对人之间的冲突行为是否发生,以及如何发生等都会产生很大影响。本文将以微观社会学中的互动理论为研究视角,审视分析警察在执法活动中与相对人之间冲突行为互动的具体情境,并在此基础上,对警察执法活动中如何降低或避免出现冲突行为提出若干建议。
2 警察执法中的微观互动
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认为:“互动大致可以定义为当若干个体面对面在场时,彼此行为的交互影响。一次互动可以定义为一组给定的个体持续在场,他们从头至尾彼此间发生的一切互动。”[4]从微观层面来说,警察“执法本身是一种面对面互动,法律在互动过程中实现。互动双方的观念、情感、诉求、利益不可避免地对执法产生影响。”[5]警察在执法中与相对人之间面对面的互动,既包括语言上的互动,也包括行为上的互动。基于警察的特殊身份、权力与职责,以及个案中相对人的种种特殊情况,这种互动与其他社会互动形式存在明显差异,具有特定的表现。一般情况下,警察在执法中与其相对人之间的微观互动主要以冲突为主,特别是在与违法犯罪行为人的互动中,身体上的暴力冲突更是这种互动中最常见的表现形式。此外,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在警察与其相对人之间的互动中,基于警察维护社会秩序,以及保护公民的人身与财产安全等法定职责,大多数情况下警察都是互动的发起方,如主动对违法犯罪嫌疑人进行盘查、讯问,主动对正在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予以制止等。
2.1 警察在执法互动中的微观表现
警察的主要职责是维持社会秩序、打击违法犯罪、保护公民的人身与财产安全等。基于特殊的职责及工作中特有的危险性,法律赋予警察很大的权力,例如,在特定的危险情形下,警察甚至有当场击毙犯罪嫌疑人的权力。和其他的社会职业一样,警察会形成特定的职业思维及行为习惯,而这些都会在其执法时有意或无意地表现出来。就警察执法的具体情境而言,无论是执行危险任务的刑警,还是执行街头巡逻任务的巡警,或是在道路上维持交通秩序的交警,他们的日常执法工作都会不同程度地面临某种危险。因此,警察在执行任务时大都会出于职责的需要及自身特有的职业习惯,在其与相对人进行互动时表现出强硬的执法姿态,以及对执法现场强烈的控制欲望。例如,“当警察拦下路人询问时,他们会摆出控制对方的身体姿态;在非正式的搜身中,警察会随时准备缴下对方的武器,或是彻底压制住对方。即使没有这么做,警察们至少也会用更加微妙的方式获得控制权,例如咄咄逼人地盯住对方不放。”[3] 96警察执法过程中这些强硬的职业表现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这些强硬的职业表现可以有效地威慑违法犯罪嫌疑人;另一方面,这些表现在很多时候也会引起执法相对人心理上的恐惧、反感,甚至愤怒。双方互动中的这种不和谐或者尖锐对立的态度会进一步加剧彼此之间的冲突,从而可能会导致警察在执法中与其相对人之间发生更加激烈的暴力冲突行为。
2.2 执法互动中警察行为表现的成因分析
2.2.1 事实原因:警察执法活动的特点分析
2.1 治疗前后两组尿蛋白水平对比 治疗后两组尿蛋白水平均明显低于治疗前,而观察组尿蛋白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组间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1。
警察在执法时和相对人之间的行为互动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其他行为互动形式具有明显的不同。这种不同主要与警察执法活动自身的特点有关:①主动性。多数情况下,警察在执法时与相对人之间的互动主要源于以下一些事实,一是警察发现相对人正在实施违法犯罪行为而予以阻止,或者已经查实相对人实施了违法犯罪行为,并需要对其实施某些逮捕、拘留等刑事强制措施;二是警察怀疑某些相对人实施了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对其进行讯问或搜查等。无论在哪种情况下,警察出于履行职责的需要,都会主动对相对人发起执法互动,也就是说,警察是执法互动行为的发起方,具有执法的主动性。②即时性。在实践中,无论是一般的治安案件,还是重大的刑事案件,都有可能是突发性或即时性的,由此,警察的执法活动也具有即时性;而即时性反应是一种对行为人的综合素质要求较高的反应方式,也就是说,如果行为人的综合素质不高,其即时性反应的结果可能会十分糟糕。就警察的执法活动而言,如果执法警察自身的职业素质不高、执法经验较少的话,其处置突发性案件的能力就会比较低,即时性反应的结果就会不好。③正当性与合法性。警察的执法活动是其代表国家行使公权力的一种职务行为,这意味着警察的执法活动具有明显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这种行使职责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构成了警察执法中很多行为表现的巨大心理支持,而这种心理支持对其执法时的行为表现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使得警察在其相对人面前表现得十分强硬。
2.2.2 形式原因:“角色表演”的分析
“警察”不仅是一种职业和一份工作,还是一种社会身份和一种社会角色。“身份是指处于某种地位系统或地位模式中的一种位置,它通过交互的纽带及任职者所必须履行的权利和责任,同单位中的其他地位保持关系。角色由这样一种活动构成:如果任职者纯粹根据处于他这样地位的人所应遵守的规范来行事的话,那他就会置于这一活动之中。”[6] 71警察的社会身份正是这样,作为代表国家行使公权力、维护整个社会秩序和公民人身及财产安全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警察通过自身的一系列执法活动来履行自己的权利和责任,在整个社会管理系统中处于一种较为特殊的地位,与其他社会地位群体保持各种复杂的关系。
戈夫曼认为,“在扮演某一角色的过程中,个体必须努力使他在情境中传达出来的印象与实际赋予他的同角色相称的个人素质相一致。”[6] 74“当一个个体在特定地位上出现时,他就会成为其地位所允许和要求他成为的那种人,并且在角色扮演期间保持这种角色。表演者将试图做出与其身份一致的表演;他将感到不得不去控制和管理所作出的表演。”[6] 86-87众所周知,就警察这一职业所要求的个人素质来说,勇敢、强悍、不惧危险等一直都是基本要求,不但警察们自己这样认为,社会或公众也普遍对警察有这样的期待。警察所应具备的素质决定了其在执法过程中不能有丝毫的怯懦、畏缩或忍让,因此,他们必须要在执法中显得咄咄逼人,即使在一些不太危险的执法过程中,他们的“强硬”表现也不会有多大的折扣。警察在执法中对相对人的软弱或退缩往往被认为是对警察这一职业的亵渎,有辱自己作为一名警察的荣誉。此外,关于社会角色的“表演”,戈夫曼认为,“通过服饰和举止的身份暗示,任职者趋于被符号化,从而使卷入到某一情境中的人能够知道自己在跟什么人打交道。”[6] 73实际上,警察在执法过程中,正是通过警服及身上佩戴的武器或携带的警械,再加上威严的语气、强硬的态度、咄咄逼人的眼神等各种“符号”,使得其相对人知道他们是在和警察打交道,而警察的这些身体姿态、语言、眼神,以及警服、武器和警械等“符号”共同构成了其执法的特有表现形式,具有明显的仪式化象征。如果相对人在警察对其执法时不但不予配合,而且还表现出对执法警察的不屑或轻慢,甚至是侮辱或反抗,那么,相对人的这些表现不但会被警察认为是对其职业权威的冒犯,还会让警察自己觉得失去了“面子”,如果不做出相应的强硬反应,会被认为是警察这一职业身份的耻辱。例如,当警察在街头对一个他怀疑行窃的行人进行盘查时,如果该行人只是因为自己实际上并没有行窃而置警察的盘查于不顾并掉头转身就走,那么,这一行为首先就会让警察感到心理不快。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当他人正在说话时背过身去,这种姿态在绝大多数(也许是所有)社会里都表示漠视和轻蔑。”[7]因此,行人的这一举动会被警察认为是对自己的漠视和轻蔑。其次,更重要的是,这一行为还可能会加深警察对该行人的怀疑,并由此可能会进一步采取包括控制行人身体在内的其他强制措施,进而会导致执法活动中暴力冲突行为的产生。
2.2.3 本质原因:“权力仪式”的分析
从宏观上看,权力体现了一定的社会结构关系。韦伯认为,“权力是指一个行动者即使遇到反抗也能贯彻其意志的可能性,而不论这一可能性是建立在怎样的基础之上。”[8]从微观上看,警察在日常生活中对相对人的执法可以看作是一种“权力仪式”,也即一种“微观互动仪式”。柯林斯在分析人类的微观互动仪式时提出了有关“权力仪式”的理论,他认为在日常社会生活中,由于“个体所拥有的资源是不平等的,所以某些人发号施令而另一些人则惟命是从,或更常见的是主导直接的互动。”[9] 164因此,在权力行使的互动过程中,总是存在两方主体,一方是命令的发布者,另一方是命令的接受者。而基于双方社会地位或法律地位的不对等,这两方在互动过程中会经历或体验极其复杂的心理或情感变化。一方面,“命令的发布者通过在权力仪式中的支配作用而增强或维持了他们的情感能量,而他们的仪式态度是其自己忠于该组织的符号。他们的认识属于‘官方’类型。”[9] 165另一方面,“命令的接受者以另一种不同的方式参与这些仪式。这种被迫接受命令的情境本身就令人疏远。但是服从权威的人们通常又不能直接回避它……”[9] 165在命令发布与接受的过程中,命令发布者与接受者都会经历一个强烈的情感转换过程。“伴随命令发布者所要求的是一种尊敬的姿态……发布命令时如果缺少强制性,相应就会减少其有力的仪式效果……权力仪式产生了复杂的情感。命令发布者与命令接受者分享着支配/愤怒/恐惧/服从的混合情感。”[9] 165-167
上述柯林斯“权力仪式”理论的有关观点表明,人类微观互动行为中也体现了一定的宏观社会结构关系。众所周知,警察是代表国家行使合法暴力的权威机构,基于其职业的特殊性,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具有很大的权力。无论是在对普通公民的执法中,还是在对违法犯罪行为人的执法中,警察一般是命令发布者,而普通公民或违法犯罪人是命令接受者。在这样的互动中,无论是基于对自身职责还是对自己权力的有效行使,或是对于警察权威的合理维护和警察使命的高度信仰,作为命令发布者,警察都会在执法过程中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强制性或支配性,并要求普通公民或违法犯罪人尽可能或必须做到尊敬与服从,例如,警察在街头盘查时会要求被怀疑对象如实回答询问;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会要求其如实交代犯罪事实;在抓捕犯罪嫌疑人时会命令其不得反抗等。而对警察命令的接受者来说,由于其主体范围涉及不同类型的公民,因此,在与警察执法互动的特定场合中,特定的命令接受者基于自身的特殊情况会对警察的要求或命令作出不同的反应。例如,那些没有实施违法犯罪的普通公民在受到警察的怀疑而被盘问时可能会倍感愤怒;那些由于实施了违法犯罪行为而被抓现行的相对人或者会由于恐惧而对警察的命令表现得十分顺从,或者会试图强行逃离现场;那些实施了十分轻微的违法行为,或者是实施了某个事实上违法但自己却认为没有触犯法律的人,在受到警察的询问时会表现得十分不屑;那些实施了违法犯罪行为但是自认为警方没有证据的人会对警察的询问表现出假装的愤怒,或者是虚与委蛇地加以应付,等等。上述相对人的不同反应同样会相应地引起执法警察的不同应对,而无论是出于维护警察尊严还是履行特定职责的需要,很多时候,警察与相对人之间都会发生冲突行为。
此外,“警察是一个‘社会刺激多元化’的职业,即其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所受到的刺激非常广泛。他们既有社会普通人常遇到的刺激——来自个人生活或工作方面的挫折,如因工作无规律导致的恋爱或婚姻关系紧张,个人经济拮据,提职、升迁的机会有限,人际关系的冲突(如与上司或同事发生矛盾)等;又有由职业本身带来的社会刺激,如面临生死惊险,面临战友受伤、牺牲,大量地接触社会阴暗面,甚至违法者的贿赂、引诱和威胁等。”[10]这些各种各样的“社会刺激”都会对警察的心理、情绪等产生各种各样的消极影响,而这些消极影响在警察的执法活动中也会有所体现,对其执法活动中针对特定相对人的某些强制措施的不当行使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总之,身为社会秩序的守护者和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保护人,警察的职责会让他们在执法过程中不敢有丝毫懈怠。更重要的是,对某些警种如刑警或特警来说,他们所面对的总是特别危险的情境及非常危险的人,因此,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下工作,他们只得撕下温情的“面纱”,带上无情的“面具”。
2.3 警察执法活动中相对人的行为表现及原因分析
警察执法活动的相对人无疑是一个数量十分庞大、类型异常繁多的群体,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对其进行一个较为简单的分类,即主要分为事实上实施了违法犯罪行为的相对人,以及没有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相对人两大类型。第一种类型的相对人又可以分为其违法犯罪的事实和证据已被警方查证属实的相对人,以及被警方合理怀疑的相对人。第二种类型的相对人虽然事实上没有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但也可能因为各种原因遭到警方怀疑而被纳入到与警察执法的互动中,如被警方传讯或搜身及搜查住所等。在司法实践中,警察执法活动中的大多数相对人还是能够配合警察执法的,甚至许多罪行败露的犯罪嫌疑人在面临警察的抓捕时能主动束手就擒。但是,也有很多相对人,特别是那些没有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但却遭到警方怀疑的相对人,以及实施了轻微违法行为的相对人,他们在警察的执法活动中往往因为各种原因对警察的执法活动不予配合,甚至强烈抵制。一些警察执法活动中的冲突行为就是发生在警察与此类相对人的执法互动中。这类相对人对警察的执法活动不予配合,进行强烈抵制或反抗,主要以语言侮辱、肢体冲突等为主要表现形式。
相对人产生上述行为表现的成因有两方面:一是与相对人自身的性格及心理、法律意识、知识及认知水平等个人特点有关。在实践中,警察的执法相对人包括各种类型的人,这些不同类型的个体具有不同的性格特点、心理承受能力、法律意识、知识和认知水平等,因此,他们在与警察的执法互动中会有不同的表现。一般情况下,那些性格强悍、脾气暴躁、心理承受能力较差、法律意识淡薄,以及知识和认知水平较低的相对人更容易对警察的执法不予配合,尤其在其没有实施违法犯罪但被警察怀疑并要求接受调查,或者,只是实施了一些轻微违法犯罪但被警察予以处置的情况下,他们与执法警察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会更高。当然,在特定个案中的特殊情况下,那些性格脾气较好、心理承受能力较强、法律意识、知识和认知水平较高的相对人,也可能基于某种特定的原因对警察的执法不予配合或进行抵制,甚至是反抗。二是与警察执法活动不规范有很大关系。尽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等诸多法律的规范,但在司法实践中,仍有不少警察在执法中存在不规范的地方,警察执法中自身不规范的言行对那些事实上没有实施违法犯罪行为,而只是被警察怀疑的相对人来说尤其不能容忍,在这种执法互动中,双方之间也最容易发生暴力冲突。
3 警察在执法中与相对人之间的行为互动
3.1 警察在执法中与相对人行为互动的一般分析
一般情况下,警察在执法中与相对人之间的行为互动主要以冲突行为为主,既包括警察对相对人使用某种强制措施,也包括相对人对警察非法使用暴力。如果说警察执法活动是警察与其相对人之间的一种微观互动的话,那么,他们之间的冲突行为便是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互动内容,特别是在某些严重违法行为或是刑事案件中,警察与相对人之间发生暴力冲突行为更是一种普遍现象。实践中,警察在执法时对相对人使用某种强制措施可能会过当或是涉嫌违法,甚至会导致相对人受伤、致残或死亡的严重后果,因此,对警察执法中与相对人之间的暴力冲突行为进行研究,有助于警察执法中强制措施的合法行使,对维护警察与相对人双方的合法权益都有帮助。
基于警察执法活动的特殊性,以及警察与相对人在警察执法互动中不同的行为表现,警察与相对人之间的执法互动与日常生活中的其他互动形式具有明显的差异。从前述戈夫曼有关“社会表演”的观点来看,这种差异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警察在执法互动中的“表演”往往会因为相对人拒绝配合或者强力反抗而导致“表演失败”,也即戈夫曼所谓的“表演崩溃”。而一旦“表演崩溃”,无论对执法互动的现场,还是对执法警察个人及其背后的警察机构,其后果往往都十分不利。“就社会互动观点而言,可能中止于窘迫与混乱中,由有序的社会互动创造和维持的小社会系统变得紊乱无序。就社会结构的观点而言,表演崩溃可能导致一种更加深远的后果。每一次个体表演的常规程序,较大的社会单位都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表演者,不仅这些单位的合法性得到重新检验,而且这些单位的声誉存亡也与每次表演休戚与共。”[11]
从警察在执法活动中的“表演”来看,如果一旦发生“表演崩溃”,其影响外延较大。首先,执法现场会发生混乱,在现实中我们见证了太多警察执法现场混乱的场景:争吵、谩骂、推搡,甚至扭打等;警察执法现场的混乱既是“表演崩溃”的表征,又是其结果。其次,参与执法的警察在心理或情绪上会发生相应变化,他可能会感到其作为警察的权威受到了挑战,他会觉得“失去了面子”,并因此会变得愤怒。执法警察的这些情绪可能会导致事情向着更为糟糕的方向发展。最后,“表演崩溃”对警察机构也会产生不利影响,因为警察的执法不当可能会使得一起原本普通的治安案件转变为一起重大的刑事案件,这样的事情如果一再发生,警察机构的权威也会逐渐下降。
总之,虽然从理想的情况来看,如果在警察的每一次执法中,相对人都能够按照警察的命令或指示,完全服从警察的安排,如实回答所有讯问,诚实地交待所有问题,安静耐心地接受各种检查,那么,这将是异常完美的执法互动。但遗憾的是,在现实生活中,真实的警察执法现场却远不是这般理想图景:酒驾的司机在交警面前装疯卖傻、轻微违法行为人在治安警察面前撒泼耍赖、刑事犯罪嫌疑人对刑警的暴力反抗,等等,所有这些才是警察执法的真实场景。正是因为每一次具体的执法情境不同,而参与执法互动的警察与相对人具有不同性格及心理特点、不同生活经历和知识水平,更重要的是,执法互动的前提天然地具有矛盾与冲突的性质,所有这些都可能会导致警察在执法中与相对人之间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与冲突,而如果警察对执法现场处置不当,那么这些矛盾与冲突会就进一步演变为双方之间的暴力互动。
3.2 “恐慌进攻”:一个解释警察执法暴力行为的微观互动观点
国内外学界对警察执法活动中的暴力行为研究很多,但现有研究大都从宏观社会结构方面对警察执法中的暴力行为进行分析,例如,美国的一些学者主要从种族歧视的角度研究白人警察对黑人执法时使用暴力。而从警察与相对人之间的微观互动方面进行研究的较少,其中较为典型的是柯林斯关于暴力的微观互动研究,其在《暴力:一种微观社会学理论》中从行为人之间的微观互动情境出发,提出了关于暴力发生的“恐慌进攻”的理论。柯林斯认为,包括警察暴力在内的很多暴力行为中,“恐慌进攻”是一种当事人由于冲突情境中的紧张和恐惧而向对方发动的暴力进攻。如前所述,基于警察职责的特殊性,警察在执法时与相对人之间的互动天然地以矛盾与冲突为主,执法活动多数是在相对紧张的冲突情境下发生的。在这种特定情境下,警察与相对人双方都会产生紧张与恐惧的心理或情绪。特别是在某些特定的个案中,这种紧张与恐惧可能会更加强烈。例如,当警察抓捕犯罪嫌疑人时,无论警察还是犯罪嫌疑人都会感到紧张与恐惧:对犯罪嫌疑人来说,由于罪行败露及被抓捕后就可能面临的刑事处罚,其紧张与恐惧是必然的;对警察来说,由于犯罪嫌疑人可能激烈反抗或是逃跑,警察同样会感到紧张与恐惧。由于双方的这种紧张与恐惧,导致在面对面的执法互动中,双方的心理及情感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
柯林斯在分析出现在警察执法中的强制行为时认为,当警察与犯罪嫌疑人或其他公民对峙时,“首先是紧张感的累积,当条件允许时,这些紧张就会随着狂热的攻击动作被释放出来……这种紧张和恐惧是与他人发生直接冲突时所特有的情绪。当冲突双方彼此接近时,这种冲突性紧张便愈发强烈……市民的抵抗带来了冲突性紧张,进而使得警察可能同时采用正式权威和非正式压力来获得控制权。”[3] 95在分析“恐慌进攻”时,柯林斯特别强调冲突双方的心理与情感反应,“恐慌进攻的情绪无论包含什么,都具有两种特质。首先,这是一种炽热而高昂的情感,它的产生具有爆发性。其次,这种情绪具有节奏感和强烈的吸引力,能令人沉浸其中。处于恐慌进攻中的人们会不断重复攻击性的动作。”[3] 98正是这种高涨的情绪使得“恐慌进攻是一种无法组织的暴力。当人们从紧张进入恐慌进攻的情绪时,他们就已进入了一条无法回头的隧道,无力停止自己在当时当下的行动。恐慌进攻往往看起来带有几分残忍,因为那种情形很明显是不公平的:恃强凌弱;以多欺少;全副武装者对付手无寸铁者(或是已被解除武装者)。”[3] 99
此外,柯林斯还结合许多其他学者的个案研究,分析了“恐慌进攻”最容易发生的情形,“最为人所知的恐慌进攻事例都发生在群体之间,往往是一群人殴打落单的个体,或者是武装力量攻击手无寸铁或暂时失去武装的人。在场群体的规模越大(即人数越多),就越有可能发生恐慌进攻。因此,警察暴行的绝大多数例子(过度杀伤或长时间殴打),多发生在多名警察在场的情况下。警察暴力更常见于犯罪嫌疑人进行反抗,尤其是试图逃跑的时候。”[3] 132事实上,正如柯林斯所言,“没有暴力的个体,只有暴力的情境”[3] 2,尽管身负维护社会秩序及保护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等职责,但绝大多数情况下,警察并不会随意对其执法相对人使用暴力,正是特定个案中警察与相对人之间在微观互动情境中心理及情绪的剧烈变化,才更有可能导致警察在执法中的暴力行为发生。
4 警察执法活动中冲突行为的降低或避免
实际上,在警察的执法活动中,很多冲突其实是不可避免的,如制服正在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相对人、抓捕不肯束手就擒的犯罪嫌疑人等。但与此同时,警察执法活动中的很多冲突行为又是可以避免的,或者说其激烈程度是可以降低的。由于警察执法是警察与相对人之间的微观互动行为,因此,警察执法中冲突行为的降低或避免需要警察与相对人双方的共同努力。
4.1 相对人理性配合警察执法能有效避免或降低冲突行为
对那些实施了严重违法犯罪行为的相对人来说,接受法律制裁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任何拒绝接受或抵制、反抗警方合法处置的行为既是不明智的,也是非法的。但对很多无辜的普通人来说,在日常生活中,就像他们会突如其来地面临诸如火灾、交通事故、地震等异常危险的情境一样,有时候,他们也会因为某种原因而陷入与警察相互对峙的情势之中,例如,被警察怀疑与某起案件有关而突遭询问等;或者,对那些只是实施了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相对人来说,他们在接受警察执法时自认为警察的某些处置措施过于严厉或者根本没有必要。那么,在这些情况下,相对人该如何处理呢?
一般来说,对于一个其实并没有实施任何违法犯罪行为或只是实施了轻微违法犯罪的相对人来说,无论他是受到警察的合理怀疑还是受到警察的无端指控,当面临警察盘问,甚至被采取某种强制措施时,就觉得自己受到了委屈,并因此倍觉愤怒,从而对警察的盘查报以讽刺挖苦或肆意谩骂,或对警察采取的强制措施进行针锋相对的暴力反抗,那么,其结果往往只会对自己更加不利。因为这样做的后果只会进一步刺激警察,并极有可能会招致他们的“恐慌进攻”。正如美国警察执法所表现出的那样:“如果犯罪嫌疑人拒不配合,咆哮、挣扎、逃逸、试图掏出或已经掏出武器,为了保护自身安全和避免伤及无辜,警察有权使用武力或武器将犯罪嫌疑人制服。犯罪嫌疑人的态度决定了警察对他的态度。拒捕,无疑会招来警察更强悍的以暴制暴。犯罪嫌疑人挣扎越激烈,警察对他越暴力。”[12]实际上,公民应该了解到,很多时候,警察执法时的那些让人感到不快的言语或行为方式只是他们的一种职业习惯,或者只是他们一种有意或无意的“表演”。当然,这并不是说上述相对人在面临警察执法时,甚至受到某些警察的违法对待时,都要像待宰的羔羊一样,任凭警察处置。只是建议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要冷静应对、合法应付。正如柯林斯对我们的提醒一样:“你的任务是降低他们的冲突性紧张。如果你觉得有失尊严,请提醒自己,是你正在控制局面并让对方冷静下来。当在场警察的数量增加时,请格外小心这一问题。”[3] 478
4.2 警察规范执法能有效避免或降低冲突行为的发生
正如公民有很多理由认为警察在执法中可能会滥用权力一样,警察们也同样有很多理由认为其在执法中使用某种强制措施是正当与合法的。在传媒高度发达的今天,这种关于警察执法中采取某种强制措施正当性与合法性的争论甚嚣尘上,充斥于各种媒体。随着我国社会进入转型阶段,格局重塑,警察由于其自身与社会的全面贴合,在不涉及犯罪的治安领域,也容易与公民发生冲突[13]。在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的今天,关于警察在执法中实施强制措施是否正当与合法往往会也成为舆论场中激烈争论的焦点。每当出现一个社会热点案件,如近年来出现的“雷洋案”“徐纯合案”等,这样的激烈争论会在网络上持续很多天。那么,对警察来说,如何在执法中尽量降低甚至避免使用暴力呢?
事实上,美国学者在研究中发现,警察在执法中真正使用暴力手段的情况很少,而过度使用暴力的就更少。“为什么警察暴力很少见?因为大多数时候人们都会敬畏和服从警察,包括被捕时。当犯罪嫌疑人威胁、攻击警察(或警察如此认为)或尝试逃跑的时候,暴力最可能发生;如果人们辱骂警察或是拒绝服从命令,也有可能诱发暴力。最可能引发警察暴力的是身体上的抵抗。”[3] 395
实践中,警察在执法时要根据执法情景或者是相对人的具体情况,灵活选择不同的执法方式,也即警察执法应该遵循比例原则。警察在执法中遵循的“比例原则是指警察功能仅止于维持公共秩序必要的最低限度,其条件与状态,与秩序违反行为产生的障碍应成比例。”[15] 37例如,在对严重暴力犯罪行为人进行执法时,警察就应该采取震慑式执法,以自己的强硬言行对严重暴力犯罪嫌疑人进行有效震慑,以求获得执法的主动权,并力争取得最好的执法效果。相反,在日常生活情境中或是在对一般相对人即普通公民的执法中,警察就可以采取一些相对温和的执法方式,其执法时的言行不必过于强势。笔者认为,在很多情况下,从警察执法的目的来看,履行自己的职责,完成自己的执法任务是其执法的根本要求,而维护警察的权威或尊严只是其执法的形式要求(仪式要求)或心理需求。对任何一名理性的警察来说,完成自己的任务显然应该摆在首位。因此,警察在执法中,必须尽可能将自己的执法强制行为控制在最低限度以内,除非是相对人或犯罪嫌疑人具有身体上的激烈抵抗,否则,不要轻易使用强制力,因为这会激怒相对人或犯罪嫌疑人,甚至会引发双方之间的暴力互动,使得冲突陡然升级。须知,“警察权威的理想状态主要不是依靠外在面向的强制力,迫使被执法主体履行法定义务,而是依靠内在面向的被执法者尊重法律、尊重执法行为,即基于理由正当的信赖而服从。”[14] 127特别在一些普通的治安案件或者轻微刑事案件中的执法过程中,“警察权威实现的重要元素是‘认同’和‘服从’。‘认同’来自于对警察执法依据的实体性理由的认同和警察执法履行的执法程序合法、规范的认同。警察强制力的手段尽管有授权,然而不是必然使用,在用与不用的裁量空间之内,不用优先。”[14] 126总之,最为关键的是,警察在执法时一定要注意规范自己的执法行为,特别是在使用强制措施处置违法犯罪嫌疑人时,一定要根据有关法律的规定,严格遵循法定程序,这既是保护相对人,也是在保护自己。
个案中具体的微观互动情境、执法过程中警察与相对人双方的心理和情绪变化、紧张和恐惧等,是警察执法中与相对人之间暴力冲突行为得以发生的几个重要原因。对警察来说,这种激烈的暴力冲突行为可能会使得原本合法的或适当的强制措施变得非法或不当,进而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相对人来说,这种激烈的暴力冲突行为也可能会导致自己不必要的伤害,甚至是死亡的严重后果。因此,在警察的执法活动过程中,警察和相对人都要尽力避免紧张和恐惧,以免对双方造成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