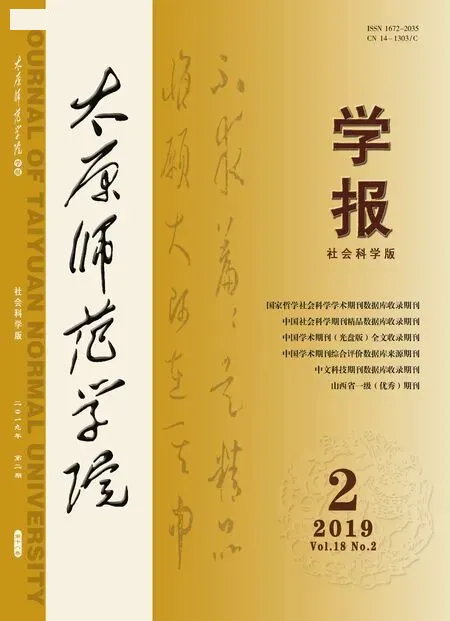论《无名印度人自传》的书写策略
潘 珊
(中国政法大学 人文学院, 北京 100088)
《无名印度人自传》(以下简称《自传》)是印度作家乔杜里的第一部自传,亦是他的成名作,创作于1947—1949年,1951年在英国得以出版,很快便被尊为同类作品之圭臬,成为“一部以自传形式撰写的极具历史价值的杰作”[1]177。作为一部印西文化激荡下的产物,这部自传无论从其书写策略还是从其传主的文化身份定位上都体现出了跨文化自传的典型特征。
自传作为一种文类,由来已久。然而,有不少传主作传之时,对于自传这一文体并无清晰认识,因此他们的自传或有名不副实之嫌。自传作为“舶来品”,对不少印度人而言,并未成体系地了解。比如印度“圣雄”甘地的自传就侧重自传之名,而写自我试验之实。正因为传主对于自传的认识千差万别,所以考察传主的书写策略及其对自传的认知就显得尤为重要,这既是了解其作传观的一大门径,亦是窥见其写作动机的一种方式。
《自传》自问世至今,常印不衰,成为传记文学世界的一名经典成员。[注]① 《自传》的英文原版于1951年由Macmillan出版社首发,到2003年先后出版了48版(参见http://www.worldcat.org/wcidentities/lccn-n78-78744,2010-03-15),这还不包括重印与加印以及其他语言译本的数量,足见其在英语图书市场的畅销。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莱辛(Doris Lessing)称它是“20世纪最伟大的一部书”[2]214。著名的印裔英国侨民作家拉什迪(Salman Rushdie)也指出:“尽管他(乔杜里)奋力抵抗时下的各种潮流,却没能阻止人们将《自传》视为杰作”[3]153。那么,这部自传的独特性何在呢?
乔杜里的《自传》,皇皇五百页,只涵盖其前二十四年的人生经历,可想而知乔杜里在自传中所述之细。在他事无巨细的回忆中,关于他人的传说、轶事与议论比传主自己的人生经历更为丰富。这是乔杜里与众不同的书写策略,而这部《自传》之奇、之新也恰在于此:它将个人经历与20世纪初印度民族的跌宕命运熔于一炉,名为自传,作者又申明是历史,那么它究竟是一部自传还是一部历史呢?
一、作传缘起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看看乔杜里自述的创作初衷。《汝之手,伟大的叛乱者!印度:1921—1952年》(以下简称《汝之手》)是年届90的乔杜里的一部晚年自述,也是《自传》的续作。其中有一节名为《自传缘起》,传主详细记录了他在不惑之年突然萌生作传念头的原因:
我扪心自问:与其对没能写成的史书而白白懊悔,为何不写下你所耳闻亲见的历史呢?这样也免去做研究之累。对此,我的回答也同样自然:我愿意。……在此我要多说一点,有一个愿望由来已久,那就是写一部描述我们在印度,特别是在孟加拉,在英国殖民统治后期的生活的自传,此类题材的作品尚无人做,但它有巨大的文化价值。不过我以为自己会先出版一部严肃的历史著作,之后再动笔,写这部自传,以作为那部专著之跋。我不认为有谁会对一个无名之人的自传感兴趣。后来这动笔的决定成就了《自传》,也使它成为我的第一部而不是最后一部著作。不过,我把全书的视角彻底改变了。它原本就是我没有条件书写的那部历史。[4]868-869
这番告白传递出两个重要信息:一是《自传》的内容并非作者的个人生活,而是他所处时代的生活记录;二是乔杜里的写作初衷本为撰史,这部自传乃是历史专著的替代品。这与他在《汝之手》前言中的一段话正相印证:“除了书(指《自传》)的标题,它并非真正的自传。它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图景。”[4]至此,乔杜里的写作初衷与他对《自传》的定性已了然纸上。
在乔杜里心中,写史书已然成为其挥之不去的情结,而这一情结在他早年求学之时就已种下。他自幼好读史书,进入大学后更是专修历史。但是,研究生资格考试的失利使他失去了继续深造的机会,他从此步入社会。学业的夭折成为乔杜里终生未解的心结。在《自传》中,他专辟一节,命名为《学术失败》(“academic failure”),以4页篇幅,详尽记述了此番经历。没能成为科班史家,成了乔杜里的终生憾事。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他饱读史书,并时时希望能出版一部史学专著,聊以自慰。进入天命之年,他回首前尘过往,立志不再蹉跎,决定以自传代替史书,了却平生之愿。然而,问题在于,乔杜里所言之自传与史书界限模糊。他也直言《自传》有名无实,顶着自传之名,写的其实是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印度社会史。他在《自传·前言》中并不讳言他写作的主要动机是“历史性的”,因此他所写的乃是以他“力所能达之至诚、至真的记录”,这一动因也与“希望此书能被视为对当代史的一大贡献”的宏大抱负交织在了一起。[5]乔杜里多次强调他所写的并非一般意义的传记而是历史,足见其写作初衷与立足点皆在撰史。诚然,自传作为一种个人的发展史,也是一种历史。自传与历史固然有不少相似之处,但其不同亦不可小觑。这两者虽都着眼于发展,然而它们在材料的利用、撰写的方式、对真实的理解等方面都存在差异。
二、史传之辨
要判断《自传》究竟是传记还是历史,我们可以先考察一下它的作者乔杜里在书写时采用了怎样的第一手材料。因为尽管史家与传记家有着不少相似之处,但是两者的一个主要区别就在于:史家写作时必须有第一手的史料作为依据,他要辨析材料,考证历史;而自传家对史料的依赖并非必须,因为他要写的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如果迫于环境和条件的限制,无奈之下,他是可以凭借记忆创作的,不必依赖史料。乔杜里在写作《自传》时,可谓煞费苦心。他的初衷是要写史,不过他坦言自己“既无日记、书信或笔记”帮忙,也没有“史书中的大事年表”作参照。[4]870很显然,乔杜里的历史创作缺乏史料依据,他凭的主要是记忆和写作的良心。当然,不可否认,有些人具有超乎凡人的“图像记忆”能力,可以过目成诵。乔杜里是否如此,我们不得而知。然而,即便我们假定他有此能力,那么在提供他所记忆的事实的同时,作为一名严谨的史学研究者,他也应该向读者提供相应的证据,以证实其所言非虚。遗憾的是,《自传》全书没有提供任何注释以佐证其所忆之事与所论之理。因此,就此点而言,他并非一位严格意义上的史学家,倒是一位自信、诚实的自传家。
那么,乔杜里对他的写作方式又是如何阐述的呢?他在《自传》序言中表明他的创作立场就“如同一架与地面保持联系的飞机”,“为了保持与地面的联系,它不能飞得太高,但是飞行又使它获得了比在地面更佳的观察视角”[5]。正因为这一贴近地面的视角,才使得他的观察角度不高不低,界限模糊,也就不成其为历史。另外,《自传》在结构编排上还照顾到“环境优于其产物”这一基本原则[5]3。有趣的是,乔杜里在《自传》的第一部分——“早期环境”中把英国单设一章,并将其与祖先的村庄和母亲的村庄并置在了一起。他的这一做法正说明他早年受英国文化的影响之深堪比其故乡。
历史与自传对真实性的理解不尽相同,乔杜里在《自传》中是这样对待“真实性”这一问题的:他试图在《自传》中将自己塑造成一位史家,而且,他也多次强调自己的史家身份。[5] vii,viii,127,258此外,他还在书中特别收录一篇自己早期的论文,名为《历史学中的客观方法》(“The Objective Method in History”),此文颇可见出其对治史方式所持的态度:
史家须满足于按事情发生的本来面目陈述事实,或者套用现代术语,要揭示一种发展过程,并避免在叙述中掺入自己的观点和偏好。史家的地位不应摆在他所记述的人中。他不与他们同喜悲或是介入到他们的事务之中。他的定位应该是一个旁观者,站在露台观察下面繁忙的街道。有两个词他是不该使用的,那就是“好的”和“坏的”。他可以谈较早的或是近前的发展历程,但不可过于绝对。他作为人的观点必须与他作为史家的立场相区分。事实必须自我辩护。[5]339-340
写作此文时,乔杜里还是“一名本科生”,“时值1918年1月”[5]337,不过佐以他在《自传》序言中的一番初衷陈述,他依然将其视为写作《自传》的指导纲领。需要指出的是,历史研究自20世纪中下叶业已在危机中进行反思和转向,尤其是随着后现代思潮的兴起,这一思潮的两位代表人物——海登·怀特(Hayden White)与史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先后于70年代和80年代强调历史文本中的文学元素,并以此挑战传统历史叙述的纯客观理想。[6]9,11因此,我们今天再审读乔杜里的治史理想不免觉其落伍。但是,作为19世纪末出生的学者,我们不该用今天的标准去苛求他,而应将他放到他所处的时代来审视他的思想,这样,从他的这番表述中反而可以见出他的卓尔不群之处。尤其是在当时的印度,当人们还普遍相信《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记录的是真实发生的事情时,他已在提倡科学客观的治史理念,这无疑是一大突破。
可惜的是,乔杜里未能在其《自传》中实现这一宏伟的构想,他并没有保持自己定下的“纯客观立场”,而是热衷于品评其所见之人、所经之事,而且往往以一种偏执的、自以为是的方式处之。米什拉为证明乔杜里的“伪史家”身份,举了如下一例:
印度教徒自认是至纯至高的血脉传承人,在这方面,纳粹不过是个新贵而已。具有这种意识和骄傲时,他若是碰到了一个不可接触者(Mlechccha),一个不洁的老外,肤色比他还浅,那他整个人都会出离愤怒。他内心深处的仇外心理就会被唤起,他遭到了不可容忍的羞辱。在这种无法遏抑的嫉妒与仇恨中,他选择毁掉这个外国佬的优越感,把他的肤色说成是最恶心的、折磨人的一种疾病,并以此来羞辱他。这个疯狂之人想通过幻觉来进行自我安慰,在他的假想中,要是有哪个外国人肤色比他浅,那他准是个白癜风患者。[5]124;[7]12
米什拉对此的解读是:“乔杜里将印度教徒对肤色的固有成见当作了历史事实。”[7]12这当然击中了乔杜里的软肋,因为他过于想当然地认为:所有印度人都将白种人等同于白癜风患者,但是事实上,这不过是少数印度人的偏见罢了。但是,他将成见与史实混同的错误尚不止于此,他还犯了一个“普遍化”的错误,即将个别人的观点和言论推而广之到一个族群的成见之上,从而易使读者误将个别认作一般,这犯了史家的大忌。试问印度教徒就都持此见吗?他们都仇外吗?显然不是,因为同为印度教徒、与乔杜里同时代的甘地与尼赫鲁显然就是例外。
在追溯印度人对英国人的偏见时,乔杜里采用了类似的解读方式,他回忆起曾教过他的一位老教师的话:“英国人都是一只母猴和魔鬼的后代。”[5]114他由此评论说:“我们对英国人的这种普遍态度是一种无理的、根深蒂固的胆怯,同时还是一种不理性的、无法克服的仇恨。”[5]114在此,乔杜里将那位老师的话当作印度人对英国人所持的普遍态度,但他却忽视了这一看法在传播中所受的地域与人群等因素的限制。首先,那位老师的话并非所有印度人都耳闻过;其次,听过此话的印度人也未必个个都认同。但是,乔杜里很巧妙地借老师之口道出他所需要的证据,他似乎是在从事实出发得出结论,而实际情况却是他从这一孤立的细节出发,再依靠自己的想象与演绎进行推论,得出了一个看似公允,实则失真、偏颇的结论,这种以偏概全的推论方法与他所谓的客观性的历史研究方法大相径庭。
《自传》中以偏概全的又一例证是他对英国人以及欧洲人对现代印度新文化所持的仇视态度的评判。他认为那些“所谓的欧洲人”通常会“无视现代印度的新文化,要是它们碰巧接触到了,会表现出比本土的孟加拉人更强的敌视态度”,但是乔杜里本人“从未与在加尔各答生活的英国社群接触”。[5]363在此,乔杜里既未亲自到在印度生活的英国社群中进行调查研究,也没有提供任何合理可信的证据,就断言这些英国人对现代印度新文化抱有仇视态度,这是否过于武断、偏颇?他在记述人、事、景物时也多次违背自己立下的不评断好坏的标准,屡屡表露好恶,臧否人物。比如在他初入加尔各答,站在此城一座高楼远眺时,他对这座城市的印象就包括了“一片由歪斜的砖块圈起的丑陋大海留下的建筑堤坝的清晰印记”。[5]260-261在此,“丑陋”这一含有贬义色彩的评判词与他此前强调的史家所应避讳之“好”“坏”等词同属一类,真可谓自相矛盾。事实上,在《自传》中,类似上述的例子不胜枚举,而这些例证非但没能支撑他的史家地位,反而瓦解了他此前所声称的“纯客观立场”。
三、写传策略
乔杜里的史家身份已告破灭,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名合格且出众的自传家。《自传》从内容、形式到写作方法无不与其标题切合。此书的核心是个人的成长经历与生存环境,所以他将祖先的村落和自己接受高等教育的学府所在地加尔各答都一一列入目录。[5]xi-xii这部自传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其叙述并未遵从传统自传所采用的时间顺序,而是以地点为线,与乔杜里所持“环境优于其产物”[5]3暗合。
乔杜里在《自传》中所采用的写作方法也确立了他作为自传家的地位。在《自传》中,如他所述,他并未参阅多少史料,而是全凭记忆,更重要的是他得以依靠记忆“创作出那些地点和事件的精神与环境”[4]870。正因如此,他笔下的人物、事件和景物的描述总是充满了个人感情与价值取向。比如他在描述自己的出生地时就特别强调此地是他日后“城市生活的道德旨归”[5]4。虽然他的记录和评述常常有失偏颇,但是,他至少表露了其内心最真实的感触,这种真性情的流露表明他的创作更依赖于“心灵的证据”,而这正是传记文学所特有的“传记事实”。[8]12除了全书俯拾即是的“心灵的证据”之外,乔杜里的《自传》在形式上也自成一格,不同凡响。这部出版于1951年的自传在形式上正体现了后殖民时期自传文学的文体转向,即文学体裁的杂糅。殖民时期那种在传统历史观念统摄下一以贯之的时间顺序模式已经日渐被后殖民时期解构与戏谑历史的观念下多种文体杂糅的模式所取代。同为英国移民三大家的奈保尔和拉什迪等众多后殖民作家的作品都体现了这种文体杂糅的特征,它与后殖民研究去中心化的初衷一脉相承。
乔杜里在出版《自传》之前,一直生活在印度,从未踏出过国门。然而,他的自传中对于印度以外的文明,尤其是欧洲文化的论述俯拾即是。乔杜里对印欧文化的态度亲疏有别,这与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尤其是文化方面的英语教育直接关联。而他在对各种文化评头论足之时,也流露出他对自我身份的文化定位。因此,研究乔杜里在自传中对于欧洲文明的态度,也是对他的自我身份认同的考察。同时,探究一位土生土长的印度作家对于欧洲文化的认知态度和他在不同文化中的自我身份定位也是一种跨文化的具体实践。印裔英国作家奈保尔曾评价乔杜里的《自传》是“印英遭遇中产生的一部伟大的书”[9]59,我们姑且不论这一判断是否夸张,他的这一论断倒是如实点出了这部自传的核心,即“印英遭遇”,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印西文化的冲撞。乔杜里在《自传》中对东西文化都有涉猎,但他在对不同文化大发议论之时,我们也可以从中见出他的文化身份定位。
乔杜里在自传中呈现东西文化的方式有其独到之处。他不仅在讲述自己的印度生活时常常以英国为参照,在对某种现象进行评议时也将各种文化罗列出来,而且每谈及一种,就势必将其与另一种文化进行比较,并评判其优劣。乔杜里在回忆自己的童年生活时曾经讲述了这样一段往事:
宠物在我的幼年生活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总是养一些鸟或是其他动物。……不过我在这里要特别讲的是我七岁左右养的一只母羊。我越是看小西屋里的“少年耶稣”那幅画,就越想养一头羔羊,那时这成了我在此世最强烈的愿望。然而,在我们这个地区,羊并不常见,要弄到一头羔羊更是绝非易事。我父亲问了好多人,终于有一天,我得到了一只小母羊。它虽然不是羔羊,可是我却异常喜欢它。我把书本撇到一边,总是喂它吃草,或是与它一起坐在草地上或是树底下。小母羊也非常喜欢我,以致于后来只要我离开它几分钟,它就开始凄惨地咩咩叫起来。要是我吃饭的时候听到了它的叫声,我就会放下饭碗,跑去找它。我身上开始有了羊一般的气味儿。
起初所有人都对我的举动十分钦佩。他们说我看起来就像是那幅画中的少年耶稣。[5]357
乔杜里在讲述自己与宠物的故事时,特别描写了他所格外喜爱的一只小母羊,而且明确指出他的喜爱源于家中一幅耶稣与羔羊的画。因此,他对羊的喜爱,并非出自他对这种动物的偏爱,而是因为羊或更确切地说是羔羊,代表了基督教中最为人耳熟能详的意象,即耶稣的化身。乔杜里在讲述中明显地套用了圣经中的这一意象,而且借家人之口将自己比作耶稣。因此,乔杜里养羊,与其说是表现了他对羊的喜爱,倒不如说是表露了他对家中那幅圣经画的喜爱,而他对那幅油画的喜爱也体现出他对那幅画所代表的基督教文明的偏爱。同时,乔杜里对渴望拥有与画中一样的羔羊的迫切心情,也折射出他对基督教文明的急切认同。乔杜里对于基督教文明的认同也映衬出他对以此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认同,这一认同使得他在讲述故事和品评人物时,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西方文化为准绳。
如果说乔杜里的养羊事件因为引入了耶稣与羊羔的典故而具有了浓郁的基督教文明色彩,那么在他对一些现象进行评论时,他的参照标准依然是西方式的。在乔杜里讲述毕业后走入社会的经历之前,他曾提到印度的社会对于年轻人的教诲:
印度社会不会教它的年轻人去勇敢地面对生活。“生活的勇气”这一词组对于一个印度人而言是不可理解的,他们将出生的第一次啼哭视作存在的主旨,在此后的人生中成功地过上一种假海龟[注]乔杜里饱读诗书,极爱用典。假海龟(mock-turtle)的比喻来自卡罗尔的《爱丽丝梦游仙境》(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1865),卡罗在此书中虚构了假海龟这一角色,它本来活得很好,却总是故作忧郁。似的生活。……我们看到老人们,不论男女,都把头支在手上,思考的不仅是他们自己的愁苦,还有他们盼着降生的孩子们的忧愁。[5]357
我们在乔杜里的笔下看到的是印度社会人们意志消沉的状态,他对印度社会的这番评论,显然过于武断。但我们在此关注的是他的评论方式,他在下判断时引入的是一个西方的概念“生活的勇气”,并以此为参照准绳,指出它在印度社会不被人理解。进而,他又继续引申,指出印度人整日愁眉苦脸,并将这种状态与英国作家路易斯·卡罗(Lewis Carroll)笔下故作忧郁的“假海龟”一角相提并论。至此,乔杜里的评价标准和他的判断倾向都已明了,他以西方社会的“生活的勇气”为评判标准,并站在这一立场讽刺挖苦印度社会人们意志的消沉,至此他亲英贬印的态度已跃然纸上。乔杜里的这一态度更是清晰地表明:在衡量自我文化身份的天平上,他明显地倒向西方文明一边。
四、文化身份
乔杜里的文化身份导向性十分明显,这集中体现在他对印度文化与印度人、西方文化和西方人(尤其是英国文化与英国人)的褒贬评论上。乔杜里对于印度人和印度文化有着非同一般的成见与鄙夷,这一点在他的《自传》中随处可见。比如他批评印度人对于星象的迷信时曾说:
占星带给生活的担忧和麻烦简直罗列不尽。它把每个人的问题,包括职业的选择、婚姻与旅行,疾病的治疗,都扯到不相干的地方去,结果把每种理性的处理方式都给搅乱了。[5]131
确实,对于星象的迷信在印度十分普遍。另一位印度英语作家纳拉扬(R.K. Narayan)也在他的小说《英语教师》(TheEnglishTeacher, 1945)和自传《我的光阴》(MyDays,1974)中对此有大篇幅的描写。但纳拉扬的描写是就事论事,尽量保持公正平和的心态。相比之下,乔杜里对待同一问题的态度就显得夸大和主观得多。他的夸大体现在他将印度大多数人对占星的迷信扩大为整个印度人群的症候,并将占星术看得一无是处。乔杜里所忽略的是,占星术不光在印度流行,在中国和欧洲也由来已久,且风靡至今。
占星术固然有其迷信的一面,但天文学这一现代科学也对其多有借鉴,这证明它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乔杜里对占星术的看法存在偏颇,他的评判依据是西方科学,但他却忽视了西方天文学的鼻祖正是占星术。在评论此事时,他的语气也充满嘲讽。“罗列不尽”“不相干”和“搅乱”是他形容占星术时使用的词汇,在这三个词中,后两个都为贬义。“罗列不尽”虽是中性词,但它所限定的是“担忧”和“麻烦”这两个贬义词,它也因此被染上了负面色彩。短短两句话中,他一连用了三个贬义词,不仅增加了否定的意味,也加重了语气,夸大了事实,他的判断也因此具有了嘲讽性。
与对占星术的否定相类似,乔杜里对印度人的做事态度也颇有微词。他如是说道:
印度人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他要么这样考虑,要么就想的与之截然相反,这正如一位孟加拉语批评家所言,一个印地语诗人能够在色情文学与禁欲文学之间轻松转换,由此,要一个印度人在不同事物之间取得平衡,并样样干好,就好比要他放松对这些不同事物的专注程度,其结果就是他哪一样都徒劳无获。他既缺乏活力也没有由此激发出的意志来均衡分配任务。他只能被冲动和情感支配,并对此习以为常,结果就丧失了干劲儿。[5]212-213
乔杜里对印度人的判语有失公允,他对印度人的做事态度下了如此宏大的判断,那么在印度莫非人人都是如此?其实不然。乔杜里是在以偏概全,他下此评判的潜台词是崇尚西方人对做事效率的追求,他的判断标准依然是西方化的。耐人寻味的是,乔杜里评论此事时所使用的绝对口吻,与他所批评的那些“从一个极端摆向另一个极端”的印度人如出一辙。在他笔下,印度人的做事态度非黑即白,这显示出他评判的武断;更令人匪夷所思之处在于,当乔杜里将自己摆在旁观者的位置时,难道他忘了自己的印度人身份吗?他将自我置身事外,评论时又语带夸张、讽刺,这表明他对自我的定位高于他所批评的这些印度人。乔杜里自视优越在他研究印度发展史的文章中表露得更为明显:
恐怕在这个问题上,我的假设与我同胞们的相去甚远。……就印度历史而言,我与我的同胞们所使用的理论之不同就如同哥白尼与在他之前的人看待地球的观点那般南辕北辙:如果我的理论是以太阳为中心的,那么我的同胞们的理论则是以自我为中心的。[5]456
乔杜里特意将此文附在《自传》末尾,强调他的自传“与其说是个人的历史,不如说是一个民族的历史”[5]456,可见他对这篇有关印度发展史的散文之重视。他在文中开门见山,指责印度历史学者的通病——自我中心化,对自己的理论他则自命客观,即如哥白尼的日心说一般。结果,他后文的叙述情绪化十足,他说:“印度的历史就像是喜马拉雅山的地势,广大而不复杂。”[5]457这与他前文所自夸的客观性毫不对等,最终落入了自设的批判陷阱之中。
五、亲西情结
不论是品评印度的占星术,还是嘲讽印度人的做事态度,抑或是贬低印度的历史学者,乔杜里都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评论西方文明与西方文化时的态度。
他自幼受家庭熏陶,喜读西方文化之书,并很早就对其心向往之。乔杜里在《自传》中谈及西方文化之处数不胜数,他旁征博引,以示其对西方文化了解之深,这也体现出他的文化传统是以西方为本位的。在乔杜里的《自传》中,他将英国置于与他的出生地、祖先的故乡与母亲的家乡同等的位置上,借此彰显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对他的幼年影响之深。为了表现自己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他不仅将自幼就烂熟于胸的西方名人一一列出,包括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拿破仑(Napoleon)、莎士比亚(Shakespeare)、拉斐尔(Raphael)等,还对其中一些人物作了格外点评,以溢美之词表达他对这些伟人的崇敬,展现出乔杜里在文化上的西方渊源。
除了这些西方的著名人物之外,乔杜里还在《自传》中不时提及他所阅读的西方书目,以及这些书籍带给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其中最典型的一部书莫过于《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了。对于此书,乔杜里是这样回忆的:
1911年印度发生的最重大事件莫过于“德里朝觐”(Delhi Durbar)[注]“德里朝觐”是指1911年,为庆祝刚刚登基的大英帝国国王乔治五世(King George V)莅临英属印度的首都德里,上百个土邦和藩王们全部前往首都新德里朝觐。此事在当时的印度以及大英帝国都是史无前例之事,因此声势浩大,史称“德里朝觐”。了,不过对我来说,最难忘的事要数我第一次看到新发行的第十一版《不列颠百科全书》。在吉绍尔甘杰(Kashorganj),我们得知,最大的英语词典是韦氏词典(Webster),那里的人要想强调一本书的尺寸和重量就会说:“和韦氏词典那样大”。从那以后,我们又听到了传言,说有一本比韦氏词典更大的词典,名字叫《不列颠反百科全书》(Anti-cyclopaedia Britannica)。这个错误要归咎于那场民族主义运动,它教人们反对而不是赞成任何事,也让人们以为反对某事是固有的美德。到加尔各答之后,我们才得知那部书的正确名称和它的真正性质。在学校里,我们甚至看到了一套第十版,只不过它被锁在了柜子里。我们真正对《不列颠百科全书》有所了解是在1911年10月,我的一位堂兄是高等法院的律师,他在第十一版刚问世时就买了一套,之后他就出城度年假去了,这套书被暂存在我家有两个月之久。我们本不该把书从函盒里拿出来,但是我们这样做了,虽然心存愧疚,一开始,书的芳香就使我们意识到它不同凡响。书的样式更是让我们深受震撼。我打开其中一册,忍不住低语道:“这纸是多么细腻洁白,又是多么轻薄啊!”[5]292
乔杜里对《不列颠百科全书》的描述有两页篇幅,在这段引文中,他从耳闻到亲见,再到将其捧于手中摩挲,我们由此可窥见他对此书的珍视。他将与这部百科全书的相遇与“德里朝觐”相提并论,既体现了百科全书对他之重要,也暗示这两者存在着相似之处。在他看来,“德里朝觐”是英国对印度的政治施恩,而初读百科全书则是英国对他的文化启蒙。如果说“德里朝觐”是一种政治殖民,那么乔杜里与百科全书的相遇就是一种自我的文化殖民。在《东方学》一书中,萨义德曾对在一战与20世纪60年代初这段时期的东方主义者写作的三种主要形式作了概括,其中就有百科全书这种形式。[10]284百科全书包罗万象,但他的编写者也包括东方学家,因此它所构筑的是一个完整的大英帝国的学术殖民体系。乔杜里在提及百科全书的名称时,还不忘嘲讽印度民族主义运动,指责这场运动使他把此书的名称弄错。他如此抬高一部英国的百科全书,并为此讽刺印度的政治运动,未免有向英语世界的读者献媚之嫌。乔杜里在《自传》中如此浓墨重彩地描绘他与百科全书的相遇,体现出他已自愿臣服于大英帝国的百科全书。无论是献媚还是臣服,乔杜里对此书的热爱都呼之欲出。更重要的是,他对百科全书的追捧折射出他对自我文化传统的定位。他已经视自己为西方文化之子,这部细大不捐的百科全书正是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的典范之作,它以西方的视角对世界万象进行重新梳理,整合成一套百科全书似的体系,并以书的形式将这一意识形态传递给读者。
乔杜里对于西方文化的承袭远胜于印度文化,对此他并不讳言:
奇怪的是,我们对希腊文明的了解要远胜于伊斯兰文明。在吉绍尔甘杰,我和我哥哥开始接触希腊文化,现代欧洲也开始了解希腊艺术,即拉奥孔(Laocoön)与“观景阁的阿波罗”(Apollo Belvedere)。虽然我们那时还没听说过莱辛(Lessing),但是我们对印在一本孟加拉语杂志上的灰色调的拉奥孔群雕图还是留下了极深的印象。[5]193
这段往事的发生地是吉绍尔甘杰,它当时还是英属印度的一个省,居民以穆斯林教徒为主。乔杜里在这里度过了最宝贵的童年时光,但他对自己身边的穆斯林文化之了解远比不上对遥远的古希腊文明的了解,这恰恰说明了西方文明对他的影响之早和感染之深。
无论是《不列颠百科全书》带给乔杜里的震撼,还是杂志上希腊雕塑对他的熏陶,以及不可胜数的西方文学作品给他的启蒙,这些都促使乔杜里将自我定位于西方文化传统之中。如果说英国对印度的政治殖民以失败告终,那么它对像乔杜里这样的印度人的文化殖民称得上是根深蒂固。乔杜里写作《自传》时已近天命之年,如果说他在青少年时期还是无意识地接受英国的文化殖民,那么此时的他已进入到了自我殖民的状态之中。他以西方文化为本,对印度人与印度文明充满排斥和嘲讽,对西方文明却极力推崇和仿效。他的这种自我殖民的心态在他第一次亲赴欧洲之时更是显露得淋漓尽致。
在印度度过近半生的乔杜里终于第一次踏出国门,前往他所心向往之的欧洲。他将在英国和巴黎、罗马等地的见闻一一记录下来,随后以《英国之行》(APassagetoEngland,1959)为题出版。在此书开篇,他心潮澎湃地讲述道:
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我看到了数不胜数的绘画、雕塑和其他艺术品,不计其数的戏剧、壮美的建筑和花园,与美丽的风景;聆听了不知凡几的诗歌与音乐;吃得更棒,喝得更多;总之,与我生命中的其他时刻相比,这段经历要兴奋和有趣得多。同等重要的是,我所经历的这一切都是我自孩提时代起就一直憧憬的。[11]1
在这段话中,乔杜里有意无意地将自己在欧洲的所见所闻与在印度的近半生经历进行对比,对他而言,这次欧洲之行是一场文化盛宴,让他的精神食欲大增,也使他童年就有的愿望得到满足。他对这番经历的溢美可被视为是一次文化与精神上的还乡之旅,因为自幼就受欧风欧雨熏习的他,早已将欧洲文明视作自己的文化之根。自童年就浸润在西方文化传统之中的乔杜里,在长大成人后已完全认同于欧洲文明,甚至将自己的文化身份也定位于此。这一点,在《英国之行》的结尾可见一斑。当乔杜里告别英国,准备登机时,他遇到一位似乎对他颇感兴趣的英国乘客。他将与这位英国同行者的邂逅作为此书的结尾,他是这样记录这次偶遇的:
当我们在候机厅等待登机时,他(指那位英国人)走上前来,自我介绍说:他在加尔各答经商多年。当我告诉他我是孟加拉人时,他说从没见过一个像我这样的孟加拉人。随后,他转向一旁的空姐,说道:“他怎么看着这么兴奋?”我用英国式的做作回答道:“这没什么,我不过是用你的国家和法国的资助度了个假!”他们都开怀大笑。掩饰是没用的,我的快乐发自肺腑。[11]128
乔杜里的英国之行以此告结,暗含深意。他借这位英国人之口,道出自己已与一般孟加拉人的不同之处。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是他的英国文化素养,从中也可见出他对欧洲文化的深刻认同。他回答这位英国人的问题时,带着“英国式的做作”,他对英国人的模仿正如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所言,是一种“殖民式的模仿”(colonialmimicry),“是对被改造的和可识别的他者的渴望”。[12]122乔杜里在这一模仿的过程中逐渐将自己的文化之根移植于西方文明之上,他的文化身份也随之确立。
六、结论
乔杜里的文化身份认知表明:“身份问题从来不是对既定身份的确认,也从不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它总是一种身份图像的产物,以及确立这一图像的主体转变。”[12]64乔杜里的既定文化身份本该是印度文明,然而他在幼年与成年后都耳濡目染于西方文明之中,因此他的文化身份图像是西方文明的图景,他的文化身份构建也依此图景而进行主体转变。乔杜里近半生未离印度一步,然而,在他的成长环境中,他得以沉浸在西方文明之中,并对其极为推崇,这一点从他对周遭事物的品评所采用的标准,以及他对印度与西方的人与事的议论中都可以见出。乔杜里的文化身份认同植根于英国殖民统治中的文化殖民,这一身份确立的过程也经历了由无意识的被动接受到有意识的自我殖民的过渡。
作为印度英语传记中的一部佳作,乔杜里的《自传》乃是印英文化碰撞下的产物。乔杜里在《自传》中讲述的不光是有关自我的故事,作为一位在印度出生,又在英国殖民后期和印度独立前夕成长起来的作家,他试图将自我的内在矛盾投射于整个印度社会的冲突之中。[13]11乔杜里自我的内在矛盾正是东西方文化冲撞的体现,作为一位饱读印度与欧洲诗书的作家,他身上体现的文化困惑与冲突也正是他的跨文化身份的独特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