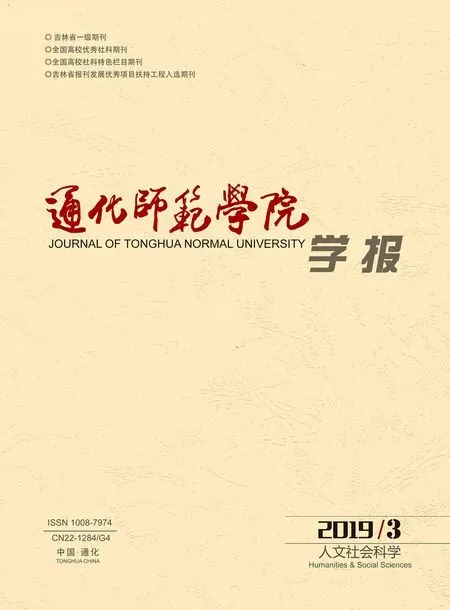中西方戏剧治疗研究现状及发展前景
吴宗会,许文胜,徐亚楠
现代社会科技在发展,物质文明日益丰富,人类精神世界却不断受到现代文明发展带来的巨大冲击,本体不断异化,精神生存空间不断遭受挤压,引发一系列精神和心理疾病,导致生存危机。戏剧独特的情感宣泄功能为人类追寻和谐精神家园提供理想场所。面临各类精神危机,戏剧治疗学作为一门学科应运而生。戏剧涵备的治疗因子如戏剧性游戏、情景演出、角色扮演、演出高峰和戏剧性仪式与戏剧治疗衍生交集。
一、现代西方戏剧治疗学研究现状
就戏剧治疗体系化程度而言,当前走在研究前沿的国家为美国、英国、德国、以色列、罗马尼亚等国。其中,英国、美国和以色列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最为透彻,临床医学实践最为深入。
早在中世纪欧洲的某些教堂里,人类已经开始尝试将戏剧剧本与宗教故事结合起来,治疗、舒缓和安抚普通大众疲惫的心理和受苦的心灵。尽管戏剧具有治疗心理疾病之功效,但是将戏剧与现代医学治疗结合起来作为交叉学科进行研究则起步较晚,相关的专业研究历史也较短,关于戏剧治疗的研究成果在西方文艺领域和医疗机构也是凤毛麟角。戏剧治疗最早的研究成果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距今不过短短四十多年历史。在西方,“戏剧治疗”概念在20世纪才开始登上历史舞台。20世纪20年代莫雷诺(Jacob Levy Moreno)在纽约创立了心理剧治疗剧场。40年代初,心理剧治疗手段日益成熟,开始广泛应用于学校、医院、军队以及公司管理机构。
玛丽安·林德韦斯特作为第一代英国戏剧治疗师,为建立戏剧治疗学科作出了相应贡献。戏剧治疗师协会在英国和美国分别于1976年和1979年成立,先驱人物包括格鲁德·斯坎特纳、罗门·高登、大卫·约翰逊、罗伯特·兰迪以及蕾妮·伊姆娜。他们分别从心理治疗、“监狱剧场”、戏剧和舞蹈治疗、行动心理治疗和戏剧治疗五阶段推动了戏剧治疗研究。1980年,理查·谢克纳在纽约大学开设具有戏剧治疗特色的人类表演学课程,招收相关专业人才并进行专业培训。自此以后,戏剧治疗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和前沿研究,迅速由英国和美国扩展到加拿大、欧洲、南美洲、澳大利亚、以色列及日本。
将戏剧表演艺术与医学治疗技术结合起来,研究戏剧艺术对于现代医疗的实践作用,从戏剧治疗术角度分析文学艺术的社会价值值得关注。70年代以来,以蕾妮·伊姆娜、罗伯特·兰迪和菲尔·琼斯等为先驱,西方涌现出一批戏剧治疗顶级大师。美国戏剧治疗先驱伊姆娜在其成名之作《从换幕到真实:戏剧治疗的历程、技巧与演出》一书中提出著名的戏剧治疗五阶段理论,即:戏剧性游戏、情景演出、角色扮演、演出高峰与戏剧性仪式。她认为,戏剧治疗为情绪发泄提供出口,映照自我瑕疵,拓展社交角色,提高自我形象,实现心理健康。不仅如此,伊姆娜还将戏剧治疗研究引入精神病院等精神治疗场所,以精神病人或其他心理不健康人士为研究对象,通过戏剧演出的方式来阐释戏剧艺术的治疗作用。[1]英国戏剧治疗师珍妮斯从创造性/表达性模式、学习性模式及治疗性模式三个模式方面研究戏剧治疗的社会效用,焦点放在人类心理潜意识问题之上。
美国戏剧治疗大师罗伯特·兰迪是西方戏剧治疗界的领袖级人物,有超过35年戏剧临床治疗经验。他在《躺椅和舞台:心理治疗中的语言和行动》一书中深入分析了行动心理治疗以及其在医院临床疾病上的应用。[2]病人通过角色扮演行动,以戏剧化的情节深入剖析内在自我,发展转化自我的心理自发性和创造性。梳理了行动心理戏剧治疗的历史脉络,从莫雷诺与心理剧、皮尔斯与完型治疗、乔治·凯利与固定角色治疗、行为排练与多功能治疗、亚历山大·罗文与生物能分析等方面研究了戏剧治疗的历史和当代特色。兰迪认为,各种剧场,如社会剧、圣经剧和回放剧场,从不同视角促进临床疾病治疗。兰迪在其扛鼎之作《戏剧治疗:概念、理论与实务》中从戏剧治疗的流派、戏剧治疗训练、戏剧治疗的概念与理论、戏剧治疗的对象和场合等角度阐释了戏剧治疗的来龙去脉,以戏剧治疗师立场详细讲解了戏剧治疗的具体技术操作,从临床技术角度揭示了“戏剧到底如何治疗病人”这个最为关键性的议题。[3]他在理论性模式、研究方法论、数据分析、方法论再思考等方面前瞻性地指出戏剧治疗作为一门独立学派确立了其学科地位,以及当前戏剧治疗研究的热点和未来研究方向。
英国著名戏剧治疗大师菲尔·琼斯从戏剧治疗的历史,圆形剧场和现代医院剧场角度研究戏剧治疗的形式与格式。琼斯在其著作《戏剧治疗》中指出,戏剧治疗涉及关键的九个核心治疗性因子:戏剧化投射,治疗性扮演过程,戏剧治疗中的同理与距离,拟人化与模仿,观众互动和见证,戏剧化身体,游戏、生活与戏剧之关联以及转变,将现代数据引用到戏剧治疗的临床实践之中。[4]数据评估与戏剧治疗密不可分,诸多其他学科的评估与评量方法可以被借鉴到戏剧治疗临床领域。琼斯是从数据评估角度研究戏剧治疗的先驱者。
近年来,通过罗伯特·兰迪等戏剧治疗界先驱者们的开拓,戏剧治疗艺术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俄罗斯戏剧艺术家尼古拉斯·叶夫列伊诺夫和弗拉德米尔·艾京,巴西戏剧艺术家奥古斯都·伯奥等对戏剧治疗的专业性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桥梁作用。英国的戏剧治疗师史雷德为儿童教育戏剧作出巨大贡献。
戏剧治疗在国外的临床发展和理论研究远远早于中国,各种理论体系和实证研究相对完善。为了较完整地综述戏剧治疗研究,本研究选取了较多国外研究文献,进行分类整理。其中,针对研究目的这一层面,国外的研究与国内大致相同,主要分为医院病人的辅助性戏剧治疗、在校学生心理问题疏导和成年人的精神压力的排遣。在第一类——医院病人的辅助性戏剧治疗中,部分案例针对精神病人,也有一部分案例针对其他类型病症,但都是运用戏剧疗法进行辅助治疗。迈克·雷斯曼(Michael D.Reisman)基于戏剧治疗运用于精神分裂症案例,探讨治疗中公正的可能性,建构对待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权利模型,探索发展转型的戏剧治疗技巧。作者将主要寻求症状控制的精神分裂治疗的核心医学模型与关注给予病人权利的精神分裂治疗的新兴康复模型对比。[5]在第二类——在校学生心理问题疏导方面,乔纳森·巴内斯(Jonathan Barnes)的研究最为典型。他的戏剧治疗研究聚焦于针对六至七岁儿童的交流困难,运用戏剧治疗提高参与的孩子的流利度、词汇量、创新性和集中度。并且在研究中,主动性和自信心也有积极的发展。[6]研究目的中的第三类为成年人的精神压力的排遣,暂时发现的研究较少,仅有两篇论文,如余瓦尔·帕吉(Yuval Palgib)的研究成果《舞台生命的十字路口:针对老年人的生命回顾与戏剧治疗之结合》,运用“回顾生命”的戏剧治疗方式,结果表明在自我接受、人际关系、感知生活意义、觉察健康衰老和压抑症状方面治疗的有效性在时间与组员间的相互作用。[7]
就西方戏剧学发展和研究总体现状而言,其诞生和发展呈现理论化、体系化和实证化特征。基于长期人文熏陶与医学技术进步,戏剧治疗理论潜心发展,自成体系,自为方家。几代薪火相传,其治疗核心精髓理论始终未变,由心理治疗衍生当今角色转换法。从医院、社区与学校,由点及面,由理论及至实践,辐射至社会诸多领域。并且,西方戏剧治疗学不断变异与创新,在最新科学前沿诞生出舞动治疗、音乐治疗、声音治疗,甚而美术治疗等诸多艺术疗育内部学科。
二、中国戏剧治疗学研究现状
戏剧治疗艺术在中国起步很晚。台湾地区的研究要稍早于大陆地区。张晓华教授于1995年邀请美国戏剧治疗界大师罗伯特·兰迪教授在台湾戏曲学院成立一系列戏剧治疗工作,取得较大社会影响。1996年国立台湾艺术学院戏剧系首次开设戏剧治疗的课程。台湾地区也陆陆续续涌现出一批戏剧治疗师,并且翻译了一些西方戏剧治疗文献资料和著作。在学校和社区,心理戏剧工作坊也陆续成立,尤其在单亲儿童心理治疗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香港地区直到2009年才成立香港戏剧治疗师协会,拥有两名注册戏剧治疗师。2010年香港成立戏剧治疗工作坊并举办研讨会。
戏剧治疗在大陆地区的相关发展和研究则几乎是一片空白。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陈国鹏和钟友彬关于心理剧治疗疾病的文献介绍。90年代,大陆地区开始了对戏剧治疗较为全面的介绍,如朱江的“莫诺和社会计量学”论文,李学谦的“心理剧治疗”文献介绍。虽然教育部早在2002年就把戏剧纳入我国中小学课程教育体系,但迄今为止没有建立一个系统的课程规划和成立一个完整的戏剧治疗团体。直到2007年才在厦门大学创立艺术治疗专业,2011年正式招收戏剧治疗专业研究生,进行戏剧治疗领域的系统人才培养。
在医学临床应用领域,戏剧治疗学起步更晚。直到近年来,国内一些精神卫生医疗机构才开始重视戏剧治疗,并将之运用到临床心理治疗中。21世纪初,北京回龙观医院开始采纳戏剧治疗作为临床辅助疗法,治疗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武汉精神卫生中心探讨如何将戏剧治疗运用于开放式心理病房,并在临床实践中创作出《皇帝的新装》和《俄狄浦斯王》等心理剧治疗剧本。西南大学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中心积极研究戏剧治疗学在突发自然灾害带来心理危机时的心理干预作用。北京安定医院利用戏剧的情感宣泄作用积极干预患者的心理情绪。河北唐山市人民医院以危重病人家属和医护人员关系为主题进行戏剧治疗学的临床实践。与此同时,在抑郁症患者、残障儿童、精神科、监狱、高职院校职业规划以及公司企业的团队建设等领域,戏剧治疗学正陆续得到研究和运用。一些具体案例如下:吉林省梅河口第五中学利用戏剧治疗学积极干预班级建设中的学生心理指导与调节,西南大学教育学院将戏剧治疗运用于学校团体心理咨询中。
伴随临床实践,产生了一些戏剧治疗学研究成果,如北京回龙观医院屈英等撰写的《戏剧治疗慢性精神分裂症的对照研究》(2000年),武汉精神卫生中心刘慧兰的《戏剧治疗在心理治疗病房运用之初探》(2005年),于桂翠的《戏剧治疗对儿童心理健康成长的影响效果》(2012年),牛小娜的《表达性艺术治疗对抑郁症残留症状疗效随机对照研究》(2014年)等研究成果。2012年大陆翻译引进了罗伯特·兰迪的戏剧治疗专著《躺椅和舞台:心理治疗中的语言和行动》。但总体而言,关于戏剧治疗学方面的研究论文和著作在中国仍属凤毛麟角。
最近十年内,中国戏剧治疗研究呈现出四个方面的特点:精神病人戏剧治疗疗法;在校学生心理问题疏导;企业员工的精神压力的排遣以及戏剧治疗如何应用于中国的本土化研究问题。其中将戏剧疗法用于精神病人,采取合理有效的方法疏导精神疾病最为普遍,研究得出的相关实践和理论成果包括施善葆的“神奇的‘戏剧疗法'”。刘慧兰等探讨了戏剧治疗在心理治疗病房的临床运用。[8-9]潘佩佩从历史视角解析了戏剧治疗从古代到当代社会在仪式方面的转化;[10]周显宝和赵倩则以“面具”为核心,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追溯戏剧治疗学的发展。[11]张鸿懿以音乐为主线研究中国戏剧治疗近二十年的实践与教育。杨俊霞则干脆直接翻译了以色列著名研究学者阿塔·席特龙的“医学小丑与戏剧治疗”。[12]牛小娜等通过抑郁症临床残留症状随机对照研究艺术治疗,探讨艾司西酞普兰合并表达性艺术治疗对于抑郁症残留症状的疗效。[13]解眉认为,日常生活中的游戏与仪式也是戏剧治疗自我呈现之一。[14]蒋佳从电影视角出发,论述了电影疗法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以及近年来电影疗法的新模式——现代计算机技术和电影结合的产物。[15]屈英等学者认为,戏剧治疗对于慢性精神分裂症诊治有明显临床效果,探讨戏剧治疗对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辅助治疗作用。[16]
第二类研究对象为学生(儿童),戏剧治疗的心理疏导作用尚处于初步研究阶段,涉及的相关研究成果较少,主要集中在学校领域。陈卫平、张楠楠以及李帮琼等以学校为研究场所对象,通过高校艺术心理治疗、心理剧及高职院校职业规划等途径,利用戏剧治疗帮助高职大学生了解与接纳自我,提升自信,树立恰当的职业目标,建立自我定位。[17-19]于桂翠专注于儿童心理健康成长,以学前班的儿童为研究对象,采用团体戏剧治疗的方法,研究戏剧治疗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效果。[20]商丹探讨了戏剧疗法,尤其是运用各种戏剧表演技巧,对学生心理的积极影响。[21]
第三类研究对象为企业员工。戏剧治疗对于精神压力排遣的作用研究处于萌芽阶段。在国内,很少有公司采取戏剧治疗对精神压力大的员工进行辅导。针对这一方面的研究实践和成果更为少见,主要有沈圣杰、于哗和张瑜雪的《戏剧治疗在中国社会工作情境中的应用研究》以及余玲艳、樊富珉和田湘文的论文《团体戏剧治疗方法在企业绩效管理中的应用》,后者借鉴应用心理学中的戏剧治疗方法来解决企业绩效提升中遇到的棘手问题。[22-23]
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对于戏剧治疗的研究开始较晚,发展较迟缓。针对戏剧治疗如何应用于中国本土化课题,相关研究成果较为不足。邵燕基于教育本土化问题,提出“照搬国外理论显然与我国的‘国情'有些不符”,认为“戏剧治疗学”在我国高等教育中则面临着民族化、本土化教学的问题。[24]轩希从宏观角度揭示了心理剧在大陆发展的艰难处境、适用领域和未来展望。[25]李世武以中国古老傩戏为研究突破口,解释了傩戏的治疗作用及其原因,揭示了迷狂宗教驱魔仪式剧成为戏剧治疗学、傩学、宗教人类学、医学人类学共同的话题。[26]关于对国外戏剧治疗研究综述成果,国内学者涉猎更少,目前主要以戏剧治疗学译介为主,详细综述以色列和德国的著名戏剧疗法。杨俊霞翻译的以色列研究学者阿塔·席特龙的论文《医学小丑与戏剧治疗》,以以色列海法大学戏剧系的新设专业医学小丑为例,探讨了继身体治疗、职业治疗等领域后,医疗小丑的发展前景;[12]商丹则综述了德国研究学者Galli的戏剧疗法,运用即兴表演,作为发展创造力和促进个人成长的手段,核心就在于让参与者去“表演”。[21]
其他关于戏剧治疗进展的学术成果难以归类,比较庞杂,大致涵盖郑玉章等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郑玉章等着重理论探讨音乐治疗学的发展历程,但是并未过多涉及实证探索。[27]胡珺《从团体戏剧治疗角度看其观众的特殊性——以心理剧技术为例》一文研究心理剧观众的特殊性,但并未对观众,即治疗对象进行明确归类,如观众到底是指向学生、精神病患者抑或其他因素。[28]周显宝和于小茵的《伪装与揭露:面具背后的戏剧性转换与投射——论戏剧治疗中面具运用的实操方法与符号象征意义》一文研究戏剧治疗中面具的运用,不足之处是并未对具体研究对象进行梳理。[29]姜澎和赵殷的《戏剧表演:心理治疗新手段》研究内容过于单薄,仅仅简略回顾了戏剧治疗的源起。[30]
基于中国戏剧治疗研究之现状,可以认为,从研究对象来看,中国戏剧治疗研究对象范围相对狭窄,仅局限于医院,部分在校学生以及企业,即便在医院临床心理治疗场所也并没有大规模展开工作,相关治疗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缺乏从戏剧视阈出发解决问题的有效措施;中国特色和优势没有落到实处,目前远没有形成制度化体系化治疗,进而迈向常规化治疗阶段。戏剧治疗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中国本土化接受过程缓慢,学术研究更为稀少罕见,学术挖掘空间巨大。
三、中西文化交融视阈下的戏剧治疗研究前景
戏剧治疗作为新兴跨学科,由于其自身因子特殊性,为中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了天然交汇融合平台。在生存危机、道家养生和临床医学等角度,戏剧治疗艺术能够发挥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从生存危机角度看,人类面临共同生态持续恶化的危机现状,精神世界不断被挤压和异化。戏剧治疗学让中西方面对共同的精神心理生存危机时联合起来,共存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无论是东方戏曲还是西方戏剧,它们皆先天具备“仪式”功能和“宣泄”价值,让人类能够排解内心积郁,共同寻找宁静心灵家园,赎回“本真自我”。从人类古老的“丰收仪式”,到阿尔托的“残酷戏剧”,格洛托夫斯基的“质朴戏剧”,到加缪的“荒诞派戏剧理论”,戏剧形式的表面形式化实质回归它的质朴母体“仪式”,从精神建设层面链接交叉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空间。戏剧治疗则更进一步从临床医学角度赤裸裸地剥离生活光怪陆离的表皮,展现人类在精神心理危机下如何向死而生,从而在医学领域为中西医学人文交集提供魔法舞台。无论是罗伯特·兰迪还是蕾妮·伊姆娜,他们都重视从心理学角度探讨戏剧治疗的作用与历史渊源,从关注人类生存角度探讨戏剧的舞台作用。同理,戏剧治疗师莫雷诺在其著作《谁将生存》一书中认为戏剧治疗中的角色扮演能够让人类预示未来,重构当下自我。
从道家养生角度看,戏剧治疗本质上注重人类心理健康平衡,通过排解精神积郁,恢复个体内在心理和谐。关于人与自然,道家倡导“天人合一”,人顺自然,无为而治,“道法自然”。人类需要“去甚、去奢、去泰”,从而达到“自然——释然——当然——怡然”之境界。关于人与他人,道家唯尊“人之道,为而不争”“厚德载物,上善若水”。东方哲学体现出的心理养生之道——平和、宽容、自然——则无疑与戏剧治疗之本质不谋而合。兰迪认为,戏剧治疗能够恢复人类日常心理平衡,产生角色认同。戏剧治疗糅合了艺术、舞台、音乐和诗文。它们的同步展开能够协同人类心理和肢体语言,实现内在心理和谐之道。内在思想和情感协同之道构建了人类心理生态之链。这种平衡之术与东方哲学注重的平衡精髓不谋而合。戏剧治疗将人类心理由二元对立人生观向大道合一精神生态哲学观转向,将戏剧宣泄功能与老庄思想契而为一,与生态主义批判发展趋势一致,与当今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时代呼声遥相一致。作为中华文化集大成者之一的《黄帝内经》则从养生视阈出发,在整体观和自然法则之上为戏剧治疗学在中华文化土壤里扎根提供天然契机。这种东西方文化艺术整合与交叉将戏剧治疗学推至理论与实践的至高境界。
从临床医学角度看,戏剧治疗学涉及强迫症、精神分裂症、药物滥用等精神心理疾病为中西方在医疗系统的合作提供契机。无论从精神还是身体层面,中医倡导的均衡养生之道对西方戏剧治疗理论的本土化建设起到推动作用。上海和北京等地医疗机构不断邀请国外精神卫生专家学者前来讲座和培训。双方在医疗领域展开越来越多相关医疗合作,对于促进我国戏剧治疗的发展大有裨益,也有利于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发展道路。戏剧治疗学本土化研究有助于推动中国戏剧治疗模式的发展。现实表明,戏剧治疗学从引进中国国内伊始,在相关领域研究和运用仍是一片空白,也从另一层面预示了多学科交叉性建设的迫切性和前沿性,既涉及文学艺术,又与心理学、精神病学和临床医学等学科紧密联系。戏剧治疗史实践证明,文学艺术研究与临床医学实践紧密结合,证明人文研究具备现实意义,终极指向“诗意的栖居”。
四、结语
戏剧治疗学在西方研究由点及面,呈辐射伞状波及社会诸多重要领域。与此同时,在秉承一贯戏剧治疗理论精髓之际,衍生出舞动治疗、音乐治疗、声音治疗以及美术治疗等最新趋势,合而总称为艺术疗育。反观中国研究现状,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坐拥道家流派、《黄帝内经》、中华医学等诸多与戏剧治疗本质一脉相承因子,却并未及时反哺戏剧治疗学科,造化中华式本土化戏剧治疗大好时机。因此,竭力将中华文化糅合与改良戏剧治疗学,进而形成中华化和本土化戏剧学科研究领域之新气象,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