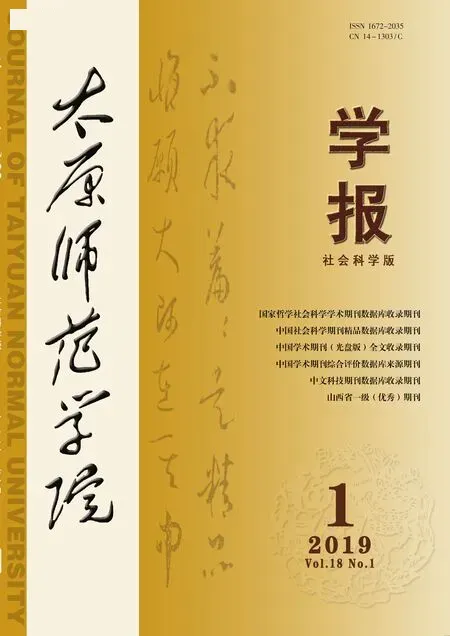论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中“公共机构”的认定
——以DSB案件对“国有企业”的认定为视角
,
(1.武汉大学 国际法研究所, 湖北 武汉 430072; 2.武汉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0)
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下,“公共”与“私人”之间本应存在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因为WTO调整的是成员的公行为。但由于WTO的《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以下简称《SCM协定》)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长期以来,对国有企业是否构成补贴主体之一的“公共机构”一直存在争议。一些WTO成员国对中国普遍存在的“国有企业”存在质疑,甚至将“国有企业”与其他企业的经济交易视为“公共机构”的财政资助。本文结合《SCM协定》规则和DSB成案,包括2018年3月21日通过的美国对中国部分产品实施反补贴措施案(以下简称DS437案)的美国执行情况专家组报告和美国对源自中国的若干产品征收反倾销及反补贴税案(以下简称DS379案)中对“国有企业”与“公共机构”的认定,对国有企业是否构成公共机构进行分析,并对中国和中国国有企业如何应对提出建议。
一、DSB成案中对“公共机构”的认定
根据《SCM协定》第1.1(a)(1)条对补贴的定义,补贴的行为主体是“政府”(government)或“公共机构”(public body),行为主要有两种形式,分别是财政资助(financial contribution)和授予利益(benefit),同时补贴主体提供的补贴要有专向性(specific),满足补贴主体、补贴形式和专向性条件才构成补贴。关于“国有企业”是否属于“公共机构”,一方面可以明确,《SCM协定》将政府和公共机构并列,因此两者不能画等号,但存在某种联系,都是补贴主体,[注]① 美国对中国部分产品双反措施案(DS379案)专家组报告肯定了这一判断。另一方面,由于《SCM协定》没有对“政府”和“公共机构”下定义和作具体区分,判断补贴不能仅执着于“公共机构”,可以先判断是否存在《SCM协定》第1.1(a)(1)条所列的行为,即是否存在财政资助和利益授予,进而帮助判断行为主体是否是“公共机构”。在WTO具体案件中,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判断往往取决于当事方提供的证据材料。DS379案中,中国在国有企业是否属于公共机构的认定上取得胜利,这一重大成果不仅影响了后续类似案件,如DS437案的执行专家组对中国“国有企业”的认定,也为以后中国将面临的案件提供了参考。
(一)从DS379案探究“公共机构”的认定
DS379案是中国在DSB中就“公共机构”认定胜诉的经典案件。2008年6月,美国商务部对来自中国的产品[注]环形焊管(CWP)、复合编织袋(CLWS)、轻型薄壁矩形管及管件(LWR)和非公路用轮胎(OTR)。提起双反调查,认定涉案的中国国有企业属于《SCM协定》中的补贴提供主体“公共机构”,并最终对四种商品加征高额的双反税。同年9月19日,中国就美国上述“双反措施”向WTO的DSB提起争端解决。2010年7月专家组作出裁决,2010年12月中国就案件中涉及“公共机构”等四方面问题提起上诉。2011年上诉机构发布报告,推翻专家组报告,支持中国主张。
1.各方对“公共机构”的主张和认定
(1)中方对“公共机构”的主张。中国认为判断某国有企业是否为“公共机构”不应先入为主仅依据控制权得出结论,相反根据《SCM协定》第1.1(a)(iv)条[注]《SCM协定》1.1条(a)(iv):“政府向一筹资机构付款,或委托或指示一私营机构履行以上(i)至(iii)列举的一种或多种通常应属于政府的职能,且此种做法与政府通常采用的做法并无实质差别。”的规定,只有证明国有企业被政府“委托和指示”履行政府1—3项列举职能的情况下才能认定作为私主体的“国有企业”为补贴主体,即仅当国有企业行使政府职能或公共性质的职能,并且行为是在政府授权下行使时,才受《SCM协定》约束。[1]8
(2)美国对“公共机构”的主张。美国至今沿用的1998年联邦《反补贴法》,将大多数政府控制企业视为政府本身。此外,美国还广泛适用始于1987年荷兰鲜花反补贴案[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USDOC), Final Affirmative CVD Determination:Certain Fresh Cut Flowers from the Netherlands,52 FR 3301 (February 3,1987).中的“五要素分析法”[注]五要素即:企业是否为政府所有;政府是否派代表在董事会任职;企业活动是否受政府控制;是否遵循政府政策谋求利益;是否通过法律创设。,一般满足五项中的第一个要素,也就肯定了后面几项要素,美国还是依政府控制因素认定该国有企业属于公共机构。本案美国依然沿用这两种方法,并引用中国的一系列法律,如《宪法》第六条、《物权法》第一条、《企业国有资产法》第一条和第三条、《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第一条,来证明中国政府有权通过直接或间接介入国有企业进而影响经济运行。
(3)专家组对“公共机构”的认定和推断。专家组需要判断涉案的中国国有企业是否是《SCM协定》第1.1(1)(a)条的公共机构。
由于《SCM协定》并未定义“公共机构”一词,专家组根据WTO争端解决的常用方法,查找权威词典解释词义。专家组查找《简明牛津英语字典》和Online免费字典[注]Free Dictionary Online.http://www.the free dictionary.com.访问时间为2018年8月7日。中“公共”和“机构”[注]公共:“属于或关于整体人民的;属于、影响或关于社会或国家的”。机构:“被认定为一个实体或一个公司的一组个人;一个整体或总体;一个公司;一个立法机构;一个办事机构。”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vol.I,1123(L.Browned.Claredon Press 1993).两者的解释,将“公共机构”解释为“属于社群(community)和国家的公司”[1],又比较了“公共行业”(public sector)和“私人企业”(private enterprise),得出“公共机构应作扩大解释,政府控制是判断公共机构的关键”的结论。专家组援引了韩国商用船舶贸易措施案(DS273案)的专家组报告,财政资助与授予利益是两个不同的问题”,[2]证明《SCM协定》第2条中衡量“财政资助”和“授予利益”的关键在于判断“专向性”(specificity),“专向性”的判断反映《SCM协定》规范贸易扭曲的宗旨和目的。专向性条款证明的是构成协定所指补贴因产生的利益而确定出来,换句话说,专向性条款不是判断是否存在补贴的条件,而是判断补贴的准入条款,并且《SCM协定》第2条对专向性规定了多种形式,表面的非专向性不能成为排除补贴不属于《SCM协定》的条件。因此《SCM协定》第2条只是判断补贴的限制性条件,如果遵从中方将“公共机构”解释为“受政府委托的机构”,在不能证明政府委托的情况下,就会将政府控制企业等同于私人企业,从而使政府借以规避《SCM协定》,严重损害《SCM协定》的宗旨和目标。而将“公共机构”解释为“受政府控制的实体”,无论“公共机构”是什么形式,政府因控制权而对控制实体的行为负责,如果行为产生“利益”授予则构成补贴。据此专家组引用了“政府控制说”来界定国有企业和“公共机构”的关系。
本文认为,专家组通过将“公共机构”解释为“受政府控制的实体”扩大了补贴的主体范围。
2.上诉机构驳回专家组对“公共机构”的认定
首先,上诉机构否定专家组的文义解释,认为不能仅根据量词“一个”“任何”武断地将“公共机构”和“政府”强行划分开,[3]289用“或者”连接表明“公共机构”和“政府”必然有某种联系。“公共机构”潜在意思丰富,包括被授予或行使政府职能的实体、国家(Nation)和社群(Community)所有的实体。[3]285
其次,上诉机构表示明确私人机构的含义有助于理解公共机构的重要特征,因为涉及私人机构的条款描述了一些主体是非政府或公共机构的情况。审查“private”定义“关于商业:个体非国家或公共机构所有的;相关人员:未任职于公共机构或官方机构”,[3]291上诉机构认为无论“公共”还是“私人”都可以产生权力和控制的概念,这种概念与实际实施权力和控制是有区别的。[3]292上诉机构援引美国和加拿大出口限制案(DS149)专家组观点,《SCM协定》第1.1(a)(1)(iv)条引入“私人机构”概念,认为“私人机构”是“国有企业”或“公共机构”的对立面,为了解释不属于这两种主体的实体,该条i—iii项列出“政府”或“公共机构”指示“私人机构”行使政府职能的行为。上诉机构特别解释“指示”(direct)指获得权力而产生控制、命令、管理的行为;在该条中的指示行为(direction)指政府对私人机构行使权力;授权(entrustment)行为是政府给予私人机构权力。同理,在该条款语境下可知公共机构同样有命令(command)、管理(govern)、授权私人机构的权力,如果公共机构能如此,它本身必须有命令和授权权力的能力,因此本条中狭义政府和公共机构的共同特点就是都有指示和授权的能力。
再次,对于专家组提出的“利益”问题,上诉机构认为,购买货物、贷款等以市场规则为本的行为,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可以行使,而有些职能的行使则具有政府属性,如放弃税收,是由政府还是企业采取某种给予财政资助的方式,与定义“公共机构”没有关系。[3]302
最后,上诉机构指出,当私营机构被政府或公共机构委托或指示,其措施仍可归因于政府,其措施可以归到《SCM协定》下。[4]303各国政府不同,公共机构界定因实体而不同。具体个案中,专家组只有准确评估涉案实体的特点、实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才能判断该实体是否是公共机构。无论如何都应避免只考虑单一因素或特点。而美国在上诉阶段提供的证据,上诉机构未将关注点放在如何举证证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公共机构”等具体问题上,而是放在国有企业是否属于“公共机构”的判断上,认为美国有义务寻找证据进行客观评估,但美国提供的证据未能充分论证“五要素分析法”中所需的信息,调查的数据是片面的。[3]163-169
(二)DS437案执行专家组报告对“公共机构”的认定
1.案情简介
中国2012年5月就美国在2007年到2012年间对华22项产品[注]包括太阳能电池板、风塔、热敏纸、铜版纸、厨房架子、钢水槽、柠檬酸、氧化镁碳砖、压力管道、管线管、无缝管、钢瓶、钻杆、油田管材、钢绞线等。的反补贴措施在WTO项下提起磋商,其中核心争议之一是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指控中国国有企业向下游生产商销售原材料的行为构成补贴,这些国有企业属于《SCM协定》中所指的“公共机构”。2014年7月14日出具的专家组报告中判定部分中国国有企业属于《SCM协议》第1.1(a)(1)条意义下的公共机构,且提供了财政资助。[注]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ispu_e/cases_e/ds437_e.htm.访问时间为2018年4月8日。2014年8月,中方就中国12起涉案国有企业被认定属于《SCM协定》第1.1条“公共机构”等判定提起上诉。2014年12月18日通过的上诉机构报告没有直面“公共机构”问题,但不支持美国对利益的算法。上诉机构作出的相关判定如下:(1)利益分析时,应集中审查与政府有关实体在市场中扮演的角色;(2)授权利益的问题推翻专家组判决,认为判断某一实体为政府或公共机构,应独立分析所授权利益的性质;(3)授权当局所具有的“管辖权”(jurisdiction)和“授予利益”两者不同,不能仅对授权当局的“身份”进行判断,应将“管辖权”和“授予利益”联系起来分析。上诉机构驳回专家组支持美国《SCM协定》第1.1(b)条的相关问题和有关利益的判决结果。美国在2015年2月作出履行判决建议的承诺,美国商务部(USDOC)依据《乌拉圭回合合规协定法》第129节[注]Section 129 of the Uruguay Round Agreements Act.启动合规程序,经过再次调查,依然认定中国国有企业为公共机构,中国国有企业向下级供应商提供原料的行为属于《SCM协定》中的补贴行为。中国认为美国没有执行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报告并提起执行专家组程序,2018年3月21日,专家组出具美国执行情况的合规报告。
2.中美双方对“公共机构”的主张
美国单挑出上诉机构对公共机构解释中“由政府所有、行使或授权的机构”[3]317中的“所有”(possesses)一词来判断向下级分销商提供原料的中国国有企业属于“公共机构”。[4]26其实早在DS379案中,上诉机构已经推翻美国以单一“政府控制论”判断公共机构的做法。中方认为美方根据《乌拉圭回合合规协定法》129节第11部分采取的做法不符合《SCM协定》第1.1(a)(1)条,采用了不合适的法律标准判断进口商是否为公共机构,错误认定所有权由政府控制或由政府授权提供进口的实体为公共机构。其次,当某实体实施《SCM协定》第(a)(1)条中列举的行为,也即财政资助时,是否就是执行了政府职能,中方主张问题的本质是美方没有阐明所谓的“政府职能”和基于调查得出相关进口产品销售之间的关系,美方认为中方国有企业行使的“政府职能”是维持社会主义经济。上诉机构判断某一实体是否为“公共机构”的因素为“有意义的控制”(meaningful control),中方主张“政府职能”与一定的财政资助相关,而不是任何“政府控制”实体都与“政府职能”有关。美方认为本案上诉机构报告已强调对公共机构的分析重点应放在相关实体核心特征的评估上,也即实体与政府的关系,而不是关注实体的行为。[1]57-59
3.专家组结论
专家组对中美国有企业争议问题从以下几方面给出结论:
专家组认为财政资助和政府行为的关系应从两方面分析,一是相关政府职能的识别,二是政府职能和引起财政资助的实体行为。虽然政府职能的识别是判断公共机构的一部分,但中方主张美方应证明补贴、财政资助与所对应政府职能之间的关系,专家组以及上诉机构对公共机构的界定,美方无需对此作出证明。美方试图通过罗列中国的相关法律证明中国政府的职能是维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国有部门的主导地位,[5]6-11对此专家组表示没有义务判断何为政府职能,美方证明的中国政府的职能之一是“维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分析公共机构的目标无关,这一职能的概念是如此宽泛,以至于对政府补助问题的分析毫无意义。
其次,对美方提供的涉案国有企业是“政府所有”和政府“正式控制”(formal control)的证据,专家组虽认可《SCM协议》项下第1.1(a)(1)条所指公共机构一定是一个政府所有、实施或被政府授权的实体,但专家组认为“正式控制”与上诉机构提出的“有意义的控制”(meaningful control)存在区别,不能仅依据不充分的“正式控制”证明某一实体属于公共机构,而以往案件的上诉报告中已明确反对将“政府对实体存在控制”和“有意义的控制”相混淆。[6]判断构成“有意义的控制”需要考虑许多因素,如政府投资的国有企业具有政府职能且需要提供支持调查结论的相关证据。国家控制条件下结合其他一些因素可以表明政府权力的委托,也不排除特殊的实体就是公共机构,正如可以通过政府授权某实体实现“政府职能”。但仅根据政府拥有所有权或控制某实体,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确定该实体为“公共机构”是不充分的。
再次,政府职能和财政资助、授予利益之间的关系问题,美方在公共机构备忘录[5]3例证了三方面:一是中国政府向国有企业提供直接或间接的利益从而最终达到控制的效果;二是中国政府产业政策影响了公司行为;三是政府拥有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说明国有企业是中国政府实现控制与管理市场的工具。[5]14-16对此,专家组认为关键应考虑实体是否实施了专属政府的职能。DS437案上诉机构报告曾解释,实体的行为是不是《SCM协议》第1.1(a)(1)条所指的财政资助和授予利益,应当根据具体案件中不同实体的特征、功能、与政府的关系,以及被调查实体所在国家现行法律、经济环境等因素确定。[3]当某实体的功能和行为在相关成员国法律下分类为政府性时,该特殊实体为公共机构。当然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政府形式,那么准确的公共机构特征也一定在各个实体、各个国家、各个案例之间都各不相同。专家组建议调查当局应避免专断或过于强调某个单一特征而忽略其他相关因素。对此,专家组援引日本对来自韩国的动态随机存取器征收反补贴税案[7]131中上诉机构的观点,调查当局应依据整体环境下的证据,将部分零散的证据相互连接起来,弥补个别证据单独考虑所带来的不公正性。中方虽然提出USDOC在确定政府职能和向被调查实体提供投入的关联方面运用了错误的法律标准的观点,但没有根据《SCM协议》第12.7条就USDOC的可用事实提出任何请求,也未能证明USDOC错误地理解了“公共机构”概念和“公共机构”实质性法律标准。综上,专家组表示,没有理由在中方缺乏相关行政职能证据的基础上,依据《SCM协议》第1.1(a)(1)条政府职能与财政资助之间相互联系的法律立场,认定USDOC的公共机构裁决与《SCM协议》第1.1(a)(1)条不一致。虽然中国政府提交了有关国资委和中国国有企业法律的信息,且中国提及的证据可能与USDOC得出相反的结论,但需要全面的证据作为支撑,专家组认为中方提供的证据是不充分的,不足以证明美国商务部的裁决与《SCM协定》第1.1(a)(1)条不一致。最终专家组适用了美方的证据标准来分析“公共机构”,也即美方是否充分考虑和解释了可以判断为“公共机构”的事实证据。
最后,关于中方指控美方援引《SCM协议》第21.5条[8]193-197与《SCM协议》第1.1(a)(1)条相违背问题,专家组援引大型民用航空器案[9]7上诉机构的观点,即原则上WTO成员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都可以成为争端解决程序中考察的成员方措施,可受到质疑的措施的范围是广泛的,并不要求申诉方证明存在一般性的规则或规范,从而推翻了中方主张公共机构备忘录不受争端解决机制调整的主张。
此外,对中方提出美方目前仍然在持续、系统地适用错误的法律标准,并且担心美国未来会持续引用错误的法律标准,专家组认为中方必须证明以下两点:其一,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结论反映了美国在《SCM协议》框架下系统性适用了错误的法律标准;其二,这些与《SCM协议》不一致的做法会持续进行。[10]180
专家组的最终意见是,虽然中方已证明美国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决定与DSU规则和建议的相关性,但中方在案件最初没有提出行政和日落复审决定,没能证明美方适用错误的法律标准与《SCM协定》第1.1(a)(1)条、第1.1(b)条、第2.1(c)条、第2.2条等条款不符,尤其是在一些关键的行政复议里面没有说明存在不合理的法律适用。关于本案第129节的内容,中方在案件最初也没有指出UCDOC适用了错误的法律标准。专家组不认为这份合规程序报告中中方证明美方存在违反《SCM协定》的情况,也不认为这种不一致会在以后的程序中被复制。虽然在每项反补贴法令下都有“一系列相互连贯的裁决”,但我们未能在这些连续的诉讼程序中看到“不变的组成部分”。[10]180-181相反,美国商务部每次适用的法律标准都有所不同,且美方每个阶段和程序相关调查得出的结论都与WTO协定保持一致,因此中方未能证明美方存在与SCM协定第1.1(a)(1)条、第1.1(b)条、第2.1(c)条、第2.2条等条款相违背的行为。
二、“公共机构”认定的问题分析和总结
美方在DS437案中几乎沿用了DS379的“公共机构”判定方法,只是将DS379案中的举证方法“政府控制说”作了简单的变形,而专家组在DS437案的执行审查中完全支持了美方观点,对中国不利,我们有必要结合各方观点梳理公共机构判定的相关问题。图1表示了“公共机构”、政府、私人机构、国有企业四者的关系,本文尝试通过图1已知条件发现未知条件,便于理解专家组处理案件时的漏洞,并从不同的衡量角度讨论。
情况一:在不讨论具体案情和不判断是否构成补贴的前提下,仅讨论国有企业是否属于《SCM协定》下的“公共机构”。
在没有具体案情的前提下,只能通过WTO文义解释。根据《SCM协定》第1.1(a)(1)条的规定“在一成员领土内,存在由政府或任何公共机构提供的财政资助”可知,构成补贴的主体有政府和“公共机构”,两者有一定共性或联系,协定中两者关系用“or”表示。图1中两圆分别代表政府和“公共机构”,两圆的交集代表两者存在的联系,矩形框内两圆外的其他部分代表私人机构。如图1,“公共机构”所在圆不是闭合区域,箭头表示“私人机构”在满足条件下可等同“公共机构”。什么条件下“私人机构”从圆圈外进入到“公共机构”的圆圈中?这是所有关系中的未知数。
DS379案中,查询英文、法文等词典依然难以释明何为“公共机构”的情况下,专家组接着衡量“财政资助”和“授予利益”两条件,最终采用“政府控制论”。针对国有企业,政府控制权包含所有的财政资助行为,不需要单独考虑财政资助有时不具有专向性的特性,且政府控制恰好是证明“直接来自政府的委托或指示”的证据之一,加之政府控制这种扩大解释方法,囊括该实体所有从政府获得的“利益”,这种扩大的解释方法让整个程序排除了判断“利益”是否属于政府授予利益的步骤。
情况一是DS379案专家组的判定,特点是没有结合各案件具体条件,仅根据词语解释、《SCM协定》规定的条件以及本身未知的政府控制因素作为判断标准,是用未知数推导未知数,不能解决问题。
情况二:《SCM协定》规定了补贴三要件,即补贴主体为政府或“公共机构”、补贴内容为财政资助或任何形式的收入和价格支持、补贴效果是令补贴者获得比正常市场更多的优惠利益。判断国有企业是否为“公共机构”本身是求解的未知数,而情况一就“公共机构”本身进行文义解释是不够的。求解未知数,对未知数本身不能作过多讨论,而应通过案件其他已知项求解。
求解未知数转化为图1就是圆圈外的私人机构如何进入圆圈等同于政府、公共机构。按照DS437案上诉机构的观点,即使不属于政府的私人机构在受到政府的委托和指示行使政府职能时也应视为政府行为,而国有企业由政府控制这一因素,仅能作为有“财政补贴”的证据之一。结合图1理解:《SCM协定》第1.1(a)(1)(iv)条[注]政府向一筹资机构付款,或委托或指示一私人机构履行以上(i)至(iii)列举的一种或多种通常应属于政府的职能,且此种做法与政府通常采用的做法并无实质差别。明示图中的私人机构(private body)在进行财政资助和授予利益时进入圆内,等同于政府和公共机构。财政资助的专向性决定了存在财政资助一定存在政府职能,但存在政府职能不一定存在财政资助。同理,某实体被定性为《SCM协定》的公共机构,该实体的性质一定是政府所有、操作或授权,但具备该性质实体的行为不一定被认定为补贴行为。正如DS379案上诉机构援引加拿大奶制品案上诉机构的观点,政府行使了某项职能和政府有权力行使某项职能是不同的含义。归根到底,判断补贴是否存在还是要看政府职能、政府财政补贴或授予利益是否同时存在。虽然《SCM协定》没有明文列出国有企业应如何界定,但根据情况二的推论,国有企业和处在圆圈外的私人机构进入圆圈内的条件是一样的,都是在确定存在政府职能、政府财政资助或授予利益时才能进入圆圈内。
而DS437案美国试图将政府正式控制与该案上诉机构要求证明的“有意义的控制”相等同,这种证明方法与DS379案美方证明的“政府控制论”实为换汤不换药。用政府控制论或类似方法的政府“正式控制”证明国有企业是否为公共机构并不能作为判断是否存在补贴的标准,这相当于取代政府资助和授予利益这些《SCM协定》中规定的连接因素,转而适用美方的单一控制论。对此专家组在2018年合规报告中表明,应将部分零散的证据连接起来成为整体性、相互联系的证据,[4]106事实上判断国有企业是否属于公共机构和国有企业是否构成补贴主体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不在《SCM协议》语境下讨论,当某实体的功能和行为被该成员国法律分类为政府性时,该特殊实体为公共机构,[11]297而在具体案件中讨论国有企业是否为补贴主体公共机构这一问题时,类似于判断私人企业是否为公共机构,正如图1圆圈外的私人企业进入圆圈的连接桥梁是政府职能的行使、政府资助和授予利益的存在,国有企业进入条件也是如此。当获得利益的来源不确定时,仅存在政府职能还不足以证明补贴,因为在《SCM协议》下判断补贴,最终能作出判断的因素不仅是讨论私人机构或国有企业属不属于公共机构。虽然2018年DS437案执行报告专家组支持仅存在政府职能时不能证明补贴的观点,但未明确如何通过政府职能、财政资助和利益授予的存在或各因素之间的关系举证存在补贴。中方试图将专家组的注意力引向美方对缺乏政府职能和政府财政资助或授予利益两者关系的证明,但专家组认为中方缺乏关于美方公共机构裁决与《SCM协议》第1.1(a)(1)条不一致的充分证据,所以最终的判定结果对中方不利。
三、反补贴实践中涉及国有企业的延伸问题
DS379的胜诉是划分“国有企业”和“公共机构”的重要里程碑,为以后此类案件提供了经验。但随着我国经济的稳步推进,我国贸易量逐年上升,发达国家对“国有企业”问题紧追不放,尤其是2018年3月DS437案件执行的合规报告,对中方指控美方行为违反《SCM协定》第1.1(a)(1)条和美方适用错误法律标准以及美方援引的公共机构备忘录内容是否能作为法律标准引用等多个问题专家组都拒绝中方观点,对我国来说实属不利,预计未来在WTO的相关摩擦案件基数会不断上升。在反补贴案件实践中,涉及“国有企业”“公共机构”认定的问题仍然存在很大隐患。
(一)国有企业认定复杂
《SCM协定》不仅没有对何为“公共机构”作出定义,也没有对国有企业作出解释,但政府控制确实是提供补贴的一个前提。实践中,如果不是政府而是国有企业向下级提供生产原料,在认定是否构成补贴主体时,首先需要认定提供者是否为国有企业,其次是财政资助专向性问题,其三是利益的授予。在没有相关具体规定可依的情况下,各国判定国有企业时都有自己的一套判定标准,而且需要逐案认定。实践中的企业股权控制错综复杂,尤其是非上市公司的数据十分难获得,股权结构不清晰,加之在实质重于形式原则下,国家实际控制公司不可能处于完全控股地位。
在非公路用轮胎案中,应诉企业贵州轮胎指出USDOC没有对国有企业进行界定,而美国的分析是:(1)贵阳国有资产公司持其33.38%的股份,第二大股东仅持有1%的股份,其他股东不能动摇贵阳国有资产公司控制地位;(2)贵阳国有资产公司行使国有资产管理者的职能;(3)贵州轮胎获得国家重点技术改造项目专项资金支持,根据中国政府规定,仅国有企业才能获得。[12]7
甚至外资企业也被列为国有企业。在厨房置物架案中,USDOC指出:政府占多数股权的国有企业也计入外资企业,因为中国将外资企业定义为外资占25%以上股权的企业。[12]8如果是外资持股25%、政府持股75%的情况,可能被认定既是外资企业又是国有企业。
面对如此多样、灵活的判断方法,中国许多行业的国有企业在未来很可能成为适用反补贴措施时的“公共机构”。
(二)政府行为经国有企业是否具有传递性
以往案件中,对判断国有企业的政府行为中行为的传递性有争议。如涉案企业的材料是几经转手从私人企业买来的源头被认定为是存在政府补贴的国有企业原料,是否依然认为该企业接受了财政资助?USDOC早期案件认为,尽管政府未直接给涉案企业提供存在补贴的原料,但涉案企业也间接通过受补贴的国有企业获得了财政资助。如非公路用轮胎案中,USDOC认定国有生产商将接受了政府补贴的产品卖给私人贸易商,这种销售属于可采取反补贴措施的补贴行为,[12]8即认定国有企业受到的财政资助补贴具有传递性。
(三)应诉方政府需要提供大量证据
判断国有企业是否构成“公共机构”、国有企业获得的财政资助是否具有传递性等,都需要应诉方提供大量信息。中国政府在面临反补贴调查时至少需要提供以下四方面内容:首先,政府需证明供应商是否为国有企业。其次,如果是国有企业需提供来自国有企业的原材料供应比例,如果中间经过转手,情况更为复杂。再次,需证明国有企业供应的原材料不具有专向性而是普遍可获得不限于特定对象的。最后,必要时需证明国有企业提供的要素在市场中不占主导地位。反补贴调查中,美国商务部会向应诉方发出问卷,中方不仅要提供指控行业的企业名单,还要判断哪些是国有企业,哪些不是,再证明国有企业的生产在市场上的份额。如果行业中企业数量庞大,政府提供完整的名单困难,应诉方会被认定举证不能,申诉方会适用“不利事实推定”[13]4。如果行业数量有限,则为政府行为专向性认定提供了证据。可见,被诉方的举证是一个难题,而无论是否提供完整名单,都可能带来不利的后果。
四、“国有企业”和“公共机构”认定标准启示
笔者认为,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中将长期处于主导地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经济体制的一种形态,它不能被用来判断国有企业是否属于《SCM协定》项下的补贴主体公共机构。正如中国在DS437合规报告中的主张,判断政府职能与财政资助两者间的对应关系才是判断国有企业是否属于公共机构的正解。虽然DS379案、DS437案中美国分别提出的“政府控制论”“正式控制”等判断国有企业的方式被推翻,但DS437合规报告专家组几乎拒绝了中国大多数主张,隐患依然存在。因此,我们有必要把处在风口浪尖的“国有企业”认定问题重视起来。笔者建议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国有企业定性路径不同导致举证不同
一方面,国有企业定性按照中美双方的观点可以分为两种证明路径。中方主张证明国有企业是否是“公共机构”先要将国有企业看作私人机构,然后结合资助行为和利益授予作出定论,而美方在DS379和DS437案件中都是直接证明国有企业属于公共机构。对美方来说,如果按照中方的路径,要先证明公共机构有政府的指示或授权,再证明因指示或授权产生了专向的利益或财政资助,不仅证据十分复杂繁琐,在WTO框架下清晰划分“私人”和“公共”界限是困难的,而且美国认为证明了某一国有企业属于公共机构,以后的案件中对类似国有企业的性质无需再次证明。相反,如果通过中方方式证明,美国需要对日后每个案件中的政府指示或授权等一一进行证明。[注]美方观点见案例WTO Panel Report, United States-Measures Treating Exports Restraints as Subsidies (US-Export Restraints), WT/DS194/R, adopted 29 Jun. 2001, para. 8.29 to para. 8.31.
另一方面,从《SCM协定》角度看,将政府和公共机构认定为补贴的直接主体,接着对私人机构何时构成补贴主体也进行了详细阐述,三者间关系又没有说明,简单说就是把国有企业放在哪一边?而公共机构属于完全未知,私人机构有政府指示或授权、产生了专向性利益或财政资助、两者间的关系这一渐进的证明方法,当然应选择将国有企业归入有明确法条可依的私人机构,否则就是前文所述的用未知数求解未知数的境况。
(二)充分利用程序权利提供有针对性的证据
从DS379案“政府控制论”到DS437案的“正式控制”,不但论证我国涉案“国有企业”属于公共机构的举证方式不断多样化,且DSB对中国申诉的审查没有统一的标准,这加大了我国举证难度。涉及国有企业不属于公共机构的举证难度表现在DSB申诉和反补贴调查两个阶段:一方面,DS437合规审查中由于我国在证据方面的缺失,致使没能证明美方一系列国有企业认定、授予利益计算方法与《SCM协议》不符,专家组在多个问题上作出对中方不利的事实认定;另一方面,随着WTO成员方对我国国有企业问题的关注,我国应诉案件将不断增加,商务、工商、财政税、海关等多部门,都无一例外承担了越来越多新的工作。个别案件中,调查机构一次性要求提供500家企业的股权情况,这些企业又分布在30个不同的省。然而,即便收集了大量证据,有时依然不能令反补贴调查当局满意,随时可能面临不利事实推定,且两个阶段的举证相互联系,反补贴调查阶段的证据收集直接影响DSB申诉。因此,我国政府和企业在调查期间和复审期间学会收集有针对性和有说服力的证据(如企业股权变动情况;行业政策、法规的修订动向;政府不参与企业经营决策过程等的细节证据)尤为关键。
(三)指导性文件要注意措词
DS437案美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条、《物权法》第一条、《企业国有资产法》第一条和第三条等法律文件证明我国政府对经济的调节、控制。美方还研究了我国《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认为“政府权力通过国资委影响国有企业,国资委监管下的国有企业从未与政府部门的控制、影响隔绝”[5]6。美国试图借此证明我国政府是以控制国有企业为手段最终达到行使政府职能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的。不仅如此,WTO其他成员方也因我国这些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对我国国有企业问题持谨慎态度。DS437案中的第三方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日本等国均对中国提出的有关国有企业认定的观点提出反对意见。[4]7这些成员国普遍认为,政府政策、一国适用的法律、现行经济环境、企业的核心特征以及企业与政府关系是影响公共机构判断的关键。这种过分敏感的反应本质上是对我国的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这种经济体形式的担忧。对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我国要清晰地向其他成员国表明立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决定了我国国有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在《SCM协议》项下讨论补贴问题仅论证国有企业性质是不充分的,《SCM协定》第1条、第2条有明确确定补贴的规则,不是仅依据控制或与政府关系等含糊的因素确定补贴。政治和经济分不开,政府和企业并非处在两个完全隔绝的空间,国家政策的变化会对社会各个层面或多或少产生影响,同样,国家政策对不同类型的企业也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不能将控制这一单一因素作为判断国家政策影响企业的唯一标准。而国家所有的企业只是企业形态的一种,在没有证据证明特定政府职能产生符合《SCM协定》特定利益的情况下指控国有企业属于公共机构本身是不符合《SCM协定》的。
其次,DS379案、DS437案中美方援引的我国政策文件、发展纲要、法律法规中“提供优惠贷款”“提供资金支持”这样的措词易引起其他成员国的误解与担忧,并被作为有力证据引用。我国应清理、修改或删除并在日后警惕使用一些容易造成误解的用语表述,或作出说明。如果属于整体行业规划,应对政策不具有专向性作出说明。对符合《SCM协定》第8.2(a)(b)(c)条规定的政策文件,按照《SCM协定》第8.3条的程序通知WTO反补贴委员会,等待委员会的评估结果,有政策变更则及时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