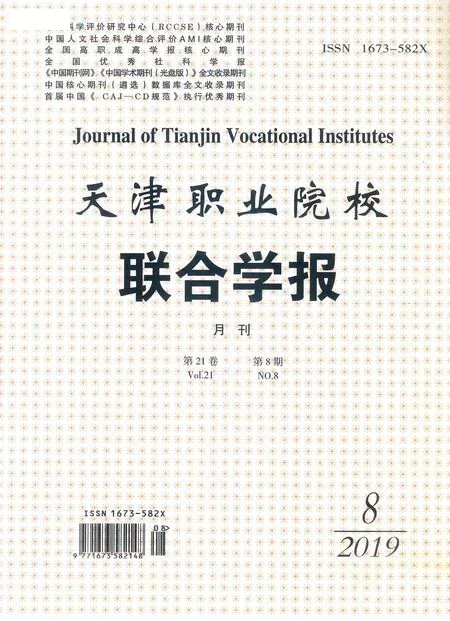七十二回的宿命
——明清长篇小说虎头蛇尾现象原因浅析
(天津市新华职工大学,天津 300070)
一、明清小说普遍表现为虎头蛇尾
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到明清时代,白话文长篇小说逐渐占领了文学的主要地位。明初,《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相继问世,标志着中国小说史又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从此,中国小说史以短篇小说为主转而进入到了以长篇小说为主的新时期。虽然短篇文言、白话小说一直在按照自身的规律发展前进,并且不断有佳作诞生,如《三言二拍》《聊斋志异》等,但总体说来,其成就与规模则已经无法与长篇小说相比拟。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中被称为“四大奇书”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在其所属的各类题材中独占鳌头:《三国演义》既是历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历史小说的典范;《水浒传》既是第一部全面描写农民起义的巨著,也是一部英雄传奇的典范;《西游记》既是第一部长篇神魔小说,也是一部神魔小说的典范;《金瓶梅》既是第一部写世情的长篇小说又是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它们各自开创了一个长篇小说的创作领域,并以其巨大成就深刻地影响着中国长篇小说的创作,以至在后来形成了长篇小说创作的几个系列:《三国》的历史系列、《水浒》的英雄系列,《西游》的神魔系列,《金瓶》的世情系列。这四个系列可以说对中国长篇小说的创作影响深远,在此后的文学创作,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中我们几乎都可以看到“四大奇书”的影子:比如:《东周列国志》《七侠五义》《封神演义》《红楼梦》《歧路灯》等。正如鳞耧子在《林兰香》序中所说:近世小说脍炙人口者,曰《三国志》,曰《水浒传》,曰《西游记》,曰《金瓶梅》,皆各擅其奇,以自成为一家。惟其自成一家也,故见者从而奇之。使有能合四家而为一家者,不更可奇乎。偶于坊友处睹《林兰香》一部,始圆之索然,再圆之憬然,终阅之怃然。其立局命意,俱见于开卷自叙之中,既不及贬,亦不及褒。所爱者,有《三国》之计谋,而未邻于谲诡:有《水浒》之放浪,而未流于猖狂:有《西游》之鬼神,而未出于荒诞:有《金瓶》之粉腻,而未及于妖淫。是盖集四家之奇,以自成为一家之奇者也。或日:子非奇士,性不好奇,兹乃以奇为言,不惮见哂于通人耶?答日:《三国》以利奇,而人奇之:《水浒》 以怪奇,而人奇之:《西游》以神奇,而人奇之:《金瓶》以乱奇,而人奇之。今《林兰香》师四家之正,戒四家之邪,而我奇之。是人皆以奇为奇,而我以不奇为奇也,奚见哂为?友是其言,遂书于卷首。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四大奇书”在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中的影响是深刻的,在此后的小说创作中,作家们或仿写,或续书,或反写(用小说形式批评反驳)不一而足,但几乎没有例外的是,我们从众多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四大奇书”的影子。这种影响,不仅仅在作品的成就上,包括作品的缺点也同样被后来的作品全盘接受。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中国明清古典长篇小说普遍表现出虎头蛇尾的现象。这种虎头蛇尾的现象如果说以《三国演义》为代表的历史小说因为有历史的原型,在表现上还显得不那么特别明显的话,而以《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为代表的神魔小说、英雄传奇小说、世情小说则由于文人创作因素占主导地位,虎头蛇尾现象便更加表现得尤为突出。
中国明清古典长篇小说普遍表现出虎头蛇尾的现象,从小说普遍情形上看,大多表现在写到第70至80回之间,故事出现一个比较高潮的段落后,情节急转直下变得乏善可陈。如果说,《三国演义》从关云长走麦城开始变得缺乏精彩是因为历史的真实走向约束的话,那么《水浒传》梁山中好汉排完座次也只好被金圣叹腰斩、《金瓶梅》自西门庆死亡始味同嚼蜡、《红楼梦》在“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后读来倍感寂寞、《歧路灯》则从“讼师婉言劝绍闻 奴仆背主投济宁 ”起全无起伏跌宕、《西游记》更是为凑足九九80一难后期大量雷同与近似、而《儒林外史》因为就是由人物串联起来的短篇小说集,完全不能归类为长篇小说。从这些经典明清古典长篇小说的普遍现象看,虎头蛇尾成为共性,其原因值得探讨。
二、作家自身原因造成
我们探究造成中国明清古典长篇小说普遍表现出虎头蛇尾的现象的原因,从作家创作的角度进行分析,可以看到作家自身原因有二:
一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在唐朝以前虽然也有可以称为小说的文学作品,但主要都是简短的笔记小说类型,基本上没有描写的。而到了唐代,特别是到了中唐时期,开始出现了有意识的小说创作,同时有了比较细致的描写。可以说,这个时候算是中国小说的成立期。到了宋元时期小说的主要构成是话本,这是中国古典通俗小说的发端和基础。但,毫无疑问的,由于话本来源于民间的说唱,必然要迎合不同演出时不同观众的爱好和需要,随着每次演出而有不同的演变,从整体结构上就必然难以形成十分规范的版本。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到明清时期,文人创作的长篇小说应该说还是刚刚诞生不久,既没有可学习借鉴的先例,又非中国文化的正统,加上创作本身素材来源没有比较规范的范本。作家在没有经验和先前的范例的情况下,把握一百回左右的作品从能力上来说是比较吃力的。同时,创作上受到话本演出的影响,用故事的起伏跌宕来追求对读者的吸引力,同时又难以摆脱作者中国知识分子修齐治平的正统思想制约,体现在作品中,在叛逆和正统直接反复摇摆,最后由主观期待回归所谓理想结局也就成为必然。但是,这所谓理想结局,常常是作家们缺乏客观生活作为依托的,于是便从创作上表现为空洞、不真实、没有生活。而这样的结局,成为蛇尾也就成为必然。
二是作家个人生活经历带来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追求,并不是要成为一个有名望的小说家,“修齐治平”才是每一位知识分子的理想,是他们毕生奋斗的目标。因此,读书致仕便成为知识分子的必然选择。我们仔细观察明清小说家的生平,这其中无论是吴敬梓还是蒲松龄,亦或是曹雪芹,从这些人中我们会发现一个比较普遍的规律:官场失意、屡试不第、家族破败、穷困潦倒……这几乎成了明清时期多数著名小说家的生活写照。最典型的表现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和《歧路灯》作者李绿园。一位是生活潦倒另一位是奔波劳碌。
我们看看曹雪芹的晚年:曹雪芹48岁的时候,他的幼子患病,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几乎没有药物可以治疗,当然即使就算是有药物,以曹雪芹的贫困状况他也买不起,于是幼子去世了,随后他自己也患病不起,同样因为贫困没有钱看病,最后同样没有熬过去,也去世了。
我们再看《歧路灯》的作者李绿园,他的生平似乎要相对好一些,但有最终未能博得春官一第,这是他认为的终身之憾。乾隆十三年(1748年),李绿园的父亲去世,葬父后守制在家。这时他已经到了不惑之年,对世情的练达阅历已经完全可以代替了当初少年时代的壮志豪情。虽然在科举仕途名上不如意,但毕竟是在他这一代,通过他的努力,把一个普通农村读书人家庭,提高到乡绅的地位。所以他没有和他同时代的吴敬梓、曹雪芹那种因家道败落而对现实产生的愤懑,仍寄希望于封建纲纪伦常的复归,这在他的小说中有着十分明显的体现。从资料上看,大约到了50岁时李绿园已写完了《歧路灯》的前80回。50岁以后,“以舟车海内,辍笔二十年”,李绿园开始了他的游宦生活。20年中,他到过全国很多地方。一直到了老年,他才把《歧路灯》续写完毕,而这一段时期的停顿,毫无疑问地影响了作品的连贯性,使小说前后风格、艺术水准、甚至主题思想等都出现了明显的偏差。出现“七十二回的宿命”的虎头蛇尾现象也就很好理解了。
三、传统大团圆审美习惯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习惯是大团圆结局,目的是给人寄予希望。而如果小说的结局是悲剧的,则不符合这一审美习惯。由于这一的审美习惯,使得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不惜牺牲事物发展规律、作品的意境和思想高度、悲剧的艺术震撼力量,而追求完美的大团圆结局。
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从其故事来源来看,目前比较公认的是来自宋元话本以及接受了元以来的戏剧演绎的影响,加之正史史籍的历史事件内容的提供。如果说,以上这些来源,仅仅为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提供了故事的内容的话,明显是有着一定偏颇的。我们必须看到,以上这些来源,同时还为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传递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习惯,这就是大团圆结局的审美特点。
从中国正史史籍来源看,比较典型的是《三国演义》和《东周列国志》,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三国演义》的以“荐杜预老将献新谋 降孙皓三分归一统”为结局,还是《东周列国志》的以“兼六国混一舆图 号始皇建立郡县”为结局,无不是选择了最后统一的大团圆结局。如果说,选择统一大团圆作为历史小说的结局是因为历史发展的脉络如此的话,那么我们再看神魔小说《西游记》和《封神演义》的结局:无论是“径回东土 五圣成真”还是“ 周天子分封列国”同样也都是大团圆的美好收尾。我们再来看看英雄小说《水浒传》、以及更明显有着文人创作特征的世情小说《金瓶梅》《红楼梦》《歧路灯》的结局:《水浒传》是“宋公明神聚蓼儿洼 徽宗帝梦游梁山泊”,而《金瓶梅》《红楼梦》《歧路灯》则分别告诉我们了“韩爱姐路遇二捣鬼 普静师幻度孝哥儿”“甄士隐详说太虚情 贾雨村归结红楼梦”“薛全淑洞房花烛 谭篑初金榜题名”。虽然是普静师幻度,但也让孝哥儿得到了善果;同样的,甄士隐详说、贾雨村归结的是沐皇恩贾家延世泽;而更进一步的则是薛全淑洞房花烛谭篑初金榜题名的辉煌。好了,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长篇小说,无不是大团圆类型的结局。
我们知道,由于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故事来源主要是宋元话本以及接受了元以来的戏剧对传说、正史的演绎,而话本和戏剧又必须是通过表演来完成。这就要求话本和戏剧必须符合现场观众的审美心理需求:舞台呈现最基础的是不能让观众感觉到生理不适。于是,“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基于这样的文化传承和审美需求,中国古典小说普遍以大团圆结尾也就很容易理解了。但是,很显然的,这样的大团圆结局往往是理想化的而与现实生活距离相对比较远,同时也忽略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于是,小说的创作者们由于缺乏生活,加之那样一个长篇小说刚刚诞生不久,作家们还普遍缺乏提炼生活的能力和技巧的时代,这样理想化的结局描写起来就难免辞藻匮乏、人物干瘪、故事呆板了。与小说的前半部来源于现实生活的活生生的故事比较起来,必然是虎头蛇尾了。因此,大团圆的审美需求,也就导致了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七十二回的宿命”。对此,我们也就很好理解了。
四、文以载道创作观念的必然结果
中国文化的另一个重要传统是文以载道。即使是作为正统文化观念里的“异类”的小说创作,作家也一样在内心深处保持着教化社会、文以载道的理想和使命。因此无论是选择了什么题材、主人公如何叛逆异类,但最终都要回归到文化的正统上来。《三国演义》要三分归一统来结束;《水浒传》要接受招安为国尽力;《西游记》历经磨难各自成佛;《红楼梦》叔侄同科;《歧路灯》金榜题名;即使是《金瓶梅》,无法让人物转变成正面形象,也要通过因果轮回惩罚恶人从而警戒世人善恶有报。
中国的知识分子自春秋战国时期以来,一直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传统。虽然在春秋战国时期,在思想上是百家争鸣的文化局面,但无论是哪一家的学说,无不是思考着富民强国的问题,提供着国家治理的建议和观点,达则兼善天下的理念成为知识分子们自觉的行动。而到了汉代独尊儒术之后,修齐治平的思想更是在知识分子中深入人心。至于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的诞生,国家统治者更是将天下英才招揽到了统治阶层的体系之中,于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这样的时候,加上统治者在思想上的有意识地引导,由知识分子提出文以载道的文学主张也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现象了。
我们知道,明清时期的中国古典长篇小说,虽然在当时的统治思想观念下不是文学的主流,但毕竟完成创作的是生长在这样文化环境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其身上,也就同样必然地会深深地烙印着文以载道的文化传统,他们同样渴望通过其创作的小说来兼善天下,传递他们的教化社会的理念。正是在这样的创作思想指导下,这个时代作家们创作出来的古典长篇小说的形象与故事,即使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地大闹了天宫,最后不得不被“逼上梁山”从而导致下人们“拐财远遁、欺主背恩”。但作家们的主观上仍然还要由“普静师幻度”来讲述无论是“三分归一统”“神聚蓼儿洼”“五圣成真”还是“中乡魁延世泽”亦或是“洞房花烛金榜题名”都在这“详说太虚情”的过程中,告诉我们了因果轮回的必然和善恶有报的正统。既警告了世人不走正途的话,所得来的一切不过是红楼一梦,同时又为大家点燃了指出歧路的明灯。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文以载道的创作立意。但即使这样的主观立意已经在创作过程中削弱了作品的艺术水准,却仍然在文以载道的正统理念下受到诟病,就如鳞耧子在《林兰香》序中的批评:“《林兰香》一部,……其立局命意,俱见于开卷自叙之中,既不及贬,亦不及褒。所爱者,有《三国》之计谋,而未邻于谲诡:有《水浒》之放浪,而未流于猖狂:有《西游》之鬼神,而未出于荒诞:有《金瓶》之粉腻,而未及于妖淫……今《林兰香》师四家之正,戒四家之邪”。
因此,在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创作过程中,文以载道的正统思想一直在左右着创作的方向。这种影响是深刻的,其直接带来的后果是:无论故事情节、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如何,客观变化的规律和方向应该如何,作品都必须符合最后达到劝诫世人要符合统治思想的要求,符合社会“正统”观念的方向上了,哪怕这样的发展方向会破坏了小说的艺术魅力和文学作品内在发展的必然逻辑。也恰恰是由于作家们过分追求文以载道、符合正统思想的这个缘故,从而导致了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普遍存在着虎头蛇尾的现象,形成了“七十二回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