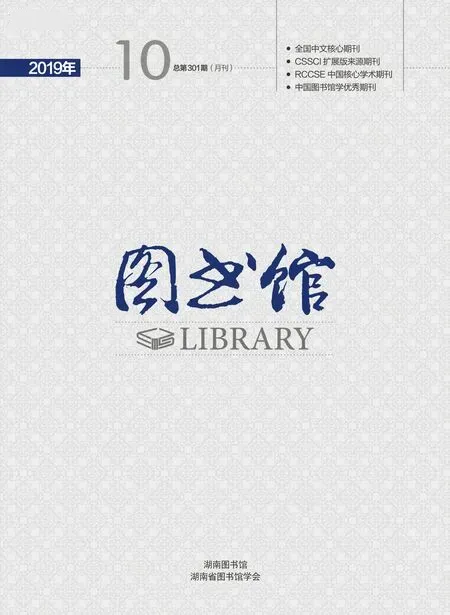论古代中国人的治学智慧(下)
蒋永福
(黑龙江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8 学有所序:治学之次
众所周知,朱熹总结的六条读书法中,第二条就是“循序渐进”,其中所言“序”,即读书治学之次序。学有所序,其理古今无异,然所序内容和方法,却古今有异。中国古人所言治学之序,大体有始终之序、时间之序和内容之序。
始终之序,即治学之起点(始)到结果(终)的先后推进过程。《荀子·劝学》云:“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荀子认为,从方法上说,治学应从诵读《书经》《诗经》等经典开始,最终以读《礼》而明礼为止,这是荀子“隆礼”观点的必然要求;从境界变化上说,学者应该通过治学达到由“士人”转变为“圣人”的目标,这是中国古人普遍持有的“学以成圣”理想的必然要求。宋人王然在《黄岩劝学文》中总结前人之说云:“孔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扬子曰:‘威仪文辞,表也。德行忠信,里也。’此学之先后也。孟子曰:‘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荀子曰:‘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此学之始终也。”[1]王然在这里明确了“学之先后”和“学之始终”的内涵,其意是说:学者应该首先学孝、悌、忠、信或者仁、义、礼、智之“礼学”之理,最终达到“成圣”的理想目标。仔细分析荀子与王然的上述言说,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的言说其实与“修己以治人”“修齐治平”以及庄子所言“内圣外王”之序并无二致。总而言之,他们都在强调“德礼为先”的儒家伦理观和“学以成圣”的理想治学观。
关于读书治学的时间安排问题,有的人强调早学为宜,有的人强调具体读书时间的安排,有的人强调“速读”之危害,有的人强调读书时间的年龄分段安排等等。“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为政者玩岁而愒日,则治不成。为学者日迈而月征,则身将老矣。……故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善。’”[2]23-24这是在说一个人的学习要从小“及时”而学,勿待老迈;就一天的学习而言,也要“鸡鸣而起”,早起早学。薛瑄心有体会地说:“晚间诵书,愈数而不能诵,……晚间多不能记者,气昏也;早间能背诵者,气清也”[3]1064,这是薛瑄自己感受到的早晨读书和晚上读书效果不同的经验总结。利用什么时间读书?对此,三国时期的董遇总结出了“三余读书法”,即“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4],在董遇看来,除了工作和生活所需的劳作时间外,其他时间都可用于读书。
关于读书治学的速度,中国古人大多极其反对“速读”“速成”。“学欲速不得,然亦不可怠。才有欲速之心,便不是学。学是至广大的事,岂可以迫切之心为之”[5]189,这是在说治学要只争朝夕但不可求速成。“读书不寻思,如迅风飞鸟之过前,响绝影灭,亦不知圣贤所言为何事”[3]1050,这是在说,读书是需要思考的,而思考又是需要时间的,缺乏思考的速读,必然带来读而不解或解而不精的后果。因此,陆九渊告诫他人说:“读书之法,须是平平淡淡去看,仔细玩味,不可草草。所谓优而柔之,厌而饫之,自然有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的道理。”[6]432
据《新唐书·选举志》记载,唐朝为了满足科举考试需要,曾制定有考生的年龄要求以及应读书目及其时间规定:考生须在十四岁以上至十九岁以下之间,考律学生须在十八岁以上至二十五岁以下之间;《礼记》《左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尚书》《公羊传》《穀梁传》为小经;《孝经》《论语》必兼通且一年内完成,《尚书》《公羊传》《穀梁传》各一年半完成,《易》《诗》《周礼》《仪礼》各二年完成,《礼记》《左传》各三年完成;须读小学类书,《石经》三体限三年,《说文》限二年,《字林》限一年;另读算学书若干种各若干年。这种规定,用现代的话来说如若“高考指南”,然而在古代科举制下俨然成为一种权威性的为学之序。
真正对学者产生广泛影响的为学之序法,是元代学者程瑞礼编修的《读书分年日程》(亦称《读书工程》)。据《元史·儒学传二》载,程瑞礼“所著《读书工程》,国子监以颁示群邑校官,为学者式”。程氏的《读书分年日程》把青少年教育分为启蒙教育、小学教育和成人教育三个阶段,分别制定的读书范围及其次序为:八岁以前读《性理字训》;八岁至十五岁期间的阅读书目次序是小学书正文→《大学》经传正文→《论语》正文→《孟子》正文→《中庸》正文→《孝经》刊误→《易》正文→《书》正文→《诗》正文→《仪礼》并《礼记》正文→《周礼》正文→《春秋经》并《三传》正文;十五岁至二十岁期间的阅读书目次序是《大学章句或问》→《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中庸章句》→钞读《论语或问》之合于集注者→钞读《孟子或问》之合于集注者→本经→钞读《周易》→钞读《尚书》→钞读《诗》→钞读《礼记》→钞读《春秋》。以上是经书的阅读次序。此外,程氏又列出了读其他书的次序:先读《通鉴》,次读韩文,次读《离骚》,次学作文。关于这些书的阅读方法,程瑞礼完全按照朱熹的读书六法提出了时间和用功方面的详细要求;最后还设计有日程记录簿样式,称“日程空眼簿式”[7]。综观《读书分年日程》,有三方面的特点:一是该《日程》为我国第一部完整的有关读书日程、阅读之序的专书,有开创之功;二是该《日程》为我国第一部配有日程的导读书目,亦有开创之功;三是该《日程》作为“为学者式”的导读书目,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其影响之巨,其他导读书目不可同日而语;四是从所列书目看,该《日程》可称为“儒家经典阅读书目”,亦即该《日程》可视为以经书为重点的阅读程式,其他方面的书籍基本未涉及(只提有《通鉴》、韩文和《离骚》),尤其是根本没有提及子书的阅读方法,这是它的局限性所在。
陆世仪把读书的时间之序和内容之序合而言之,提出了分三个年龄段读书的“三个十年读书法”:第一个十年为五岁至十五岁,称“十年诵读”阶段,这一阶段读小学、四书、五经、《周礼》《太极通书》《西铭》《纲目》、古文、古诗、各家歌诀;第二个十年为十五岁至二十五岁,称“十年讲贯”阶段,这一阶段读四书、五经、《周礼》《性理》《纲目》、本朝事实、本朝典礼、本朝律令、《文献通考》《大学衍义》及其《衍义补》、天文书、地理书、水利农田书、兵法书、古文、古诗;第三个十年为二十五岁至三十五岁,称“十年涉猎”阶段,这一阶段读四书、五经、《周礼》、诸儒语录、二十一史、本朝实录及典礼律令诸书、诸家经济类书、诸家天文、诸家地理、诸家水利农田书、诸家兵法、诸家古文、诸家诗。所列书目中有重复者,均有不同的解释,即书名虽同,但要求各不同。对所列书目,陆世仪作出总说明云:“以上诸书,力能兼者兼之,力不能兼,则略其‘涉猎’,而专其‘讲贯’;又不然,则去其诗文;其余‘经济’中,或专习一家。其余则断断在所必读。”[8]45-48综观陆世仪的“三个十年读书法”之内容,有三方面的特点:一是时间之序与内容之序一一对应,什么年龄段读什么书,以及先读什么、后读什么,让人一目了然;二是与程瑞礼《读书分年日程》不同的是,所列书目内容广泛,经、史、子、集无所不包,尤其是包括天文、地理、兵、农、经济、政典等,体现了博学与经世致用精神;三是必读与选读相资,可兼与可略自选,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特点。当然,其中亦有令人不解之处,如有兵、农之书,为何没有医书和艺术之书?我们提出此类疑问,出于实事求是的评价,而非苛责古人。总之,瑕不掩瑜,陆世仪的“三个十年读书法”仍然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之处。
说到读书次序,还应提及清康熙年间李来章为南阳书院制定的《读书次序》。该《读书次序》以小学、孝经、四书、礼记、周礼、仪礼、诗经、书经、春秋、易经、史部、文部十二类为次第,共列有57种推荐阅读书目[9]198-200。该书目的特点在于:每种书不仅有书名和作者,而且还撰有提要;提要中不仅介绍书之内容梗概,而且还有导读之语,如“学者必兼揽之”“学者宜择而读之”“学者读之,最有裨于身心”等等。这种提要式推荐书目(亦可称为导读书目),在中国古代并不多见。
关于学有所序的思想,中国古人所论甚多。以四书的阅读之序而言,朱熹认为应先读《大学》,后读《论》《孟》《中庸》,因为《大学》是“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10]。显然,朱熹的论据在于《大学》开篇所言“明明德”之大学之道。明末清初的胡承诺也认为,“《大学》最为门户,其余未尽之理,散在诸书中者,缘此求之,即能深入其奥。”[11]而程颐则认为,“学者先须读《论》《孟》,……以此观他经,甚省力”,因为《论》《孟》“如同丈尺权衡”,以此观察事物无不明[5]205。到底以《大学》为先,还是以《论》《孟》为先,这恐怕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不可一概而论。
大体而言,“经史为先,以时为序”是中国古人普遍遵循的为学之序。此故,万斯同在《与钱汉臣书》中云:“儒者读书必有先后,当先经而后史,先经史而后文集。就文集而论,当先秦汉而后唐宋,先唐宋而后元明,此不易之序也。……若乃先文集而后经史,先元明而后唐宋、秦汉,则是得流而忘源也。”从实际情况而言,读书首先是一种个体行为,个体情况千差万别,书亦种类繁多,故读书不应有固定不变的次序,应因人而异、因书而异、因需而异。所以唐彪说:“有当读之书,有当熟读之书,有当看之书,有当再三细看之书,有必当备以资查之书。书既有正有闲,而正经之中,有精粗高下,有急需不急需之异,故有五等分别也。学者苟不分别当读何书,当熟读何书,当看者何书,当熟看者何书,则工夫缓急先后俱误矣。至于当备考之书,苟不备之,则无以查考,学问知识何以而长哉!”[12]7应该说,唐彪的这种因书而异、因需而异的读书之序观有其客观合理性。
清末张之洞所编(缪荃孙等助编)的《书目答问》,亦可称为为学之序型导读书目。关于《书目答问》的编修体例、内容及其社会影响,后人所论甚多,故在此不赘述。晚于张之洞《书目答问》者,则有康有为的《桂学答问》和梁启超的《读书分月课程》。梁启超的《读书分月课程》是在康有为《桂学答问》的基础上根据康有为的授意而编的,其中“最初应读之书”部分分经学书、史学书、子学书、理学书、西学书五类,分别列出应读书目及其次第。综观该《课程》,分类有序,次第分明,有些书名下还有简单的附注或说明;在“读书次第表”中还列有按照“朝经暮史,昼子夜集”之法分六个月完成的阅读课程表,可视为初学者简易实用的导读书目及其功课之序[13]。然该《课程》编撰时间为1892年,此时清王朝乃至几千年封建王朝行将寿终正寝之际,加之新学思潮涌动,所以该《课程》几乎未能产生实际的社会影响。
9 涵泳自得:治学之要
学有所得,当然是治学的鹄的所在。学有所得之“得”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实践论意义上的“外得”,即将所学知识用于实践所得的实际效果;一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内得”,亦称“自得”“思得”“悟得”,即通过学习所得到的领悟、知晓、愉悦、通达等心智进步和成熟之感受。当然,外得须以内得为前提,但外得不等于内得,因为在内得中总是会有不宜外化或不能外化的因素。关于“外得”,文章在第3部分“经世致用”中已有较多论及,故在此不论。
那么,如何做到学有所得,或者说如何做到学有所得的最大化?对此中国古人有一个普遍共识,这就是涵泳自得。朱熹读书六法中的“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这三法,其实完全可以用“涵泳自得”来概括。涵泳是自得的过程,自得是涵泳的结果,合而言之称“涵泳自得”。
何谓涵泳?对此曾国藩曾有精辟入理的解释:“涵泳二字,最不易识。余尝以意测之曰:涵者,如春雨之润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润花,过小则难透,过大则离披,适中则涵濡而滋液。清渠之溉稻,过小则枯槁,过多则伤涝,适中则涵养而浡兴。泳者,如鱼之游水,如人之濯足。程子谓鱼跃于渊,活泼泼地。庄子言濠梁观鱼,安知非乐?此鱼水之快也。左太冲有‘濯足万里流’之句,苏子瞻有夜卧濯足诗、有浴罢诗,亦人性乐水者之一快也。善读书者,须视书如水,而视此心如花、如稻、如鱼、如濯足,则涵泳二字,庶可得之于意言之表。”[14]692其实,对读书治学而言,所谓涵泳,就是指在自由无拘的心境下对书中之意慢慢咀嚼思考的过程。一句话,聚精深思的过程就是涵泳。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涵泳是“学—思—悟”三者融会贯通的过程。宋人晁说之有言:“为学之道,必本于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不深思则不能造于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15]102-103韩愈称自己思考问题时“口詠其言,心惟其义”[16]223,这里的“心惟其义”就是涵泳深思的意思。张载说“学贵心悟”[17]274,而悟由思出,故陆陇其言“悟处皆出于思,不思无由得悟。……学者,所以求悟也”[15]113。再好的书,若无涵泳深思之功,便不能有自得之益,诚如张载所言“《论》《孟》二书于学者大足,只是须涵泳”[17]272;二程亦言为学“苟不自得,则尽治五经,亦是空言”[5]2;胡居仁指出,学者“立志已定,用功不差,潜心积虑之久,义理自当融会”[18]31。胡居仁这里所言“潜心积虑之久”,实际上就是涵泳思虑的过程。涵泳不仅是理解的过程,而且还是知识的增长和更新过程。方以智在《通雅》卷首中云“学以收其所积之智也,日新其故,其故愈新,是在自得,非可袭掩”[19]230。方以智的意思是说,学习是为了吸收前人积累的智慧,每天用新的知识来充实自己或更新原有旧的知识结构,这样原有的知识结构通过吐故纳新而获得新生,这种充实和更新就是最大的涵泳自得,这不是能用抄袭和照搬得来的。
涵泳自得的过程,是一个挺立主体性的过程,是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过程,所以涵泳自得是一种“个体主义方法论”。对读书治学而言,涵泳自得的主体是具体的读书者,每一个读书者都要自己完成涵泳自得的过程,他人不可替代。这一点对现代教育活动有重要启发。现代教育把学生视为集合论意义上的“众生”或“群体”,用统一的模式(如统一的教材、统一的教学方法、统一的试卷、统一的分数等)不加区别地加以灌输,丝毫不顾学生个体的主观感受,因而无助于发挥学生个体的主观能动性。这种教育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大多只具千人一面的“集体相”而鲜有充满创新活力的“个体相”。读书治学首先是一种个体行为,应该允许“我读故我在”的主体性、个体性空间的存在,应该把阅读的主动权交给读者,使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他人只能引导而不得强制。朱熹看出了此一道理,所以他指导学生说:“事事都用你自去理会,自去体察,自去涵养。书用你自去读,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个引路的人,做得个证明的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20]223这里朱熹说得很清楚,在学与教的关系上,教师只是“引路的人”“证明的人”“同商量的人”,而不是干涉或强制学生读书治学的人。可见,朱熹是一个懂得“学生为主体,教师为引导”之教育理念的人。
关于自得,黄宗羲有一段话说得很透彻,其云:“或问:如何学可谓之有得?曰:大凡学问,闻之知之皆不为得,得者须默识心通。学者欲有所得,须是笃,诚意烛理。……学莫贵于自得,非在外也,故曰自得。”[21]黄宗羲的这一段话,至少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闻之知之”都不算自得,只有“默识心通”才算自得,即感官感知者不算自得,只有达到心领神会者才算自得;第二,自得以“笃”“诚”为意志基础,即必须要有心无旁骛的专心深思,才能达致自得的境界;第三,自得是一种内心深处的自我领悟,是他人无法感受、无法替代的个体主观性把握,故称“非在外也”。清人袁枚《遗怀杂诗》云“书味在胸中,等于饮陈酒”,酒之味只有饮者自知,书之味只有读者自知。这种独一无二的“自知”,就是自得的“独知性”特征所在。
自得的这种主体性、主观性、独知性特征,要求读书者一定要避免“书自书,我自我”这种书我分离情况的出现。把书之所言纳入到我的主观世界之中加以融会贯通,才能最终形成自得的效果。所以中国古人强调,读书一定要“切己体察”,从自家身心出发去理解书中所言之义。这就是书我合一的读书法。对此,薛瑄在《读书录》中不厌其烦地予以强调,如其言“读书当因其言以求其所言之实理于吾身心,可也,不然,则滞于言语,而不能有以自觉矣”[3]1031;“惟精心寻思,体贴向身心事物上来反覆考验其理,则知圣贤之书,一字一句皆有用矣”[3]1056;“读书不体贴向自家身心上作工夫,虽尽读古今天下之书无益也。”[3]1511同时,薛瑄还指出寻思自得是一种慢工夫,急躁、粗心不得,他说:“凡读书必虚心定气,缓声以诵之,则可以密察其意;若心杂气粗,急声以诵之,真村学小儿读诵斗高声,又岂能识其旨趣之所在耶?……观书惟宁静、宽徐、缜密,则心入其中而可得其妙;若躁扰、褊急、粗略以求之,所谓‘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者也,焉足以得奇妙乎?”[3]1054陆九渊用一首诗告诫学生说“读书切戒在慌忙,涵泳工夫兴味长”[6]408。
涵泳自得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通过涵泳自得的东西不易忘掉。用诠释论的语言说,涵泳自得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理解文本之义的过程,而理解文本之义的过程有时需要付出冥思苦想的艰难脑力劳动,经过这种艰难过程得到的东西就不易忘掉。所以,魏源言“学问之道,其得之不难者,失之必易;惟艰难以得之者,斯能兢业以守之”[22]18。
需要指出的是,强调自得的主观性,并不表明读书解义可以天马行空、无所依循、唯我独尊。主观性不等于任意性,自得不等于自以为是。戴震说,学者“其得于学,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23]186。戴震所言“自蔽”中,应该包括读书者毫无遵循、自以为是的过度的主观性、任意性之弊端。好自以为是,是过度主观的表现之一,对此胡承诺批评说,一些人“只见己是,只见人非”,主观意见“一经先入,牢不可破,……于他人有用之言,必不留意,纵然属目,终是己见为主”[11]11。在中国古代,有很多对好自以为是、好为人师、以偏概全者的嘲讽之文,如《庄子》中的“望洋兴叹”故事、唐人李肇所讲“王积薪闻棋”的故事、欧阳修《卖油翁》中的“康肃炫射被取笑”的故事、《大般涅磐经》中的“盲人摸象”故事、韩愈《日喻》中的“盲者误识日”故事等等。
10 以学为乐:治学之趣
如果说“学以明道”是治学之旨,那么“以学为乐”则是治学之趣。孔子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知道“学以明道”为治学之旨的人,可称为“知之者”;对读书治学感兴趣的人,可称为“好之者”;从内心里“以学为乐”的人,则可称为“乐之者”。可见,治学是有旨有趣的事情。文章之所以把“学以明道”置于首而把“以学为乐”置于末,就是为了前后呼应,即旨与趣遥相呼应。
孟子言“乐则生矣”(《孟子·离娄上》),中国古人深明此理。求乐或以乐为生甚至以苦为乐,是儒家和道家共同追求的人生目标。李泽厚认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特征之一是“乐感文化”[24],这与西方基督教之“罪感文化”形成鲜明对照。“乐感文化”不仅造就了中国古人安贫乐道的道德理性精神,而且还由此塑造出了中国文人的读书为乐、以学为乐的治学精神。陶渊明有诗云:“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这是一首田园读书诗,在草、树、鸟、风、雨和耕、庐、酒、蔬构成的自然田园中“读我书”,悠哉悠哉,其乐无穷。这种毫无外在压力和诱惑即毫无功利取向的读书,已经完全融入到自然和生活之中,其自由自在境界,令人向往。
说到田园读书诗,我们又自然想起宋末翁森的《四时读书乐》。这是一首组诗,分春、夏、秋、冬四阕,结合四季风景描写读书之乐,因文长不能全录,这里只引每阕最后一句:“读书之乐乐何如,绿满窗前草不除”“读书之乐乐无穷,瑶琴一曲来熏风”“读书之乐乐陶陶,起弄明月霜天高”“读书之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地心”。
如果说陶渊明、翁森的田园读书只能是一种理想,那么欧阳修则把现实中的伏案读书和思索过程完全当作独享的快乐感受。欧阳修有一首自传体长篇诗《读书》,现节录两段:“吾生本寒儒,老尚把书卷。眼力虽已疲,心意殊未倦。正经首唐虞,伪说起秦汉。篇章异句读,解诂及笺传。是非自相攻,去取在勇断。初如两军交,乘胜方酣战。当其旗鼓催,不觉人马汗。至哉天下乐,终日在几案。”“古人重温故,官事幸有间。乃知读书勤,其乐固无限。少而干禄利,老用忘忧患。……纷华暂时好,俯仰浮云散。淡泊味愈长,始终殊不变。”[25]前一段主要描写自己至老手不释卷,在章句、解诂、笺传过程中“去取勇断”“不觉人马汗”的快乐感受;后一段描写利用官事间隙勤奋阅读古书忘却了利禄与忧患,以及淡泊之志不变所带来的“其乐无限”之情。欧阳修的感受是现实的、实在的、发自内心的,“读书本乐事”的超然境界,在欧阳修身上表现无遗。
王阳明的弟子、“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则把“读书本乐事”发挥到极致,干脆把学与乐等同起来,其《乐学歌》云:“人心本自乐,自将私欲缚。……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乐是学,学是乐。”这就把“乐”提高到学之本体的高度了,亦即学必乐、不乐非学!这当然是“以心为体”、排除一切心外之物的心学之乐,从中不难看出王艮皈依陆王“心即理”之思想理路。特立独行的李贽作《读书乐》诗云:“……世间何窄,方册何宽!千圣万贤,与公何冤!……死者是身,朽者是骨。此独不朽,原与偕殁;倚啸丛中,声震林鹘。歌哭相从,其乐无穷!寸阴可惜,曷敢从容!”这首诗充分表达了李贽以读书为战斗、以文为枪械、以“声震林鹘”为快乐的豪迈气概,这与王艮把学之乐囿于心内“自乐”的狭隘之乐完全有别。
无论是陶渊明、翁森、欧阳修,还是王艮、李贽,在现实中像他们这样超脱或独行的人是不多的。对大部分人而言,以学为乐是从学有所得、学有进步的感受中体悟出来的。“致知格物,于读书得之者多”[3]1485,在读书中“得之者多”,自然让人乐此不疲。苏辙有诗云:“人生不读书,空洞一无有。……顾念今所知,颇觉前日陋。我家亦多书,早岁尝窃叩。晨耕挂牛角,夜烛借邻牖。经年谢宾客,饥坐失昏昼。堆胸稍蟠屈,落笔逢左右。乐如听钧天,醉剧饮醇酎。”[26]168-169读书能够带来从“颇觉前日陋”到“落笔逢左右”的效果,自然乐从中出。薛瑄充分意识到此乐之贵,故其云:“万金之富,不以易吾一日读书之乐也。外物之味,久则可厌;读书之味,愈久愈深,而不知厌也。”[3]1069
有的人特别喜欢读某种书或某类书,此亦为读书之乐的应有之义。众所周知,金圣叹酷爱《水浒》,故其云:“天下之乐,第一莫若读书;读书之乐,第一莫若读《水浒》。”[27]我们知道,《水浒》《西厢记》都曾被列为“禁书”,但金圣叹偏偏喜欢读此类“才子书”。针对《西厢记》,金圣叹在《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中云:“《西厢记》断断不是淫书,断断是妙文。……文者见之谓之文,淫者见之谓之淫耳。”这里金圣叹道出了现代诠释学所讲“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之喻。其实,在史书所记和小说所描写的人物中,有不少人物的命运是悲惨的,所述“厚黑”现象是令人可怒的,但是只要记述有方、描写感人,读者就能产生共鸣,就能转怒为乐,所以张潮说“读书最乐,若读史书则喜少怒多,究之,怒处亦乐处也”[14]163。曾国藩曾把诗文趣味分为“诙诡之趣”和“闲适之趣”两类。对于具有闲适之趣的诗文,曾国藩认为韦应物、孟浩然、白居易、傅山之诗和柳宗元的游记之文“极闲适”,而他自己尤其喜欢陶渊明的五言古诗、杜甫的五言律诗、陆游的七言绝句,且称读这些人的诗所得之乐“虽南面王不以易其乐也”[34]2267。可见,曾国藩读书也是有其偏爱之趣的。有的人喜欢读某些书达到“百读不厌”的程度,如清人顾天石云“惟《左传》《楚辞》、马、班、杜、韩之诗文,及《水浒》《西厢》《还魂》等书,虽读百遍不厌”[28]201。“百读不厌”,说明其乐无穷。这种偏爱之乐,其实人皆有之,只不过所偏内容和程度有所不同而已;只要这种偏爱之乐不致于“着火入魔”“执迷不悟”的程度,即可视为正常的读书之乐。不过,在中国古人的思想观念中,这种偏爱之乐应该有所选择,即所偏之向在“正道”则可,反之则不可。对此薛瑄分析云:“岂独乐有雅郑邪?书亦有之。小学,四书,六经,濂、洛、关、闽诸圣贤之书,雅也,嗜者少也,何故?以其味之澹也。百家小说、淫辞绮语、怪诞不经之书,郑也,莫不喜谈而乐道之,盖不待教督而好之者矣,夫何故?以其味之甘也。澹则人心平面而天理存,甘则人心迷而人欲肆。是其得失之归,亦何异于乐之感人也哉!”[3]1519薛瑄此话是站在程朱理学的立场上而言的,有其压抑人性的纲常伦理之局限性,但他把书之味分为“澹”“甘”之别且提醒人们慎重选择而不要“误入歧途”的告诫是有一定道理的。
读书不应关起门来一味地“闭门造车”,有时需要劳逸结合,有时也需要“换换头脑”,以期“他山之石”之攻。明人湛若水在《大科书堂训》一文中云:“诸生读书遇厌倦时,便不长进,不妨登玩山水,以适其性。《学记》有‘游焉’‘息焉’之说,所以使人乐学鼓舞而不倦,亦是一助精神。”读书间隙有所“游”或“息”,有助于消除厌倦之绪,因此这种“游”或“息”是一种“助精神”之良法。陆世仪亦曾说:“晦庵(晦庵为朱熹之号——笔者注)诗有云:‘书册埋头何日了,不如抛却去寻春。’此晦庵著述之暇,游衍之诗也。凡人读书用工,或考索名物,或精究义理,至纷颐难通,或思路俱绝处,且放下书册,至空旷处游衍,以游衍,忽地思致触发,砉然中解,有不期然而然者,此穷理妙法。”[17]11著述之暇、读书之余,放下书册到空旷处游衍,即可以解疲倦,又可以在新鲜空气中沐浴身心、触发灵感,遂使思路“砉然中解”,岂不是“他山之石”之不请自到?这种读书方法,可称为“游衍读书法”,若用现代的话来说或许可称为“绿色读书法”。称为“游衍读书法”也好,称为“绿色读书法”也好,其实都属于“游乐读书法”——读书在游乐之中。
治学需要处理好“专心”与“闲适”的关系,亦要处理好“一意专深”与“变换角度”的关系。对此,章学诚曾以“荷担远程,屡易其肩”的道理予以说明,极富辨证性,现不嫌文长,引录于此:“夫学贵专门,识须坚定,皆是卓然直立,不可稍有游移者也。至功力所施,须与精神意趣相为浃洽,所谓乐则能生,不乐则不生也。昨年过镇江顺访刘端临教谕,自言颇用力于制数而未能有得,吾劝之以易意以求。夫用功不同,同期于道。学以致道,犹荷担以趣远程也,数休其力而屡易其肩,然后力有余而程可致也。功习之余,必静思以求其天倪,数休其力之谓也;求于制数,更端而究于文辞,反覆而穷于义理,循环不已,终期有得,屡易其肩之谓也。夫一尺之捶,日取其平,则终身用之不穷;专意一节,无所变计,趣固亦穷,而力亦易见绌也。”[29]92理解章学诚说的这段话的意思,需要把握以下几点:第一,治学如同荷担远程,需要屡易其肩,才能保证整个行程的平衡性和持续性;第二,所谓“屡易其肩”,包括“劳逸结合”“变换角度”等多方面含义;第三,治学要保持“易”与“不易”之间的循环协调,“不易”即“期于道”之志不变,“易”即方法途径的适时变换;第四,治学中的“休其力”是为了保持学之力的持续,“易其肩”是为了保持学之趣的不竭;第五,章学诚的整个这段话是以“乐则能生,不乐则不生”的原理为前提而论的,说明其言“休其力”和“易其肩”都是为了保证“学之所乐”。
11 结语
中国人在几千年文明旅程中积累有极其丰富的治学思想,这一思想遗产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热爱学习的优良传统,是这一思想遗产形成、积累和代代相传的深厚历史基础。在这一思想遗产中,闪烁着中华民族特有的智慧之光,照亮着历代学者的为学之路。通过上述可知,古代中国人的治学智慧,有旨有趣,有体有用,有方有法,有途有径,有要有次,涵盖治学活动的方方面面,且博而有约、散而有要。笔者把古代中国人极其丰富的治学智慧,梳理归纳为十大方面,不能说概括无遗,但可以说简约适中。中国古人的治学智慧,是在中国古人特有的生存环境、思维方式、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有其独特的思想特征和时代烙印。我们可以以古鉴今,但不可以以今论古、以古绳今。客观地说,古代中国人的治学思想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在这一思想遗产中所蕴含的“合理内核”及其智慧因素,是值得今人传承和发扬的。勿忘初心,方得始终。挖掘和梳理古代中国人的治学智慧,为今人治学提供借鉴和指导,是图书馆学、阅读学、文献学、教育学等学科研究的重要任务。
(来稿时间:201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