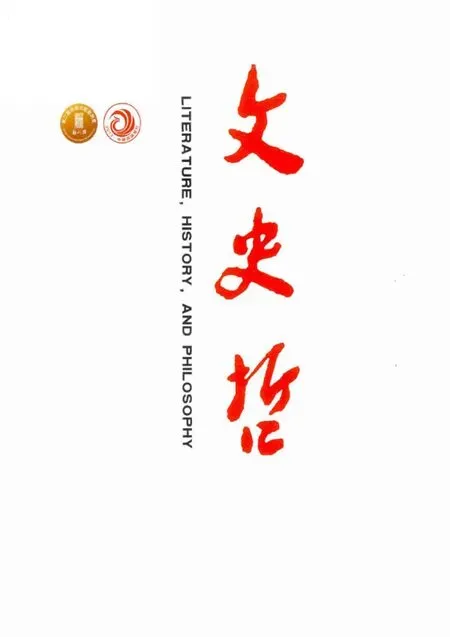“诗史”传统与晚明清初的乐府变运动
叶 晔
有关明末清初的“诗史”创作,我们最熟知的莫过于吴伟业的“梅村体”,以及相当数量的明遗民诗作。在以往的中国文学史之叙述中,吴伟业是唯一可与杜甫分享“诗史”荣誉的伟大诗人,“梅村体”也经常被拿来与中唐白居易、元稹的“长庆体”相比较,再加上以吴伟业为代表的娄东诗派,是清代宗唐诗风的最早倡导者与践行者之一,由此种种,给我们留下一个强有力的既成印象,即吴伟业的“梅村体”创作,主要是向唐代诗人学习,既吸收了《长恨歌》《琵琶行》《连昌宫词》等的“长庆体”写法,重在叙事,又辅以初唐四杰的文藻,温庭筠、李商隐的情韵。就算对明代文学的养料有所汲取,也是在文本结构上借鉴了明传奇中的多线叙事模式,而这已是不同文体之间的互动,并不是单一文体内部的成长。换句话说,在严格的诗学领域,其文学传统来自于唐代,而不是“诗必盛唐”的明代。这样的思路,总体来说没有问题,但对某一文学现象之传统的追溯,未免太强调本源(远传统)的重要性,而忽略了过往五十至一百年间尚可触摸的近代文学观(近传统)之于诗人创作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是用已成经典的唐诗之研究眼光看待明清诗歌,较少考虑到明清诗歌的自我运作机制是否有独立生长并发展出某一种新文学现象之可能。本文要探讨的“乐府变运动”,既是对晚明清初之重要文学现象的一次挖掘,也希望借此补上“梅村体”之近传统研究中的缺失一环。
文学现象以“运动”相称者,在中国文学史中并不多见,如唐宋古文运动、中唐新乐府运动、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等。归根到底,这些“运动”的称谓,都是民国以来的学术产物,新文化运动的所处时代虽然最晚,却是所有“文学运动”称谓的思想来源。在21世纪的学术语境中,继续用“运动”二字来描述文学世界中的重大潮流及变革,是否仍具有合理性,一直是笔者的困惑。但考虑到“运动”一词在当代学术话语中所包蕴的丰富内涵,以及可与中唐的新乐府运动形成文学史上的前后呼应关系,笔者还是决定采用“乐府变运动”这一概念,来概说晚明清初的新题乐府创作风气及相关诗学观念的递变。至于是否妥当,留待学界同仁批评。
笔者所称的“乐府变运动”,指以王世贞《乐府变》为肇端,从明嘉靖末年至清康熙初年,在诗坛兴起的一次以新题乐府为体式、以讽咏今事为宗旨、以“诗史”学说为理论纲领的创作潮流。据笔者统计,现存明确以“乐府变”“新乐府”“今乐府”“似乐府”“明乐府”等为题的作品,就有十数组,五百余篇;其他散见于作家别集中的反映重大历史事件和当代社会现实的新题乐府,亦数以百计。单从作家、作品的数量来看,其规模远超唐代的新乐府运动。但这一文学现象,一直以来未引起学界的关注,甚至连最基本的文献梳理工作,也尚未展开。除了王世贞《乐府变》[注]贾飞:《论王世贞的乐府诗及其“乐府变”的历史地位》,《江苏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在此之前,徐朔方、廖可斌、魏宏远、郦波等人的研究成果中,对《乐府变》有一定篇幅的论及。、“明史乐府”[注]朱端强:《万斯同〈明史新乐府〉选笺》,《西南古籍研究》,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日]児島弘一郎:《〈明史楽府〉序説——呉炎、潘檉章〈今楽府〉について》,《松浦友久博士追悼記念中国古典文学論集》,东京:研文出版,2006年;[日]児島弘一郎:《明清時代における〈連作詠史楽府〉——〈明史楽府〉を中心に》,《中国古籍流通学の確立》,东京:雄山閣出版,2007年;[日]児島弘一郎:《尤侗〈明史擬稿〉と〈擬明史楽府〉——史と詩のあいだ》,《中國詩文論叢》第27集,2008年;张煜:《万斯同〈新乐府〉对白居易〈新乐府〉的因革》,《乐府学》第4辑,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年;张煜:《吴炎、潘柽章新乐府研究》,《乐府学》第6辑,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年。有专题论文外,其他作家、作品的乐府学研究,基本上是一片空白。有鉴于此,本篇的主要目的,在梳理晚明清初之新题乐府创作的基本面貌,及其在诗学脉络上与杜甫新题乐府、白居易新乐府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结合明中叶以后日渐丰富的中国“诗史”传统,探究乐府变运动在晚明大变局及明清易代之际的文学史意义,及其与吴伟业“梅村体”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王世贞《乐府变》与晚明清初的新题乐府
所谓“乐府变”,典出王世贞的《乐府变》组诗二十二首。在此之前,历代新题乐府有“系乐府”“新乐府”“正乐府”“今乐府”诸别名,但未有以“变乐府”或“乐府变”相称者。王世贞自述嘉靖末“尝备皂衣西省,故时时闻北来事,意不能自已。偶有所纪,被之古声,以附于寺人、漆妇之末”[注]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二《乐府变》小序,《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第120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年,第144页。,则这组诗作于嘉靖四十年(1561)至隆庆元年(1567)家居时期。其诗歌本事,沈德潜《明诗别裁集》、陈田《明诗纪事》、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等有陆续考证[注]沈德潜:《明诗别裁集》卷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陈田:《明诗纪事》己签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第一卷《王世贞年谱·引论》,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既关涉严嵩、陆炳、仇鸾、赵文华等朝中显要,也涉及任环、曾铣、商大节、曹邦辅等忠臣义士,甚至还有对嘉靖间诸宗室丑闻的直白揭露。一言概之,嘉靖中后期的重大历史事件,王世贞采用“即事命题”的新题乐府创作法,多有掇拾讽咏。
这二十二篇作品,在晚明诗坛影响甚巨,很多文人的新题乐府创作,都明言受王世贞的影响。如熊明遇说:“(弇州)作《乐府变》,自谓杜陵遗诀,以备一代采择,甚盛心哉……乃后之作乐府者滥觞,将时事直叙其体,则近日歌行而题曰古乐府可乎哉。”[注]熊明遇:《文直行书诗》卷一《古体》自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06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45页。他精辟地指出,作为源头的《乐府变》对晚明乐府创作有两大贡献:一是“将时事直叙其体”,此法虽非王世贞首创,但晚明新题乐府的创作风气,无疑更多承袭弇州而来,诗人们多因王世贞的推重而溯源杜甫,少有人提及元、白的传统;另一是“歌行而题曰古乐府”,即乐府、歌行二体混一,杜甫的不少新题乐府,在严格意义上属歌行体[注]有关乐府、歌行、七古三者的关系,参见葛晓音:《初盛唐七言歌行的发展——兼论歌行的形成及其与七古的分野》,《文学遗产》1997年第5期。有关新题乐府与新乐府的差异,参见葛晓音:《论杜甫的新题乐府》,《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1期;《新乐府的缘起和界定》,《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与白居易、元稹的“新乐府”不是同一概念。王世贞在《乐府变》中称杜甫“即事命题,千古卓识”[注]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六《乐府变》小序,《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第117册,第189页。,虽与复古派的“诗必盛唐”说相契,却扰乱了读者对乐府、歌行二体的认识。他的“即事命题”说,明显脱胎自元稹《乐府古题序》中对杜甫歌行“即事名篇,无复倚傍”[注]元稹撰,冀勤点校:《元稹集》卷二十三《乐府古题序》,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55页。的评价,却对元、白一字未提,此非无意之举,当是有意回避[注]关于王世贞淡化《乐府变》在批判现实的自觉性上与白居易《新乐府》的关系,清陈田曰:“七子论诗,断自大历以上。故弇州于张文昌、白乐天乐府,曾不齿及。”(《明诗纪事》,第1880页)又,关于王世贞回避“即事命题”说源自元稹《乐府古题序》,徐朔方在《论王世贞》(《浙江学刊》1988年第1期)一文中有论及。。以上两个观念的树立,对晚明诗家的乐府史观有很大的影响。宗杜而不宗元、白,歌行、乐府在体制上的相对随意性[注]在诗学理论上,晚明亦有对杜甫歌行之乐府化的批评,如许学夷《诗源辩体》卷十九:“子美《丽人行》,歌行用乐府语,不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214页)但在创作上,作家们的辨体意识要淡薄很多。,成为多数晚明清初诗人创作新题乐府的基本宗旨。
由此,将杜甫与王世贞绑在一起论说,成为晚明文人乐府诗论中的一个常见现象。如刘城《乐府变》曰:
昔王弇州取嘉、隆间事,作《乐府变》二十余章,即事命题,比于子美。虽云依隐善托,固不啻大书特书矣。余往于崇祯间,有所感叹,皆借古题影略之,读者不觉也。今年乙酉五月中,多不忍言者,乃不能不斥言之。以其人其事稍被古声,辞取显白,亦不肯乖于田畯、女红之意。[注]刘城:《峄桐诗集》卷一《乐府变》小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21册,第541页。
这段话是对王世贞《乐府变》小序的自觉呼应。王世贞赞誉杜甫“能即事而命题,此千古卓识也。而词取锻炼,旨求尔雅,若有乖于田畯、红女之响者”[注]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六《乐府变》小序,《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第117册,第189页。,故刘城在此基础上,作了两方面的进一步发挥。首先,刘城《峄桐文集》中有《今乐府》七篇、《乐府变》九篇。但与王世贞不同,刘城的《今乐府》属新题乐府,而《乐府变》属旧题乐府,可见他认为“乐府变”的核心,不在新题、旧题之争,而是“不忍言”的讽谕精神。王世贞强调杜甫的“即事命题”精神,容易将读者对《乐府变》的理解引向“新题乐府”之形式,刘城则“借古题影略”“稍被古声”,坚持用乐府旧题来创作《乐府变》,明确了《乐府变》的核心在“即事”,而非“命题”。
其次,对崇祯间事,刘城“有所感叹,皆借古题影略之,读者不觉”;对乙酉间事,却“多不忍言者,乃不能不斥言之。以其人其事稍被古声,辞取显白”。虽然都用了旧题,二者之别却显而易见,一种是隐晦的写法,一种是直白的写法,对应的正是他眼中的“依隐善托”“大书特书”二法。而他将后一种写法落实为“不肯乖于田畯、女红之意”的态度,亦受王世贞《乐府变》的启示而来。王世贞推崇杜甫乐府,指出其唯一不足处,在“词取锻炼,旨求尔雅,若有乖于田畯、红女之响者”,即太温柔敦厚,缺少乐府诗的生气。故王世贞宁愿“鄙俗”,也要避免这种文人气。刘城在遭遇王朝鼎革后,对“辞取显白”的追求无疑更自觉,他就是要与杜甫的“词取锻炼”区分开来,用乐府诗的民间性和口语化特征,畅快地表达自己的愤懑情感。类似的情况,在明末作家中颇为普遍,如王思任《诏狱可罢行》《缇骑来》二篇,其小序曰:“少陵即事命题,弇州谓其卓识,而不满其尔雅之词,以为不似田畯、红女之口也。予偶愤二事,即冲口出之。言责官守,未遘其会,辄以鄙俚歌之。”[注]王思任:《谑庵文饭小品》卷二《诏狱可罢行》小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36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74页。在推崇杜甫、王世贞之新题乐府的基础上,在语言上有所调整,形成相对“鄙俚”的诗歌风格,其法与刘城如出一辙。
王世贞用“鄙俗”来改变杜甫的“尔雅”,在一定程度上,是诗歌语言的一种选择;而刘城、王思任等人认同王世贞的做法,则不仅是诗歌语言层面的认可,更指向乐府主题在社会批判层面的超越。嘉、隆间事,只是朝廷士大夫的内部动荡,王世贞秉持“依隐善托”“备异时信史”的态度,大致停留在温柔敦厚的范围内,有刺亦有美;天启阉乱及甲申之变,则指向了士大夫群体的灾难、国家的覆亡甚至异族政权的统治,刘城的“斥言之”和王思任的“冲口出之”,与王世贞在存削之间犹豫再三的态度迥异。
以上刘城、王思任等人,是晚明因循《乐府变》较自觉的一批作家。甚至可以说,他们对复古诗家的学习,有时胜过对杜甫的学习。刘城《今乐府》小序曰:“余读崆峒、元美集,乐府有即事命题者,无论其文古,其事核,即不以言语文字讳,先朝宽大之象可见也”[注]刘城:《峄桐诗集》卷一《今乐府》小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21册,第540页。提到了李梦阳、王世贞,而未提杜甫、白居易等人。当然,考虑到他在《今乐府》中称李、王为先朝气象,《乐府变》中又纪乙酉诸事,已是入清口吻,以明遗民自居,那么,他的乐府创作更强调明人传统,或有其他用意。类似对王世贞《乐府变》全盘接受的情况,还有陈子龙的《新乐府》6首[注]清嘉庆八年(1803)刻本《陈忠裕公全集》录“新乐府”五首,包括《白云草》中的《范阳井》,《湘真阁稿》中的《谷城歌》《小车行》《卖儿行》,《三子诗稿》中的《韩原泣》。今检《湘真阁稿》卷二“新乐府”中,《谷城歌》《小车行》间尚有《辽兵行》一篇,亦当属新乐府。,李雯的《乐府变》4首等。在传统文学史中,他们所代表的,正是明代第三次文学复古运动,发扬王世贞《乐府变》的批评精神,借新题乐府来讽咏今事,重振文坛气象,是顺理成章的一件事。
然而,晚明文学思潮的主流,已不再是文学之复古。与刘城、陈子龙等人对王世贞的一味接受不同,更多的诗人,对王世贞的乐府变体观持辩证的态度。他们不会将复古派的乐府观与王世贞的乐府观划上等号,而是对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王世贞等人的乐府创作予以区别看待。比如熊明遇,对所宗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诸家有直言批评,但对王世贞依然好评:
(王世贞)作《乐府变》,自谓杜陵遗诀,以备一代采择,甚盛心哉。然恨不数章,如《寿宁泣》等题,明矣。至《尚书乐》,非有人笺注,孰知其刺赵文华之于相嵩也。乃后之作乐府者滥觞,将时事直叙,其体则近日歌行而题曰古乐府,可乎哉。余甚宗尚四家,而其一二未稳惬处,恐开后世磔裂古体之端,又何敢随声附会也。[注]熊明遇:《文直行书诗文》诗部卷一《古体》自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06册,第45页。
熊明遇说“余甚宗尚四家”,则以上文字,是对所宗潮流的反思,而非对异己学说的批判。尽管他批评二李失之断,何景明失之白,且不认同王世贞视歌行为乐府的观念,却坦言《乐府变》为晚明乐府创作之“滥觞”。当然,他所批评的歌行、乐府混一现象,本是杜甫新题乐府的惯用之法,并非王世贞的发明,因此他再怎么疾呼“磔裂古体”的危险,也因无法撼动杜诗的经典地位而收效甚微。从这个角度来说,王世贞将杜甫标举为宗法对象,至少有两个好处:首先,将“乐府变”的体式范围扩大至广义的新题乐府,丰富了乐府变的创作内涵,促成“近日歌行而题曰古乐府”之风气的兴起;其次,找到了一个有力的理论支撑,就算晚明诗人们对其新题乐府观发起激烈的批评,他也能在“诗圣”杜甫的光环庇佑下站稳脚跟。
在晚明时代,像熊明遇这样对李梦阳、李攀龙的模拟有所不满,但认可王世贞之新变的诗人不在少数。每个人的批评角度各有不同,亦不乏对乐府诗史有更宏观认知的作家。如顾景星在崇祯十七年(1644)创作《效杜甫乐府》八首,其序曰:
唐拟古乐府,即莫善太白、长吉、文昌、仲初辈,题不必今,辞不必古。元、白辈始创新题,讽谕体裁尽变;若刘猛、李余,古题新意,流传则少。至明李西涯咏古,无切于时。于鳞则瞡瞡然,称如胡宽营新丰,为善拟其用,至剿古为己有。元美变袭各半,其后撰《乐府变》,谓少陵即事命题,千古卓识。甫本古体诗,谓之乐府也可,以其风刺善也。[注]顾景星:《白茅堂集》卷二《效杜甫乐府》小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05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549页。
顾景星的这段话,较之熊明遇有两个推进之处:一、他的辨体论更直溯本源,直言杜甫的新题乐府为古体诗,不认可杜甫在乐府诗史中的意义,而主张“元、白辈始创新题”。熊明遇虽有类似看法,但停留在对明代诗学的批评上,缺乏史的意识,顾景星比他自觉得多;二、他完全否定了李东阳、李梦阳二人在乐府诗创作层面的价值,认为李东阳“无切于时”,李梦阳“剿古为己有”。而这两位是王世贞乐府思想中的重要参照人物,熊明遇眼中的白玉有瑕,在顾景星眼中一无是处。他说王世贞“变袭各半”,无疑更认同“变”的那一半,而“变”之核心,在“以风刺善”之内容,而非“新题乐府”之形式,这也是坚持辨体的顾景星,勉为其难地承认杜甫歌行亦可称乐府的原因之一。他在创作上亦遵循这一原则,其《效杜甫乐府》八篇,虽纪甲申间事,却采用了《当石壕吏》《当留花门》一类的命题法,属于拟古乐府(视唐歌行为古)的范畴。这种变通方式,早在王世贞《乐府变》中就已出现,如《治兵使者行当雁门太守》《袁江流钤山冈当庐江小妇行》二篇,可见弇州本人亦未彻底遵行“即事命题”的原则,后来者心领神会,亦在情理之中。
当然,在晚明清初的乐府变创作中,还有走得更远的一批人,他们虽在文学思想和创作风气上受王世贞的影响,却通过对文学复古思潮的强烈批判和反思,跳过了李东阳、李梦阳、王世贞、陈子龙等人的明乐府传统,直接对接杜甫、白居易等人的唐乐府传统。落实到具体行为,或在理论层面上否认明人新题乐府的创造性,或在创作层面上贬低明人乐府的整体质量,从而达到直溯唐人传统的目的。顾景星的文字,已有这方面的痕迹,但他毕竟给予了王世贞较多的正面评价。而他的好友宋荦,就没有那么客气了:
古乐府音节久亡,不可摹拟。王、李及云间陈、李诸子,数十年堕入云雾,如禹碑、石鼓,妄欲执笔效之,良可轩渠。少陵乐府以时事创新题。如《无家别》《新婚别》《留花门》诸作,便成千古绝调。后来张、王乐府,乐天之《秦中吟》,皆有可采。杨铁厓咏史,音节颇具顿挫。李西涯仿之便劣,要当作古诗读,无烦规规学步也。[注]宋荦:《西陂类稿》卷二十七《漫堂说诗》,《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3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02页。
在宋荦看来,李东阳、李攀龙、王世贞、陈子龙等人的乐府诗皆模拟之作,步入歧途。他更认可杜甫、张籍、王建、白居易甚至杨维桢的作品。他的这段话实为顾景星而发,不仅直言“亡友顾赤方擅长此体,余最好之”,而且所论的三篇杜甫作品,都是顾景星曾经拟作的对象。但上面说过,顾景星虽对复古派的乐府创作有所批评,但并不完全否定王世贞的乐府观,对《乐府变》还赞赏有加;陈子龙、李雯等人写过《新乐府》《乐府变》,熟悉近人诗集的宋荦不可能不知道,但他予以选择性无视。王世贞跳过中唐的新乐府运动,直接揄扬杜甫新题乐府的“即事命题”传统,固然有违文学史的基本常识,但宋荦在赞誉顾景星作品时,罔顾顾氏在乐府自序中对王世贞的评价,避谈王世贞、陈子龙、李雯等人创作新题乐府之事实,而将他们与一贯坚持拟古乐府的李攀龙一概而论,同样有悖文学史常识。这种歪曲文学史的书写方式,固然根植于王世贞或宋荦个人的诗学思想,但作为在文学思潮转变中的有效推动力,自身也成为了文学史事实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我们可知,在王世贞《乐府变》创作事实及思想的影响下,晚明清初涌现出一批诗人,他们或承复古思潮,或应时局之变,开始有意识地创作以讽咏今事为主旨的新题乐府。在理论层面上,有的人完全认同王世贞的观点,有的人对王世贞作辩证的认可而基本否定其他复古诗家的贡献,有的人则跳过明人乐府传统,直接对接唐人乐府传统,大致呈现为三种观念有差的批评态度。但无论他们怎么思考,其乐府创作和理论争鸣,都受到晚明乐府变创作风气之不同面向的影响,皆可追溯至王世贞提出的“乐府变”概念。从这个角度来说,“乐府变”不再是一组特定的作品,而是一个明晰的文学观念,以及一场围绕这个观念而风起云涌的文学运动。
二、“乐府变”运动的体类范围及持续时间
以上分三个层次,概述了晚明清初同中有异的“乐府变”思想,涉及新题乐府、拟古乐府、新乐府、讽谕诗等诸多概念。然而,肇其端的王世贞《乐府变》,我们无法用“新题乐府”或“讽谕诗”来简单定义,受其影响的后续作品,其情况自然更复杂。从这个角度来说,王世贞《乐府变》的属性为何,不仅涉及晚明清初诗家在新、旧乐府观念上的不同认知,还关系到对整个乐府变运动之体类范围及持续时间的界定,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古乐府自郊庙、宴会外,不过一事之纪,一情之触,作而备太师之采云尔。拟者或舍调而取本意,或舍意而取本调,甚或舍意调而俱离之,姑仍旧题,而创出吾见。六朝浸淫以至四杰、青莲,俱所不免。少陵杜氏,乃能即事而命题,此千古卓识也。而词取锻炼,旨求尔雅,若有乖于田畯、红女之响者。[注]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六《乐府变》小序,《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第117册,第189页。
在这里王世贞表达了三层态度:一、在拟古乐府内部,无论舍调取意(尚旧义),还是舍意取调(尚乐),皆不及舍意调而创吾见(尚新义),即提倡不拘形式以求新,故他对李白的旧题乐府评价甚高;二、推崇杜甫“即事命题”的新题乐府,不再像李白那样“创吾见而仍旧题”,以为千古卓识;三、在新题乐府的创作上,主张尚辞(词取锻炼)、尚义(旨求尔雅)兼顾尚乐(田畯、红女之响),在三者无法兼顾的情况下,则优先考虑辞、义的表达。其《弘治宫词》《正德宫词》《西城宫词》,继承的就是唐代的新声乐府传统,作为另一条创作之路,与《乐府变》并行不悖。综上而论,王世贞《乐府变》的核心在“尚义”,即“讽咏今事”的传统。
那么,晚明诗人如何看待王世贞的这组作品呢?顾景星评价王世贞乐府“变袭各半”,可见在他看来,《乐府变》的核心内涵在一“变”字。我们有必要明确此“变”的参照对象为何,是在文学文本层面,对李攀龙“剿古为已有”的拟古创作有所改变?还是在文学现实层面,突破李东阳《西涯乐府》中“无切于时”的保守思想?这涉及两个不同的文学传统,一为“乐府新题”传统,一为“诗史”传统,有必要作细致的区分。一旦我们细究这两个文学传统的不同之处,有两种特殊的乐府类型就凸显出来:一类以乐府新题纪咏旧史,渊源于李东阳《西涯乐府》,在晚明清初有不少效作;一类以乐府旧题讽咏今事,渊源于唐刘猛、李余诸家,明末以顾景星《拟杜甫乐府》为代表。这两类作品是否也在“乐府变”的范围内,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乐府变运动的文学史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说,对王世贞《乐府变》的定性并不难,但受其影响而发展壮大的乐府变运动,其各式作品的文体边界就要复杂得多。
我们先看晚明作家对“乐府变”三字的常规理解。刘城《乐府变》九首,明言“间仍古题,皆增字以别之,而调亦加变”[注]刘城:《峄桐诗集》卷一《乐府变》小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21册,第541页。,所用诸题皆袭改元前旧题,而所咏为乙酉国变事;其《今乐府》七首,赞赏李梦阳、王世贞的新题乐府“其文古,其事核,不以言语文字讳”[注]刘城:《峄桐诗集》卷一《今乐府》小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21册,第540页。,多和李梦阳新题之作;另撰《乐府》34篇,沿汉魏旧题,却一再强调“其文则古,而其事与义则别,余固不为拟古乐府”[注]刘城:《峄桐诗集》卷一《乐府》小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21册,第536页。。以上种种,皆见刘城对“乐府变”的理解,甚至对“乐府”原初概念的认知,在内容上的讽咏今事,而非新、旧题之形式。
明遗民薛敬孟,其《击铁集》中有“乐府变声”11首[注]薛敬孟:《击铁集》卷一《乐府变声》,《四库未收书辑刊》第7辑第20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123页。,兼具讽咏今事和乐府新题二要素;另撰“乐府新声”23首,效唐人王建、张籍等人的新题乐府。可见在他眼中,无论“乐府新声”还是“乐府变声”,都是讽咏今事之作,它们的主要差异,是借唯名定义之不同,将唐人、明人的新题乐府区分开来。另一遗民潘江,其《木厓集》中有“乐府变体”24题,这些作品以首句的前二、三字为题,每题下有“美禁火耗也”“美通商也”“美禁关节也”[注]潘江:《木厓集》卷三《桐山谣》,《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32册,第34页。之类的小序,明显学习白居易《新乐府》的命题法。潘江将之定类曰“乐府变体”,亦希求在时代上有别于唐人“新乐府”。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与薛敬孟一样,只是将“变”视为区分时代的一种标签,在内容上仍遵循讽咏今事的宗旨。
由上可知,在多数作家眼中,《乐府变》创作的第一义在“尚义”,在讽咏今事的“诗史”实践。但他们对“变”的理解,大多停留在时代之变上,缺少对乐府学流变的深层认知。而一旦“诗史”观念被固定下来,作为第二义的“新题乐府”,便有了在形式上寻求变化的多种可能。王世贞为了改变复古派的拟古风气,力倡“即事命题”之说,而在当时,根据前人的创作经验,“即事命题”至少有三个学习方向:一是以杜甫新题乐府、白居易《新乐府》为代表的极意讽谕之作,此为王世贞的本旨,诚然大流;二是以李东阳《拟古乐府》为代表的“因人命题,缘事立义”的批评前事之作,晚年王世贞对此评价甚高;三是以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元稹《连昌宫词》为代表的哀感顽艳之作,直至清初,方见气象(后有详论)。这三种类型中,只有第二类与早期乐府传统无关,是明乐府自身发展出来的新传统,且对王世贞乐府观的转变有重要影响,不可不提。
李东阳《拟古乐府》二卷(又名《西涯乐府》,共100首),取明以前正史故事作咏。虽曰“因人命题,缘事立义”,实缺少杜甫乐府讽咏今事的精神。他回顾唐以来的乐府发展史,“唐李太白才调虽高,而题与义多仍其旧。张籍、王建以下,无讥焉。元杨廉夫力去陈俗,而纵其辩博,于声与调或不暇恤。”[注]李东阳:《诗稿》卷一《拟古乐府引》,李东阳撰,周寅宾校点:《李东阳集》,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第3页。根本未提杜甫的新题乐府;至于元、白的新乐府,也在“张籍、王建以下无讥”的轻蔑语调中略过。可见李东阳对乐府创作的理解,与杜、白等人大相径庭。其作虽曰“拟古乐府”,实为拟古事之乐府,而非拟古乐府之题与义,与复古派的拟古乐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这样的创作形式,在嘉靖以后的诗坛,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王世贞也认为其作“十不能得一”[注]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六,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46页。。但他晚年对《西涯乐府》的态度大变,成为诗人们判断复古诗风转变的一个窗口:
吾向者妄谓乐府发自性情,规沿风雅。大篇贵朴,天然浑成。小语虽巧,勿离本色。以故于李宾之拟古乐府,病其太涉论议,过尔抑剪,以为十不得一。自今观之,亦何可少。夫其奇旨创造,名语迭出,纵不可被之管弦,自是天地间一种文字。若使字字求谐于房中、铙吹之调,取其声语断烂者而模仿之,以为乐府在是,毋亦西子之颦、邯郸之步而已。[注]王世贞:《弇州山人读书后》卷四《书李西涯古乐府后》,《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第123册,第90页。
这段文字关涉“弇州晚年定论”,故现今学界主要关注王世贞前、后期文学思想之转变,及对晚明文学思潮的诸多影响,较少从乐府文体学的角度,来探究李东阳《拟古乐府》之所以造成王世贞乐府观变化的原因。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说“李文正为古乐府,一史断耳”[注]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六,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第1046页。,评价甚低,却在晚年盛赞他“奇旨创造,名语迭出”,“自是天地间一种文字”。与此同时,看衰“求谐于房中、铙吹之调”在乐府发展中的前景,此法正是嘉靖年间他与李攀龙一同奉行的创作圭臬,故他所嘲笑的“取其声语断烂者而模仿之”,实可视为早年的自己。我们不禁要问,西涯乐府到底有什么魅力,让王世贞晚年幡然醒悟,以致态度有如此大的转变呢?
李东阳的拟古乐府,本质上是咏史诗。后人评曰:“李西涯之乐府,其文不谐金石,则非乐也;不取古题,则不应附于乐府;又不咏时事,则不合于汉人歌谣及杜陵新题乐府。当名为咏史乃可。”[注]吴乔:《围炉诗话》卷二,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13页。这种前所未见的“三不”特征,让读者很难将之归入《乐府诗集》的分类体系中,因为它与宋以前的古、近乐府皆不同。从王世贞、李攀龙的早年创作来看,他们在“不谐金石”“不取古题”二事上,与李东阳截然不同,只在“不咏时事”的态度上基本一致。但严格地说,“后七子”主张不咏事,李东阳主张咏古事,故弇州批评其“太涉论议”。王世贞晚年看重的,亦非“咏古事”本身,而是“咏古事”中的议论之法,这超越于今事、古事之上,可资借鉴。《弇州山人续稿》中有不少以新题咏古事的“拟古乐府”,如《信陵行》《东方曼倩行》《乌孙公主歌》等,都是王世贞乐府思想转变之后的作品。至于《西涯乐府》是否“有直刺时事者”[注]陈仅:《竹林答问》,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第2234页。,笔者未敢妄论,但“西涯乐府,得古诗之遗,风刺并见,含蓄可味”[注]朱彝尊编:《明诗综》卷二十二引陈恭尹语,《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第317册,第388页。的看法,是晚明清初诗人的普遍观念。作为创作技法的“风刺并见”,完全可能被他们拿来所用。
巧合的是,对王世贞《乐府变》有过效仿的刘城,也对李东阳《拟古乐府》发表过看法。作为在王世贞乐府观影响下的一代人,他对李东阳的认识,多少带有王世贞的某些痕迹:
唐惟杜少陵即事创题,不仍往昔。本朝李西涯别用故事,尺度自裁。皆古今卓识。教俗订讹之功,斯为大矣。余少得《西涯乐府》本,读而好之,后览元美《卮言》,谓一史断耳,心然疑其说。夫不拟古之既作者而自为之,此有所动千中矣。然其事则古,其文则古,即安能无美刺讽谕其间……不盈不肯拟古,持论正与余同。其独和西涯者,盖以题无因仍,事见本末,情有感触,语具兴观,故能独纵己力为之也。[注]刘城:《峄桐文集》卷二《和西涯乐府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21册,第398页。
这是刘城为顾尔迈《和西涯乐府》撰写的序文,虽然他对王世贞《乐府变》推崇备至,却没有读过王的《读书后》,以致于当他看到王世贞评价西涯乐府为“史断”的时候,难免心疑其说。但即使如此,他还是认为西涯乐府“美刺讽谕其间”,指出从不创作拟古乐府的顾尔迈之所以和《西涯乐府》,就是因为其中有一般拟古乐府没有的东西,“题无因仍,事见本末,情有感触,语具兴观”。可见在刘城等人看来,《西涯乐府》区别于一般拟古乐府的关键之处,在今人所谓的“尚义”。
顾尔迈的《和西涯乐府》是否涉明代史事,因文献不存,无法确言。从他欣赏《西涯乐府》“题无因仍,事见本末,情有感触,语具兴观”来看,如果只是一味地因题次韵,就会变成对其欣赏对象的一种解构,这种可能性不大。后来的明遗民陶汝鼐,撰《广西涯乐府》三卷120首,前二卷仿《西涯乐府》吟咏古事,第三卷续《西涯乐府》咏明朝事,则有怀念故国、反思旧史的明确指向。在他眼中,与七子乐府的“斤斤学步”不同,《西涯乐府》虽咏古事,却寄批评于其中,有“风义”“救时”之旨[注]陶汝鼐:《荣木堂文集》卷二《嚏古自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85册,第490页。。在清政权渐趋平稳的局势下,委婉刺时的咏史诗,比直白讽谕的新题乐府,更适宜生存。如清初人单隆周,撰《似乐府》54首,其序曰:
拟古之外,取近代可歌可咏之事,立题制什,此亦变通唐人《系乐府》《新乐府》之意也。尝读明史,因刺取其事,兴会所起,繁简听之,被以古体,间以唐音。既境写情,遇物成象,得如干首,题曰《似乐府》。昔李西涯自为乐府,王元美始痛抑之,已而自悔,称其奇旨创造,名语迭出。李空同以乐府音节谣咏近事,极得讽谕之体。数百年来,竞称卓绝。余窃取其义,用抒于邑云尔。[注]单隆周:《雪园诗赋初集》卷三《似乐府》小序,《四库未收书辑刊》第8辑第17册,第226页。
单隆周明言其作有两个传统,一是唐人《系乐府》《新乐府》,取近代可歌咏之事,立题命篇,即“刺取其事”;二是西涯乐府的“奇旨创造”、空同乐府的“极得讽谕之体”,即“窃取其义”。也就是说,于唐人乐府更关注新题,于明人乐府更关注新义。从批判精神来说,他继承的是李东阳、李梦阳、王世贞一脉而下的明人传统,后万斯同《明乐府》68首,尤侗《拟明史乐府》100首,吴炎、潘柽章《今乐府》100首等,都是类似的情况。之所以清初人有这样的普遍认识,王世贞晚年对西涯乐府的高度评价,及钱谦益对“弇州自悔”的再三宣传,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从当下的文学眼光来看,李东阳、陶汝鼐、单隆周、万斯同等人的乐府,皆咏前代事(古事、近事)而非今事。虽然他们都有批判精神寄寓其中,但一个是历史批评,一个是现实批评,二者有不小的差别。我们需要认识到,王世贞晚年之所以赞誉西涯乐府,是因为其中的批判精神不同于嘉靖后期的模拟之风,其“变”的参照物,是李攀龙乐府;而清初人效仿西涯乐府,是由于整个时局造成的,他们不便对新政权的统治进行直白的批判,只能转向对明朝史事之吟咏,借此对旧王朝的覆灭有所反思,其“变”的参照物,是创作空间渐小的乐府变传统。时代不同,“变”的初衷和诉求亦不同。王世贞试图借李东阳的历史批评来改变李攀龙的模拟风气,殊不知百年后的另一批诗人,面对新政权的文网,又借李东阳的历史批评躲进小楼,将王世贞开创的乐府变运动引向了终结之路。
既然王世贞题曰《乐府变》,后人也认同其意义在“变”不在“袭”,那么,我们在接受他变革前人乐府之事实的同时,也得允许后人在核心内涵不变的情况下,可以对他的乐府观念有细微的改变。就像刘城的《乐府变》稍改乐府旧题,只要讽世刺时的主旨尚在,就仍是“乐府变”的精神。从这个角度来说,无论是创作者还是研究者,都没有必要过度拘泥于形式,否则只会遮蔽对真实面貌的探究。
综上而论,乐府变运动的起始时间,在嘉靖四十年(1561)至隆庆元年间,王世贞的《乐府变》创作于这一时期;其结束时间大致在清康熙前期,因吴伟业卒于康熙十一年(1672),万斯同《明乐府》作于康熙十八年(1679)上京前,尤侗《拟明史乐府》作于康熙二十年(1681)。其作品内容,主要针对晚明国家变局和地方民生状况,以及明清鼎革带来的社会巨变,涉及王世贞、陈子龙、李雯、王思任、刘城、顾景星、薛敬孟、潘江、钱澄之等诗家。入清以后,风气渐弱,虽有魏裔介《今乐府》、陈维崧《新乐府》诸篇,但规模已大不如前。其创作主流,转为陶汝鼐、单隆周、万斯同等人的明史乐府。当然最重要的,是在明末乐府变风气与清初变局的合“变”影响下,出现了一位以歌行创作名垂诗史的作家。吴伟业是这次乐府变运动的殿军,还是超越于乐府变运动之上的更伟大的诗人,接下来会继续讨论。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即吴伟业身上最鲜明的“诗史”和“梅村体”两个标签,都与晚明清初的乐府变运动有密切的关系,这是学界以往考察吴伟业诗歌较少关注的一面。
三、“七子”乐府变体思想与“诗史”传统的自觉
如果将乐府变运动视为又一次的新乐府运动,我们不禁要问,这次运动为什么会发生在晚明清初这一历史时段?晚明的政治变局与清初的国家动荡,固然是非常重要的外在原因,但类似场景在两宋之交、宋末元初、元末明初皆有出现,且都与民族政权的更迭有关,为什么在此之前没有如此大规模的新题乐府创作现象?我们只有将内因与外因结合在一起考察,方能对乐府变运动的思想基础有更深刻的认知。
“乐府变”肇始于王世贞,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王世贞后期思想在乐府创作中的一次实践。他在《乐府变》中赞誉杜甫的新题乐府,未提元、白二人,表面上是“新题乐府”和“新乐府”两个概念的差异,甚至可以理解为在复古派“诗必盛唐”学说下的必然选择。但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明以前诗人,论杜甫而及“诗史”,已成常态;但白居易、元稹及其新乐府,却少有人以“诗史”相称。强调杜甫的“即事命题”,可以有效地与晚明兴起的“诗史”思潮挂钩。之前何景明、王廷相等“前七子”,对杜甫的“变体”创作多有批评[注]廖可斌指出,复古派作家在考察中国古典诗歌的审美特征及其发展变迁过程中,就对“诗史”概念的合理性产生怀疑(《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00页)。,如何景明《明月篇》小序曰:
仆始读杜子七言诗歌,爱其陈事切实,布辞沉着,鄙心窃效之,以为长篇圣于子美矣。既而读汉魏以来歌诗及唐初四子者之所为而反复之,则知汉魏固承三百篇之后,流风犹可征焉。而四子者,虽工富丽,去古远甚,至其音节,往往可歌。乃知子美辞固沉着,而调失流转,虽成一家语,实则诗歌之变体也。[注]何景明:《何大复先生集》卷十四《明月篇》小序,《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第274册,第122页。
在何景明看来,乐府、歌行须音调流转,杜甫的歌行过于强调切实,属于诗歌之变体,“其调反在四子之下”。显然,在何景明的诗学体系中,这种变体不是最好的学习对象,《明月篇》的风格,也更接近四杰之流丽。王廷相对杜甫“变体”的看法亦类似,其《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曰:
若夫子美《北征》之篇,昌黎《南山》之作,玉川《月蚀》之词,微之《阳城》之什,漫敷繁叙,填事委实,言多趁帖,情出附辏,此则诗人之变体,骚坛之旁轨也。[注]王廷相:《王氏家藏集》卷二十八《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53册,第164页。
他提到的四首叙事诗,杜甫《北征》、韩愈《南山诗》、元稹《阳城驿》为五言古诗,卢仝《月蚀诗》为杂言古诗。在后世的文学评价中,这四篇不止内容上的“填事委实”,还有政治上的含蓄批评。如果说何景明是从杜诗向前批评,那么,王廷相是从杜诗向后批评,韩愈、卢仝、元稹一并进入他的论说范围。对比可见,同为对“变体”的批评,何景明更关注声与辞的差异,王廷相更关注情与事的差异,于此来说,王廷相的关注点更具“诗史”意识。
既然何景明、王廷相一再批评杜甫“变体”,而王世贞却借杜甫的新题乐府突出一“变”字,我们实可从用词中发现前、后七子的思想关联,即王世贞针对何、王的“变体”说,赋予了“变”字新的诗学内涵。究其原因,一方面,与王世贞后期力求为复古诗学注入新的活力有关;另一方面,弘治朝的欣荣气象和嘉靖朝的党同伐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家国带来的巨大悲愤,是他求变的外部动力,承袭了《诗经》而下的变风变雅传统。
讨论了“变”字在复古诗学内部的观念变化后,我们再来看王世贞《乐府变》小序中的一段话:
其前集取亡害者半留之,几欲削去其余。既复自念三百篇不废风人之语,其悼乱恶谗,不啻若自口出,乃犹以依隐善托称之。《诗》亡然后《春秋》作,至直借赏罚之柄,而不闻有议其后者。秦兴而始禁偶语、焚载籍,然不久而汉竟洗之。以国家宽大显信,其必亡虑,于它可推已。[注]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二《乐府变》小序,《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第120册,第144页。

《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者,史也,史能及事,不能遽及情;诗而及事,谓之诗史,杜少陵氏是也。然少陵氏蚤疏贱,晩而废弃寄食于西诸侯,足迹不能抵京师,所纪不过政令之窳衺,与丧乱乖离之变而己。独王司马建生于贞元之后,以宗人分,偶有所稔,习于宫掖而纪其事,得辞百首。[注]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四十三《编注王司马宫词序》,《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第120册,第588页。
很显然,王世贞认为诗与情、史与事是两组对应的关系。史不能及情,诗却能及事,那么,诗的功能和意义无疑要比史大,其代表作家就是杜甫。由此,我们不难理解王世贞为什么要在《乐府变》中标榜杜甫,一来《乐府变》属于乐府新题,而非乐府新声,正匹配杜甫的歌行之体;二来王世贞创作时正值家居期间,其情形与杜甫晚年远离京城有相似之处,就诗情、史事二者关系的处理方式来说,更接近杜甫新题乐府的情况。他在《乐府变》和《宫词》的序言中都提到“《诗》亡然后《春秋》作”,显然不是无心之举,自有其深层的用意。他的《乐府变》和《弘治宫词》《正德宫词》《西城宫词》,即其“诗史”思想在不同类型创作中的自觉实践。
我们继续向前追溯,在“前七子”的另一篇重要文章中,又发现“《诗》亡然后《春秋》作”的踪迹。那就是李梦阳的《诗集自序》:
夫诗者,天地自然之音也。今途咢而巷讴,劳呻而康吟,一唱而群和者,其真也,斯之谓风也。孔子曰:“礼失而求之野。”今真诗乃在民间。而文人学子顾往往为韵言,谓之诗。夫孟子谓“《诗》亡然后《春秋》作”者,雅也,而风者,亦遂弃而不采,不列之乐官。悲夫。[注]李梦阳:《空同子集》卷首《诗集自序》,《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第40册,第129页。
以上论说文字,治明诗者很熟悉,因为李梦阳“真诗在民间”的主张,被后来学者视为“空同晚年自悔”的重要证据。在这篇文章中,李梦阳借同年文友王崇文之口,回顾了自己过往的诗歌创作观念,并作了一定的反思和完善[注]参见廖可斌:《关于李梦阳“晚年自悔”问题》,《诗稗鳞爪》,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可能是学界太关注“真诗乃在民间”一句的缘故,竟未留意此文是明代文学思潮中最早论及“《诗》亡然后《春秋》作”的作品。当然,李梦阳的态度以批评为主,认为此说虽雅,却间接造成了风诗、真诗遂弃不采的状况。以诗情、史事来说,他崇尚诗情一路,与王廷相、何景明等人批评杜诗“填事委实”“陈事切实”,实殊途同归。而王世贞的《乐府变》则不同,既在“变体”的创作概念上,阐发出有别于王廷相、何景明的乐府新内涵;又在“《诗》亡然后《春秋》作”的理论概念上,选择了与李梦阳截然不同的“诗史”观。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王世贞的变革都是实质性的,作为乐府变运动的开端,无可争议。

综上所述,乐府变运动有两个文学传统,一是体式层面的“新题乐府”传统,二是功能层面的“诗史”传统。向前追溯,它们同源于杜甫的歌行。故在很大程度上,王世贞小序中宗尚杜甫而不是白居易,有其必然的一面。晚明的乐府作家,更看重的是王世贞力振的“新题乐府”传统,他们对“诗史”概念及内涵的讨论,其实比较单一,尚没有像清初作家那样挖掘出丰富的内涵。与之相比,清初的乐府作家,更看重王世贞的“诗史”观念,这与整个时代环境的变化有一定关系,晚明时局让诗人们仍抱有讽时刺世、以求上听的愿景,这也符合乐府采风的初始功能;但异族政权的统治,让新题乐府丧失了沟通上下的路径,立足未稳的统治者未必从善兼听,诗人们也畏惧于潜在的文字之祸,更愿意在私人空间中行使“诗史”的创作权利。这个时候,“新题乐府”和“诗史”两个文学传统的不同,已不再是简单的体式、功能之别,而是文学创作与传播之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不同。从这个角度来说,明清之际的家国灾难,让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诗史”传统进入一个更深刻、更丰富的自觉阶段,而这种自觉性,又反过来延续了晚明乐府变运动的生命,促使其创作方向上的某些调整和转变,从向上进言转为向内诉说,并最后引出了吴伟业的“梅村体”歌行。综上而论,自觉的“诗史”观念,是乐府变运动走向高潮的重要原因,也是乐府变运动较之中唐的新乐府运动在文学史意义上的最大不同。
四、晚明“乐府变”与清初“梅村体”的关系
有关吴伟业及“梅村体”的研究,是清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对其歌行风格的溯源,早在清初,王士禛就说过:“明末暨国初歌行,约有三派。虞山源于杜陵,时与苏近;大樽源于东川,参以大复;娄江源于元白,工丽时或过之。”[注]王士禛著,张宗柟纂集,夏闳校点:《带经堂诗话》卷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21页。指出钱谦益宗法杜甫、苏轼,陈子龙宗法李颀、何景明,吴伟业宗法元稹、白居易,颇有暗示明人学明、清人学唐的分流清源之意。此后的诗家,亦有补充发明,或以为学初唐四杰,如四库馆臣评曰“格律本乎四杰,而情韵为深;叙述类乎香山,而风华为胜”[注]永瑢、纪昀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三《梅村集》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520页。;或以为学李商隐、温庭筠,如朱庭珍评“以《琵琶》《长恨》之体裁,兼温、李之词藻风韵”[注]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二,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第2355页。。以上说法,皆精辟有见。他们都认为,吴伟业之所以能形成“梅村体”之风格,主要来源于对唐诗名家的学习。在清人大力批判明代文学遗产的形势下,跟着清人的溯源脚步,我们也理所当然地认为清人的创作一定跳过明代,直接向更早期、更经典的文学传统学习。亦有不少学者指出,“梅村体”学习了明传奇的叙事手法[注]有关“梅村体”与明传奇的关系研究,最新成果可见李瑄:《“梅村体”歌行与吴梅村剧作的异质同构:题材、主题与叙事模式》,《浙江学刊》2016年第1期;李瑄:《“梅村体”歌行的文体突破及其价值》,《文学遗产》2017年第3期。,这主要是从小说、戏曲等更被当代学术所认可的俗文学体式中寻得灵感。事实上,明代文学与清代文学之间的关系,远没有像清人所划界线那么简单[注]廖可斌:《关于明代文学与清代文学的关系——以诗学为中心的考察》,《文学评论》2016年第5期。。本篇尝试探究吴伟业“梅村体”与晚明乐府变运动之间的关系,以此为个案,观察明中叶以来形成的诸多文学“近传统”之于清代文学复兴的文学史意义。它们不仅发生在小说、戏曲等俗文学领域,及性灵诗歌、小品文等艺术审美领域,在更大的文体范围内,皆有错综复杂的表现。
王世贞将“乐府变”定义为新题乐府,并以杜甫为标杆,在很大程度上,为后来很多诗人视歌行为乐府的创作行为,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虽然也有一些诗人力辨杜甫歌行之体,如熊明遇、顾景星、许学夷等,但这种唯名之争只停留在批评层面,在创作上仍趋从大流,顾景星的《拟杜甫乐府》就是最好的例证。这一趋势,在观念上为“乐府变”与“梅村体”的衔接,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
如前所述,在晚明时代,“即事命题”的新题乐府呈现为两个学习方向,一是以杜甫新题乐府、白居易《新乐府》为代表的极意讽谕之作,二是以李东阳《拟古乐府》为代表的批评前事之作。入清以后,前一种情况基本上已不可能,单隆周、万斯同等人选择了第二种方案,这与他们的遗民身份及思痛精神有关。吴伟业则尝试了一个新的方向,即以白居易《长恨歌》、元稹《连昌宫词》为代表的“哀感顽艳”的创作风格。从吴伟业前后期歌行风格的转变,可以很好地认识到这一点。
现可考知的吴伟业的较早歌行,是作于崇祯四年(1631)的《悲滕城》,十年的《高丽行》《东皋草堂歌》,十一年的《殿上行》,十二年的《悲巨鹿》等。分咏滕州水灾、朝鲜臣清、瞿式耜党争陷狱、黄道周廷谏遭贬、卢象升死难诸事。无论在语言风格上,还是叙事结构上,都与文学史中所谓“梅村体”之哀感顽艳、宛转流丽不同,反而与王世贞《乐府变》中的《大地变》《辽阳悼》《商中丞》《黄河来》等多相似之处。叶君远就指出,吴伟业的早期歌行中,苍凉沉重地反映现实之作甚多[注]叶君远:《重新审视吴梅村的早期诗歌》,《清代诗坛第一家——吴梅村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这种风格,从宗唐的角度来说,更接近杜甫的新题乐府,如果一定要说他学习元、白,也是学白居易的“讽谕诗”而非“感伤诗”。至于吴伟业后期为什么会转向哀感顽艳,笔者以为,政治气氛的变化,让他不再一味敢言,需要用一种更委婉的批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感。故其吟咏对象,从重要历史人物转为非帝王将相式的人物;其描述内容,从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变为宫苑园亭的兴衰变迁;其创作出发点,也从政治上的批评和劝谕,变为对历史的咏怀和思考。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和万斯同等人异中有同,其主旨都从现实批评转向历史批评,他们希求回应的,并不是统治者的虚怀若谷,而是普通读者(同时代文人和后世的历史观察者)的认同和永恒。
以上考察“乐府变”和“梅村体”在风格、体式层面的关系,这属于文学内部研究之法;与之相应的,是外部研究之法,主要体现在对王世贞、吴伟业二人关系的探究上。在中国文学史中,我们称吴伟业及“太仓十子”为“娄东诗派”,对这个地域诗派来说,同为太仓人的王世贞,是一位先行者的形象。无论在唐诗学上,还是地缘诗学上,王、吴二人都有不少相似之处。但吴伟业的文字中,提到王世贞的次数屈指可数,给人一种欲说还休的感觉。有关二人在唐诗学上的关系,吴伟业《致孚社诸子书》曰:
弇州先生专主盛唐,力还大雅,其诗学之雄乎。云间诸子,继弇州而作者也;龙眠、西陵,继云间而作者也。风雅一道,舍开元、大历,其将谁归?[注]吴伟业:《吴梅村全集》卷五十四《致孚社诸子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087页。
吴伟业推崇唐诗的风雅之道,在此思想体系下,肯定王世贞、陈子龙、李雯等人之于明代唐诗学的贡献。所谓的龙眠,指以方以智、钱澄之为代表的桐城诗人群。毛奇龄《龙眠风雅序》曰:“当夫黄门(陈子龙)崛兴,与海内争雄,一洒启、祯之末驵狯余习。而其时齐驱而偶驰者,龙眠也。故云龙之名,彼此并峙。”[注]毛奇龄:《西河文集》序卷十二《龙眠风雅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87册,第279页。而《龙眠风雅》的编者,正是前面提到的创作《桐山谣》的潘江。以上诸人,王世贞、陈子龙、李雯、潘江皆有《乐府变》或《新乐府》存世,方以智、钱澄之是以“诗史”有声于时代的遗民诗人[注]钱澄之:《藏山阁集》文存卷三《生还集自序》:“所拟乐府,以新事谐古词,本诸弇州新乐府,自谓过之。”(《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9册,第704页)足见王世贞《乐府变》对其“诗史”创作的影响。亦可参见张晖:《易代之悲:钱澄之及其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吴伟业的叙事歌行亦享有“诗史”的评价。一条以诗歌宗唐为主张、在创作中践行“诗史”传统的跨地域诗学脉络,已隐约浮现出来。

尽管吴伟业肯定了王世贞在宗唐、地缘诗学上的重要地位,但没有明说自己的文学思想是否受其影响。李瑄指出,吴伟业《杂剧三集序》中论诗、词、曲三者关系的文字,实沿袭王世贞《曲藻序》旧说而来[注]李瑄:《“梅村体”歌行的文体突破及其价值》,第177页。,可为一例。更早的洞察者,如乾隆年间的程穆衡,以《吴梅村诗笺》闻名诗坛,其评曰:
今观梅村之诗,指事传辞,兴亡具备。远踪少陵之《塞芦子》,而近媲弇州之《钦行》,期以摭本反始,粗存王迹。同时诸子,虽云间、虞山犹未或识之,况悠悠百世欤![注]程穆衡:《娄东耆旧传·吴伟业传》,见《吴梅村全集》附录一,第1413页。
程穆衡明确指出吴伟业的诗歌特征,是“指事传辞,兴亡具备”。这八字正指向了乐府变运动中最重要的两个文学传统:指事传辞,即新题乐府传统;兴亡具备,即“诗史”传统。另外,他对“梅村体”宗法对象的远近关系,也把握得很到位。杜甫的《塞芦子》,在白居易《与元九书》中被专门提到,与“三吏”、《留花门》并论。前及顾景星《拟杜甫乐府》八篇,选题就是“三吏”“三别”和《塞芦子》《留花门》,宋荦亦有“少陵乐府以时事创新题,如《无家别》《新婚别》《留花门》诸作,便成千古绝调”[注]宋荦:《西陂类稿》卷二十七《漫堂说诗》,《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35册,第302页。的评价,可见清人将这批作品视为新题乐府,已成常态。王世贞的《钦行》,是《乐府变》中的一篇,沈德潜以为刺严嵩,此诗以鸟喻人,有寓言诗的特色,是一篇讽咏今事的佳作。程穆衡的“远踪近媲”说,使我们对“梅村体”的认知,不再孤立地遥接唐人传统,同样对近代传统有所关注。毕竟对任何作家的创作来说,文学史及已有经典,是他们知识体系中的基础部分,晚近的文学风貌和社会现实,是他们知识体系中的变动部分。前者代表了理性的文学史认知,后者代表了对现实世界的文学体验,即使再伟大作家的创作,也是由这两个部分合力形成的。
总的来说,“梅村体”中的精神、主旨一脉,形成于崇祯年间,从杜甫、王世贞继承而来;而风格、形式上的特征,来自对元白、四杰的学习,及对早年诗风的自觉改造,从而提升了其歌行的艺术审美价值。较之先前的王世贞、陈子龙、顾景星等人,他不仅在作品质量上有所超越,更有其他多方面的文学意义,如将“乐府变”的核心内涵从精神主旨转至风格形式,从现实批评转至历史批评等。随着这些要素离王世贞的原旨越来越远,最终发展为自成一家的文学样式。它自“乐府变”脱胎而来,又以新的面貌“梅村体”被后世诗人学习效仿,成为另一个文学传统的开端。
故笔者以为,“梅村体”的出现,是乐府变运动的一次突变。它的最大贡献,是将乐府变运动的创作主旨,从向外的刺时或咏史,内转至对文本语言、风格的锤炼与尝试。这一内转趋向,固然有被政治环境所迫的原因,但晚明宗唐诗家内部对复古学说的反思,造成“诗必盛唐”观念的瓦解,及对中晚唐诗风的探索,亦值得留意。但不管怎么说,王世贞提倡乐府“变”的初衷,是为了赋予杜诗“变体”纪实刺世的时代内涵,而清人话语中对“梅村体”之语言、体式特征的偏重,却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这一内涵的影响力。至于它是否开启了另一种时代内涵,不在本篇的讨论范围内。
最后,笔者想说的是,在中国文学史中,杜甫和吴伟业是最当得起“诗史”荣誉的诗人,虽然也有人对汪元量、黄遵宪等有过“诗史”的评价,但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尚不能与杜、吴二人并论。从杜甫的新题乐府,到吴伟业的“梅村体”,二者在本质上都是歌行,但位居“诗史”金字塔尖的作品之风格,前为沉郁顿挫,后为哀感顽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诗史”的荣誉未曾落到兼擅《新乐府》之沉痛和“长庆体”之流丽、且被吴伟业推崇备至的白居易身上?除了白居易所处时代不像安史之乱、明清易代那么剧烈外,是否还有其他原因?笔者以为,这涉及之前所说的文学创作中的私人空间、公共空间等问题。无论是杜甫还是吴伟业,他们的“诗史”作品,虽为纪实,但首先有感而发,充溢着饱满的私人感情。白居易略有不同,《新乐府》自云“欲见之者易谕”“欲闻之者深诫”[注]白居易撰,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卷三《新乐府》序,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52页。,有以求上观的诉求,其理性批评难免对情感有所约制;《长恨歌》《琵琶行》等作品,或虚构太多,或个人行迹太显,与社会现实的关系颇疏。不管哪一种情况,都未能在情和事之间达成一种平衡。这种平衡,唯有杜甫和吴伟业处理得最好,包括王世贞、陈子龙、顾景星等人,皆有顾此失彼的遗憾。这或许是为什么在读者及批评者的眼中,乐府变运动不为人知、而“梅村体”世人皆知的深层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