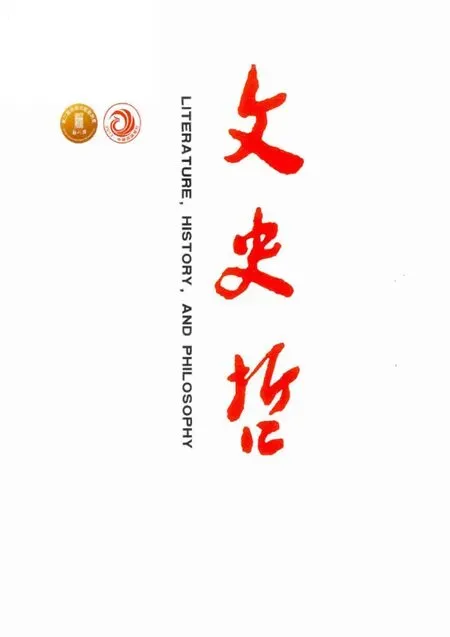中近古“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政策模式探研
李治安
自战国始,古代中国步入帝制地主社会,或称战国肇始的“封建社会”。该历史阶段在社会经济领域的基本特征,一是地主经济,二是帝制国家对百姓的直接管辖役使。两千年来帝制国家临民理政或管辖百姓及地主经济的政策模式,大体分为编民耕战与“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两大类[注]①两种模式的全称分别是编民耕战政策模式和“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政策模式。关于编民耕战模式,参见拙文《秦汉以降编民耕战政策模式初探》,《文史哲》2018年第6期。。以齐国四民“通货积财”肇始和晚唐两宋“不抑兼并”为导向的“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政策模式(简称“士农工商”模式),兼容行政和经济手段,变身丁管控为财税调节掌控,中唐以后甚而上升为主导。本文尝试运用模式分析与历史、逻辑阐述相结合等方法,侧重于国家政策与社会经济互动的视角,对“士农工商”模式自齐国发轫到晚唐两宋定型的曲折历程、内涵特色和历史地位,试作较系统的探研,就教于方家同好。
一、齐四民“通货积财”之雏形及其与秦“军功爵”编民耕战的博弈
与秦的“军功爵”编民耕战政策模式不同,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开创了四民“通货积财”“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政策模式的雏型。《国语》卷六《齐语》载,齐桓公问管仲:“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对曰:“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易。”桓公曰:“处士、农、工、商若何?”管仲对曰:
昔圣王之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
令夫士,群萃而州处,闲燕则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为士。
令夫工,群萃而州处,审其四时,辨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协材,旦暮从事,施于四方,以饬其子弟,相语以事,相示以巧,相陈以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为工。
令夫商,群萃而州处,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资,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荷,服牛、轺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市贱鬻贵,旦暮从事于此,以饬其子弟,相语以利,相示以赖,相陈以知贾。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为商。

《史记》卷六十二《管晏列传》曰:

从上述史料不难窥知,自管仲相齐开始,齐国的官方政策与社会秩序至少有如下四个特点:
第一,“士农工商”四民各治其业,各得其所。这是较早把“士农工商”排列在一起。请注意,此处与商鞅“军功爵”编民耕战体制有异。虽然所辖均为国家编户,但侧重有所不同,编民耕战突出的是一律由国家编籍管控,“士农工商”则彰显四种职业。《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又云:“其中具五民。”服虔解释为“士农商工贾也”[注]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第3265页。。就职业粗略划分,商贾属同类,“五民”或可归入四民。某种意义上,“士农工商”四民冲破了商周“工商食官”和“国人”“野人”等旧制,反映了春秋到明清四种社会基本职业群体的实际状况。并且首次把“工商”与“士农”同列,“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不仅“工商之乡”数量占到总数的1/3弱,而且允许工商专心本业,免除兵役。士乡亦农乡,平时农夫耕田,战时当兵[注]白寿彝总主编,徐喜辰、斯维至、杨钊主编:《中国通史》第三卷《上古时代》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62页。。此处的“士”,已非诸侯、卿大夫、士旧序列的士,而是基本进化为“事君者言敬”且具备文武或“秀民之能”的新型士人,亦即从属于君主官僚政治的新型士人。尽管仍保留四民分别编组居处和世袭为业的旧俗,但又规定“相示以巧”,“市贱鬻贵”,“农之子”“其秀民之能为士”,给予四民一定的经营自由或上升流动的空间。
第二,强调“仓廪实”和“衣食足”,将官民储备和民众富庶置于首位。以民众富庶为基础,进而追求“富国强兵”与“强国富民”的统一[注]周振鹤说:“提高老百姓的道德水准并非用行政命令的手段,而是采取强国富民的方法以达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自觉水平。”参见周振鹤:《假如齐国统一了天下》,《二十一世纪》1995年第2期;又见氏著《随无涯之旅》,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44页。。前揭鼓励商贾“相语以利”,“市贱鬻贵”。《说苑》载,管仲自称“‘贫不能使富’,桓公赐之齐市租”[注]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二《管晏列传》张守节《正义》引《说苑》,第2134页注[二]。,亦即市场交易税。结果管仲本人率先“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表明管仲应该是把包括自身在内的民众生活富裕“衣食足”,放在和官府“仓廪实”同等重要的位置,或主张以富民作为“强国”的基础。由是,“强国”也就有了广泛深厚的财富生成积累保障。
第三,“通货积财”,重视工商。所谓“通货积财”,简而言之,就是往来流通货物以积累财富的意思。由于齐国“士农工商”四民模式初定,允许手工业者“辨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协材,旦暮从事,施于四方,以饬其子弟。相语以事,相示以巧,相陈以功”;也允许商人“负、任、担、荷,服牛、轺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市贱鬻贵,旦暮从事”。在职业活动等方面,丝毫看不到歧视和压制工商的倾向。强调“通货积财”和工商居中必不可少的作用,重视工商业和农工商并举致富。这在二千六百多年前的春秋时代是难能可贵的。正如周振鹤教授所说:“设工商之乡是齐国的特制,四民分工,并且地位平等是齐的创举,表明工商业在齐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注]周振鹤:《假如齐国统一了天下》,《二十一世纪》1995年第2期;又载同氏《随无涯之旅》,第40页。而后,还由“商就市井处”逐渐造就工商市民为主角的新型城市,带来临淄等都市的繁荣富庶。如《战国策》所云:“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踘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注]缪文远校注:《战国策新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7年,第327页。这也是相当先进和可贵的。与之比较,千余年后的唐代长安坊市制为特色的行政主导型城市,就显得有些倒退落伍了。反倒是两宋开封、临安等与之惊人相似。
第四,因俗随欲而治。讲究“与俗同好恶”,讲究“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主张“贵轻重,慎权衡”,“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拒绝行政强权的简单粗暴,追求低调务实易行,将“轻重”“权衡”“与”“取”等商贾理念或管理方式,寓于官府行政过程之中。此种因俗随欲而治,有其高明之处,即使是对现代行政管理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尤其是对照比较秦制的种种暴虐手段:如“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天资刻薄”,“恃力”,“少恩”,“内刻刀锯之刑,外深钺之诛”,“号哭之声动于天地,畜怨积雠比于丘山”[注]司马迁:《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第2230、2237、2238页注[四]。。二者在手法巧拙和社会、民众承受顺逆方面,确有天壤之别。
若是将齐四民“通货积财”模式与秦国模式两相比较,虽然都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但齐国四民“通货积财”即“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模式的雏形,其特质是重视工商和农工商并举致富,是藏富于民,类似自由资本主义。秦“编民耕战”模式崇尚耕战,崇尚集中财富、军力于国,类似国家资本主义或军国主义。手法上,齐国注重“与俗同好恶”,“贵轻重,慎权衡”,较多顺应社会经济或民众的自然走向;秦国则一味仰赖行政强权。“士农工商”模式发轫于海岱,“军功爵”编民耕战模式最初植根于“好稼穑,殖五谷”的关中,二者各有其深厚的地域文化根基。“海岱之间”“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注]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第3261、3265页。,恰恰是“士农工商”模式的最好“摇篮”。
在这个意义上,春秋战国之际齐模式和秦模式的对决,既是地域族群差异的对决,也是经济发展形态不平衡的博弈。诚然,从政治军事成效看,二者在军事兵戎领域对决博弈之际,秦与齐间的优劣悬殊。齐国民众容易沉湎“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踘”,“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注]缪文远校注:《战国策新校注》,第327页;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第3265页。。秦国则“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注]司马迁:《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第2231页。。最终结局是秦始皇倚仗“军功爵”编民耕战这一制胜法宝,构成举国动员的战争机器,其甲士锐卒无敌于天下,战胜了齐燕赵魏韩楚,进而统一全国。
若是从更长的时段看,特别是从有利于社会经济繁荣发展的层面看,齐国四民“通货积财”又具有较多的合理性和优长。周振鹤教授指出:“齐国由于重视工商业,相应也就注重理财,管仲的轻重之术就是很高明的经济手段,是使齐国走上富强之路的重要因素”,“齐国的政策也并不强求思想一律,而是顺其自然”,“提高老百姓的道德水准并非用行政命令的手段,而是采取强国富民的方法以达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自觉水平”,“如果齐文化当真推行到四海,则其后二千年的历史恐怕要有点两样”[注]周振鹤:《假如齐国统一了天下》,《二十一世纪》1995年第2期;又载同氏《随无涯之旅》,第41、44、34页。。这是基本符合历史实际和经济发展趋势的见解。换言之,似乎不能简单地以战国末兼并战争的一时成败论“英雄”,更应当着眼和看重两千年来对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功用角色。尽管仍存在四民分别居处和世袭其业等时代局限,尽管在集中财富、军力于国以支撑军事战争方面,齐国四民“通货积财”模式相形见绌,但它在重视工商、农工商并重、促进商品流通、藏富于民、崇尚顺民心和顺应社会经济自由发展,以及为“强国”提供财富保障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价值规律及市场供求法则的明智方略,从而在国家临民政策层面另辟蹊径,开风气之先,成就“士农工商”同为四民、各治其业和较自由发展的早期雏形;还对战国以降,特别是对唐宋社会转型中临民理政方式等变通更新,发挥了值得称道的先驱效用。
二、两汉“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政策模式的起落浮沉
(1)汉初黄老政治与“士农工商”模式的短暂复活
刘邦建立西汉王朝之际,曾下达诏令“复故爵田宅”,还强制“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注]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第1417、1418页;班固:《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54页。,基本承袭的是秦朝“军功爵”编户耕战政策模式。
鉴于战乱甫定,经济残破,刘邦时已开始实施“与民休息”的策略。惠帝刘盈即位不久,任用曹参为丞相,改行“无为而治”的黄老政治。笔者认为,当时崇尚“无为”的黄老政治,不仅表现在大幅度减少徭役和兵役征发,将编民耕战规制在“与民休息”状态,而且还和齐国四民“通货积财”模式的复活及私人工商业勃兴等存在着明显的因果联系。“无为而治”的黄老政治,是汉初全局性的政策环境和政治气候。在此种政策环境和气候之下,秦及西汉统一之际曾遭打压而销声匿迹的齐国四民“通货积财”模式才转而短暂部分复活。而汉初私人工商业的蓬勃兴盛,正是短暂复活的齐国四民“通货积财”模式在经济领域内的基本展现及成果。
关于汉初私人工商业蓬勃兴盛的起因,《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披露:“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注]班固:《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第1127页。班固此言颇有道理,只是比较笼统含蓄,需要略加阐释。
在农、工、商等职业分野中,何者为本,何者为末?主要是见于商鞅变法中所强调的农本商末和重农抑商理论。如果从其“军功爵”耕战体制出发,这种理论不无合理性。前揭班固“本”“末”说亦代表汉代的主流政策话语。因为私人工商业与国家耕战的基本需要——甲士与粮食,毕竟不存在直接关联,反而容易与之争夺劳动人手等资源,涣散以劳役兵役为特定内容的耕战体制。但是,依照齐国四民“通货积财”模式,私人工商业者与士、农并列为四民,同为春秋以降社会新秩序下职业分工和经济繁荣发展的产物或需要,只有职业分野差异,没有本末贵贱的高下。即使是战国时期,也并非呈现“军功爵”耕战体制的“一统天下”,至少在齐国为代表的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私人工商业并不受歧视和打击,反而较多重视工商业的风俗。时至汉初,此类热衷工商业的风气重新流行。所以,才有了班固“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之说。而在汉初私人工商业随原齐国四民“通货积财”模式部分复活且短暂繁荣的过程中,先任齐国相后任汉丞相的曹参,又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

惠帝二年,萧何卒。参闻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将入相”。居无何,使者果召参。参去,属其后相曰:“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后相曰:“治无大于此者乎?”参曰:“不然。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扰之,奸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注]司马迁:《史记》卷五十四《曹相国世家》,第2029页。
以上“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句,殊为要害。迄今对“狱市”的解释,主要有两种:一是宋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下云:“狱也,市也,二事也。狱如教唆词讼,资给盗贼;市如用私斗秤欺谩变易之类,皆奸人图利之所。”二是陈直《汉书新证·萧何曹参传》指出,“狱市”为齐国大市名称,“狱”为“嶽”字省文,即齐国庄嶽之市[注]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下,《丛书集成》初编本,第54页;陈直:《汉书新证》,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52页。另参见李根蟠:《汉代的“大市”和“狱市”——对陈直〈汉书新证〉两则论述的商榷》,《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笔者比较倾向于陈直的说法。退一步讲,即使朱翌、陈直二说都有合理处,“狱市”一词也肯定包含有商业市场的意思。如此,曹参力主“并容”“狱市”,保护庄嶽等商业市场,不允许官府轻易扰乱的方略,洞若观火。实际上,在曹参治理齐国的“贵清静而民自定”的策略中,当含有抛弃秦商鞅“重农抑商”旧制,重新回归齐管仲重视工商或“士农工商”四民并重等内容。如果此种阐释能够成立,汉惠帝以后私人工商业的迅速复兴,就与曹参保护齐国境内商业市场的方略大有关联了。换言之,无论汉初“贵清静而民自定”的黄老政治,抑或全力保护庄嶽等商业市场的新方略,都肇始于原齐国海岱之地,都是由曹参经办和推行。称曹参居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殆非虚言。


上述史实表明,西汉初曹参推动下的黄老政治,促成齐国四民“通货积财”模式的部分复活,实现了该模式由“在野”步入合法,进而充当西汉编民耕战主导模式的补充或辅助。其直接经济成果就是私人工商业的繁荣及其短暂的黄金时代。
(2)汉武帝“役费并兴”极端化与轮台罪己“富民”


为解决浩大的军费开支及由此派生的财政危机,汉武帝任用桑弘羊等,实行有名的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告缗等。这些财经垄断措施,除去告缗打击剥夺商贾可以在商鞅变法中看到若干类同物,或是在国家强权管制上与商鞅有相通处外,基本上和秦军功爵编民耕战体制风马牛不相及。而是颇多借用管子轻重理论,选择性吸收齐国“通货积财”及轻重术等某些内容为其所用。
汉武帝上述财经垄断,具有如下三个特色:起用大商贾及子弟,使其摇身变为“兴利臣”;采用管仲轻重、权衡、榷卖等术;出卖军功爵,使其发生商业化变异。以上特色,显然是在吸收齐国式“通货积财”及轻重理论的基础上又有所变异,突出之处,就是把齐国式“通货积财”等某些因素掺入财经垄断,使之充任编民耕战模式的某种补充,共同服务于战时“役费并兴”的极端化。

然而,上述收益毕竟是有限和暂时的。大规模的黩武开边和财经垄断维持三十余年,终于招致农户破产流离,商人破家,货少价贵,民贫穷,国亦贫弱等灾难性后果。首先是农户破产流离。元封四年(前107)“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注]班固:《汉书》卷四十六《石奋传附石庆传》,第2197页。。其次是商人破家,货少价贵。史称,“杨可告缗遍天下”,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随之出现“商者少,物贵”,“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等不正常现象[注]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第1435、1440页。,社会生产、流通及财富积累储存等皆遭受严重破坏。再次是百姓和国家相继贫弱,民力和国力虚耗空竭。由于“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天下虚耗,人复相食”[注]班固:《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第1137页,,与汉武帝黩武开边、财经垄断相依存的富国强兵走向反面,导致了国家和百姓的一概穷困窘迫。

昭、宣二帝受大将军霍光的辅佐,承袭武帝富民政策,“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于是“流民稍还,田野益辟,颇有蓄积”,“岁数丰穰”,社会经济重新得到发展,史称昭宣“中兴”[注]班固:《汉书》卷七《昭帝纪》,第233页;卷八《宣帝纪》,第275页;卷二十四上《食货志四上》,第1141页。。然而,“盐铁会议”上围绕如何继续实行武帝末“与民休息”和“富民”等政策,统治层曾出现分歧。贤良文学主张废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桑弘羊极力反对,认为财经垄断政策乃“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仅是和丞相田千秋“共奏罢酒酤”,以为妥协。不久,桑弘羊因怨恨霍光和参与上官桀等谋反,被诛[注]班固:《汉书》卷二十四下《食货志四下》,第1176页。。霍光继续废罢酒榷,继续实行“与民休息”和“富民”等政策。
无论曹参“并容”齐“狱市”,汉初“网疏而民富”“富商大贾周流天下”,抑或武帝罪己“富民”,都不难看到汉代“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早期形态一波三折的非主流境遇。
西汉后期,重商观念再度“抬头”,“士农工商”四民秩序,随而受到朝野一定程度的认同。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等说,表明重商观念在西汉前期已见端倪。桑弘羊在“盐铁会议”上又说:

因操办财经垄断有功而升任御史大夫的桑弘羊等,对待富民和工商业的态度是比较复杂的。他并没有因为官职权势赫然及算缗告缗带来诸多商贾破家,丧失商人子弟固有的价值理念。汉昭帝盐铁会议之际,他在固守盐铁榷卖的同时,又强调“殷富大都”、“街衢五通”及“万物之所殖”之中“商贾之所臻”的功用,依然尊商重商,赞誉“宛、周、齐、鲁,商遍天下”,“乃商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羡”等,属于“智者因地财”。至于鼓吹“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实际上是某种程度地否认秦商鞅等农本商末和重农抑商理论,又质疑帝制国家单凭授田以富国强兵的政策,主张“富国”“足民”并重,农商皆可以“足民”,皆利于“富国”。可见,桑弘羊等虽然反对废罢盐铁榷卖,但他同样反对编民耕战模式中的重农抑商,更倾向于重商或农商并重。桑弘羊等身为商贾子弟而曾被汉武帝利用来为其黩武开边服务,他的重商言论,并不足怪。西汉初工商业的短暂辉煌发展及编民耕战与“士农工商”二模式交替消长,成就了桑弘羊等微妙处境及复杂态度。
(3)东汉“士农工商”的演化变态
东汉实行不抑制商人的政策,又兼和帝废除盐铁专卖制,给富商大贾带来发展膨胀的机会,他们操纵大商业,“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注]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九《仲长统》引《昌言·理乱》,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648页。。中叶以后,商业资本发达,商人在经济上得势,又多投资土地,变为商人地主,还寻求政治上的官府靠山,呈现某种程度的商人、地主、官僚三位一体。
如果说前揭桑弘羊语反映的是重商观念在西汉后期的再度上升,那么东汉班固、荀悦有关“四民”的论说,则大抵表现出当时文人舆情对“士农工商”四民秩序的逐步认同。尽管《汉书·货殖传》也曾抨击商贾“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皆陷不轨奢僭之恶”,“伤化败俗,大乱之道也”[注]班固:《汉书》卷九十一《货殖传》,第3694页。。班固云:
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圣王量能授事,四民陈力受职。

荀悦又曰:
国有四民,各修其业,不由四民之业者,谓之奸民。奸民不生,王道乃成[注]荀悦:《前汉纪》卷十,《四部丛刊》初编本,第3页A。。

魏晋南北朝世家大族对士的异化,坞壁、部曲等对编民的侵蚀,庄园自然经济膨胀和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所带来的手工业、商业萎缩,等等,尤其是私家依附关系的膨胀发展,较大程度上改变了战国以来地主经济和帝制国家对百姓的直接管辖役使的秩序。由此,编民耕战和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之临民理政模式也随之在中原地区基本中断。直至北魏“均田制”、西魏“府兵制”等创立和隋唐二王朝相继承袭,又建立起类似秦西汉的均田民耕战体制。
三、晚唐两宋“两税法”、“不抑兼并”与“士农工商”模式的定型
先说“两税法”顺应“田制不立”且为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模式定型开辟道路。马端临指出:
随田之在民者税之而不复问其多寡,始于商鞅。随民之有田者税之而不复视其丁中,始于杨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坏于鞅,唐租庸调之良法坏于炎。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称,而后之为国者,莫不一遵其法。一或变之,则反至于烦扰无稽,而国与民俱受其病。[注]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页。
唐德宗朝的“两税法”,是学界公认的赋役制度变革,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注]参阅陈明光:《20世纪唐代两税法研究评述》,氏著《汉唐财政史论》,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第245页。。这正是马端临将“两税法”和商鞅变法相提并论的缘由。无独有偶,商鞅变法与“两税法”,恰又分别和笔者讨论的编民耕战、“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二模式的确立,紧密联系在一起。笔者拙见,作为“唐宋变革”或社会经济转型核心内容的“两税法”,其重要贡献之一就是顺应“田制不立”亦即“随田之在民者”变为“随民之有田者”[注]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第4页。的大势,从国家税制层面为晚唐两宋“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模式升为主导而奠基开路。
“两税法”的核心内容是“随民之有田者”舍丁身而税田产。因其税制属性,故更是直接关乎帝制国家的临民理政。《旧唐书·杨炎传》云:“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人不土断而地著”[注]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一八《杨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421、3422页。。陆贽讲得更透彻:(两税)“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注]陆贽:《陆贽集》卷二十二《中书奏议六·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56页。。之所以舍丁身而税田产,根子就在于均田制瓦解及“田制不立”。正如《新唐书·食货志》载:“租庸调之法,以人丁为本。自开元以后,天下户籍久不更造,丁口转死,田亩卖易,贫富升降不实。……而租庸调法弊坏。自代宗时,始以亩定税,而敛以夏秋。至德宗相杨炎,遂作两税法”,“盖口分、世业之田坏而为兼并,租、庸、调之法坏而为两税”[注]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五十二《食货志二》,卷五十一《食货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351、1342页。。“两税法”实乃认可和顺应均田制瓦解及“田制不立”大势的赋役变革。万国鼎评论:“租庸调不计亩而计丁或户,则与均田制度相辅而行,盖必人皆授田,始可按丁征租……逮唐之中叶,均田制度坏,租庸调亦不能复行,改为两税法矣。”[注]万国鼎:《中国田制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88页。胡如雷云:“均田制的破坏是由租庸调发展而为两税法的关键。”[注]胡如雷:《唐代两税法研究》,《河北天津师范学院学报》1958年第3期;收入氏著《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论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需要厘清的是,这里的“田制不立”的田制,准确地说,并非先秦领主制共同体占有的井田,而是战国秦西汉式的郡县制国家计口授田[注]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65、166、175、176页。另参阅刘泽华:《论战国时期“授田”制下的“公民”》,《南开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北朝隋唐的均田与之类似。由于编民或均田民通常授田百亩,所以租庸调等以“丁身为本”而划一定额交纳租调,就是简便易行的。而当“田制不立”和根本无法简单按丁身征收租调之际,就不得不让渡于“两税法”了。
“两税法”实施后,大土地占有及租佃制的发展获得了更大的空间与便利,而开“不抑兼并”之先河。“盖口分、世业之田坏而为兼并”说,是也。譬如,北宋初孟州汜水县(今河南荥阳市)酒务官李诚占田“方圆十里,河贯其中,尤为膏腴。有佃户百家”[注]魏泰:《东轩笔录》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2页。。这方面的史料甚多,恕不胪列。
关于与“两税法”相伴随的“不抑兼并”的政策转向,王明清《挥麈录·余话》所引《枢廷备检》载:
置转运使于诸路,专一飞挽刍粮,饷军为职,不务科敛,不抑兼并。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缓急盗贼窃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
对这段史料,近年学者们颇有争议。有人依然认为“不抑兼并”是赵匡胤制定的宋代国策,有人撰文质疑反驳[注]杨际平:《宋代“田制不立”、“不抑兼并”说驳议》,《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2期;宋政超:《也谈宋代的“田制不立”与“不抑兼并”——与〈宋代“田制不立”、“不抑兼并”说驳议〉一文商榷》,《中国农史》2009年第2期;杨际平:《宋代“田制不立”、“不抑兼并”说再商榷》,《中国农史》2010年第2期。。笔者觉得争论双方见仁见智,都有史实依据,暂不妄加评判。退一步讲,“不务科敛,不抑兼并。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缓急盗贼窃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或非出自赵匡胤谕旨。但是,揆以“城郭人户,虽号兼并,然而缓急之际,郡县所赖,饥馑之岁,将劝之分以助民,盗贼之岁,将借其力以捍敌,故财之在城郭者,与在官府无异也”[注]苏澈:《栾城集》卷三十五《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奏乞外任状附)》,《四部丛刊》初编本,第3页B、第4页A。另,叶适:《水心别集》卷二《民事下》说,“然则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宋集珍本丛刊》本,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第709页)。清初王夫之又提出“不禁兼并,而兼并自息”(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四《孝武帝》,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41页)。后者显然是主张用经济自然运作去平息兼并。等多种类似说法,“不抑兼并”和“富室”“为国守财”的政治理念,在宋代得到了皇帝大臣们的普遍认可接受而被官方化,成为一种主流政策倾向,估计是没有什么疑义的。
顺便说说不抑兼并的相对性。近日有幸拜读李华瑞教授《宋代抑兼并述论》[注]李华瑞:《宋代抑兼并述论》,载厦门大学国学院等联合主办:《“重走朱熹之路”与宋代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7年。,收获匪浅。笔者赞同文章所持的宋朝对合理土地买卖兼并不加抑制,同时又抑制打击非法兼并和占田不纳税,以及王安石变法实乃国家政权重拳出击下的抑兼并等观点。有必要补充和强调的是赵宋的“不抑兼并”政策具有相对性。第一,宋朝廷的政策既非一味的“不抑兼并”,也不是一味的抑兼并,虽然整体上“不抑兼并”占主导,但只是相对于“抑兼并”而言。况且,“不抑兼并”与“抑兼并”,二者在不同时段或有偏重,或呈现消长交替。譬如,在宋初“不抑兼并”是主导性的,神宗“王安石变法”之际“抑兼并”又升为主导。秦晖教授有关中国经济史上存在“抑兼并”与“不抑兼并”的某种交替循环的说法[注]秦晖:《中国经济史上的怪圈:“抑兼并”与“不抑兼并”》,《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4期。,用在宋代或多半不差。第二,从较长时段看,赵宋的“不抑兼并”,主要是相对于汉唐而言,这就是多数人认为赵宋以“不抑兼并”为主导政策或“国策”的原因。第三,谁也不会否认赵宋没有搞秦西汉、北朝、隋、唐前期式的授田或均田,就传统的农业社会而言,此类“田制不立”,亦即“随田之在民者”变为“随民之有田者”[注]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第4页。,乃是最根本的不抑兼并。前揭《新唐书》“盖口分、世业之田坏而为兼并”语,可为证。倘若笔者的判断不错,自然应该承认赵宋统治者的临民理政方式已摆脱了汉唐“编民耕战”式的强制管束和藏富于国的窠臼,确实发生了“不抑兼并”导向的改变。这应是顺应中唐以降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的务实性选择。请不要小觑这种导向改变。恰恰是赵宋“不抑兼并”及藏富于民的政策推动,“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模式才得以较快取代“编民耕战”的主导地位,走到了历史前台。
换句话说,晚唐两宋“两税法”、“不抑兼并”和“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模式定型三者,确实存在较多的因果联系。“两税法”是晚唐两宋转而以财税为主调节掌控的基础或前提,“不抑兼并”和四民较自由发展又因其促成且皆有利于两税税源保障,三者在财税为主的调节掌控新格局下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且,在国家临民理政层面上,“不抑兼并”偏重充任士农工商发生如下五项“较自由”变化的官府侧导向或特定“催化剂”,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又是其导向之下四民职业群或产业的发展效应[注]拙文撰写之初,为措辞简洁和突出特色,一度径直冠名“不抑兼并模式”(参见李治安:《试论“不抑兼并”时代》,“中国古代‘农商社会·富民社会’高端学术研讨会”发言稿,昆明,2014年;《多维度诠释中国古代史——以富民、农商与南北整合为重点》,《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6年第4期)。而后,考虑到溯源齐四民“通货积财”、两汉起落浮沉及其与编民耕战模式的关联性,遂改称为“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政策模式”。。这就是晚唐两宋以“不抑兼并”为导向的“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模式的逻辑根由。
接着讨论“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模式定型后的内涵及属性特色。秦、西汉、北朝、隋和唐前期的编民耕战模式的内容及特征主要是:以授田为基础,“编”为户籍组织排列,“耕战”(含重农抑商)体现赋役义务,“军功爵”及强制分户充当保障手段,举国动员和富国强兵为目标。与编民耕战模式相比,“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模式既有延续继承又有扬弃变异。主要是将近乎偏执的身丁管控,改为财税为主的调节掌控。其内容特质至少有四点迥异:一是不搞授田,不抑兼并。二是沉重的劳役和兵役,已多数转变为代役钱和货币税收等。三是变重农抑商为农商并重。四是变一味藏富于国为偏重藏富于民。“士农工商”模式不仅在称谓上直接展示突出官府临民理政的四民对象,不再强调“编”及耕战义务,而且突出体现着四民较自由发展的社会经济秩序。正如钱穆所云:“自从唐代租庸调制破坏,改行杨炎两税制,自由经济又抬头,农田兼并,再度造成小农与大农。”[注]钱穆:《中国社会演变》,《国史新论》,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4年,第21页。这里说的“自由经济”,大抵是“士农工商”及后三产业较自由发展的意思。与西汉初“黄老政治”“网疏而民富”和汉武帝晚年“富民”政策[注]班固:《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第1136、1138、1139页注[一]。分别替秦皇暴虐、汉武黩武收拾残局类似,杨炎创“两税法”的直接诱因,无疑是在隋唐均田民耕战模式崩溃之际,出于财政税收或维持统治的需要,不得不改弦易辙,同时也体现着让渡给“士农工商”模式的无可挽回的趋势。南宋陈耆卿、郑玉道说:
古有四民,曰士,曰农,曰工,曰商。士勤于学业,则可以取爵禄;农勤于田亩,则可以聚稼穑;工勤于技艺,则可以易衣食;商勤于贸易,则可以积财货。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易之者也。[注]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三十七《风俗门·土俗·重本业》,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宋元方志丛刊》本,第7578页;郑玉道:《琴堂谕俗编》卷上《重本业》,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241页。
黄震亦云:
国家四民,士农工商……各有一业,无不相干……同是一等齐民。[注]黄震:《黄氏日抄》卷七十八《又晓谕假手代笔榜》《词讼约束》,《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786、802页。
清人沈垚言:
封建之世,计口授田,处四民各异其所,贫富无甚相悬。周末兼并,而货殖之术以兴。魏晋后崇尚门第,九品士庶之分,事虽异古而杂流不得与清班并。仕者禄秩既厚,有功者又有封邑之租以遗子孙,故可不与小民争利。唐时封邑始计邑给绢,而无实土。宋太宗乃尽收天下利权归于官,于是士大夫始必兼农桑之业,方得赡家,一切与古异矣。仕者既与小民争利,未仕者又必先有农桑之业,方得给朝夕,以专事进取。于是货殖之事益急,商贾之势益重,非父老先营事业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身通显。是故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注]沈垚:《落帆楼文集》卷二十四《费席山先生七十双寿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第663、664页。
综观上述议论,陈耆卿、郑玉道和黄震所言比较简约,重点反映的是迄南宋完全挣脱汉唐“重农抑商”的桎梏,包括工商在内的四民最终取得了皆为“本业”和“同是一等齐民”的社会地位。晚至清代的沈垚,上溯西周,下及宋元明,纵论三千年,大体属于阅尽沧桑之反观。尽管“封建之世,计口授田”等描述稍显张冠李戴,但“周末兼并,而货殖之术以兴;魏晋后,崇尚门第”,“故可不与小民争利”;两宋前后“一切与古异矣,仕者既与小民争利,未仕者又必先有农桑之业,方得给朝夕,以专事进取”,等等,可谓切中底里。尤其是“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之说,更是点出了中唐以降“四民”自等级秩序向皆为“本业”、“无不相干”和“同是一等齐民”的嬗变。简言之,陈、郑、黄、沈的议论,不约而同地披露出中唐以降特别是两宋士农工商较为自由发展的多种重要信息。兹结合以上“两税法”和“不抑兼并”等论述,着眼于晚唐两宋“四民”相应的五项变化,进一步阐发“士农工商”较为自由发展模式的新内涵及特色。

(2)募兵及差役取代兵役、徭役。自中唐募兵逐渐取代府兵,宋代更盛行募兵制。宋太祖说:“吾家之事,唯养兵可为百代之利。盖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变生,有叛兵而无叛民。”[注]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页。荒年招募破产流民当兵及耗巨资养兵,遂成为宋朝另一项国策。募兵之精锐选为禁军,欠合格者编入厢军。百姓不复承担兵役,相当多的劳役也由厢军充任[注]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卷四十一《兵制门·州兵》,《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37册,第571页。。北宋初夫役尚多,或主户、客户“共分力役”,或“计田出丁”[注]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69之78,70之167,第8093、8200页;脱脱等撰:《宋史》卷九十四《河渠志》,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347页。。北宋末定制并实行“尽输免夫之直”,即官府征收免夫钱代替身役[注]脱脱等撰:《宋史》卷一七五《食货志》,第4248页。,以适应大土地占有和农民丧失土地等情况。又普遍实施依户等轮流充当里正、主首等的差役制。由此国家基本放弃直接无偿征发力役的旧制,此与汉唐编户有异。
鉴于以上两条,“四民”中包括地主、自耕农及佃农的“农”,田产数量不再受管制,租佃关系合法,徭役和兵役因多改招募而负担大为减轻,获得了较自由发展。

(4)士大夫演进。科举制推行后,士庶由对立逐渐走向合流,原先讲究家世门第高低和世代显宦的士族,演化为凭借智力科考且功名系于自身的士大夫。因谏议制成熟及以“致君行道”为己任,两宋“与士大夫治天下”,迎来一段士大夫的“黄金时代”。科举对商人子弟开放,“士之子恒为士”旧格局不复存在,“士大夫始乃兼农桑之业,方得赡家”;士大夫求贵更求富,“非父老先营事业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身通显”。士大夫在四民中保持其政治优势的同时,又获得与农、工、商间交流的一定机动空间。士与商等交往及社会流动增加,士商雅集唱和渐多,士大夫获取富商资助,富商借交往士大夫而附会风雅。更有甚者,官吏之家“货殖之事益急,商贾之事益重”,兼做商贾的日渐增多。北宋中叶以降仕宦者“纡朱怀金,专为商旅之业者有之,兴贩禁物茶、盐、香草之类,动以舟车,贸迁往来,日取富足”[注]蔡襄:《端明集》卷二十二《废贪赃》,《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0册,第510页。。官吏经营商贾及工商子弟允许科考,大大缩小了原“四民”中最尊贵的“士”与最低贱的“商”间的距离,二者的“名位”界限,因贫富贵贱的错综复杂而日趋淡漠。此与汉唐编户中的“士”稍异。
(5)“富民”阶层崛起。宋人说:“乡村上三等并坊郭有物业户,乃从来兼并之家。”[注]韩琦:《上神宗乞罢青苗及诸路提举官》,载赵汝愚编,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整理:《宋朝诸臣奏议》卷一一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208页。此“上三等并坊郭有物业户”,即构成两宋的富民。“富儿更替做”,“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注]袁采:《袁氏世范》卷三“兼并用术非悠久计”“富家置产当存仁心”,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71、173页。,“富民阶层的崛起,是唐宋社会在商品经济发展推动下财富分化不断加剧的结果”。为营求增殖财富,以维持家业不败及更好的社会地位,富民率多培养子弟问学应举,参与社会赈济,还担负国家赋税差役的主要来源[注]林文勋:《唐宋社会变革论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34、135、150、154页。。宋代因“不抑兼并”,富民得以横跨四民而较纵深发展,取得“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注]王夫之:《黄书·大正》,《续修四库全书》第94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47页。的重要地位。它与西汉司马迁时代的“素封”,相隔千年而或多相似。“富民”的财富优势更趋显著,在和士大夫分别构成四民的经济、政治二支配力量方面,又独具“唐宋变革”的时代特色。
还有一点需要解释,随着科举制发展,士人或士大夫已涵盖所有官僚和拥有功名的儒生等。他们在政治上依然在四民中居超然高等。正如《金瓶梅》中西门庆对自己和亲家乔大户的评说:“乔家虽有这个家事,他只是个县中大户白衣人。你我如今见居着这官,又在衙门中管着事,到明日会亲,酒席间他戴着小帽,与俺这官户怎生相处?”[注]兰陵笑笑生著,秦修容整理:《金瓶梅(会评会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559页。从“官户”、“大户”等称谓看,《金瓶梅》大抵是明人记述宋朝故事。宋代所谓“官户”,是指一品至九品的官员之家。西门庆原系生药铺商人,靠行贿买官得到五品官职,故也能硬充“官户”。所谓“白衣人”,就是白身平民,亦即“农工商”中没有官职功名者。西门庆语表明,晚唐两宋“贫富贵贱”“离而为四”[注]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二,翁元圻注引游氏《礼记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69页。,虽然四民中的士人缙绅凭借权势,富民凭借金钱,各自拥有政治或经济的支配力,但官户士人的政治地位或身份,仍旧超然高于后三者“农工商”。即便“白衣人”财富雄厚乃至借其财力交结权贵,仍然在服饰等礼法上难以和官户士人平起平坐。
以上五方面,体现晚唐两宋“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模式的新内涵,亦即王夫之笔下的“耕者耕,工者工,贾者贾”[注]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二《玄宗》,第772页。。秦汉编户齐民,大抵反映的是一种来自官方的政治法律秩序,在职业和社会等级层面,当时又具体表现为“士农工商”四民前贵后贱的秩序。与秦汉编民耕战模式下的“四民”比较,晚唐两宋“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模式显示出:四民自前向后排列的政治等级色彩已淡漠,租佃制和贫富凸显,商人地位提高,四民间相互流动较频繁和士大夫、富民同为支配等。而且,“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的主体,既指谓四民职业群体,也包含农、工、商三产业。沈垚所云“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的“分”,直观上看是“分际”“界限”,更表示“名分”“位分”。因为秦汉至唐前期的“士庶”之别和重农抑商,当时的士农工商“四民”虽然都属于编户齐民,但同时又大体是一种贵贱等级排序。直到唐初仍有法令规定:“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注]李林甫等撰:《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年,第66页。这就是“古者四民分”的意思。由于中唐以降发生士庶合流和农工商皆“本业”等变化,由于发生“贫富贵贱,离而为四”[注]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二,翁元圻注引游氏《礼记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69页。,“四民”贵贱等级“位分”排序及国家的相应管制,随之不复存在,“四民”遂演化为“位分”界限趋淡、“无不相干”且可以相互流动转化的四种社会职业群体。这又是“后世四民不分”的意思。
林文勋曾从富民和财富力量崛起层面剖析唐宋“贫富贵贱,离而为四”的过程。他指出,此种变化至少包括“贵者未必富”、“富者未必贵”、“贫者未必贱”、“贱者未必贫”和贫富贵贱处于经常性的转化之中;“士农工商等级制在贵者贫和贱者富的上下对立运动中被财富力量摧毁了。”[注]林文勋:《唐宋社会变革论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00、101、104页。实际上,此变化过程与前揭沈垚说的“四民”嬗变,是体现着一场互为因应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更新。“贫富贵贱”四者相分离或错综复杂,背景和终极原动力诚然是经济进步发展及“财富力量”,同时也是帝制国家顺应经济趋势,放松“重农抑商”、“抑兼并”之类强势管制的产物和表现。在这个意义上的,“贫富贵贱”相分离,促成了“四民不分”或“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而“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政策模式的定型,又意味着“贫富贵贱,离而为四”从观念到“四民”物态乃至国家政策层面,都被普遍兑现了。
四、“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政策模式的历史地位

有必要解释的是,秦汉以降的编民,若按职业又可称士、农、工、商四民。“士农工商”,既言编民的四种社会职业类别,也涉及与其关联的经济产业。在平民或非贵族身份的层面上,编民与士、农、工、商是相通的。当时,编民耕战政策模式的管控,将士、农、工、商置于授田、户籍、赋役等框架内,进而被整合管制为编户齐民。四民(主要是后三者)也大抵蜕变为身丁受管控、受役使的国家农奴,其业已呈现的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经济属性则被钝化或暂时掩盖。而在“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政策模式下,士、农、工、商四民属性及其经济产业重新凸显,因授田、徭役等消亡又导致其国家农奴属性减弱。这就是上述两类政策模式彼此消长及主辅易位,与其伴随的编民与四民之间既相通又各有偏重的背景缘由。
晚唐两宋“士农工商”模式的定型,意味着“唐宋变革”中帝制国家临民理政的第二种基本政策模式升为主导。该模式的精髓在于:扬弃“授田”和劳役,较多遵循“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注]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第3282页。,亦即“不抑兼并”法则,产业上农商并重,鼓励藏富于民,容许富民支配。该模式既深刻触动土地赋役和第一、二、三产业等社会经济结构,又含有官方主导政策及国家与百姓间关系等改善。从长时段看,以“两税法”为先导的“唐宋变革”及其在农商领域的“不抑兼并”,顺应晚唐社会经济趋势而更新政策模式,较务实地将原本近乎偏执的身丁管控悄然变通为以财税为主的调节掌控,旨在从体制上迈向便于地主经济发展繁荣的秩序。在这个意义上,晚唐两宋定型的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模式实乃替编民耕战政策模式寻找到了更为合理的发展出路。
由于上述改变,“士农工商”模式往往能够较多祛除编民耕战模式“经理其物产,生聚其人民”而将“井疆耕耨之丁壮”抑为“国家农奴”之弊政[注]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四《安帝》,第452页;卷二十二《玄宗》,第769页。,较多祛除暴君假借富国强国而滥征徭役赋税、祸国殃民之弊政,较多祛除过度管制经济、妨害农工商产业发展及民间财富“造血”机能之弊政[注]参阅拙文《秦汉以降编民耕战政策模式初探》,《文史哲》2018年第6期。。它偏重藏富于民,类似自由资本主义。与编民耕战模式一味集中财富、军力于国不尽相同。虽然在完成军事政治统一、从事重大工程和开拓疆域等方面,该模式略逊色于编民耕战模式,但是在发展生产、提高生产力及改善民生,有利于完善国内商品市场及商品经济,最终增强综合国力等方面,“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政策模式又具有不可替代的活力和优越性。它能够基本顺应农民依附关系改善和地主租佃制及手工业商业发展的趋势,较有利于刺激促进生产力、社会财富积累及新经济因素的孕育。无论是多数王朝中叶抑或近古时代,经济繁荣发展就会转而选择“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模式,“唐宋变革”及元明南北因素整合发展,在临民理政方面皆以该模式为主导或引领倚仗,就是例证。
应当注意,“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政策模式同样有其特定适用范围或所依赖的时空环境。通常是在地主经济形态发展比较充分,商品交换或商品贸易比较发达,商品货币关系较多进入生产关系等场合,往往容易提供该模式扎根施展的时空条件。譬如地域空间,战国秦汉以齐国为代表的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海岱”地区,东晋以降的东南地区等。又如发展时期和阶段,中唐或唐宋社会变革也会最终迎来“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模式升为主导地位。编民耕战与“士农工商”二模式的博弈或演进过渡,某种意义上也是中近古社会经济发展中地域或时段不平衡的产物和表现。
中唐以降“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政策模式虽然在内容特质上发生过上述较突出变化,同时又在若干方面依然保留了编民耕战模式的基本内容,故而只能算“较自由”而非完全自由,只能算是前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通。依然有如下四个方面未曾或较少发生变化:(1)皇权国家“溥天率土”最高所有权;(2)土地买卖、诸子继承等造成的土地兼并周期性危机;(3)帝制官僚支配社会经济与“权力商品化”;(4)国家榷卖垄断及其与特权商人勾结。由于这四条基本未变,“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政策模式虽然经历近千年的曲折进步,从土地占有、赋税、徭役及百姓人身束缚诸方面较大程度上改变了编民耕战式的官府强势管制或管控及“国富民穷”阻碍经济发展等弊病,但其管制或管控只是放松,而非放弃。而且,该模式只是临民理政方式的相对进步,并非彻底解决帝制传统社会基本矛盾的“灵丹妙药”。特别是以上四个未变中的后三项还成为中唐以降较突出的遗患,严重制约着宋元明清“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政策模式本身乃至社会经济的整体进步。
第一,皇权国家仍然保持对“溥天率土”的最高所有权。在编民耕战模式及授田、均田实施之际,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无甚疑义。但在“田制不立”和“不抑兼并”为前提或导向的“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政策模式下,一方面,皇帝“溥天率土”最高所有权,专制皇权对农民的直接统治、隶属等,因君主官僚政治传统惯力及儒家纲常鼓吹因素制约,依然长期延续。另一方面,晚唐两宋租佃制高度成熟,土地频繁转移,土地使用、占有和所有权又呈现复杂化,特别是“押租制”、“永佃权”、“一田二主”等渐多出现,造成地主的占有权及所有权趋于多元且法律保障渐重,国家最高所有权大多是体现或保持在最终褫夺等层面。这个问题相当复杂,且容另文探讨。

第三,帝制中央集权官僚制所派生的“权力商品化”愈演愈烈。自战国秦汉,帝制中央集权官僚制高度发展和高度成熟完善,帝制官僚制支配社会经济,也成为两千年来难以动摇的惯例。如果说秦西汉等编民耕战政策模式下是通过授田、重农抑商和户籍、里甲、人头税、徭役等行政干预或管制,来实现主导或支配社会经济的,那么,晚唐两宋“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政策模式下上述行政干预管制或有所放松,其支配社会经济的具体做法即较多放弃行政强制的管控管制,转而较多采用税收和榷卖等财税手段。一方面,该模式依然延续着部分行政干预或管制,“越俎代庖”地配置社会财富资源,违背和粗暴践踏市场价值、供求法则等弊病,仍然不时发生。另一方面,官府与民争利,榷卖和税收等变本加厉。尤其是科举盛行之后,大批寒门贫穷士人借科考获取功名,改换门庭,凭借官职权力攫取巨额资财,进而使“权力商品化”愈演愈烈。其卖官鬻爵、贪赃枉法、贿赂公行者有之;“纡朱怀金”“兴贩禁物茶、盐、香草之类,动以舟车,贸迁往来,日取富足”[注]蔡襄:《端明集》卷二十二《废贪赃》,《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0册,第510页。,甚至“资之以县官公籴之法,负之以县官之徒,载之以县官之舟,关防不讥,津梁不呵”[注]苏洵:《嘉祐集》卷五《衡论下·申法》,《四部丛刊》初编本,第3页B。。总之,此时率多是用官职权势换取财富利益,而且较之自命清高、不屑与民争利的汉魏门阀贵族,更显得格外放肆和明火执仗。
第四,国家榷卖垄断及其与特权商人勾结,导致工商业颇多畸形。帝制国家征榷及官府与商人从对立走向联手勾结,萌生于齐国管仲,成型于汉武帝,复兴和固定于唐后期刘晏理财。它在某种意义上彰显帝制国家的最高所有权,或保留举国体制的某些遗制。两宋“刻剥之法”“皆备”,愈演愈烈。尽管有相关王朝财政亏空压力等直接背景,却又是贯穿汉唐编民耕战和晚唐两宋“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政策模式的共有财经现象,且在中唐以降更为常见,更为普遍,对“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模式的影响程度,往往超过前三者。


这种财经垄断或掠夺,在国家强权管制原则上,与商鞅“抟力”有较多相通处,又大量借用吸收齐国管仲榷盐和“轻重”理论且为其所用。后世王朝理财大多把盐铁榷卖等财经垄断奉为圭璧。元明清概莫能外。榷卖垄断或掠夺中的官商勾结和官商瓜分,表面上是官府向商人的妥协,但更是官府利益最大化的需要,当官府不方便或全面垄断遭遇困难之际,就准许部分商人出面经营,然后与之共享分沾“公利”。正如欧阳修所云:“盖为国者兴利日繁,兼并者趋利日巧,至其甚也,商贾坐而权国利,其故非他,由兴利广也。夫兴利广则上难专,必与下而共之,然后流通而不滞。”[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九“康定元年十二月乙巳”,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069页。后世的官商勾结合法化或固定化,逐渐在盐商、“开中法”、票号商、皇商等范围内扩展实施,进而形成一种特权商人群体,而且在明清“十大商帮”中占据颇大比重。其基本手法是官府给予榷卖活动中与之勾结的少数商人以市场准入等特权,并和他们分割巨额垄断性暴利。

官商勾结,对农工商经济运行抑或行政管理危害很大,对私营工商业的独立发展和新经济因素的孕育成长的潜在危害,更是不可小觑。正如人们所熟知,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总量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曾在世界各国中名列前茅,但15、16世纪以后难以在农业、手工业、商业中较多孕育和健康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难以顺利完成资本积累,最终在工业化为主流的世界经济新格局中落伍溃败。究其原因,除去“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国内官与商榷卖勾结所造成的工商业畸形,连同皇权最高所有、土地兼并周期性危机、官僚“权力商品化”等结构性弊病,较多抵消掉“唐宋变革”焕发的正面能量与活力,似乎也难辞其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