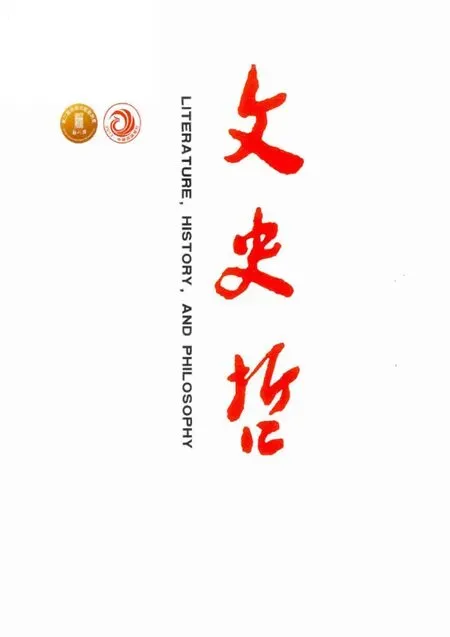中国文明的复兴和知识重建
郑永年 杨丽君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杨丽君,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

然而遗憾的是,当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社会科学界最大实验场的时候,中国知识界并没有承担起解释中国的变革,为世界社会科学发展贡献知识的责任。社会科学领域发展滞后的现状不仅影响到了中国的知识重建,更累及中国文明的复兴。任何一种文明,其内核都是代表这个文明的知识体系。或者说,知识体系是一种文明的最高表达。从知识构建的角度讲,正是伟大的知识造就了文明,任何文明都需要一套完善的知识体系来支撑。但今天中国所面临的局面并非如此。一方面是改革的作为和文明的复兴,另一方面是能够解释改革实践的知识的缺失。近年来,中国政府提倡媒体和智库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但是由于缺乏一套知识体系支撑,结果总是事与愿违。我们所讲的“中国故事”,外界听不懂。用一位西方外交官的话来说,讲好“中国故事”的最终结果却是“唤醒了中国在西方的敌人”。笔者认为,诸如此类现象的产生,最根本的症结在于改革开放乃至近代以来,中国一直没有发展出自己的知识体系,而是在用西方的知识体系来解释中国问题,结果不仅外在世界不感兴趣,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曲解”了自己。很显然,这种现象必须得到改变。
一般意义上,人们把1840年代的鸦片战争视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其主要意味是凸显西方对中国发展的影响。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了,大清帝国从此开始走向衰败。的确,在促成中国传统帝国体系离开历史舞台过程中,西方的作用不可低估。因此,马克思尽管无情地谴责西方殖民地主义和帝国主义,但也充分肯定了殖民地主义和帝国主义在推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关键作用。在马克思之前,另一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中国没有历史,因为中国的历史是静止的[注]参见[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如果按照欧洲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中国的确没有历史,因为自秦始皇帝统一中国之后,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形态几乎没有发生过巨大的变化。而中国新的历史就是在和西方接触后才开始的。鸦片战争是关键,之前中国的体制和意识形态一直有能力应付外来的挑战,因此没有深刻变革的意图和需要,但几次战争失败之后,不得不开始进行主动的变化和变革。
那么,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是如何变化的呢?有两种主要的解释。第一种是美国史学家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认为中国是随着西方的变化而变化的,西方带来冲击,中国予以回应[注]Ssu-yü Teng and John K. Fairbank,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18391923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与此相反,另一位美国史学家柯文提出了“中国中心论”,提供了另外一种解释。这种解释强调,中国的变化体现得更多的是中国自身的发展逻辑,外来(西方)力量促使甚至促成了中国的变化,但变化并没有改变中国本身的发展逻辑,或者说,中国的变化没有使得中国西方化[注]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如何解释这两种不同的看法?不同学者看法不同,这里并没有对错之分,主要的区别就在于他们所指的变化层面的不同,因为在不同层面,人们看到不同的东西,因而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在思想意识层面,近代以来肯定是“西方化”的。近代以来,中国的语言、概念、理论和思想所呈现出来的都是“西化”的结果,无论是浅层的思考还是深层的思维,无一不和西方有关。到今天为止,思想知识界还没有能力拿出一个基于中国现实并且能够解释中国现实的概念或者理论。现象的背后有很多原因,撮其要者,在于近代文明由西方主导,有人甚至把近代文明等同于西方文明。西方在近代文明的发展和构建过程中,建立起了一整套基于西方近代化发展经验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近代以来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理论,无一不是建立在西方发展经验的基础之上,而这种由区域经验产生的理论,自诞生以来就被作为人类发展放之四海皆准的理论,这使得西方知识体系不仅具有了普世性,同时也被赋予了价值观。
很容易理解,西方学者在解释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时,总是以西方的制度为模版,认为西式的制度模式是先进的,反之就是落后的和需要改造的。这种具有普世性价值观的西方知识体系思考导向,也使得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问题时,总是以中国所没有的东西来解释中国,探讨中国为什么没有西方所具有的东西。从近代早期孟德斯鸠的“中国没有贵族”,到后来的“中国没有私有产权”、“没有法治”、“没有人权”、“没有民主”等等,都是用中国所没有的东西来解释中国的发展。简单地说,近代以来,西方学者从来没有用中国已有的东西来解释中国。其实无论是“冲击回应”模式,还是“中国中心论”,都是在用西方经验所产生的理论,而不是从中国的现实出发来解释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这样的解释与其说是“解释”,倒不如说“判断”。这里的荒唐性不言自明。如果要解释中国,那么必须找到中国所具有的因素。如何用中国所没有的东西来解释中国呢?这是不符合逻辑的。
无疑,近代以来占主导地位的西方知识体系也严重影响和主导了中国学者对自己的认知。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学者对西方文明和知识体系的学习过于“全盘西化”,特别是对西方知识体系的学习,注重知识的吸收而轻方法论的思考。这也正是中国学者尽管在思想和概念方面非常西化,却不能够发展出解释本国社会变迁的理论的原因所在。
这里必须指出的一点就是,即使整个社会科学话语是从西方“进口”,人们也习惯于使用西方概念和理论来解释中国,但这并不否定在更深层次上中国式思维的存在。实际上,这种传统思维根深蒂固,并且不时表露出来,成为一些人抵御西方思想的有效武器。但因为现代社会科学及其思维的缺失,传统思维不能表述为概念和理论,同样不能解释中国的现实。在这个意义上说,传统哲学、国学和文化现象的再生,很难聚合成为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动力;相反,这股力量正在成为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巨大阻力。
在物质变化方面也是如此,表现出诸多西方化的迹象。首先,至少没有人会拒绝西方式的变化。当然,在很短的一段特殊时期里,例如文化大革命时期,人们把西方式物质变化高度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实际上,近代以来到今天为止最长盛不衰的口号“富国强兵”,就是要学习西方物质发展模式。这并不难理解。近代中国被西方所打败,主要是因为西方物质方面尤其是军事方面的进步。在早期,一些人秉持义和团式“刀枪不入”的态度,鄙视西方的物质进步,但在被西方彻底打败后不得不放弃这种态度,转向学习西方。早期学习西方主要是想学习西方的物质进步,等到被亚洲第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昔日的学生日本打败之后,才又意识到光有物质的进步远远不够,还要学习西方的思想。至少就日本本身的解释,其进步是“脱亚入欧”的结果。中国要在物质层面学习甚至赶超西方,这是近代以来大多数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的梦想。从毛泽东时代到当代,“赶超”几乎已经成为中国人的一种“哲学思维”了。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在各个方面落后于西方,并且被帝国主义所包围,提出“赶超西方”还可以理解。今天,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没有面临毛泽东时代那样的地缘政治环境,不过人们仍然具有强烈的“赶超”心态,足见这种哲学的根深蒂固的心理基础。即便是在某一时期部分性地在制度方面借鉴西方,其根本目的也是为了物质文明的进步。比如说1980年代进行政治和经济制度改革,其最终目的是实现“四个现代化”。
最大的分歧在于制度层面。不管怎样的社会,制度是其核心,因为制度是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中介。可以说,没有制度就没有社会。近代以来,就中国的制度如何变化有海量的讨论,但根据历史进程归纳起来,不外乎如下几种。第一,早期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说基本制度不用变革,需要变革的是那些能够解决问题的“术”。第二,“全盘西化”。五四运动之后很长时间里,盛行这种观点。直到今天,此种观点在知识分子中间仍然有一定的市场。第三,“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这是20世纪80年代提出来的观点,当时东亚一些经济体已经或者开始实现民主化,包括日本、韩国和中国的台湾,在这些社会,政治体制民主化了,但社会生活仍然是东亚传统[注]对这几个观点的综合性论述,见Zheng Yongnian, Globalization and State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很显然,近代以来,就制度而言,无论是社会层面,政治层面还是经济层面,中国并没有像思想和物质层面那样西方化。当思想西方化的时候,人们总是以为制度也会西方化;当物质生活西方化的时候,人们总是以为制度也会西方化,更不乏有人呼吁主动的西方化。但从经验层面看,并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在制度层面,有些变化似乎是朝着西方化方向在发展,但结果发现只是浅层的西方化,仅仅只是表象甚至是假象。更有意思的是,在思想和物质越来越西方化的今天,制度层面呈现出越来越中国化的趋向。
此种悖论如何予以解释?一种解释是基因论,即认为中国的制度在不同时期面临不同的思想和物质条件,有能力进行“再生产”,而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黑格尔就是这么解释中国的,他认为中国没有历史。的确如此,如上所述,西方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走到黑格尔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变化眼花缭乱;但中国自从秦始皇帝统一之后,在制度层面没有发生过任何类似西方的变化。
第二种解释强调制度变化的缓慢性[注]史学家钱穆先生在强调中国历史的变迁的同时,指向了中国历史的韧性和一致性。见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物质层面的变化是有限的,因为它往往首先发生在某一个或者几个领域;思想层面的变化最具有局限性,因为它往往只发生在知识界的某些人中间。因为制度乃社会最大多数人的生活调节器,它不会随着物质和思想的变化而变化。在这个层面,人们往往指向既得利益对制度变化的阻碍。如果当社会的大多数就是阻碍变化的既得利益者的时候,制度变化就很难进行。中外历史上,也经常发生通过“消灭”“既得利益”而引入的制度变化,即革命。不过,还没有任何一个社会就这种需要付出巨大的生命代价的变革达成过共识。
第三种解释指向“量变而质不变”,强调建立在世俗文化之上的中国制度的灵活性和伸缩能力。就是说,中国的制度能够吸收消化任何外来的压力,在“量”的层面不断变革自我,而在“质”的层面(也就是在结构层面)“再生产”自己,从而实现自我更新[注]参见Yongnian Zheng and Yanjie Huang, Market in Stat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omination in China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物质、思想层面的变化与制度层面的变化的高度不一致性,直接地反映在了中国近代以来的知识体系上。简单地说,中国的概念理论与制度实践严重脱节,知识体系对制度现实没有解释能力。这种情况自近代到今天,不仅没有变化,反而越来越严重。就以今天人们一直在讨论的“中国道路”为例。中国道路是客观存在的“社会事物”,自近代到今天中国所经历的历程就是“中国道路”。如同前面所讨论的,在物质和思想层面,“中国道路”受西方(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其他“主义”)的影响也属显见,在这两个层面西方的概念和理论能够解释一些东西。然而,在制度层面如何解释“中国道路”呢?
如果不加以“中国化”,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发展史观也解释不了中国制度的演进,更不用说其他西方理论了。例如,在经济制度层面,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的主要概念是“亚细亚生产方式”或者后来的“水利社会”。如果人们搞清楚西方思考中国的思维脉络,那么就不难发现,今天西方指称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就与早先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水利社会”直接相关,或者说后者是前者的思想来源。
很显然,“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与其说是解释中国的概念理论,倒不如说是西方对中国的“偏见”。自古到今,中国的“国家”在经济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并非西方的“国家”所能比拟,甚至经济本身的概念在中西方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抛开其意识形态性质不说,问题在于,“国家资本主义”不能解释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至少从汉代开始,国家始终垄断关键的经济领域。国家对关键经济领域的垄断,决定了中国没有可能发展出西方那样的自由市场经济。但是,这并不是说中国就没有市场,就没有除了国家之外的经济角色。恰恰相反,在大多数历史时间里的大多数经济领域,国家并不是主要的经济角色。除了国家之外,还有民营企业,还有民间和政府的合作。近代的人们把当时的经济分为“官办”、“官督商办”和“商办”是相当科学的。当然,也有外国人开办的经济企业。今天人们称中国经济为“混合经济”,就是指这种复杂的经济形态。当经济活动的半壁江山是非国有且非国有部门的就业人数超越国有部门的时候,就很难用“国家资本主义”来解释中国经济了。
更重要的是在政治制度方面。从古希腊的“东方主义”到近代的“东方专制主义”、20世纪的“极权主义”,再到当代层出不穷的各种版本的“权威主义”,西方对中国的解释只有一个范式。马克思主义对传统中国的解释也是这个范式的一个变种。无论是马克思本人还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对解释中国的贡献就是证明了在“东方专制主义”背后还存在一个经济基础,即“亚细亚生产方式”或者“水利社会”。但正如“亚细亚生产方式”解释不了中国经济,“东方专制主义”也解释不了中国的政治制度。早期西方传教士来中国的时候,他们误以为中国比西方更为“共和”,甚至认为中国才是真正的“共和”体制,即皇帝和大臣(官僚体系)之间的“共和”。这当然是一个假象,因为此“共和”并非西方意义上的“共和”,但也点出了中国皇权体系内部的权力分配的客观状态,这种状态并非“东方专制主义”所能解释。
今天,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的学者,基本上仍然是沿着这个古老的思维范式来解释中国的体制变化,解释这个体制为什么那么具有韧性,但鲜有人解释这个体制到底如何运作,以及用什么样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这个体制。尤其是当中国的社会经济利益高度分化和多元化的时候,怎能仍沿用原来的范式来解释呢?中国学者完全可以通过观察中国体制的实际运作,形成能够解释中国的概念和理论,但这个基本的任务鲜有人感兴趣,导致理论解释严重滞后于中国自身社会变化的局面。直到今天,人们仍热衷于拿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的一切。
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来质疑和怀疑近代以来所形成的中国知识体系,因为这个知识体系是对西方知识体系的简单移植,并不能有效解释中国自身。人们更有足够的理由来重塑中国的知识体系。在实践与人们所接受的理论概念之间出现巨大差异、甚至发生重大矛盾的时候,人们就会惊讶,甚至愤怒,对现实产生巨大的不满。这种情绪在思想意识上可以理解,但在理论构建上则是一无所用。无论哪个社会,在理论与现实不相符合的时候,需要改变的是理论而非现实。因为不管人们喜欢与否,现实是客观存在的。
如何重塑中国的知识体系?对中国的知识界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任务。可以这么说,如果中国学者不能担当起这个责任或者不能完成这一历史使命,那么学者们的思维会一如既往地处于“被殖民”的状态,学者们所扮演的角色充其量也只是西方知识的“贩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