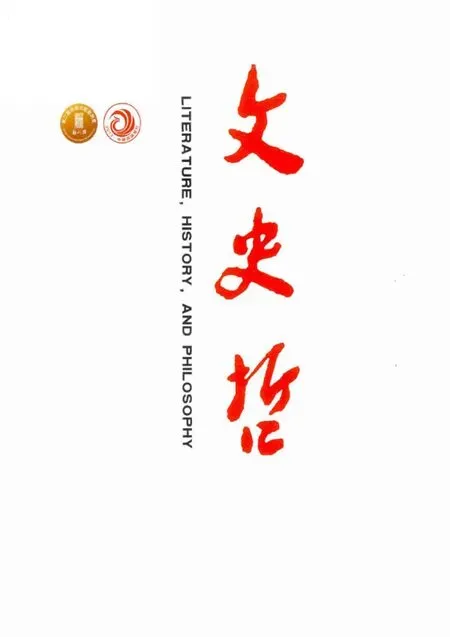儒家传统与中国人类学的学术自觉
麻国庆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2003年,笔者在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讲演会上有个发言,主题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再建构”。在最后的总结中提到中国人类学有两大特点,一为自身社会的人类学,一为国家主义的人类学。在全球化和文化自觉相互交织的今天,专注于异文化研究的人类学家开始思考本文化的研究者在对其熟悉的社会文化进行研究和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特殊取向,即“自身人类学”(Native Anthropology)。与此相联系,人类学在研究一国之内众多的民族、文化、社会的研究对象时,来自国家的力量对于地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相当多的人类学家参与到国家具体的决策和行动之中,由此形成了人类学的另一大领域,即“国家人类学”(National Anthropology)。这两个概念在西方人类学话语里是近几十年较受瞩目的领域,如果把这些概念纳入到中国人类学史的框架中,我们会发现近百年中国人类学的发展特色之一,就是以自身社会为对象的本文化的研究与多民族国家框架下的多元文化及国家建设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与家族结构成为讨论人类学中国研究特别是人类学的学术自觉的重要切入点。
而费孝通先生作为中国人类学的集大成者,他的“三篇文章”——汉人社会、少数民族社会、全球化与地方化的研究和思考,把社会、民族与国家、全球置于相互联系、互为因果、部分与整体的方法论框架,超越了西方人类学故有的学科分类,形成了自己的人类学方法论体系。费先生留下的学术遗产还需要我们不断地继承和发扬,这也是中国人类学学术话语与学术自觉的问题意识。

在人类学家陈其南看来,“家族议题不仅构成儒家学者著作的主题,也是儒家思想理论的核心,更是许多传统文人士绅的社会伦理实践内涵”。“从‘社群’和‘民族’等这些新思想观点出发,探讨如何走出传统总体性的家族意理或儒家‘仁学’思想,我称之为从‘仁学’到‘群学’的轨迹。”[注][日]首藤明和等主编:《中日家族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71页。因此,关注儒家传统是中国人类学学术话语体系的重要基础。兹举几点,以说明儒家与人类学现实研究的关系。
一、儒家思想是中国社会延续的重要基础
中国社会结构的延续性,主要依靠几个方面的基础。首先,是祖先崇拜的宗教性、礼教性的家族伦理范式。中国是“上有祖先,下有子孙”的社会。中国社会的祖先崇拜是社会组织得以延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传统社会结构延续的基础。祖先的力量对于社会关系的维护,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血缘关系清晰的社会集团。以父子关系为特征的延续性,已经扩大成为整个中国文化的主要特性之一。这种延续的观念扩大到整个民族,使数千年历史文化得以延续至今。
其次,是作为传统精神文化的亲子反馈模式。它不仅是延续中国文化的道德规范,更成为中国纵式社会延续至今的关键。纵向的反哺模式不仅存在于从个人到家庭进而扩展到家族的结构体系,而且事实上也外推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和对国家的想象,逐渐建构起一种以家庭成员之间的血缘关系为依据,确定人际关系及其衍生的规范、观念和价值的知识体系。
再次,作为民俗宗教的儒家伦理也是社会延续的重要保障。中国的家观念是与儒家的伦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儒家伦理道德在本质上就是家族伦理孝道,在个人与个人、家庭与家庭、社会与社会、国家与国家之间构建起一条共生之道。因此,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把祖先崇拜看做汉族独立于国家干涉之外的唯一的民俗宗教,对民间社会组织的整合起着重要作用。
此外,儒家思想和家族组织也是基层社会公共性的重要支撑。1949年以前,在中国的南方地区,特别是江西、福建、广东等宗族比较强盛的地区,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力有限,宗族作为地方上的主要社会组织,同时也是地方自治的基本单位。宗族既运用族规家法在自身血缘关系范围内进行自我管理,有效地维护着宗族内部秩序的稳定,还广泛运用各种村规民约维护着乡村社会的公共秩序。宗族作为国家和个人的中介,承担了国家赋役征收、社会公益设施建设以及乡村秩序管理等职能,成为国家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所扶持和利用的主要社会力量。这一时期的宗族实际上构成一种融政治、经济、社会为一体的社会组织,使宗族的公共性具备了政治性、社会性、文化性和公益性的特征。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将权力的触角伸向基层,对传统的宗族和乡村治理体制实施了革命性的政策,否定了宗族的公共性和公益性。但是“文化的宗族”并未消退,包括认同感和归属感在内的宗族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得以保留,为改革开放以来宗族的复兴创造了条件。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思想的不断解放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宗族得以复兴,宗族的公共性得以再生。再生的公共性并不是对传统的完全复制,而是既有继承,也有转变:原有的公益性、社会性和文化性等特征得以延续和保留,而政治性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有所减弱,逐渐转变为一种有限的公共性。
宗族在这些仪式性活动中既扮演着规则制定者角色和文化角色,又扮演着活动组织者、操办者和援助者角色。宗族成员的日常生活,从生到死,从家务处置到社会交往,总离不开宗族组织及其形成的族内人际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宗族已经成为一个社会文化的共同体,使村民对传统的宗族活动仍保持着较高的热情和较强的认同,并积极参与其中。同时,伴随着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自治组织的建立,当代宗族的政治功能已经大大弱化。宗族的家法族规已经被政府制定的村规民约和村民理事会章程所取代。在调解宗族内部纠纷的事务上,宗族的公共性是有限的,需要国家力量的介入。
总之,当代宗族组织的公共性能够上升为乡村社区的公共性,并通过参与国家主导的公共建设,获得国家的认同,成为国家和个体互动的中介。在乡村生活的实践中,当代的宗族因其本身具备的公共性、现代性,正在由传统的血缘组织向现代的公民组织演变,成为“家族化的公民社会”形成的重要基础。由此,我们会进一步展开讨论,儒家传统中的“公共性”与现代社会的关系。
二、儒家思想与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1988年,费孝通先生提出了“多元一体”的重要概念,从中华民族整体出发来研究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及其规律。多元一体的格局,对研究汉族社会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方法,那就是在探讨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互动过程中,必须要考虑汉族与周边的少数民族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形成一个“你看我与我看你”的视角。如此,对于更清楚地认识多元一体社会中的汉族,便有了积极意义。所以面对中国这一多民族的社会,我们应该思考儒学在对汉族周边少数民族社会影响的同时,也要思考其在社会结构上呈现出何种特点。这样说来,汉族社会中儒家思想中的“家观念”便成为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在中国这样一个民族互动非常剧烈的社会中,以一种所谓“纯”的观念,单纯站在汉族的角度去理解汉族文化和社会,可能会找不到亮点。相反,在一些少数民族中,由于和汉族的亲缘和交融关系,已经积淀下了汉族性的社会和文化因子,从中也许会发现一些在汉族现代社会中消失的东西。
三、儒家思想也是研究东亚社会人类学的关键词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东亚经济的发展,人们开始关注东亚经济圈与“儒教文化圈”的关系。例如,韩国学者金日坤教授在《儒教文化圈的秩序和经济》中指出,儒教文化的最大特征是以家族集团主义作为社会秩序,以此成为支撑“儒教文化圈”诸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但是,即使东亚社会都接受了中国的儒学,不同的社会对于儒学的取舍和吸收的重点也不尽相同。如日本的儒教理论,与中国相类似的就是特别强调儒教的家族主义传统,把“孝行”和“忠节”作为人伦的最主要的道义。但由于特殊的神道作为一个变量介入家与国之间,便更加突出了“忠”的位置,把“忠”作为最高的“德”,把“孝”附属于“忠”之下。这就与中国社会把“孝”作为以血缘为基础的家或族内的一种纵式关系完全不同,而更强调“忠”作为一种对己而言的“家”外关系。所以在社会结合的本质上,日本更为突出的是集团的概念,而中国更为突出的乃家族主义。
在以大传统的儒家文化为基础的社会中,社会结构上的同异性问题,就成为东亚社会的人类学研究的突出特征。虽然,家族主义与家族组织、亲属网络与社会组织、民间结社与民间宗教组织等,都是东亚社会非常有特点的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如中国、日本和韩国,都用相同的汉字表示“家”,其内容却完全不同。这就需要从社会、文化因素诸方面探讨其各自的特征,通过家、亲戚、同族的概念异同,说明“家”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家、宗族、村落及社会结构的比较,进而探讨各自的异同,所以说“家”的研究是探讨东亚社会基础的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