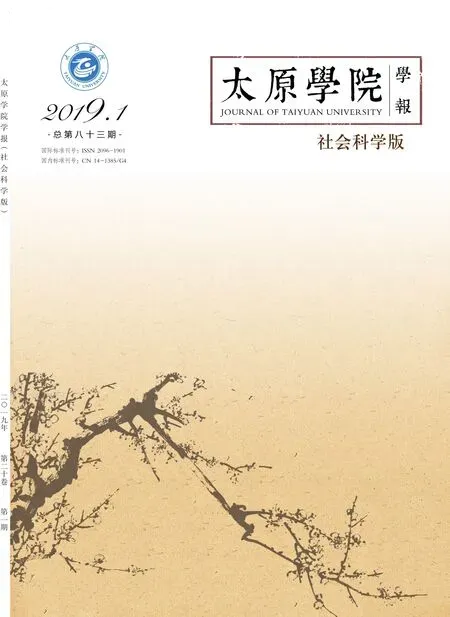论袁宏道“狂”的思想根源及历史影响
刘硕伟
(临沂大学 沂蒙文化研究院,山东 临沂276005)
作为晚明重要作家和文学理论家的袁宏道(1568-1610),学界通常认为其贡献在于提出了反对复古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这固然正确。但是,如果就此而止,不将问题推向深入,就忽视了袁宏道最鲜明的个性特征及最基本的诗学策略。袁宏道不仅有“性灵”说,更是在大量诗歌、散文及书信中反复论“狂”。他的“狂”论,体现着个性自由,指向着生命意义,不仅是一种人格期许,也是一种诗学策略和美学标准。“狂”较“性灵”更能反映他的思想实质,更能体现他的理论贡献,也有着更广泛的思想根源和更深远的历史影响。
一
袁宏道的生命比较短暂,但相当饱满。他从十七岁成为诸生,始作诗文,至四十三岁去世,一直以狂士自居,三仕三隐,二十六年间留下大量诗歌、论文、杂著,成为晚明诗坛最耀眼的作家。
袁宏道自少即表现出不同凡俗的狂者气质。据袁中道《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以下简称《行状》)载:袁宏道四岁时,穿着云纹新鞋,其舅龚孝廉(仲敏)随口说:“足下生云。”袁宏道应声答:“头上顶天。”以至“孝廉大骇”。又载,“年方十五六,即结文社于城南,自为社长。社友年三十以下者,皆师之,奉其约束,不敢犯”。[1]755可见袁宏道意气之豪。这位名著乡里的少年豪俊,喜用“狂歌”入诗,爱以“狂生”自许。如,万历十四年(1586)《病起偶题》:“独坐真成闷,孤砧急暮声。乾坤偏恶道,世路几狂生。”[2]10同年冬作《冬菊》,用陶潜采菊东篱及李白痛饮狂歌之意象:“惊心寒节破,载酒故人来。忽忆东篱叟,狂歌试举杯。”[2]48
未仕之前,袁宏道即流露出不愿受官场束缚的意愿。万历十六年(1588)袁宏道参加乡试,中举。然而次年会试失利。返乡后有《偶成》诗:“谁是乾坤独往来,浪随欢喜浪悲哀。世情到口居然俗,狂语何人了不猜。彭泽去官非为酒,漆园曳尾岂无才。百年倏忽如弹指,昨日庭花烂熳开。”[2]28“世情到口”是对俗世的批判,“狂语何人”是对自己的期许。何宗美先生说:“一个‘狂’,在此并不是给李贽的评价,而是给自己下的一断语。”[3]78十九年(1591)秋,袁宏道再次北上,参加次年会试。途中,登易州黄金台,有《登台》诗:“登台当此日,潦倒尽余欢。古木何年有,林花尽日寒。霞来鳞作市,山晚气成澜。去去沧江暝,狂歌兴未阑。”[2]48-49在萧瑟的秋日傍晚,远离故土的诗人没有怀乡之愁,只有狂歌不止,其豪放可知。次年(1592)三月,袁宏道进士及第,其后归乡侯选。袁中道回忆这段时光:“忆予与二郎二十四五时,视钱如粪土。与酒人四五辈,市骏马数十蹄,校射城南平原;醉则渡江走沙市,卧胡姬垆旁,数日不醒。寘酒长江,飞盖出没波中,歌声滂湃。”[1]444放浪形骸的乡居生活让袁宏道十分满意。《郊外小集》:“浪迹真无赖,狂心今若何。一尊聊对酒,万事且狂歌。”[2]89但这种生活没有持续太久。二十二年(1594)袁宏道赴京候选,十二月,授吴县令,次年二月离京赴吴,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
但令家人及朋友想不到的是,在上任的第二年袁宏道就屡上《乞归稿》,请求致仕。二十五年(1597)春,又连续呈牍求去,获准。袁宏道为何在仕途之始就匆匆离职呢?应当说,社会风气对他有很大影响。上任当年,袁宏道给他的堂叔写信说:“金阊自繁华,令自苦耳。何也?画船箫鼓,歌童舞女,此自豪客之事,非令事也。奇花异草,危石孤岑,此自幽人之观,非令观也。酒坛诗社,朱门紫陌,振衣莫厘之峰,濯足虎丘之石,此自游客之乐,非令乐也。令所对者,鹑衣百结之粮长,簧口利舌之刁民,及虮虱满身之凶徒耳。”[2]221他在同一时期给其他人的信中,也无不大叹为官之苦。当然,客观环境的影响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袁宏道追求自适的性格起到更大作用。他的“四种人”及“五快活”之说,就是这种性格的鲜明表达。二十三年(1595)他在给徐大绅的信中把人分为玩世(道家)、出世(佛家)、谐世(儒家)以及适世四种。对于前三种,他认为都有很大不足,即便是“谐世”的儒家,也是“用世有余,超乘不足”。所以他说:“独有适世一种其人,其人甚奇,然亦甚可恨:以为禅也,戒行不足;以为儒,口不道尧舜周孔之学,身不行羞恶辞让之事,于业不擅一能,于世不堪一务,最天下不紧要人,虽于世无所忤,而贤人君子则斥之惟恐不远矣。弟最喜此一种人,以为自适之极,心窃慕之。”[2]217这种“适世”,实际是融合儒释道而张扬生命个性的一种人生态度。同年,他在给舅父龚仲庆的信中提出“五快活”。如“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谈”等,皆感官之乐。甚至“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亦为一快活。并且宣称:“士有此一者,生可无愧,死可不朽矣。”[2]205-206其语或有戏谑之意,但真实地反映了袁宏道对“适意”“任性”生活的向往。
解除吴县令之后,袁宏道先是寓居无锡,后又与友人陶望龄(字周望,号石篑)作东南之游,游山玩水,切磋诗艺,历时三月有余,足迹二千余里。《行状》云:“先生之资近狂,故以承当胜;石篑之资近狷,故以严密胜。两人递相取益。”[1]758杭州临别,袁宏道赋《别石篑》十首,诗中屡用“狂”字。如,其三:“三入净寺门,寺僧笑狂呆。”似贬抑,又似褒扬。其四:“谁家薄福缘,生此两狂子?”似自嘲,又似自负。其八:“狂态诚可取,其若头上巾。”[2]404用陶渊明《饮酒》“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之意。此外还有《湖上别同方子公赋》七首,诗意相近。如,其三:“醉中发狂思,醒后益周张。”[2]410其六:“安得清神药,止我狂华心。”[2]411
二十六年(1598)袁宗道致信促宏道至吏部就选。宏道北上京师,任京兆校官。次年(1599)三月,升国子监助教。宏道所居为闲官,终日以读书为事。即使读书,也显出狂者姿态。他在《答王以明》信中说:“近日始学读书……古人微意,或有一二悟解处,辄叫号跳跃,如渴鹿之奔泉也。”[2]772二十八年(1600)授礼部仪制主事。数月之后,即请告归。未几,宗道去世。宏道感念不已,更无复宦情,乃于公安城南筑柳浪馆。此后六年,或高卧柳浪,或游历吴越,看山听水,角诗论学。其《新买得画舫将以为庵因作舟居诗》其一:“拟将船舫作庵居,载月凭风信所如。鱼鸟教他为侍史,云烟呼我作尚书。”似乎完全融入寂静的自然。其二:“囊中随意贮青蚨,歌吹虽喧不可无。隐逸也须添故事,江山真合点狂夫。”[2]909作者认为,即使隐逸,也要搞出点青蚨(代指金钱)、歌吹的花样,如此江河山岳,正适合自己这般如曾点一样放荡不羁的人。
然而袁宏道并未完全忘却儒家用世情怀。三十一年(1603)在给友人信中说:“山中粗足自遣,便不思出,非真忘却长安也。”[2]1255加上父亲的督促、经济的窘迫等多种原因,他决定复出为官。三十四年(1606)秋,补仪曹主事。但是,第二年他的妻子李安人就病故了。宏道乃以存问蒲圻谢公(已致仕垂三十年的右都御史谢鹏举)之便,扶柩南归,三十六年(1608)二月抵里。他本有“山栖之志”,而归途中新的任命已下,旋入京,补吏部验封司主事。翌年(1609)典试秦中。试毕,与陕西右布政汪可受等同游秦中名胜。他的《华顶示同游樗道人》诗云:“芙蓉一削五千仞,不是狂夫不上来。”[2]1452考功事竣,请假南归,“有意栖迟,遂定卧游之计”。其《醉归》诗:“不寐即狂歌,莲花漏水多。醉来寻白足,定起唤青娥。梵唱嗔吴肉,荷衣剪越罗。亦知风景煞,争奈老颠何!”[2]1078
二
袁宏道“狂”的思想,受多元文化因素影响。其中既有魏晋名士风度及道家思想的影响,也有佛教禅宗及作为时代哲学的晚明心学的影响。
盛于魏晋的名士风度是袁宏道效法的榜样。《晋书》载:“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后进之士,莫不景慕仿效,选举登朝,皆以为称首,矜高浮诞,遂成风俗。”[4]1236何晏等人服五石散,注重仪容修饰,对当时社会风气有很大影响。鲁迅先生《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说:“何晏他们以外,又有一个团体新起,叫做‘竹林名士’,也是七个,所以又称‘竹林七贤’。正始名士服药,竹林名士饮酒。竹林的代表是嵇康和阮籍。”[5]532袁宏道诗中多有称引阮籍、嵇康之句。如,《长陵》其二:“天幸酒伯多知音,嵇阮贺李相推许。”[2]646《归来》:“野服科头常聚首,阮家礼法向来疏。”[2]60当袁宏道再仕京师的第二年,其妻及媵婢染病去世,扶柩南归途中,小修赋诗相送。宏道《潞河舟中和小修别诗,次韵》相答。在这种“不胜酸楚”之中,他仍然未能忘怀其狂:“慢世稍同朔,绝交亦似康。东皋犹滞酒,余乃醒而狂。”[2]1353认为自己的玩世不恭与东方朔稍同,与不合性情之人绝交的爽快利落和嵇康差不多,王绩(号东皋子)虽然性情简傲,却滞情美酒,自己才是“醒而狂”的超脱者。悲凄无限,犹能称狂,可见他对“狂”的深切认同。名士风度之实质,是魏晋之际名教危机背景下,士人个体自觉但又无路可走的一种无可奈何的痛苦排遣。而袁宏道的深层心理与阮籍、嵇康也是一样的,都在看似洒脱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痛苦。如《显灵宫集诸公,以城市山林为韵》:“言既无庸默不可,阮家那得不沉醉。眼底浓浓一杯春,恸于洛阳年少泪。”[2]651西汉贾谊年少才高,深遭嫉妒,三十三岁而终。袁宏道认为,他像阮籍一样的沉默,却有着比贾谊更深刻的痛苦。
名士风度背后是道家思想。当现实无路可走,士人便想起宁愿“曳尾泥途”的庄子。然而拒绝楚王之聘的庄子生活并不“逍遥”,而是“槁项黄馘”“感慨无端”。这是庄子的困境,也是末代儒士的困境。袁宏道在诗文中常常抒发庄老思想。《夏日即事》:“世事输棋局,不情转辘轳。浮生宁曳尾,断不悔江湖。”[2]83完全是对庄子思想的诠释。《夏日邹伯学园亭》:“兀坐无俦侣,观空绝想尘。床头高士传,花下上皇人。养鹤移茶灶,怜鱼辍钓纶。蒙庄去已久,斯意竟谁陈。”[2]82充满了隐士的闲情逸致。他在《朱司理》信中说:“曳尾山中,但得任意歌咏,鼓吹休明足矣!”[2]303又在《识张幼于箴铭后》中说:“率性而行,是谓真人。”[2]193物我一体、率真适意的生活,真正做到是很难的。自玄风煽起以来,陶渊明可谓第一位达到这一境界的人。陶渊明能够在“误落尘网”之后全身而退,采菊东篱,诗酒自娱,让袁宏道十分羡慕。羡慕不得,遂生感慨。其《偶成》诗:“嵇叔终疑傲,陶潜总任真。只因图事简,不敢恨家贫。宦邸为欢少,乡书报死频。弥天都是网,何处有闲身。”[2]123他屡以陶潜自况,如《乞归不得》:“不放陶潜去,空陈李密情。有怀惭狗马,无路达神明。竹影交愁字,莺啼作怨声。但凭因果在,陨血誓来生。”[2]118陶渊明有采菊东篱的悠然,不仅在于玄学修养及儒家的观念,更在于佛家万有皆空的思想。袁宏道也为自己指出了摆脱世俗纠缠的答案,那就是倡因果、修来生的佛教。
袁宏道深于佛学。十八岁有诗:“空江隐隐流清梵,别壁沉沉起暮钟。昏黑谈经人不去,知君学佛意初浓。”[2]4-5可见彼时已对佛教经典有深厚兴趣。袁中道《解脱集序》说:“及我大兄休沐南归,始相启以无生之学。自是以后,研精道妙,目无邪视,耳无乱听,梦醒相禅,不离参求。每于稠人之中,如颠如狂,如愚如痴。五六年间,大有所契,得广长舌,纵横无碍,偶然执笔,如水东注。”[2]451二十二年(1594)已进士及第的袁宏道赴北京候选,游览寺庙时有《宿僧房》诗,曰:“夜雨沉清磬,霜林起暮鸦。莲台三品叶,佛果一时花。觉路昏罗縠,禅灯黑绛纱。早知婴世网,悔不事袈裟。”[2]95可见佛教的出世思想对他影响已是非常深刻。二十五年(1597),袁宏道在给张幼于的信中说:“仆自知诗文一字不通,唯禅宗一事不敢多让。当今劲敌,唯李宏甫先生一人,其余精炼衲子,久参禅伯,败于中郎之手者往往而是。”[2]503显示出对自己禅学修养的高度自信,也反映了狂禅思维对他的影响。袁宏道有一首题为《狂歌》的诗:“六藉信刍狗,三皇争纸上。犹龙以后人,渐渐陈伎俩。嘘气若云烟,红紫殊万状。醯鸡未发覆,瓮里天浩荡。宿昔假孔势,自云铁步障。一闻至人言,垂头色沮丧。”[2]40诗中对儒道文化传统提出质疑,蔑视六经、三皇,否定假借孔子的虚伪权威,将李贽这样的狂者奉为“至人”。黄宗羲谓泰州之后的狂儒“掀翻天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6]821此诗可做生动的注脚。不过,袁宏道进京任职期间(1598-1600)思想有所变化。《行状》说:“逾年,先生之学复稍稍变,觉龙湖(指李贽)所见,尚欠稳实,……遂一矫而主修,自律甚严,自检甚密,以淡守之,以静凝之。”[1]758他修持净土的收获,即是《西方合论》的问世。袁宏道在《西方合论引》中说:“余十年学道,堕此狂病,后因触机,薄有省发。遂简尘劳,归心净土。……如贫儿得伏藏中金,喜不自释。”[2]1638但不久之后,他又转回到激进的禅悟立场。他在《德山麈谭》中说:“我只要个英灵汉,担当此事耳。夫心行根本,岂不要净?但单只有此,亦没干耳。此孔子所以不取乡愿而取狂狷也。”[2]1295乡愿有形式而舍价值,故谓“德之贼”。取狂狷者,并非为其形式,而是为价值而不拘形式。
袁宏道对心学的推崇是随处可见的。二十六年(1598)他在答梅国祯的信中说:“仆谓当代可掩前古者,惟阳明一派良知学问而已。”[2]738三十二年(1604)《为寒灰书册寄郧阳陈玄朗》说:“至近代王文成、罗盱江辈出,始能抉古圣精髓,入孔氏堂,揭唐、虞竿,击文、武铎,以号叫一时之聋聩。”[2]1226这说明阳明心学是袁宏道求学论道的首选。袁宏道写这些信时,罗汝芳已去世,更遑论王阳明了。对袁宏道有直接影响的,是李贽。万历十九年(1591)袁宏道初次拜会李贽,即深受其影响。中道说:“先生(指袁宏道)既见龙湖(指李贽),始知一向掇拾陈言,株守俗见,死于古人语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至是浩浩焉如鸿毛之遇顺风,巨鱼之纵大壑。能为心师,不师于心;能转古人,不为古转。发为语言,一一从胸襟流出,盖天盖地,如象截急流,雷开蛰户,浸浸乎其未有涯也。”[1]756可见这次会见对袁宏道影响之大。此后袁宏道对李贽以师相称。二十一年(1593),袁宏道再次拜会李贽,临别作诗八首相赠。李贽赋诗八首相答。诗中可见二人思想、情感深相契合。二十五年(1597)九月,李贽至北京,寓居极乐寺,袁宏道前往拜访,李贽作《九日至极乐寺闻袁中郎且至喜而赋》。李贽的思想十分驳杂,但总体而言仍为心学支派,终在儒家界内。二十九年(1601),七十五岁的李贽寓居河南商城黄蘖山中,成《言善篇》一书。该书之《对教小引》曰:“余自幼读圣教不知圣教,尊孔子不知孔子何自可尊。所谓矮子观场,随人说妍,和声而已。是余五十以前真一犬也。”[7]196李贽认为,五十岁前他虽然尊崇“圣教”,不过是人云亦云。五十岁后,研读佛经,而后再习儒典,乃洞彻圣教之真义。李贽的“狂”论,实际上是发挥了儒家经义中强调主体性的部分。
三
儒家有三德之说。《尚书·洪范》:“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孔颖达疏:“此三德者,人君之德张弛有三也。一曰正直,言能正人之曲使直。二曰刚克,言刚强而能立事。三曰柔克,言和柔而能治。”对应三德,就有三种处世方式或人生态度:中行、狂、狷。《论语·子路》:“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孟子解释孔子此言:“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又说:“如琴张、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谓狂矣。”(《孟子·尽心下》)
李贽在《焚书》中借孟子的观点对“狂者”作出更明确的阐释:“又观古之狂者,孟氏以为是其为人志大言大而已。”何谓“志大言大”?他说:“盖狂者下视古人,高视一身,以为古人虽高,其迹往矣,何必践彼迹为也。是谓志大。以故放言高论,凡其身之所不能为,与其所不敢为者,亦率意妄言之。是谓大言。……是千古能医狂病者,莫圣人若也。故不见其狂,则狂病自息。又爱其狂,思其狂,称之为善人,望之以中行,则其狂可以成章,可以入室。仆之所谓夫子之爱狂者此也。”[8]182认为狂者虽有大言、乱言的缺点,但本质近于圣人,只是环境逼迫使他不得不如此。李贽在《与耿司寇告别》中说:“狂者不蹈故袭,不践往迹,见识高矣。所谓如凤凰翔于千仞之上,谁能当之?”[8]67这种思想与王阳明一脉相承。
王阳明曾多次强调自己的“狂者胸次”。嘉靖二年(1523)五十二岁的王阳明对弟子说:“吾自南京已前,尚有乡愿意思。在今只信良知真是真非处,更无掩藏回护,才做得狂者。”[9]1287黄宗羲《明儒学案》亦载此言,文字略有出入:“我在南都以前,尚有些子乡愿意思。在今信得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才做得个狂者胸次,故人都说我行不掩言也。”[6]241王阳明所说的“狂者”是什么样的人呢?他说:“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纷嚣俗染,举不足以累其心,真有凤凰翔于千仞之意,一克念即圣人。”[9]1287-1288阳明所谓狂者,乃近圣之人,其精神饱满而张扬,一念之间即可越入圣域。阳明本意,是强调主体性,强调主体的个性与自由。《传习录》载阳明与弟子论“仲尼与曾点言志”,说:“以此章观之,圣人何等宽洪包含气象!且为师者问志于群弟子,三子皆整顿以对。至于曾点,飘飘然不看那三子在眼,自去鼓起瑟来,何等狂态!及至言志,又不对师之问目,都是狂言。设在伊川,或斥骂起来了。圣人乃复称许他,何等气象!圣人教人,不是个束缚他通做一般。只如狂者便从狂处成就他,狷者便从狷处成就他。人之才气如何同得?”[9]104嘉靖三年(1524)王阳明与弟子共度中秋,作《月夜》:“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9]787
很有意思的是,不仅王阳明、李贽都使用了“凤凰翔于千仞之上”这一意象,朱熹也说过:“曾点之志,如凤凰翔于千仞之上。”[10]1026又说:“且看莫春时物态舒畅如此,曾点情思又如此,便是各遂其性处。尧舜之心,亦只是要万物皆如此尔。”[10]1034可见肯定曾点之狂,认同各遂其性,从孔子到朱熹再到王阳明、李贽、袁宏道,是一脉贯通的。
以狂者自居的袁宏道更注重对“狂”的追根溯源的阐释。他主试陕西时作对策呈文,集中表达了他关于“狂”的思想。他先是引述了《论语》“四子侍坐”一章,接着提出问题:夫子何以赞叹曾点?袁宏道认为,夫子之所以“喟然与之”,在于曾点之“识趣”。他感叹说:“噫,世但知才气之可以集事也,而恶知妙天下之用者在识趣也?才气如疾风振落,枯朽自除;识趣如明月澄空,万象朗徹。是故以点论三子,觉宇宙之自清,而经世者之搅扰也。夫凤凰之翔于千仞也,骞翥未毕,而天下之鸟,已黯然无色矣。此夫子之所以与点也。与其用之大,而非谓其不用也。夫点固圣门之所谓狂士也。世人不知狂为何物,而以放浪不羁者当之,则谓点一放浪不羁之士,而何与于治天下?不知夫子思中行,而狂即次之。”[2]1518可以看出,原儒的价值系统对他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狂的本质,是对个性的肯定、对自由的追求。狂是儒家价值系统中固有的因素。只是在不同阶段,这一因素被忽视或压抑,袁宏道要做的,就是将其发扬光大。
四
袁宏道对晚明狂放士风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与友人之恣情山水、放歌酒肆,固无论矣,他还把狂作为一种理想人格,以之自许,且以许人。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张幼于》诗:“家贫因任侠,誉起为颠狂。盛事追求点,高摽属李王。鹿皮充卧具,鹊尾荐经床。不复呼名字,弥天说小张。”[2]145-146格调十分高亢,似乎一个任侠与癫狂之士呼之欲出。但是,作为一个专注制艺的儒生,张献翼(字幼于)本人并不接受。二十五年(1597)袁宏道又写信解释:“仆往赠幼于诗,有‘誉起为颠狂’句。颠狂二字甚好,不知幼于亦以为病。……夫颠狂二字,岂可轻易奉承人者?狂为仲尼所思,狂无论矣。……不肖恨幼于不颠狂耳,若实颠狂,将北面而事之,岂直与幼于为友哉!”[2]502-503据《万历野获编》载,张献翼由于科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而有“怪诞”之行。[11]582但从他的作品看,他是一个言论谨慎的人。其晚年狂行,一方面由于科场打击,一方面由于世风影响。其中与袁宏道以“狂”期许,或许不无关系。袁宏道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弟尝谓天下有大败兴事三,而破国亡家不与焉。山水朋友不相凑,一败兴也;朋友忙,相聚不及,二败兴也;游非其时,或花落山枯,三败兴也。”[2]506这种狂放或许有些矫情。这种矫情与儒家精神式微相表里,折射出儒学在晚明的困境。
狂不仅是袁宏道的人格期许,也是他最基本的诗学策略。这种策略体现在宣扬诗学主张及进行诗歌创作两个方面。
首先,在宣扬诗学主张时,袁宏道具有睥睨古今的气概、破而不立的旨趣。佛教善于运用“但遮其非,不言其是”的“遮诠”法。特别是狂禅派诃佛骂祖,掀翻天地,以狂为传道悟道的基本手段和特征。袁宏道深受狂禅风气影响,自谓“余性狂僻,多诳诗,贡高使气,目无诸佛”。[2]465又说:“除却袁中郎,天下尽儿戏。”[2]403所以,他常以非凡的勇气对文坛进行广泛否定。例如,他在《张幼于》信中说:“世人喜唐,仆则曰唐无诗;世人喜秦,仆则曰秦汉无文;世人卑宋黜元,仆则曰诗文在宋、元诸大家。”[2]501又如《答李子髯》诗:“若问文章事,应须折此心。中原谁掘(崛)起,陆地看平沉。矫矫西京气,洋洋大雅音。百年堪屈指,几许在词林。”[2]81以中原陆沉喻文坛之全军覆没,指责前后七子的复古潮流虽有百年之久,但不能在词林留下什么。这样的句子,并非一时意气之作,而是有着清醒认识的刻意经营。袁宏道的目的,就是要“力矫弊习,大格颓风”。他在给李子髯的信中说:“弟才虽绵薄,至于扫时诗之陋习,为末季之先驱,辨欧、韩之极冤,捣钝贼之巢穴,自我而前,未见有先发者,亦弟得意事也。”[2]763这种“扫”与“捣”,往往尽现狂士姿态。例如他常常称古人或时人为奴仆、奴儿。在《答梅客生开府》中说:“空同(李梦阳)才虽高,然未免为工部奴仆,北地(李梦阳)而后,皆重儓(奴仆的奴仆)也。”[2]734《喜逢梅季豹》:“举世尽奴儿,谁是开口处。我击涂毒鼓,多君无恐怖。”[2]387禅宗往往只破不立,或以破为立。袁宏道在激烈的否定之后,也不做理论建树。因为在他看来,任何理论都会带来束缚。他说:“拘儒小士,乃欲以所常见常闻,辟天地之未曾见未曾闻者,以定法缚己,又以定法缚天下后世之人。”[2]796他不欲缚己缚人,睥睨古今却破而不立。
其次,在进行诗歌创作时,袁宏道具有冲决束缚、不循理路的勇气,并选择宁今宁俗、不求典雅的表达方式。袁宏道既不打算创立任何诗学规范,也不打算在诗歌创作时遵循任何规范。他说:“至于诗,则不肖聊戏笔耳。信心而出,信口而谈。”[2]501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的诗,不合平仄处比比皆是,甚至也不讲句法。如《别石篑》诗十首,有五言,有四言,有杂言,最后一首只有三句。他不仅不受诗体的限制,于炼字亦殊不经意,诗中多用平淡、俚俗、俳谐之语。平语者,如《新安江》其三:“怪石穿江出,江寒石亦寒。或从舟底见,或作假山看。聚客多茶店,逢人上米滩。溪流虽较险,下水也平安。”[2]392俚语者,如《得家报》:“清晨阁外逢乡使,持得平安书信来。初问三哥何处去,次言八口几时回。”[2]560俳语者,如《天目书所见》:“独有知见人,不食本分草。拾他粪扫堆,秘作无价宝。”[2]377-378他在为江进之《雪涛阁集》所作序中回答有人对江进之诗“近平、近俚、近俳”的非难,实际表达了他自己这样做的原因:“矫枉之作,以为不如是,不足以矫浮泛之弊,而阔时人之目也。”[2]711
虽然说袁宏道睥睨古今、破而不立,但不可能没有理论倾向。学界一般认为袁宏道的理论贡献在于提出性灵说。然而“性灵”并非袁宏道的首创(很多早于袁宏道的作家如屠隆、焦竑、汤显祖、李维桢等都曾多次论及),也不是袁宏道论述的重点(在《叙小修诗》中赞扬袁中道的诗:“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在《叙呙氏家绳集》中说:“不可造,是文之真性灵也。”)。袁宏道更着意一个“狂”字,在人格上以“狂”自许,在诗坛上以“狂”为策略,在关于诗的美学特征上,则提倡基于“狂”的“趣”和“韵”等审美范畴。
袁宏道将狂者之“趣”用于论诗。他在专门论“狂”的《策·第五问》中列举了张良、谢安、狄仁杰、陶渊明、李白等五位狂者,说:“夫张子房、谢安石、狄怀英三人者,古今所称人杰也,夷考其用,皆以识趣。”[2]1518“若晋之陶潜、唐之李白,其识趣皆可大用。”[2]1519最后总结说:“盖曾点而后,自有此一种流派,恬于趣而远于识。无蹊径可寻,辟则花光山色之自为工,而穷天下之绘不能点染也;无辙迹可守,辟则风之因激为力,因窍为响,而竭天下之智,不能扑捉也。其用也有入微之功,其藏也无刻露之迹,此正吾夫子之所谓狂,而岂若后世之傲肆不检者哉?夫傲肆不检,则《鲁论》所谓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者,游谈不根之民而已矣。”[2]1520-1521既然狂士并非“傲肆不检”而是“识趣”,既然“妙天下之用者在识趣”,那么妙天下之文者也是“趣”。趣之于主体,是对人的本性的肯定;趣之于文本,是对诗的本色的宣扬。质言之,“趣”是袁宏道基于主体之狂的关于文本审美特征的重要主张。袁宏道有很多“趣”论。如在《叙陈正甫会心集》中说:“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当其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也。面无端容,目无定睛,口喃喃而欲语,足跳跃而不定,人生之至乐,真无逾于此时者。《孟子》所谓‘不失赤子’,《老子》所谓‘能婴儿’,盖指此也——趣之正等正觉最上乘也。”[2]1542这是“趣”之于人。在《西京稿序》中提出“夫诗以趣为主”。[2]1485又在《与李龙湖》中说:“仆尝谓六朝无诗,陶公有诗趣,谢公有诗料,余子碌碌,无足观者。”[2]750这是“趣”之于诗。陆云龙说:“中郎叙《会心集》,大有取于趣。小修称中郎诗文云率真,率真则性灵现,性灵现则趣生。即其不受一官束缚,正不蔽其趣,……中郎遂自成一中郎矣。”[2]1721拈出一个“趣”字,可谓知味之言。
“趣”之外,袁宏道还经常使用“韵”的概念。用于人,则“高人韵士”或“幽人韵士”;用于声音,则“韵致高远”或“韵致悠扬”;用于物,有“松韵”“泉韵”;用于诗,则有“气韵”“风韵”等。当然,以“韵”来标示一种审美质性,不始于袁宏道。但是,袁宏道强调“韵”是诸如“稚子”“醉人”等不受约束之人(狂者)的表现。他在《寿存斋张公七十序》中说:“故叫跳反掷者,稚子之韵也;嬉笑怒骂者,醉人之韵也。醉者无心,稚子亦无心,无心故理无所托,而自然之韵出焉。”[2]1541稚子与醉人之叫跳反掷、嬉笑怒骂之所以称“韵”,皆因其“无心”。“无心”即无刻意经营之心,也就是自然而然。在“无心”论之后又提出“纵心”的主张,认为:“纵心则理绝而韵始全。”[2]1542不论无心还是纵心,都强调不受既定规范的约束,强调自然而然的表达。那么,韵之于文本,也是一种自然之美的呈现。如他评价李攀龙和王世贞“于鳞有远体,元美有远韵”。[2]1248总之,狂可以识趣,狂可以得韵。“韵”与“趣”都是基于主体之狂而达于诗歌文本的重要美学标准。
袁宏道“狂”的诗学策略对晚明文坛产生了巨大影响。首先,袁宏道狂者遮诠法猛烈涤荡了文坛复古模拟风气。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说:“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12]567朱彝尊说:“一时闻者涣然神悟,若良药之解散,而沉疴之去体也。”[13]478其次,袁宏道信手信口的诗歌创作深刻影响了当时文坛。袁宗道说:“岑寂中读家弟诸刻,如笼鸲鹆,忽闪林间鸣唤之间,恨不即掣绦裂锁,与之偕飞。”[14]214袁中道说:“余以濩落,依之真州,相见顷刻,出所吟咏,捧读未竟,大叫欲舞。”[1]451-452汤显祖读了袁宏道的《锦帆集》,谓之“明月珠子,的皪江靡”。[15]1359梅守箕《读袁中郎诗》曰:“君有昆吾刀,切玉如切泥。……愧我十年间,冶容效蛾眉。”[16]434袁宏道诗文集在晚明成为竞相翻刻的“畅销书”。毕懋康《袁中郎先生全集序》谓:“悬日月而走南北,则人人知当世有中郎矣。……乃中郎之曩集出,则啧啧欣赏,至有闭门索句,欲效之以妙天下者。”[2]1713
五
入清之后,袁宏道其人其诗皆不被推崇,甚至成为攻击的对象。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世人竞说袁中郎”,袁宏道居然成为学界和社会热点。
最早把五四运动与晚明思潮联系起来并且把袁宏道宣传推广成学界热点的是周作人。1932年他在辅仁大学作了系列演讲,同年9月整理成《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该著认为:“今次的文学运动,和明末的一次,其根本方向是相同的。”[17]51“假如从现代胡适之先生的主张里面减去他所受到的西洋的影响,科学、哲学、文学以及思想各方面的,那便是公安派的思想和主张了。”[17]23受周作人的启发,林语堂热衷研读袁宏道的作品。其《四十自叙诗》云:“近来识得袁宏道,喜从中来乱狂呼。宛似山中遇高士,把其袂兮携其裾。又似吉茨读荷马,五老峰上见鄱湖。从此境界又一新,行文把笔更自如。”[18]502林语堂创议重印《袁中郎全集》,郁达夫、刘大杰、周作人等为之作序。周作人的序,申明了重印袁宏道著作的必要,评价了袁宏道不同类型的作品,反驳了清代以来称袁宏道作品为亡国之音的谬说。《袁中郎全集》的出版以及《论语》《人间世》等杂志的发行,使“袁中郎”成为持续升温的话题,以致形成文化界无人不谈袁中郎的氛围。
面对这种风气,左翼作家展开了疑问和批评。阿英《袁中郎与政治》说:“世人竞说袁中郎,世人竞学袁中郎,可是所说的中郎,究竟能有几分像,所学的中郎,究竟还是姓袁不?”[19]77鲁迅先生《“招贴即扯”》说:“就以现在最流行的袁中郎为例罢,既然肩出来当作招牌,看客就不免议论这招牌,怎样撕破了衣裳,怎样画歪了脸孔。……现在的袁中郎脸孔究竟画得怎样呢?时代很近,文证俱存,除了变成一个小品文的老师,‘方巾气’的死敌而外,还有些什么?”[20]235接着引用《顾端文公年谱》中袁宏道“过劣巢由”的例子证明“中郎还有更重要的方面”。袁宏道确实不仅有纵情山水、放浪形骸的名士之狂,还有果敢刚强的志士之狂。如,他的《送刘都谏左迁辽东苑马寺簿》:“奇谋若可展,簿尉何足厌。胸臆不得行,三公犹为贱。”[2]579即为志士之狂。其志士之狂不仅见于诗文,更是见诸行动,任吴令时,清欠税、断积狱、裁冗员、除弊政,手段果敢,雷厉风行。以致申时行感慨:“二百年来,无此令矣!”[1]757再仕京都后,他惩治奸恶猾胥,致其坐重辟。又制定年终考察书吏之法,“更立刑具,同于诸曹,不法者,不时扑责”。主试秦中时,不避嫌疑,通场搜求落选之卷。《行状》载:“试官以避嫌,不过搜求。先生曰:‘岂可以一己之功名,忽多士之进取!’故通场皆阅,所取士大半得之落卷中。”[1]761这不仅说明袁宏道爱才心切,也显示出狂者敢作敢为的风格。鲁迅先生极有眼光,他说:“中郎正是一个关心世道,佩服‘方巾气’人物的人,赞《金瓶梅》,作小品文,并不是他的全部。中郎之不能被骂倒,正如他之不能被画歪。”[20]236
两派的论争,显示出双方审美趣味的巨大差异。周作人在《中国文学的变迁》中说:“‘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这是公安派的主张。在袁中郎《叙小修诗》内……这些话,说得都很得要领,也很像近代人所讲的话。”[17]23-24林语堂支持周作人的观点,他说:“性灵派之排斥学古,正也如西方浪漫文学之反对新古典主义,性灵派以个人性灵为立场,也如一切近代之个人主义。其中三袁兄弟之排斥仿古文辞,与胡适之文学革命所言,正如出一辙。”[21]146在《杂谈小品文》中鲁迅批判了“性灵”:“这经过清朝检选的‘性灵’,到得现在,却刚刚相宜,有明末的洒脱,无清初的所谓‘悖谬’,有国时是高人,没国时还不失为逸士。逸士也得有资格,首先即在‘超然’,‘士’所以超庸奴,‘逸’所以超责任:现在的特重明清小品,其实是大有理由,毫不足怪的。”[22]418鲁迅批判的,不是文学水准,而是审美趣味。他在《致郑振铎》中说:“比如现在正在盛行提倡的明人小品,有些篇的确是空灵的。枕边厕上,车里舟中,这真是极好的消遣品。然而先要读者的心里空空洞洞,混混茫茫。假如曾经看过《明季稗史》《痛史》,或者明末遗民的著作,那结果可就不同了,这两者一定要打起仗来,非打杀其一不止。”[23]443鲁迅《读书忌》表达了相同的意思,在引用屈大均《自代北入京记》后,说:“如果看过这样的文章,想像过这样的情景,又没有完全忘记,那么,虽是中郎的《广庄》或《瓶史》,也断不能洗清积愤的,而且还要增加愤怒。”[24]619
审美趣味的差异性是由双方的阶级立场决定的。以鲁迅和周作人为例,二人虽为同胞兄弟,但阶级立场迥异。鲁迅先生在1928年后,因论争的需要,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成为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此后,他参与并领导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工作,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周作人在五四前后发表了系列关于“人学”的论文,如《人的文学》(1918)、《平民的文学》(1919)、《贵族的与平民的》(1922)等,形成既肯定人的生理欲求也肯定人的精神追求的灵肉二元统一的“人学”理论。他建立在自然人性论之上的个人主义,迎合了很多人的需要。然而,时代的发展特别是列强的侵略使人们逐渐认识到个性解放必须以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为前提,大批个人主义者开始向社会主义者转化。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25]26当然,“人各有己”不是向“群之大觉”转化的充要条件,周作人的附敌从反面证明了这个道理。
这种各取所需的分化,不仅是阶级主体的差异所造成的,袁宏道“狂”的内蕴的不确定性也是原因之一。在出与处的交替中,在古与今的变化中,在儒学与佛道的交融中,“狂”会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如前所述,袁宏道之狂,既有名士之狂,也有志士之狂。名士之狂,深受道家玄学与佛教禅宗影响,追求一己之肆情、适意。志士之狂,秉承原儒系统“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著,追求社会之公平、正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周作人、林语堂)选择的是袁宏道的名士之狂;无产阶级革命者(如鲁迅、阿英)看到的是袁宏道的志士之狂。当然,无产阶级革命者不用像明季儒士那样痛苦、彷徨,也不用像袁宏道们那样只从传统内部寻求力量以反叛传统,寻求出路。由于时代的发展,外来文化的冲击,先驱者已经扛起崭新的思想旗帜。还需指出,新的思想固然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但又不能说它完全是泊来品。外国学者提出了“寻找中国史自身的‘剧情主线’(story line)”。[26]171我们更应当重视自身文化生命的延续性。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观,不是某些国家的专利,也不是可以移植的现成东西,需要从我们自己的文化生命中生长壮大。从某种意义上说,五四之后的狂飙突进,是自曾点到袁宏道的“狂”的一种扬厉。只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时代先锋将个性自由寓于群体解放,生命意义服从思想意义,古典的“狂”不仅褪去过时的外衣,而且更新了内涵,从而上升到一个崭新的境界。
——以黄麻士绅纠葛为中心的讨论
——《李贽学谱(附焦竑学谱)》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