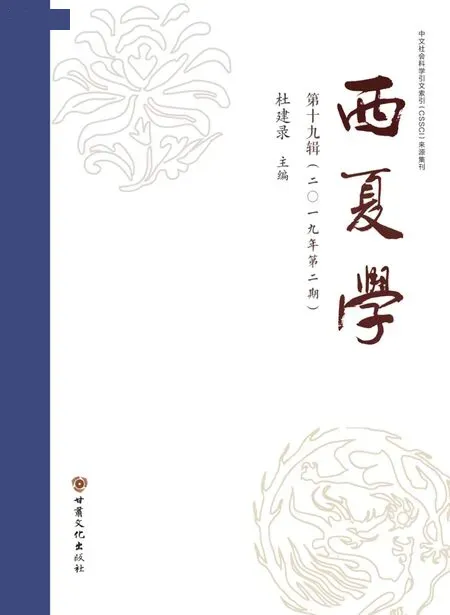武威亥母洞寺出土西夏汉文“宝银”账单及其学术价值
黎 李 黎大祥
一、西夏汉文“宝银”记账单概况

图1 武威亥母洞寺出土汉文“宝银”记账单
1987年5月,甘肃省武威市博物馆在清理亥母洞石窟寺1号洞窟时,出土了大量西夏文献及文物,其中同时出土的有一件西夏汉文“宝银”记账单。其它文献文物《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6册已刊布,①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6册,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385—523页。但该件文献因故未收入。该件记账单为汉文写本,纸质,残长26厘米,残宽16厘米。汉文墨书行楷,残存竖写13行(见图一),录文如下。下文笔者补录,□的字为残缺字;(银)的字代表前面的异体字。

该件汉文“宝银”记账单发现于武威亥母洞石窟寺1号洞窟内,与此同一地层出土的有大批西夏文文献及文物,其时代应属于西夏晚期的遗物。①黎大祥:《武威地区西夏西夏遗址调查与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79—206页;《从亥母洞寺发现的汉文文献谈西夏的寺院经济及多元文化》,《甘肃金融》2017年增刊,第55页。从记账单保存状况及整个文字内容来看,记录的是西夏时期武威亥母洞石窟寺内商业经营和佛事活动中,收入的“宝银”数量的账单。由于残缺,账单前面的第一号至第叁拾号的记录内容已不存在,仅存其第叁拾壹至第叁六号“宝银”收入的记录账单。从整体文字内容看,武威亥母洞石窟寺内保存的汉文“宝银”账单,有编号,即第一号至第叁拾六号;每一号后面记有宝银数量。其数字书写似为计数符号,暂不能认读,因此,在释文中用“□”代替,有待于以后进一步释读研究。第7行:第叁拾四号,第9行:第叁拾五号下面均写一“仝”字,即“同”字。说明这两个号中所有的银两数额相同。12行:“状多知其整保人中弍拾五定(锭)□”,其断句应为:“状多,知其整,保人中,弍拾五锭”。这应当是对“宝银”整体形状、数量的说明,即“弍拾五锭”;“保人中”,即中间的证人。这张记账单虽然残缺,内容也比较单一,但为了解认识早期亥母洞石窟寺的佛教发展、佛事、商业经营活动中白银使用、寺院经济状况等,提供了诸多信息。
二、宝银账单的学术价值
(一)宝银账单反映了西夏时期亥母洞石窟寺经济发达
据有关史料及寺内发现的文物可知,武威亥母洞寺开凿于西夏正德四年(1130),也盛兴于西夏,属于藏传佛教石窟寺院。因寺内供奉金刚亥母像而得名,是西夏时期创建的藏传密教静修之地,是我国现存较早的藏传佛教遗址。从寺内发现的大量西夏文物可以看出,在西夏时期佛教盛兴,洞中发现的西夏时期的唐卡“上乐金刚和金刚亥母如意轮坛城”也清楚地表明,寺窟中尊奉的是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本尊之一金刚亥母。①谢继胜:《一件极为珍贵的西夏唐卡——武威市博物馆藏亥母洞寺出土唐卡分析》,原刊于北京大学文博学院编:《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595—611页。发现的“文殊菩萨”像唐卡,在主尊文殊菩萨的左右上方两个重要位置上,分别安置着藏传佛教萨迦派和噶举派的上师,说明在西夏时期,藏传佛教萨迦派特别是噶举派在凉州藏传佛教的传播中占有重要地位。从亥母洞遗址发现的乾定申年(1224)西夏文典糜契约,立约者没施隐藏犬向寺院讹国师处借糜可以看出,武威亥母洞寺是西夏时期的佛国院。②孙寿龄:《西夏乾定申年典糜契约》,《中国文物报》1993年2月7日第3版。发现的大批不同版本的西夏文印本和写本佛经,特别是西夏文泥活字版本的发现,是当时佛教传播及佛教发达的历史实物见证,汉文“宝银”记账单的发现也进一步折射出了西夏时期亥母洞石窟寺佛教的盛兴。
亥母洞遗址发现的大量文物及西夏文典单契约、汉文收款记账单反映了当时寺院经济经营的主要活动。高利贷经营、商业经营、典当经营、医学及医药经营等是当时寺院经济发展的主要经营活动。③黎大祥:《武威地区西夏西夏遗址调查与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79—206页;《从亥母洞寺发现的汉文文献谈西夏的寺院经济及多元文化》,载《甘肃金融》钱币研究2017年增刊,第60—62页。“宝银”记账单的发现对研究西夏时期社会经济,特别是寺院经济具有重要的价值。
关于西夏寺院经济的状况,史金波先生《西夏社会》第五章“商业和借贷”④史金波:《西夏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95页。、杜建录先生《西夏经济史》在探讨西夏高利贷和债务法时⑤杜建录:《西夏经济史》,中国社会科学从出版社,2002年,第250页。根据出土西夏文献做了相关专题研究,揭示出了西夏社会寺院经济的面貌。关于西夏寺院经济的来源,崔红芬认为“其经济来源非常广泛:一方面,是来自社会不同阶层的施舍、纳钱度僧、从事宗教活动所得及亡故僧尼的部分遗产施入寺院等。另一方面,寺院通过不同手段占有大量田产并利用农田所得从事各类经济活动,尤其是高利贷经营在西夏寺院经济中占居重要地位”。⑥崔红芬:《试论西夏寺院经济的来源》,《宁夏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第103页。
武威亥母洞石窟寺发现的该件“宝银”记账单则为研究西夏寺院经济及其寺院的职责提供了新的材料。从该件宝银账单内容可以看出,当时寺内保存的银两编号和数量。编号当为存放银两的设施或者器具的顺序号,编号从壹号到叁拾六号;白银是以“两”或“锭”来折算,其内容是西夏时期发现寺院文献中的首次发现,具有重要的史料研究价值。在宋、辽、金、西夏时期,白银的货币职能主要体现在朝贡税赋、财富贮藏、大额支付及对外贸易等。尤其是宋代“在政府的重大政治或经济活动中,在民间某些私人交往中,白银却被视为事实上具有重大价值的货币,其作为货币的经济作用甚至高于铜、铁钱,‘以银化钱,无往不可’。白银这种事实上的货币职能,在政府的重要政治或经济活动中表现尤为突出。”①李兆超:《宋代货币经济中的白银》,《中国钱币》1989年第2期,第56页。因此,“宝银”记账单的发现,对于研究西夏时期的寺院经济乃至商业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从一个侧面反应出西夏时期亥母洞石窟寺佛教活动的盛兴及寺院经济的来源及发达。
亥母洞石窟寺“宝银”记账单的发现,说明了西夏时期一些重要的、较发达的佛教寺院中白银是寺院经济来源收入的一部分。而这些白银应当为皇室敕赐,或是各级官吏及普通信徒对寺院施舍的银两。对西夏寺院经济的来源,学术界已多有论述,这里不再赘述。至于白银是否作为西夏寺院经济来源收入的一部分,在学术界尚未有人提及和论述。在史料中有零星记载:一是《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汉文碑文载:“其月十五日,诏命庆赞,……特赐黄金一十五两,白金(白银)五十两,衣着罗帛六十段,罗锦杂幡七十对,钱一千缗,用为佛常住,又赐钱千缗,谷千斛,官作四户,充番汉僧常住,俾晨昏香火者有所资焉,二时斋粥者有所取焉。西夏文碑文载:“为佛常住,黄金十五两,白金(白银)五十两,衣着罗帛六十段,绫罗杂绣幡七十对,千缗钱。为僧常住,又赐四户官作,千缗钱,千斛谷等”。②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5—138页。二是蒙古人在1207年对西夏发动进攻期间,据说止贡噶举支派的创始人奇丹衮波,曾为西夏王朝送去文殊师利的肖像。为此,西夏统治者馈赠了奇丹衮波丝绸和金子(金银),以换取一份讨人欢心的安慰③邓如萍著、聂鸿音等译:《党项王朝的佛教及其元代遗存》,《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第46页。。以上两条记载说明,西夏时期的佛教寺院有金银,并在使用金银。武威亥母洞石窟寺“宝银”记账单,是专门记录西夏石窟寺院白银使用的记载文献,它的发现真实地记载了西夏石窟寺院使用白银的状况。为研究西夏时期石窟寺院流通使用白银增加了新的珍贵实物史料,说明在这一时期白银亦作为一种货币形态,在寺院经济支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宝银账单为研究西夏使用白银问题提供了新材料
1987年9月,甘肃省武威市城内署东巷修建行署家属大楼,在开挖地基时,距地表三米多深处发现一批西夏窖藏文物,其中有一批银锭,除散佚的外,武威市博物馆共藏22件,总重量为35995克。笔者曾撰文介绍了该批西夏银锭的情况,其中錾刻有铭文及戳记的银锭11件,錾刻有不同符号的银锭5件,无铭文、记号的银锭6件。银锭中錾刻的铭文及戳记,记录了当时白银流通的真实情况,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砸印“使正”、“官正”戳记的,錾刻“行人”、“秤”、“秤子”的,砸有“赵铺记”、“夏家记”戳记的,自铭银锭重量的,反映银锭成色铭文的等。笔者提出,甘肃武威市城署东巷出土的一批西夏金器、银锭,是西夏考古史上的一次重大收获,并撰文将这批银锭的特征予以了详细介绍,根据这批银锭的特点和同时出土的瓷器、货币等文物,提出了这批银锭是西夏通用的,是国内首次发现的西夏银锭实物,填补了在西夏使用银锭有史料记载而无实物的空白。①黎大祥:《甘肃武威发现一批西夏通用的银锭》,《中国钱币》1991年第4期,第42—48页。资料公布后,引起西夏学界的极大关注。陈炳应先生在《西夏货币概述》②陈炳应:《西夏钱币概述》,《中国钱币》2002年第3期,第29—37页。《西夏的衡制币制》③陈炳应:《西夏的衡制与币制》,《中国钱币》1994年第1期,第3—17页。以及《西夏货币制度概述》④陈炳应:《西夏货币制度概述》,《中国钱币》2002年第3期,第39—42页。中也认同是西夏流通银锭;牛达生先生《西夏遗迹》⑤牛达生:《西夏遗迹》,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58-177页。,《西夏白银与交钞使用考述》⑥牛达生:《西夏白银与交钞使用考述》,《文献研究》2014年第4辑,第43—52页。,党寿山先生《武威文物考述》⑦党寿山:《武威文物考述》,武威市光明印刷物资有限公司,2001年,第115—123页。等著作都赞同此观点,认为这批银锭就是西夏流通的银锭,并且根据出土实物及文献资料在西夏是否铸造银锭和使用银币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
但是,西夏是否铸造银锭以及流通使用银锭一直在争议之中,也有一些学者,对这批银锭提出了质疑之声。如王勇先生认为出土的银锭是文物部门追缴回来的,上面的铭文以及形制都与宋代和金代银锭的铭文和性质相同,同时出土的宋代货币和西夏瓷器可能是西夏以后遗留的,认为是西夏利用宋代的银锭作为货币使用,西夏是否使用金银货币未见实物⑧王勇:《西夏货币研究琐议》,《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会议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81—385页。。白秦川先生认为武威出土的银锭形制与金代银铤相同,且铭文格式行人、使正、官正、重量等八个方面认为都在金代银铤中出现过,该批银铤具有明显的金代银铤特征,有可能是蒙古军队在消灭金朝后带到武威的⑨白秦川:《武威出土银鋌应为金代银鋌》,《中国钱币》2005年第3期,第19—20页。。2006年白秦川先生再次提出了相同的观点,认为西夏用银作货币,只有零星的记载,是否铸为铤型,不大清楚⑩白秦川:《金代银鋌研究三题》,《中国北方地区钱币发现与研究学术研讨会专辑》,《内蒙古金融研究》2005年第2—3期,第48—53页。。之后笔者与于光建再次撰文从西夏文辞书、西夏文法典、新发现银锭实物、西夏银锭来源等方面论述了西夏社会流通使用银锭的事实。⑪于光建、黎大祥:《关于西夏银锭的几个问题》,《吴天墀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1913-2013》,四川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54页。
武威亥母洞石窟寺发现的汉文“宝银”记账单文献,明确地记载了西夏时期亥母洞石窟寺院流通使用“宝银”银两、银锭的情况,是西夏流通使用白银,即银锭的实物见证,为研究西夏时期流通使用银锭提供了可靠的珍贵实物史料。
“宝银”记账单12行“状多,知其整,保人中,弍拾五锭。”从字面意思来看,寺内所收入的白银,其形状大小不一,数量比较多,按收入的银两知其整数,正好是弍拾五锭,中间有保人作证。从这些记载内容来看,在西夏时期,石窟寺院内的使用银两收入管理,有一套具体的管理办法。即,收银两的管理人,保人和记账人相互制约。另一方面还可看出,当时寺院收入的白银都是形状大小不一的碎银,记账时碎银(银两)以银锭为单位,折合计算,即整个银两为“弍拾五锭”。关于银锭的重量,从武威出土的一批银锭来看,有大小两种。一般大的重五拾两,小的重弍拾五两。从这里可反映出西夏在使用白银过程中的折合方法,折合银两是以银锭为单位计算的。由此可见,西夏时期流通和使用白银,在一些大额支付贸易中,是以银锭作为计量单位支付的。
武威亥母洞寺出土的该件武威亥母洞石窟寺发现的西夏汉文“宝银”记账单又为研究西夏铸造银锭提供了新证。“宝银”记账单记载的整体内容很明确记录的是甘肃武威西夏时期亥母洞石窟寺内商业经营活动中收入的“宝银”、银两、银锭。账单记录了存放“宝银”设施或器具的顺序号,编号为第壹至第叁拾六号;每个设施或器具记录了保存“宝银”的数量;有整个银两保存的形状、银两折合为银锭的数量、保人等的记载。
同时,账单12行文字中记载了碎银(银两)折合成为银锭,这需要有一个铸造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也就是“金银铺店”铸造银锭的过程,这在武威出土的一批银锭中也可找到答案。武威出土的银锭,1号银锭砸印有一个“夏家记”戳记,5号银锭砸印有两个“赵铺记”戳记,这与苏南茅山出土的南宋金牌、银锭上砸印的“周王铺”“张周铺”“王周铺”“清河记”“颜十记”和黑龙江阿城出土的金代银锭上砸印的“戳家记”以及西塞出土的宋代银锭上砸印的“沈铺”“徐沈铺”“王家记”戳记很类似。茅山、阿城与西塞金牌、银锭上的这种戳记被视为是当时的“一个作坊字号”或是“一个银店铺号”,说明这一时期在宋、金社会上由于白银的广泛使用,“金银铺店”兴起。“银铺业的发达,在南宋的文献记载中也有反映”①黄成:《从考古发现谈南宋白银流通的几个问题》,《中国钱币》1989年第2期,第49—55页。。在西夏流通的银锭中,“赵铺记”和“夏家记”的出现,也进一步说明西夏和宋、金王朝一样,在当时社会上已经出现了一些铸造和专门经营银锭的作坊和金银店铺,“赵铺记”和“夏家记”就是西夏时期在武威当地出现的“金银铺店”②黎大祥:《甘肃武威发现一批西夏通用的银锭》,《中国钱币》1991年第4期,第42—48页。。武威亥母洞石窟寺发现的汉文“宝银”记账单,为西夏铸造银锭提供了新证,帐单中“状多,知其整,保人中,弍拾五锭”的文字记载,进一步证实了西夏时期铸造银锭,并流通使用银锭。它的发现进一步证实了在西夏社会不仅已经有白银出现,而且还铸造、流通使用银两、银锭。
综上所述,武威亥母洞石窟寺1号洞窟出土的西夏汉文“宝银”记账单虽然残缺,内容也比较单一,但其记载的宝银数量及其相关信息,真实的记录了西夏时期亥母洞石窟寺内商业经营和佛事活动中收入的“宝银”情况,为研究西夏亥母洞石窟寺的寺院经济、寺院的职责提供了新材料。同时也为进一步研究西夏社会铸造白银,使用流通白银,白银在西夏社会经济中的的功能等经济问题提供了新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