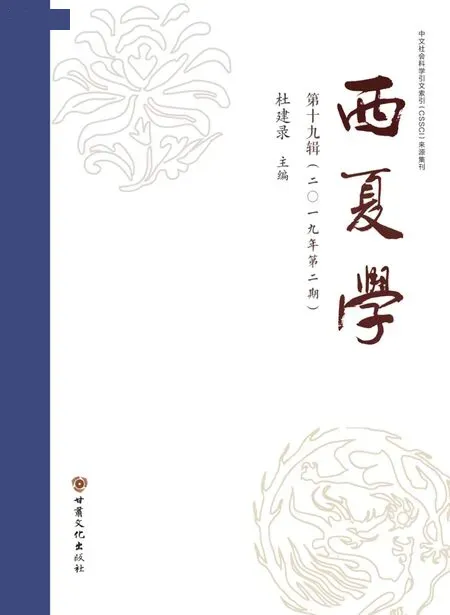四川广元千佛崖石窟元代西夏遗裔题记及其史料价值初探
邓文韬
坐落于广元市嘉陵江东岸山崖上的千佛崖石窟是四川境内规模最大的摩崖造像群。山崖之下,原有沟通古代川陕两地的金牛古道。便利的交通要素使得这些开凿于北朝至唐代龛窟在历代皆受到往来信徒的顶礼膜拜,香火不绝。入元以后,广元依旧保持了川陕要道的交通地位,因公务奔波于蜀道之上的官员群体在千佛崖石窟多有烧香朝拜,捐俸出资,装饰佛像等活动,仅《(民国)广元县志稿》所收元代题记即有31条之多。在这些朝拜千佛崖的元代官员群体中,不乏有西夏遗裔的身影,千佛崖的元代题记中有不少就是由他们留下的。然而,这些题记尚未引起学界重视,史金波、崔红芬等学者在论述元代西夏遗裔的佛事活动时①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第九章《西夏灭亡后党项人的佛事活动》,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97—215页;崔红芬:《文化融合与延续:11—13世纪藏传佛教在西夏的传播与发展》第六章第二节《西夏遗民的佛事活动对后世的影响》,民族出版社,2014年,第299—317页。也没有将他们在千佛崖的事迹列入考察。故笔者在此抛砖引玉,辨析千佛崖现存和已佚元代题记中的西夏人名,以推动学界对元代西夏遗裔佛事活动的研究。
一、现存题记
《广元石窟内容总录·千佛崖卷》将千佛崖现存之龛窟分为A、B、C三段,现存的两方元代西夏遗裔题记均处于B段南侧的地面至第一层栈道之间的窟龛或崖壁上,共有两方,以下逐一考辨。
(一)《至正六年十月陕西行台监察御史普达实礼等题记》
该题记位于第229龛与230龛正下方,+26龛左上方,占璧面高约96厘米,宽约77厘米,字径约4.5厘米,阴刻楷书9行,满行15字,共77字,外有忍冬纹边框。以下按图版一录文:
1.至正六年冬十月乙巳朔粵八日壬子
2.陝西諸道行御①此处应脱“史”字,《广元石窟内容总录·千佛崖卷》已据文意补入。臺監察御史
3.甘肅普達②此处原字已残,据缪荃孙《分地金石编目》所录拟题补入“达”。實禮士達
4.廣平秦③此处原字已残,按《元史》卷一七六《秦起宗传》,秦起宗“其先出上党,后徙广平洺水县”,起宗长子即“钧,西台御史”,与题记中人物之籍贯、名讳与官职相符。故此处残字应为“秦”。鈞彥樞 偕
5.書吏
6.固始朱思恭敬夫
7.鎮原王 謙 克恭
8.守云南行省過此以記岁月云
9.至正丙戌良 月八日 誌
按此题记系至正六年(1346)冬十月陕西行台御史普达实理(字士达)与秦钧(字彦枢)偕书吏分司出巡,至云南守省时路经广元时朝拜千佛崖之记事。
文中第三行之“甘肃”为普达实理之籍贯,即元代之甘肃等处行中书省,下辖甘州、永昌、肃州、沙州、亦集乃、宁夏府、兀剌海等七路之地,辖境相当于故西夏王国之宁夏平原、河西走廊和阿拉善高原等地,是元代西夏遗裔广为认同的故乡。如侨居松江府的武威人迈里古思,被称为“甘肃人而假馆松江”④[元]邵亨贞:《野处集》卷二《进士吴善卿赴黟县教谕醵赆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5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97页。,又如唐兀氏文殊奴去世后,其家人在葬地昆明为之立经幢祈福,幢中文字称其原在“甘肃省居住”⑤方国瑜:《云南金石文物题跋》,《方国瑜文集》第4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03—304页。。至于用甘肃之雅称,如“陇右”“河陇”“河西”等名词形容元代西夏遗裔之籍贯则更为常见,如《(洪武)苏州府志》称平江路总管唐兀氏元童为“河陇人”⑥[明]卢熊撰:《(洪武)苏州府志》卷二五《名宦》,成文出版公司,1970年,第1073页。,又如族出西夏,侨居杭州的散曲家邾经自署为“陇右邾经”⑦[清]钱熙彦编次:《元诗选补遗》戊集《舟中连句》,中华书局,2002年,第507页。,再如张掖人沙剌班与文友交流时亦自称“河西人”①[元]宋褧:《燕石集》卷九《竹山山中太皇观小憩道士白刘伯温御史旧所题二絶句即景和寄》,北京图书馆藏古籍珍本丛刊第92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190页。等。元代之西夏遗裔以甘肃或其代称为籍贯者,由此可见一斑。
以“普达实理”(Buda Siri)为名的西夏遗裔,在传世与出土文献中所见有二。其一见诸于《元史·亦怜真班传》,该普达实理为知枢密院暗伯之孙,江西行省左丞相亦怜真班之次子,仕至翰林学士丞旨、知制诰兼修国史②[明]宋濂:《元史》卷一四五《亦怜真班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3447页。;其二见诸于《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该普达实理③按《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阴面耿世民先生所译之回鹘文,部分普达实理全名作ügаbubахir,“第一字回鹘文意为‘智者’,汉文一般译写作‘于伽’”(耿世民:《回鹘文〈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译释》,阎文儒,陈玉龙编:《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51页),碑刻阳面之汉文部分无此字。为首任肃州世袭达鲁花赤阿沙之曾孙,令只沙长子,受其侄定者帖木儿之逊让,得以充任肃州路达鲁花赤,后又将官职让与定者帖木儿之弟赤斤帖木儿。
遗憾的是,由于题记所言不详,所以我们无法判断这里的“普达实礼”是以上两名普达实理之一还是另有其人。但从其“甘肃”之籍贯来看,他极有可能是一名西夏人。
(二)《至正三年二月陕西行台监察御史朵儿只班题记》
该题记位于第213号龛门左侧力士上方,占璧面高约41厘米,宽16厘米④四川省文物管理局等编著:《广元石窟内容总录·千佛崖卷》,巴蜀书社,2014年,第206页。,字径约3厘米,阴刻楷书4行,满行12字,共39字,第2行“吏李郎”系由行左补入,字号稍小。以下按图版二录文:
1.陝西諸道行禦史臺監察禦史
2.朶⑤《广元石窟内容总录·千佛崖卷》录为“尕”,今据图版改正。兒只班奉訓字善卿備俸粧 吏⑥《广元石窟内容总录·千佛崖卷》录为“史”。此字前似脱一字,参考其他题记,此“李郎”应为监察御史朵儿只班之随从,极有可能是书吏,故改为“吏”。李郎
3.飾一堂
4.至正三年二月吉日記
与前一题记中明确出现的“甘肃”籍贯有助于我们推定普达实理的族属不同,朵儿只班(字善卿)的族属在题记中未有明确说明,我们只能根据传世文献进行推测, 元代史料文献中以朵儿只班(Dorji Bal)为名者较为常见,仅《元人传记资料索引》即收录有12人之多⑦王德懿:《元人传记资料索引》,中华书局,1987年,第2355—2356页。。活跃于题记年款至正三年(1343)前后的朵儿只班主要有四人,分别为至正八年(1348)受命征讨方国珍的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朵儿只班(氏族不详),于至正元年(1341)人翰林学士承旨,至正五年(1345)累迁中书参政、右丞的朵尔直班(札剌儿氏),至正元年(1341)上任江南行台监察御史的朵儿只班(唐兀氏)以及《索引》失载的至正元年广西道廉访使朵儿只班(氏族不详)①[明]林富、黄佐纂修:《(嘉靖)广西通志》卷二四《学校上》,齐鲁书社,1997年,第301页。。笔者认为,至正元年上任江南行台御史的唐兀人朵儿只班更有可能是题记中的西台御史朵儿只班,其原因主要有三:
首先,两者职官品级相同。江南行台与陕西行台作为元代御史台的两个分支机构,其“设官品秩同内台”②[明]宋濂:《元史》卷八六《百官志二》,中华书局,1976年,第2197页。,故而两行台之监察御史,均比拟中央之御史台为正七品职级。而行省参知政事(从二品)、翰林学士丞旨(从二)、中书省参知政事(从二)、中书省右丞(正二)以及廉访使(正三)均属高品级官职,担任这些官职的其他朵儿只班,其政治地位远高于题记中的西台御史朵儿只班。
其次,两者散官品级较为接近,并可以接续。《(至正)金陵新志》载唐兀氏朵儿只班于1341年上任南台监察御史之际其散官为承直郎(正六品)③李勇先,王会豪,周斌点校:《至正金陵新志》,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34页。,而题记所见1343年的西台监察御史朵儿只班,其散官为奉训大夫(从五品)。两至三年间散官提升一级,符合《元典章》中随朝官散官“三十个月为一考,一考升一等”④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卷八《吏部二·官制·选格·循行选法体例》,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37—238页。的定例。
最后,元代监察御史在江南行台与陕西行台接连任职较为常见,可资佐证。行台监察御史的职能主要是分道出巡和留守察院,处理各地之监察事务。由于职官品级和工作性质相同,元代文献中不乏有监察御史在南台与西台间辗转任职者,如师克恭“拜南台监察御史,改西台”⑤[元]柳贯著,柳遵杰点校:《柳贯诗文集》卷十《师氏先茔碑铭》,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17页。,杨焕“拜南台监察御史,移西台”⑥[元]许有壬著,傅瑛、雷近芳校点:《许有壬集》卷六二《杨尚书墓志铭》,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676页。,褚不华“连拜南台、西台监察御史”⑦[明]宋濂:《元史》卷一九四《褚不华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4395页。,忽都鲁沙“历江南、陕西两台监察御史,转汉中佥宪”⑧[元]欧阳玄:《欧阳玄集》卷九《元赠效忠宣力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赵国公谥忠靖马合马沙碑》,岳麓书社,2010年,第134页。等。与他们仕宦轨迹相反的有畅笃与忽都禄,二人先“拜西台御史”,后“移南台”⑨[元]许有壬著,傅瑛、雷近芳校点:《许有壬集》卷四九《畅文肃公碑》,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567页;同书卷五一《赠济南总管奥屯公碑》,第585页。;又有陈允文由“陕西诸道行御史台监察御史迁江南诸道行御史台监察御史”⑩[元]戴良:《九灵山房集》卷九《陈廉访圹记》,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32页。,王武“历西、南两台监察御史,入为大宗正府员外郎”⑪王颋校注:《黄溍全集·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九《蓝田王氏先茔碑》,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718页。等。更有甚者,梁克忠由江东廉访司经历“进南台御史,迁西台御史,入为监察御史”⑫[元]马祖常著,李叔毅点校:《石田先生文集》卷九《梁氏寿庆堂诗序》,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87页。,段辅“由应奉翰林历西台、南台、中台三御史”①[元]吴澄:《吴文正公集》卷六八《元赠奉议大夫骁骑尉河东县子段君墓表》,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四),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570页。,也就是说,梁、段二人曾接连在元朝的三个御史台任职。通过以上案例可见,监察御史无论是由南台调至西台,还是由西台调任至南台,甚至是连续任职于三个御史台,在元代政坛上都是极为常见的②又按《金石萃编未刻稿》所收后至元五年(1339)《大元勑修曲阜宣聖廟碑》碑阴御史台题名,其中“监察御史”条下同样有“朵儿只班”题名。据此推测,朵儿只班极有可能也是一名遍历元代三御史台的察官,其履历应为内台监察御史(1339年前后)——南台监察御史(1341年上任)——西台监察御史(1343年前后)。当然,以上履历只是推测,还欠缺其他资料的佐证。。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至正金陵新志》记载的那位于1341年以承直郎任江南行台监察御史的西夏遗裔朵儿只班,就是1343年2月题名于广元千佛崖213号龛外壁上的陕西行台监察御史、奉训大夫朵儿只班。
在完成江南行台与陕西行台的任期以后,朵儿只班(字善卿)依旧长期供职于元代监察体系中,今福建省福州市乌石山,还留存有至正九年 “宪副朵儿只班善卿公”③黄荣春主编:《福州十邑摩崖石刻》,福建美术出版社,2008年,第16页。的联句题记。由此可见,朵儿只班在完成西台御史的任期以后,终累迁至福建闽海道肃正廉访副使。
二、已佚题记
广元千佛崖石窟始建自北朝,兴盛于唐代,距今年代已较为久远,若干龛窟、造像与题记已在长年累月的风化作用下磨损殆尽。1935年,国民政府为修筑川陕公路而炸崖毁窟,开辟道路,又将千佛崖造像损毁半数以上。出于上述之自然、人为原因,部分千佛崖古代题记今日已难寻得。所幸清代学者缪荃孙《分地金石编目》(以下简称“《编目》”)和《(民国)重修广元县志稿》(以下简称“《县志稿》”)均曾为千佛崖题记纂录过编目,使我们仍能结合编目内容和其他文献推测现已不存之西夏遗裔题记。
(一)《美里吉台题记》
《编目》载“《美里吉台题名》,正书,至正丙戌(1346)中秋吉日”④缪荃孙著,张廷银、朱玉麒主编:《缪荃孙全集》金石卷五《分地金石编目(下)》,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1100页。;《县志稿》载“《美里吉台装佛像记》,元至正丙戌,共六行,五十一字,正书”⑤[民国]谢开来修,罗映湘纂:《(民国)重修广元县志稿》第一卷第三编《古迹》,巴蜀书社,1992年,第92页。。
美里吉台之生平,以《秘书监志》卷一〇《题名·校书郎》记载最详,谓之“字洪范,唐兀人,庚午(1330)进士,至顺四年六月二十九日上”⑥[元]王士点、商企翁编次,高荣盛点校:《秘书监志》卷一〇《题名·校书郎》,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05页。。“唐兀”即西夏人在元代之称呼,可确证美里吉台为西夏遗裔。
千佛崖题记并非美里吉台于至正六年(1346)留下的唯一行迹。今陕西兴平尚存《马嵬诗碣》一方,阴刻“至正六年六月,上澣西台监察御史美台吉洪范偕书吏丁宜骥克驯、贺中彦正审囚西道。至兴平,知马嵬去此不远,因感兴,乃述口号,以纪岁月云”①兴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兴平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29页。等文字。联系此诗碣和千佛崖题记来看,我们可以勾勒出1346年夏秋之际美里吉台的行迹——当年,他以陕西行台监察御史的身份偕书吏由奉元路出发,赶赴四川或云南道“审囚”,六月至兴平,又翻越秦岭与大巴山入蜀,于七月中秋到达广元,并为千佛崖中某个龛窟装饰了佛像。
又萧启庆先生据《(至正)金陵新志》卷首《序》言美里吉台于至正六年(1346)在任江南行台监察御史,似乎与《马嵬诗碣》和千佛崖题记所见之史实相悖。然而,《(至正)金陵新志》应初刊刻于至正四年(1344)四月,非至正六年(1346)。故以江南行台监察御史题名于该志卷首的美里吉台任职应在1344年,而非萧先生所言的1346年。也就是说,美里吉台很有可能也是先任南台御史,后调任西台御史的,其履历与前述唐兀氏朵儿只班类似。
(二)《耳力嵬题记》
《编目》载“《耳力嵬等题名》,正书,至正八年三月吉日”②缪荃孙著,张廷银、朱玉麒主编:《缪荃孙全集》金石卷五《分地金石编目(下)》,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1101页。,《县志稿》载“《御史台管勾耳力嵬承务题名》,元至正八年三月,正书,五行四十四字”③[民国]谢开来修,罗映湘纂:《(民国)重修广元县志稿》第一卷第三编《古迹》,巴蜀书社,1992年,第92页。。
由于史籍无载,耳力嵬之生平现已难以查证。然而,“力嵬”及其同音译写多见于元代西夏人名,却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如黑水城出土文书中就有“李黑党立嵬”“河逆你立嵬”“即立嵬”“也火汝足立嵬”“阿立嵬”“罗即节立嵬”等党项人名。立于西夏故地的元代《重修皇庆寺记碑》和《莫高窟六字真言碑》中也有“乙立嵬”“各立嵬”“依立嵬”“耳立嵬”“刘耳力嵬”“解逆立嵬”等人名,苏莹辉与松井太亦分别指出其中部分姓名“为西夏人姓名”④苏莹辉:《跋莫高窟造像及功德题名石刻拓本》,苏莹辉著:《敦煌论集》,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第413页;松井太著,杨富学、刘锦译:《敦煌出土察合台汗国蒙古文令旨》,达力扎布主编:《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四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81页注3。。就传世文献来看,《元典章》记载唐兀卫亲军中也有百户名为“即力嵬尼”⑤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卷二九《礼部二·礼制二·牌面·军官解典牌面》,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37—238页。,《元史》中则收录有出身唐兀乌密氏的《立智理威传》。因此耳力嵬是西夏遗裔,甚至是党项人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三)《文书讷等题名》
《编目》载“《文书讷等题名》,正书,至正十六年十一月”⑥缪荃孙著,张廷银、朱玉麒主编:《缪荃孙全集》金石卷五《分地金石编目(下)》,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1101页。,《县志稿》失载。
文书讷姓杨氏,唐兀人,为御史中丞杨朵儿只与妻刘氏所生之次子。关于他的生平,周峰《元代西夏遗民杨朵儿只父子事迹考述》已有充分研究⑦周峰:《元代西夏遗民杨朵儿只父子事迹考述》,《民族研究》2014年第4期。,不赘述,仅对其最后仕履略作商榷。
周文认为,史籍所见杨文书讷的最后任职是至正十四年(1354)七月前后的淮南行省参知政事。然而,据周文所引的《杨朵儿只墓志》(成文于至正十五年)载文书讷“由河东、山东二道佥宪拜监察御史……累迁各道宪使”,可周文仅考出至正九年(1349)杨文书讷任过一次江西湖东道廉访使,似乎称不上是“累迁各道宪使”。因此笔者推测,文书讷在完成淮南行省的任职后,可能还以肃政廉访使的身份监临某道。千佛崖上的文书讷题名,应该就是他在迁调过程中题写的。
除在广元千佛崖拜佛朝觐和书写题记以外,杨文书讷还曾为山东长清的大灵岩寺书写寺名(至今仍立于该寺山门之前),又于任职都水庸田使时为平江路铜观音寺内之观音像修饰法衣①[元]陈基著,丘居里、李黎点校:《陈基集·夷白斋稿》卷二七《光福观音显应记》,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237—238页。,可见其对佛教之虔诚是始终如一的。
三、千佛崖元代西夏遗裔题记的史料价值
千佛崖元代题记反映了西夏遗裔对元代监察事业的贡献和他们对佛教的信仰。
以上题记中考出的5名元代西夏遗裔,4人均任职于陕西诸道行御史台。元朝的陕西行台,本是至元二十七年设置的云南诸路行御史台;大德元年(1297),元成宗移云南行台于京兆(即奉元路,今陕西西安),置陕西诸道行御史台,提领陕西汉中、河西陇北、西蜀四川、云南诸路等四道的监察工作。行台监临诸道,并“振肃纲维,省观俗化,察吏贪廉,询民利病”②[元]苏天爵著、陈高华、孟繁清点校:《滋溪文稿》卷三《浙西察院题名记》,中华书局,1997年,第35页。的职能,多由监察御史以分省出巡的方式来完成。而广元地处川陕咽喉,所以被行台派往四川和云南两道出巡的监察御史,必取道广元路。
上述4名西夏人官员中,朵儿只班、普达实理与美里吉台皆为监察御史③四人中唯耳力嵬之身份为御史台管勾,即管理承发司或架阁库案牍文书的低品级官员,通常情况下似乎并无出巡各地之必要,其以管勾身份出现于千佛崖题记之缘由现已难考。。普达实理自称出行目的为“守云南行省”,即前往云南省治之察院停留一段时间,处理当地监察事务④关于监察御史的出巡与守省,详见李治安:《元代行省制度》,中华书局,2011年,第811页。。朵儿只班之目的地虽在213龛题记中未尝提及,但《广元县志稿》载已佚题记中有“《四川守省奉训大夫姚家奴尹忠装佛像记》,元顺帝至正三年”⑤[民国]谢开来修,罗映湘纂:《(民国)重修广元县志稿》第一卷第三编《古迹》,巴蜀书社,1992年,第91页。等字,由此推测,同样于至正三年(1343)出巡的朵儿只班只可能是前往云南守省。又美里吉台于《马嵬诗碣》中自称“审囚西道”,据《元典章》载诸处罪囚“仰肃政廉访司分明审录……有禁系累年,疑不决者,另具始未及其疑状,申御史台呈省详谳。在江南者经由行御史台,仍自今后所至审囚,永为定例”⑥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卷四《朝纲一·政纪·省部减繁格例》,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34页。等推测,美里吉台应该是被行御史台派往四川和云南审理那些“禁系累年,疑不决者”的囚犯。
虽然云南与两广等地在历代皆有开发,但元代之北方官僚依旧视之为“烟瘴之地”。如《元典章》载延祐四年(1317)御史台奏“南台文字里说将来,广东、广西、海北烟瘴歹地面,有五、六月里省台差去的使臣,著烟瘴多有死了的。廉访司官署月审囚去呵,也著烟瘴死了有……这三道并云南,俱系烟瘴重地”①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卷六《台纲二·体察·巡按·巡按一就审囚》,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34页。,可反映元代监察官员前往迤南地区执行公务之风险。千佛崖题记则说明,作为察官的西夏人虽同样出身北方,却不畏烟瘴而勇于前往四川、云南等地巡按审囚,是元代西夏遗裔察官群体忠于其监察职守的实物资料。
与此同时,广元千佛崖西夏遗裔题记也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元代西夏遗裔佛事活动的空间和时间特征。从空间来看,以往学界只知晓西夏遗裔在河西故地、藏区、腹里地区和江南地区继续从事开窟造像和刻印佛经等活动。千佛崖的西夏人朝拜、彩装题记和云南省博物馆藏文殊奴神识经幢②方国瑜:《云南金石文物题跋》,《方国瑜文集》第4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03-304页。则说明任职和迁居至西南地区的西夏遗裔也同样传承了西夏文化中对佛教的尊崇。从时间来看,千佛崖的西夏人题记主要集中于元顺帝至正年间(即元朝晚期),而文殊奴神识经幢更是北元宣光年间刻制的,其上可承高纳麟、智妙酩布等党项人参与居庸关云台六体陀罗尼经的刻制,下可接明中期西夏文《高王观世音经》的刊印和保定韩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的立石,证明自十四世纪中期至十六世纪末之间,西夏遗裔依旧在绵延不绝的从事各种佛事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