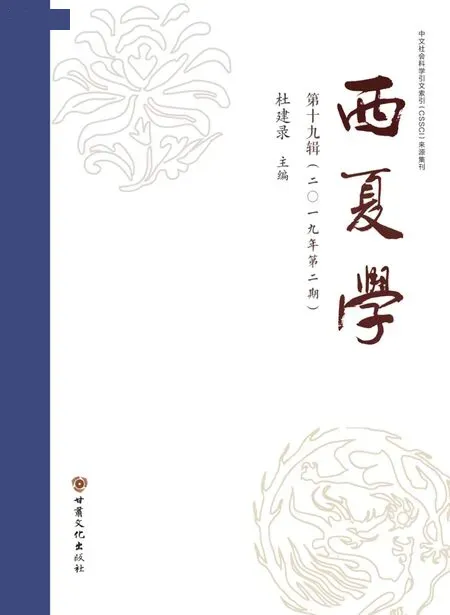简论西夏“军籍”文书的性质及其价值
陈瑞青
黑水城文献的发现和近年来集中公布,直接促成了西夏学的兴起。随着大量西夏文文献的翻译、考订,利用西夏文献研究西夏历史的时代已经到来。史金波先生近年来致力于西夏文草书社会文书的整理和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仅就西夏“军籍”文书的研究而言,史先生《西夏文军籍文书考略》一文对俄藏的4件西夏文草书“军籍”文书进行了翻译和研究①史金波:《西夏文军籍文书考略》,《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143—174页。。之后,又对英藏的3件西夏文草书“军籍”文书进行了系统整理②史金波:《英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军籍文书考释》,《文献》2013年第3期,第3—19页。。史先生对上述7件文书均冠以西夏“军籍”,并就文书中涉及的军籍登记制度、人员构成、组织特点、军兵装备等主要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同时,史先生还利用西夏“军籍”文书和军抄“除减”文书,探讨了西夏军抄的组成、分合以及死减续补问题③史金波:《西夏军抄的组成、分合及除减续补》,《宋史研究论丛》第15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56—576页。。一系列西夏“军籍”文书的集中翻译推出,无疑对研究西夏军事史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笔者在研读这批已经译出的西夏“军籍”文书时,发现从文书学的角度来看,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军籍”,因此有必要对文书性质进行重新探讨,而这批文书不仅是研究西夏军事制度的重要材料,同时还是研究西夏文书制度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有鉴于此,笔者试对上述西夏“军籍”文书性质及价值进行粗浅的研究,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上面已经提及,史金波先生翻译的西夏文“军籍”文书共计7件,其中俄藏4件,分别是Инв.No.8371号天庆戊午五年(1198)“军籍”文书、Инв.No.4197号天庆庚申七年 (1200)“军籍”文书、Инв.No.5944-1号天庆乙丑十二年 (1205) “军籍”文书和Инв.No.4169号应天元年(1206)“军籍”文书;英藏3件分别是Or.1238O-0222号和Or.12380-0222V号拼合后的天庆己未六年(1199)“军籍”文书、Or.12380-1813号和Or.12380-3521号拼合后的天庆乙丑十二年(1205)“军籍”文书以及Or.12380-3865号天庆乙卯二年(1195)“军籍”文书。这7件“军籍”文书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属于同一性质的文书,为研究方便,现择取一件俄藏文书译文进行说明①本文所使用的俄藏西夏文译文出自史金波先生的《西夏文军籍文书考略》,特此说明。。俄藏天庆戊午五年(1198) Инв.No.8371号文书译文:


俄藏Инв.No.8371号文书为写本,麻纸,卷子,高 22.7,宽65.5厘米,西夏文行草书40行,第 38行有“天庆戊午五年六月(1198)”年款,有朱印4方,有朱点,有签署、画押。背面有签署文字4 行。该文书首尾完整,且多处有朱笔勾点,异于其他同类文书。
粗看此类文书,确如史先生所言:“(文书)记载着众多西夏基层军事的人员、马匹、装备等详细内容。这类文书属西夏的军籍文书,是依照西夏政府的相关规定,对西夏社会基层首领所辖各军抄详细登记的簿籍”①史金波:《西夏文军籍文书考略》,《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145页。。如果这类文书为西夏军籍文书,在中国古文书学上的价值无疑是巨大的。在时代稍早的敦煌文书中,虽然存在大量唐代军事文书,但多数为维持基层军队运转的牒、帖、状,少数为登记士兵军装、装备的簿、历,尚未见到唐代军籍文书,只有藏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的编号为P.3249背面的写卷文书,冯培红先生将其定名为《唐咸通二年(861年)归义军队下残剩兵士军籍残卷》②冯培红:《P.3249背《军籍残卷》与归义军初期的僧兵武装》,《敦煌研究》1998年第2期,第65页。,但从该文书的内容来看,是咸通二年克复凉州之后前线将领上报给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的除阵亡将士外的残剩军籍名单,并非唐代军籍,因此唐耕耦、陆宏基在《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中将其定名为《将龙光颜等队下名簿》是有一定道理的③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4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9月,第521—522页。。
在时代稍后的黑水城元代文献中,只有F249:W22号文书、M1·0780[84H·F197:W1/2251]号文书、M1·0273[F197:W23a]号文书、M1·0274[F197:W23b]号文书和为M1·0276
[F197:W13]号文书涉及元代牌兵,其登记形式分为地方组织牌子头登记方式和军事组织牌子头登记方式,前者以户作为单位进行登记,后者以人为单位进行登记;前者登记时,牌子头并不包含在牌子户中,而后者牌子头是包含在“牌兵”之内的④陈瑞青:《黑水城所出元代牌子头文书初探》,未刊稿。。现以M1·0276[F197:W13]号文书为例进行说明:

彭大雅、徐霆《黑鞑事略》中称“其民户体统十人,谓之排(牌)子头,自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各有长”①彭大雅、徐霆:《黑鞑事略》,王国维笺注本,载《蒙古史料校注四种》,清华大学研究院刊行,第16页。。元代军队中的牌子是抽调十人组成的军事组织。吴超先生指出,元代的“牌子”是以人为主组成的军事组织的基本单位,牌子头统领的十人,为军事人员,而非普通部民(民户),尚不具有户籍管理(保甲)的职能②吴超:《〈黑城出土文书〉所见“牌子”考》,《北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第102页。。从文书中可以看出,在鲁即柔责牌下的士兵中第一个列出的就是鲁即柔责本人,表明元代军队中的牌子头包含在十名士兵之中。
时代更晚的明代黄册中,并未发现明代军黄册,只在部分民黄册中发现泰州军户的登记信息,如上海图书馆藏《乐府诗集》第一叶纸背文献:

《乐府诗集》纸背文献大致反映了明代军户登记形式,黄册中主要登记军户户主充军、任职以及补役情况,由于文书残缺,尚有部分信息未能显示,通过其他黄册民户登记信息推测,大致还应包括军户人口构成、土地数量以及应纳夏税秋粮等情况。
以上列举的唐、元、明文书可以看出,在西夏王朝时代前后的文书序列中,并没有发现真正意义上的军籍文书。那么,黑水城发现的这7件涉及西夏军抄的文书是否为西夏军籍?笔者认为这类西夏军抄文书不可能是军籍,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文书在书写形式上,均采用固定的叙述模式,如前引两件西夏军事文书中都采用“黑水属军首领某某,正军一种纳 告/前自全军籍告纳,某年年六月一日始,至次年五月底止,无注销。已定。”这并非簿籍所采用的书写形式,而是典型的公文叙述方式。其二,文书多处钤盖首领印,这与簿籍登记形式相左。在明代黄册中虽然也有印章存在,但一般为黄册主管机构如“管理后湖黄册关防”等①孙继民、张恒:《后湖黄册悄然现身》,《光明日报》2017年8月21日第14版。。明代军事文书中有时也会出现朱色长条戳,主要为文字转页或转行的阻字章。从公布的西夏军事文书图版来看,首领印的使用主要钤盖在文书中的数字、人名等关键信息上,防止有人改动,这种情况一般在公文中最为常见。其三,文书不仅有年款还有人名款。如Инв.No.8371号文书中的年款为第38行“天庆戊午五年六月”;Or.12380-3865号文书中的年款为第39行的“天庆乙卯二年六月”。从上面两件文书可以看出,文书的人名款既有文书的行文主体黑水属军首领官,也有具体书写者主簿,而这些信息是不可能出现在西夏军籍之中的。其四,这类文书背面有文书检查者都案、案头,说明此类文书单独成篇,各件文书之间前后没有明显的衔接文字,缺乏连续性。总之,由于这类文书由于缺少抬头,在文书末尾亦缺少固定的公文套语,因此极易将其误会成簿籍一类的文书。
通过对文书叙述形式、款识以及印章使用情况判断,这类文书属于首领官汇报军抄人员、装备等情况的公文,而非军籍。有了这个初步判断之后,我们对文书性质再作进一步的探讨。
首先,我们来看文书的行文主体。俄藏Инв.No.8371号文书第1行有“黑水属军首领梁吉祥盛”,落款中有“吉祥盛”,“吉祥盛”即“首领梁吉祥盛”;英藏Or.12380-3865号文书第1行有“黑水属军首领布阿国吉”,落款中有“阿国”,颇疑漏录“吉”字。笔者还对比了其余5件西夏文书,无一例外,文书中第1行中的“黑水属军首领”的名字与落款中的名字一致,这表明文书的行文主体是黑水监军司的军抄首领官。
其次,我们来看文书的体裁。在俄藏Инв.No.8371号文书和英藏Or.12380-3865号文书中都有“正军,一种纳 告/前自全军籍告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书第1行“告”字与“纳”字之间有空格,且“告”字后转行书写,这是古代文书中十分明显的“平阙”制度,表明文书的体裁应当是“告”一类的公文。文书中出现的西夏文“告”字,在黑水城西夏文献《乾定申年(1224)黑水守将告近禀帖》和《黑水城副将上书》中也曾出现,但学者翻译前后有所不同,如黄振华、史金波等先生早期研究论著中均将“告”字译作“禀”②黄振华:《评苏联近三十年的西夏学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2期;史金波、白滨、吴峰云:《西夏文物》,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340页。。《乾定申年(1224)黑水守将告近禀帖》和《黑水城副将上书》都属于上行文,由此可见西夏军抄文书亦属于“禀”、“告”一类的上行公文。
再次,我们来看文书的呈报对象。通过观察文书,可以看出这类西夏军事文书并没有抬头,因此只能推测其具体呈报对象。从上面两件西夏军事文书可以看出,首领官汇报的是所下各抄人员包括正军、辅主的人数、年龄,以及马匹、甲披的配备情况,因此可以推断其呈报对象是军抄上一级的军事管理组织,但是否为黑水监军司尚不得而知。
最后,我们来看文书所汇报的事项。上述两件西夏军事文书中都有“前自全军籍告纳”,这表明所汇报的事项为军抄首领官所管全部军籍的登记情况。《天盛律令》中规定了西夏国内纳军籍法:“每年畿内三月一日,中地四月一日,边境六月一日等三种日期当年年交簿”①史金波等译:《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六《纳军籍磨勘门》,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155页。。黑水城属于西夏边境地区,因此需要在每年六月一日之前交纳当年军籍簿,文书中登载的军籍时间是上一年六月一日至次年五月五月底,而文书的落款是在“六月”,这与《天盛律令》的规定基本符合。但这些军抄文书并不是正式的军籍簿,而是各军抄首领汇报所辖兵员等注籍情况的官文书,上级主管部门再依据这些基层军抄文书,检校各军抄兵员、官马、甲披等情况。西夏的检校分为季校和年校,“季校时诸正军、辅主之官马、坚甲检校完全不至者,庶人徒六个月。本人不来校,派别人时,何人徒三个月。首领、正军等知情者十三杖,不知者不治罪。一正军、辅主、负担之着籍官马、坚甲应依籍点名检验。其中正军、辅主新请领取官马、坚甲,有应注籍而未注籍者,按数有注册则依注册校,无注册则当分析按状上校验。不校而隐瞒者,正军、辅主之已向局分处告,且已减除,隐瞒者及不校者一律徒一年”②史金波等译:《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五《季校门》,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139页。。这是《天盛律令》对于“季校”的规定,大体可以反映年校的情况。西夏军队检校的主要内容是“正军、辅主、负担之着籍官马、坚甲”是否与注籍一致,是否存在隐瞒官马、甲胄的短损情况。文书中标明“无注销”,说明军员没有逃故、官马没有倒毙、甲披没有损坏等注销情况。文书中的“已定”,是指经过核查后,确定的军抄兵员(包括正军、辅主)、官马、甲披、印信等注籍情况。尽管这类军事文书不属于西夏军籍簿,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夏军籍登载的主要内容和登记形式。
综合以上,这类西夏军事文书并非是西夏军籍文书,而应当是黑水城军抄首领官向上级汇报所管军抄一年来兵员、官马、甲披、印信等注籍情况的告秉公文,因此我们依据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定名原则,大致可对上面两件文书进行重新定名,俄藏Инв.Nо.8371号文书可定名为《天庆戊午五年(1198)六月首领梁吉祥盛告秉文为军抄年校注籍事》。以此类推,其余几件性质相同的西夏军事文书亦可遵循此原则重新定名。
明确了文书性质,下面我们简要探讨一下文书的学术价值。笔者以为这批西夏军抄文书对于研究西夏军事史具有不可替代的资料价值。其一,文书反映了西夏时期确实在黑水城地区设置黑水监军司。这7件文书都以“黑水属军”作为开头,史金波先生已经指出,“黑水”应是黑水监军司的略称③史金波:《西夏文军籍文书考略》,《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146页。。聂鸿音先生曾依据《黑水城副将上书》对西夏后期黑水城是否设置黑水监军司产生过质疑,认为主持安置来黑水投诚者的并不是预期的黑水镇燕军司,而是不见于《宋史·夏国传》记载的“西院监军司”,这似乎说明黑水只有西院监军司的下属部门。同时对西院监军司、肃州和黑水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推测,指出也许在西夏朝廷颁布《天盛律令》时的确有西院、肃州、黑水三个监军司并存,而在其后的某个时间,肃州、黑水两个监军司都被撤销了,有关事务统一归西院监军司管理①聂鸿音:《关于黑水城的两件西夏文书》,《中华文史论丛》第6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45—146页。。在《乾定申年(1224)黑水守将告近禀帖》中,明确记载了黑水城守将没年仁勇,“历宦尚那皆、监军司、肃州、黑水四司”,说明乾定申年(1224)时,黑水监军司是存在的。同时,黑水城出土的这7件西夏军抄文书和《黑水城副将上书》时代相近,从这7件军事文书可以看出,西夏后期黑水监军司并未撤销。《黑水城副将上书》中没有出现黑水监军司和肃州,这可能与西夏对投诚人员的跨区安置有关。
其二,文书反映了西夏军抄组织形态。从西夏军抄文书可以看出,西夏时期的军抄在数量上并不一致,多则9个,少则3个,这说明西夏军抄在正军辅主的配备上并没有严格的人员数量限制。通观这7件军事文书,有一个比较奇特的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文书开头的首领官即文书登记的第一抄的正军,俄藏Инв.No.8371号文书和Or.12380-3865号文书中均登记有六抄兵员,但只有第一抄的正军前加有“首领”两字。按照西夏《天盛律令》的规定,西夏军抄中一般配备有“一等使军所属之战具法中,其披、甲、马三种”②史金波等译:《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五《军持兵器供给门》,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115页。,但从文书中可以看出,并不是所有的军抄都配备有“披、甲”。在7件军事文书中,首领官一般都掌管一定数量的甲、披,而其余军抄中配备甲披的情况并不普遍,英藏Or.12380-3865号文书六个军抄中,除首领官外只有正军布梁吉所在的军抄配备有甲披。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俄藏Инв.No.5944-1号文书中,该文书共登载九个军抄的兵员情况,除首领耶和小狗盛所在军抄配备甲披外,还有鲜卑宝双、耶和心喜吉所在的两个军抄配备有甲、披,耶和心喜长所在的军抄有披无甲。以上情况说明,西夏军抄中的首领官一般由正军中实力较强者充任。在西夏军抄文书中,呈报的军抄内容包括正军、辅主、甲、披、官马、印等信息,但以下开列具体信息中,没有出现“印”的实物,而从文书中多处钤盖有“首领印”的情况看,既有防止篡改文字的功能,同时也具有证实首领印印文内容、形制、规格的功能。文书中钤盖的多处印文,就是由军抄首领官掌管并在文书中行用的“首领印”。
其三,文书反映了西夏军抄战具配备情况。按照西夏《天盛律令》的规定,一般军抄包括正军、辅主和负担三类,但从文书中可以看出黑水城地区的军抄人员配备不齐,有的正军配备有两名或以上的辅主,但有的配备一名辅主,有的则只有正军单人而没有辅主,在所见文书中并没有出现“负担”的身影。文书中还反映了西夏军抄马匹配备并不统一,一般一抄配备一匹官马,但有的用骡子代替,有的则没有配备任何马匹。甚至在有的军抄内部既没有辅主,也没有马匹。上面已经提及,各军抄中“披、甲”的配备也不统一。即使配备了披甲的军抄,在披甲的种类、数量上也不均衡,有的数量多些,有的数量少些,有的甚至只有“披”而没有“甲”。西夏时期的军事组织形态是在部落兵基础上演化而来的征兵制,一般男子十五岁成丁著籍,至于六十岁为止停止服役。西夏军抄二丁取一强壮者为正军,另外一丁则为“负担”,与正军组成一“抄”。据曾巩《隆平集》记载:“年六十以下,十五以上,皆自备甲胄弓矢以行”①[宋]曾巩:《隆平集》第卷二〇,引自韩荫晟编:《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 上卷 ),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116 页。。这大致反映的是西夏建国之初部落兵制下,军抄自备甲胄弓矢的情况。随着征兵制的实行,西夏政府开始为兵员配备甲胄、官马和兵器。按照《天盛律令》的规定“正军有:官马、弓一张、箭六十枝、箭袋、枪一枝、剑一柄、囊一、弦一根、长矛杖一枝、拨子手扣全。正辅主有:弓一张、箭二十枝、长矛杖一枝、拨子手扣全。负担:弓一张、箭二十枝、长矛杖一枝、拨子手扣全”②史金波等译:《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五《军持兵器供给门》,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114页。。按照这些规定,西夏军抄中的正军官马、武器,而辅主、负担只配备一定数量的武器而无官马。但从文书中可以看出,正军和辅主都没有配备武器,前面已经提及西夏的战具只包括“披、甲、马”三种,因此弓矢、枪剑等兵器并不在战具之列,因此军抄文书中没有出现兵器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从文书中可以看出,军抄内所有甲披、官马,都归正军所有,而辅主名下什么也没有登记,说明西夏军抄是以“正军”为主要战斗力量,“辅主”主要配合“正军”作战。
其四,文书还反映了西夏基层军抄的“户头”管理制度。在这批西夏军抄文书中,出现了很多年龄偏高的正军、辅主,其中不乏八九十岁,甚至上百岁者。史金波先生曾对这种现象进行过解释:“大约西夏后期战乱频仍,青壮年减少,军队的士卒多老迈,战斗力十分衰弱”③史金波:《西夏社会》(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27页。。但是我们依据常识判断,这些高龄士兵不但没有战斗力,恐怕是否存在还是个问题。同样类似的情况在明代黄册中,在一件徽州黄册中也记载了高龄户主的情况,现将文书节录如下:

民瓦房三间④栾成显:《明代黄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88页。
又如现存《明万历三十年徽州休宁县二十七都五图黄册底籍》文书中,最后载有三十六户军绝户,如册中第一甲最后一户:

栾成显先生曾对这一现象进行过解释,认为:“这些绝军人丁的年龄多在百岁乃至二百岁以上,实系名存实亡。但每次大造仍照旧开报,主要怕其子孙更改户籍,以备查考”①栾成显:《赋役黄册于明代等级身份》,田澍等主编:《第十一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3页。。栾先生讲的这些户主名存实亡应当是成立的,但似乎忽略了这些户主为“户绝”,当然不存在子孙更改户籍的情况。明代黄册中的高龄户主,说明这些户主属于虚拟户头,并不是真实存在的。由此可以推断,西夏军抄文书中的高龄士兵应当是不存在的,之所以进行登记,当另有原因。笔者曾就此问题请教过军事史专家张金奎先生,张先生认为黄册中高龄户主的存在和明代实行的“户头”管理体制有关。户主出现绝户等情况下,户主财产包括土地、房屋等可由族内近支侄辈继承,当然继承财产者需要承担赋役或兵役义务。由于在民间的继承关系相当复杂,不可能在黄册中完全写明,因此实行“户头”管理制度,在原始户头名下的财产继承者负担兵役,但原始登记的户主不作变更。由此反观西夏军抄文书,其登记的各高龄士兵应当是虚拟的,国家不可能允许如此高龄的士兵上战场作战,按照西夏《天盛律令》的规定,士兵一般六十岁退役,说明士兵一旦年老丧失战斗力,国家允许其退出战斗序列。据此推断文书中这种登记高龄士兵的现象只能是国家管理的“户头”,这些户头可能为绝户,国家在户头财产的继承者中抽丁补役,出任正军或辅主。当然也存在着国家通过管理户头,由部落首领组织兵员的可能。这是西夏对兵役制度的一大创造,既适应了军户不断繁衍、变化的复杂实际情况,又保证了兵员得以不断有效补充。
其五,文书还反映了西夏兵员、战具的检校制度。前面已经提及,西夏军队的检校分为季校和年校,文书集中反映了西夏后期黑水城地区军抄年校的情况。从文书中可以看出,年校的内容是以正军为中心展开,检校正军姓名,年龄,一抄人数,马匹、甲、披三种配备,同时还要登记马匹毛色、甲披具体明细以及配备辅主数量、强弱、姓名以及年龄等。总的来说,西夏军队检校的关注点在于兵员、战具和官马三大类。西夏《天盛律令》规定:“(季校时,正军)披、甲、马三种有一种不备,十三杖;二种不备,十五杖;三种皆不备,十七杖”①史金波等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五《季校门》,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132页。。当然,辅主、负担的装备如果不全,也有相应的处罚规定。因此,在文书中特别注出正军马匹、披、甲三种配备的情况是三种都有,还是有两种、一种,甚至三种都没有。对于兵员的检校,主要看兵员是否在籍、是否亲自接受检校、是否迟到,《天盛律令》规定:“军正首领因公任其他职,军上权检校在,校集日迟至及完全不至时,其权检校中为末驱小首领、舍监者,不论有官无官,与正首领校集日迟至及完全不至罪相同判断”②史金波等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五《季校门》,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139页。。西夏《天盛律令》中还严格规定了甲、披的尺寸和规格:“获披、甲:甲者,胸五,头宽八寸,长一尺七寸;背七,头宽一尺一寸半,长一尺九寸;尾三,长一尺,下宽一尺四寸;头宽一尺一寸;四,宽八寸。裾六,长二尺五寸,下宽二尺四寸半,头宽一尺七寸;臂十四,前手口宽八寸,头宽一尺二寸,长二尺四寸;□目下四,长八寸,口宽一尺三寸;腰带约长三尺七寸。披者,“河”六,长一尺八寸,下宽三尺九寸;头五,长一尺五寸,头宽一尺七寸,下宽九寸;背三、长九寸,下宽一尺七寸;喉二,长宽同六寸;末尾十,长二尺八寸,下宽二尺九寸,头宽一尺七寸;盖二,长七寸,下宽一尺,头宽八寸”。这些细致的规定,是战具检校时的重要依据。检校时主要检验甲披是否短缺损坏,是否符合样式,“校验各种披、甲、马及种种杂物时,如有损毁、式样不合,及官马肥瘦等因,正军、辅主、当事人之罪,使与校验短缺罪状高低相同判断……如其所修整式样不合,及全未修整者,一律当于季校时计量,按高下当承杖罪”③史金波等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五《季校门》,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135页。。
总而言之,从文书学的角度来看,黑水城出土的西夏军抄文书无论是行文、落款、签押、用印、平阙等都符合官文书的特点,因此就其性质而言并非西夏军籍,而是军抄首领官向上级报告军抄年校情况的告秉文。基于此种认识,故对这批西夏军事文书的价值进行重现审视。这批军事文书不仅证明了西夏中后期黑水监军司确实存在,同时还为研究西夏军事制度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文书中“首领官”是由军抄中实力较强的正军担任,负责申报在籍兵员、披甲、官马情况。从文书中所记载的军抄情况看,西夏中晚期黑水城地区的军抄并没有按照统一的标准配备人员、披甲和官马,各军抄之间的力量存在不均衡发展状态。文书中的高龄士兵,应当是徒有虚名,并非实际在籍的兵员,而是西夏军籍中的原始“户头”,西夏政府通过管理“户头”,保证补充兵员。同时文书还反映了西夏军队的检校制度,通过季校审查基层部队兵员、战具、官马的实际在籍情况,并通过制定战具样式、惩罚渎职官员等手段,保证基层部队的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