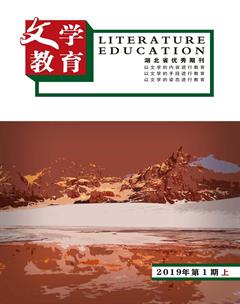周晓枫散文的题材取向
内容摘要:周晓枫散文,坚决地放弃选材上的洁癖,而保存叶子上的泥。作为一名女性写作者,唯美与温柔并非她的关键词,暴力与纯粹才是流淌于她骨骼中的血液。其散文挖掘隐秘而复杂之处的黑暗,努力地逼近破损的真相,最后获得艺术的真实。
关键词:周晓枫散文 题材 破损 真实
周晓枫的散文,在表达上给人印象很深的无疑是穿插在字里行间的“巴洛克的修辞”,这是她一直以来所偏爱的形式。对于语言的打磨和技巧的运用,她有着匠人般的执念。但这并不是她在追求华丽的语言所带来的阅读与审美快感,而是要通过一个绝妙的比喻,将看似无关的事物联结得恰到好处。“修辞立其诚。”【1】越过考究且浓稠致密的语言,去抵达纯粹的真实和事物的真相,才是作者真正的创作立场。
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周晓枫的文字,在唯美和沉郁之外更多体现着冷静的观察和凌厉的表达。她常常发问,继而思考有关于女性、身体、人性等一切复杂的事物。但在我看来,最特别之处还在于她的散文在努力地逼近破损的真相以还原某种艺术意义的真实。人们的内心往往是复杂而隐秘的,对于现实生活中的苦痛与黑暗,往往选择逃避或修饰,“我们不敢面对,我们包庇,我们在黑暗上刷涂明亮的油漆以自欺欺人”【2】。而周晓枫以此为切入口,不断地去挖掘光明背后藏着的黑夜,让真相和无法示人的丑陋如决堤的洪水喷涌而出。
一.被虫子啃过的坏果子
《有如候鸟》讲述了一个小女孩在童年被性侵,而在之后的日子里如候鸟一般不断地迁徙,让灵魂和肉体四处远游和流浪的故事。对于世人羞于启齿的丑恶,周晓枫选择大胆地撕破并直白地暴露:“她躺上羞耻之床,再次分开蚌壳般闭合的部分……听任探测者打开光线,照射秘密的溶洞。”类似这样的描写文中还有许多,不禁让我联想到了林奕含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在运用比喻方面,这两位女性作家都是天赋异禀的:每一个比喻都是一个暴力现场,每一句话都仿佛是一记重拳,重重地打在读者的心上,疼痛与眩晕中还带有血的咸腥。散文中的小女孩把自己当作“一枚被虫子啃过的坏果子”。她失眠,与和她年龄相仿的房思琪一样害怕闭上眼睛,因为即便进入梦里,也只是坠入深深的黑暗:“梦里的铁匠带着强烈口臭,用老年的猥琐,释放他不能平息的情欲……叔叔的犁,数次开垦在她身体荒凉而坚硬的冻原上,他身体前行的每一步,都是她每一公分的黑暗。”小女孩梦里的邻居叔叔就像房思琪噩梦里的李国华老师,他们一步步地吞噬掉少女的肉体和灵魂,肆无忌惮。因为,他们知道“一个如此精致的小孩是不会说出去的,因为这太脏了。自尊心往往是一根伤人伤己的针,但是在这里,自尊心会缝起她的嘴”【3】。
由于社会观念和家庭教育向来都和性保持着一种安全距离,即使是公开谈论也都被当成一种禁忌。因此,当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后,作为受害者的女性,特别是没有接受性教育的年幼者,往往羞于启齿而选择独自忍受。说到底,性侵其实是一场社会性的谋杀,施暴者逃之夭夭,旁观者冷眼相向,只留下受害者独自将丑恶与肮脏深埋土中,最后,沃土变成荒原,寸草不生。
二.男友的密纹唱片
“假设抹除那些破损,我们只会目睹一个失真的丰收。”【4】周晓枫深知,真实的丑要比失真的美更具有存在的价值。因此,除了写性侵,她还在《布偶猫》中揭露了爱情中的破损:男方对女方的暴力行为。
女主人公叫小怜,听名字就让人怜惜,而她正是这场爱情中的殉葬品。布偶猫是作为一个施暴者的男友在肢体冲突后给她的道歉和补偿。布偶猫因性格温和而常常成为家养宠物的首选。可不幸的是,在这场爱情悲剧中,小怜的命运和这只猫有着惊人的相似:她们一同收起自己的爪牙,以超乎寻常的忍耐去艰难地消化着自身的不幸,向“主人”乞讨垂青与偏宠。
在同样作为女性的“我”看来,她可真傻,就算是被伤到剧烈,也还要在掩饰中歌唱,“仿佛注定是男友的密纹唱片,可以承受他重复中不断的划痛”【5】。“我”并不明白,为何小怜会对施暴者产生如此强烈的依恋。但在惋惜和不解之余,却忍不住想要去剖析这场悲剧中的男女主角。在“我”这个旁观者看来,“女之耽兮,不可脱也”,小怜已沉湎于这场悲剧的美学之中。可“我”需要在这场关系失衡的畸形爱情里,把那些埋藏在内心隐秘处的病态的念头全都暴露出来,并在此基础上去思考暴力与爱。因为,“我”知道,自己的身边有千千万万个小怜存在,她们“蜷起四肢,形同遭受暴力的姿态,回缩成为母腹中脆弱的胎儿……既不能接受现实,也难以面对未来”【6】,而悲剧的根源正是她们和布偶猫一样,拥有着耐痛的美德。
在社会角色的认定中,除去母系社会的那个时代,很多时候,女性都被当作弱势群体。因为她们的身体里总是流淌着母性的血液,其中包含著宽容。而流淌着“暴君”血液的男性,常常会选择暴力来完成他们的统治。沉湎于错觉的女性,在畸形的宽容中,进行自我欺骗以实现自我的救赎。当逾越界限的暴力将失控的情绪和肢体配合在一起时,她们以为这是强烈到失控的爱欲。既然是爱,当然需要无限的给予:让自己如教堂一般的身体,去宽容那些施暴后的悔意与求饶,让这具伤痕累累的身体去孕育暴力与爱交媾的产物。然而,在男性眼里,女性的“悲戚、恐慌和屈服,对他来说是一种小娱乐──哭红的眼睛,颤抖的肩膀,女人反而具有旦角般的一种妩媚……哀感顽艳的形象让他兴奋,仿佛听到做爱中的叹息”【7】。他们寻求的是快感,即使这背后充斥着罪恶与残忍。
三.殡仪馆里的化妆
在《离歌》中,周晓枫说屠苏那张像经过不自然地敷粉的美颜自拍给了她不祥的感觉,因为这有点像殡仪馆里的化妆。描写中流露出作者对“化妆”的厌恶。当然,这里的“化妆”应该是广义的。是的,化妆掩盖不住残酷的真相。在周晓枫的散文中,她索性将人世间的“美颜”“化妆”通通卸掉,还他一个真实的面容。
青春或是童年,这些词语“特别容易被文人过度修饰,其亮度几近饱和,最后变成美妙的乌托邦”【8】。很多文人深知世人希望看到的是什么,所以他们选择自动过滤掉丑和恶,为读者构筑一个虚幻却又真实的乌托邦。但周晓枫不同于这些文人,她在散文中常常给那些过度修饰的词语卸妆。在《恶念丛生》中,童年的我们不再如表面那般天真无邪,其中还隐藏着常常被大人们忽略的残忍:“我们烫死蚂蚁和蝴蝶;撕断蜻蜓的翅膀,让它成为一根新鲜的铁钉;我们用汽油浸泡野猫的尾巴,让它边奔跑、边燃烧,像雷神降下的小火球……”【9】卸掉浓妆艳抹,童年也有其残忍的一面。这或许才是童年的真实面目。
周晓枫的散文中,还有比这更为残忍的景象。
在《石头、剪子、布》中,她这样描写被无轨电车碾压后的猫:“前半截的身子粘贴在地面,突然消灭了体积,只有勉强形成的厚度;后半截的肢体完整,甚至饱满,奇怪的是两条毫发无伤的后腿一直在轮流蹬踏,遭受了电击似的。这只猫暂未接受自己瞬间的死,它还在持续逃跑的惯性里。没有头脸和胸腔的猫,它只剩腰下的抽搐身体。”周晓枫在冷静地描述一个无比惨烈的画面,但越是这般的冷静,就越使人毛骨悚然。她的这类文字,已接近于孙绍振先生所说的“审丑”了。孙绍振先生指出,“审丑不一定是对象丑,而是情感的冷漠,冷漠是最根本意义上的丑”【10】。被碾压后的猫,已经是“丑”了;而把如此惨烈的画面当作艺术品去细细地品鉴,则显示出情感的冷漠,冷漠到近乎残忍,这才是真正的“丑”。作者想要传达的,或许就是人性中的破损。
对于那些被掩盖掉的破损、残忍等丑恶,周晓枫选择“放弃选材上的洁癖,保存叶子上的泥”【11】,用丰富的联想、暧昧的象征以及绝妙的比喻去和读者的精神“洁癖”来一场正面的交锋。她深知读者保留着美化女性的期待,但她却偏爱站在边缘写作,因为边缘地带往往更靠近真实。她不会回避灵魂或肉体的黑暗与不堪,相反,她“小心翼翼地敲击一个又一个的词,直到它们的蛋壳上出现细小的裂隙。那些精美因她而破裂的纹路,是属于她的创造”【12】。正是因为破裂,才在更大程度上接近圆满。因为,透过破裂的缝隙,读者才能看到隐匿于文本背后的真相——作者以耻为荣,以冷静和理性去直面破损和羞于启齿的欲望。
入之愈深,其进愈难。想要“深入黑暗中去理解,也不在名利的强光里造成瞬盲”,【13】本就不是一件易事,而要在黑暗中找到裂口去更深入地逼近真相也就更难。但是,“老少咸宜”的安全,只会使人错失探险者才能目睹的极境。只有直面自身的黑暗带给我们的危险,才会在探险中收获“其见愈奇”的真实与美丽。在散文的这场探险中,周晓枫无疑是满载而归的。
参考文献
[1][2]周晓枫:《与姜广平先生对话》,《周晓枫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278、297页。
[3]林奕含:《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版,第124页。
[4]周晓枫:《来自美术的暗示》,《周晓枫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73页。
[5][6][7]周晓枫:《布偶猫》,《有如候鸟》,新星出版社2017年版,第44、21、47页。
[8]周晓枫:《与姜广平先生对话》,《周晓枫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289页。
[9]周晓枫:《恶念丛生》,《有如候鸟》,新星出版社2017年版,第89页。
[10]孙绍振:《孙绍振解读经典散文》,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75页。
[11]周晓枫:《来自美术的暗示》,《周晓枫散文選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74页。
[12]周晓枫:《初洗如婴》,《有如候鸟》,新星出版社2017年版,第71页。
[13]周晓枫:《有如候鸟》,新星出版社2017年版,第300页。
(作者介绍:薛胜寒,山东大学文学院在读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