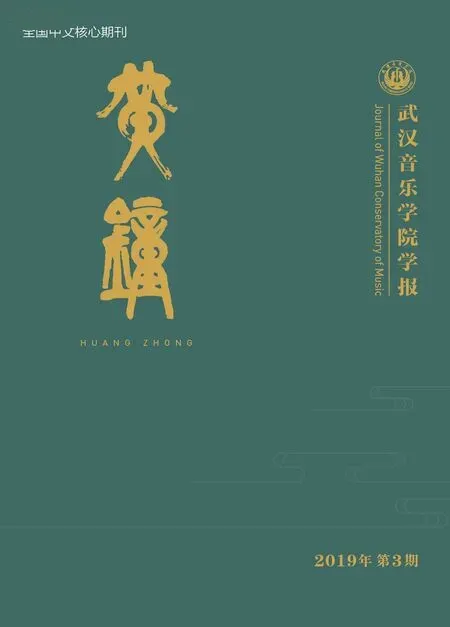中国古代音乐制度百年研究回顾
张建华 余 虹
从近百年(1910年代至2010年代)学术发展史看,关于中国古代音乐制度的研究,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一是20世纪上半叶,此期是音乐制度研究的萌发期;二是20世纪50至70年代,此期是音乐制度研究的自觉期;三是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此期是音乐制度研究的发展期;四是21世纪初期约20年间,此期是音乐制度研究的繁荣期。
一、20世纪上半叶:音乐制度研究的萌发期
叶伯和《中国音乐史》(1922),向来被认为是中国近代第一部音乐史。是书第四篇“秦汉以后”之第二节名曰“乐府的设立”,这是近代学术史首次将音乐机构纳入到音乐史的论述范围。不过其名虽云“乐府的设立”,但却仅引马端临《文献通考·乐考》之“武帝立乐府”一则材料寥寥带过,其实却重在论述汉代歌曲。①叶伯和:《中国音乐史》(上卷)第四篇,成都:昌福公司1922年版,第58-61页。按:叶氏《中国音乐史》(下卷),原载于《新四川日刊·副刊》1929年第587-593期;转载于《音乐探索》1988年第1期;2019年7月,成都巴蜀书社首次将叶氏《中国音乐史》上、下卷合刊出版。这种名实相左的事实,以及叶氏对西汉以外其他朝代音乐制度的阙如,正说明他对音乐制度的研究尚处于朦胧的无意识状态。王光祈《中国音乐史》(1934)第七章“乐队之组织”,对《周礼》和陈旸《乐书》所载周代乐悬、《乐书》所载堂上乐和堂下乐、杜佑《通典》所载唐代燕乐之配器均做简要介绍。②王光祈:《中国音乐史》(下册)第七章,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版,第83-90页。王著所涉各要点,尚停留于一般性的译述,且所述皆不系统。此外,顾梅羮《中国音乐史》(1920,一说1923)、童菲《中乐寻源》(1926)、郑觐文《中国音乐史》(1929)、许之衡《中国音乐小史》(1931)、宋寿昌《中西音乐发达概况》(1936)、杨荫浏《中国音乐史纲》(1943石印、1952铅印)、岸边成雄《支那音乐小史》(见《东亚音乐史考》,1944)、刘伯远《中国的古乐》(1947)等著述,均不同程度地述及雅乐或雅乐体制,在一定意义上与音乐制度研究具有关联性。
这一时期,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古代音乐制度的专题研究论文,如《四部乐考》(1938)、《唐代的梨园》(1940)、《唐代教坊的成立及变迁》(1941)、《十部伎的成立及变迁》(1941)、《宋代教坊之变迁及其组织》(1941)、《唐代教坊之组织》(1944)等,这些论文并未被及时译介国内,故在20世纪上半叶未能在国内产生重要影响,其主要观点大多被吸收进岸边氏此后的专著《唐代音乐史的研究》(下文将详述该著)。从岸边氏所发表论文看,他对中国音乐制度的思考和研究,从20世纪30年代已经开始,其先知先觉的学术敏感和日积跬步的探索精神,注定他要在中国音乐制度研究领域走在中西学者之前。但岸边氏此期研究的影响,仅限于日本一隅,尚未引起中国学者的响应。
王国维《释乐次》(1916)考证了周代天子、诸侯、大夫、士的迎送、宴饮、祭祀等用乐制度。③王国维:《释乐次》,《王国维手定观堂集林》卷二,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31-43页。按:王氏撰《乐诗考略》,原载于《学术丛编》月刊1916年第3册〔辑〕,后将之析为《释乐次》《周大武乐章考》《说勺舞象舞》《说周颂》《说商颂(上)》《说商颂(下)》《汉以后所传周乐考》共7篇,收入1923年王氏手定密韵楼刊本《观堂集林》卷二。这是近代以来,首次对周代用乐制度的系统论述,不过王氏所论的目的,乃在解读周代诗乐,而不在廓清周代音乐制度。王书奴《中国娼妓史》(1934)梳理了中国古代娼妓的生存史,所论娼妓也包括古代歌妓,对认识古代官妓、家妓及其寄生组织有重要意义。王史也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部研究娼妓和歌妓的专史,对后世研究歌妓制度、歌妓与诗词曲之关系等均具开拓意义。④王书奴:《中国娼妓史》,上海:生活书店1934年版。王芷章《清代伶官传》(1936)和《清升平署志略》(1937)分别对清代宫廷伶人和音乐管理机构予以论述,其中对清后期升平署之沿革、成立、分制、职官、署址所述尤详。⑤王芷章《清代伶官传》由上海中华印书局于1936年10月初版,王氏《清升平署志略》由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于1937年4月初版,二著均有多种翻印本行世。二著对研究清代宫廷音乐制度颇有导夫先路之功,唯所述乐人仅限于有清一代宫廷伶人,是为研究戏曲之目的而作,又且升平署也并非一专门音乐机构,故还不能看作音乐制度研究之专著。冯沅君《古优解》(1941)则专就先秦从事歌舞调笑的优伶进行论述,涉及古优的起源、性质、特征、影响。该文是第一篇系统考察先秦优伶的长文,对认识先秦乐人及其活动形态具有重要意义。⑥冯沅君:《古优解》,《冯沅君古典文学论文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73页。按:冯氏另有《汉赋与古优》(1943)、《古优解补正》(1944)二文。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1943)第一编第二章“乐府之产生及其沿革”,对两汉乐府机构略有考证,并指出“则高祖之时,固已有乐府之设。至惠帝二年,乃以名官”,“然乐府之立为专署,则实始于武帝”。⑦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第一编第二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页。按:萧氏之史,实为其1933年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论文,1943年由上海中国文化服务社首印,因其撰成之初传之不广,故本文定其初版年为产生影响之时间。近代以来,萧氏是第一位高标乐府始立于汉武说者。萧史虽专立一章论及乐府机构,但也不过区区两千字,其重点更不在于梳理两汉音乐机构发展之具体情形,而在于论述乐府机构与乐府歌诗之关系。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1944)第五章专列“音乐”,但其所论多属音乐形态之渊源与发展,并未直接触及音乐制度本体。
此期学者对中国古代音乐制度的研究主要存在如下问题:一是国内音乐界学者对音乐制度的研究还处在朦胧状态,虽然偶有涉及,但只不过是一笔带过,所论既不系统,也不深刻;二是国内文史界学者对音乐制度的研究较音乐界略显成熟,出现了论述音乐制度的独立章节和单篇论文,但所论仍然较为简略和单薄,其论述重点也不在音乐制度本体;三是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未被及时译介国内,中外学术信息交流不畅,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学术研究的催化和激发;四是论述对象分布不均,所论主要集中在周代、汉代、唐代,清代则略有涉及,其余朝代几乎完全缺失。
二、20世纪50至70年代:音乐制度研究的自觉期
王运熙《汉魏两晋南北朝乐府官署沿革考略》(1958)一文,对两汉魏晋南北朝的乐府官署进行梳理和考证。文章指出,这一时期乐府官署的发展,从汉代的两分法到魏晋的三分法,再退缩到宋齐的一分法和梁陈的二分法。王氏另文《汉武始立乐府说》(1958),则指出《史记·乐书》所称“乐府”、《汉书·礼乐志》所称“乐府令”均为泛称,实际乃指“太乐”或“太乐令”。⑧王运熙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乐府官署沿革考略》和《汉武始立乐府说》均见于《乐府诗述论》中编,《王运熙文集》第一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67-172、173-175页。按:王氏二文,初撰于20世纪40年代末期至50年代初,首次公开发表载于《乐府诗论丛》,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王氏二文,粗线条地勾勒出汉至唐前音乐机构的沿革,也为武帝以前“乐府”之称,寻求到一种可立之说。二文均是以音乐机构为研究对象的专题论文,昭示着中国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将音乐制度纳入到学术研究之范围。但王文所论的落脚点,仍然是以研究中古诗歌为目的,故还不能视为对音乐制度研究的真正自觉。日本学者寺田隆信《关于雍正帝的除豁贱民令》(1959)一文,专列一节论述明末和清代乐户制度。寺田氏指出,在明代末期,一部分乐户在生活内容方面,大体与一般下层农民相差无几;雍正除豁乐户,仅停留于户籍制上,并不意味着乐户已从贱业中解放出来;直到乾隆四十八年(1783),乐户出身的人如要报捐应试,仍需苛刻条件,即从正式除豁算起,下逮四代,本人及亲族悉不从事贱业者方可报捐应试。⑨[日]寺田隆信:《关于雍正帝的除豁贱民令》,原载于《东洋史研究》第十八卷第三号,1959年12月。亦见于刘文俊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六卷,杜石然等译,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88-492页。这些论述直指音乐制度本体,只是它的体量还比较短小,又且并非关于音乐制度的专题论文,仅在其中夹议一节,故在音乐界未足产生重要影响。
任半塘《唐戏弄》(1958)第七章“演员”,对唐五代优伶有详细考述,藉此可窥唐五代优伶之生存状态。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唐代音乐史的研究(上、下)》(1960、1961)实为其唐代音乐史研究构架之“乐制篇”,含“序说”和“各说”两部分:“序说”首章对唐前音乐制度略作梳理,其余四章则分论唐初太常寺乐工制度、唐中期教坊和梨园的设置、唐末妓馆的活动、唐代音乐制度对宋代音乐制度之影响等;“各说”则详细考证太常寺乐工、教坊、梨园、妓馆、十部伎、二部伎和太常四部乐。岸边氏此著虽不乏商榷之处,但作者运用考据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与广阔视野,总体上呈现了唐代官府音乐机构和民间音乐组织的基本风貌,堪为唐代音乐制度研究之典范。⑩[日]岸边成雄《唐代音乐史的研究》(上、下册)中的上册于1960年2月由东京大学出版会初版,下册于1961年3月由东京大学出版会初版;梁在平、黄志炯所译中译本,于1973年10由台北中华书局出版,2017年3月中译本被收入《中华艺术丛书》,由台北中华书局再版。岸边氏的著作,相较于同期其他日本汉学家和中国学者来讲,可谓已迈出别样的一步,在中国音乐制度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学者对中国古代音乐制度的研究真正走上自觉的道路。任半塘《教坊记笺订》(1962),是任氏构建其“唐代音乐文艺研究”宏大格局之一种,也是唐代教坊制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该著对唐代教坊制度和相关乐官、乐人逐项考订,初步梳理出唐代教坊制度的基本概貌;对唐代教坊所保留的46支大曲和278支普通曲目逐一考订,基本还原了唐代教坊演唱的盛况。⑪任半塘笺订《教坊记笺订》,于1962年7月由北京中华书局初版,2012年4月收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典籍丛刊》,由北京中华书局再版。另有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10月《任中敏文集》单行本和2015年10月《任中敏文集》十卷本。任著和岸边氏的著作,一部属专题音乐制度研究,一部属断代音乐制度史,二著几乎同时公开发表,皆对唐代音乐制度的研究具有奠基意义,可并称20世纪唐代音乐制度研究之双璧。
杨荫浏《中国音乐史稿(远古至宋)》(1964)经过多年的讨论和修改也出版面世。在史稿中,作者把音乐机构和音乐制度作为重要章节论述,例如,其第三章列“音乐机构和音乐教育”一节、第五章列“国家设立的音乐机构——乐府”一节、第九章列“太乐署、鼓吹署、教坊和梨园”一节、第十八章列“燕乐”一节,这些内容已把先秦至宋的主要音乐机构融入到音乐史的论述之中。相较于20世纪上半叶的音乐史著,这是一个明显的转变。杨氏在修订本《中国音乐史稿(远古至清)》(1981)中,坚持了这一学术主张,这标志着在传统的“律、调、谱、器、人、事、歌”的维度之外,中国音乐史开始把“制”也纳入到常态化的论述范围。杨著在中国音乐史的撰写上具有典范意义,对此后的音乐史著产生了深远影响。⑫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音乐史著,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把音乐制度作为重要的论述对象。通代史如:沈知白《中国音乐史纲要》(1982)对汉代的乐府、唐代的教坊、宋代的瓦肆等均有论述;祁文源《中国音乐史》(1989)对远古的教育机构和音乐教育、周代的礼乐和礼乐教育、汉代的音乐机构、唐代音乐机构和乐工等均有论述;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1989)对西周的乐官制度、汉代的乐府、唐代的音乐机构、宋代的瓦肆勾栏等均有论述;郑祖襄《中国古代音乐史》(2008)对周代礼乐制度、汉代乐府、隋唐音乐机构等均有论述。断代史如:李纯一《先秦音乐史》(1994)对周代的制礼作乐、春秋的乐官和乐工均有论述;孙星群《西夏辽金音乐史稿》(1998)对西夏乐舞机构、辽代音乐机构均有论述;关也维《唐代音乐史》(2006)对唐代音乐机构和乐舞教育有详论。另外还有许多通代史和《中国艺术史(音乐卷)》(2006)所收断代史涉及音乐制度,限于篇幅,恕不一一举证。另外,张世彬《中国音乐史论述稿(上册)》(1974),在第三篇专设“近古期各种音乐制度”,对汉唐太常寺、唐宋教坊、唐代梨园、唐代十部伎、二部伎和太常四部乐分别予以论述。张稿虽云“近古期各种音乐制度”,但其所论却主要集中在唐代,并未涉及元明清三代。⑬张世彬:《中国音乐史论述稿》(上册),香港:友联出版社1974年版,第109-149页。按:张稿上册,由香港友联出版社于1974年11月出版;张稿下册,由香港友联出版社于1975年11月出版。实际上,张稿第三篇仍然是一部唐代断代音乐制度简史,或者说,其论述尚囿于乃师岸边氏《唐代音乐史的研究》之范围,并没有明显突破。李健《历代乐官制度试析》(1975),是迄今所见第一部研究乐官制度的小书。该著除去“序说”和“结语”外,共分八章,其第六章“雅、俗乐之分途及音乐与文学之结合”和第九章“明清时际之古乐整理”,皆与乐官制度关系不甚密切。⑭李健:《历代乐官制度试析》第六、九章,台北:五洲出版社1975年版,第29-34、53-58页。此著篇幅尚短(约4万字),体例亦不周备,所论未免流于泛泛,时或偏离主旨,故不足以在学界产生重要影响。陈万鼐《清史乐志之研究》(1978),所论重在清史乐志之音律器数,唯在第九章列“圆丘大祀的乐仪”和“圆丘大祀的乐队组织”二节,略及清代圆丘大祀音乐制度。⑮陈万鼐:《清史乐志之研究》第九章,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78年版,第282-283页。从以上著述来看,这一时期的学者对中国古代音乐制度的研究已经初具自觉意识,只是还未形成整体性的观念或贯通性的观点。
此期学者对中国古代音乐制度的研究主要存在如下问题:一是对音乐制度的研究虽然初步自觉,但成果较少,还不足以形成浓厚的学术氛围,更未能把音乐制度提升到学术史上一个新研究领域的高度;二是对音乐制度的研究还停留在简要勾勒和一般描述上,并没有把音乐制度的研究与音乐本体的研究联系起来,二者脱节比较严重;三是对音乐制度的研究仍然分布不均,主要集中在汉唐,对其他朝代音乐制度的研究则相对薄弱,还未形成对音乐制度进行整体研究的基本格局。
三、20世纪80年代至世纪之末:音乐制度研究的发展期
万依、黄海涛《清代宫廷音乐》(1985)是第一部研究宫廷音乐制度的专著。是书“引言”称:清代宫廷音乐,就其性质而言,可分为典制性音乐和娱乐性音乐;就其使用场合来说,又可分为内廷音乐和外朝音乐。首章又将外朝音乐分为四个阶段: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至崇德末年(1643)、顺治元年(1644)至康熙晚年(约1712)、康熙五十二年(1713)至乾隆初年(约1740)、乾隆六年(1741)至宣统三年(1911),并对外朝乐队组织有详述;二章论内廷音乐机构之沿革及其乐队组织。⑯万依、黄海涛:《清代宫廷音乐》引言及第一、二章,北京、香港:紫禁城出版社、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5年版,第7、12-38页。该著既重律调谱器,又重音乐制度,初步勾勒出有清一代宫廷音乐的基本风貌。其对清代宫廷音乐的分类和分期,均对进一步研究清代音乐制度具有开创和启示意义。胡忌、刘致中《昆剧发展史》(1989)从家庭戏班、职业戏班和宫廷演剧三个层面,论述了昆剧发展史。⑰胡忌、刘致中:《昆剧发展史》,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版。从胡史开始,民间音乐组织开始逐渐受到学者重视。张发颖《中国戏班史》(1991)是继胡史之后,又一部既关注宫廷音乐机构,又关注民间音乐组织的专著。从该著所论要目看,如中国历史上的乐户、唐代宫廷散乐机构、宋教坊与勾栏演出、金元家庭流动戏班演出、明代一般营业戏班、清代北京诸戏班递变、清代徽班、历代家班、清代宫廷演剧与民间戏班、戏班之经营管理等,其对民间音乐组织有明显倾斜,较之此前音乐制度研究仅重宫廷的风气,算是一股清流。⑱张发颖:《中国戏班史》,沈阳:沈阳出版社1991年版。萧亢达《汉代乐舞百戏艺术研究》(1991)之“绪论”专列“汉代乐舞管理机构及其职能”一节,对西汉和东汉音乐机构,如乐府、太乐署、太常、少府职能均做简要梳理。⑲萧亢达:《汉代乐舞百戏艺术研究》(修订本)绪论,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第3-9页。是书所论,重在乐舞百戏,故对音乐制度仅作背景式的概述。李尤白《梨园考论》(1995)实为一部散论集,其中《梨园的来历》《梨园的遗址》《梨园的组织》三文,对唐代梨园的产生、位置和职能均有简述。李氏在论及唐代梨园位置时,对陈寅恪、任半塘二先生的观点略有辨正,并提出唐代梨园的真正位置,只能在西安城西六华里许的未央区未央乡大白杨村,可备一说。⑳李尤白:《梨园的遗址》,《梨园考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页。川上子《中国乐伎》(1992)初步梳理了乐伎这一群体的发展流变,多涉乐伎的生存、生活、交往等活动。㉑川上子:《中国乐伎》,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92年版。修君、鉴今《中国乐妓史》(1993)对中国古代官妓、私妓、营妓、家妓、胡妓、歌馆乐妓、宗教乐妓、地方乐妓等,进行了全景式的论述,此著对认识中国古代乐妓制度的变迁和乐妓群体的发展都很有意义。㉒修君、鉴今:《中国乐妓史》,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3年版。孙崇涛、徐宏图《戏曲优伶史》(1995)主要梳理了中国古代从事戏曲、音乐、歌舞、说唱等音乐活动的艺人,对研究中国古代官府音乐机构和民间音乐组织的乐官、乐人等,具有一定参考价值。㉓孙崇涛、徐宏图:《戏曲优伶史》,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5年版。谭帆《优伶史》(1995)第二章“优伶的组织和培养”,结合官府音乐机构和民间音乐组织,论述优伶的培养及其活动,富有生活图景。㉔谭帆:《优伶史》第二章,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5-61页。孙民纪《优伶考述》(1999)分为三十个主题,对优伶这一群体进行了细致解读,其中“教坊”“部班”“家优”“行会”等几个主题,论述了优伶在官府音乐机构和民间音乐组织的生存情景,对研究优伶音乐制度颇有裨益。㉕孙民纪:《优伶考述》,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167页。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教育》(1997)之着眼点虽在音乐教育,然而中国古代的音乐教育多依附于一定的制度和机构,故其在论述中不可避免地需对中国古代音乐制度和音乐机构进行梳理和讨论。此书是关于中国古代音乐教育的首部系统论著,既注重官学和宫廷音乐教育制度,也注重私学和民间音乐教育组织,对认识中国古代音乐制度来说,可谓又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㉖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李剑亮《唐宋词与唐宋歌妓制度》(1999)首章追溯唐前歌妓制度(先秦女乐、汉代倡乐、魏晋南北朝乐户),并详述唐宋歌妓制度,将唐宋歌妓分为官妓、家妓、私妓,重点描述其歌舞活动及在文人生活中的参与方式。㉗李剑亮:《唐宋词与唐宋歌妓制度》(修订本)第一章,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40页。该著从歌妓制度入手,探讨歌妓与唐宋词发展的关系,这是把音乐制度与文学相结合进行研究的首例。陈元锋《乐官文化与文学》(1999),将先秦乐官文化分为商前艺术文化、巫官文化和乐官文化三个阶段,通过考察乐官文化从形成、发展到解体的历程,对先秦诗乐舞和诗乐礼关系进行考察,进而探讨先秦诗歌审美功能、文化功能和演进规律。㉘陈元锋:《乐官文化与文学》导言,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以上二著是将音乐制度或乐官文化,同文学本体相结合进行研究的代表著作,它们突破了既往音乐制度研究中就制度言制度的单一视角,也启示着将音乐制度与音乐本体相结合研究的可行性。
关于乐府的设立,曾一度成为音乐制度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1976年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墓附近出土刻有小篆“乐府”字样的秦代编钟,随即引发一场关于“武帝立乐府”的大讨论;1983年又在广州象岗山南越王赵昧墓出土刻有“文帝九年乐府工造”字样的一组铜勾鑃,从而又加剧了这场讨论。这场讨论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一直持续到当下,发表论文近百篇。㉙1978-2018年间,均置此论述。为省篇幅,所涉论文均不具出处。综合这些论文来看,其观点大致可归纳为五类:第一类,认为秦时已设乐府机构,汉初因袭不改,至武帝予以扩建、扩充,寇效信《秦汉乐府考略——从秦始皇陵出土乐府编钟谈起》(1978)、赵生群《西汉乐府考略》(1988)、王洪军《作为音乐机构的西汉乐府相关问题探究》(2014)等持此说;第二类,认为秦乃至战国已有“乐府”,但它只是钟官或府库之意,武帝以前的乐府主要负责制造和监管乐器,武帝以后的乐府,一方面掌管宫廷俗乐,另一方面继续负责制造乐器,李文初《汉武帝之前乐府只能考》(1986)持此说,笔者比较赞同李说;第三类,认为乐府乃武帝始立,是一个新的音乐机构,它相对于专管祭祀宗庙乐歌的太乐而存在,专司宫廷非宗庙乐舞,倪其新《汉武帝立乐府考》(1991)持此说;第四类,认为武帝以前即已设立乐府,武帝立乐府乃重建乐府、扩充职能,或应在更加广阔的意义上理解“立乐府”,王运熙《关于汉武帝立乐府》(1998)、赵敏利《重论汉武帝“立乐府”的文学史意义》(2001)、孙尚勇《乐府建置考》(2002)、裴永亮《肩水金关汉简中的汉文帝乐府诏书》(2018)等持此说;第五类,认为武帝立乐府不仅是机构扩建,乐府的性质、地位、职能等均发生显著变化,陈四海《从秦乐府钟秦封泥的出土谈秦始皇建立乐府的思想》(2004)、王福利《汉武帝“始立乐府”的真正含义及其礼乐问题》(2006)等持此说。关于乐府设置的讨论,直接促进了对秦汉音乐制度研究的深化,提高了秦汉音乐制度研究的整体水平。
此期有关中国古代音乐制度研究的代表性议题还有如下若干:李纯一《曾侯乙墓编钟的编次和乐悬》(1985)指出,曾侯乙编钟的一架三层八组系临时凑成,不宜作为研究宫悬的证据,复原的两层五组编钟属于正规的曲悬;曲悬是三面编悬,但其所缺并非南面,而是东面。㉚李纯一:《曾侯乙墓编钟的编次和乐悬》,《音乐研究》1985年第2期,第63-71页。郎秀华《清代昇平署沿革》(1986)对清代教坊司、和声署、南府、昇平署等宫廷音乐机构皆有简要梳理,并指出,昇平署的中和乐处主要负责宴筵、祭祀、礼仪奏乐,该处乐工悉用太监,与南府时期相同。㉛郎秀华:《清代昇平署沿革》,《故宫博物院院刊》1986年第1期,第13-18页。张正明《明代的乐户》(1991)指出,明代的乐户,包括京师教坊司供奉皇室的乐舞之人和官府管辖之官妓,其来源包括降附之人、罪犯家属、被卖妻女三部分,他们在京师统属于教坊司,在地方统于属郡县,其地位则属“贱民”,乐户除供奉皇室歌舞和陪侍缙绅行酒,还在立春日和迎神赛社日表演节目。㉜张正明:《明代的乐户》,《明史研究》第一辑,合肥:黄山书社1991年版,第208-213页。项阳《山西“乐户”考述》(1996)以山西乐户为例,论述了乐户的内部组织结构和职能、乐户的信仰崇拜和重大活动、乐户存在的经济文化地理背景、乐户的生活条件和心态、乐户对保存传统音乐文化的贡献等。㉝项阳:《山西“乐户”考述》,《音乐研究》1996年第1期,第76-88页。这是21世纪以前,对乐户制度论述最为详赡的文章。沈冬《论隋唐燕乐乐部》(1996)指出,隋唐燕乐乐部的制度酝酿于元魏以下,承袭自北齐、北周,而其一脉相承的渊源是北周“行《周礼》,建六官”的“大司乐”“四夷乐”体系,而其根源乃是在于《周礼》。㉞沈冬:《论隋唐燕乐乐部》,原以《隋唐燕乐乐部申论(一)——根源的探寻》为题,载于《台大文史哲学报》第44期,1996年6月,第89-122页;转载于《民族艺术》1997年第2期,第181-196页。李英《宋代音乐机构述论》(1992)指出,宋代因施行礼乐分司,致使音乐机构日渐多样化,文章就宋代六种官府音乐机构,即教坊、云韶院、钧容直、东西班乐、衙前乐、大晟府的沿革、编制、职能予以初步梳理和论述,概况性的勾勒出两宋官府音乐机构的基本框架。㉟李英:《宋代音乐机构述论》,《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3期,第60-64页。罗明辉《清代宫廷燕乐研究》(1994)对清代宫廷燕乐之乐部构成予以初步梳理,对认识清宫燕乐之乐部有一定意义。㊱罗明辉:《清代宫廷燕乐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第55-63页。陈应时《有关周朝乐官的两个问题》(1995)指出,大司乐仅是周朝的乐官,而非音乐机构。作者统计《周礼》地官司徒和春官司徒下乐舞人员总数为1610人。㊲陈应时:《有关周朝乐官的两个问题》,《艺术探索》1995年第1期,第12-15页。孙晓辉《先秦盲人乐官制度考》(1996)指出,盲人乐官是上古音乐的主体,盲人乐师曾活跃于郊庙朝廷和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㊳孙晓辉:《先秦盲人乐官制度考》,《黄钟》1996年第4期,第26-30页。李方元等《北魏宫廷音乐机构考》(1999)对北魏一朝音乐制度进行了首次系统论述,文章指出,北魏音乐机构乃伴随着拓跋氏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和吸收而不断演进,北魏宫廷音乐机构统管雅乐、俗乐和鼓吹乐三大部类共七种乐类。㊴李方元等:《北魏宫廷音乐机构考》,《音乐研究》1999年第2期,第40-46页。
此期学者关于中国古代音乐制度的研究主要存在如下问题:一是音乐制度的专题论著较少,此期音乐制度研究涉及宫廷音乐制度、家班制度、歌妓制度、音乐教育制度、乐府制度、乐户制度等专题,但仅有少数几部专著,其余多停留在若干论文的初步探讨上;二是对民间音乐组织的研究仍显薄弱,此期更加注重对官府音乐机构的研究,仅在讨论家班制度、歌妓制度、乐户制度、音乐教育制度时略及民间音乐组织,但有意识地对民间音乐组织进行系统而有深度研究之成果还未出现;三是音乐制度与音乐本体相结合的研究仍未得到有效开拓,此期音乐制度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有明显进展,但音乐制度与乐种发展、音乐传播、音乐体裁、音乐风格、音乐类型等相结合的研究未能及时跟进。
四、21世纪初期约20年间:音乐制度研究的繁荣期
陈戍国《中国礼制史》自1991年出版首卷“先秦卷”,至2002年全六卷出齐,实为世纪之交礼制研究的重大突破。陈著各卷多次论及乐舞制度,为系统考察礼乐制度梳理了基本脉络。㊵陈戍国:《中国礼制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陈万鼐《中国古代音乐研究》(2000)第二章“中国古代中央音乐官署制度”,对中国古代官府音乐机构的乐官职称、编阶、音乐教育、乐律制度、乐舞、乐歌、乐器、乐事等予以简要述论,可视为一篇中国古代音乐制度简史。㊶陈万鼐:《中国古代音乐研究》第二章,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0年版,第79-100页。沈冬《唐代乐舞新论》(2000)首篇“乐部考”,对“乐部”的含义、“部”与音乐脉络的关系、隋唐燕乐乐部的属性均有论列,作者同时对乐部制度的渊源予以追溯,揭示了乐部音乐的仪式属性及其与乐工团体的关系。㊷沈冬:《唐代乐舞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50页。按:沈著于2000年3月由台北里仁书局初版。沈著首次将“乐部”提高到音乐制度研究层面,足以引起学术界之重视。项阳《山西乐户研究》(2001)首章“乐户的源流”,对乐户的起源及其在隋唐至明清的发展脉络予以梳理剖析:乐户肇自北魏,历经唐代的繁荣,宋代政策的宽松,元代政策的吃紧,明代的畸变,清代由盛而衰直至解体,可视为一篇乐户制度发展简史;其余五章分论“山西乐户”“乐户的组织和文化形态”“山西乐户的文化特征”“乐户对音乐文化传统的贡献”“乐籍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该著“以制度与乐人与音乐本体相结合”的视角进行研究,相较于20世纪的音乐制度研究多脱离音乐本体的状况,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第五章对轮值轮训制有详论,并指出中国传统音乐主脉得以世代传承实赖此制,这对从宏观上认识中国传统音乐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著是对乐户制度进行全面深入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填补了我国音乐制度中关于乐户制度研究的空白,由此也开拓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即对乐户制度或乐籍制度的研究也拉开序幕。㊸项阳:《山西乐户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乔健等《乐户:田野调查与历史追踪》(2002)分十章,对乐户的历史、上党乐户的分布与迁徙、婚姻和家庭、世系与社会关系、存在形态与执行活动、神灵信仰、迎神赛社、与中国音乐和戏剧关系、上党乐户的变迁、地位与角色等进行论述。㊹乔健等:《乐户:田野调查与历史追踪》,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该著更加注重考查当下乐户群体及其后人的生存状况,对历史上的乐户制度研究略弱。刘德玲《两汉雅乐述论》(2002)第四章专列“两汉宫廷雅乐制度”一节,对西汉和东汉雅乐的乐官编制和乐器编配有详考,对认识汉代宫廷音乐制度有一定意义。㊺刘德玲:《两汉雅乐考述》第四章,台北:文津出版社2002年版,第87-111页。赵维平《中国古代音乐文化东流日本的研究》(2004)第一章专设“音乐的制度”,主要梳理日本奈良、平安时期雅乐寮和内教坊两个音乐机构的形成、发展、构成、职能,以及唐代音乐制度对日本此期音乐制度的影响,为全面认识唐代音乐制度贡献一种新的视角。㊻赵维平:《中国古代音乐文化东流日本的研究》第一章,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51-81页。张国强《宋代教坊乐制研究》(2004)对北宋教坊四部之名称、教坊四部合一的年代、教坊四十大曲的影响、教坊乐人、宫廷队舞表演的起止年代等问题分别予以探讨。张著指出,宋代教坊不仅承担着宫廷宴飨中的音乐表演,而且还承应一些庄重肃穆场合的音乐表演,宋代教坊乐的性质应该是礼俗兼备,这对重新认识宋代教坊乐的性质有重要意义。㊼张国强:《宋代教坊乐制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学位论文打印稿,2004年5月。张发颖《中国家乐戏班》(2002)主要对明清家乐戏班的来源、构成、盛衰、组织、演出等予以梳理,基本勾画出明清家乐戏班的概貌。㊽张发颖:《中国家乐戏班》,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刘水云《明清家乐研究》(2005)较为系统地对明清家乐进行了研究,其中涉及家乐史、家乐构成、演出形式、演出场所等,对明清家乐制度研究颇具开拓之功。㊾刘水云:《明清家乐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杨惠玲《戏曲班社研究:明清家班》(2006)分上下两编:上编属宏观研究,主要对明清家班的历史、结构、运作进行论述;下编为个案研究,选取二十个明清家班个案予以简述。㊿杨惠玲:《戏曲班社研究:明清家班》,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该著宏观与微观对照、议论与资料相融,对认识明清家班制度颇有裨益。王清雷《西周乐悬制度的音乐考古学研究》(2006)从用器制度、摆列制度、音列制度三个层面指出:商代末期,以可悬之钟与可悬之磐为特征的乐悬制度己成雏形;西周早期,以钟磐为代表、严格等级化的乐悬制度初步确立;西周晚期,乐悬制度臻于成熟;西周的乐悬制度应为“王宫悬,三公轩悬,诸侯、卿、大夫判悬,士特悬”。[51]王清雷:《西周乐悬制度的考古学研究》结语,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第190-193页。王氏观点,对重新认识西周乐悬制度具有重要意义。毛子水《唐代乐人考述》(2006)对有唐一代乐人进行集中考述,既包括宫廷乐人,也包括民间乐人,对系统认识唐代乐人及其音乐活动提供了线索。[52]毛子水:《唐代乐人考述》,上海: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康瑞军《宋代宫廷音乐制度研究》(2007),将宋代宫廷音乐机构和乐官制度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宋初至元丰改制”“元丰改制至绍兴”“绍兴至宋末”,对宋代宫廷音乐制度与乐官制度、乐籍制度及其在宋代宫廷音乐中的作用、和雇制度及其在宋代宫廷音乐中的作用、宋代宫廷音乐的演出体制及特征等展开论述。该著指出,宋代和雇制度的出现概有三个条件:一是音乐技艺商品化的观念普及,二是乐籍制度的宽松,三是宫廷音乐机构的缩减;和雇乐人的构成包括路歧、杂攒、市人、行院、散乐、小鬟、赶趁人等七类;南宋绍兴以降,和雇乐人逐渐取代由在籍乐工完成的大部分教坊演出任务。该著对和雇制度的研究富具创新意义,提升了学界对和雇制度的总体认识。[53]康瑞军:《宋代宫廷音乐制度研究》,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3年版。刘洋《唐代宫廷乐器组合研究》(2008)对唐代正乐、四夷乐、宫廷鼓吹乐以及宫廷其他音乐类型的乐器组合和乐队排列均有详细论述。[54]刘洋:《唐代宫廷乐器组合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学位论文打印稿,2008年3月。黎国韬《先秦至两宋乐官制度研究》(2009)分上下两篇,上篇“先秦至两宋乐官制度发展史”,下篇分别就古代乐官功能、太乐和鼓吹的沿革、乐府总章的乐官、教坊宣徽院乐官予以论述。黎著指出,中国古代乐官制度可分三个阶段:先秦、秦宋、元明清。乐官源出于巫官,商后期乐官制度形成,西汉奉常之设是乐官制度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此后乐官制度发展的关键线索,隋唐乐官制度臻于成熟,安史之乱以后,乐官制度整体呈衰势,近古礼部取代太常。黎著基本勾勒出先秦至宋乐官制度的发展脉络及其各期主要特征,为音乐制度的研究贡献一部可资参考的通史范例。[55]黎国韬:《先秦至两宋乐官制度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赵维平《中国与东亚音乐的历史研究》(2012)论及唐代宫廷音乐和音乐制度对外来音乐文化之吸收,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音乐机构及其与中国音乐文化之关系,藉此可略窥中国与东亚邻邦音乐制度建设之交互影响。[56]赵维平:《中国与东亚音乐的历史研究》,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年版。王志清《东晋南朝音乐文化研究》(2012)第四章“东晋南朝音乐制度研究”,对东晋南朝音乐机构、用乐制度、蓄伎制度、赐乐制度予以梳理。作者指出,东晋哀帝“废鼓吹”是指鼓吹并入太乐,音乐职能被太乐兼并;东晋太乐除掌管雅乐外,还兼管鼓吹、清商和其他杂乐;刘宋直取魏法,建总章署,是其音乐制度的新变。[57]王志清:《东晋南朝音乐文化研究》第四章,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6-75页。王著整体流于泛述,对东晋南朝音乐制度的研究尚缺乏深刻度和系统性。章华英《宋代古琴音乐研究》(2013)第一章专设“宋代的琴待诏制度”一节,略述宋代琴待诏的归属、官职、品阶与迁移等。[58]章华英:《宋代古琴音乐研究》第一章,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57-71页。章著对琴待诏制的论述为此书一个创新点,但所论仍显简略。黄敬刚《曾侯乙墓礼乐制度研究》(2013)第四章“从曾侯乙钟磬看其乐悬制度”,作者从曾侯乙墓中编钟和编磬的曲尺形悬挂组合,指出“三面悬挂钟才是‘曲尺形’的‘悬轩’”,从而认为曾侯乙采用的乐悬制度为轩悬,与周代礼乐制度吻合。[59]黄敬刚:《曾侯乙墓礼乐制度研究》第四章,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9-178页。任宏《两周乐悬制度与礼典用乐考》(2013)分三章分别对西周、春秋、战国礼乐制度的建成、发展、延续、变异、衰落予以论述。作者指出:就两周乐悬之乐器种类讲,成昭时仅有甬钟,穆厉时发展为甬钟、石磬二元组合,西周晚期出现甬钟、编磬、编镈或钮钟三元组合,春秋中期已见甬钟、编磬、编镈、钮钟四元组合,春秋晚期四元组合成为通例;就所用乐器之音列讲,成昭时为宫—角—宫三声结构,穆厉时统为四声结构,幽王以后已见五声结构,春秋早期则四声与五声混见,春秋中期四声与五声音列相对稳固,至春秋晚期,五声音列占主流,但六声、七声音列呈蓬勃发展趋势。[60]任宏:《两周乐悬制度与礼典用乐考》,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7年版。作者另对不同阶层的乐悬摆列及部分乐官均有考证,此著对认识两周乐悬制度有重要意义。任方冰《明清军礼与军中用乐研究》(2014)分上下两篇,其中上篇“明清军礼及其用乐研究”对明清军礼的制定、分类、内容、仪节、特点等分别给予详细论述,是对明清军礼用乐进行探讨的首部系统论著。[61]任方冰:《明清军礼与军中用乐研究》,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4年版。黎国韬《古剧续考》(2014)中编“古剧形态杂考”对勾栏和汉唐百戏管理机构均有详考。[62]黎国韬:《古剧续考》中编,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3-97页。栗建伟《周代乐仪研究》(2014)在周代历史背景下和五礼框架中,对周代礼制的建立、发展、鼎盛、崩溃及礼与乐之关系予以探讨。[63]栗建伟:《周代乐仪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打印稿,2014年5月。洛秦主编《宋代音乐研究文论集:音乐机构与制度卷》(2016),收单论11篇、硕博论文选段5篇、专著选段4篇,集中反映了宋代音乐制度研究的热点问题和目前的整体水平。[64]洛秦主编:《宋代音乐研究文论集:音乐机构与制度卷》,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6年版。
此期还有两个专题研究值得注意:一是音乐制度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二是以正史乐志乐律为切入点而涉及音乐制度的研究。就第一个专题来讲,许继起《秦汉乐府制度研究》(2002)、柏红秀《唐代宫廷音乐文艺研究》(2004)和《音乐文化与唐代诗歌研究》(2014)、黎国韬《古代乐官与古代戏剧》(2004)、吴大顺《魏晋南北朝音乐文化与歌辞研究》(2005,后更名为《魏晋南北朝乐府歌辞研究》出版)、左汉林《唐代乐府制度研究》(2005,后更名为《唐代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出版)、卫亚浩《宋代乐府制度研究》(2007)、赵敏俐《汉代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2009)、杨隽《典乐制度与周代诗学观念》(2009)、刘怀荣等《魏晋南北朝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2010)、龙建国《唐宋音乐管理与唐宋词发展研究》(2012)、付林鹏《两周乐官的文化职能与文学活动》(2013)、张丹阳《唐代教坊与文学》(2017)等著述,将音乐制度或乐官文化,与文学本体相结合地开展研究,提出许多新命题和新观点。例如,许著首章“秦代乐府考论”,以存世文献与出土文物相结合,对秦代音乐机构、职能、乐舞类型等进行较为细致的梳理和论证,弥补了此前音乐制度研究中对秦制的缺失。[65]许继起:《秦汉乐府制度研究》第一章,扬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打印稿,2002年5月,第5-39页。黎著分上下二篇,上篇“古代乐官概论”,主要梳理先秦至明清中央宫廷乐官制度的发展,下篇“乐官与中国古代戏剧”,则探讨乐官对戏剧起源、形成、发展、流变的诸种影响。黎氏指出,乐官制度至迟在商末形成,历史越靠前,乐官文化在政治、生活上所发挥的作用也越大。[66]黎国韬:《古代乐官与古代戏剧》引言,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2、3页。乐官制度是中国古代音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黎著对全面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制度与有功焉。龙著对宋代大晟府、宋代书会、宋代勾栏等官府音乐机构和民间音乐组织的音乐管理与词之关系的论述,颇值得注意。[67]龙建国:《唐宋音乐管理与唐宋词发展研究》(第二版),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龙著从“音乐管理”视角切入,讨论音乐机构或音乐组织对宋词发展的影响,这对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制度与音乐本体关系不无启发意义。就第二个专题来讲,继20世纪中叶丘琼荪《历代乐志律志校释》(1964)之后,21世纪初期,学者们又相继推出后续研究,如孙晓辉《两唐书乐志研究》(2001)、李方元《宋史乐志研究》(2001)、王福利《辽金元三史乐志研究》(2001)、温显贵《清史稿乐志研究》(2004,后更名为《〈清史稿·乐志〉研究》出版)、陈万鼐《〈清史稿·乐志〉研究》(2010)等。孙著下篇“唐代礼乐制度”,乃是“通过制度结构研究音乐结构”,如通过对太常官制因革、太常八署四院的职能、太常乐部等的考察,指出唐代音乐制度管理实质是对音乐结构的管理,唐太常寺音乐官署的管理职能代表着唐代音乐的真实结构。[68]孙晓辉:《两唐书乐志研究》,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王著第二章“辽金元三朝宫廷音乐”,对三朝宫廷音乐的内容、种类、功能和音乐机构分别予以梳理和论述;第五章“元朝宫廷音乐的文化特质”,则对元朝祭祀、朝仪、朝会、巡幸等制度及其用乐分别予以剖析。作者指出,从三朝宫廷音乐机构的设置看,辽是番汉有别,两种建制并存;金乃倾心汉化,多用唐宋形制;元则既承宋金之旧,又有创新发展。[69]王福利:《辽金元三史乐志研究》第二章,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王著揭示了辽金元宫廷音乐的总体特征,填补了元朝音乐制度研究的空白。陈著实为其《清史乐志之研究》的增订本,相较其旧著,其卷一第三章增设“清代内廷乐官制度”一节,简要梳理清代内廷音乐机构,如乐部、神乐署、和声署、中和乐署、掌仪司、銮仪卫、什傍处等的基本职能和设立时间,其“内廷”之说,显系受万依、黄海涛《清代宫廷音乐》之影响;卷六第三章增设“清代宫廷乐队组织形制与乐器名目”一节,亦对研究清代音乐制度颇有裨益。[70]陈万鼐:《〈清史稿·乐志〉研究》卷一第二章,卷六第一、三章,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5-46、283、335-346页。
此期有关中国古代音乐制度研究的代表性议题还有如下四个方面[71]为省篇幅,所涉论文均不具出处。:一是音乐机构研究,如许继起《汉代黄门乐署考》(2002)、《乐府总章考》(2013)、《魏晋南北朝清商乐署考论》(2016)、《魏晋南北朝鼓吹乐署考论》(2017),黎国韬《辽金元教坊制度源流考》(2008)、《略论唐宋教坊梨园中的几个问题》(2011)、《历代教坊制度沿革考》(2015),赵维平《内教坊、梨园在唐代音乐中扮演的角色与历史作用》(2012)、《宋教坊的形成、内容及与唐教坊的关系考》(2014),以及王海英《隋唐时代的乐舞机构》(2001)、徐蕊《略论宋代教坊》(2004)、陈四海等《梨园考》(2005)、康瑞军《论唐末仗内教坊的实质及其他》(2008)、郭威《地方官属音乐机构三题》(2012)、李西林《唐代宫廷音乐管理机构制度考述》(2012)、李薇等《明代南教坊制度考》(2017)、杨宝刚《宋初太常寺礼乐职能考》(2018)等;二是礼乐制度研究,如项阳《“合制之举”与“礼俗兼用”》(2009)、《礼乐·雅乐·鼓吹乐之辨析》(2010)、《中国礼乐制度四阶段论纲》(2010)、《周公制礼作乐与礼乐、俗乐分类》(2013)、《礼俗·礼制·礼俗——中国传统礼乐体系两个节点的意义》(2017)等,刘桂腾《清代乾隆朝宫廷礼乐探微》(2001)、张振涛《国家礼乐制度与民间仪式音乐》(2002)、王清雷《史前礼乐制度雏形探源》(2007)、徐文武等《元代朝仪制度略论》(2015)、沈学英《辽代雅乐与礼乐制度探微》(2019)等;三是部色、乐队、盏制研究,如张振涛《北乐与南乐——鼓吹乐的两个乐部》(2001)、曾美月《唐代“十部乐”功能的再度审视》(2003)、张国强《宋初教坊四部与云韶部关系考述》(2004)、王小盾等《唐代乐部》(2004)和《论中国历史上的隋代七部乐》(2009)、韩启超《宋代宫廷燕乐盏制探微》(2007)、赵宏声《论宋代九盏制宫廷燕乐表演》(2009)、蔡菲等《宋代教坊之部色制度》(2009)、柏互玖《清商三调歌诗的乐器组合》(2017)、黎国韬《清商乐部制度考》(2018)、文琳《宋代唱赚乐队组合考》(2018)等;四是其他规章制度或用乐仪式规范研究,如邵晓洁《楚乐悬钩沉》(2009)、付林鹏《周代彻乐制度考论》(2015)、张闻捷《周代葬钟制度与乐悬制度》(2017)、孙晓辉《唐代乐判论议》(2017)、熊晓辉《明清时期土家族土司音乐制度考释》(2017)、曾凡安《清代前期教坊乐籍制度改革及其戏曲史意义》(2018)等。
综观此期音乐制度研究,已形成官府音乐机构与民间音乐组织兼顾、音乐制度研究与音乐本体研究结合、各朝音乐制度基本覆盖的格局,充分体现20世纪初期约20年间音乐制度研究的繁荣景象。但若从更高层面来讲,此期中国古代音乐制度的研究还存在如下问题:从横向研究维度看,现有成果对具体的规章制度及其实际实施情况、音乐机构的运作形态及其管理模式、音乐制度同中国古代音乐发展流变的内在关系、官府音乐制度与民间音乐制度的互动关系等还缺乏系统论述;从纵向研究维度看,现有成果对各阶段音乐制度之前后呈递关系、中国古代音乐制度的发展规律和嬗变规律等重要问题还缺乏宏观和微观的双向观照。
五、音乐制度研究的展望与设想:范围、路径、方法、目标、意义
中国古代音乐制度的研究范围大体包括如下五个方面:一是相关规章制度和行会规定等制度形态,如乐籍制度、歌妓制度、和雇制度、戏班制度、乐悬制度、盏乐制度等;二是官府音乐机构和民间音乐组织的构成形态和运作形态,如乐府、清商署、总章、教坊、梨园等及其管理模式;三是乐官、乐工、歌妓、倡优、乐户等人事形态,主要是指那些与音乐制度和音乐管理具有密切关系的乐人及其相关活动;四是乐部构成、乐队组织、乐器编配等音乐形态,从这三个方面可以略窥各时代音乐的基本构成和用乐规模,侧面反映音乐管理的模式和成效;五是乐舞节目、排演场所、用乐仪范、表演程式等表演形态,通过对具体乐舞节目编演盛况的论述,可较为生动地再现每一时代音乐制度的运作形态。
中国古代音乐制度的研究路径大致包括两个步骤:一是开展资料搜集、整理、汇编,形成中国古代音乐制度研究资料库。在搜集资料时,既注重传世文本,也注重出土文物,既注重国内资料,也注重海外遗存,既注重静态文献,也注重活态文化;在整理资料时,坚持“竭泽而渔”和“去伪存真”两个观念并行,坚持“以类相从”和“以时相系”两个层面并用;在汇编资料时,坚持学术研究与传播普及兼顾,坚持原始风貌与提炼加工并重。二是对搜集到的第一手资料进行整合研究。如开展编年研究、专题研究、分类研究、断代研究、通代研究、综合研究等。整合研究与第一步骤的工作并非绝然分开,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每一步骤均各有侧重。
中国古代音乐制度研究的具体方法主要有三种:一是三重证据法,即地上文本与地下文物相结合、国内资料与海外遗存相结合、静态文献与活态文化相结合,简单地说就是地上与地下、国内与海外、死的与活的相结合。二是文献细读法,一方面是指读懂文本,回归文本、忠实文本,是一切学问之关键,也是确保结论可靠之关键;另一方面是指对文献进行条理化、系统化加工,进而归纳、推绎、提炼出学术认知和学术观点。三是比较分析法,这是一切研究方法中最可凑效之法,既可用于不同时代音乐制度之前后比较,也可用于同一时代音乐制度之横向比较,更可用于中外音乐制度之互相比较,但采用此法的前提是,两个事物之间具有可比性,也即具有关联性、同质性、对应性等特点。当然,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可能还会运用到其他多种具体研究方法,然而大多是对此三种基本方法的丰富和补充。
中国古代音乐制度研究的目标主要有六个方面:一是形成专题研究成果,即对音乐制度的某些问题点进行深入研究;二是形成分类研究成果,即对音乐制度中的某一个方面或某一类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三是形成断代研究成果,即将中国古代音乐制度史划分为若干阶段,分别对每一阶段音乐制度进行深入研究;四是形成通代研究成果,即将整个中国古代音乐制度史进行贯通研究,包括通史研究和编年史研究;五是综合研究,即采用多种研究方法,对多个层面的问题进行多角度研究,涉及到比较研究法和跨学科的视野,主要用于解决音乐制度研究中的难点、重点、重大问题;六是通过对中国古代音乐制度的研究,揭示中国古代音乐的生存语境和嬗变轨迹,进而揭示中国古代音乐的运动规律(此点既是目标,也是意义)。总的来讲,对中国古代音乐制度的研究,属于基础性的研究,其目的是知识的证实、还原和生成,以为音乐领域其他方面的研究提供可靠的支撑材料。
中国古代音乐制度的研究意义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一,对中国古代制度研究和中国古代音乐研究具有重要的补充意义和学术史意义。在普通历史学中,制度研究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但关于中国古代音乐制度的研究还相对薄弱。其二,对于从外围研究中国古代音乐本体和文学本体,都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音乐制度不仅是音乐本体依附的机制之一,也是文学本体依附的机制之一,因此,探究中国古代音乐制度,也为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和中国古代文学提供了多重视角。其三,探求中国古代音乐制度发展规律,可以从制度层面揭示中国音乐的生存语境和嬗变轨迹,进一步揭示中国古代音乐的运动规律。其四,总结和提炼中国古代音乐管理经验和管理模式,对当下艺术管理,尤其是对音乐管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