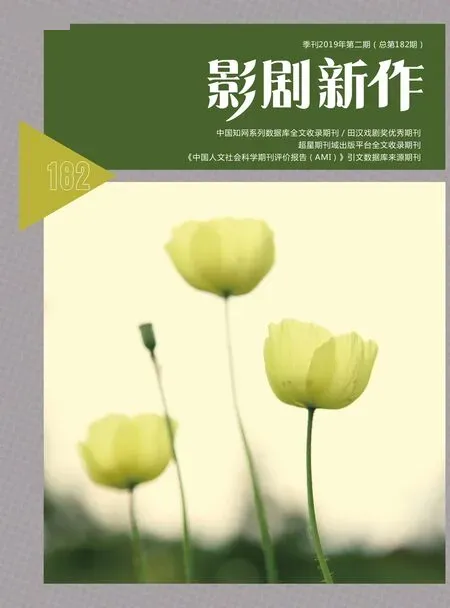曲部风流辨假真 革新儿女共得失
——黄梅戏《黄梅春秋》观后浅谈
童孟遥
黄梅戏老艺人丁永泉,艺名丁玉兰,因在家中行六,又称“丁老六”。其人嗓音圆润,演技精湛,戏路宽广,与程积善并称早期黄梅调旦行中的“南程北丁”,更被人称誉为“黄梅戏的梅兰芳”,在黄梅戏艺术界享有很高的声望。丁永泉的一生都奉献给了热爱的黄梅戏事业,对黄梅戏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其一是把黄梅戏从农村带进安庆市,成为黄梅戏从农村草台进入城市舞台的先行者;其二是将黄梅戏带到上海,进一步扩大了黄梅戏在城市舞台的影响力。在演出中他大胆探索革新,虚心吸取姊妹剧种的表演艺术,移植了一批剧目,大大提高黄梅戏的表演艺术水平,丰富了剧目内容题材,在黄梅戏发展史中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
六场黄梅戏《黄梅春秋》即以丁永泉为主角,在其真实生活的阅历基础上进行了精心的深耕移植,讲述了20世纪20、30年代丁永泉带领双喜班进安庆城、到上海演出的遭遇和变故。全剧除序幕和尾声外共六幕,从被逐、赴沪、走红、改良、遇阻,再到黯然返回安庆,故事发展的时间跨度约为十年(1926-1937),围绕黄梅调“进安庆、进上海”的故事线索一气呵成,赞颂了丁永泉对于黄梅戏发展的贡献和成就,同时也间接反映黄梅戏发展的不易和改革的艰难,体现了编剧的一种黄梅调情怀和对黄梅调宗师艺术魅力、人格魅力的景仰。
全剧剧情紧凑,环环相扣,既扣人心弦又合情合理。剧本具有人物传记特色,结构设计注重虚实相生,“戏中有戏,唱中有唱”。剧中人物鲜活生动,语言简洁明快,唱词绝大部分为三言、七言或十言,既具有诗词的格律之美,又不失安庆方言的精准丰富,给人一种真挚、真情、真实的生活感受,达到了雅俗共赏的效果。编剧通过巧合与误会、真实与虚构、补充与对比等多种手法的运用,巧妙制造作品中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人物之间的误会,充分发挥偶然性因素的作用,丰富人物性格特征,积极推进故事情节的有效发展。
一、巧合与误会的错落之美
戏曲界自古崇尚“无巧不成书”的原则,此“巧”即为巧合。王骥德《曲律杂说》中也说:“入曲三味,在‘巧’之一字。”因为戏剧的演出受到时间、空间及其他舞台演出条件等诸多因素的限制,要求剧作家必须更为集中地铺垫故事事件,更直接有效地安排人物与场面。本剧中即存在着诸多的巧合,一方面既合理推进剧情,另一方面也导致不同立场、不同个性的人物之间在特定的机遇中相互冲撞,组成了各式各样的矛盾冲突方式。比如许老小的设置,他是安庆人,在上海从事裁缝工作,正是因为他的出现,直接引出了后文中丁永泉进上海的故事情节。而且因为许老小认识一位客轮上的厨师,所以一并解决了船票的问题,也就间接引出了第二场江上行船这一载歌载舞的表演模式,展示了黄梅戏的做工。许老小的出现,不仅推动了情节向前发展,同时还刻画、凸显了人物性格特征,初步展现了丁永泉与师兄一声雷的心胸与境界的高下之分,也就为后文中二人的分道扬镳埋下伏笔。丁永泉是身怀“要为黄梅调正名”“要为黄梅调争口气”远大志向的君子,而一声雷则是安于现状、畏首畏尾、习惯给人打退堂鼓的俗夫。又如反面人物二狗子,他作为丁永泉事业发展的阻碍,前期在安庆城扰乱双喜班的正常演出,后期又冤家路窄在上海再度撺掇李太太使绊子陷害丁永泉等人披枷游街。二狗子的两地出现和死性不改,既是坚定丁永泉进城与改良黄梅调信念的反面因子,也是引起丁永泉与一声雷的角色性格之间必然性冲突的重要推手。正是因为二狗子的多次出现,加剧了丁、雷之间的分裂,尤其是那些潜藏在一声雷内心的黑暗动机,在通过一系列存在着利害冲突关系的结拜、改良等事件后,使得二者间的矛盾纠葛越发明显,直至不可挽回。再如丁翠霞的临危请命登台演出也是一个巧合,是她偷听到了丁、白在商讨改良黄梅调,也是她在一声雷出走后主动请缨演出,从此改变了“黄梅少(无)女角”的现象。
在全剧的结构布局和情节编排上,编剧除了精心串联人物、事件的巧合外,还穿插设置了一次男女主人公的误会,既揭示了人物关系,同时也进一步引发了冲突和纠葛。所谓误会,其实是由人们的错误性判断造成,故常常可以产生“以真为假,以假为真”的情节片段。当误会一旦发生,总不免要酿出事端、导引矛盾,是编制戏剧情节的一种重要手段。该剧即是如此,剧中的误会就是丁永泉、白玉霜的所谓私情。丁、白其实是性格、志趣、身世相似之人,故而相互爱护、同情乃至欣赏,“同是艺人心连着心”“同是天涯沦落人”“唱评戏唱黄梅都是一家”,所以他们惺惺相惜但无关风月,彼此之间的情感是纯粹的,并不是外人所想的暧昧不清。二人在自艾自怜对唱之时,触动彼此的伤心处,互相宽慰,在结拜为兄妹后动情相拥,却被别有心思的一声雷看到,于是误会产生,甚至被一声雷有意以讹传讹,在班社内诱发轩然大波。此误会的设计一是款款道出丁、白二人间的亦师亦友、相扶相携的情谊,二则是凸显出一声雷心胸狭隘,自私自利,也为之后他勾结李太太阻挠黄梅戏改革做了提前说明。
二、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虚实之美
丁永泉与白玉霜在同一时期都曾在上海月华楼演出,而据陆洪非《黄梅戏源流》所载,丁永泉曾经看过白玉霜演的《马寡妇开店》,并从中受到很大启发。至于二人之间是否有过相交往来以及具体详情,并无记载,后人也就无从得知。但这些历史真实细节和情节给予了编剧启发,凭借事件逻辑上的可能性,于是妙笔生花,杜撰了丁永泉与白玉霜的相交过程,通过两人的对话、交流,反映了当时戏曲环境以及人物成长经历和性格,充分肯定了戏曲改良的必要性。这种寓实于虚的戏剧创作,也就涉及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两个概念。所谓历史真实是实有层面的,注重事实上的真实性;而艺术真实是在假定性情境中表现内蕴的真实,是抽象层面的,更注重逻辑上的真实性。历史真实提供和孕育了艺术创作的可能性,而艺术真实才是历史题材的文学艺术创作的关键所在。所以,对于创作者而言,二者应当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编剧朱大平在总结历史剧创作原则时曾如是说:“历史剧改编在基于史实的基础上,在大的框架下,历史人物个人的命运、情感、性格、人物关系可以成为创作者的切入点,体现当代人对于历史的理解。”
本剧编剧理解并遵循了这一原则,巧妙地倚靠传统戏剧的戏剧结构和表现手法,在尊重历史真实(丁永泉看过白玉霜的戏,并且受到白玉霜的启发)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丰富的想象力,在假定性情境下勾勒出一个符合历史可能性与事物逻辑性的核心事件,即丁永泉与白玉霜互帮互助改良戏曲,同时又并不过分纠结于细节的真实和逻辑性,而是提供一个笼统的情节线,顺次发展。同时缀以丰富的舞台表现方式,将情节线之外的“骨肉”丰满起来。除丁、白二人的艺术虚构外,编剧还不拘泥于真实事件的时空限制,巧妙“张冠李戴”,如在上海游街事件其实是在安庆城时发生的,为了集中矛盾,移植到了上海。这样的“移花接木”并不妨碍人物的行动和情节的发展,是一种由实见虚、由虚衬实、虚实相生的艺术手法,正如编剧所言“展示民国时期戏曲艺人所遭受的屈辱,特别是‘男旦’艺人在人格上受到的侮辱。”
三、主要人物性格特质、戏剧氛围的对比之美
丁永泉与一声雷是同门师兄弟,都是学艺有成的成熟艺人,原本是同一战线上的亲密同盟关系,却最终因为两人性格特质的不同而背道而驰,选择了截然相反的人生轨迹。在遭逢相同的境遇时,丁永泉和一声雷展现了性格中的本质区别:他们一个温和,一个暴躁;一个从善如流,一个执拗蛮横;一个胸有正气,一个觍颜求荣;一个外柔内刚,一个色厉内荏。他们的人物设置不同于正反面的角色对立,一声雷不是二狗子式的地痞流氓,而是潜藏在队伍内部的蠹虫,消磨心志,缺乏骨气,更恶劣的是他从中作梗,带动不知情的盲从者走向堕落的深渊。同为女性角色,白玉霜身世凄怜却侠肝义胆,李太太出身豪门却蛮不讲理,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编剧不置一词,只把具有明显差异、矛盾和对立的双方安排在一起,进行对照比较,观众自然便能分清好坏、辨别是非,留下深刻的印象和启示。
同样,编剧还能通过同一场次的不同事件,渲染出对比强烈的戏剧氛围。第五场中,丁永泉与一声雷决裂这一场可算是一个小高潮,师兄弟二人当面锣对面鼓地交流争论,丁永泉将一声雷蛮横执拗的言辞一一驳斥,气氛渐趋紧张。俗语有云:“灯不拨不亮,理不辩不明。”虽然丁永泉始终是温言以对,但他的言语态度是毫不退让的,徐徐将心中改良之志娓娓道出,可谓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一声雷最后理屈词穷,于是恼羞成怒,将象征着戏班名誉和受欢迎度的“玻璃挂匾”砸碎,宣告二人正式决裂,道不同终不相为谋。此处丁永泉与一声雷的对峙,包含了对白、对唱、帮唱等多种表现形式,既是一种站队的表现,也是一种人心所向的暗示。而决裂之后紧接着的是另一场丁永泉与白玉霜的诉心事的对唱,丁永泉将心中苦恼、苦闷向白玉霜诉说,白玉霜作为改良的先行者,软语宽慰沮丧颓然的丁永泉,让丁永泉重新恢复并坚定黄梅调改良的信心和勇气。与上一场暴风骤雨式的反目决裂相比,后一场戏是春风化雨式的,二者形成鲜明对比,同时也是对上一场戏形成的紧张气氛加以缓和、过渡。
老子《道德经》云:“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通过人物之间、气氛之间的强烈对比,彰显提示人事物的本质,使好的显得更好,使坏的显得更坏,呈现一种强烈的审美感受。
四、舞台蒙太奇手法和常规线性叙事的补充之美
该剧的故事情节在叙述丁永泉生平事迹的时候基本是按照时间顺序发展演变,由1926年的安庆被驱逐开始,八年后带班进上海,故事的主要发生地集中在上海城(第三场至第六场的故事地点都在上海)。而在上海经历的一切喜怒哀乐,也都是采用顺叙手法,按照正常时间模式叙事,讲述事情的发展顺序,即常规线性叙事。而第五场“改良遇阻”,则打破单一的线性叙事,凭借灯光的明暗运用,将一声雷醉归、白玉霜捧场、李太太和二狗子找茬三个场景并列表现,同一时间、同一场景、不同人物的同时、连续上场,三方立场不同,目的不同,善恶不同,却被编剧统一在一个完整的舞台结构和叙事主题中,造成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危机重重的戏剧效果,这是一种典型的舞台蒙太奇手法。该手法能对情节进行集中,通过分切与组接,突出主题,吸引观众的注意,激发人们的想象,为舞台创造出独特的时空效果。两种手法相互补充,各自成趣,既避免了常规叙事的无趣,又不致于节奏过分跳跃。
所谓戏剧的显著特性之一便是以有限的舞台时间、空间的艺术形式,来表现包罗万象、纷繁复杂的现实内容,最终或是托物言志,或是借古讽今,宣扬真善美。编剧吴彬将原本松散、零碎甚至阙失的原始状态下的人物素材进行一番带有自我审美的加工提炼、剪辑升华后敷演成戏,演绎了一代黄梅戏名伶丁永泉的改良人生,突出了他自尊自爱的艺人气节和不向世俗献媚的高尚情操,真正做到了“生活戏剧化”。但本剧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硬伤,包括行文的上下衔接不顺、故事布局的节奏失衡、主要人物的性格不突出等问题。
第一、许多前情、背景知识交代不清,导致主要人物的经历、性格特征不够突出。剧中无论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的经历和背景都叙述模糊,弱化了矛盾的可看性。比如,看前面的几场戏时都以为一声雷不过是一个普通演员而已,直到第五六场时才恍然知道他其实算得上是戏班的台柱子之一,少了他,戏甚至就没法正常开演,而这些细节和情况在此之前读者未能知晓。尤其是主人公丁永泉的人物背景,包括丁永泉的高超技艺、为人的铮铮傲骨与高远志向的描写都不够。第一场中许老小张口即说:“就凭你丁老板的艺术,在上海演出,准定叫座,称得上‘黄梅戏的梅兰芳’”,此处即缺少对丁永泉高超技艺的前情说明,因而显得出言突兀,以至于第二场、第三场中连续出现的“黄梅戏的梅兰芳”都透着几分生硬和尴尬。因为根据前文的描述和塑造,丁永泉似乎只是一介极普通的艺班老板,虽然实际上在黄梅戏圈子而言,丁永泉无疑是鼎鼎有名的名角。但对于不熟悉黄梅戏的观众而言,则不能从剧的前半部分得此感受。其实解决之法也很简单,这些都可在序幕中有所铺垫:借观众的反映表现其技巧高,借与二狗子对峙表现其性格中的不服软。但现在的序幕中“被逐”一节没能表现和突出这些,仅能表明丁永泉的身份——戏班老板,而这就与后文的许老小的称颂、丁永泉立誓“黄梅要进城”“我就是要为黄梅调争口气”的志向等信息不对称、不匹配,显得突兀、无来由。相比一声雷的矛盾性格,丁永泉的性格特征、人物特性比较温吞,不够突出。不妨在思想性上再下功夫,把丁永泉的形象挖掘更深一些。
第二、行文时有跳脱,前后衔接不畅,缺少足够的铺垫。戏剧讲究前铺后垫,才能自圆其说。本剧的人物转变缺少前期的预埋伏笔。比如一声雷的转变从何而来?序幕中的他性急刚硬,后文中的他却摇身一变为软弱、卑怯的性格。其实一声雷是个很有看点的角色设置,人物性格很矛盾,既保守又激进,保守体现在不肯改良黄梅调,激进则是体现在进上海后他抛弃艺德,积极投靠大上海上流社会,集蛮横与软弱、媚俗于一体。如果编剧能够将这之间的转变衔接地更顺畅些,人物才立得住脚,也更有说服力。又如,第五场末白玉霜的一句唱词“从此黄梅多女角”,显得无缘无故、莫名其妙。这句话的过渡很突兀,令人费解。丁永泉此时并未想到一声雷走后如何解决无人演出《秦雪梅》的难题,而白玉霜却贸贸然唱出一句“从此黄梅多女角”,若丁永泉受此言启发,大胆改用女角上台倒也罢,可算得上是引出下文的钥匙,但第六场偏偏开篇就是丁永泉愁眉不展,陷入缺少演员开不了戏的困境,而且在女儿丁翠霞主动请缨上台的时候还百般纠结,那就说明白玉霜的这句话在此时此刻没起到任何作用,反而类似有剧透之感,实属鸡肋。
第三、题旨不突出,结尾匆忙潦草,有虎头蛇尾之嫌。编剧在后记中自述,剧本旨在突出改良这一中心事件,但全剧穿插了与白玉霜的相交、与一声雷的决裂、李太太与二狗子的从中作梗等事件,当然这些事件也是为核心事件服务的,但是正因为此,反而改良一事给人一种雷声大雨点小之感,没能将丁永泉改革黄梅调的具体做法或说是成就凸显出来,稍显遗憾。丁永泉的人生履历丰富坎坷,不妨更多撷取一些能够表现人物个性和能力的核心事件,敷演成戏,如初进安庆时被捕在法庭上自辩等事件,既有戏剧冲突,又能为其不甘自轻、誓将黄梅带进城的志气的形成和由来做了铺垫,显露人物气质。
其他还有人物称谓的疑惑,为什么丁翠霞一直管父亲叫伯伯?是方言还是另有内情,不得而知;部分唱词为求押韵而导致语义不通,如“怎能够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旁”等。
《黄梅春秋》从历史出发,又不拘于已有的历史真实,大胆想象,架构了一个虚实参半的艺术故事,以黄梅戏讲述“黄梅人”的故事,在方寸舞台之上尽情演绎梨园轶事。全剧集中在丁永泉“进上海,改黄梅”的故事线索,一气呵成却又一波三折、高潮迭起、动人心弦,更难得的是加入了更多历史反思、人性内涵与现代意义,尤其丁永泉在黄梅调改革过程中,不断学习吸收评剧、京剧、昆曲中的精髓这一行为,更是现代戏剧发展所需的难能可贵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