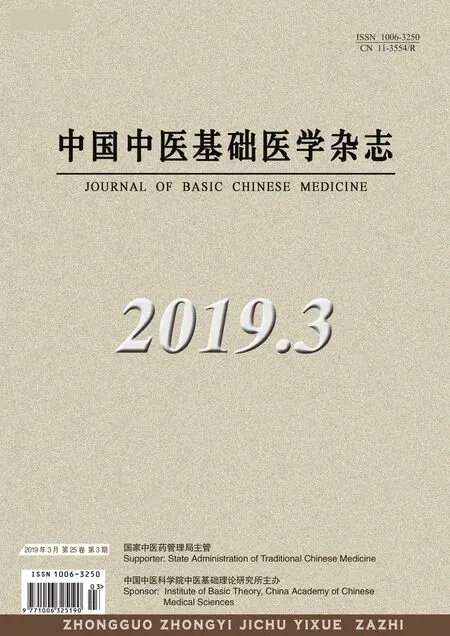关于针刺最佳刺激量的几个关键因素❋
鲁 海,张春红
(1.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武连仲全国名中医传承工作室,天津 300193;2. 天津中医药大学,天津 300193)
针刺是在人体体表特定部位进行的一种物理刺激,以达到防病治病的目的,因此物理刺激的“量”与“疗效”之间存在一定的数量关系。早在相当于古代世界观方法论的《易经》中已有记载:“以类族辨物”:一曰取象,二为运数,而在中医学中不仅有“象”的描述,也不乏对“数”的研究,可见易学之象数理论已孕育了量化的思维方式[1]。后自20世纪70年代初,石学敏院士提出“针刺手法量学”理论,并创立“醒脑开窍”针刺法治疗中风病以来,随着中医针灸的发展,针刺的量学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尤其是影响针刺疗效的重要因素针刺量,即针刺最佳刺激量。所谓“量学”简言之就是临床针刺,根据病情确定相应的手法及足够的刺激量,以获取对疾病治疗和转归的最佳疗效。临床针刺过程中,影响针刺刺激量的因素较多,本文就几个关键因素加以阐释。
1 治神是前提
《灵枢·九针十二原》:“粗守形,上守神”;《素问·宝命全形论篇》:“凡刺之真,必先治神”,治神一直是医者高度重视的针刺要领,临床获效的前提,针刺过程实质是刺激与反应的过程[2]。针刺最佳刺激量的产生取决于患者对医者一定强度的针刺刺激作出的“良性预应激”[3],因此针刺疗效必须由医患双方的共同治神来实现。正如张景岳所言:“医必以神,乃见其形,病必以神,气血乃行,故针以治神为首务。[4]”所以,治神包含医者治神和患者治神两个方面。
医者治神,针刺前,《灵枢·本神》所言:“是故用针者,察观病人之态,以知精、神、魂、魄之存亡得失之意”;针刺时,《素问·宝命全形论篇》:“如临深渊,手如握虎,神无营于众物……众脉不见,众凶弗闻,外内相得,无以形先,可玩往来,乃施于人。”医者治神以沉,沉以接物以察百态;医者治神以稳,稳以持物以游刃有余。患者治神,《灵枢·邪客》:“持针之道,欲端以正,安以静。”《标幽赋》:“凡刺者,使本神朝而后入,既刺之,使本神定而气随。神不朝而勿刺,神已定而可施。[5]”患者治神以静,静以调气以利速效。
在针刺过程中,医患双方的治神条件需要彼此提供,医生虽然处于主导地位,但需要患者安静以待;患者如果想做到气定神闲就必须通过医生的正确诱导,故两者治神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
2 针具是媒介
毫针是针刺过程的直接媒介,其长短粗细与针刺最佳刺激量直接相关[6],关乎针刺手法的实现、针感的体现及留针时间的长短,故治疗不同疾病应选择相应规格的毫针。《灵枢·官针》:“九针之宜,各有所为,长短大小,各有所施也。不得其用,病弗能移”,及“病小针大,气泻太甚,疾必为害;病大针小,气不泄泻,亦复为败”,强调针具不同用处各异,疗效亦各异。但长期以来,研究者们对毫针制作、使用的独立性研究较缺乏,也未形成统一的规范。
对留针时间的影响,《灵枢·经水》曰:“足阳明刺深六分,留十呼。足太阳深五分,留七呼”,按常人呼吸16~20次/min,则十呼不足1 min;又如《针灸甲乙经》记载留针十呼以上仅 15个腧穴,最长也就二十呼约1 min。《内经》中留针时间一般较短,这可能与古代针具较粗大相关;后世留针时间普遍较长,现代针具做得细小,针感相对较弱,需要延长留针时间。临床目前多用25×40 mm毫针,普遍留针20~30 min,但对不同疾病也有差异。
总体来说,针具粗大者其刺激量为重,得气感强烈,留针时间较短;细小者,其刺激量为轻,得气感轻微,留针时间较长;间于两者之间,其刺激量、得气感、留针时间为中。
3 经穴是基础
3.1 经穴特异性
《灵枢·九针十二原》:“五脏有疾也,应出十二原。而原各有所出,明知其原,睹其应,而知五脏之害矣。”《灵枢·寿夭刚柔》:“病在阳之阴者,刺阴之经。”《针灸聚英》:“中风肘缩治内关”[7],针刺治病,刺经刺穴。针刺平阴阳、调虚实、和五脏之效应有赖于针刺作用于经络穴位所产生的经穴效应,这种效应的产生是针刺作用于特定经络、特定腧穴所产生的特定效应[8]。每个经穴由于其所处位置不同、所属经脉不同、所属脏腑不同而具有不同刺激效应,不同经穴也可能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效应,称之为经穴的“特异性”。经穴特异性是针灸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针刺量学核心-最佳刺激量研究的切入点,又是临床合理选穴组方以提高疗效的关键。
3.2 腧穴数量
合理的取穴也是针刺取效的基础。古人选穴多精简,《灵枢·厥病》:“肾心痛也,先取京骨、昆仑……胃心痛也,取之大都、太白”,但对选穴多寡与针刺最佳刺激量及针刺疗效的关系研究却十分鲜见。承淡安提出[9]取穴如用药,贵精不贵多。取穴过多,不仅会让患者因心生畏惧而畏针或拒针,且易增加病人的疲劳感而削弱刺激量,影响针刺疗效。此外,经穴因分部、局部解剖特点、敏感度及特效性的不同,实施刺激量也应不同。
石学敏院士认为针刺疗效有一定的局限性, 根据不同的病症,认真针刺每一个腧穴,实施不同的刺激量,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针刺-经穴效应。并提出了最具有代表性的“醒脑开窍”针刺法治疗中风的固定组方,其取穴精良,以阴经穴和督脉穴为主,主配穴相辅相成,并根据不同的合并症、并发症设立了相应的配穴[10],配伍科学合理;根据腧穴所在部位、经络循行、神经分布、穴位主治,提出了针刺穴位时患者体位、医生体位、手法、针刺方向和具体刺激量的量学要求[11],使临床操作更加规范化和科学化。
4 针刺手法是核心
针刺手法是影响针刺疗效的重要因素,体现针刺治疗中的量效关系,适量、适当的针刺手法是达到针刺“量学”关键最佳刺激量的核心,而在临床针刺过程中,运用比较多的提插、捻转手法是针刺手法的研究焦点。《黄帝内经》等古医籍对此也有诸多方面的论述。如《素问·刺要论篇》云:“病有浮沉,刺有浅深,各至其理,无过其道。”《灵枢·终始》云:“春气在毛,夏气在皮肤,秋气在分肉,冬气在筋骨。刺此病者,各以其时为齐”及“久病者,邪气入深,刺此病者,深内而久留之”。《针灸大成》第三卷“策”中专列“针有深浅策”,强调针刺提插之深浅,其量化在病位之浮沉、在四季分时、在病程之长短、在病性之寒热虚实。《灵枢·小针解》:“‘徐而疾则实’者,言徐内而疾出也。‘疾而徐则虚’者,言疾内而徐出也。”《医学入门·杂病穴法》:“凡提插,急提慢按如冰冷,泻也,慢提紧按火烧身,补也”[12],强调针刺提插之补泻,其量化在进出针之快慢、在提插之速度变化;《灵枢·官能》“切而转之”为泻,“微旋而徐推之”为补。《针灸大成》:“补针左转大指努出,泻针右转大指收入”[13],强调针刺捻转之补泻,其量化在速率之疾缓、在方向之左右(大指向前为左,大指向后为右),以上为后世提插、捻转补泻手法的概念及操作奠定了基础,对提插、捻转补泻手法虽然已有“量”化的标准,但仍然是定性的,仍是一种理念,并未形成明确的量学定义,且未对某一具体病种作出量学规定。
石学敏院士首次针对中风病对针刺手法给出了量学界定,创造性地提出了“针刺手法量学”概念和捻转补泻手法的四大要素,即作用力方向、作用力大小、施术时间、2次针刺间隔时间,使针刺补泻由定性上升至定量的水平[14]。即作用力的方向,向心者为补,离心者为泻;作用力的大小,小幅度、高频率,其限度为 1/2转,频率为120次/min以上为补,大幅度、低频率,其限度为1转以上、频率在50~60次/min为泻;持续时间的最佳参数为单穴操作1~3 min。提插手法以患肢抽到3次为度,使针刺补泻更具有规范性、可重复性和可操作性。
5 得气是标志
得气是衡量针刺刺激量的信度标志[1]。《灵枢·九针十二原》:“刺之要,气至而有效”,强调针刺得气是起效的关键。《金针赋》曰:“气速效速,气迟效迟”,得气的快慢反映针刺起效的快慢;针刺得气感有术者和患者的不同,术者的得气感,《标幽赋》曰:“轻滑慢而未来,沉涩紧而已至……气之至也,如鱼吞钩饵之浮沉;气未至也,如闲处幽堂之深邃”[5];患者的得气感,如酸、麻、重、胀、电、冷热、蚁行等感觉及循经红线现象[15]。得气虽是一种主观感受, 但却客观地反映了针刺的刺激“量”,是量变引起质变的前提。“刺之而气不至,无问其数”,表明针刺未得气未达到一定刺激量,仍需继续行针以催气或留针以候气;“刺之而气至,乃去之,勿复针”,表明针刺已得气,已达刺激量,产生了针刺疗效,就可以停针或出针了。古人强调“气调而止”,但针刺得气后则未必达到针刺治病所需的最佳刺激量,所以古人所说的“气至”或“得气”可看作每次针刺达到最佳刺激量的阈值点。
针刺最佳刺激量的获得仍需得气后结合施术时间、留针时间等参数,且石院士强调针刺时应双手配合,刺手进针施手法,押手持握患者肢体体会针感,若针刺后患者得气感柔和、轻微,其刺激量为轻;得气感强烈,有些难以忍受,其刺激量为重;间于两者之间,其刺激量为中,避免患者因惧针或耐受力差而出现叫喊“假得气”,以求更加客观地控制患者得气量的大小。
6 留针时间和2次针刺间隔时间是补充
针刺效应也是蓄积效应,类似于药物在体内达到一定的血药浓度方能显效,当针刺“剂量”积累至一定的量值才能起效,故需要留针及重复针刺以维持针刺有效刺激量,巩固疗效。
留针时间是研究针刺“时-效”关系的重要参数。《灵枢·经水》:“足阳明刺深六分,留十呼……手之阴阳,其受气之道近,其气之来疾,其刺深者,皆无过二分,其留皆无过一呼。”古人把留针时间的量化标准定为呼吸次数(息数),以衡量针刺刺激量的大小。《灵枢经·五十营》“呼吸定息,气行六寸……二百七十息,气行十六丈二尺,气行交通于中,一周于身,下水二刻。”一刻相当于14 min 24 s,则经气循环1周的时间为28 min 48 s,是现行临床普遍留针20~30 min的依据。
《灵枢·终始》:“久病者,邪气入深,刺此病者,深内而久留之,间日而复刺之。”《灵枢·逆顺肥瘦》:“婴儿者,其肉脆,血少气弱,刺此者,以毫针,浅刺而疾发针,日再可也。”“间日”“日再”是古人对针刺间隔时间的量述,可见间隔时间长短受诸多因素影响,也未有统一的定论。目前研究认为,针刺治疗以日针2次较1次为佳[16];石学敏院士针刺治疗中风病给出2次施术间隔时间的最佳参数为 3~6 h。
7 因人制宜是原则
《灵枢·逆顺肥瘦》:“刺壮士真骨,坚肉缓节监监然。此人重则气涩血浊,刺此者,深而留之,多益其数。”《灵枢》对刺肥人、瘦人、王公、布衣有不同针刺刺激量的论述。因体质差异且不同的个体对针刺敏感性有很大的离散度,故针刺最佳刺激量也应个体化。正如上文所说,可通过把握患者的得气感来掌握刺激量的大小,以避免“过犹不及”。
综上所述,古人对针刺量学探讨已有一定的参考标准,然不够明确,对针刺最佳刺激量探究就更少,但为今后针刺量化研究提供了宝贵指示。针刺“量学”研究主要集中在针刺“量-效”关系和针刺“时-效”关系的研究,针刺“量-效”关系重点在针刺手法量学的研究,包括作用力的方向、大小及施术时间等;针刺“时-效”关系重点在留针时间和针刺频次,两者都是针刺最佳刺激量的研究。同时结合针刺-经穴效应,针具的合理选择、治神与得气的把握及因人而异的治则,俱为实现针刺最佳刺激量的关键参数。没有“量”就没有“效”,即针刺最佳刺激量是临床取效的关键。针刺量学研究使得针刺操作更加量化、规范化、标准化,这种标准绝不是一概而论,而是针刺“剂量”的因人而异、因病而异。故临床如何根据患者的具体年龄段、病情来确定相应的最佳刺激量,是今后乃至更长时期的一项系统研究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