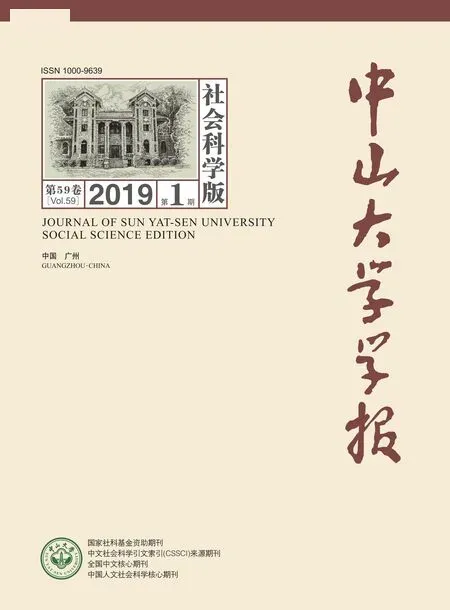责任伦理与儒家工夫论:船山《读四书大全说》另解*
姚育松
根据最近的梳理,近六十年来对于船山思想的评价,可大致分成两种范式:一是由侯外庐确立的马克思主义船山学,认为船山的“气论”是唯物主义的先行倡导;另一是由熊十力开创的新儒家船山学,认为气论仍是实在论的,并经由唐君毅的阐释,肯定了船山兼重超越的天道性命与历史的实践经验①参见陈焱:《晚清以来百年王船山哲学与思想研究述评》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四十年船山思想与哲学研究述评》,周发源、刘晓敏、王泽应主编:《船山学刊百年文选》船山卷(哲学),长沙:岳麓书社,2015年,第436—448、449—460页;方红姣:《现代新儒学与船山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79—191页。。
必须注意的是,这两种范式并非完全相互排斥。首先,他们都是援引西方的概念来“反向格义”中国的思想。其次,正如林安梧所指出的,新儒学由于过于注重对哲学义理的研究,以致于将研究限定在对抽象形式的讨论。因此,他建议往后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应要借鉴船山思想,尤其是历史哲学的部分,关注对“实践性”和“物质性”的把握②参见林安梧:《儒学革命:从“新儒学”到“后新儒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77—106页;林安梧讲述,山东大学尼山学堂采访整理:《林安梧访谈录──后新儒家的焦思与苦索》,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27—137页。。
无独有偶,林安梧对港台新儒学的内部检讨,与近年来蓬勃兴起的大陆新儒学,两者旨趣大有相通之处。即欲从对抽象义理的关注,转至对现实制度的关注,乃至于具有“回到康有为”的旨趣③参见唐文明:《回到康有为与陆台新儒家之争》,《中华读书报》2015年5月20日,第15版。。也就是针对此旨趣,本文要问的是,船山的思想对于现代的政治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借鉴。
其实,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船山学还是新儒家船山学,大部分的研究多关注抽象义理的分析,尤其是理气关系,或说道器关系,至于对船山的历史哲学,也多是为肯定其在哲学史上的价值,而非以其思想来与实际问题关联起来进行探讨。这当中的原因自是不言自明。因为尽管船山多有史论政论,但毕竟这些论述全是针对传统之政治人事以及典章制度,在与现代社会科学所累积的知识相较之下,其与现代的政治环境有多少相通或可借鉴处,恐怕是不尽乐观的。
那么,这是否意谓着,船山思想在当前,总括来说是只能提供哲学义理上的指导,而陋于提供现实政治上的指导呢?对此,港台新儒学的内圣外王观正可以指明一个方向,意即把外王限定在当事者(agent)的道德活动,而不用非要以客观制度再现出来①此即“政道”与“治道”的分别,参见牟宗三:《政道与治道》,《牟宗三先生全集》第10卷,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3年,第49—68页。。由此,要指出的是,尽管船山思想在现代对于当前政治制度的指导意义或许不大,但是对于指导当事者如何进行政治活动却大有裨益。而关键就在于,船山论修身工夫,特有“责任伦理”之面向。
所谓“责任伦理”(et hics of responsibility),乃由韦伯(Max Weber)提出,来与“意图伦理”(et hics of intention)相对待,以指出政治人物所需有的品格②“责任伦理”与“意图伦理”取自于林毓生的翻译及介绍,但在其之后,对于“意图伦理”却有其他翻译。例如钱永祥译成“心志伦理”,李明辉译成“存心伦理学”。其实,不只汉语之翻译莫衷一是,即便英文翻译亦然,除ethics of intention之外,还有ethics of conviction和ethics of ulti mate ends。据笔者观察,可能是因为蒋庆特别针对林毓生的介绍,指出其所谓的政治儒学乃具有责任伦理之面向,因此“意图伦理”这一翻译在大陆最为通行。考虑到此缘故,本文于是沿用林毓生的翻译。参见林毓生:《两种关于如何构成政治秩序的观念──兼论容忍与自由》,《政治秩序与多元社会──社会思想论丛》,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9年,第3—48页;李明辉:《存心伦理学、责任伦理学与儒家思想》,《儒家视野下的政治思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6—87页;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127—152页;[德]马克斯·韦伯著,钱永祥等译:《学术与政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93—275页;John Dreij manis ed.,Gordon C.Wells trans.,Max Weber’s Complete Writings on Academic and Political Vocations,United States:Algora Publishing,2008,pp.155-208.。简单而言,责任伦理是指当事者必须认识到其行动有相应之后果,并对此后果负责,以此引申的观念,即是承认客观世界有其制约及影响当事者行动的条件,而当事者在伦理上有义务去认识这些条件,否则便不足以对其行动的后果负责;而意图伦理是指当事者必须坚守其信念并坚定地将其信念客观地实现出来,而以此引申的观念,即是当事者在伦理上不能以客观世界的制约条件来作为其不去实现信念的理由,否则便表示当事者是在逃避其义务。
船山气论的精到处,即在于认定“理”是“气”之流行的显现。因此,船山论修身工夫,就不与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一般,预设道德境界的升华,可使当事者“自然而然”地去实践道德,换句话说,即表示认为当事者对客观时势的理解,是其道德实践的必要条件,而非仅仅是充分条件③本文之论述,取自于唐君毅与曾昭旭的研究。唐君毅有言,“王船山之学之言理言心,固多不及朱子阳明之精微。盖犹外观之功多,而内观之功少”。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413页;曾昭旭有言,程朱与陆王皆是“由末探本”,而船山是“由本贯末”,故船山言“格物即非只是立本工夫之入路或助缘,而自有其独立之范畴矣”。曾昭旭:《王船山哲学》,台北:远景事业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第471页。。
据以上两点,可以认为船山的工夫论其实就是“责任伦理的”。而由于责任伦理是韦伯特别就现代政治发展而提出的政治伦理,故船山的工夫论,在现代仍具有可“接着讲”的重要意义。
必须注意的是,有别于“照着讲”,“接着讲”④“接着讲”与“照着讲”乃取自于冯友兰言其研究宋明理学,参见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4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页。的工作是要在阐明经典的义理之后,再接着诠释出对于当下语境及生活方式仍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或论述⑤本文对“接着讲”的看法,取自于陈少明教授对中国哲学研究方法提出的观察及反思,参见陈少明:《中国哲学史研究与中国哲学创作》,氏著《做中国哲学:一些方法论的思考》,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第68—119页。。本文的研究是为接着讲,那自是要在格义之后,还要就某种共通的生活经验来诠释船山的工夫论。在格义方面,便以着重论修身工夫的《读四书大全说》为文本来分析,并指出在何种意义上船山之工夫论是“责任伦理的”。而在诠释方面,则取材自《读通鉴论》和《宋论》中船山对光武帝与王安石之评议①《读四书大全》及《尚书引义》乃船山壮年47岁修订完成,《宋论》和《读通鉴论》则为晚年69岁所作,时间相隔22年。本文认同曾昭旭的看法,即船山思想的要旨,以37岁所作《周易外传》为根本见地,往后但有补充展开,而无根本歧异,因此将三书相互对照同论,应是可成立的。参见曾昭旭:《王船山哲学》,台北:远景事业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第22—37页。而陈来亦认为,船山之思想不管是就其前期对《四书》之发明,还是就其后期对《张子正蒙》的注解,其实都是“参伍于濂洛关闽”,而“归本于横渠濂溪”,参见陈来:《诠释与重建──王船山的哲学精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页。。
必须澄清的是,本文并不是以“责任伦理”来反向格义船山的思想,而是为提出另一种发问问题的方式来检视船山思想。此即表现在,责任伦理在儒家思想中,乃兼顾道德动机的“存心”及道德实践的“结果”,但我们知道,结果之好坏毕竟非人力可以完全决定,如此,则在何种意义上,道德上的修身工夫,可以在存心的纯良之外,来对结果负责呢?而本文对船山思想的再诠释,便是试图回答此问题。
按以上所述,下文乃分三节以说明。
一、责任伦理与意图伦理之区别
首先需指出的是,责任伦理与意图伦理并非相互排斥。尽管儒家传统是以意图伦理为根本,但在船山思想中,却是可兼容责任伦理的。在厘清这一概念前,需先回顾责任伦理的提出背景,以明确责任伦理是现代政治不可或缺的政治伦理。
1919年,韦伯应邀到慕尼黑大学演讲,对象是未来有很大机会成为政治菁英的大学生,题目即为《政治作为一种志业》(PoliticsAsAVocation)②本文所据的英译文本收录于John Dreij manis ed.,Gordon C.Wells trans.,Max Weber’s Complete Writings on Academic and Political Vocations,pp.155-208.。本来主办方邀请韦伯作演讲的目的,是请韦伯就当时脆弱且混乱的威玛政府提出一番评议,但韦伯却狡慧地避而不谈,而先是长篇大论地议论起现代政治之发展,然后才在结尾处,勉励学生若要从事政治,便需有责任伦理的意识来担当③有关《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演讲背景,本文取识自由钱永祥、顾忠华中译,Wolfgang Schluchter以德文作的《价值中立与责任伦理──韦伯论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收录于[德]马克斯·韦伯著,钱永祥等译:《学术与政治》,第101—152页。。
众所周知,韦伯是解剖分析“现代性”的大师。他所得出的最重要结论,即是指出所谓现代性是一种除魅并理性化的过程。他在演讲中便是沿循此结论,论述了现代政治专业化分工的发展。韦伯从欧洲官僚政治的出现谈起,指出现代国家的形成惯例,即是需有主君(princes)能针对各种坐拥私人武力或掌握地方行政司法之豪强或贵族,将他们的权力和资源收拢于己,而其发展结果,即是国家垄断了所有的政治资源和权力。而紧接着所需有的发展,便是有“专门的政治从业员”(pr of essional politicians)的出现来供主君御使。韦伯特别指出,这些从业员固是以政治作为志业,但其中有个分别即在于,是“为政治而生”(lives f or politics)还是“以政治维生”(lives fr o m politics)。此两者自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可彼此兼容。但就历史的发展而言,政治从业员越益增多,越加专门,则后者所揭示的经济因素才是现代政治发展的主要动力。而因此所带来的两个结果,即是官僚政治和政党政治的出现。
对于成为官僚的政治从业员来说,其收入来自于政府的支付;对于参与政党的政治从业员来说,则需要求政党能安排工作或支付薪酬。如此,政党的机能和权力势必发展,而最终结果,便是政党控制国会,主君退出政府运作,内阁政治于焉出现。韦伯接着指出,政党政治的出现,意谓着政治也需犹如资本主义之运作般追求利润,否则无以获得民众和社会有力人士的支持,来与其他政党竞争,来赢得选举掌控政府。
韦伯指出,以政治为志业,就需同时具有热忱的抱负以及冷酷的算计。韦伯最后断言,以政治而言,只有两宗大罪,即缺乏客观认识(lack of objectivity)和不负责任(irresponsibility)。前者让人只求舆论上光鲜亮丽而非实质上能大有作为的权力,后者让人只享受权力而无视权力之大有作为的目的。这是为何韦伯勉励学生若投入政治便需有责任伦理,并同时警诫学生勿只信奉意图伦理的原因所在。
下文以李明辉的澄清,来说明意图伦理其实是可涵摄责任伦理的,而也就是在这层意义上,儒学的工夫论才能表现责任伦理这一面向。
李明辉指出,与意图伦理相反的伦理观,应是“功效伦理学”,而非责任伦理①李明辉自己采用的翻译是“责任伦理学”和“存心伦理学”,见李明辉:《存心伦理学、责任伦理学与儒家思想》,《儒家视野下的政治思想》,第66页。本文为行文方便,故不以此为词。。李明辉以康德之伦理学来定义意图伦理,即指“一个行为之道德意义只能凭其所依据的原则(即存心),而不能凭其后果去判定”②李明辉:《存心伦理学、责任伦理学与儒家思想》,《儒家视野下的政治思想》,第79,80页。。反之,与之逻辑上不能兼容的功效伦理学,即指一个行为之道德意义只能凭其结果,而不能凭其存心去判定。确立此分野,李明辉接着指出,意图伦理之根本原则即是当事者的自我立法,也就是道德的自律,而有此自律,并不意谓此自律原则是不必考虑结果的。对此,李明辉便以康德之语来提出三点以佐证。首先,“没有意志能完全不具目的”,这就意谓着道德的自我立法必定是有指向达成某种结果。其次,道德之普遍性的原则,包含促进自己与他人幸福的义务。最后,促进幸福的义务是道德意志的“一个先天必然的对象”③李明辉:《存心伦理学、责任伦理学与儒家思想》,《儒家视野下的政治思想》,第79,80页。。
李明辉于是判定,意图伦理在逻辑上是可以兼容责任伦理的,因为即便一个行为之道德意义是以存心之纯良作为唯一判准,但这无碍于当事者以其自我立法的意志,要求自己对其行为之结果负责。而他便以论语中孔子盛赞管仲“如其仁”为例,指出儒学的伦理观是可以同时兼容意图伦理和责任伦理的。
要特别指出的是,按儒学之传统,当事者之修身,其外王必定是以内圣为前提,也就必定是意图伦理,而非功效伦理。而船山的独特贡献在于,其在意图伦理之外,又特别强调责任伦理。此中关键就在于,船山论修身的根本意向,并非收摄到主观的道德境界,而是投射至具体的事功。
二、船山论修身工夫的根本意向
众所周知,中国思想之表达方式,并非如西方哲学般以层层论证为形式,而是以偶作议论的判语为形式。换言之,中国思想在文本的表达是散见的,而非体系的。即如船山的《读四书大全说》,便是以读书笔记的形式来随笔随想地表达其思想,当中论及修身工夫的,既是芜杂,又是旁涉,以一篇万字的文章来叙述,断难统理整备。
也就因此,本节并非对船山论工夫作一统括的梳理,而是将主题限定在船山论工夫的根本意向,并要特别指出船山的工夫论,并非如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一般是收摄到主观的道德境界,而是投射至具体的事功对象。对此以两点为论证:(一)船山反对将格物与致知打成一片;(二)船山反对将气质与性理二分。
(一)船山反对将格物与致知打成一片
格物与致知,出自于《大学》:“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④[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4页。
船山明言反对阳明心学的“知行合一”,故此他认为致知与格物,乃两截根本不同的工夫,而非一体之两面。
所谓“格物”是指道德实践,所谓“致知”是指求诸本心来认识道德价值。按阳明的知行合一论,作为道德价值的性,尽管是实存的,却是内在于己的道德能力。换言之,性即理,心也即理,心也即性。如此引申的工夫论,即是把未发的良知和已发的道德实践完全打通,于是动静合一而根本在可涵摄一切的“致良知”这一工夫上。
承此要旨,阳明对格物和致知不作工夫上的分别。因为对阳明来说,道德价值是完全根存于自己的本心,并且是人人皆同,故此,人人都可求诸本心而认识道德价值,而本心经此认识便可去人欲而存天理,于是便会自然而然地去做道德上的实践,然后又在实践中求诸自己道德的本心,以此类推不断循环。总归来说,阳明论工夫即以致良知为始,亦以致良知为终。用阳明的话来说,即是“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①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第30页。。
船山与阳明之不同便在于,他并不把道德价值的呈现完全理解为对本心的观照,而是理解为气之流行大用而成就的各个事物之合理。用船山的话来说,“性”是“二气五行妙合凝结以生底物事,此则合得停匀,结得清爽,终留不失,使人别于物之蒙昧者也。”②[清]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11,12页。
因此,船山与朱子一样,认为性即理,心不即性亦不即理。承此要旨,船山便无法认同阳明将格物与致知完全打通,而是分作两截工夫。就“致知”而言,船山与阳明所解相同,即是求诸本心而“知善知恶”。然而,船山特别强调,有些善恶之理是求诸本心也不可得,而只能去透过道德上的实践来认识,也就是“格物”。因此,船山便有与阳明迥然不同的表述,他固然认为“孝者不学而知”,但又强调“夫事亲之道,有在经为宜,在变为权者,其或私意自用,则且如申生、匡章之陷于不孝,乃藉格物以推致其理”③[清]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11,12页。。也就是说,即便真可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也并不意谓道德实践便即有成,换言之,道德要如何实践是需要在客观的世界中认识,而不管再如何求诸主观的本心亦是有限。
其实,船山将致知与格物分作二截,不只与心学不同,亦与理学不同。因为朱子言格物致知,亦是认为两者可以打通,只不过阳明是从内来打通,而朱子是从外来打通。此中之曲折,需兼采唐君毅和陈来的研究来进行说明④参见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第166—181页;陈来:《诠释与重建──王船山的哲学精神》,第63—70页。。
陈来指出,船山并不赞成朱子“格物则知自致”的主张,并从知识来源与型态来区分格物和致知。他指出,船山认为格物得知的是客观的知识,而致知得知的是内在于己的知识。他又引船山原文,格物是“心官与耳目均用,学问为主,而思辨辅之”,而致知是“唯在心官,思辨为主,而学问辅之”⑤[清]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11,12页。。最后,他判定,船山不似阳明注重致知,忽略格物;也不似朱子注重格物,忽略致知;而是两者兼论而不偏废。
朱子之论“格物则知自致”,乃指他将格物到致知的过程解释为“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⑥[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7页。。
对此,唐君毅透过观察朱子论读书之法,从而判定朱子言格物穷理,其实是“求诸外而明诸内”。而当中的关键在于,朱子所谓“理”既指事物本身的“实然之理”,也指人如何应对事物的“当然之理”,而且并不特别区分,甚至可以说,是当作一体两面。因为要知道如何应对事物,前提自是要知道事物本身的实然之相。也就因此,尽管“理”是在外的,但内在于己的“心”既可知“理”又可应“理”,如此归根究底,理的显现,其实就是心的作用。由此前提,便就可作如此推论,即知理应理越多,也就意谓心之作用越大越显,于是就最终结果来说,理论上必是“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故此,朱子论工夫,要旨上其实也就是将格物与致知打通。
由此可见,如同阳明所谓的致良知,朱子所谓的格物穷理,也就是存天理去人欲的工夫,故两者的工夫虽不同,但其实都预设了经此一关,当事者是会“自然而然”地去实践道德。然而船山则不预设这“自然而然”的一转,因为其工夫论并不契“存天理去人欲”这一关,于是也就不将格物与致知打成一片。此中关键在于船山认为天理与人欲可以共存。
(二)船山反对将气质与性理二分
陈来指出,船山与朱子理学有一重大不同在于,船山反对使用 “性在气质中”的讲法,而主张“气质中之性”的讲法①参见陈来:《诠释与重建──王船山的哲学精神》,第414—419页。。而此判定,便是根据船山对《论语·阳货篇》的注记②船山之注记载,[清]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第466—472页。。
所谓“性在气质中”,是新安陈氏取自朱子对“性相近,习相远”这句的注解:“此所谓性,兼气质而言者也。气质之性,固有美恶之不同矣。”③[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75页。
朱子的注解,意在指出天理之性是完全实存及超越的,也是内在于人人而完全相同的,因此孔子所谓的“性相近”便不能是指“天理之性”,而只能是指具有经验义涵的“气质之性”。此中牵涉到的形上学根据,即是理学将天理之性与气质之性二分,而人之为何有美有恶,乃气质之性造成的偏离,意即气质之性即是人欲之来源。故此,只要将气质之性去除,天理之性便会复又彰显,也就是存天理去人欲,这就是“性在气质中”这句提法的意旨所在。用日常用语表达,即是“土豆在泥土中”,把泥土清理干净了,便会见到土豆。
船山主张“气质中之性”牵涉的形上学根据,则不是将天理之性与气质之性二分,而是认为天理的显现即是气质造成的结果。在船山的思想中,“气”与“质”不尽完全等同,因为“气”的第一义是指宇宙流行大用,故“气”只能是善的,而不可能是恶的,否则即在等于说宇宙流行大用有可能是恶的。而气流行所造成的种种殊相结果,则以“质”来指涉。固然,人与人,万物与万物的“质”都是不尽相同。但即便如此,也不能说“质”有善有恶。因为气既然是全善的,则其化生结果就不可能会有恶的。也就因此,所谓有善有恶,便不是气质造成,而是人未加利用或修行不足造成。总而言之,“性”虽是气质之性,但有善有恶非气质之性造成,而是人之“习”造成,此即船山解“性相近,习相远”。依此,用日常用语表达船山所谓“气质中之性”,便是“泥土中的土豆”,意指土豆乃因泥土生成,人只能利用泥土来栽培土豆。
由此引申的,即是船山并不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因为天理之显现,也要因于人欲而成就。但必须注意的是,船山并不是高唱所有的人欲皆是合理的。对此,陈来指出,船山亦是严于分辨天理人欲,有区分“私欲”和“公欲”,并主张克去私欲④陈来:《诠释与重建──王船山的哲学精神》,第155—160页。。而要特别指出的是,固然儒学各宗各派都不会完全否定人欲,否则即是变异为释教,但无论如何,各宗各派也皆对私欲和公欲作出分别。但对船山来说,由于他对性理的理解,除了具有实存及超越义之外,又另有经验义,因此,他对于道德价值的理解,亦是从经验上说,而不纯从实存上来说。
我们发现在朱子和阳明的思想中,他们所谓的天理是实存的,人欲是经验的(超出本性而过分的私欲)。因此,他们所谓的存天理去人欲,可以被理解为是将经验的杂质去除,而复返纯真实存的本性。但在船山的思想中,天理与人欲都是经验的,因此复返之功就无堪举重。在这层意义上,船山论工夫的根本意向就并非在主观的道德境界上用功,而是投射至具体的对象,以经验的人欲去实现经验的天理。
但遗留问题是,经验毕竟是外于当事者,那么当事者又要如何掌握对经验的观察及判断,来对结果负责呢?下文透过船山的论述,以诠释出儒家式责任伦理的道德格律来回答。
三、责任伦理的道德格律
在韦伯的论说中,责任伦理同时包含冷酷的算计和热忱的抱负。同样地,船山论工夫亦指向此冷热两面向。但必须注意的是,由于船山是坚守儒家立场的士人,故其思想的责任伦理面向,特有一种严肃的道德态度。对此,本文将首先论述船山对知、仁、勇的次序规定,然后据此来诠释三条道德格律。
(一)船山对知、仁、勇的次序规定
船山对《中庸》里“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此句,以“诚”来统摄,并对接下的“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①[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9页。,有特别的论述。
所谓“一”即是指“诚,而“豫”即是指未作事功前当事者的内在状态。在船山思想中,“诚”是特指气体流行之大用,必是要有客观事实上的功效才可言“诚”。船山特别强调,“一”和“豫”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而如果将之相提并论,即是“异端”。这其实是意指阳明的知行合一论,因为阳明思想中的“诚”,是特指心体流行之大用,乃是以道德境界的复返来言。
故此,引文中的“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按心学的思想,亦是特指道德境界的修养,因此,“一”和“豫”是可相提并论的,也就是说,当事者可从道德境界开出种种外王成就的“九经”。
但在船山的论述中,“豫”是特指“学问思辨以求其理”,他并又言:“唯学问思辨之功,则未有此事而理自可以预择。择之既素,则繇此而执之,可使所明者之必践,而善以至。”②[清]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第135,585,537页。
由此可知,船山论工夫极为特别的一点就是,当事者有义务在道德对象还未呈现之前,便需有学问思辨来作准备以应对。因此,船山对知仁勇三者有一次序的规定。其言:“故三达德之序,曰知,曰仁,曰勇。不知则更无仁,不仁则勇非其勇。故必知及而后仁守,若徒勇者则不必有仁。”③[清]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第135,585,537页。
按此次序的规定,再与《中庸》的论述结合,船山论三达德便可以日常用语表述为,“要先好学,才能力行,然后才能知耻”。而正是就此次序的规定,本文要透过船山对人物之臧否来层层诠释出三条儒家式责任伦理的道德格律。
(二)儒家责任伦理的道德格律诠释
如同韦伯提出责任伦理是特别针对政治活动,船山思想的责任伦理面向,亦与政治活动紧密相关。要特别指出的是,船山对政治抱持着相当保守的态度。即如嵇文甫指出的,船山与梨洲政治思想的其中一个重大歧异,便是“梨洲热烈赞扬某些群众性和政治性的政治斗争,而船山则持否定的或批判的态度”④参见嵇文甫:《论王船山与黄梨洲政治思想中的一个歧异点》,氏著《嵇文甫文集》下册,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28—638页。。船山对政治的保守态度,正是源自于其思想中责任伦理的面向。
本文要诠释出的第一条道德格律,乃以“从好学到力行”来展开。所谓“从好学到力行”,意思甚明,即指当事者的作为需有智识的准备。而需注意的是,船山是把“好学”当作一种修身工夫,因此就牵涉到意志力的修养。对此,从船山如何盛赞光武以及如何批难王安石便可一目了然。
船山对光武的政术盛赞道:“以静制动,以道制权,以谋制力,以缓制猝,以宽制猛而已。”⑤[清]王夫之:《读通鉴论》,《船山全书》第10册,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第223页。而对王安石则是如此批难:“唯智小而图大,志陋而欲饰其短者,乐引取之,以箝天下之口,而遂其非。”⑥[清]王夫之:《宋论》,《船山全书》第11册,第152页。其实这两句判语都共通地指涉一个概念,即船山所言之“盖志,初终一揆者也,处乎静以待物”⑦[清]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第135,585,537页。。
在船山看来,当对事物的观察及认知还未明朗前,当事者必须先抱持住其欲为事功的志向,静静地克制住自己不去贸然行动。可以说,船山言“志”,同时兼具内外两面向。就外而言,“志”乃是欲大有作为的自我勉励;就内而言,“志”乃是静观其变的自我克制。对船山来说,王安石欲为改革,固然是大有志向,但船山还是诘其“志陋”,恰恰就是因为王安石高谈阔论变法,却不事先虚心调查后果将会如何,反而之后招来党派之争,而缺乏的正是“志”的向内用力,即自我的克制。
由此,本文要提出的第一条责任伦理的道德格律,即是“当事者不止要有志向,还要克制自己处乎静以待物”。
接下来,本文要以“从力行到知耻”来诠释出第二条及第三条道德格律。从发生状态而言,“从力行到知耻”,可以指“耻于未能力行”,也可以指“耻于力行之后”。
先论“耻于未能力行”。回到一个老问题,事功的结果总非当事者能完全控制。而且,即便当事者总能约束自己处乎静以待物,然而要处乎静到什么时候?又要待物到什么时候?而这便有可能会沦为当事者不去行动的借口。对此便要以船山对王安石的另一个评价来做申论。
众所周知,王安石变法的其中一个目的,便是要增加财政收入,因此他以桑弘羊及刘晏自任。在船山的评论中,王安石增加财政收入的措施,在实行之后便冒出许多人民不堪其扰的怨言,而如此王安石应要有所更改,但他仍是一意孤行,以为久行之后人民皆会接受习惯。船山对此便作此判语:“君子之道,有必不为,无必为。小人之道,有必为,无必不为。”①[清]王夫之:《宋论》,《船山全书》第11册,第154,155页。
所谓“必不为”,是指君子必定有某些不可妥协的道德底线;但对于小人来说,则无此道德底线,因此凡事皆未必不为。而所谓“无必为”,是指君子自知要自度量力,故必有自我克制,而不能断言某事必定可为;但对于小人来说,则为遂足自欲,因此便会认为凡事皆是可为。简单而言,船山以王安石的一意孤行而判定他是一个小人。
但必须注意的是,船山并非断言君子无必为之事,其此段判语颇可寻味:
夫君子亦有所必为者矣,子之事父也,臣之事君也,进之必以礼也,得之必以义也。然君子之事父,不敢任孝,而祈免乎不孝;事君不敢任忠,而祈免乎不忠。进以礼者,但无非礼之进,而非必进;得以义者,但无非义之得,而非必得。则抑但有所必不为,而无必为者矣。②[清]王夫之:《宋论》,《船山全书》第11册,第154,155页。
由引文可知,君子之必为,是知道自己“总有应该做的事”,但此中之行动如何具体作为,总不能说有一万试万灵的办法,而总是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进退措宜。因此,君子所能自勉负责的,只能是后果不失不坏,而非结果必得必好。按船山给出的例子,即是一个称职的儿子,只会警惕自己是否有何作为是“不孝”的,而不敢有信心自己是否有何作为是“孝”的。同样地,一个负责的人,也只会警惕自己是否有何作为是“不礼不义”,而不敢有信心自己是否有何作为是“必礼必义”。
由此,本文要提出的第二条责任伦理的道德格律,即是“当事者需坚守不可妥协的道德原则,而据此道德原则,来判断自己有何不可做或不可不做的事。”
第二条道德律则,是特别为克服第一条道德格律可能沦为“当事者不去行动的借口”这一问题的。按第二条格律,根据特定的道德原则,在许多情况中,不去行动将会是种过错,而无法以事情未明朗为借口去规避。例如,以“仁爱”为道德原则,孺子将入井而不去搭救就必定是种过错;或甚至更复杂的情况,有晚辈将误入歧途而不去阻止也必定是种过错。当然,要如何阻止,就是当事者必须去想方设法的。
然而,就在“如何想方设法”这一点上,又出现了问题。而这便有关本文将要诠释的最后一条道德格律,乃关乎“耻于力行之后”这一面向。
显然,所谓“耻于力行之后”,应是特指力行之后的结果不尽人意。但我们知道,实践之结果本就非当事者可完全控制。根据道德原则,当事者可确认“应该/不应该去做”,但却无法确认“如何去做”。我们知道,在许多情况中,达成特定结果的最有效手段,与特定的道德原则,很可能是相互冲突的,而这也是儒家传统一直在探讨的权变问题。按上述例子,阻止晚辈误入歧途,很可能最有效的办法是编造某种说词,但显然这可能有欺骗之嫌。若纯粹地根据责任伦理,只要真能阻止了晚辈误入歧途,当事者也就完成了其负责的义务。但本文所要诠释的是儒家式的责任伦理,故此是要以不违反意图伦理为前提的,因此当事者不能仅以确实阻止了晚辈误入歧途这一结果,来正当化其编造某种说词的行为。简单而言,问题即是“当事者要如何在效果与原则之间做衡量?”
对此,船山对光武的一个评价正可资解答。而这牵涉到两起事件。
第一起事件:更始二年(24),刘秀奉更始皇帝的命令讨伐自称赵汉皇帝的王朗。进军邯郸时,王朗派遣谏议大夫杜威请降,并求封万户侯。但光武不允,只承诺饶其性命。最后谈判破裂,刘秀急攻邯郸而杀王朗①事情详见[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第1266—1267,1309—1310页。。另一起事件:建武三年(27),已经称帝的光武攻讨拥立盆子的赤眉军。光武屡战屡胜,赤眉军败溃后辗转游移。到宜阳时,赤眉军遇到已经严正以待的光武军,终于决定放弃,于是派遣刘恭请降。刘恭问光武请降后的封赏,光武也只承诺饶盆子性命。最后,盆子还是投降了②事情详见[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第1266—1267,1309—1310页。。
船山对光武这两个作为极为赞赏。在他看来,诈称自己是汉成帝儿子以得到拥立的王朗是个“妖人”,而出身卑贱却接受赤眉拥立的盆子是个“愚者”。因此,若光武真答应封赏,便无以警惕世人。而最难能可贵的,便是光武并没有先假装答应,事后再追究诛杀。
船山以此设立了两种相互对立的情况:一种是光武的“决于一言,而更无委曲之辞以诱之,明白洞达,与天下昭刑赏之正”;另一种是“为权术者之说者则不然,心恶之而姑许之,谓可以辑群雄之心”,而船山认为后果是“然则权者非权也,伪以长乱而已矣”③本段引文皆出自[清]王夫之:《读通鉴论》,《船山全书》第10册,第218页。。
要澄清的是,船山对于权变这一行为的评价,其所谓的“正”和“伪”其实不是以时间长短的成效来估量,也不是以当事者动机的纯良来估量,而是特别地以世人的观感来估量。也就是说,权变的正当性,其实就是以其昭示的道德示范来作为根据。
回到“当事者要如何在效果与原则之间做衡量?”的问题,按船山对“正”和“伪”的分别,则问题应更改为“衡量后所作出的抉择,对于世间会产生何种道德示范?”再回到上述的例子,本文要以此申论的是,为了要阻止晚辈误入歧途,如果当事者选择编造某种说词,会予人欺骗的示范,那就是不可取的;反之,若是予人善意谎言的示范,那就是可取的。
本文以此要提出的最后一条责任伦理的道德格律,即是“当事者在原则与效果之间衡量后作出的行为,必须不予人不良的道德示范”。
结 论
本文试图以船山的工夫论及政论,来诠释出三条儒家式的,也就是被意图伦理涵摄的责任伦理的道德格律:(一)当事者不止要有志向,还要克制自己处乎静以待物。(二)当事者需坚守不可妥协的道德原则,而据此道德原则,来判断自己有何不可做或不可不做的事。(三)当事者在原则与效果之间衡量后作出的行为,必须不予人不良的道德示范。
——探《船山之尊生尊气与尊情才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