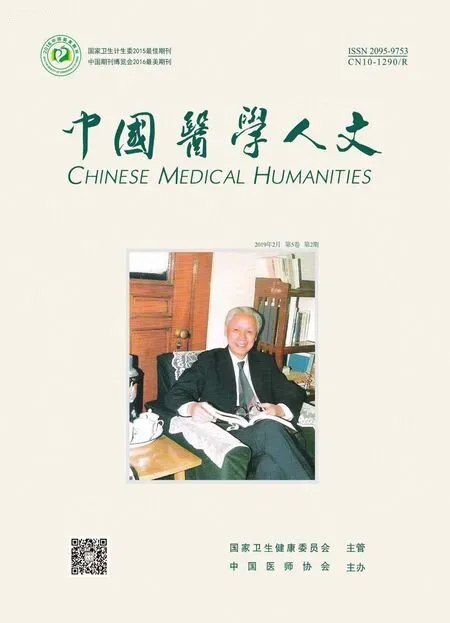医学与文学融合意味着什么
文/赵美娟
医学与文学融合意味着什么?
是否是让医生们都成为具有作家、诗人、语言学家、艺术家那样的文采与水准?当然,有文采、善表达、懂艺术与审美,对人的生活品质和职业促进都是极其必要和有益的。然而,笔者以为,这里的“意味”不止于这个层面,比这个层面更值得关注的是,提倡医学与文学的关联与融合,意味着:对当代医学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一根本问题具有历史性与现实性的反思反省意义,具体表现在:如何从总体上认识当代医学迫切需要的分析综合有机一体的整体驾驭?如何看待评估现实医学的利弊得失?如何借鉴人类一切智力文化成果使医学更智慧地理解人自身这一复杂生命?使人像对外部世界拥有的探索兴趣并取得的诸如天文学、物理学、化学、数学等自然科学成就那样,去探究揭示人内在生命世界——肉体的精神的世界及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进而,最大限度地在医学中还原人在开放生成中的生命样态的复杂丰富面向与维度,历史地、现实地而不仅仅是一般地、逻辑地认识人和健康与疾病问题,更好地兑现医学的本质与目的——“以人为本的、对生命现象的认识理念与救护帮助的方式体系”(笔者语)——这一医学存在意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要言之,文学之于医学的意味,与其说是文学在诸如理念上、方法上如何助力医学,不如说,是医学基于“人学”前提下的、伴随现有医学模式在其结构与功能上的反思性觉悟,其隐喻在于,不仅医学与文学,还可以是:医学与哲学、医学与美学、医学与宗教、医学与人类学、医学与音乐、医学与绘画、医学与体育、医学与建筑、医学与政治经济、医学与社会、医学与法律等医学与人文社会学科的关联与融合趋势,如同医学与生命科学、医学与工程学、医学与计算机、医学与人工智能、医学与统计学、医学与心理学等自然科学学科的关联与融合一样,彰显的是,人们对医学的学科综合性、开放性与人的复杂性、生成性之间的历史性认识提升,标志着,步入21世纪的医学围绕“人之生命问题”在“人学”尺度上从认知理念到方法手段上的了不起的文化性与思维意识上的变革拓展!所谓人把握自身于医学精髓上的再度领悟。
伴随百余年的现代脚步,医学的专业化将各个学科局限在狭窄的特定方面,在病理、生理、解剖等层面把人分解为器官、组织、细胞等后,忽略了其与心灵的、智力的、道德的、艺术的、情感的、经济的、社会的有机关联,一个时期以来,医学中的机械还原论作为一种思维工具,阻碍了医学对自身复杂生命体的系统性探究。众所周知,思维工具与技术工具一样,都有其适用范围和前提条件。尤其,高度专业化的头脑无法在广度上拥有开阔的视角与多样思维视角,标准化、量化本身没有问题,专家绝对需要,但问题在于,如何挣脱学科局限获取关于人的整体知识?过度专业性势必导致专业偏见?
英国剑桥大学科学哲学家蒂姆·卢恩斯(Tim Lewens)教授认为,世间有诸般科学。物理学是一种,化学是另一种。还有一些学科也能产生知识与洞见,但是,我们当中绝少有人会即刻视其为科学,历史学和文学研究便属于这一类。他还说,科学能否洞察一切?科学能否把值得我们了解的一切最终都交给我们?抑或,是否还存在着另外一些殊途同归的理解形式,比如文学、抽象反思?这类哲学问题关乎科学的界限,这类问题也有助于我们去理解:科学与艺术如何对人类知识做出不同的贡献。
此类问题,早在19世纪英国著名生物学家T·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1825-1895),那位我国晚清著名学者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的原作者,就曾认为科学无法解决一切问题。其孙子,于1932年写出的著名的反思人类科学主义的科幻哲理小说《美丽新世界》的文学家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1894-1963)在这部小说中旁征博引生物学、心理学知识,虚构了福特纪元632年(公元2532年)的一个从生到死都受到垄断科技控制的精致调制出的社会——美丽新世界——书中那无任何副作用的可以使人服用后及时享受福乐的药物“苏摩”,以及那为推动美丽新世界更向前发展而实施的可以长生不老的、更加美好的基因加强制定计划,以及那鳞次栉比的大型购物中心和充斥其间的被设计出来的各色人群,读之,恍若现实般离我们不远,提醒着读者,一味追求“幸福快乐”的人类为之借助科技手段需要怎样的代价。
对人之生命奥秘与人之命运的关注、思考与诠释,医学与诸如文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之间从来都是“一体”的。著名文学批评家韦恩·布斯(Wayne Clayson Booth,1921-2005)认为真正的小说一定是现实主义的,无论是战争史,城市空间,还是心灵探幽等,都指向现实、指向人性。所不同的是思维侧重与语言方式,比如,对一位从未见过“红色”的人要告诉他红色什么样时,可以表述为“红色指620-750纳米波长”,虽然精确严谨,但听者还是不得要领,唯有视觉呈现,有图有真相。比如,病痛之于患者更多的是感受描述,之于医生更多的是知识学术,各说各话,看似对不上频道,实则相反相成,文学艺术作为人类心灵生活的一种样式,与讲究实证实验的科学语言一起,共同构成了人的内在心智的真实维度。
1912年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获得者、发明了更有效的血管缝合术的法国医生亚历克斯·卡雷尔(Alexis Carrel)在分析为何人对自身的了解还停留在初级阶段、以及人的科学是一切科学中最难的时,曾说过一段话:人是一个极其复杂、不可分割的整体,我们无法获得人的一个简单表达。我们找不到什么方法,能够同时在整体上、部分上以及与外部世界的关联上理解人。为了分析自己,我们被迫求助于各种不同的方法,从而运用好几门科学。从人这个对象身上,它们只能抽象出各自方法所能产生的结果,这些抽象概念全部累加起来依然没有具体事实那么丰富。它们丢弃了抽象后的残余,而这些残余部分十分重要,不容忽视。解剖学、化学、生理学、心理学、教育学、历史学、社会学以及政治经济学,它们对各自主题的研究都不够透彻,在这些专家眼中,人远远不是一个具体的人、一个实在的人,他仅仅是一个模式,由各种科学方法所建立的基模构成。卡雷尔想表达的是,一方面,人无法被分解、被简单化,另一方面,虽然人被专业化、逻辑化为数据、指标、影像、概念,但没有更好办法,所以,医学必须要用其他所有学科,抵抗过度专业化的风险,获取人的整体知识。
医学与文学融合的意味,虽然篇幅所限,也尽在意会言传之间了。不过,强调人文,不意味着否定或轻视科学,同样,强调科学,也不意味着否定或轻视人文。切忌矫枉过正,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