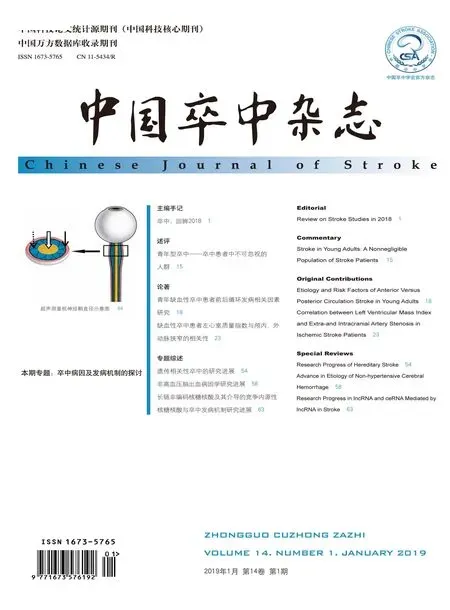非高血压脑出血病因学研究进展
王茜茜,张雨蕾,吴云成
ICH占全部卒中的20%~30%,往往发病迅速、病情凶险,治疗效果不佳。2012年第一个按病因分类的系统将ICH病因分为结构病变(structural lesions)、药物因素(medication)、淀粉样血管病(amyloid angiopathy)、全身性疾病(systemic disease)、高血压(hypertension)和不明原因(undetermined)等,这一分类系统地阐述了ICH的病因,极大地促进了ICH的研究进展[1]。目前,长期高血压所致的脑内细小动脉破裂已被明确证实参与ICH的发生,其他相关病因如脑AVMs、脑淀粉样血管病变、抗凝或溶栓治疗、全身性疾病等的研究也有较大进展,为ICH的诊治提供了更多的思路和更广阔的前景。
1 脑血管结构病变
脑血管结构病变,包括AVMs、海绵状血管瘤、动脉瘤、静脉发育异常等,与ICH密切相关。这些结构病变使血管变得脆弱,从而更容易导致ICH。
脑AVMs是指病变部位脑动脉和脑静脉间缺乏毛细血管,血液直接从动脉流通到静脉血管系统。AVMs部位的动脉血压无法正常消散,可导致ICH发生[2]。虽然目前AVMs生长、破裂的机制尚不清楚,但研究发现,细胞因子上调、黏附分子表达、白细胞募集并释放MMP-9等炎症可能是AVMs发生发展的重要因素,这可能会成为AVMs新的治疗靶点[2]。Rete MCA是在胎儿期丛状血管形成的一个突出的大分支,从解剖结构上看,是一种网状异常且不汇聚的血管。针对1937例患者的临床和影像学分析发现,13例Rete MCA患者中有9例发生了卒中,其中3例为ICH[3]。虽然目前Rete MCA发生、发展、转化的机制尚不明确,但其高ICH风险的特点不容忽视。另外,一项关于海绵状血管瘤血浆生物学标志物的研究发现,基于血管生成和炎症机制在血管结构异常中的作用,ICH的症状波动可以通过潜在的生物学标志物,如白介素1β、白介素2、γ干扰素、肿瘤坏死因子α等炎性细胞因子进行预测,高炎症反应状态的患者新发ICH、病灶生长或新病灶形成率显著升高,这也为此类患者ICH的治疗提供了可能的靶点[4]。
虽然生物学标志物检测未来可能应用于脑血管结构性病变患者发生ICH的临床预测,并对临床试验中的病例进行分层,但是目前关于脑血管结构病变导致ICH的机理尚未阐明,仍需进一步的基础研究。
2 脑淀粉样血管病
CAA是以β淀粉样蛋白(amyloid-β,Aβ)在脑血管内沉积为主要表现的一种病理改变。Aβ可以诱发炎症因子释放、活化,通过氧化应激等机制,损伤血管内皮细胞和平滑肌细胞,导致ICH的发生[5]。近年来开展了很多关于CAA的研究,但多针对阿尔茨海默病的模型,对CAA ICH模型的研究较少[6]。
研究发现,还原型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磷酸(nicotinamide adenine dinucleotide,NADPH)氧化应激产生的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在CAA诱发的脑血管事件中是关键媒介[7]。血红蛋白代谢产物、兴奋性氨基酸和炎症细胞均可产生ROS,过量的ROS破坏氧化和抗氧化平衡,通过脂质过氧化、DNA损伤、蛋白质氧化等途径导致细胞死亡、结构损伤及血脑屏障破坏,损害中枢神经系统[8]。此外,有研究显示,当线粒体膜通透性转变孔打开时,ROS正反馈诱导自身释放,导致线粒体衰竭,诱发ICH[8]。蛋白质组学分析还发现,肿瘤抑制基因SRPX1可能与Aβ共同沉积到脑血管中,介导脑血管事件的发生[9]。有趣的是,2017年一项关于遗传性CAA(荷兰型)突变携带者的研究发现,脑脊液中的Aβ40、42的水平可能在出现Aβ沉积病理性改变前就已经发生变化,这种临床前的生物学标志物对于疾病的早期诊断具有重要意义[10]。
3 药物因素
3.1 抗凝药 抗凝药是指通过影响某些凝血因子阻止凝血过程的药物,可用于防治血管内栓塞或血栓形成疾病,包括维生素K拮抗剂(vitamin K antagonist,VKA)和新型口服抗凝药(new oral anticoagulants,NOAC)。随着抗凝药的使用,出血性事件不断发生,老年人ICH的风险增加了2倍左右[11]。
VKA相关ICH,如华法林相关ICH,是华法林治疗中最严重的并发症。华法林所致的抗凝状态可以引起血肿扩大、神经功能受损以及增加死亡或残疾的风险。就绝对风险而言,在70岁受试者中,自发性ICH的发生率约为每年0.15%。在接受华法林治疗并使INR控制在2.0~3.0的患者中,ICH的发生率增加至每年0.3%~0.8%,在INR>3.0的患者中,ICH的发生率则进一步升高[12-13]。因此,在使用VKA时,需权衡其抗凝优势与出血风险之间的利弊,做好ICH的应对措施。对NOAC相关ICH和VKA相关ICH患者的影像学及临床表现系统分析发现,与VKA相关ICH相比,NOAC相关ICH患者NIHSS评分更低、出血量和神经功能缺损症状更少,这可能与NOAC特异性作用于单个有活性的凝血因子有关[14]。但是,联合使用NOAC和双联抗血小板(阿司匹林加氯吡格雷)则会导致ICH的风险增高2~3倍。例如,在双联抗血小板的基础上加用利伐沙班(2.5 mg或5 mg,每日2次),患者ICH的发生率由0.2%分别增加至0.4%和0.6%[15]。
3.2 溶栓药 在缺血性卒中发生4.5 h内使用rt-PA溶栓能有效改善患者预后。一项检测MMP-9溶栓前后水平的研究发现,MMP-9作为一种蛋白水解酶,能够特异性降解脑血管周围基膜成分,使细胞基质退化、破坏细胞和脉管系统的完整性,引发ICH转化[16]。MMP-9是出血转化的独立危险预测因素,也是ICH的一个新的生物学标志物。
幸运的是,静脉溶栓前的高微出血负担(MRI>10个微出血灶)可以对ICH风险做出预测[17]。最新研究提出,用10个变量包括:收缩压、年龄、从发病到溶栓时间、NIHSS评分、葡萄糖、阿司匹林、阿司匹林+氯吡格雷、抗凝使INR≤1.7、当前梗死标志、动脉高密度征象构建的列线图,可以个性化预测静脉溶栓患者的出血风险,这为溶栓治疗的选择提供了一些参考[18]。在出血后的管理上,有试验推荐使用冷沉淀来逆转凝血病理机制达到止血的目的,具体的处理方案还没有标准[16]。
3.3 抗抑郁药 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SSRIs)是一种常见的抗抑郁药,它通过抑制5-羟色胺再摄取过程,保持突触中5-羟色胺的较高含量来维持神经元的活动。目前,关于SSRIs与ICH风险关系的观点各异,早期研究没有发现SSRIs增加ICH的风险[19]。但是最近一项Meta分析表明,队列、病例对照、病例交叉研究均显示,在口服抗凝药同时服用SSRIs患者的出血风险是单纯服用抗凝药患者的1.56倍[20]。对于口服抗凝药的患者而言,SSRIs延长了出血时间,增加了ICH的风险。因此,对于有高出血风险,如长期使用抗凝药、有颅内出血史、有CAA病变的患者,临床应当考虑换用不同种类的抗抑郁药。
4 全身性疾病
全身性疾病可以引起人体内环境改变,导致ICH的发生。研究指出,空腹血糖浓度过低(<4.0 mmol/L)或过高(≥6.1 mmol/L)都与ICH的高风险相关[21]。慢性肝病和肝硬化患者由于肝脏代谢酶受损,出现脑内氨、乳酸聚集,血脑屏障通透性,小胶质细胞活化和神经炎症反应等改变,可能与ICH有关[22]。研究发现,肝硬化患者在9年随访期间ICH发生率与对照组相似,但ICH风险有增高趋势[23]。
研究发现,被HIV感染的个体发生ICH的风险是未感染个体的1.85倍,这种危险在年轻患者和成年女性中更明显[24]。病理活检发现,HIV感染者小血管出现血管扩张、色素沉着、血管壁钙化和血管周细胞浸润,大血管出现进行性的血管扩张,这些变化可能会削弱血管壁的抗拉强度,破坏血脑屏障,从而增加ICH的风险[25-27]。
5 其他危险因素
身高可以反映遗传潜能和儿童时期生长环境。丹麦学者曾经做过一项研究,通过记录小学生7~13岁的身高,调查儿童身高及身高的增长与成年后缺血性卒中及ICH风险的关系,结果发现儿童时期身材矮小与缺血性卒中及男性患者ICH风险的增加密切相关[28]。这提示卒中可能与儿童时期生长暴露有关。
另外,还有一些关于基因对ICH的预测效应和基因突变增加ICH风险的研究,但是目前研究还只是基于小鼠模型和部分临床试验,而且存在很多的特异性,所以基因在ICH中的影响还需要更多的试验佐证[29-31]。
综上所述,ICH病因复杂,除了常见的病因高血压外,脑血管结构病变、脑淀粉样血管病、药物应用、其他疾病,甚至儿童时期的生长暴露均可能与ICH的发生有关。随着脑研究的不断深入及分子生物学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病因及生物学标志物被发现,这不仅有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ICH的病因学,更有利于我们针对不同病因进行相应的诊治和预后评估。
【点睛】本文对脑血管结构病变、脑淀粉样血管病、药物、全身性疾病和其他危险因素等导致ICH的病因学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并在病因学分类的基础上介绍了相关生物学标志物,为非高血压ICH的临床诊疗提供一定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