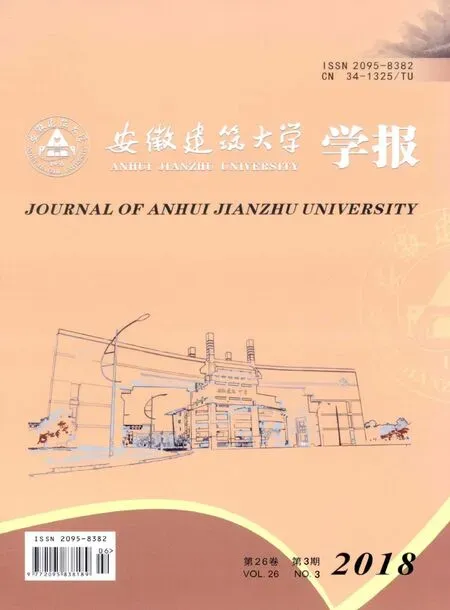建筑意象的空间隐喻叙事艺术
孙卫红
(安徽建筑大学 外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关键字:大教堂;城堡;监狱;空间批评;隐喻叙事
雷蒙德·卡佛(1938-1988),美国当代短篇小说家,著有四部短篇小说集《请你安静一下,好吗?》(1976)、《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1981)、《大教堂》(1983)和《我打电话的地方》(1987)。评论界谈论卡佛,言必称“简约”,称其为“小说界‘简约主义’大师”。[1]对于这一标签,卡佛自己颇不以为然,认为“简约”仅限于其短篇集《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2]在卡佛的作品中,《大教堂》是最受读者欢迎的一个短篇,相较于其他作品,这个短篇并不具有卡佛典型的“删减至骨”的艺术特征。这篇小说篇幅更长,文字更慷慨,情感也更丰富。[3]教堂是欧美人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小说无关乎大教堂的宗教意义,其建筑意象颇为耐人寻味。结合当下的空间叙事诗学剖析卡佛的《大教堂》,可以更丰富对卡佛作品评论的多维视角。
自当代学术界“空间转向”以来,空间理论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平台。文学批评界的“空间转向”,必然带来一种对文学中空间的文本意义和文化意义的自觉思考,及由此展开的空间批评实践。空间批评理论的代表人物包括列斐伏尔、福柯等。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一种生产”,换言之,空间既是一种认知行为,又是一种强大的社会生产模式。[4]在空间批评理论看来,文本中的空间不再是静止的容器,而是一种蕴含多维文化信息的指涉系统,是一种隐喻。本文借鉴空间批评理论视角,探讨卡佛小说《大教堂》空间化叙事特征,揭示空间概念在卡佛小说中所呈现的丰富的艺术表现形式和深层的思想内涵。
1 家的隐喻——固守与禁闭的城堡和监狱
卡佛《大教堂》创作于其写作生涯后期,故事内容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较长,叙述者描述了在家中等待他妻子的一个男性朋友瞎子罗伯特的来访,接着罗伯特到来以及晚上吃饭、看电视,一直到他妻子上楼换睡袍。第二部分属于过渡,叙述者和瞎子继续在客厅喝酒、吸大麻、看电视。第三部分午夜电视里播放着大教堂和中世纪的节目,从起初的“我可不愿意一人跟一个瞎子待着”[3],叙述者在这一部分出乎意料地和瞎子建立起一种密切关系,这种关系的结尾是叙述者在瞎子指引下在一只购物袋上画大教堂,瞎子的手放在他的手上面,而叙述者的感受是“真是不一般。”[5]纵观故事发展,结合空间视角,文中表现显著的是叙述者的家(房子)和叙述者在瞎子指导下绘制的大教堂这两个建筑空间意象及其丰富的隐喻内涵。
西谚有云,“一个人的家就是他的城堡”,风可以进,雨可以进,国王不可以进。家属于个人私有空间,个体在其间拥有足够的权力和权威,是个体构建和强化自我身份的主要场所,对身份的固守让家(房子)成为身份的象征符号,兼具个性、排他性和显而易见的束缚性。城堡作为欧美历史上的重要建筑,是封建领主用于守卫家园、抵御外来侵犯的坚固堡垒。城堡的隐喻诠释了叙述者对自我身份的固守和对外来侵犯的抵御意识,城堡赋予人以归属和安全的空间,防护的同时也导致隔绝和孤立。
在《大教堂》中,叙述者的家或者更多时候他的客厅就是他的城堡,具体、坚固、实在的物质空间,是其个人空间,他在自己的家中喝酒、看电视、抽大麻,掌控自己的生活,对自己的空间拥有绝对的主导权。
而家(房子)作为个人空间是一把双刃剑,既赋予其身份建构的自由,逃避社会空间对个体的压制和胁迫,摆脱社会分类和身份建构的限定,同时也会恶化个体自我的封闭状态。家(房子)和自我因而会相互影响,相互塑造。
叙述者妻子的一位瞎子朋友要来拜访,叙述者很不情愿:“在家里招待一个瞎子不是一件令人向往的事情”;而在他描述“现在,就是这个瞎子要来我家过夜”[5]的过程中,叙述者表现出焦虑,感受到威胁。毫无疑问,“城堡”受到外来的侵犯,叙述者要“抵制外来的进攻”,来保证他是他的“城堡”的唯一占有者,他和妻子说,“我可没有什么瞎子朋友。”也正是这一点使得他妻子很直截了当地说,“你什么朋友都没有,”她说,“句号”。[5]叙述者在城堡中的孤独和隔绝由此可见。
叙述者的孤独和隔绝还表现在他和妻子的关系上,不仅体现在故事发生时他们两人围绕瞎子到来的争吵,而且也表现在讲述他妻子几年前试图自杀的故事的时候,叙述视角既遥远又陌生。
“但是她没有死,她病了。她吐了。她的那位军官——他为什么应该有个名字?打小时候的甜心,青梅竹马,他还想要什么?不知道从哪里回来了,发现了她,打电话叫来了救护车。”[5]
在叙述者的描述中没有任何亲密关系的体现,没有任何关心或惋惜或心痛的情感流露。而在他妻子和瞎子的客厅家常谈话中,叙述者“盼望着能从我老婆那张甜蜜的小嘴里听到我的名字,像‘后来,我亲爱的丈夫进入了我的生活’之类的话。可是我一点也没有听到。”[5]叙述者的孤寂和落寞显露无疑。
叙述者的生活不仅孤寂而且空洞、乏味,直至压抑,在其对城堡生活的描述中可以看到:“每天晚上我都要抽大麻,一直熬到快睡着了才去睡觉。我和我老婆几乎没有同时上过床。等到我真的去睡觉,我总是做梦。有时,我会从梦中惊醒,心狂跳不止。”[5]叙述者的孤独和压抑只有在无意识的梦中找到突破口。无意识的梦可以视为叙述者自我构建的精神空间或心理空间,其意味深长,表明叙述者压抑、混乱的精神和心理状态。城堡空间,由具体而抽象,承载深重的精神孤寂。叙述者个人主体意识在城堡中获得自我建构,又为其所束缚,自我表现出压抑和混乱,城堡赋予叙述者的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均昭示了自我的封闭、隔绝和压抑。
人们对继续教育的需求从以往注重学历补偿到现阶段的以职业技能提高和职业素养提升为主,逐步向终身化的继续教育目标发展。如何提供适合社会经济发展要求和学习中多样化、个性化需求的各类非学历教育资源供给摆在了继续教育面前。
如迈克·克朗所言,家园给人以归属和安全的空间,但同时也是一种囚禁。[6]而福柯所言的规训的社会空间[7]以其无所不在的监视和同质化的生产性也会使居住在家中的个体失去建立个人空间的意识和能动性,而自动捍卫它,使家(房子)从属于它,成为它的延续。从而使家这一空间意象,被赋予了极其深刻的社会内涵,不仅是叙事的焦点,也是俯视小说中所有人物的空间焦点。
作为城堡的叙述者自我,任何访客都可能是一个潜在的攻击者,而一个瞎子访客似乎构成了一种更为强烈的威胁。
叙述者反复强调他对瞎子的来访没多大兴趣,并一再地划分他和瞎子访客的距离,而且“他是盲人这件事也让我感到不自在。”[5]叙述者对于“失明的情况”感到不自在的是什么?叙事中的一个重要提示是叙述者无法理解瞎子罗伯特和他刚刚过世的妻子比尤拉的生活:
他俩结了婚,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一起睡觉,最后瞎子还得给她送葬。他做了这些事情,却从来没看见过那个该死的女人长得什么样子......想想看吧,一个女人,从来不知道自己在爱人眼里是什么样的。[5]
城堡的隐喻表现了叙述者自我那种深重的“隔绝或孤立”,这种隔绝和孤立尤其表现在他和他人的关系,如叙述者和妻子,叙述者和瞎子,而这里是瞎子和他的妻子。对瞎子和其妻子隔绝的表现产生了第二个建筑隐喻,一个由眼光和视野所激发的比喻,即边沁的圆形监狱,使得城堡的意象进一步延伸为监狱意象。
边沁提出的圆形监狱,四周是一个环形建筑,中心是一座瞭望塔。环形建筑则被分成许多小囚室,所有的房间都要不断地被圆圈中心瞭望塔里的人监视。福柯以下列方式描述建筑物的构成,“在圆型监狱的环形边缘,被监视者是彻底地被观看,但他不能看到监视者;而在瞭望塔里的人能观看一切而不被看见”。[8]圆形监狱是一个很棒的比喻。叙述者在他的城堡里的一个主要活动就是在客厅里看电视,他的生活充斥着“关掉电视”,“起身把电视机打开”,“换了几个频道”,“换回到原来的频道”,电视上的小人似乎听从叙述者的吩咐,叙述者陷入到一种他没有意识到的机制中。从叙述者提供他妻子试图自杀的叙述来看,故事中的妻子,军官,瞎子,似乎很远、很小的彼此分隔的人物,被一只超然的、看见一切的眼睛观察着。他们就像是电视屏幕上的人物,是叙述者自己主要的消遣方式,叙述者在其中监控一切,确定一切被“看见”,这也就是他在城堡中的生活。圆形监狱的隐喻体现了通过视力控制的监禁特质,而逃脱视力掌控的状况则令叙述者感到恐惧,尽管叙述者声称同情盲人的妻子,但更为明显的是无意识地害怕一个看不见的女性逃脱视力控制。同时,作为叙述者自我的隐喻,圆形监狱也表明了这儿由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的距离体现的自我的孤独倾向。
家(房子)作为个人空间无法摆脱社会空间的裹挟,暴露了社会空间对个体自我的扭曲和异化。城堡、监狱意象加诸于叙述者的是双重禁锢。
2 大教堂的建筑意象——自我的新生和成长
卡佛的大教堂不是建筑实体,是在城堡和监狱的建筑意象之中所诞生的,是叙述者和瞎子相互协作、共同实践绘制的大教堂所拓展的想象性空间(心理空间)。
故事第三部分,叙述者和瞎子访客还是在客厅里看电视,两个男人在电视上看到“一群穿着骷髅服和扮成魔鬼的人正在攻击和折磨戴着道士方巾的人。”
瞎子罗伯特对骷髅的反应是“‘骷髅?’他说,我知道骷髅是什么东西。”[5]尤其是他刚刚经历妻子的死亡。
接着电视屏幕上出现了盛行于欧洲各地的大教堂。
叙述者继续描述大教堂的外部有雕成魔鬼样子的小塑像,有的大教堂的正面雕刻着魔鬼之类的东西,有的雕刻着公爵和贵妇。
叙述者对魔鬼和道士,魔鬼和公爵、贵妇的强调无意识中隐喻了黑暗和光明或者说死与生之间的争斗,对死亡的意识和体验也是个体新生和成长的必要前提。
如果无意识和对死亡的意识之间的关联对叙事者暗示的是把他的内心世界(心理空间)和外部世界(社会空间)联系起来,而不是顽固地防守,那么他开始表现出积极的行为,很高兴那天晚上能有瞎子作伴。他问瞎子,“你知道大教堂是什么吗?它们看上去像什么?如果有人对你说大教堂,你明白他在说什么吗?”
瞎子回答说他在电视上听到的,几代人建造一座大教堂,一生都在建大教堂的工人,从来都没有活到大教堂完工的时候。并且强调“在这点上,他们和我们没有两样。”大教堂因此成为一个共有的历史的工程项目的隐喻。叙述者的新生和成长需要支持,就像大教堂的建设,“它们一直往上升,往上,往上,一直升向天空。必须要用支撑物,这些支撑物叫做拱架。”[5]瞎子就是那个支持叙述者的拱架,是瞎子不受欢迎地突入禁锢叙述者的城堡和监狱,打破了叙述者个人空间的边界,扮演了导引的角色。
叙述者并不十分明白,当他费劲想要对瞎子解释大教堂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时候,罗伯特建议画一个大教堂,他的手将跟随叙述者的手。“画吧,你会明白的。画吧。”叙述者起初不愿意,最后,它确实开始了。画画很快获得了它自己的很棒的时刻:“我放进拱形的窗户。我画上拱架,加上大门,我停不下来了。”瞎子用手感知画,赞扬叙述者,并且让他“现在往里面加几个人,没人还叫什么大教堂。”在绘画最后阶段,瞎子叫叙述者闭上眼睛,继续往下画。“当我的手在纸面上移动时,他的手指就搭在我的手指上。我这一生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在故事结尾,叙述者“我还闭着眼睛。我在自己的家里,这个我知道,但我觉得自己不受任何约束。‘真是不一般。’我说。”[5]
故事结尾清楚表明,叙述者拒绝封闭和禁锢,承认一种释放和超越。大教堂的比喻展现了超越自我限制的一种可能性,通过对无意识、对死亡的认知,他人的扶助和支持,认识精神维度的价值。人物内心从压抑的无意识心理状态向有意识不断转化,努力建构自我与世界、自我与他人的和谐关系,并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与社会实践中认识自我、确立自我和实现自我。通过发现寻找,实现和内心生活、和物质世界、和他人的连接。
不同于城堡和圆形监狱,在家中绘制的大教堂,这个乌托邦式的建筑设计,成为一个建筑的隐喻,是叙述者自我主体活动空间的陌生化,突破实体空间,拓展想象性空间。打破个人空间的禁锢,融入社会生活。叙述者最终“明白”看似普通的绘制大教堂的精神影响,实现了自我的新生和成长。
家这一建筑实体承载了城堡、监狱和大教堂三重建筑意象,空间概念有机融入叙事之中,彰显了小说深刻的思想内涵,体现了卡佛小说《大教堂》独特的叙事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