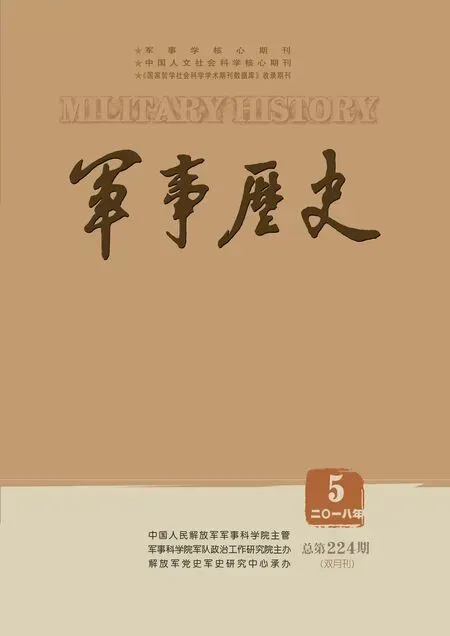“敌进我进”方针在华北敌后战场的形成过程
★
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日军把军事进攻的重点逐渐转向占领区。1941年是日军着手南进、走向太平洋战争的关键性一年,同时也是其调整并确立新的侵华战略、导致中国抗战出现严重困难局面的第一年。日军侵华战略调整的核心内容是坚持持久战态势,在正面战场实施“兵力渐减”方针,在占领区则强化“治安肃正”作战。日军战略调整的重要特征是将在占领区进行的“治安肃正”作战上升为侵华作战的战略性任务。为此,日军改变以往的作战原则,把单纯地侧重军事进攻抗日根据地调整为以“治安强化运动”和“清乡”为主要内容,以“扫荡”“清剿”“蚕食”为主要手段,以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相配合进行全面的“总力战”,实行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达到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的目的。
一、严重困难阶段华北敌后战场斗争形势
华北是中日矛盾的聚集点。日军认为华北是“治安”最差的地区,1941年初日军华北方面军制定的《1941年肃正建设上的重点事项》规定:“肃正的重点,仍然在于剿共”,“剿共一事,仅靠武力进行讨伐,不能取得成效。必须以积极顽强的努力和统一发挥军、政、民的力量,摧毁破坏敌的组织力量和争取群众为重点”*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上册,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64页。。1941年夏,日军华北方面军制定《肃正与建设三年计划》,将华北划分为“治安区”(日伪占领区)、“准治安区”(抗日游击区)、“未治安区”(抗日根据地)*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上册,第414页。。为此,日军华北方面军提出了一系列配套措施:在军事上,逐次集中优势兵力进攻各个抗日根据地,先是以烧光、杀光、抢光为手段进行大“扫荡”,大规模制造“无人区”,随即又沿纵横交错的公路大量增设据点,以三里一个岗楼、五里一个据点的“格子网”状部署,挖沟修路,进行分割、封锁;在分割封锁的基础上,对各个抗日根据地进行逐步“蚕食”,扩大和巩固其占领区。在政治上,极力强化伪军伪组织,加紧特务活动,破坏中共的党、政组织,疯狂屠杀和镇压抗日群众,妄图使人民屈服。经济上,对抗日根据地采取严密的封锁,摧毁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并加紧对人力和物力的肆意掠夺。日军华北方面军在加紧“扫荡”和“蚕食”的同时,于1941年3月至1942年12月期间策划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作为在抗日根据地实行“总力战”的一部分,以达到逐步消灭八路军主力和摧毁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目的。这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加重了对抗日根据地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破坏。1941、1942年的“治安强化运动”被日军大本营看作是“肃正建设”的全盛时期,而又以1942年夏秋之际为鼎盛。
一方面,日军借助军事上的优势,导致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生产经济极端困难,人口由一亿降低到五千万,八路军也由四十万人左右减少到三十万人。[注]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上册,第99页。另一方面,国民党继第二次反共高潮之后,为了削弱和消灭共产党,在全国制造摩擦事件,对根据地进行军事和经济封锁,根据地的情况更是苦不堪言。毛泽东在谈到根据地军民的生活时曾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注]第一二〇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抗日战争史编审委员会编:《第一二〇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抗日战争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22页。聂荣臻在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高干会议上曾经这样形容:“根据地的斗争,进入了更艰苦的阶段,吃饭穿衣都要用鲜血去换”[注]聂荣臻:《在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高干会议上的报告》(1942年9月11日),聂荣臻传记编写组:《聂荣臻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212页。。
二、“敌进我进”对敌斗争指导方针相关概念
“敌进我进”一说,最早见于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在1940年4月21日黎城会议上作的《党军建设问题》报告。[注]军事科学院《刘伯承年谱编写组》:《刘伯承年谱》,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2年,第253页。刘伯承针对日伪军残酷进攻、根据地日渐缩小的局面提出:“一退再退,退到何处?现在就是敌进我进,打磨盘摸敌人的屁股。”其基本做法,是我军针对日伪军对根据地进行的“扫荡”“清乡”“蚕食”等进攻,抽出有力部队脱离自己的后方,深入外线,在敌后方组织动员群众,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使得敌人后方转换为我军前方,化被动为主动,直至粉碎敌人疯狂进攻,缓解我方不利局面,夺取战争主动权。用根据地军民形象的说法,就是要“你到我家来,我到你家去”,用进攻对付进攻。[注]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3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62页。此后,随着对敌斗争的日益尖锐及斗争经验的不断积累,“敌进我进”的思想更加明确。1943年刘伯承在《敌后抗战的战术问题》一文中,对“敌进我进”的含义进行了总结:“‘敌进我进’,就是我军敢于脱离自己的后方,进入到敌人的后方,与广大民众结合,作斗争行动。”“假若我们在反‘蚕食’、反‘扫荡’中,在战役战术上,不以一部或主力到敌人侧背作战,强化游击与政治攻势,而能巩固根据地,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此外,他还分析我军采用“敌进我进”方针进行对敌斗争而获得成功的原因:“日寇对作战的见解,是建筑在‘敌退我进’之上的。故在抗战之初,以为我军只是掩护主力,收容部队之散兵,其次则认为游击队尚可聚歼,以后才喊出‘八路军在占领区如此滋蔓,实乃皇军心腹之患’。这是由于日寇作战要务令上并无‘敌进我进’的条文。”[注]刘伯承:《敌后抗战的战术问题》(1943年9月),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研究部编:《游击战参考资料选编》(九),第94页。
敌进我进,深入敌境袭击敌人,是牵制、分散敌人之兵力,力争主动的有效对策。[注]贾若瑜:《游击战》,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37页。这一方针与之前土地革命时期红军采取的“敌进我退”方针略有不同,但深究其内涵,两者都是保持“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基本原则,但又具有各自的特点,并非完全一致。“敌进我退”是以我军后方作为依托,利用根据地的有利条件,诱敌深入,在运动中寻找有利于我的战机,而后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军。“敌进我进”是在我军无可靠后方可以依托的情况下,深入到敌军后方进行战争行动,形成内外线相配合的作战形式,从而打破敌人的围攻,保存和发展我军作战力量,最终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抗日战争初期,八路军继续沿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擅长的“敌进我退”战术,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当战略相持阶段到来后,随着日军采用了“总力战”方针,“敌进我退”已经让八路军无处可退、无路可走,只得改变斗争方式,将“敌进我退”转化为“敌进我进”。
三、 “敌进我进”对敌斗争指导方针的形成
为了适应困难时期严酷的斗争形势,中共中央对以往的军事斗争方针政策作了调整。1941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北方局率先发出了《关于敌占区及接敌区工作的指示》,肯定了中央、北方局关于“缩小与封锁敌占区,深入敌后去开展敌占区的工作”[注]《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敌占区及接敌区工作的指示》(1941年2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文献)》,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第620页。的方针。11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明确了:“敌寇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残酷‘扫荡’,我军人力、物力、财力及地区之消耗,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敌我斗争,进入新的更激烈的阶段。”“在这一新阶段中,我之方针应当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从最激烈的武装斗争方式到最和平的革命两面派的方式)与敌人周旋。”[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1941年11月7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12—220页。12月17日,中共中央下达的《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提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的方针应当仍旧是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准备将来的反攻”;号召艰苦抗战的敌后军民“咬紧牙关,渡过今后两年最困难的斗争”。[注]《中央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1941年12月17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262—265页。
在1940年刘伯承提出“敌进我进”的战术后,八路军第129师派出武装宣传队深入到敌占区,宣传抗战必胜的道理,揭露日军的侵略罪行,收到了一定的效果。这既是武装工作队的雏形,也是“敌进我进”初露头角。面对华北严峻的斗争形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针对日军的进攻特点和各抗日根据地对敌斗争的经验,提出了“敌进我进”方针。1942年2月的反“扫荡”作战中,八路军第129师和太行军区根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实行了“敌进我进”。在“强化游击兵团内地坚持,主力兵团打击外线,组织轻便支队深入敌占区打击敌人要害”[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史研究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抗日战争时期史料摘要》第2册,1961年,第109页。的作战指导方针下,主力部队与地方武装采用内外线结合的反“扫荡”作战:在内线坚持斗争的同时,在外线组成若干轻便支队深入敌占区,乘虚袭击日军交通线和城镇据点,迫使“扫荡”之敌撤退。这是“敌进我进”第一次应用于指导对敌斗争,也是八路军第129师和太行军区对于刘伯承关于“敌进我进,打磨盘摸敌人屁股”说法的实践。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央军委华北军分会在1942年5月联合发出《关于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指示》指出:“反‘蚕食’斗争是目前华北全党全军的一个最紧急的任务,只有争取这一斗争的胜利,我们才能度过这一黎明前黑暗的艰苦路程。”“应以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正规部队分散为连营单位到各县去,深入到敌后去活动。”[注]《北方局军分会关于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指示》(1942年5月4日),军事科学院战史研究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抗日战争史料选编》第2辑第2册《对敌斗争(一)》,第149—151页。
“敌进我进”是刘伯承在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对敌斗争形势的发展需要,提出的军事概念。即:敌向我根据地进行“扫荡”“蚕食”和推行“治安强化运动”时,我则深入敌之后方,广泛开展军事、政治攻势,配合根据地内军民反“扫荡”、反“蚕食”斗争。1943年7月,刘伯承师长在《武工队在敌后活动的战术问题》中,明确了武工队在敌后作战要采用“敌进我进”的方法:“武工队要接受我们的传统,我师抗战开始就‘敌进我进’,进到敌后,但敌进我进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不这样做就不能存在。敌人今天不能攻大后方就是因为我们在拉腿。”他分析了“敌进我进”方针克敌的优势:“反‘蚕食’有三种经验:一是从正面挤;二在敌后发展;三在正面抗击,同时在敌后发展。这三种以后一种最好,这是真正的内外夹击。我们武装工作队的出路就在于,最后把日本打出去。”[注]《武工队在敌后活动的战术问题》(1943年7月27日),军事科学院《刘伯承军事文选》编辑组编:《刘伯承军事文选》,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548页。“敌进我进”方针对于战略相持阶段我军能够摆脱极端困难、无路可走的境地,以及对于整个抗日战争的发展趋势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从1942年下半年至1943年初,经过八路军总部和毛泽东的推广,各战略区都正式把“敌进我进”作为本地区对敌斗争的指导方针。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针对自身情况,结合本地区对敌斗争实际,通过实践和不断总结经验,将“敌进我进”的斗争形式多样化并将其完善和发展,成为打破日军“囚笼”政策的法宝,形成我军对敌斗争的重要指导方针。
四、多种形式的“敌进我进”在各战略区展开,指导军民克敌制胜
华北敌后战场物产和资源丰富,无论是山地还是平原,都被日军的碉堡、据点、封锁沟、封锁墙遍及,形成了一张纵横几省的“大网”。在如此紧密的攻势下,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提出了“敌进我进”对敌斗争方针,指导各抗日根据地扭转极端困难的形势。各抗日根据地依据自身的地理环境,以及本地区的敌我斗争形势,创造了符合本地区特点的“敌进我进”。
(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军民提出“向敌后之敌后进军”,反敌“蚕食”蔓延。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除冀中区为平原外,大多是山岳、丘陵地带。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实行“敌进我进”方针之初,明确指出反对日军的“蚕食”政策,就是要向“敌后之敌后”挺进。早在1941年1月,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主持召开军分区以上领导干部会议上指出:“在敌人前进时,我伸到封锁线外展开活动,到‘敌后之敌后’去,将可能收到大的效果。”[注]北京军区晋察冀战史编写组:《晋察冀军区抗日战争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278页。1941年底,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领导机关总结1941年的对敌斗争经验,又提出下一阶段的斗争要在不同的地带采取不同的工作方针,利用灵活的斗争方式与日军展开一个村庄、一寸土地及一个人民的斗争。“把我们的工作伸到敌人的背后和侧翼”,“去一点一滴的建立,恢复与开展工作”。[注]林铁:《关于晋察冀边区新形势和新任务的报告》(1941年12月3日),军事科学院战史研究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抗日战争史料选编》第2辑第2册《对敌斗争(二)》,第180页。针对日军对根据地的大面积“蚕食”,1942年5月,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在《关于反“蚕食”斗争的训令》中强调:“在反‘蚕食’斗争中,要坚持武装斗争,要求各地正规军,在平原地区,将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正规军队,以营、连为单位,分散到各县去活动,到敌后去运动。”[注]《晋察冀军区关于反“蚕食”斗争的训令》(1942年5月15日),军事科学院战史研究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抗日战争史料选编》第2辑第2册《对敌斗争(二)》,第193页。
1942年9月,晋察冀边区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会上总结了反“扫荡”反“蚕食”反封锁斗争的经验,并强调要切实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敌进我进”的指示。会议明确指出:“我们必须组织若干支游击部队,向敌后反复扰袭,不断的疲劳敌人,把敌人从面的占领压回据点去。”“在敌占领面之中建立许多小块的‘活动从堡垒’——游击根据地,加强敌我犬牙交错的形势,以阻碍敌人继续进行面的占领,孤立敌之点线,如敌前进‘蚕食’,我即可转到敌后活动。”[注]《聂荣臻在晋察冀边区高干会议上关于对敌斗争问题所作的结论》(1942年9月15日),军事科学院战史研究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抗日战争史料选编》第2辑第2册《对敌斗争(二)》,第260页。针对日军兵力部署前紧后松、前强后弱的特点,会议决定,以武装斗争为核心,配合各种斗争,把游击战开展到敌后之敌后去,即到根据地周围日军统治的地区进行活动。此后,晋察冀边区将主力军、地方军以及大量的游击队向敌后开展积极的活动,将敌后活动与正面斗争相配合,平地与山地斗争相配合,地方军与主力军相配合,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以打破敌人的“蚕食”。
(二)晋冀鲁豫边区军民率先采用“敌进我进”,力克“扫荡”之敌。晋冀鲁豫边区各战略区山地平原交替,几条主要铁路干线遍布其中。日军正是依托了铁路,对各个抗日根据地进行一次又一次疯狂的“扫荡”。晋冀鲁豫边区军民面对这一情况,一方面采取从宽正面进行伏击、炸车、突进袭击等方式摧毁敌人的补给线;另一方面派小部队奇袭敌人基干铁路并配合政治攻势,在“扫荡”之敌的后方进行活动,与在腹地作战的我军形成相互配合。
为了动员、团结根据地军民克服困难,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北方局结合根据地实际情况发出《关于坚持冀鲁豫边区的基本条件在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正规军必须坚决分散行动。除远道新来之疲劳部队以外,一般的应以三分之二分散,三分之一轮番集结休息整理为原则。分散部队以连为单位独立活动,深入敌后,找寻敌统治薄弱地区,发动与建立隐蔽的群众小型武装。”[注]《北方局关于坚持冀鲁豫边区的基本条件在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1942年6月30日),军事科学院战史研究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抗日战争史料选编》第2辑第2册《对敌斗争(三)》,第259—261页。《指示》强调在军事上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主力军实行地方化的同时也要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1943年1月,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召开的“温村会议”上,时任太行分局书记的邓小平作了《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的报告,就“敌进我进”方针指出:“敌我斗争形势是敌进我进,敌人一定要向我们前进,所以我们也一定要向敌人前进,才能破坏或阻滞敌人的前进,巩固我们的阵地。”同时指出:“敌人‘扫荡’这一区域时,其他区域应利用空隙展开对敌斗争,被‘扫荡’区域亦应组织腹地坚持与外线活动相配合的反‘扫荡’斗争,以取得主动。”[注]邓小平:《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1943年1月26日),《邓小平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2页。刘伯承在1944年的延安整风学习期间写的《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现状报告》中,总结了该地区对敌斗争与武装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根据地党、政、军、民的建设,与对敌斗争密切联系,才能巩固我们的阵地。”“在敌占区组织斗争,才能破坏或阻滞敌人摧残根据地。现在根据地与敌占区的游击性同时增加,就是‘敌进我亦进’的结果。敌深入根据地的特务活动,与我深入敌占区伪军、伪组织内隐蔽积蓄力量的斗争,也是同样发展的。我们应在掌握中日矛盾的基础上,争取主动权。”[注]《对敌斗争与武装建设中最大的经验教训》(1944年4月30日),军事科学院《刘伯承军事文选》编辑组:《刘伯承军事文选》,第554页。
晋冀鲁豫边区军民将反“扫荡”与反“蚕食”斗争密切结合起来。在敌“扫荡”时,积极进行反“扫荡”,使敌在“扫荡”中不能毫无顾忌地大量建立据点与分割、封锁抗日根据地;在反“蚕食”时,扫除一切可能扫除的据点,扩大回旋区,巩固根据地,给再次反“扫荡”创造有利条件。根据地军民在“敌进我进”方针指导下,采取内线与外线相结合,主力部队与地方武装相结合,军事与政治相结合,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经过艰苦斗争,达到了坚持根据地,扩大游击区,缩小敌占区的目的。
(三)晋绥抗日根据地开展“把敌人挤出去”,拔除敌人据点。晋绥抗日根据地,是陕甘宁边区门户上一道令日军无法逾越的屏障,是保卫延安和中共中央的核心地带,其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挤”字说明,八路军在晋绥抗日根据地必须做到寸土必争、分毫不让,否则我抗日革命圣地将不保。能否把敌人“挤”出去,关系到根据地能否坚持,更关系到游击战争能否开展。在晋绥区,对敌斗争的主要方面都围绕着“拔据点”展开。
1942年春季,晋绥根据地领导人贺龙、林枫等前往延安参加整风学习,曾向中央汇报晋绥根据地对敌斗争和其他情况。当时,各抗日根据地都正处在极端困难时期。中共中央、毛泽东也在考虑如何打败日军实施的“总力战”,使各根据地早日得到恢复和发展。毛泽东告诉林枫说,要在正面发动群众,搞敌后武装工作队。当前晋西北的任务,就是“把敌人挤出去!”[注]第一二〇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抗日战争史编审委员会:《第一二〇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抗日战争史》,第393页。同年10月31日,毛泽东给林枫发出《关于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向敌人挤地盘》电文,指示:“晋西北只有人口七十万至一百万,望检查如此迅速缩小的原因,与周(士第)、甘(泗淇)商讨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向敌人挤地盘的具体方案(即具体的、积极的、全面的反 ‘蚕食’斗争)。必须振奋军心、民心,向敌人采取积极政策,否则再缩小,前途甚坏。”[注]《毛主席关于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向敌人挤地盘给林枫的指示》(1942年×月31日),军事科学院战史研究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抗日战争史料选编》第2辑第2册《对敌斗争(二)》,第30页。11月4日,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在兴县蔡家崖军区司令部驻地召开了晋西北高级干部会议,林枫正式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注]第一二〇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抗日战争史编审委员会:《第一二〇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抗日战争史》,第394页。会议根据晋绥根据地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得出了要彻底粉碎敌人的“蚕食”,就必须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主力军、地方部队和民兵相结合,实现党、政、军、民团结一致,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种斗争全面配合起来,广泛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通过争夺一个又一个村庄的主动权来向敌人“挤”地盘。
执行“把敌人挤出去”,成为了自1943年以后晋绥抗日根据地军民恢复和发展根据地的三大任务之一。各级党、政、军、民组织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形成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思想上紧密结合的总力战,利用自身优势,积蓄力量,在保存自己的同时削弱敌人,以较小的牺牲换得了较大的胜利。在1943年上半年,晋绥区军民已经基本将日、伪军挤到据点和交通线附近,使整个晋绥地区出现了“我进敌退”的主动局面。
(四)山东抗日根据地军民运用“翻边战术”,打破敌人包围。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长期处在“扫荡”和反“扫荡”“蚕食”和反“蚕食”的斗争之中,这也成为了山东敌后游击战争的显著特点。山东抗日根据地实行“敌进我进”方针,要求山东八路军要在被“蚕食”地区的地方武装和工作人员坚持县不离县、区不离区,就地坚持斗争,并以主力一部配合地方武装,坚持边沿区,积极打击敌人的“蚕食”和伪化运动。因此,边缘游击区就成为了可以改变敌我双方在战争中处境的重要地带。“翻边战术”正是立足于在边沿区作战的斗争指导方针。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领导人罗荣桓在《关于坚持我们的边沿游击区的报告》中提出:“坚持我们的边沿游击区,使其成为我们外围的扩展线,活动的跳板,以打破敌人紧缩政策,建设起通向敌占区或越过严密封锁线之潜渡桥梁,这对我们克服最艰巨的一段过程是有特殊意义的。”[注]《罗荣桓关于坚持我们的边沿游击区的报告》(1942年8月1日),军事科学院战史研究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抗日战争史料选编》第2辑第2册《对敌斗争(四)》,第82页。
针对山东地区军事斗争的特点,罗荣桓在《关于准备打破敌人紧缩包围封锁我们根据地的意见》中,提到:“坚强我们外围游击区的工作,向着敌人占领区内部去活动,把敌人的紧缩包围封锁圈拉破口子,使敌人纵深与面的控制有不可牢固的环节,而且使我们有条件的向着敌人占领地带上打击他们的虚弱。”[注]《罗荣桓关于准备打破敌人紧缩包囲封锁我们根据地的意见》(1942年8月1日),军事科学院战史研究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抗日战争史料选编》第2辑第2册《对敌斗争(四)》,第84页。他在《反对敌人“五次治强运动”与“新国民运动”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要加强边沿地区及接敌游击区的活动,到敌人占领区域去,以小型游击队武装宣传,配合组织广大群众,深入日伪腹心,打击敌人特务活动,瓦解伪组织、伪军,镇压与捕杀那些死心塌地的汉奸。我们要学习新的斗争组织形式与斗争艺术,必须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光强调灵活的活动方式是不够的,而且会犯错误的。”[注]罗荣桓:《反对敌人“五次治强运动”与“新国民运动”的报告提纲》(1942年8月),《罗荣桓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第149—153页。罗荣桓总结了历次对敌斗争的经验,根据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创造性地提出了“敌打到我这里来,我打到敌那里去”的“翻边战术”。罗荣桓认为,由于敌后根据地地域狭小,缺乏回旋余地,如果仍然照搬内战时“诱敌深入”打运动战的方法,就难于突破日军的包围,因此必须采用“翻边战术”,即把主力部队不是设置在根据地的腹部,而是部署在靠近一路日军的根据地的边沿区。[注]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暨山东军区战史编辑室:《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暨山东军区战史》,济南:黄河出版社,2005年,第95页。“翻边战术”的内涵,就是当日军“扫荡”时,不是敌进我退、诱敌深入,不再向根据地的中心后退,而是“敌进我进”。一方面,趁敌人的包围圈尚未紧缩时,选其弱点,由根据地经边沿区,翻到日军后方去,打乱日军的部署,粉碎其“扫荡”;另一方面,由于八路军具备良好的群众基础,可以在敌人进行“扫荡”时,坚持边沿游击作战的同时,趁敌军后方空虚,组织部队和民兵打入敌占区,袭扰敌人的后方,开展政治攻势,打击敌伪政权,以牵制敌人对我根据地的“蚕食”。
1942年10月以后,“敌人打到我这里来,我打到敌人那里去”的“翻边战术”成为指导山东根据地军民开展对敌斗争的指导方针。八路军第115师发动的海陵战役、郯城战役是“翻边战术”在全山东范围内粉碎日军进攻的经典战例。此举帮助了山东抗日根据地军民收复了滨海地区的大部分土地,变日军的后方为前线,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一地区的斗争形势。海陵、郯城战役之后,“翻边战术”成为“敌进我进”方针的具体展开形式,被陆续推广到整个山东抗日根据地。
“敌进我进”方针是在抗战极端困难时期提出的,是军事战略上的创新,是顺应当时战场环境而执行的对敌斗争指导方针。主力部队改变以往只依托根据地进行退却方式的作战,打破固有的正面交锋,勇于跳出包围圈,敢于深入敌占区,在不熟悉的斗争环境中开展工作,组织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紧密联系地区环境特点,进一步发展了“敌进我进”,创造出“到敌后之敌后去”“把敌人挤出去”“翻边战术”,并发展了敌后游击战术,以多种形式进行反“扫荡”、反“蚕食”和粉碎日军“治安强化运动”的斗争,让日军实施的“总力战”以失败告终。在此期间,八路军主力部队与地方武装、民兵自卫队一起,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使内线斗争与外线作战紧密结合,利用时间的推移和空间的转换,实现敌我力量在各个局部小战场上实现强弱转换,使敌由强变弱,我由弱变强,坚持现有根据地,进而发展新的根据地。同时,八路军各部队派出大批武工队深入敌后,开展以军事斗争为中心,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开展全面的对敌斗争。通过一系列战争实践,“敌进我进”方针指导敌后抗日军民扭转了不利于我的局势,保存了自己的力量,渡过了抗战的最困难时期,并为战略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一方针成为指导敌后抗日军民能够“以弱胜强”的重要法宝,也是巩固华北敌后战场的重大举措,同时给中国的抗日战争争取了时间和空间,最终形成敌后战场的独特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