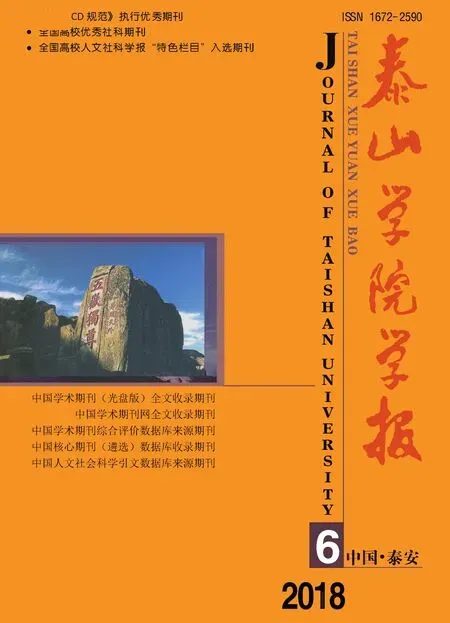战争灾难地居民参与黑色旅游开发的社区增权效用研究
——以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为例
张 秦,龚 珍
(1.复旦大学 旅游学系,上海 200433;2.南京农业大学 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95)
增权即赋权,是居民社区参与的最高形式,构成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哲学核心,也成为个人、组织与社区发展的重要结构[1]。旅游业的发展离不开目的地居民的支持与推动[2],尤其是在文旅融合不断推进的时代背景下,对于旅游文化的挖掘、旅游资源的开发等更是需要目的地居民的智力、体力与精神的大力支持,旅游社区中居民的参与作用成为促进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力。然而,目前居民在参与旅游开发的过程中仍然处于弱势、非主体的地位[3],与居民作为核心利益相关者的角色权利相悖,社区增权的作用日渐突出。
黑色旅游的产生及发展打破了人们对旅游活动的思维惯性,休闲娱乐、观光度假并非构成旅游行为产生的唯一原因,感受战争残酷灾难、追求传统文化认同、满足内心教育需求、迎合历史好奇情愫等逐渐演变成为旅游者外出旅游的重要动机。对于社区居民而言,黑色旅游的发展与其他旅游形态相比具有更多复杂性,其在经济、政治、心理等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去权现象,不利于黑色旅游的持续发展。本研究以战争灾难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黑色旅游为例,分析了社区居民在主体参与意识、参与权利等方面的去权现象,并分别从政治、经济、心理、社会、信息、教育六个方面进行增权建议,以期促进社区居民主动参与黑色旅游之中,实现纪念馆社会经济价值与居民社区价值、个人价值的共同提升。
1 文献研究进展
1.1 黑色旅游相关研究
类似于“灾难旅游”,黑色旅游(Dark Tourism或Black Tourism)是情感最沉重的色彩旅游,具有极高的精神启迪与教育价值。它承载着因自然灾害、人类行为等引致的死亡主题文化,呈现出灾难性、死亡性、恐怖性等敏感的旅游印象,丰富了旅游形态的深刻内涵。国外学者经历了“遗产旅游-死亡旅游-战争旅游-病态旅游-黑色旅游”的漫长探究过程,随后又衍生出“监狱旅游”[4]、“公墓旅游”[5]等黑色旅游子类。
20世纪初期,英国学者Stone(1996)将黑色旅游界定为游览和访问以死亡、灾难及恐怖事件为主题的景点、吸引物及展览地[6],填补了黑色旅游概念的空白;后来Lennon、Fol⁃ey(2000)将黑暗旅游的概念概括为一种位于遗产旅游中的现象[7]。Miles(2002)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更黑色旅游”、“最黑色旅游”,丰富了黑色旅游在颜色层次与灾难深重程度等方面的内涵[8]。黑色旅游本身所具有的灾难性成就了黑色旅游本质的特殊性,将原有灾难性的事件或回忆打造成旅游景点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例如Dunkley、Morgan等(2011)从分析参观战争与冲突相关场所的游客动机及经历,得出黑色旅游之旅能够为游客朝圣、集体或个人纪念等提供机会[9];Yoshida、Bui等(2016)对日本广岛、长崎太平洋战争中原子弹场址的旅游复杂性进行分析,并探究了现代遗产转化为旅游资源中需要重点突出战争旅游和和平教育两个方面,并针对游客需要开发相应的旅游产品[10];此外,关于黑色旅游的研究还包括游客动机研究、游客情感体验的研究、游客旅游管理的研究等,如Boateng、Okoe等(2018)以加纳海岸角城堡为研究对象,通过内容分析的方法探究了游客对黑色旅游景点的认知和情感,得出游客不仅经历着焦虑和悲伤,还会感到兴奋[11];Po⁃doshen(2013)以黑金属音乐及相关黑色事件为着眼点分析了旅游者的参与动机[12];Ozer、Ersoy等(2014)使用时间序列分析,对前往澳大利亚加里波利地区参与黑色旅游体验的旅游者数量进行预测,为相关旅游投资、旅游管理提供参考[13]。
国内关于黑色旅游的研究正处于探索阶段,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期,有些学者将黑色旅游的对象局限于封建迷信、黑土文化资源、煤炭资源或是工业遗产等方面[14-15],并非与死亡或灾难相关;刘丹萍、保继刚(2006)在对旅游者摄影与窥视欲进行探究的过程中首次将西方黑色旅游的概念引入学术界,并将其定义为“以纪念人类历史上各种悲剧甚至恐怖事件为目的,将这些事件转化为商品(旅游景点)满足游客需求”[16],而后李经龙、郑淑婧(2006)基于国外研究,首次对黑色旅游的类型、动机、争论以及核心进行了梳理,并指出未来黑色旅游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的各种问题[17]。此外,国内对黑色旅游的研究还集中在旅游者行为、发展对策研究、目的地居民研究等。例如,陈星、张捷等(2014)以自然灾害型旅游地为例,对黑色旅游参观者动机进行量表测量,并探究事件关注度、认知欲望对不同类型动机的影响程度差异[18];石英(2013)从供应链角度出发,结合中国黑色旅游的资源分布情况、开发条件等探究黑色旅游供应链发展的路径选择,以促进游客的满意度提升[19]。
1.2 旅游社区增权相关研究
社区增权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主要运用于社会工作方面的研究,其产生与发展弥补了社区参与相关研究的缺陷与不足。所谓增权,主要是指在外界的干预与帮助下,通过增强个人的能力以及对权利的重新认识,从而减少甚至消除无权感的过程[20]。随着现代旅游业的超高速、亚健康式发展,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旅游学者认为增权理论被是化解这一矛盾的有效理论工具,20世纪90年代,增权理论首次应用于生态旅游活动的研究,开辟了社区旅游增权研究的先河[21]。1999年,Scheyvens明确了社区旅游增权的主体与受体,并从政治、经济、心理、社会四个角度构建起社区旅游增权框架,奠定了社区旅游增权的理论基础[22]。此外,Buzinde、Kalavar(2014)等指出对居民赋权具有价值,原因在于在旅游发展的过程中赋予边缘化群体的权力有助于帮助其摆脱贫困,并建立起社区福祉与赋权之间的联系以促进社区旅游的可持续发展[23];Boley、Strzelecka等(2018)认为心理增权是地方特色与旅游支持之间的中介,是目的地居民旅游自豪感与自尊产生所需要的先决条件[24];为了衡量居民在社区旅游发展中是否具有政治、经济、心理等权力,Bol⁃ey、Mcgehee等(2014)制定了旅游赋权规模指标(即RETS)以判断居民被旅游业赋予或剥夺的权力情况[25]。
国内对社区增权的研究始于21世纪初,保继刚、左冰等最先将社区增权理论应用于旅游业,指出旅游发展过程中权利平衡与社区旅游发展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并在国外研究的基础上突出个人权利增进权与制度增权的重要性[26-27]。后来,关于社区增权的旅游研究逐步丰富起来,总的来说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对旅游领域的社区增权应用问题展开论述与探讨,一是对旅游增权对策的发展与探究,例如张福春、吴建国(2013)对民族地区的乡村旅游增权进行研究,提出要从去权的现实中发现问题,帮助居民树立权能感[28];潘植强、梁宝尔等(2014)认为社区居民参与权利的实现需要从内外增权出发,分别从制度增权、自主增权两个方面出发研究社区增权的实现路径[29];另外,学术界还对滨海[30]、少数民族传统民艺[31]、传统村落[32]等旅游形态的社区增权进行了延伸研究;二是社区增权的评价研究,如张河清、廖碧芯等(2017)根据社区增权理论构建起滨海旅游社区增权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广东海陵岛的社区增权情况进行评价[33];黄如梦、白祥(2017)运用层次分析法分别对罗布人村寨、塔西河乡两个社区的增权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并提出从收入分配方式、法律法规、居民知识技能培训等方面完善社区增权[34]。
1.3 研究述评
国内外关于黑色旅游及社区增权的研究已经逐步得到发展,然而,将社区增权运用至黑色旅游领域的研究仍处于空白状态。一方面,黑色旅游相关研究主要着眼点在于对游客的动机、满意度等的研究,关于居民权利、居民利益的相关研究不多;另一方面,黑色旅游的公益性特征要求社区的经济增权需要从不同的思维角度出发进行探索。本研究基于社区增权理论,以战争灾难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为案例地,研究社区增权对战争灾难地黑色旅游开发的效用与价值,以期探寻增权理论下黑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2 社区增权理论在黑色旅游发展中的应用价值
2.1 社区增权理论在黑色旅游发展中的必要性
赋权是可持续旅游发展的核心[35],作为利益相关者的核心主体,居民需要充分参与到当地旅游发展中去,黑色旅游目的地的发展更是离不开当地居民的支持与参与。
首先,目的地居民的旅游态度与情感变化影响旅游发展。黑色旅游目的地一般处于在原有战争遗址、自然灾害遗址或附近区域,原有重重苦难画面与现有欣欣旅游景象形成鲜明差异,难免造成目的地居民心理上的落差及不平衡,对于旅游的发展也会逐渐由被迫接受、排斥、反感向反对、阻碍等负面方向发展,黑色旅游发展与居民心理建设之间的矛盾突出。因此,在发展黑色旅游的过程中有必要对居民进行增权,重视目的地居民对于旅游开发的态度,以消除旅游者与目的地居民之间的情感交流障碍[36],引导其充分参与到旅游活动之中。
其次,目的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与生态环境受到游客破坏。一方面,外来旅游者的大量涌入对于原有社会公共设施、交通等公用系统带来多方压力,并通过消费的增加引起居民生活成本的上涨,直接影响到居民日常幸福生活的感知,导致居民在心理上产生无力感、无权感,不利于和谐旅游社区环境的构建;另一方面,游客的整体素养与旅游的快速发展相脱节,游客的不文明对脆弱的黑色旅游地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居民在此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对于游客的外来冲击感到无能为力,因此需要从心理建设、社会服务等方面出发促进居民树立主人翁意识,以提升居民在旅游活动中的主体地位。
最后,目的地居民的旅游利益与共享权益未能得以满足。一方面,与其他利益形态相区别的是,黑色旅游目的地一般采用免费形式,目的在于促进更多的人们了解过去,以充分发挥其历史文化、爱国爱家等精神鼓舞价值;此外,黑色旅游的经营主体主要以政府为主导,居民无法获得其他旅游形态的目的地居民所能获取的门票分享利润、旅游服务收入;另一方面,在黑色旅游发展中,只有小部分居民群体以小贩经营的形式直接参与到旅游经营与服务之中,而大部分居民却无法获取与旅游相关的经济利益,且需要承担商贩经营带来的环境责任,进一步刺激了目的地居民对于社区权利的渴望。
2.2 社区增权在黑色旅游发展的作用价值
如表1所示,基于左冰、保继刚总结整理的社区增权四维框架理论,增加了信息增权、教育增权,由此整理出关于社区增权在黑色旅游发展中的主要表现和作用。

表1 社区增权对黑色旅游发展的作用关系
3 战争灾难地黑色旅游发展中居民去权问题
3.1 案例地选择
黑色旅游种类繁多,例如自然灾难式、战争灾难地等。新世纪以来,国内关于黑色旅游的研究主要出现两次高潮,首先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后关于自然灾难式的黑色旅游相关研究;其次是2014年1月27日,国家正式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后,学术界关于博物馆类、纪念馆类等战争灾难地的黑色旅游研究。
本文主要选择战争灾难地黑色旅游目的地的代表之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以下简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该纪念馆主要为纪念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对南京同胞施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行为,成为中华民族抗战记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不仅彰显了国家对战争期间遇难同胞的深切缅怀,也表达了人民奋发图强、追求和平的美好愿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占地面积约10.3万平方米,展陈面积达2万平方米,主要以南京大屠杀现场之一——江东门“万人坑”遗址为基础进行建设布局,景区内陈列有大量独特的建筑、雕塑、历史文物和历史图片,主要包括史诗展、主题展、罪行展三个基本陈列以及两处“万人坑”遗址,通过光、影、声等手段深刻反映出战火纷飞的时代背景下南京人民的反抗暴乱与英勇不屈精神。1997年,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被评为全国首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为国际间倡导和平共处的重要基地;2008年、2010年分别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37],已形成集“还原真相—传播讯息—渲染气氛—培养情怀—宣传公祭”为一体的黑色旅游系统,成为接待国家领导人、外交访客以及国内外观众的主要参观景点。
3.2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黑色旅游发展中居民的去权现状
旅游者前往纪念馆参观战争遗骸并回忆二战期间日军的残暴行径,以满足内心寻求历史、接受警示教育的精神需求。作为国家级4A级景区,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不仅拥有相对完善的硬件配套设施,也能够在充分利用网络资源的基础上强化与游客、文学爱好者、爱国志愿者以及国际友好馆等之间的联系。然而,纪念馆附近的社区居民在黑色旅游活动开展过程中参与程度普遍不高,并对社区内黑色旅游的发展存在较多不满情绪,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2.1 社区居民对旅游开发及自身主体意识认知不足
社区居民对当地发展黑色旅游的认识不够充分,尤其是对黑色旅游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处于较低的层次。首先,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建立在原屠杀遗址的基础之上,社区居民未完全认清黑色旅游开发的重要性,而是出于风水与迷信的考虑对黑色旅游的开发常常闭口不谈,甚至会认为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作为景点开放破坏了纪念馆庄严肃穆的气氛,是一种对战争逝去者的不尊重;其次,纪念馆的教育性、灾难性催生出黑色旅游的公益性特征,因此,馆内主要实行游客免费的制度,居民无法直接获取旅游发展产生的收益,直接影响居民主动参与纪念馆黑色旅游开发与管理的热情与投入;最后,随着人口流动的不断变化,现有居民中有一部分属于外来居民,该部分群体对于其作为社区主体的地位认识不足,导致对当地发展黑色旅游的整体参与程度不强。
3.2.2 社区居民对旅游影响及社区参与权利认知欠缺
发展黑色旅游具有深远的影响,然而当地居民对此的认知与了解并不深。一方面,黑色旅游的开展并非只是与政府外交或是游客参观相关,同时对于世人铭记战争带来的创痛以及渴望世界和平具有突出的现实价值,其社会价值远远超过经济价值;另一方面,游客的涌入所带来的欣欣向荣之景象也会为社区居民带来生活上的困扰,尤其表现在公共交通、生态环境、生活成本等方面。受自身知识水平、旅游知识培训等方面的限制,社区居民既未能充分认识到其在开发黑色旅游中的参与地位,是否通过相应的渠道或平台对黑色旅游的发展建言献策;也未及时认清黑色旅游发展对于其日常生活带来的多重影响,甚至完全置身于周边黑色旅游发展之外。
3.2.3 社区居民的旅游经营及经济权益保障门槛偏低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主要实行的是免费的制度,与景点直接相关的收入主要包括交通收入、餐饮收入、纪念品收入等。社区居民通过纪念馆游客的接待能够获取的经济权益得不到保障,这是因为纪念馆主要实行的免费入馆制度,馆内设有纪念品售卖等,其收益一般用来对场馆的基础维修建设、工作人员工资等,以上也是部分社区居民获得经济收益的主要渠道;此外,纪念馆周边有快餐饮食,主要由个人摊贩经营。此类经营方式虽然为旅游者提供餐饮方面的便利,但是一般为无证经营,准入门槛相对较低,游客在食品安全方面得不到保障,从根源来看不利于经营者长久的经营与管理。
4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黑色旅游发展对策研究
具体来说,社区增权在黑色旅游发展中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4.1 构建社区参与组织体系,保障居民政治地位的提升
社区政治体系的完整程度影响整个社区群体集体利益的被保障程度。社区需构建起以社区居民为主体的专门机构或组织,并通过“负责人轮岗”的形式保证社区成员政治意愿与利益诉求的充分表达以及成员间权利的相互监督。此外,社区组织应采取先进的技术设施构建适用于社区居民参与旅游活动的网络交流平台,社区居民不仅能够通过交流平台向管理者表达自己参与纪念馆黑色旅游开发与管理的政治意愿,并积极投入到纪念馆黑色旅游发展相关政策与规划方案等的编制与修订中,还可以在自身权益受到威胁时寻求组织的帮助,以维护其正常的社区参与权益不受侵犯,保障其社区内部政治地位的稳步提升。
4.2 完善旅游发展盈利模式,满足居民经济利益的诉求
作为重要的爱国教育基地,纪念馆发展黑色旅游主要采取“免费门票”的制度,单纯的旅游活动并不能为社区居民带来经济水平的提高以及生活水准的提升。为了满足居民对经济利益的诉求,社区政府及相关旅游企业应采取相关措施完善旅游景区的盈利模式。一方面,政府与企业应优先安排当地居民特别是位于景区附近的零散商户集中经营、集中管理,保证居民充分参与到黑色旅游活动发展进程并分享旅游业为地方带来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政府应支持、鼓励居民延展旅游产业链长度,开展为游客提供盈利性质的旅游服务项目,如出售鲜花、战争历史图书与影音制品、纪念馆旅游纪念品,提供导游服务、旅游演艺等,增加居民参与到纪念馆旅游发展的就业机会,满足自身经济利益诉求。
4.3 打破传统思维惯性限制,引导居民传统观念的转变
社区发展黑色旅游的同时应当充分考虑社区居民内心情感的需要,逐步引导社区居民打破原有的思维模式,转变固有的传统观念,促使居民主动认识到发展黑色旅游的重要意义,从心理上认同黑色旅游的存在与发展,避免居民在心理上抵制、在情感上孤立、在行为上被动;此外,政府还应增强居民对社区发展黑色旅游的归属感以及依存程度,认识到自身在旅游活动中的关键性地位,积极投入到纪念馆旅游秩序管理、环境监督等工作进程中,提高其主动参与纪念馆旅游业发展的积极主动性。
4.4 发挥社会各界协同作用,促进居民生活质量的改善
社区政府应积极联合旅游企业投资者、非政府组织以及居民等社会各界力量,制定有效应对混乱或缓和矛盾方案,防止大量游客涌入对景区承载容量的压力、对社会交通的巨大负担、对公共秩序的各种破坏等问题的出现,缓和社区居民与旅游发展之间的矛盾;与此同时,社会各界应共同致力于引导居民自豪感、认同感以及凝聚力的树立,例如,将旅游的部分附加收入投入到公共基础设施的完善、教育事业的建设、医疗水平的改进等方面,从而促进居民生活环境的优化、文化水平的提升和社会保障的完善,增强居民在黑色旅游发展中的主体地位。
4.5 扩大公共信息共享范围,重视居民法律意识的培育
旅游公共信息的普及程度、开放程度以及对称程度逐渐成为影响居民参与黑色旅游活动开展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居民整体偏低的文化素质水平影响了对公开信息的理解程度,削弱了居民在信息化社会的存在感,加深了居民对旅游开展的不信任与不认同情绪。社区政府应在黑色旅游活动开展的进程中充分公开与居民切身利益相关的旅游信息,例如,旅游组织构建情况、收入分配情况、组织人员调动情况、旅游规划制定等,促进居民对相关信息的了解与参与程度的加深。同时组织部门及时公布公祭日的活动安排,保证居民对纪念馆大型活动安排的知晓;此外,社区还应当及时公布与居民权利与义务等相关的重要信息,保证居民参与过程中对自身权利与义务的知晓,并能够在权利受到侵犯、权益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学会用法律武器进行自我保护,促进居民维权意识与社区参与意识的逐步形成。
4.6 增加教育事业投入力度,实现居民综合素质的提高
旅游目的地教育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了旅游服务的质量。纪念馆黑色旅游的教育价值要远远大于观赏、游憩或休闲价值,黑色旅游资源所蕴含的丰富历史文化内涵对参与旅游工作的社区居民文化知识水平及专业背景提出较高要求。旅游社区组织机构或部门应在居民主动参与的情况下组织社区居民,尤其是纪念馆服务人员参与历史文化、旅游服务等培训课程的学习,从而促进知识水平与服务技能的提升,提高旅游服务的质量;与此同时,公祭日的确立吸引了大批境外游客的到来,为了满足国外旅游者的服务需求并拓宽国际旅游市场范围,社区可以考虑针对性地挑选并培养一批知识水平高、服务技能好、英语能力强的综合化国际性旅游服务人才,促进纪念馆黑色旅游朝跨区域、国际化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