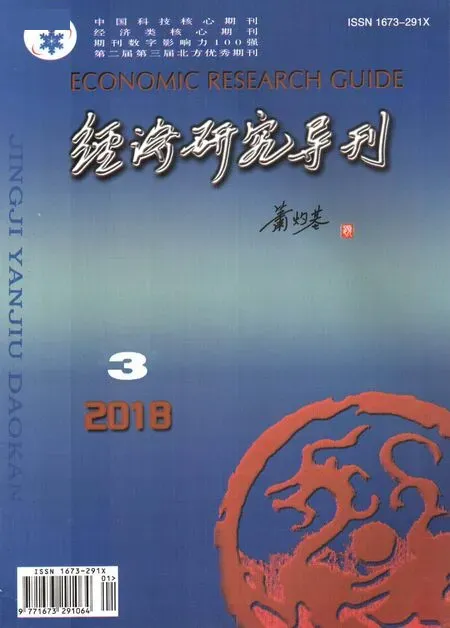明清陶瓷行会与社会组织的利益博弈与互动
梁富新
(黄河科技学院艺术设计学院,郑州 450063)
陶瓷工商业成员与政府、其他社会团体及个人之间存在着极为复杂矛盾甚至对立抗衡关系,这些关系诸如经济税收、政治法律、伦理道德、规则公约、个体与群体利益等关系。行会组织在这些众多的复杂关系之中扮演者十分重要的平衡、调节、斡旋的角色:一方面,它迫于压力和权威而委曲求全甚至不惜损害成员的权益;而另一方面,它又不畏高压和威胁而竭尽全力甚至不惜一切以维护成员的利益。
一、陶瓷行会和官方的博弈与联合
陶瓷行会作为陶瓷工商业成员的集体组织,对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维护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与官方的利益博弈与互动中,行会的集体力量及影响力均优于个人。
余昭林在《余姓独业的挛窑店》的回忆录中载:
“还有一次替陶务局挛窑,他们用武力威胁我们,叫我们早晨在汪家街花鸡公茶馆吃油条。油条吃完后,几个教师傅就回家去了,他们马上派警察把几个师傅强行叫到陶务局软禁起来,为此,我们挛窑店全体工人停工不做,可是有的窑户又急需挛窑,最后又是九窑公会出面调解,请我们出来,陶务局也只好三餐一点照例执行。”[1]
官方组织陶务局无法满足挛窑工人的饮食需求,刻意降低标准,引起公愤而导致挛窑工人罢工。在“九窑工会”的斡旋之下,陶务局最终做出了让步,恢复了挛窑工人原有的饮食标准。“九窑工会”在这一事件中秉承了兼顾公平的原则,既保护了成员的基本权益,又兼顾了需要修窑、补窑窑户的迫切需要。这一事件体现了九窑工会在维护成员合法利益方面的积极作用。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江西巡抚柯逢时上书清政府“关于开办江西瓷器公司陶务奏折”[2]载:
臣周谘博访,查有湖北候补道孙廷林,器识宏通,办事精审,自其先世承办御厂事务,工匠商贾,信服尤深。当即电调来江,与之考察一切事宜,悉能洞中要,其于此事,确有心得,而精核罕有其伦。即经委办瓷器公司,筹拨银十万两,以为之创,余由该道自行集股。据称已得五万金,于三月间,在该镇建设窑厂,招集工人,专造洋式瓷器,必精必良,约计秋间,即可出货。
巡抚柯逢时为推动江西陶瓷市场顺应时代发展,鼓励陶瓷窑户的产品更新,故以官方名义召集陶瓷工商巨贾联合开办“瓷器公司”。其中,孙廷林凭借“其先世承办御厂事务,工匠商贾”对其信任有加(“信服尤深”)的优势,获得了主持制瓷公司筹办的权力。同时,官方对此公司“拨银十万两,以为之创”。由此可以看出,官方对陶瓷工商业发展的支持力度。
同时,此处的“工匠商贾”宽泛地指陶业从业人员,实际上是指陶瓷行业行会的代表人物,如会首、董事、会长等。他们在行会、行帮组织中最具权威和影响力,多数情况下也最具经济实力。景德镇民间陶瓷工商业行会顺应时代所需积极与官方协作承办制瓷公司,体现出其开放与务实的精神。行会与官方的相互合作,对陶瓷产业的发展与行会成员的经济利益意义重大。
二、陶瓷业行会组织内部矛盾的博弈
发展至明清时期,陶瓷业行会的组织种类、体系、制度等都已十分成熟。不同陶瓷行会组织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矛盾与冲突。当利益冲突发生时,行会组织之间会展开各种方式的博弈:或协商调节、或官方裁决。
“九窑公会”属于烧窑业(陶庆窑)与制瓷业(包括四大器等九种陶瓷产品种类)的业主组成的团体组织,清末民初形成,组织成员地域来源绝大多数来自都昌。据《陶庆窑总老板余用正》回忆录载:陶庆窑会首余用正,“在任期内,为烧窑业办了不少实事,其中最突出的一件事,就是为了解决烧窑户与搭坯户之间纠纷,于民国9年(1920年)他代表陶庆窑前往省府南昌打了一场官司。诉讼结果,维护了烧窑业的合法权益,得到烧窑户的拥戴。”[1]
行会组织代表行会成员利益通过官方途径解决不同行会成员之间的利益纷争,从而最大程度上维护本行会组织成员的利益。陶庆窑会首余用正代表陶庆窑(烧柴窑的窑户)与搭坯户到“南昌打了一场官司”,并最终取得胜诉从而维护了烧窑业的合法权益。“九窑公会”在政府组织、民间窑户与挛窑工匠之利益调解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缓冲了各组织之间的矛盾冲突,最大程度上维护了组织成员的利益、窑户的利益。
另据宣统元年(1909年)景德镇湖北书院碑刻关于鄂帮同庆社与华帮之间关于合理商定茭草工工价的碑文记载:
茭草工价碑[2]
据鄂帮同庆社磁商黄春生……牛松记等禀称:伊等在镇贩运磁器,历有年所,于茭草一行,所有茭草扎篾凳价,向有定章,毫无异议。突于今年夏间,茭草工头,不明大义,惟知利己,欲翻旧章加价,两造开具节略,呈请商会,议订草篾皮数,每条凳加钱三百文,两造均各遵允,禀请给示勒石,俾垂久远等情到县。
据此批示外,合行给示,为此示仰该茭草人等知悉:嗣后尔等工价,务须遵照此次商会议订章程办理,不得稍有违背争竞,倘敢故违,一经查出,或被告发,定即拘案严惩。
……
以上所开茭草章程,系两面在商会当面议订,草结照旧不得偷减外,扎蔑悉照开明皮数,自后永为定案,不得偷减翻异。
……宣统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909年)示
实刊湖北书院晓谕
鄂帮同庆社即湖北鄂城人(今湖北武昌鄂城)于景德镇在明末清初建立的瓷商行会组织,茭草行(华帮)则是由为瓷商运输瓷器所需包装器具的制造工匠群体组成的同业行会组织。茭草工头为获得更多利益随意提高原定茭草价格,从而引起同庆社瓷商的抗议。最终,双方在官方及商会调节下制定出双方均认可的茭草工价格。
而从“为此示仰该茭草人等知悉”之官方定语分析,茭草行——华帮之于鄂帮同庆社还是理亏在先,就制定的茭草价格判断,鄂帮在较大程度上维护了本帮的利益,虽然最终“每条凳加钱三百文”,但这要低于华帮单方“加价”的数值。
同治辛未年(1862年)八月由方德荣、胡宏立、陈文辉、吴大四人所立《次色磁器专卖碑》[2],碑文记载景德镇黄家洲各店与湖北马口帮之间为“四色瓷器专卖”权发生争执,最后经官方协商解决。马口帮属湖北汉川人与马口镇人旅景瓷商构成之行会组织,兴起于清代中后期,主要从事瓷器买卖和运输,清末成立“马口公所”。其成员正当瓷器贸易受到“黄家洲各店阻拦”后,讼之兼管窑务的浮梁景德镇分司,最终获得“四色中脚磁器,向来任客各处自行买办。其破烂由黄家洲买卖,何得拦阻滋事”之结果。马口帮在矛盾分歧的解决过程之中所承担的角色十分重要,虽然文中未详尽述说诉讼的整个过程,但最后列述立告示的四人应属于马口帮中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成员,即行会会首或董事。
三、陶业行会组织与社会群体的权利博弈
陶瓷行会与社会其他群体之间存在着极为紧密的关系,或利益相关,或权益相悖。在社会民众、陶瓷工匠与商人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时,陶瓷行会组织会运用其组织力量保障成员的正当利益以及社会群体的合法权益。
乾隆四年(1739年),佛山石湾人霍文升、霍学致、陈植之等人强占“石湾乡土名湾头冈高庙前附近海旁”[3]的港口,严重阻碍了“商民船只湾泊搬运柴米、缸瓦、出入往来,悉由于此。而远近商民又赖以资生贸易”[3]。黎允甫、霍项、潘寿等石湾陶瓷业乡民(会首)据实讼于官府,并获得胜利,立《奉督抚两院大老爷府县太爷饬禁碑志》。
奉督抚两院大老爷府县太爷饬禁碑志[3]
……石湾乡土名湾头冈高庙前附近海旁,向有旷地一所,约税二分零。该乡烧造缸瓦,所需装运瓦泥以及商民船只,藉此湾泊,易于挑运。前朝里民陈通等借称祖坦地脚告承,当有乡民霍项、潘寿等,以冒承官埠(官方渡口)具控。业经前朝按院批行,委勘明白,勒石竖(小木桩),不许告承。嗣因日久法驰,土豪霍冠南等恃强占据,搭盖寮篷,以致蔽塞官埠。复经乡民藿项等赴县具陈,前县涂令批行黄鼎司巡检勘折,各在案……庙前官埠俱系湾泊柴米,停顿缸瓦、泥船以及各项船只,等情。卑职查该处淤积稍宽,而商民船只湾泊搬运柴米、缸瓦、出入往来,悉由于此。而远近商民又赖以资生贸易。今霍文升等希图瞒承筑占,将来任其抽剥取利,竟以屡经断定之案,视为具文,此等奸民不加重惩,无以惩众。应该将首承之霍文升、霍学致、陈植之各于埠前枷号一个月,满日重责三十板,俾该乡附近奸棍各知儆戒,永绝觊觎。……查霍文升等所承沙坦,系归庙管业,崇祀起见,似与冒承归己者有间。况时值减刑,可否从宽。(注:霍文升最终因将霸占商埠所获之利益归入高庙管理而减轻了罪责,由枷号一个月及重责三十板而最终仅受责罚三十板。缘由在于:高庙为石湾民众信奉的最高神氏之一,高庙与佛山灵应祠(祖庙)并昭显赫,崇祯十四年《重修灵应祠记》[3]载,重修祖庙是彰显佛山人忠义之精神的最好例证。霍文升将非法获取之利益用于“彰显佛山人之忠义”上,也姑且是将功补过。故此,减轻了责罚。……
乾隆四年八月十六日乡众里民(人名略)等仝勒石
“石湾高庙前海旁官埠”主要方便于石湾窑业运输制陶所需的土泥、烧窑所需的柴植、以及生产出的缸瓦。此外,官埠也便于商民的各种贸易往来,成为石湾“艺业陶冶”之民赖以生存的重要交通要道。后因霍文升等假借“承筑铺归庙”,将商埠强行霸占。嗣后,豪强奸民在商埠沿岸种植树木、搭盖圈占、寄顿食物,阻碍搬运缸瓦柴泥米谷肩挑出入。石湾陶瓷业因此受害颇巨。故此,黎允甫、霍项、潘寿等“乡众里民”向官方具控,并最终赢得胜利。
据顺治十六年(1659年)《三院严革私抽缸瓦饷示约》载:“南海石湾一隅……居民以陶为业,聚族皆然。陶成则运于四方,易粟以糊其口。”石湾民众借制陶易粟以糊其口,由此陶业是其生活的根本来源。石湾高庙前之商埠则是石湾陶业民众输出缸瓦等陶瓷产品,换回“米谷”的重要通道。如果扼住此海湾通道,即遏制住了石湾陶业民众的咽喉。乾隆四年(1789年)这一案例说明:为了防止咽喉要道被霸占而损害石湾窑户、工匠的利益,黎允甫等以窑业行会组织代表人物的角色向府县、督抚对霍文升的不法行为提请诉讼,并最终如愿维护了行会成员的利益,“甫等伏睹各宪恩惠生灵,万民仰沾德泽,遵批勒石饬禁。”[3]
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藩宪严禁挖沙印砖碑示》[3]载,“石湾东北一带山岗”被“无赖”之人私挖沙土贩卖,导致本乡人之祖茔被挖掘者甚众,且致“露棺抛骨”。石湾有缸瓦窑四十余处,其所制作缸瓦器需用沙土。故此,唯利是图者即在“石湾东北一带山”挖掘沙土以售卖给窑户而从中渔利。为杜绝此处田园坟墓遭受破坏,切断借挖掘沙土以营利的源头。官方禁止缸瓦器窑户在本境采购沙土。无论从生态、农业生产,还是从伦理、信仰方面,缸瓦窑户都应服从官方的“示禁”。缸瓦窑户自觉放弃购买成本较低的本地沙土,而花费较多资财去购买别境沙土,从道义上讲,这正属于一种社会公益行为,即是缸瓦窑户(行会组织)的一种社会赞助行为。
四、陶瓷业行会、官方、个人三者之间的博弈
据《佛山文史资料选辑·陶都石湾》研究,“石湾陶瓷业的‘行’,早在明代嘉靖年间即已成立。至天启年间已有明文的行规。”[4]行规成文标志着行会组织进一步成熟和完善,行会成员对行会组织制定的管理办法、运营机制、奖惩与收徒制度、入会及从业规则、产品规格与售价标准等方面都达成了共识。
石湾窑业于明嘉靖时期始逐步形成成熟的“行会组织”,顺治十六年发生的“三院严革私抽缸瓦饷”事件中,“曾宗瑜等群棍”与窑户廖跃沧联合共同盘剥以姚昌为首的石湾窑户“缸瓦”税饷,导致窑户“万不能堪,是以为之激控”。姚昌于窑户行会中的角色在“示约碑刻”无明确说明,但可合理推测:姚昌是众多窑户公推出的、具有极强领导力和产业影响力的“行首”或“会首”。因碑文中也前后两次重点提及“廖跃沧等以姚昌名字借窑户为名题争剥于后”、“廖跃沧以姚昌名字,借窑户为题,争剥缸瓦一税”,说明姚昌在窑户群体中具备极强的影响力,故此廖跃沧才会借其之名“剥缸瓦一税”。
故此,姚昌向三院控诉廖跃沧、曾宗瑜等违法抽剥窑户缸瓦税之行为,并大获官方支持,从而最终维护了行会成员的经济利益,“合示谕石湾窑户里排乡民人等知悉:缸瓦税饷今奉三院宪批,永行禁革,尔等各宜安生乐业”。但最终对于廖跃沧、曾宗瑜二者的处罚结果是:“既经督、抚批革,姑不追究,嗣后永不许窑户、商人告承”,由此可以看出,在行会、官方、社会其他群体的矛盾关系之中,官方的权威地位不可撼动。
附:三院严革私抽缸瓦饷示约[3]
……顺治十六年二月十五日奉钦差巡抚广东部院董批;本司呈详,兹得生业者,民命之攸系也……南海石湾一隅……居民以陶为业,聚族皆然。陶成则运于四方,易粟以糊其口。官司量其船之大小,薄征其税,以抵正赋。听其自输自卖,属税司稽核之。而公务取用照例办应,此章程也。鼎革之际,奸民出为承饷之举,民斯因矣。况狼戾之徒非法横取,不可枚举,如曾宗瑜等群棍是也。……姚昌等万不能堪,是以为之激控。……缘由,蒙批:缸瓦为民间日用微小之物……借此承饷,实为害民。曾宗瑜等以罗兴名字指承饷为名横抽于前,廖跃沧等以姚昌名字借窑户为名题争剥于后,总属假公济私,回详洞见其隐矣……廖跃沧以姚昌名字,借窑户为题,争剥缸瓦一税,俱经本部院拟革,以符功令矣……
五、结论
明清陶瓷行会在复杂的社会组织关系之中为了维护组织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良好的社会形象,他们会巧妙地运用组织力量、官方权威、社会规则等手段与其他社会群体展开博弈与互动,进而最终推动陶瓷业的发展。
[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景德镇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景德镇文史资料:第10辑(余姓独业的挛窑店)[M].景德镇:乐平市印刷厂,1994:56-86.
[2]熊寥.中国陶瓷古籍集成注释本[M].南昌: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233-244.
[3]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古代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广东省佛山市博物馆.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15-125.
[4]佛山市政协文史组佛山市史志编集办公室.佛山文史资料选辑·陶都石湾[M].佛山:内部资料,1982:2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