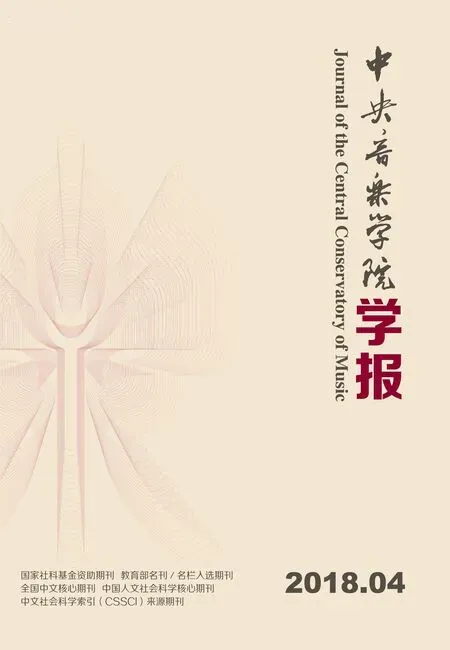曾侯乙编钟是否有“—曾体系”之验证
黄大同



曾侯乙钟的十二音位系列,可以用田野号中层三组低起四钟,衔接中层二组低起五钟、列为图式……[注]该图此处略,见下文。黄翔鹏:《曾侯乙钟、磬铭文乐学体系初探》,《音乐研究》,1981年,第1期,第37—38页。




上方大三度音徵羽宫商基础音↑徵↓↑羽↓↑宫↓↑商↓下方大三度音徵曾羽曾宫曾商曾

1.四个阶名是“四个基本阶名”,这加入“基本”一词的表述,是后来学者们简称其为“四基”的最早出处;
2.四个基本阶名的先后排列,因具有三分损益关系而呈现出宫—徵—商—羽的损益相生序,并不是黄文所说由低到高的徵—羽—宫—商这一音阶的音级序;
4. “曾”是“角”的再上方大三度,不是黄文所说在基本阶名的下方大三度位置。
现把李文相关内容用表格表示如下:
表2.李文“四基”与变化音名的构成关系表

再上方大三度音宫曾徵曾商曾羽曾上方大三度音↑宫角↑徵角↑商角↑羽角基础音↑宫↑徵↑商↑羽
图1.李文的曾侯乙编钟新旧音阶示意图[注]李纯一:《曾侯乙编钟铭文考索》,《音乐研究》,1981年,第1期,第67页。


1986年,黄翔鹏先生在《中国传统音调的数理逻辑关系问题》[注]黄翔鹏:《中国传统音调的数理逻辑关系问题》,《中国音乐学》,1986年,第3期。一文中,提出了“钟律音系网”概念,与此同时,又以“中国传统理论中,宫音是很重要的。按三分损益法,它是生律法的起点。上五度出来一个‘徵’……在曾侯乙钟中,宫商徵羽音是最基础的四个音”[注]同注,第9页。的认识,调整了“四基”原为徵、羽、宫、商的表述顺序,并再次强调其“体系”以宫为首的四个基础阶名与“四”“四曾”的关系:“叫做“曾”的是本名的下方大三度,叫做“甫页”的是本名的上方大三度。”[注]同注,第10页。接着他还否定了李纯一先生关于“曾”的观点:“钟铭的解释中,有种说法:什么叫做曾,曾就是两次的。这是不对的,两次的不等于曾,在律学上这是两回事,音的性质不同,两个方向”[注]同注。。

二、从曾侯乙编钟的两种十二音结构形态看“—曾体系”
然而,周代乐人是否真的在曾侯乙编钟上,设计了这种“体系”的十二音生成方式?编钟各套甬钟、钮钟的完整音列里,是否确实存在这种“体系”的十二音结构形态?问题的提出首先基于这样的疑惑——黄先生提出的“体系”是指编钟上的十二音组织与其生成方式,而在编钟钟铭上,能找出来的、十二音齐全的音组织只有两种:一种是由十二个音名的命名规律而表现出来的,另一种是由十二个音名与一钟两音的结合所形成的;前者是后者的形成基础,是一种十二音的理论形态,后者是前者与一钟两音的结合,是一种十二音的钟体形态。它们都以十二音为整体结构单位,但似乎都与“体系”十二音的结构形态不相吻合。现让我们对其作出逐个分析,看看它们的生成形态是否与“体系”十二音相符。
1.由音名命名规律表现的理论十二音
就如学者们早已指出的那样,从音名的命名规律角度看,编钟的十二个基本音名可分为4个三音组:宫、宫角、宫曾的宫三音组,徵、徵角、徵曾的徵三音组,商、商角、商曾的商三音组和羽、羽角、羽曾的羽三音组。在这些分组音名中,宫、徵、商、羽是4个基础音名,被称为“四基”,另外8个音名是这4个基础音名分别与“角”以及“曾”组合而成,被称为“四角”与“四曾”。这样,在“四基”是一个具有连续四五度进行之序列的前提下,它们的“四角”之间和“四曾”之间的依次顺序,也就无疑与“四基”一样,有一个宫→徵→商→羽的横向四五度音程进行序列。这就意味着:其一,在由4个“基—角—曾”三音组组成的十二音形态之中,这些三音组各自的“基”之间、各自的“角”之间和各自的“曾”之间,都必然具有宫→徵→商→羽的横向四五度音程进行关系;其二,若我们把这4个“基—角—曾”三音组内的三个音,按它们各自所具有的横向四五度音程关系加以对应,该4个“基—角—曾”三音组的整体音高关系,就呈现出一个纵横交织的十二音立体形态。
图2 .以横向四五度和纵向大三度音程关系交织而成的十二音立体形态图

从图2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这种以四五度音程关系为横向纽带的纵向4个三音组排列样式,就是“四基”“四角”和“四曾”这3个四音组作依次纵向大三度叠置的产物。即该十二音立体形态在音程关系上,既可以从横向角度看——那就是“四基”、“四角”和“四曾”的3个四音组;又可以从纵向看——那就是音律设计者通过音名取名所强调的、组内音程关系为连续大三度的4个三音组。两者的区别只是“横看成岭侧成峰”一类的视角纵横转换![注]就如我们在论述十二律的音程关系时,除非与律学研究有关,一般不涉及所述音程究竟是属于三分损益律、纯律还是十二平均律的律制问题一样。此处也只从音程关系角度着眼,不涉及十二音的两种形态关系有没有“律制”的区别问题。“音程”与“律制”是两个主题,属两个研究视角,曾侯乙编钟的“律制”问题需另文探讨。
这种3个四音组与4个三音组的排列样式可以互转的现象,可以让我们运用对等关系推理来作出如下判断:
既然上述3个四音组之间具有一种连续四五度交替进行的相生关系,它们的先后次序是“四基”→“四角”→“四曾”。
而“四基”→“四角”→“四曾”的依次纵向叠置,就是4个三音组——宫三音组、徵三音组、商三音组和羽三音组的立体呈现样式,即“四角”位于“四基”的上方大三度,“四曾”位于“四角”的上方大三度。
那么,按音名命名规律分为宫三音组、徵三音组、商三音组和羽三音组的曾侯乙编钟音名十二音,就必定是以“四基”为低音,“四角”为其上方大三度、“四曾”为“四角”上方大三度的十二音立体结构形态,并且在“四基”“四角”和“四曾”之间的大三度音程生成顺序上,也必然具有由低到高的“基→角→曾”这种“叠角式”纵向建构关系。这与以“四基”为中心,分别向上方、下方大三度生成“四角”和“四曾”的“体系”之说相比,在大三度音程的生成方向与整体十二音结构形态方面的表现完全不一样。
2.由理论十二音与一钟两音结合产生的钟体十二音
在得出编钟以音名表现的理论十二音,不是“体系”形态样式的认识后,我们再来看在编钟各套甬、钮钟音列中的十二音实践存在形态——理论十二音与一钟两音结合而产生的钟体十二音,是否与之相符。事实上,黄先生提出这一概念的证据,也正是来自编钟中层甬钟的一钟两音音列。
通过对64件两音钟的正侧鼓音与音名配置关系的梳理,可以发现,编钟音律设计者把十二个音名分配到大小三度的一钟两音正侧鼓音上时,遵循着以下两条原则:
一是把所有的大三度钟,都配以宫、徵、商、羽四个三音组中的、某一组的两个组成音(由加粗黑体字表示同组),如宫、商三音组都是同组的“角—曾”——[宫角—宫曾〗和[商角—商曾〗(请注意这里没有“基”——“宫”和“商”),而徵、羽三音组都是同组的“基—角”——[徵—徵角〗和[羽—羽角〗(请注意这里没有“曾”——“徵曾”和“羽曾”)。
二是除构建音阶所用的[羽—宫〗小三度钟以外,把其余所有小三度钟,都配以分属一对含有四五度相生关系的“宫—徵”或“商—羽”三音组的组成音(由加粗黑体字表示四五度关系组),如[宫—徵曾〗、[商—羽曾〗以及[宫曾—徵角〗、[商角—羽〗等。
为什么要这样配置音名?其目的是什么?若从中下层各组音列中的2个大三度钟和1个小三度钟以“一横两纵”的组合模式,以及上层二、三组音列中的3个小三度钟以“三横纵叠”的组合模式,恰好能互相弥补、丝丝入扣地形成一对三音组的结果,来运用因果关系推理法倒推其原因,可知那是当时音律设计者用这样的配置方案,来使3个一钟两音构成三钟六音的组合,并进而以2个三钟六音组合的相加,来形成曾侯乙编钟主体的六钟十二音结构形态。[注]详见黄大同:《基于一钟两音的曾侯乙编钟十二音结构形态(上)》,《中国音乐学》,2017年,第4期,第29—31页;《基于一钟两音的曾侯乙编钟十二音结构形态(下)》,《中国音乐学》,2018年,第1期,第47—49页。
如中层二组无枚甬钟的音列,具有前半为十二音区域和后半为音阶区域的二分布局(见下文表3)。其十二音区域以“中二12”的“商D4”为最低音,并且在该组无枚甬钟十二音区域音列的第一个八度中,“宫”位于最低音“商D4”的上方小七度。在这里,音律设计者是以“一横两纵”方式,即1个小三度钟的正侧鼓音(“一横”——“宫—徵曾”/“商—羽曾”),分别与2个大三度钟(“两纵”——“宫角—宫曾”与“徵—徵角”或“商角—商曾”与“羽—羽角”)进行结合,使无枚甬钟以两对三钟六音的组合,构成两对三音组——“商—羽2”+“宫1—徵”[注]本文用下标数字表示三音组转位,不标数字为原位:下标1为第一转位,如宫1;下标2为第二转位,如徵2。的十二音立体结构形态(见图3左)。
又如上层二、三组陶纹钮钟都是小三度钟,其中上层二组音名属于“商—羽”三音组类,上层三组音名属于“宫—徵”三音组类,并以“上三1”的“宫#F4”为最低音。在这里,音律设计者是以“三横纵叠”方式,即3个小三度钟的正侧鼓音(“三横”——“宫—徵曾”“宫角—徵”“宫曾—徵角”/“商—羽曾”“商角—羽”“商曾—羽角”),进行纵向结合(“纵叠”),使陶纹钮钟以两对三钟六音的组合,构成两对三音组——“宫—徵2”+“商—羽2”的十二音立体结构形态(见图3右)。
图3.无枚甬钟、陶纹钮钟的两对三音组构成图

但不论是“一横两纵”还是“三横纵叠”的组合,两者在音程方面的呈现是完全相同的。如从横向角度看,“一横两纵”式除了“一横”的小三度音程关系外,其余“两纵”之间的横向音程关系也是小三度,等于“三横纵叠”的三个横向小三度;而从纵向角度看,“一横两纵”式也好,“三横纵叠”式也好,它们都是由三钟六音组合形成的成对三音组形式,其三音组内的音程关系由连续两个纵向大三度进行而构成。
由于钟体十二音是以2个三钟六音组合的两对三音组形式出现,而在一钟两音的横向小三度勾连下,含有四五度相生关系的成对三音组的排列样式,一定是前原位的宫、商三音组接后第二转位的徵、羽三音组,或是前第一转位的宫三音组接后原位的徵三音组。如中下层三套甬钟的钟体十二音是“商—羽2”+“宫1—徵”,上层钮钟十二音是“宫—徵2”+“商—羽2”。这样,尽管在编钟钟体十二音的成对三音组中,后一个三音组常出现“曾”为下,“基”为中,“角”为上的“曾—基—角”排列样式,但由于前一个三音组不是“基—角—曾”原位,就是“角—曾—基”第一转位,没有出现“曾—基—角”第二转位,而后一个三音组有时也不是第二转位,而是因前三音组是第一转位而使后三音组必然是原位样式,如“宫角—宫曾—宫”接“徵—徵角—徵曾”。这种必然导致的结果表明了两点情况:
其一,因成对三音组都是原位接转位或转位接原位,这是钟体十二音来自以原位三音组排列的音名十二音与一钟两音结合的佐证之一,因此其成对三音组内的两个大三度音程的构建方式,应以原位为标准,按由低到高的纵向方向来分析。

编钟的主体部分,由中下层组的长枚、无枚、短枚甬钟和上层二三组的陶纹钮钟组成。在这些甬、钮钟的完整音列中,以十二音为结构单位的只有由“一横两纵”(甬钟)和“三横纵叠”(陶纹钮钟)这两种三音组组合方式为基础构就的六钟十二音结构形态,除此之外再无别的十二音整体呈现样式[注]上层一组6件无纹钮钟所透露出来的音组织,是一种与中下层组和上层二、三组完全不同的八钟十二音结构。由于黄翔鹏先生的“体系”内容,只与中下层组的编钟音列有关,并且它们的一钟两音也构不成完整的音列,因此本文不把上层一组6件散钟列入讨论范围。,因此上述对理论十二音与钟体十二音的分别剖析,都明确导向同一个结论,即在编钟全部的甬、钮钟完整音列中,没有这种“体系”的十二音构建方式,也找不出一个具有完整十二音的“体系”音结构形态。于是一个疑问油然而生——黄翔鹏先生之所以提出此说,必然有他的道理,有他的依据,那么他究竟是依照什么证据,来作出编钟有此“体系”十二音组织的判断呢?
三、从黄文的证据看“ —曾体系”


然而令我大吃一惊的是,示意图上的这一音列,竟然不是曾侯乙编钟长枚甬钟中层三组音列的真实记录,而正如黄先生自己介绍,这是两套甬钟音列片段——“中层三组低起四钟,衔接中层二组低起五钟”的人为“衔接”产物。也就是说,他在中层三组的10件长枚甬钟中,抽取了其中的“中三10”“中三9”“中三8”与“中三7”这4件两音钟音列;同时又在中层二组12件无枚甬钟中,抽取了从该组第二件“中二11”起至“中二6”的6件两音钟音列,然后再把这分属不同形制编钟的两段甬钟音列,按音高顺序拼接在一起,用以组成论证该“体系”十二音组织之存在的新音列(见表3长枚甬钟和无枚甬钟的灰底部分)。

音列布局十二音区域音阶区域长枚甬钟下二4下二3下二2下二1中三10中三9中三8中三7中三6中三5中三4中三3中三2中三1侧鼓音F3羽曾#G3宫曾#A3商曾B3徵角#C4羽角bE4徵曾F4羽曾G4徵C5宫F5羽曾G5徵#A5商曾C6宫正鼓音D3商E3中镈#F3商角G3徵A3羽C4宫D4商E4宫角A4羽D5商E5宫角#F5商角A5羽无枚甬钟中二12中二11中二10中二9中二8中二7中二6中二5中二4中二3中二2中二1侧鼓音F4羽曾#G4宫曾#A4商曾B4徵角#C5羽角bE5徵曾F5羽曾G5徵反C6宫反F6羽曾G6徵反C7宫反正鼓音D4商E4宫角#F4商角G4徵A4羽C5宫D5商E5下角A5少羽D6少商E6角反A6羽

但是在长枚甬钟中层三组音列中,缺少宫曾,只有徵曾bE4(中三8侧鼓音)、羽曾F4(中三7侧鼓音)和商曾#A5(中三2侧鼓音)这3个“曾”。由于徵和羽这两“基”位于这一段音列的低音部位,而“商曾”位于这一段音列的第二高音位置,所以若按曾侯乙编钟的八度分组规范,“中三8”侧鼓音“徵曾bE4”、“中三7”侧鼓音“羽曾F4”与“中三2”侧鼓音“商曾#A5”这三“曾”,必然只能被分析为“中三10”正鼓音“徵G3”的上方增五度、“中三9”正鼓音“羽A3”的上方增五度以及“中三4”正鼓音“商D5”的上方增五度(见表3上半部分),即它们都不在“叫做曾的是本名的下方大三度”的音高位置,它们与其“基”和“角”,只能共同形成如下3个“基—角—曾”原位三音组样式:
[徵G3—徵角B3〗 +徵曾bE4
[羽A3—羽角#C4〗 +羽曾F4
商D5+ [商角#F5—商曾#A5〗
这就意味着,暂且不说中层三组缺少宫曾的问题,仅若遵循曾侯乙编钟钟铭中所明确的八度分组规范,中层三组音列中的3个“曾”是其“基”下方大三度音的可能性就为零。
先把“中三6”侧鼓音“徵G4”作为中心音“基”,并把“中三8”侧鼓音“徵曾bE4”划作它的下方大三度“曾”;再把“中三5”正鼓音“羽A4”作为中心音“基”,并把“中三7”的侧鼓音“羽曾F4”划作它的下方大三度“曾”。






结 语
黄先生并没有任何隐瞒,在文章中他明确告诉读者,他判断曾侯乙编钟有“体系”十二音生成形态的证据,来自他自己对长枚甬钟中层三组的音列片段与无枚甬钟中层二组的音列片段所作出的“衔接”。坦诚地讲出自己的证据来自自己的“衔接”之举,足以证明他绝无主观伪造证据的动机。有许许多多的例子包括我自己向他请教的亲身经历,可证黄先生的学术人格和师德之高尚,绝非常人可以企及。但在这里,他以自己拼接的音列为证据来证明自己学术观点的情况,却就是这样真实地发生了。怎么解释他这一不可思议的行为呢?
从研究的思维角度分析,他应该是把研究初期发现的、还未经检验的“线索”,等同于经过“小心求证”后确认的“证据”,并把因“线索”触发灵感而在头脑中浮现的、属于主观意识的“大胆假设”,等同于对事实证据认定后得出的客观结论。因而他可能会这样认为:既然钟铭有证据(实为线索),结论已得出(实为假设),那么为方便读者的阅读与理解,把分散的证据现象组合起来呈现也无妨。然而,此举事实上造成了以自编“证据”来求证自己主观假设的结果,那么得出的结论就无法属于历史“发现”,而只能属于当代“发明”。

通过曾侯乙编钟两种十二音与“体系”的结构形态比对,通过以“曾”为低音的“曾—基—角”三音组与六钟十二音结构的关系梳理,以及通过对“体系”证据的剖析,本文得知:


第三,如同对案件的判决必须依赖事实确凿的证据,学术观点的提出也必须以客观真实的证据认定为前提,但黄翔鹏先生自己在文章中所说,他的“体系”证据,是他把长枚甬钟和无枚甬钟的各自音列片段抽取出来,再作出拼接的人为产物。“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且不论曾侯乙编钟十二音组织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结构形态,仅凭这一“证据”来自他自己的编创,以及即使是这编创的“证据”依然十二音不全的现象,就足以说明以十二音为结构单位的“体系”之说能否成立的问题了。


——史蒂芬·哈特克《列队》的音高组织方法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