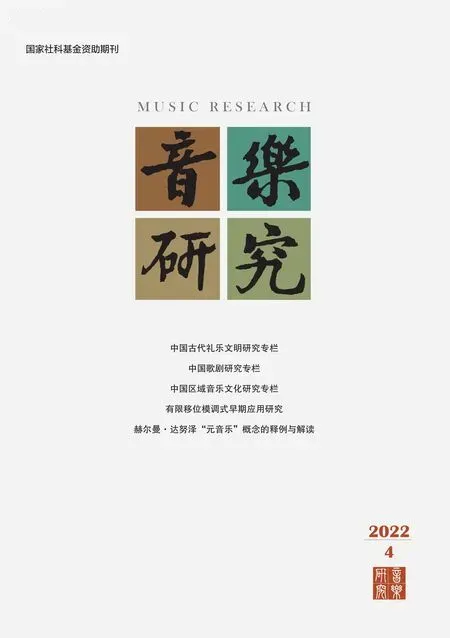论中国传统唱腔的腔音列原生性差异
文◎马志飞
我国传统唱腔①这里的“传统唱腔”,是指戏曲、曲艺、民歌等歌唱的传统曲调,包括腔词关系、唱腔体式、演唱方法、旋法、调式、润腔等构成要素,具有地域性、民族性、多元化等特征,在腔系分布上具有内在的相通性和关联度。的地域特征十分明显。影响我国传统唱腔形态的核心要素有很多,其中,“腔音列”决定着唱腔的音调框架和旋律走向。典型性腔音列②典型性腔音列,是指唱腔中能够体现某种地域、民族、乐种风格的腔音列,往往具有标志性的形态走向和特定的审美情趣。为唱腔展开提供了“乐之框格”,各种色彩性乐汇、润腔技法等在此基础上发展变化,从而产生各种音色变化和“色泽”呈现。本文着眼于腔音列原生性差异在唱腔形态中的重要意义,意图探索我国传统唱腔地域差异的内生性基础。
一、唱腔谱系分布的腔音列基础
考察我国传统唱腔的地域分布,典型性腔音列从北往南大体呈现递减趋势,突出表现为从北方的超宽腔音列、宽腔音列,到中部的大腔音列,再到南方的小腔音列、窄腔音列,直至近腔音列的缩减式分布。
(一)北方音乐区
主要包括北方草原支脉、关东支脉在内的中国北方及东北地区,唱腔形态表现为:超宽腔音列和宽腔音列为旋律展开特色,以四度以上的大跳音程为标志,突出豪迈奔放的风格。例如,秧歌调《正对花》③谱例见《中国民间歌曲集成·辽宁卷》,中国ISBN 中心1995 年版,第514 页。本文所用谱例中,典型性腔音列三个音所形成的前后两个音程的关系,用数字标注,谱例中数字代表音程度数,“6”即六度,“2”即二度,下同。,典型性腔音列是“——”(原位集合[0,2,8]④福特的音级集合理论,对于中国传统音乐的唱腔结构及音高关系分析,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的音级集合命名方法为:先将腔音列的3 个音从低到高排序(原位),以最低音起始,标记为0,第二音、第三音与它的音程距离所包含的半音数量,即为它们各自的标记数字。)的逆行,在每一乐句句末出现;由“—”的六度下行造成活泼欢快的效果,然后稳定下行到,形成一种模式化的终止式。
笔者对该地区代表性剧种唱腔进行初步分析统计:《中国戏曲音乐集成·黑龙江卷》收录龙江剧55 段唱腔,有43 段包含典型性超宽腔音列(78%),以“——()”最为典型;《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吉林卷》收录吉剧44 段唱腔,有32 段包含典型性超宽腔音列(73%),以“——”最为典型;《中国戏曲音乐集成·辽宁卷》收录辽南戏63 段唱腔,有37 段包含典型性超宽腔音列(59%),以“——”最为典型。
(二)华北音乐区
再以评剧为例,《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北京卷、天津卷与河北卷共收录192 段唱腔,其中采用典型性宽腔音列的唱腔有135段(70%)。其他宽腔音列在本地曲目中也有一定影响,如山东成武县民歌《包楞调》的典型性腔音列“——”([0,5,7]),突出“—”上行四度;河北梆子的徵调类唱腔中,以“—”上行四度音程为核心的宽腔音列最具代表。
(三)西北音乐区
唱腔以“宽腔音列”为典型性腔音列,主要分为两类。(1)以“徵”为基音的宽腔音列“——”([0,5,7]),调整结构而形成双四度框架“——”([0,5,10])或重复基音而形成“———”([0,5,7,12]),多见于以苦音见长的徵调式唱腔中。(2)以“羽”为基音的宽腔音列“——”([0,5,7]),调整结构而形成双四度框架“——”([0,5,10])或重复某音而形成“———”([0,5,7,12]),在欢音风格唱腔中常与“——”结合使用。例如,《脚夫调》以宽腔音列“——”为主体,形成“———”的双四度框架(原型);后半部分由于腔音列的调整变化(4-4),导致句末出现这一双四度框架的移位。
《中国戏曲音乐集成·陕西卷》收录秦腔唱段81 段,其中,突出第一类的唱段有51 段(63%);突出第二类的唱段有7 段(9%);二者相结合的唱段有23 段(28%),“——”在唱段中独立出现的次数很少,似与西北音乐擅长表现激越悲苦因而弱化其羽调色彩有关。
(四)中原音乐区
主要指黄河中下游地区,以中州支脉为主体,涵盖部分江淮支脉及齐鲁支脉的音乐,以大腔音列为代表。典型性腔音列是:(1)以“宫”为基音的“——”([0,4,7]),“—”起到基础结构作用,典型唱腔形态是其逆行;(2)以“徵”为基音的“——”([0,4,7]),“—”构成腔音列的发展基础,典型唱腔形态是其逆行;(3)以“商”为基音的“—♯—”([0,4,7]),由于“变徵”(♯)不稳定,常与相结合,形成附加四度音的音列“—♯——”。例如,豫剧《花木兰》中的《谁说女子不如男》,典型性腔音列是“——”,突出“—”的大三度进行。再以《中国曲艺音乐集成·河南卷》收录的45 段河南坠子唱腔为例,突出第一类的唱段有13 段(29%),第二类的唱段有10 段(22%),第三类的唱段有3 段(7%),复合性唱段19 段(42%)。
(五)江南音乐区
主要指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音乐,兼及上游的巴蜀支脉,典型性腔音列大致分为:(1)以“徵”为基音的窄腔音列“——”([0,2,5])及其转位;(2)以“羽”为中心的窄腔音列“——”([0,3,5])和小腔音列“——”([0,3,7])及其转位。两类腔音列均突出小三度音程进行。例如,昆曲唱腔《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以“——”和“——”为典型性腔音列;在共计47 小节的唱段中,前者出现14 次,后者出现15 次,兼以“——”“——”等腔音列,均突出“—”或“—”的小三度进行。再以《中国民歌》⑥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中国民歌》(一至四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1985 年版。中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湖北、湖南六省的196 首传统民歌展开分析(见表1)。

表1 江南民歌腔音列频次分布表
(六)西南音乐区
主要包括滇桂黔支脉,兼及巴蜀支脉音乐和青藏高原支脉,典型腔音列是窄腔音列、小腔音列和近腔音列,旋法突出小三度、大二度的进行,调式以羽调式、徵调式居多。如贵州省惠水县的布依族山歌《好花红》⑦谱例见《中国民间歌曲集成·贵州卷》,中国ISBN 中心1995 年版,第636 页。,典型性腔音列为“——”([0,3,7]),第1 乐句开始为其转位形式,突出“—”四度和“—”五度进行,穿插出现音(经过音、倚音、辅助音方式),形成从属性的近腔音列“——”(第2、3 小节),以大二度的上下级进为主;句末突出“—”的小三度进行。再以黄庆和《 云南民间歌曲选》⑧音乐出版社1957 年版。中的153 首民歌展开分析(见表2)。

表2 《云南民间歌曲选》腔音列频次分布表
(七)华南音乐区
主要指五岭以南的粤海支脉音乐,涵盖了广东、海南、广西东南部等地区,唱腔特点是:(1)以近腔音列“——”与“——”([0,2,4]),中近腔音列“——↑”([0,2,3.5⑨这里的“3.5”,是指到↑的音程距离,由于微升,故以此标注;其后的“1.5”“5.5”等也采用此法标注。])与“↓——”([0,1.5,3])为特色;(2)助音式中立二度,如“—↑”“↓—”之间的辅助式进行,其间距为3/4 全音,由于↓、↑、↓等中立音的出现,使得腔音列“——”“—↓—”“↑——”“——”等发生了腔式及音色变化;(3)小腔音列(——)也较常见,并辅以大跳的跨越型旋法(—,—,—,—,—等)。例如,广东惠东县的《好君要有好娘配》⑩谱例见《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广东卷》,中国ISBN 中心2005 年版,第703—704 页。,典型性腔音列是“——”,辅以“——↑”和“——”,这里的“”微升,与“”构成中立二度,间或出现“—”四度大跳。笔者选取《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海南卷》中的402 首黎族民歌,分析统计得出:近腔音列为主的歌曲有137 首(34.5%),中近腔音列为主的歌曲33 首(8%),小腔音列为主的歌曲33 首(8%),复合型歌曲36 首(9%),其他163 首(40.5%)。
综上,笔者尝试对作为唱腔框架基础的典型性腔音列及其特性音程进行编码,如表3 所示。

表3 典型性腔音列的音级集合表
据表3 初步得出结论:(1)典型性腔音列的音位数差和核心音程数差由北向南逐渐收窄;(2)腔音列的分布没有明确边界,而是逐渐过渡,一个音乐区的音体系往往包含1—3 个典型性腔音列,其中特性音程的音位并不固定;(3)高纬度地区的音调,以大跳音程和迁跃式的腔音列为基础,低纬度地区的音调,以小跳、级进音程和舒缓式的腔音列为基础。
这种呈递性的分布规律,具有标识唱腔风格的核心作用。乔建中先生指出:“当环境不断陶冶人的审美爱好时,审美趣味也必然对人的歌唱、演奏活动产生种种潜在影响。使他们喜欢这样的音调而舍弃另一种音调;选择这种唱法而淘汰另一种唱法等。久而久之,地域性的‘音乐特质’就会得到集中、提炼,并愈发鲜明。最后形成某种‘审美定势’。”⑫乔建中《音地关系探微——从民间音乐的分布作音乐地理学的一般探讨》,载乔建中《中国音乐学经典文献导读·中国传统音乐》,上海音乐出版社2009 年版,第403 页。

表4 腔音列谱系分布表
二、腔音列的“宽化”与“窄化”:原生性差异的核心驱动
腔音列的原生性差异,是形成唱腔形态特征的主要驱动,主要体现在典型性腔音列的不同。(1)原生腔音列,是当地人民经过长期审美选择而形成的音调结构序列,具有早发性和历史延续性。(2)继生腔音列,是其他腔音列传播至本地区后,经本地人民高度认可而内化于本地音体系。“典型性腔音列一旦形成,将具有民族、地域、乐种、流派的代表性意义,用来改造它们所吸收容纳的其他曲调。”⑬王耀华《论腔音列(下)》,《音乐研究》2009 年第2 期,第29 页。继生腔音列会通过与原生腔音列的深度互融实现本土化,构建起“原生—继生”型的复合唱腔体系。“继生腔音列”的迁入,主要有两种途径:宽化和窄化,具体手法有转位式、并置式、互融式、附加音式等四种。
(一)较窄腔音列的“宽化”
当“继生腔音列”的特性音程数差比“原生腔音列”的特性音程数差较窄时,会通过“宽化”手法扩大特性音程数差,使之等于或大于“原生腔音列”的特性音程数差,即将“外生腔音列”中的三个音级转位,出现新的宽音程并有意强化之,对接“原生腔音列”的特性音程,从而改变原有的音调旋法和风格。
“宽化”主要发生在北方地区,是将窄腔音列、大腔音列、小腔音列“宽化”处理,变为突出四度及以上的大跳音程,使平稳的旋律变得更加跳动活泼(见谱例1)⑭《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吉林卷》,中国ISBN 中心2000 年版,第327 页。。

谱例1 《丢戒指》(徐雅秋唱,那炳晨记谱)
在华北音乐区,“宽化”的处理大多对标宽腔音列,主要强调旋法中的四度进行。例如,京剧《捉放曹》⑮《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北京卷》,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第355—357 页。中的一段唱腔,窄腔音列“——”,转位后出现“—”上行四度;大腔音列“——”以级进为主,但到第4 小节出现了“—”四度跳进。窄腔音列“——”转位后,出现了“—”下行四度跳进。
“宽化”主要发生在腔音列由南到北的传播过程中,随着特性音程的逐渐扩展,原有的调式音级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徵色彩逐渐加强。
(二)较宽腔音列的“窄化”
当“继生腔音列”的特性音程数差比“原生腔音列”的特性音程数差较宽时,会通过“窄化”手法缩小特性音程数差,使之等于或小于“原生腔音列”的特性音程数差。“窄化”主要发生在南方音乐区,北方的超宽腔音列、宽腔音列、大腔音列传播至此地后逐渐“窄化”,处理方式有两种:并置式和加附加音,使腔音列中的特性音程变窄,对接“原生腔音列”的特性音程,从而改变原有的音调色彩。例如,晋州小调《反对花》⑯《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河北卷》,中国ISBN 中心1995 年版,第434—435 页。,上句第1 小节为窄腔音列“——”,突出“—”四度跳进,接着是窄腔音列、近腔音列,直到下句句末才出现超宽腔音列“——”的逆行,与前面的窄腔音列形成“舒缓—跳跃”的音程分布。其后的发展大体循此。综合来看,由于较窄腔音列比超宽腔音列所占比例更大,减缓了超宽腔音列带来的跳跃性冲击,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窄化”。
江南地区在历史上长期与北方地区频繁交流,因此,其唱腔体系受到了北方音乐较大影响,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宽腔音列在江南音乐作品中的迁入和融合,通过诸多手法实现“南方化”。例如,昆剧中的一首北曲曲牌【点绛唇】,通过添加附加音而出现窄腔音列,以弱化宽腔音列的北方风格。
“窄化”主要发生在典型腔音列由北到南的传播过程中,随着特性音程的逐渐缩小,原有的调式音级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羽调色彩逐渐加强(羽角化——王耀华语)。除了以上分析,从梆子腔向南方传播导致宽腔音列被四川扬琴、潮州音乐、广东音乐等吸收改造,以及《老八板》在诸多乐种中的腔音列变化,都可以看到这一现象,表明“窄化”在唱腔的结构层次和调式色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腔音列变化与唱腔形态之应变
由以上分析可知,典型性腔音列既具有稳定性,也具有可变性。“继生腔音列”在进入某一音乐区的初期,经由本地人群的审美选择而与“原生腔音列”相互对接或融合,甚至演化为新的“原生腔音列”,从而内化于本地的唱腔体系当中。可见,原生腔音列与继生腔音列之间的关系不是绝对的,某一地区的音调体系放在历史长河中看是阶段性的。
唱腔形态一般包含典型性腔音列和若干个辅助腔音列。典型性腔音列所框定的音调骨架及其中的特性音程,是构成唱腔风格的稳定因素,典型性腔音列经过长期的艺术实践而发生“价值沉淀”,逐渐积淀出较为稳定的音调形态与风格特征,在标识唱腔形态的地域性方面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当然,腔音列的作用不是全能的,决定唱腔形态的本体要素绝不仅仅是腔音列,具体的音阶、特性音级、临时变化音、调式、调性、节奏、音色、润腔等手法,整体的曲式、腔词、韵律、腔格、腔系、演唱(奏)、声部等布局,都会影响唱腔的体系特征。本文所述腔音列之原生性差异,并不能解释所有地区、所有民族的唱腔形态的丰富内涵,也无意于提供一种标准化模式。
各个音乐区之间的交流是持续不断的,“音乐史的进程总在步步向前,传统音乐既在发展变化中延续生命,又能在形态转化中保留遗传基因,大体承袭了民族风貌而青春不朽。”⑰黄翔鹏《论中国古代音乐的传承关系》,载黄翔鹏《传统是一条河流》,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 年版,第123 页。典型性腔音列具有“游移”的一面,会发生动态的“宽化”与“窄化”变易,这是形成原生性唱腔形态的重要方式之一,并需要经过区域认同、民族认同和语境认同,才能契合本地人的音乐审美趣味,而内化为塑造本地区音乐风格的重要手段。探寻唱腔形态的这种应变能力,需要回归生活现场,在“历史”与“当代”的对话中观察唱腔风格的变迁。
——史蒂芬·哈特克《列队》的音高组织方法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