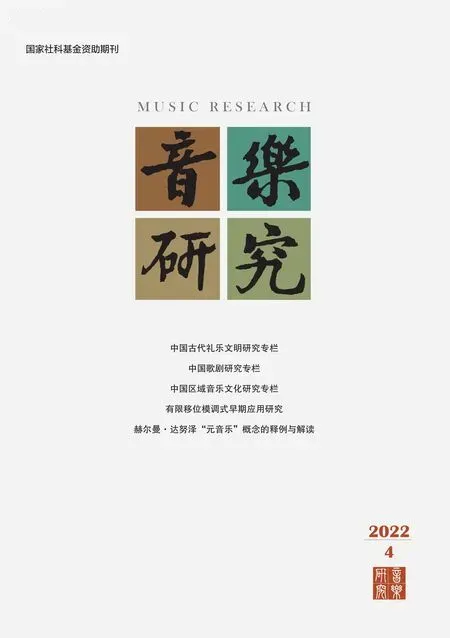流域音乐人类学钩撢:以川江流域为例
文◎胡晓东、谢佳丽
近年来,“线性文化空间(景观)”逐渐成为人类学研究的新热点,具体表现为“流域”“通道”“走廊”等“路”文化空间的关系探讨。它跳出原有定点民族志研究的域限,采用多学科交叉融合视角,对“线性文化空间”内的历史背景、社会经济与文化结构等要素进行综合分析。其中,田阡、周大鸣等学者主导的“流域人类学”①流域人类学,是遵循人类学的普同、整体、整合的理论与方法,并以跨流域比较研究为其方法论特色,来研究流域中人与自然、人与人、族群与族群关系的人类学研究新方向。参见田阡《流域人类学导论》,人民出版社2018 年版,第10 页。,备受学界关注。流域作为文化大动脉,有力推动了文化的传播与发展。所谓“流域音乐人类学”,即指在吸收“流域人类学”研究理念的基础上,取整体性、动态性、关系性与开放性视角,对流域内部所有水系的音乐文化事项进行立体式研究,其主旨在于以多学科交叉融合方法探究流域音乐文化的多元叙事,深刻揭示流域音乐文化的整体全貌。②相关代表性成果,如赵塔里木分别于2011 和2021 年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澜沧江——湄公河流域跨界民族音乐文化实录》,以及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黄河流域音乐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研究》,产出了一批优秀的流域音乐文化研究成果。本文以川江流域的音乐文化生境(habitat)③源自生物学术语,是生物生活的空间和其中全部生态因子的总和,具体指某一个体、种群或群落的社会环境、生存空间和工作条件。为例,从上述四个视角对川江流域音乐文化做多元立体阐释。
一、川江流域音乐文化的整体性研究
川江流域位于长江上游地区,西起四川宜宾,东至湖北宜昌,因主要流经四川盆地而得名“川江”,全长1040 公里,其中,重庆以上的370 公里为上川江,重庆以下的660 公里为下川江。④郭予《千里川江》,《中国水利》1988 年第10 期,第42 页。川江流域作为连接西南丝绸之路、茶马古道、苗疆走廊、藏彝走廊等地的交通大动脉,是沟通川藏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客家文化、荆楚文化的文化通道。川江流域音乐文化的整体性研究,是将川江流域作为一个整体文化大通道和音乐地理单元,根据其独特的文化传播功能,从历时性与共时性角度审视流域内各音乐文化的历史演变轨迹和互动关系。
(一)历时性研究
川江流域音乐文化的历时性研究,以时间为脉络,观测川江流域通道内各类音乐文化符号传播演变的历史脉络、意义转换与互动关系。杨民康指出,在历时性的维度中展开对音乐符号线索的追踪时,不仅会看到音乐符号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转换,而且还会看到文化意义与象征也在此过程中不断地得到改变和置换。⑤杨民康《由音乐符号线索追踪到“隐喻—象征”文化阐释——兼论音乐民族志书写中的“共时—历时”视角转换》,《中国音乐》2017 年第4 期,第30 页。川江航运历史久远,早在新石器时代,巴蜀先民即已开始从事舟楫船筏活动。⑥赵冬菊《三峡航运史述略》,《三峡学刊》1997 年第1 期,第42 页。传说远古时期的巴人在选举首领时,要根据浮舟水平的高下来决定竞选者。⑦范晔《后汉书·西南蛮夷列传》载:“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这一古老的水脉,在维系巴蜀地区人们生产生活、商贸往来的同时,也促进了流域周边的文化沟通,建构起川江流域鲜活的音乐文化景观。
在数千年国家力量的主导下,体系庞大、制度森严的政府机构、军队卫所等大一统国家机器,借助川江流域的航运优势,也输入了国家主流音乐文化。至今,在川江流域沿岸,那些曾经辉煌威严的州府衙门、戍边卫所或宣慰司的遗址,以及纳入国家体制之下的寺院、道观等,成为国家礼乐传播的重要承载。此外,由于战争或灾害导致的大规模移民运动,⑧明清时期战乱频仍,导致四川人口骤减,招各邻省百姓入川垦荒,形成了长达几百年的“湖广填四川”,川江水道,即是这场移民运动的主要迁徙路线。以及商贸往来建立的集市、会馆、船帮、茶馆、码头等社交娱乐场所,皆是川江流域音乐文化滋长蔓延的温床,使得巴蜀地区不仅成了长江上游重要的经济商贸中心,也成了上、下江地区音乐文化交融演变的集散地。我们可从“侯人兮猗”“巴渝舞”等古歌、古乐舞到传统音乐的历时性发展演变中,窥探川江流域音乐文化的整体性传播。
《吕氏春秋》载:“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经侯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侯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⑨吕不韦撰,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版,第338 页。据学者考证,涂山之地为今之江州涂山地区(重庆境内)。⑩幸晓峰《试论南音之始“候人兮,猗”》,《音乐探索》2001 年第3 期,第5 页。而“侯人兮猗”之歌,是目前史料所见最早的川江流域民歌资料,歌曲中的“兮”“猗”均为语气助词,后被广泛应用于长江流域的诗词创作中,如《楚辞》中的《离骚》《九歌》等篇章中,即多以“兮”“猗”做语气词缀于句尾。在后世千百年的民歌传承演变中,“‘候人兮猗’体”深刻影响了川江流域沿线的多数传统音乐。例如,“啰儿调”“竹枝词”“川江号子”“薅草锣鼓”“穿号子”等以穿插衬词、歌颂爱情为特色的民歌。这一音乐文化符号,依托川江流域独特的文化大通道功能,对流域两岸的音乐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衍生出“高腔山歌”“湘西花灯调”等丰富的音乐品种。从古歌“候人兮猗”到《楚辞》,再到遍布川江流域水系的“南方民歌”,川江航运助推了音乐文化的历史变迁。
“巴渝舞”是川江流域的代表性乐舞,舞者持矛、弩等道具,始为武舞。据《晋书·乐志》载:“汉高祖自蜀汉将定三秦,阆中范因率賨人以从帝,……其俗喜舞,高祖乐其猛锐,数观其舞,后使乐人习之。阆中有渝水,因其所居,故名曰‘巴渝舞’。”⑪[唐]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 年版,第693—694 页。此后,魏文帝改“巴渝舞”为“昭武舞”,西晋时改为“宣武舞”。唐时,“巴渝舞”在宫廷日渐衰落,但在民间用于劳作、祭祀,得到新发展,蜕变成各种表演形态:一是三峡库区僚人铜鼓图案上的“羽人舞”;二是三峡库区的“盾牌舞”;三是三峡库区巴人后裔的“踏蹄舞”;四是土家族的“摆手舞”。⑫王密《巴渝舞的发展过程探析》,《中华文化论坛》2017 年第4 期,第169 页。除此之外,流行于重庆地区的民间“花灯”“龙灯”“马马灯”,川东北部流传的“翻山铰子”,以及湘、桂、粤、滇、黔等地区的“瑶族鼓舞”,皆不同程度地延续了“巴渝舞”的血脉,在舞蹈语汇和表演形式上与“巴渝舞”一脉相承。以土家族“摆手舞”为例,这一广泛流传于酉水河和乌江流域的土家族传统舞蹈,在表演内容与技巧上与“巴渝舞”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在“摆手舞”中,表演者身披“西兰卡布”(花被面)的装扮,与古代“巴渝舞”披甲戴盔相似;其击鼓鸣钲的演奏形式,与“巴渝舞”伐鼓击金也如出一辙;舞蹈时所唱的“摆手歌”,与“巴渝舞”中的“叫啸歌号”大体相同,就连舞蹈动作都采用了相携跳舞的形式。⑬袁革《土家族摆手舞源考》,《社会科学家》2004年第3 期,第75 页。尤其是大摆手梯玛跳的“八苞舞”(又名“八宝铜铃舞”)中,指挥群众摆手的动作,与古时打仗的“军前舞”大都相似。⑭李伟《土家族摆手舞的文化生态与文化传承》,《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1 期,第145 页。“巴渝舞”作为中国舞蹈源头之一,通过川江流域这一线性流动空间,在历史演变过程中与周边地区的歌舞艺术产生碰撞与交流,而川江流域的社会环境,赋予它们共同的文化基因与精神内涵。
川江流域音乐文化的历时性整体研究,就是要揭示作为显性因素的川江流域文化大通道的意义,以及作为隐性因素的国家治理力量统摄下的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并阐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川江流域音乐文化,在国家政策与治理制度的主导下,显现出整体性与共通性。周初制礼作乐,“以乐辅礼、以礼相乐”为执政理念,不仅对后世政治、文化影响巨大,也贯穿于川江流域音乐文化的发展历程中。如巴渝地区的瑜伽焰口仪轨音乐,便是礼乐制度下一种特有的文化样态,其等级森严的清规制度、仪式轨范,与封建礼制之间有着高度的意合。⑮参见胡晓东《佛乐传播与国家在场——以瑜伽焰口仪轨音乐为例》,《民族艺术》2017 年第1 期,第118—128 页。此外,古时统治者所推崇的节日庆典,亦对川江流域的民间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如“上元灯节”,即是在历代统治者的统一推行下逐步形成。据《史记·乐书》载:“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时夜祠,到明而终。”⑯[汉]司马迁著,[清]蒋善辑《史记汇纂》,商务印书馆2017 年版,第57 页。最初由汉武帝推行举行的正月祭天燃灯仪式,后之历代统治者不断施行,现已演化成川江流域的上元灯节,并衍生出“花灯”“龙灯”“马马灯”等民间歌舞形态。可见,国家在场对川江流域音乐文化的历时性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只无形之手建构起川江流域庞杂的水脉文通网络。在漫长的社会历时变迁中,川江流域凭借特有的线性文化空间属性,促使其音乐文化传播在整体上呈现出相互影响、共同繁荣的发展状态。
(二)共时性研究
川江流域音乐文化的共时性整体研究,在凸显流域作为线性文化景观的前提下,关注流域内具体音乐事象和文化主体在不同空间语境中所展现出的多元一体格局和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结构关系,全方位拓展川江流域音乐文化的整体性研究。今之川江本土音乐文化——巴蜀传统音乐,既有古代本土音乐的遗存,也有后世中原音乐的影响,还有长江中下游荆楚、吴越音乐的流入。多种音乐成分的积累,多种风格色彩的融会,构成了巴蜀传统音乐的总体特征。⑰蔡际洲《“天府”风情:巴蜀音乐文化区鸟瞰——长江流域音乐文化巡礼之三》,《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1 年第1 期,第18 页。川江流域的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空间结构,不同的音乐品种都有各自的区域文化归属和地域特色,但在不同空间结构内又形成某些渊源关系及共性。以“川江号子”“啰儿调”和“川剧”为例,“川江号子”主要流传于川江流域支系岷江、沱江、乌江等水系,其起源、发展与川江航运息息相关;“啰儿调”发源于土家族,依山傍水的生存环境赋予其鲜明的地方色彩;“川剧”形成于清朝乾隆年间,城镇、码头等区域是其表演的主要场所。上述音乐品种在地理空间分布上存在较大差异,但究其形态却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互文关系:其一,“川江号子”与“啰儿调”的衬词、衬腔,都是它们极富特色的表现方式,“啰儿”“啷啰”“哟喂”等语气助词丰富了歌曲的情感表达;其二,根据不同场合,二者皆有独唱、对唱、齐唱、一领众合等多种演唱形式;其三,“啰儿调”歌曲分类中,劳动号子类是其主要类型之一,在搬运劳作时留下了《打夯号子》《背工号子》《土家开山号子》等大量的劳动号子。可见,这两种不同生存空间内的音乐品种,在艺术形态上具有一定的共通性,究其原因主要是歌种存活的空间场域——川江流域独特的地理环境,以及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使然。同时,这一共通性与川江“盐道”的发展息息相关。古巴蜀地区盛产井盐,《华阳国志·巴志》载:临江县(今重庆忠县)“有盐官,在监、涂二溪,一郡所仰”⑱[晋]常璩辑撰,唐春生等译《华阳国志》,重庆出版社2008 年版,第301 页。。巴国时期,巴盐水陆两向运输通道就逐步形成,后在历代国家政策主导下逐步完善,形成以水路为主、陆路为辅,横跨川、鄂、湘、黔、滇各省的综合运输网络,为经济贸易、军事战略以及移民活动提供便利,促进各区域文化交往和融合。⑲参见杨亭《“巴盐古道”在“国家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5 期;赵逵《川盐古道的形成与线路分布》,《中国三峡》2014年第10 期。
再以“川江号子”与“川剧”为例,“帮”“打”“唱”是“川剧”高腔的主要表现手段,其中“帮腔”通常采用“领腔”与“和腔”相配合的形式来渲染气氛,这与“薅草锣鼓”“川江号子”一领众和的表演方式极为相似;此外,“川江号子”有些曲目的唱词借鉴吸收了“川剧”的故事内容和演唱风格,如陈邦贵所唱川江平水号子《王出宫》,就借用了“川剧”【红纳袄】的内容和风格。⑳张永安《川江号子与巴渝地方戏曲音乐的发展》,《重庆社会科学》2008 年第7 期,第84 页。二者间的共通性,与川盐古道上府衙、卫所、驿站、会馆、码头、茶馆等场所的兴起紧密相关。这些场所,广泛分布于川江流域周边区域,不仅成为官员、商贾、行旅的云集之地,更有船工苦力、川剧艺人等在此观演交流,促进了“川江号子”与“川剧”表演之间的互鉴互融。比如,船工们在漫长乏味的平缓水域,歌唱内容与劳动本身无关,会将茶馆听来的“川剧”故事进行即兴演绎;“川剧”艺人也从“川江号子”表演中汲取营养,丰富其艺术形态;二者形成音乐形态的融合与互文。可见,川江流域作为文化大通道发挥了重要的沟通作用。
上文通过对川江流域不同空间结构下民间音乐品种之间的共性分析,探究它们在文化传承与传播上的内在联系,可见在国家力量主导下,川江流域作为音乐文化传播交流的重要通道,有着巨大的文化整合力。事实上,川江流域音乐文化的关系性、动态性、开放性中,均体现了国家在场的意义。
二、川江流域音乐文化的关系性体现
“关系性”是从研究对象及其所联系的现实事物之间的辩证关系出发,以动态的、真实的“关系”思维,观照动态的关系性“对象”。㉑㉑ 王洪波《“本体论承诺”之破解何以可能——以布迪厄和吉登斯的“关系性思维”为研究对象》,《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6 年第5 期,第99 页。㉒《礼记·乐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㉓ 乔建中《土地与歌》,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256 页。古时便有关于音乐关系思维的表述,《乐记》载:“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㉒㉑ 王洪波《“本体论承诺”之破解何以可能——以布迪厄和吉登斯的“关系性思维”为研究对象》,《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6 年第5 期,第99 页。㉒《礼记·乐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㉓ 乔建中《土地与歌》,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256 页。。说明古人对“物”(环境)、“声”(音乐)、“人”三者进行了音乐关系的探讨。乔建中在《音地关系探微》中亦提出:“地形地貌作为一种物质存在,制约并影响着作为意识形态的音乐艺术;而音乐当中又极其自然地表露出种种地区风貌及民族特征,两者的联系,一方面体现在流传的作品中,但同时也体现在音乐行为的主体——人的身上。”㉓㉑ 王洪波《“本体论承诺”之破解何以可能——以布迪厄和吉登斯的“关系性思维”为研究对象》,《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6 年第5 期,第99 页。㉒《礼记·乐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㉓ 乔建中《土地与歌》,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256 页。可见,“地—人—音”三者,在特定区域内都会产生相互依存的内在关系。
川江流域音乐文化,主要是由诸类音乐主客体经由线性地理空间联系在一起的有机综合体,其关系性便体现在“流域—人—音”三者的互文性结构关系上。在“流域—人—音”三维结构关系中,流域作为物质存在,处于至关重要的位置,其地理面貌、气候环境、生产生活状况等因素作为内在驱动力,影响着社会各阶层(音乐主体)的思维观念和行为,进而推动音乐艺术(音乐客体)的多样化发展;三者之间构成“流域—人”“人—人”“人—音”“流域—音”等动态多维互文性结构关系(见图1)。

图1 川江流域音乐文化互文性结构关系
在区域音乐文化研究中,音乐文化主体在通道、区域、族群语境中处于至关重要的位置。音乐行为作为人类的实践活动之一,与地理环境之间有着比其他文化现象更为密切的关系。㉔㉔ 同注㉓,第262 页。㉕ 谯珊《专制下的自治:清代城市管理中的民间自治——以重庆八省会馆为研究中心》,《史林》2012 年第2 期,第3 页。㉖ 岳精柱《“湖广填川”历史研究》,重庆出版社2014 年版,第118 页。
川江流域音乐文化中“流域—人”这一结构关系长期存在,流域内特殊地理面貌、气候、生态环境决定了居住者的生活方式,也在历时性演进中形成特定的社会阶层。例如,川江航运促进了流域上下和两岸的商业贸易,川江码头旁的会馆、船帮、码头帮、商会等社会主体便应运而生。据史料记载,鼎盛时期的重庆城曾有“八省会馆”之说,包括湖广会馆、广东会馆、江南会馆、江西会馆、福建会馆、陕西会馆、浙江会馆和山西会馆。㉕㉔ 同注㉓,第262 页。㉕ 谯珊《专制下的自治:清代城市管理中的民间自治——以重庆八省会馆为研究中心》,《史林》2012 年第2 期,第3 页。㉖ 岳精柱《“湖广填川”历史研究》,重庆出版社2014 年版,第118 页。同时,川江流域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演变与发展,亦离不开“人”这一主体的推动,音乐主体携带着川江流域所赋予的历史、语言等文化基因,在音乐传播的过程中随机形成“人—人”之间复杂多样的文化主体间性。以音乐表演主体与观赏者之间的互动为例,近代川江流域码头簇立的会馆、商会内部,戏台是核心构件之一,行使着文化传播、高台教化和商贸往来等重要功能。同时,会馆“祀神、合乐、义举、公约”等功能,亦间接影响了“川剧”表演者的风格与演出形式。清代重庆海关税务司好博逊在《重庆海关1981 年调查报告》记有重庆江南会馆的祭祀仪程:“江南会馆内新建祠堂供奉神祇,每年应举行春秋二祭,定二月十二日为春祭之期,八月十二日为秋祭之期。祭日酬神应演大戏,分胙肉醴酒,早午开席。”㉖㉔ 同注㉓,第262 页。㉕ 谯珊《专制下的自治:清代城市管理中的民间自治——以重庆八省会馆为研究中心》,《史林》2012 年第2 期,第3 页。㉖ 岳精柱《“湖广填川”历史研究》,重庆出版社2014 年版,第118 页。可见,“川剧”演戏是会馆酬神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会馆外,码头河岸和沿街兴起的茶馆、酒肆、货栈等娱乐场所,也是近现代“川剧”的主要演出场所。茶馆管理者大多会以“川剧”表演为噱头,卖票招揽顾客,获取更多收益。此外,文化主体间性在流域内部亦彰显无遗。例如,茶馆的盛行促使戏班、艺人之间为争夺演出市场而展开激烈的竞争,纷纷从各地招揽其他剧种的演员来表演与交流。这对“川剧”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促进了戏班之间的合作,以及各声腔剧种的互融与演变,从整体上导致“川剧”由单一声腔向多腔融合的发展历程。由此可见,流域作为文化大通道,以其超强的整合力,将内部各文化主客体结构在一起,组合成内紧外松、复杂多元的互文性结构关系。
川江流域“人—音”之间,构成了音乐文化主客体关系,而音乐主体是使音乐客体产生与发展的重要因素。例如,川江下游稻作文化区,以喊号子的方式指挥集体劳作和缓解辛苦,“田歌”由此产生并在川江流域广泛发展,形成“薅草锣鼓”“薅秧歌”“车水锣鼓”等多种田歌类型;它们在演唱与传承(传播)群体、演唱方式、表演形态,以及文化功能上形成内在的相通性。这种集体劳作的方式,可以牵引出一系列与之相关的音乐种类,如“川江号子”也是在这一大致相同的情况下产生的。还有在川江地区广泛盛行的“竹枝词”,起初作为民歌发源于巴渝地区,并多用于祭祀、婚嫁等风俗活动中,后由刘禹锡等人将“竹枝歌”创作为诗词,掀起文人创作“竹枝歌”的热潮,借“竹枝词”格调以写七言绝句,演变为诗体“竹枝词”。《辞海》云:“竹枝词本巴渝一带民歌,唐诗人刘禹锡根据民歌改作新词……盛行于世。”㉗㉗《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 年版,第198 页。㉘ 肖常纬《竹枝曲寻踪》,《音乐探索》1992 年第4期,第30 页。㉙《中国民族民间歌曲集成·四川卷》(上),中国ISBN 中心1999 年版,第48 页。㉚ 胡晓东《论客家音乐对川腔佛乐的涵化与濡化——以重庆罗汉寺瑜伽焰口唱腔为例》,《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16 年第4 期,第91 页。说明文人墨客影响了川江音乐的发展趋势,同时也是推动“竹枝词”广泛传播的因素之一。
“流域—音乐”的关系,是以“人”这一音乐主体为媒介,构架起流域与音乐之间的动态关系,同时在流域动脉中促进不同音乐种类之间的多元联系。上文提及的“巴渝舞”“侯人兮猗”,论证了川江流域音乐客体间的历时性赓续关系,而“川江号子”“啰儿调”“川剧”,则例证了音乐客体之间共时性的空间延展关系,正是这种繁复交织的关系,才使得川江流域的音乐品种变得璀璨夺目。又,作为川江地区独具特色的“竹枝词”,与其他多种音乐品种形成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早期民歌形式的“竹枝歌”,现只遗存历代诗人的诗词文体,却不存曲谱。我们可据唐人诗体《竹枝词》中所供《竹枝曲》的歌词格律,从互文性结构关系探寻其中奥秘。“竹枝词”有以下两种文体类型:七言二句体与七言四句体,两体的第四和第七字之后均有“和声”。㉘㉗《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 年版,第198 页。㉘ 肖常纬《竹枝曲寻踪》,《音乐探索》1992 年第4期,第30 页。㉙《中国民族民间歌曲集成·四川卷》(上),中国ISBN 中心1999 年版,第48 页。㉚ 胡晓东《论客家音乐对川腔佛乐的涵化与濡化——以重庆罗汉寺瑜伽焰口唱腔为例》,《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16 年第4 期,第91 页。如唐皇甫松二句体《竹枝》:“芙蓉并蒂(竹枝)一心连(女儿),花侵隔子(竹枝)眼应穿(女儿)。”其中,“竹枝”与“女儿”是正词之外的附加词(和声)。刘禹锡四句体《竹枝词九首》(其八)亦是如此:“巫峡苍苍(竹枝)烟雨时(女儿),清猿啼在(竹枝)最高枝(女儿)。个里愁人(竹枝)肠自断(女儿),由来不是(竹枝)此声悲(女儿)。”这种创腔体例,在川江地区的汉族民歌中极为常见,歌词大多七言四句居多,句逗、词组间常穿插衬词衬腔,以美化唱腔。如川江地区的“啰儿调”“薅草锣鼓”“薅秧歌”“丧歌”“灯调”,以及小调曲牌【绣荷包】等。《太阳出来喜洋洋》是较为接近“竹枝词”四句体的“啰儿调”歌词:
太阳出来(罗儿)喜洋洋(欧啷罗),挑起扁担(啷啷扯光扯)上山冈(欧罗罗)。手里拿把(罗儿)开山斧(欧啷罗),不怕虎豹(啷啷扯光扯)和豺狼(欧罗罗)。㉙㉗《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 年版,第198 页。㉘ 肖常纬《竹枝曲寻踪》,《音乐探索》1992 年第4期,第30 页。㉙《中国民族民间歌曲集成·四川卷》(上),中国ISBN 中心1999 年版,第48 页。㉚ 胡晓东《论客家音乐对川腔佛乐的涵化与濡化——以重庆罗汉寺瑜伽焰口唱腔为例》,《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16 年第4 期,第91 页。
尤其值一提的是,江南吴歌也随川江流域嵌入巴渝音乐文化土壤中,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胡晓东通过比较重庆罗汉寺佛教唱腔《受食赞》与下江地区古老曲牌【长城调】在整体旋律形态上的高度一致性,论述了江南吴歌顺川江流域溯江而上影响巴渝佛乐的历史事实。㉚㉗《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 年版,第198 页。㉘ 肖常纬《竹枝曲寻踪》,《音乐探索》1992 年第4期,第30 页。㉙《中国民族民间歌曲集成·四川卷》(上),中国ISBN 中心1999 年版,第48 页。㉚ 胡晓东《论客家音乐对川腔佛乐的涵化与濡化——以重庆罗汉寺瑜伽焰口唱腔为例》,《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16 年第4 期,第91 页。无独有偶,【长城调】还与綦江民歌《妇女翻身歌》㉛㉛ 熊勇《綦江民间歌曲集》,中国纺织出版社有限公司2020 年版,第98 页。㉜ 《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四川卷》(上),中国ISBN中心1993 年版,第288 页。㉝ 同注㉜,第1405 页。㉞ 田阡《村落·民族走廊·流域——中国人类学区域研究范式转换的脉络与反思》,《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2 期,第30 页。㉟ 〔美〕卢克·拉斯特著,王媛、徐默译《人类学的邀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74—75 页。㊱ 陈世松,贾大泉主编《四川通史》第2 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243 页。㊲ 杨匡民、周耘《巴音、吴乐和楚声——长江流域的传统音乐文化》,《音乐探索》2001 年第1 期,第10 页。㊳ 《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四川卷》,中国ISBN 中心1997 年版,第1379—1386 页。在整体旋律框架上相差无几。【茉莉花】进入川江地区后,也被各类音乐体裁所借鉴吸收,如四川清音中的【鲜花调】㉜㉛ 熊勇《綦江民间歌曲集》,中国纺织出版社有限公司2020 年版,第98 页。㉜ 《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四川卷》(上),中国ISBN中心1993 年版,第288 页。㉝ 同注㉜,第1405 页。㉞ 田阡《村落·民族走廊·流域——中国人类学区域研究范式转换的脉络与反思》,《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2 期,第30 页。㉟ 〔美〕卢克·拉斯特著,王媛、徐默译《人类学的邀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74—75 页。㊱ 陈世松,贾大泉主编《四川通史》第2 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243 页。㊲ 杨匡民、周耘《巴音、吴乐和楚声——长江流域的传统音乐文化》,《音乐探索》2001 年第1 期,第10 页。㊳ 《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四川卷》,中国ISBN 中心1997 年版,第1379—1386 页。、南坪弹唱中的【茉莉花】㉝㉛ 熊勇《綦江民间歌曲集》,中国纺织出版社有限公司2020 年版,第98 页。㉜ 《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四川卷》(上),中国ISBN中心1993 年版,第288 页。㉝ 同注㉜,第1405 页。㉞ 田阡《村落·民族走廊·流域——中国人类学区域研究范式转换的脉络与反思》,《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2 期,第30 页。㉟ 〔美〕卢克·拉斯特著,王媛、徐默译《人类学的邀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74—75 页。㊱ 陈世松,贾大泉主编《四川通史》第2 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243 页。㊲ 杨匡民、周耘《巴音、吴乐和楚声——长江流域的传统音乐文化》,《音乐探索》2001 年第1 期,第10 页。㊳ 《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四川卷》,中国ISBN 中心1997 年版,第1379—1386 页。,便将其引入作为基本唱腔曲牌。
三、川江流域音乐文化的动态性体现
动态性是事物发展的永恒状态,体现了事物发生发展的运动系统和内在规律。从动态性视角考察川江流域音乐文化景观,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流域作为不同族群生活并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空间与载体,建构了中华民族“水脉文通”的历史事实,其功能如费孝通所言:不同族群在流域内流动汇聚,频繁交流互动,确保了族群众多的历史与文化积淀。㉞㉛ 熊勇《綦江民间歌曲集》,中国纺织出版社有限公司2020 年版,第98 页。㉜ 《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四川卷》(上),中国ISBN中心1993 年版,第288 页。㉝ 同注㉜,第1405 页。㉞ 田阡《村落·民族走廊·流域——中国人类学区域研究范式转换的脉络与反思》,《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2 期,第30 页。㉟ 〔美〕卢克·拉斯特著,王媛、徐默译《人类学的邀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74—75 页。㊱ 陈世松,贾大泉主编《四川通史》第2 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243 页。㊲ 杨匡民、周耘《巴音、吴乐和楚声——长江流域的传统音乐文化》,《音乐探索》2001 年第1 期,第10 页。㊳ 《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四川卷》,中国ISBN 中心1997 年版,第1379—1386 页。川江流域作为连接西南丝绸之路、茶马古道、苗疆走廊、藏彝走廊的交通大动脉,其音乐文化在继承本有文化传统的同时,也不断受到外域、外族文化的影响,乃至相互吸收、相互通融,在历史变迁中呈现出动态性衍生状态,主要表征为文化“涵化”与“濡化”现象。
(一)文化涵化
涵化(Acculturation)这一文化人类学术语,专指不同文化种类在长期接触与交流过程中产生的文化形式与内涵等多方面的相互包涵与交融的动态过程,即异质文化接触引起原有文化模式的变化。当处于支配从属地位关系的不同群体,由于长期直接接触而使各自文化发生规模变迁,即是涵化。㉟㉛ 熊勇《綦江民间歌曲集》,中国纺织出版社有限公司2020 年版,第98 页。㉜ 《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四川卷》(上),中国ISBN中心1993 年版,第288 页。㉝ 同注㉜,第1405 页。㉞ 田阡《村落·民族走廊·流域——中国人类学区域研究范式转换的脉络与反思》,《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2 期,第30 页。㉟ 〔美〕卢克·拉斯特著,王媛、徐默译《人类学的邀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74—75 页。㊱ 陈世松,贾大泉主编《四川通史》第2 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243 页。㊲ 杨匡民、周耘《巴音、吴乐和楚声——长江流域的传统音乐文化》,《音乐探索》2001 年第1 期,第10 页。㊳ 《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四川卷》,中国ISBN 中心1997 年版,第1379—1386 页。音乐涵化是指不同区域或族群的音乐文化因长期交往、交流而引发的相互影响与交融的结果。
由于川江流域重要的水脉文通功能,星罗棋布的航运水系接引各地区、族群的音乐文化汇入川江地区,纵横贯通、彼此吸融,深刻改变了川江地区的文化特质与结构,形成广泛而鲜活的文化涵化过程。川江流域是沟通巴蜀内部以及楚、吴联系的主要干线之一。㊱㉛ 熊勇《綦江民间歌曲集》,中国纺织出版社有限公司2020 年版,第98 页。㉜ 《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四川卷》(上),中国ISBN中心1993 年版,第288 页。㉝ 同注㉜,第1405 页。㉞ 田阡《村落·民族走廊·流域——中国人类学区域研究范式转换的脉络与反思》,《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2 期,第30 页。㉟ 〔美〕卢克·拉斯特著,王媛、徐默译《人类学的邀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74—75 页。㊱ 陈世松,贾大泉主编《四川通史》第2 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243 页。㊲ 杨匡民、周耘《巴音、吴乐和楚声——长江流域的传统音乐文化》,《音乐探索》2001 年第1 期,第10 页。㊳ 《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四川卷》,中国ISBN 中心1997 年版,第1379—1386 页。其本土“巴蜀音乐文化”在历史进程中受到长江流域其他音乐文化如“吴越音乐文化”“客家音乐文化”“荆楚音乐文化”“川藏音乐文化”等不同程度的影响。杨匡民认为:“荆楚歌乐舞艺术传统对上、下游的巴蜀和吴越音乐文化都有重大影响,而与巴蜀音乐文化在艺术特征、审美追求上更为趋同。”㊲㉛ 熊勇《綦江民间歌曲集》,中国纺织出版社有限公司2020 年版,第98 页。㉜ 《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四川卷》(上),中国ISBN中心1993 年版,第288 页。㉝ 同注㉜,第1405 页。㉞ 田阡《村落·民族走廊·流域——中国人类学区域研究范式转换的脉络与反思》,《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2 期,第30 页。㉟ 〔美〕卢克·拉斯特著,王媛、徐默译《人类学的邀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74—75 页。㊱ 陈世松,贾大泉主编《四川通史》第2 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243 页。㊲ 杨匡民、周耘《巴音、吴乐和楚声——长江流域的传统音乐文化》,《音乐探索》2001 年第1 期,第10 页。㊳ 《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四川卷》,中国ISBN 中心1997 年版,第1379—1386 页。事实上,川江流域内部微观意义上的文化涵化现象也是俯拾即是。如四川“曲剧”的演唱风格,多继承四川曲艺的演唱风格,特别是在润腔特色上,主要应用了“四川清音”中的“哈哈腔”、装饰润腔、情绪润腔等几种润腔手法,其中“哈哈腔”还是四川“曲剧”唱腔的主要特色之一。㊳㉛ 熊勇《綦江民间歌曲集》,中国纺织出版社有限公司2020 年版,第98 页。㉜ 《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四川卷》(上),中国ISBN中心1993 年版,第288 页。㉝ 同注㉜,第1405 页。㉞ 田阡《村落·民族走廊·流域——中国人类学区域研究范式转换的脉络与反思》,《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2 期,第30 页。㉟ 〔美〕卢克·拉斯特著,王媛、徐默译《人类学的邀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74—75 页。㊱ 陈世松,贾大泉主编《四川通史》第2 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243 页。㊲ 杨匡民、周耘《巴音、吴乐和楚声——长江流域的传统音乐文化》,《音乐探索》2001 年第1 期,第10 页。㊳ 《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四川卷》,中国ISBN 中心1997 年版,第1379—1386 页。
除此之外,由于战争灾难、移民运动、经济重心东移等因素导致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则是促成川江流域音乐文化宏观涵化的主要推手。例如,历史上数次规模空前的“湖广填四川”等移民大潮,促使下江地区的“客家音乐文化”“荆楚音乐文化”等经川江流域进入巴蜀、川藏地区,与之发生深刻的涵化过程。其中,有两次“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影响范围最广:第一次是元末明初(1361—1387),以湖广地区为主的南方移民首次进入四川;第二次在清初(17 世纪中叶—18 世纪中叶),以湖北、湖南、江西和广西为主的十余个省的移民南移入川。㊴㊴ 同注㉛,第81 页。㊵ 李世平《四川人口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156 页。㊶ 孟凡玉《论傩歌“啰哩嗹”的生殖崇拜内涵》,《音乐研究》2007 年第4 期,第46 页。㊷ 参见胡晓东《民歌的地方音色与文化认同——以綦江汉族民歌为例》,《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17 第1 期。谱例见熊勇《綦江民间歌曲集》,中国纺织出版社有限公司2020 年版。㊸ 陈朝友、王敏主编《永城吹打》,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 年版,第9—15 页。㊹ 同注㊱。据清宣统元年出版的《成都通览》载:“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也”,该书统计,各原籍的比率是:“湖广25%,江西15%,江苏、浙江10%,云南、贵州10%,陕西10%……”㊵㊴ 同注㉛,第81 页。㊵ 李世平《四川人口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156 页。㊶ 孟凡玉《论傩歌“啰哩嗹”的生殖崇拜内涵》,《音乐研究》2007 年第4 期,第46 页。㊷ 参见胡晓东《民歌的地方音色与文化认同——以綦江汉族民歌为例》,《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17 第1 期。谱例见熊勇《綦江民间歌曲集》,中国纺织出版社有限公司2020 年版。㊸ 陈朝友、王敏主编《永城吹打》,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 年版,第9—15 页。㊹ 同注㊱。各地文化经由川江流域,有效增强了区域间音乐文化的交融和传播,形成多元一体并存之格局。
在频繁的音乐文化交汇互融过程中,各音乐品种的样态展示出内在的线性联系。以綦江地区民间音乐为例,在綦江汉族民歌中流传大量体裁结构、衬词衬腔格式与江淮地区传统曲牌【啰哩嗹】具有高度相似性的民歌。如安徽贵池傩歌《啰哩嗹》歌词中,“啰哩嗹”作为特色衬词衬腔反复出现:
撇帐东,好似巫山十二峰,二人入了桃园洞,天地灵刹一水啊通啊。啰嗹子哩呀,哩嗹子啰,啰嗹啰哩嗹啊,哩嗹子啰。㊶㊴ 同注㉛,第81 页。㊵ 李世平《四川人口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156 页。㊶ 孟凡玉《论傩歌“啰哩嗹”的生殖崇拜内涵》,《音乐研究》2007 年第4 期,第46 页。㊷ 参见胡晓东《民歌的地方音色与文化认同——以綦江汉族民歌为例》,《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17 第1 期。谱例见熊勇《綦江民间歌曲集》,中国纺织出版社有限公司2020 年版。㊸ 陈朝友、王敏主编《永城吹打》,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 年版,第9—15 页。㊹ 同注㊱。
这与綦江汉族民歌《人生在世为哪样》的衬词衬腔格式极为相似,歌词中“啰”“里呀”“连那个”与“啰哩嗹”具有一致性。除此之外,郭扶镇高庙村民歌《寸金难买寸光阴》《说根生来道根生》等綦江民歌亦属同类。因此可推测,綦江汉族民歌与下江地区的【啰哩嗹】具有亲密的血缘关系。㊷㊴ 同注㉛,第81 页。㊵ 李世平《四川人口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156 页。㊶ 孟凡玉《论傩歌“啰哩嗹”的生殖崇拜内涵》,《音乐研究》2007 年第4 期,第46 页。㊷ 参见胡晓东《民歌的地方音色与文化认同——以綦江汉族民歌为例》,《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17 第1 期。谱例见熊勇《綦江民间歌曲集》,中国纺织出版社有限公司2020 年版。㊸ 陈朝友、王敏主编《永城吹打》,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 年版,第9—15 页。㊹ 同注㊱。又如,綦江地区代表性吹打乐“永城吹打”中的“綦江调”“青山调”,与“湖北吹打”在乐器构成、表演方式和音乐形态上有诸多的相似之处;“永城吹打”中还包含了横山和三角的“昆词”,是江苏地区的“昆曲”唱腔进入綦江地区后由“吹、打、唱”三者结合的表演形式。㊸㊴ 同注㉛,第81 页。㊵ 李世平《四川人口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156 页。㊶ 孟凡玉《论傩歌“啰哩嗹”的生殖崇拜内涵》,《音乐研究》2007 年第4 期,第46 页。㊷ 参见胡晓东《民歌的地方音色与文化认同——以綦江汉族民歌为例》,《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17 第1 期。谱例见熊勇《綦江民间歌曲集》,中国纺织出版社有限公司2020 年版。㊸ 陈朝友、王敏主编《永城吹打》,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 年版,第9—15 页。㊹ 同注㊱。这种“三元”合流的现象,证实川江流域与其他地区音乐文化的涵化现象,也展现出川江流域水脉文通的文化驱动功能。
(二)文化濡化
濡化(enculturation)由赫斯科维茨首先提出,是指发生在同一文化内部的、纵向的传播过程,是人与人的文化习得和传承机制,本质意义是人的学习与教育。从群体角度讲,濡化是不同族群、不同社会赖以存在和延续的方式及手段,同时也是族群认同的过程标志之一。㊹㊴ 同注㉛,第81 页。㊵ 李世平《四川人口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156 页。㊶ 孟凡玉《论傩歌“啰哩嗹”的生殖崇拜内涵》,《音乐研究》2007 年第4 期,第46 页。㊷ 参见胡晓东《民歌的地方音色与文化认同——以綦江汉族民歌为例》,《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17 第1 期。谱例见熊勇《綦江民间歌曲集》,中国纺织出版社有限公司2020 年版。㊸ 陈朝友、王敏主编《永城吹打》,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 年版,第9—15 页。㊹ 同注㊱。川江地区的音乐文化,以流域水系为生存空间,在漫长的社会历史变迁中通过内部代际传承,延续音乐文化基因,进而对文化主体的观念、行为产生熏习和浸润,体现出文化濡化的意义。
以“薅草锣鼓”为例,作为我国长江流域特有的民间文化,其产生和发展与农耕社会有着紧密联系。根据四川绵阳新皂乡东汉墓出土的陶秧鼓俑,可推测川江流域汉时便有击鼓劳作的方式。目前关于“薅草锣鼓”最早的文献见于公元957 年可朋的《耘田鼓》。《唐诗纪事》载:“寺之外皆耕者,曝背烈日中耘田,击腰鼓以适倦。”㊺㊺ [宋]计有功《唐诗纪事》,中华书局1965 年版,第1086 页。㊻ [清]朱锡谷《巴州志》卷1,道光十三年(1833)刻本。㊼ [清]吴振棫《黔语》卷下,咸丰四年(1854)刻本。㊽ 刘小琴《四川宣汉县薅草锣鼓初探》,《中国音乐》2010 年第3 期,第80 页。㊾ 刘传清《土家族薅草锣鼓的流变及其式微》,《中华文化论坛》2016 年第6 期,第148 页。㊿ 薛艺兵《在音乐表象的背后》,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 年版,第23 页。文中之“寺”,是指九龙山净众寺(今四川眉山市地区的竹林寺),此考古资料及历史记载说明了汉唐时期“薅草锣鼓”即已形成,其原始音乐形态是以鼓击节,助力劳作,消除疲劳。“劳者歌其事”,“薅草锣鼓”的发展,离不开川江流域稻作文化的土壤,在农事中形成的农耕气息是其独特的文化基因。
唐以降,“薅草锣鼓”的传播区域以川江流域为主线并进一步扩大,广泛流传于川、渝、黔、滇、湘等地区,演唱形式也得以发展。比如,宋元时期的陕东南和鄂西北出现击鼓吹笛的劳作场面,改变了徒鼓击节的单一表演形式,表演场地也不局限于水田。同时,川江流域的文化通道功能促进各地“薅草锣鼓”的互鉴交流,呈现出相似的表演方式。据道光十三年《巴州志·风俗》载:
春田栽秧,选歌郎二人击鼓鸣钲于垄上,曼声而歌,更唱迭和。丽丽可听,使耕者忘其疲,以齐功力,有古秧歌之遗。夏芸亦如之。㊻㊺ [宋]计有功《唐诗纪事》,中华书局1965 年版,第1086 页。㊻ [清]朱锡谷《巴州志》卷1,道光十三年(1833)刻本。㊼ [清]吴振棫《黔语》卷下,咸丰四年(1854)刻本。㊽ 刘小琴《四川宣汉县薅草锣鼓初探》,《中国音乐》2010 年第3 期,第80 页。㊾ 刘传清《土家族薅草锣鼓的流变及其式微》,《中华文化论坛》2016 年第6 期,第148 页。㊿ 薛艺兵《在音乐表象的背后》,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 年版,第23 页。
清咸丰《黔语》记载了贵州德江县“薅草锣鼓”的表演:
安化、务川农人薅苗,用钲鼓杂歌,名曰打闹,以作其气,使用力勤也。俞秋农大令,汝本当作打闹歌。㊼㊺ [宋]计有功《唐诗纪事》,中华书局1965 年版,第1086 页。㊻ [清]朱锡谷《巴州志》卷1,道光十三年(1833)刻本。㊼ [清]吴振棫《黔语》卷下,咸丰四年(1854)刻本。㊽ 刘小琴《四川宣汉县薅草锣鼓初探》,《中国音乐》2010 年第3 期,第80 页。㊾ 刘传清《土家族薅草锣鼓的流变及其式微》,《中华文化论坛》2016 年第6 期,第148 页。㊿ 薛艺兵《在音乐表象的背后》,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 年版,第23 页。
可见,“薅草锣鼓”的传播范围在这一时期得以扩大,但伴奏形式、表演方式大体趋同。
近代以来,“薅草锣鼓”表演形式多变。比如,四川宣汉的“薅草锣鼓”,以一至三人自击锣鼓自唱的方式表演,伴奏乐器有鼓、钹、马锣等。㊽㊺ [宋]计有功《唐诗纪事》,中华书局1965 年版,第1086 页。㊻ [清]朱锡谷《巴州志》卷1,道光十三年(1833)刻本。㊼ [清]吴振棫《黔语》卷下,咸丰四年(1854)刻本。㊽ 刘小琴《四川宣汉县薅草锣鼓初探》,《中国音乐》2010 年第3 期,第80 页。㊾ 刘传清《土家族薅草锣鼓的流变及其式微》,《中华文化论坛》2016 年第6 期,第148 页。㊿ 薛艺兵《在音乐表象的背后》,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 年版,第23 页。从现在保留下来的“薅草锣鼓”表演程式来看,程序体制上大体相仿,少不了“请神”“送神”等环节。如湘西“薅草锣鼓”(又称“挖土歌”)的表演程式为:开声、请歌师、请神、请歌娘歌爷、扬歌、送神、送歌娘歌爷、收尾;川东的“薅草锣鼓”(又称“打闹歌”)包含:歌头、请神、扬歌、送神四部分;黔东铜仁地区的“薅草锣鼓歌”的表演程序为:“引子、请神、扬歌、送神”;这与古代川江地区盛行祭鬼神、祖先崇拜、歌颂巫术相关。㊾㊺ [宋]计有功《唐诗纪事》,中华书局1965 年版,第1086 页。㊻ [清]朱锡谷《巴州志》卷1,道光十三年(1833)刻本。㊼ [清]吴振棫《黔语》卷下,咸丰四年(1854)刻本。㊽ 刘小琴《四川宣汉县薅草锣鼓初探》,《中国音乐》2010 年第3 期,第80 页。㊾ 刘传清《土家族薅草锣鼓的流变及其式微》,《中华文化论坛》2016 年第6 期,第148 页。㊿ 薛艺兵《在音乐表象的背后》,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 年版,第23 页。同时,“薅草锣鼓”流布湖广、江浙、云、贵、川等地,各地插秧歌的称谓、内容、形式以及曲调也各具特色,鄂北称“栽秧歌”,湘赣叫“插田歌”,江浙谓“栽秧号子”……这类歌曲的内容或与劳动有关,或以逗趣为主,或随意演唱当地的民歌小曲,或整套搬唱民间传说故事。㊿㊺ [宋]计有功《唐诗纪事》,中华书局1965 年版,第1086 页。㊻ [清]朱锡谷《巴州志》卷1,道光十三年(1833)刻本。㊼ [清]吴振棫《黔语》卷下,咸丰四年(1854)刻本。㊽ 刘小琴《四川宣汉县薅草锣鼓初探》,《中国音乐》2010 年第3 期,第80 页。㊾ 刘传清《土家族薅草锣鼓的流变及其式微》,《中华文化论坛》2016 年第6 期,第148 页。㊿ 薛艺兵《在音乐表象的背后》,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 年版,第23 页。
可见,在漫长的社会历史变迁中,“薅草锣鼓”依托川江流域文化通道实施代际濡化传承,既延续了文化基因,又展现出历时性语境下的鲜活变通,也深刻影响着文化主体的文化观念和心理素质。
四、川江流域音乐文化的开放性体现


(一)时空开放性
“时空”即时间和空间,不同学科语境对“时空”的理解不大一样,一般而言,时空是物质存在的基本属性。哲学上,时间和空间的相互关系,维系着事物的运动方式和演化秩序,任何事物都在时间和空间建构的维度中无穷尽地发展演进。因此,对于川江流域音乐文化这一时空景观而言,绝对的开放性是其存在与发展的重要前提。时间上,川江流域音乐文化在历史长河中一以贯之地保持传播与发展的开放性,无论是世纪更迭、朝代替换,其文化结构与社会功能皆承续无碍。在川江流域,那些先秦乃至远古时期的音乐文化,依然以某种方式顽强地遗存至今,超越了时间的边界。空间上,由于水脉文通的流动性,川江流域音乐文化景观纵贯整个长江水系,并与陆路交通接轨,形成水陆纵横、八方畅通的开放性地理空间,也孕育出丰富多元的音乐文化景观。
时空开放性使川江流域建立起一个无界的传播通道,让音乐文化在流传演变过程中畅通无阻,彼此交融。川江地区尚武重巫的精神风貌,孕育出“巴渝舞”这一歌舞形态,并经由水陆交通传播至更广泛的藏、滇、黔、湘、桂等地区,演化出许多同类型的歌舞音乐品种。例如,川西高原的“铠甲舞”、三峡库区的“踏蹄舞”、土家族“摆手舞”,以及川东地区“翻山铰子”等,都承续了“巴渝舞”的文化属性。又如,我国西南地区节庆期间广泛盛行的“灯戏”(亦称“花灯戏”),也是明清时期川江流域普遍的民俗活动,后经由川江流域广泛传播至西南各地。如《阆中县志》记载五月十五瘟祖会“演灯戏十日”的情形,乾隆《苍溪县志》亦有“元夕,放花灯、演灯戏”的相似记载。这些具有普遍性、共通性的音乐文化,证实了川江流域时空开放性的体现。
(二)族群开放性
川江流域的族群开放性,是指在川江流域水脉文通功能的驱动下,各族群进行广泛而深入的交往、交流与交融,族群文化逐渐趋于认同,族群边界趋向模糊,展示出强烈的族群开放性。川江流域族群众多,在商周以前,川江流域已是诸多民族族群的活动区域。如藏、彝、羌、汉、土家、回、苗等族群,即已在此繁衍生息。在频繁的交往、交流与交融过程中,各族群共享资源,逐步形成多元一体格局,彰显出川江流域族群文化的开放性。
川江流域不同族群之间存在着多种外部表征略有差异,但实际文化内涵一致的“同质异构”型传统节庆仪式,生动体现了川江流域族群的开放性。以火把节为例,作为彝、白、纳西、藏、土家、傈僳、布朗、哈尼、普米、拉祜等族群共有的传统节日,不同族群的称谓、举办时间、节日缘起与举办方式等不尽相同。如彝族语称火把节为“都则”;尔苏藏族称“啧啧”“啧嘎”,简称“啧”,意“迎送节”;纳西族语称此节为“川美生恩”;白族语叫“付旺勿”,意为六月尾、六月中的意思,又叫“搭星回”。彝族、纳西族、基诺族等族群的火把节,在农历六月二十四至二十六举行;尔苏藏族火把节的日期,为农历六月十六至十八;白族是六月二十五;拉祜族是六月二十。关于火把节的起源记忆亦各有表述,甚至在同一族群的不同支系或不同地区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举办方式及节庆仪式内容更有区别。尽管各族群火把节的上述形式表征各具特色,但是仪式的主旨与文化内核却大致相同,都意在表达本族群对火、神灵、祖先等超自然力量的原始崇拜,显示出族群文化认同的一致性。火把节民俗仪式,就是各族群对“火”这一文化符号虔诚崇拜的庆典。正是由于川江流域文化大通道的时空开放性,促使各族群在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分配等方面的“共场”,进而超越了传统族群边界的鸿沟,建构了共同的文化心理认同。葛剑雄在《中国移民史》中详细阐述了清代“改土归流”政策的推行,引发中央王朝与地方土司的冲突与战斗,动荡不安的局势迫使大量滇东北彝族人途径川江流域逃至四川凉山地区,将火把节带至整个川江流域的历史事实。可见,川江流域作为西南地区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交流的线性文化空间,具有时空与族群的开放性,牵引着各族群的心理凝聚力与族群认同,对促进各族群之间的文化交往、交流和交融,建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结 语
作为“路”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流域音乐人类学”有效促进了线性音乐空间(景观)研究的多元纵深发展,开拓与丰富了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学术视野。首先,“流域音乐人类学”将流域视为一个有机整体,考察内部诸文化主体的主体间性与互文性,达至对文化空间结构与社会功能的整体把握。其次,“流域音乐人类学”强调流域作为文化大通道所具有的开放性与文化沟通功能,突破过往定点民族志静态、单一视角的局限,转向线索、多点民族志动态、开放、整体性的研究范式,借助地理学、生态学、人类学、传播学、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等学科理念,在交叉过程中相互推进,以综合立体的视角来关注与思考流域空间内音乐文化的结构关系与多元互动,探讨流域生态文明对其内部音乐文化传播与流变的影响与功能,具备了“新文科”的理论品质。因此,在新文科背景下,“流域音乐人类学”将以跨学科理念与不同学科的交叉融合发展为基础,新构学术研究平台与学术共同体。同时,新文科亦倡导构建系统性、整体性的知识体系。“流域音乐学”作为新民族音乐学研究的代表,应该继续坚持以创新、开放的学术诉求,加强系统性构建,将这一研究领域夯实深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