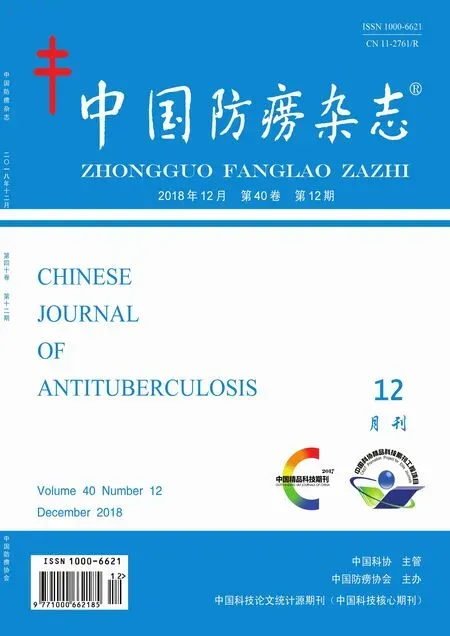肺上叶切除术后胸内残腔发生的危险因素及其对术后早期并发症的影响
蒋钰辉 申磊 戴希勇
肺上叶是肺结核好发部位,对局限于上叶的结核空洞、毁损肺、结核并发肺癌、曲菌球等结核病的后遗症和并发症,肺上叶切除术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手段。相对于肺癌而言,肺结核、曲菌球等感染性肺病行肺上叶切除术后胸内残腔的发生率较高,而与之相关的并发症如肺漏气、残腔感染等是导致患者住院时间延长、住院费用增加的常见原因。笔者回顾性分析2014年10月至2017年10月武汉市肺科医院外科行肺上叶切除术患者的临床资料,对术后胸腔残腔产生的危险因素进行分析,并总结其对术后早期并发症的影响,为此类患者的术前评估与术后治疗提供参考。
资料和方法
一、研究对象
回顾性分析2014年10月至2017年10月武汉市肺科医院外科行肺上叶切除术的80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原发肺恶性肿瘤者23例(28.75%),感染性肺病者57例(71.25%);男70例,女10例;年龄范围23~73岁,平均(52.40±11.74)岁;56例患者具有肺功能检测数据,34例患者未进行肺功能检测或数据不完整。根据患者术后胸腔内是否发生残腔分为有残腔组(29例)和无残腔组(51例)。(1)纳入标准:①具备手术指征,且经胸腔镜或常规开胸行肺上叶切除术者(肺癌患者术中加行系统性淋巴结清扫术)。②术前心肺功能评估无绝对手术禁忌证。③术前无器质性心脏病、肝硬化、四肢运动障碍等影响术后恢复的并发症。(2)排除标准:①行肺部分切除术、支气管袖式切除术、复合肺叶切除术、肺叶联合肺段切除术者。②出现大咯血等行急诊手术者。③并发糖尿病患者因数量太少,亦予排除。
二、术前准备
患者行术前常规检查,并完善胸外科术前评估检查,如心脏彩色多普勒超声、肺功能、动脉血气、纤维支气管镜、胸部CT增强扫描检查等;疑似肿瘤患者需行颅脑CT扫描、腹腔脏器彩色多普勒超声、骨正电子发射计算机体层摄影(ECT)等检查。肺结核患者需经规范抗结核药物治疗至少6个月以上(耐药肺结核患者为规范抗结核药物治疗1年以上),待肺部病变局限和稳定后进行手术。肺曲菌球病患者术前需抗真菌治疗至少2周以上。并发肺部感染者术前需抗感染治疗至血常规及降钙素原检查正常。吸烟者术前需严格戒烟。营养不良者术前予以营养支持治疗,使血清白蛋白>30 g/L,血红蛋白(HGB)>100 g/L,电解质正常。
三、手术方法
全麻后行双腔气管插管,取健侧卧位,经常规开胸或胸腔镜行肺上叶切除术。常规开胸采用第5肋间后外侧切口,胸腔镜采用三孔法或单操作孔法。按标准操作流程行肺上叶切除术,病灶处胸膜致密粘连者于胸膜外游离,避免病灶破溃。术中行快速冰冻切片检查,若为恶性病变,加行系统性淋巴结清扫术。术毕后于锁骨中线第2肋间(胸腔镜手术为腋前线第4肋间)及腋中线第7肋间各置引流管一根行持续胸腔闭式引流。手术标本除行病理检查外,快速冰冻切片诊断炎性病变者取病灶内坏死组织行病原学检查(革兰染色、抗酸染色、普通细菌培养、真菌培养、结核分枝杆菌培养等)及分子生物学检查(GeneXpert MTB/RIF、TB-DNA、线性反向探针杂交法等)以指导术后治疗。
四、术后处理
常规治疗与护理同肺叶切除术后常规处理。胸腔引流液少于200 ml/d时拔除下胸管,上胸管需待无明显肺漏气时拔除。肺结核患者根据病史及病原学检查结果,由结核科专家制定抗结核药物治疗方案及疗程。肺曲菌球病患者术后以伏立康唑或伊曲康唑抗真菌治疗3~6个月。肺恶性肿瘤患者恢复后转肿瘤科行术后综合治疗。
五、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1.术后胸腔内残腔的评价标准:患者于术后第7~14天行胸部X线摄影或CT扫描,若胸腔内残腔体积大于患侧胸腔容积的20%,即术侧胸腔余肺上缘低于第3后肋水平,则视为发生术后胸内残腔。
2.术后胸内残腔发生的危险因素观察指标:(1)一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吸烟史、有无基础肺部器质性疾病(肺结核纤维钙化灶、肺气肿、尘肺等);(2)疾病与手术相关因素,包括原发病(感染性肺病与肺恶性肿瘤)、手术部位、手术入路、手术时间、有无全胸膜腔粘连;(3)肺功能指标,包括用力肺活量(FVC)、第1秒用力肺活量(FEV1)、FEV1/FVC、每分钟最大通气量(MVV)。
3.术后胸腔内残腔对围手术期的影响指标:术后72 h引流量、术后拔管时间、手术重大并发症发生率(如胸腔活动性出血、残腔感染等)。

结 果
一、基本情况
80例肺上叶切除者中,原发肺恶性肿瘤者23例(28.75%),感染性肺病者57例(71.25%)。感染性肺病患者中肺结核21例(36.84%)、支气管结核并发肺不张2例(3.51%)、肺曲菌球病24例(42.10%)、支气管扩张8例(14.04%)、机化性肺炎2例(3.51%)。并发基础肺器质性疾病患者57例,其中肺结核纤维钙化灶31例(54.39%)、肺气肿23例(40.35%)、尘肺3例(5.26%)。80例患者行左肺上叶切除术30例(37.50%),右肺上叶切除术50例(62.50%);胸腔镜手术26例(32.50%),常规开胸手术54例(67.50%)。术中探查见全胸膜腔粘连者35例(43.75%),无或局限性胸膜粘连者45例(56.25%)。术后发生胸内残腔者29例,发生率为36.25%。
二、术后胸内残腔发生的危险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术后有残腔组与无残腔组相比原发病、基础肺部器质性病变、手术时间、全胸膜腔粘连、FVC、FEV1、MVV等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年龄、性别、吸烟史、手术部位、手术入路、FEV1/FVC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表1)。进一步的logistic分析显示,有全胸膜腔粘连和FEV1<1.85 L是导致患者术后发生胸腔残腔的危险因素(表2)。
三、术后胸内残腔对术后早期并发症的影响
术后发生胸内残腔者72 h引流量[M(Q1,Q3)]为1380(1010,1635) ml,明显高于未发生者的920(630,1150) 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U=351.00,P<0.05);术后发生胸内残腔者拔管时间[M(Q1,Q3)]为15.0(11.5,25.0) d,明显较未发生者[9.0(7.0,10.0) d]延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U=215.50,P<0.05)。术后早期发生手术重大并发症者4例(5.00%),均为发生术后胸内残腔者;其中残腔感染3例,迟发性胸腔活动性出血1例。
讨 论
肺切除术后出现胸腔内残腔这一现象在临床上并不少见,但国内外相关文献报道较少,也没有统一的判断标准和定义,其原因可能是因为这是一种术前可以预料到的状况,大多数没有临床症状,除非并发感染,或者出现有症状的大残腔[1]。Solak等[2]遵照气胸的临床处理原则,认为残腔体积大于患侧胸腔容积的20%者具有临床意义,可定义为术后胸内残腔。他们通过分析不同肺部疾病手术后各时期胸内残腔的发生率时发现,肺切除术后第1天胸腔内残腔的发生率为41.4%,其中62.1%的患者经治疗后胸内残腔可在1周后吸收,认为术后胸内残腔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术后随着时间的延续,其发生率逐步下降。由于术后1周仍然存在胸内残腔会导致持续性肺漏气、残腔感染等延长患者住院时间或需再次处理的并发症,因此,笔者观察的是术后7~14 d胸腔内残腔的体积大于患侧胸腔容积的20%者。为了方便临床判断,笔者将术后7~14 d影像学检查见余肺上缘低于第3后肋水平作为术后胸内残腔的判断标准。

表1 行肺上叶切除术患者发生术后胸内残腔的单因素分析


表2 肺上叶切除术术后发生胸内残腔危险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肺切除术后胸内残腔的代偿机制包括余肺代偿性的扩张、纵隔移位、肋间隙缩窄、膈肌上抬等,而术后早期起主要作用的是肺的代偿性扩张和纵隔移位。由于胸膜顶的锥形解剖结构,余肺在重力的影响下难以扩张填充胸膜顶,这是肺上叶切除术后容易出现胸内残腔的原因之一。如果患者并发限制肺扩张(肺气肿、炎性肺病等)及纵隔移位(放化疗史)的基础疾病,术后胸内残腔更容易出现。Solak等[2]的研究证实了这一观点,他们分析认为肺上叶切除术及上中叶切除术的术后胸内残腔发生率明显高于肺中、下叶切除术,且在发生术后胸内残腔的患者中,13.8%的患者因严重持续性肺漏气(prolonged air leak,PAL)或残腔感染需再引流或者二次手术。Elsayed等[3]研究显示,肺切除术后发生PAL的患者中68%为肺上叶切除术,肺上叶切除术是PAL的独立危险因素之一,其原因主要是肺上叶切除术更容易发生术后胸内残腔。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全胸膜腔粘连与FEV1<1.85 L是肺上叶切除术后发生胸内残腔的危险因素。笔者分析,上述危险因素引起术后胸内残腔的机制主要有以下3个方面:(1)胸腔再粘连。本次研究对象中,原发病为感染性肺病者占71.25%,有基础肺部器质性疾病者中54.39%为肺结核。据笔者观察,肺结核、肺曲菌球病等感染性肺病常并发全胸膜腔粘连,这可能与并发胸膜炎有关。全胸膜腔粘连者,术中松解粘连时易损伤胸膜导致肺漏气,松解后的粘连带内纤维素弥漫附着胸膜上,导致胸膜正常解剖结构和生理功能被破坏,在术后早期患侧很快再次形成胸膜粘连,此时余肺因肺漏气或顺应性差而未扩张移位至胸膜顶,从而发生术后胸内残腔[4]。(2)肺顺应性差。研究表明,FEV1降低是导致PAL的重要独立危险因素[5-6],原因可能是FEV1降低主要见于并发有肺部器质性疾病(如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结核等)患者。肺部器质性疾病可引起肺实质的病理性改变和气道阻力增加,一方面可降低肺顺应性,限制肺扩张,另一方面使肺损伤及肺切缘创面难以愈合而持续漏气。肺扩张受限与肺漏气均可限制余肺的扩张和移位,使残腔难以被余肺填充,导致发生术后胸内残腔。(3)纤维素束缚:这种机制主要与全胸膜腔粘连有关。松解胸膜粘连后,纤维素附着于胸膜表面,可对肺形成束缚效应,限制肺的扩张。除此之外,笔者临床观察发现,广泛附着纤维素的胸膜去纤维化与再吸收功能明显下降,术后早期胸腔血性渗液形成凝血块附着于肺表面,进一步限制肺的扩张。
本次研究中发生术后胸内残腔的患者术后拔管时间[M(Q1,Q3)]为15.0(11.5,25.0) d,较未发生者术后拔管时间延迟,其主要原因就是PAL。肺切除术后PAL发生的原因目前尚不明确,可能与肺实质与胸膜损伤修复机制有关[7]。笔者认为,术后肺漏气通常是由于肺损伤或肺切缘漏气引起的,其愈合机制类似于自发性气胸,除了肺实质的愈合外,更重要的是让漏气的肺创面帖附于周围组织如胸壁、膈肌、纵隔胸膜等,使其被“封堵”并形成牢固的粘连。而在发生术后胸腔内残腔的情况下,肺创面直接暴露于残腔内,无法被胸腔内组织覆盖、封堵而导致PAL。除此之外,本次研究中发生术后胸腔内残腔的患者术后72 h胸腔引流量明显较多,其原因可能与全胸膜腔粘连有关。一方面,胸膜粘连带内分布有丰富的滋养血管,术后胸腔负压环境使滋养血管再次开放,导致胸膜弥漫性渗血。另一方面,胸腔粘连松解创面大、渗出多,而胸膜由于被粘连带的纤维素附着导致再吸收能力差,术后胸腔渗液增多。由于体液经胸腔丢失较多,此类患者在术后早期常会并发低蛋白血症和电解质紊乱,临床上需注意监测和补充。
本研究中统计的重大并发症均发生于术后有胸内残腔者,其中并发感染共3例,1例为肺曲菌球病,1例为支气管扩张并发感染,1例为慢性肺脓肿,均经使用敏感抗菌药物及持续胸腔引流后治愈。残腔感染发生原因可能与术中病灶破溃、余肺感染播散及持续漏气后长期胸腔引流等有关。持续残腔引流和抗菌药物灌洗是治疗残腔感染的一种比较安全和保守的方法[8],但对于严重感染或者较大的残腔,这种方法效果往往不理想,需二次手术治疗。目前文献报道的手术方法主要有胸腔廓清术、胸腔开窗引流联合胸廓成形术、残腔填充术(带蒂肌瓣、大网膜等)等[9-12],总体效果尚好。
值得关注的是:本组1例术后发生迟发性胸腔出血患者,原发病为继发于肺结核的肺曲菌球病,术后第9天排便后上胸管见鲜红色血性液体引出,随后出现失血性休克症状,急诊剖胸探查,见第2肋间动脉后段破裂出血。分析出血原因可能是因病灶处肺上叶与胸壁呈胼胝样粘连,术中于胸膜外松解粘连时损伤肋间动脉,行缝扎止血,术后变换体位时胸管摩擦致该处动脉再次破裂。在感染性肺病手术中,这种病灶局部呈胼胝样胸膜粘连甚至融合的患者并不少见,而胸膜外游离粘连是确保完整切除病灶、避免术后残腔感染的有效手段。由于没有明显的解剖界限,术中肋间血管的损伤往往难以避免。笔者总结认为,避免出现这种并发症的方法除了术中进行牢靠的缝扎外,关键是胸管不能置入太深,防止胸管末端摩擦胸顶及侧后胸壁导致再出血。
通过对肺上叶切除术后胸内残腔发生的危险因素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若患者原发病为感染性肺病或并发通气功能障碍,尤其是术中发现全胸膜腔粘连时,应警惕可能发生术后胸内残腔。术后胸内残腔的形成,在术后早期可以导致胸腔大量渗液及PAL,导致延长患者住院时间、增加住院费用。虽然术后胸内残腔相关的严重并发症发生率不高,但对这些并发症的处理比较棘手,且耗时较长。目前,关于术后胸内残腔早期预防和采取处理措施的文献报道较少,如何降低术后胸内残腔的发生率和对患者术后早期转归的影响,仍需做进一步的探索和进行大量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