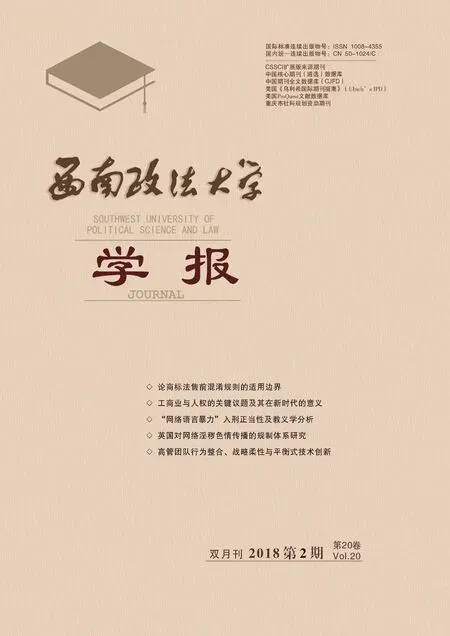尼采对西方人权及自然法的批判
明 辉,李 霞
(1.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法学院,北京100191;2.中国社会科学院 法学研究所,北京 100720)
有一种古老的幻想,叫做善与恶。[1]
——尼采
就德国法学家及其法律思想而言,中国学者更多关注的是康德、黑格尔、萨维尼、马克思、拉德布鲁赫等人的法律思想,相对于哲学界和文学理论界而言,法律学者对尼采的关注则较少*依据笔者从中国知网(http://law1.cnki.net)“中国法律知识资源总库”中的检索(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2月28日),国内中文期刊鲜有刊发从法学的视角研究尼采哲学思想的学术性文章。例如,以“尼采”为篇名或关键词,仅检索出4篇:胡光,弓伟.论尼采思想的法哲学价值[J].台声·新视角,2005(5);冯念学.尼采的精神三变给法官的启示[N].人民司法,2012(13);张薇薇.尼采的大地与中国之天命观:法则展开之源叙事[J].政法论坛,2014(6);邱帅萍.尼采的刑罚观[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9-21.;而在西方法学研究领域,早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关注并研究尼采的法哲学思想*例如,参见:Peter Goodrich, Mariana Valverde. Nietzsche and Legal Theory: Half-written Laws[M].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5;John Linarelli. Nietzsche in Law’s Cathedral: Beyond Reason and Postmodernism[J]. Catholic University Law Review,2014,53:413;Francis J. Mootz III. Nietzschean Critique and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J]. Cardozo Law Review,2013,24:967;Jonathan Yovel. Gay Science as Law: An Outline for a Nietzschean Jurisprudence[J]. Cardozo Law Review,2003,24:635;Adam Gearey. We Fearless Ones: Nietzsche and Critical Legal Studies[J]. Law and Critique,2000,11:167;Richard H. Weisberg. It’s a Positivist, It’s a Pragmatist, It’s a Codifier!——Reflections on Nietzsche and Stendhal[G]∥ Morris Dickstein. Revival of Pragmatism: New Essays on Social Thought, Law, and Cultur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8:312-323; Barbara Stark.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Feminist Jurisprudence, and Nietzsche’s Eternal Return: Turning the Wheel[J]. Harvard Women’s Law Journal,1996,19:169;Marianne Constable. Genealogy and Jurisprudence: Nietzsche, Nihilism, and the Social Scientification of Law[J], Law and Social Inquiry,1994,19:551.。对尼采的研究在法学领域的兴起,多少有点令人意外,因为按照通常对法学家的评判标准来看,尼采并没有提出一套系统的法哲学或者法律理论,甚至因其否认人类基本权利的存在而被视为法律上的虚无主义者。
或许,西方法学界对尼采的关注,在相当程度上源于后现代主义思潮以及非基础性的、批判性的、碎片化的法律研究进路。倡导“解构”的欧洲学者因将解构主义的方法追溯至尼采,而被称为“新尼采主义者”;同时,基于非基础性的研究进路,尼采还被视为第一位后形而上学思想家以及“后现代主义之父”。与之相应,在法学研究领域,尼采的作品同样吸引了诸多研究者对非基础性法律研究进路——特别是法律实用主义(legal pragmatism)和批判法律研究(critical legal studies)——的极大关注与兴趣。
在卷帙浩繁的著述作品中,尼采似乎很少关注法律问题,更多地是运用零散的格言或谚语,以碎片化的方式谈论某些法律问题,甚至缺乏起码的系统性或者论证逻辑。因此,如果想要认识、理解、阐释尼采的法哲学,就不得不超越他对法律的片断式讨论,从其对相关哲学问题——诸如形而上学、基础性方法论、基督教理念等——的探讨中获取可供认识、理解与阐释的智识线索。
如果说,尼采的作品隐含着某种独特的法律研究进路,那么,或许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从整体上对西方法律传统——尤其是自然法理论——的批判。尼采的作品不仅仅是批判性的、否定性的,而且也有利于提出一种肯定的法哲学。不可否认,在部分段落中,尼采对民主、法治、国家及女性主义持有一种贵族式的嘲讽态度。故而,不得不从尼采碎片化的哲学格言中推导出他的法律理论。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出,尼采的作品中隐含着一种暂时性的、非基础性的、试验性的法哲学;同时,尼采并不是一个法律虚无主义者,因为他承认,在优选的意义上,法律制度既确认生命,也创生权力。
一、人权、自然权利与自然法传统
在讨论西方自然法理论时,通常至少涉及三个基本的核心观点:(1)存在特定的永恒不变的自然权利,在公民社会出现之前,个人享有自然权利;(2)当人们集合起来构成一个公民社会时,这些基本权利必须受到尊重,因为只有形成保护基本权利的机制,公民社会才具有正当性;(3)公民社会的法律是自然或者上帝的命令,可以依据理性加以确定。一般而言,自然法与自然权利是行为的法典,被认为是上帝赋予的、人性固有的,并且是可以凭借理性发现的或者推导出来的。自然法理论认为,法律与道德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因而,检验“法律”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符合一项预先确定的、永久遵行的道德命令。在绝对的意义上,不道德的法律不是真正的法律。也就是说,背离自然法原则的人定法(或实证法)不是真正的法律,在道德上不具有约束力[2-3]。
虽然自然法概念至少可以追溯至亚里士多德对“自然正义”与“约定正义”的区分[4],但最早明确阐释自然法概念的却是西塞罗,他曾在《国家篇》中指出:
真正的法律乃是与本性相合的正确的理性;它是普遍适用的、不变的和永恒的;它以其指令提出义务,并以其禁令来避免做坏事。此外,它并不无效地将其指令或禁令施加于善者,尽管对坏人也不会起任何作用。试图去改变这种法律是一种罪孽,也不许试图废除它的任何部分,并且也不可能完全废除它。……罗马和雅典将不会有不同的法律,也不会有现在与将来不同的法律,而只有一种永恒、不变并将对一切民族和一切时代有效的法律;对于我们一切人来说,将只有一位主人或统治者,这就是上帝,因为他是这种法律的创造者、宣告者和执行法官[2]。
从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倡导的自然法理论中,也可以看到这种对自然法的早期阐释。阿奎那认为自然法包括了一套永恒不变的基本原则,可以依据理性予以发现,并且可以适用于所有人。由人类创制的“人法”,只有在能反映自然法的情况下,才会被视为在道德上是可接受的,而任何试图超越自然法疆域的尝试都被认为是不道德的[3]107、112-117。自然法为基本的公民权利与自由提供了一种超验的基础,因而也就创设了一种人们可据以拒绝压制法律的标准。此外,如果从建构国家基本框架的角度讲,公正的国家应当忠实遵守自然法的基本原则;如果从构成公民社会的个体角度讲,也就是“人权”,至少包括自由、安全以及财产权利。然而,尼采恰恰否认、甚至解构了作为西方——无论是古希腊—罗马时期,还是在中世纪——自然法理论基础的道德观,在他看来,“道德〈的〉价值评估乃是为一种权力意志(群盲的意志)效力的谎言和诽谤术的历史”[5]149,即便是“更高的道德生活,圣徒的生活,也只不过是为了满足未和解的心灵而被虚构出来的手段之一”,因为“不存在永恒的道德”[5]6、20。
迄至19世纪,自然法观念在西方社会思想中已经根深蒂固,“社会契约论”就是其主要的理论表现之一[6-9]。不可否认,法国大革命与美国独立战争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以“社会契约论”为表现形式的自然法观念的影响,即使如此,尼采依然敏锐地意识到西方自然法学者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相互矛盾的理论阐释[10]。尽管并没有专门针对社会契约理论进行详细评论,但显然,对于可基于历史的或者假设的社会契约建构社会、乃至主权国家的自然法观念,尼采明确表示拒绝[11]。
由于尼采拒斥“自然法”(natural law)和“自然法则”(laws of nature)概念,所以有必要对这两个概念进行适当辨析。“自然法”意指针对人际关系的行为法典,而“自然法则”是指支配自然事件的永恒不变的法则。在阿奎那看来,“自然法”这一术语仅仅适用于施予统治与评判的某种存在物,即理性的动物——“人”[3]107。相对而言,“自然法则”适用于其自身受到统治与评判的诸种存在物,诸如树木、岩石与动物。这些存在物不得不遵守自然法则,因为它们不具备意志自由。另一方面,在运用理性认识自然法后,人类只能通过做其应做之事来遵守自然法。与自然法则不同,通过观察人类的行为,并不能直接发现自然法,而只能运用洞察力与理性才能感知到自然法。由此可见,或许可以将自然法理解为在某种理想化的道德秩序或者理想化的公正社会中存在的法律。一种理解此类观念的方法是,假定自然法暗含着某种关于人类生活的目的与功能的目的论观点。
通常而言,西方学者的习惯看法认为,人权出自法国大革命的精神,这一精神又是法国启蒙运动的政治表达,故人权是一种“反抗的宣言”,而《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显然是法国大革命初期的产物。其中,所谓的“人权”是“至高无上的”,是“天赋的”,是“不可剥夺的”,至少包括“自由、财产、安全与反抗压迫”[12]。这些正是近代西方自然法学者在政治哲学层面上的基本诉求。然而,耶里内克却冷静指出,不可高估自然法与人权之间的连续性,因为单单自然法本身无法导致人权的制度化;质言之,人们不可能从这样的哲学中推导出那些规定实证法的约束性的“元规范”[12-13]。当然,耶里内克对自然法与人权之间联系的切割,旨在论证“人权宣言”、乃至“人权”本身的宗教根源。
总体上讲,西方传统自然法学者主张,在自然法则之上,存在一种应当支配人类行为的道德法,并且可以依据理性推导出这样的法律——自然法。对此,尼采曾经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讨论过法律以及一些与法律相关的理论问题,尽管内容并不多,但至少可以从中梳理出以下三条对西方人权、自然权利与自然法传统的批判线索:(1)提出一种认知怀疑主义,排除了自然法的可能性;(2)通过一种语言学理论,将自然法揭示为一种人类的“虚构”,是一种保存生命的、或许有益的传统习俗;(3)提出了一种法律起源的谱系学,摧毁了人权与自然权利的观念。由此可见,尼采的法律研究进路是批判性的,因为他意欲破除19世纪西方主流观念,包括当时流行的自然法观念——即可以依据关于自然、纯粹理性、不证自明或上帝的形而上学的或者认知性的主张发现法律。
二、尼采的第一批判:人权与自然法的幻想
如果想依次展开尼采对西方人权与自然法传统的批判,首先,或许可以从尼采对自然法则的批判中推导出其关于自然法的观念:即对自然法则的拒斥必然导致其对自然法的拒斥。为此,必须让人们意识到尼采拒斥存在永恒不变的自然法则。对于尼采而言,“自然法则”并不是从现实中可以找到的既有模式,而仅仅是一种渗透于理论之中的解释,“人们该会原谅我,作为一个老语文学家,忍不住要恶意指摘一下低劣的解释伎俩:你们这些物理学家那么自负而煞有介事地谈论的那个‘自然的合规律性’——它多亏了你们的诠释和低劣的‘语文学’才得以延续——并不是事实要件,不是‘文本’,而毋宁只是一种天真而人道的编造和曲解,由此你们尽情迎合了那些现代灵魂的民主本能”[10]40,而“合法”与“非法”是从“法律建立”之后才有的区分,本质上,就其基本功能而言,“生命发挥着伤害、强暴、剥削、消灭的功能,没有这种特征生命不可设想,就此而言,谈论法和非法本身缺乏任何意义,某种伤害、强暴、剥削、消灭,其本身当然可能并无‘非法’之处”[11]392。
尼采想要否认存在某种仅仅需要发现即可认识到的先在的自然法,因为在他看来,现实中根本不存在可以发现的规则,也根本不存在“法律”规则。[10]40实际上,尼采将自然法视为一种“迷信”和“神话”。在尼采看来,看似永恒不变的“自然法则”并不真正存在于预先设定的事物秩序之中,而仅仅是一种“作为对权力联系和权力等级的无条件确立的公式”[5]13。此类法律仅仅是一种受到利益驱动的对事物的解释,是无数竞争性解释中的一种。当然,有些解释是优于其他解释的,因为它们更好地考虑到经验的因素,具有更多的内在的一致性,可以做出更好的预测。但是,即使是最好的解释也仍然是一种人的创造,一种保护生命的传统习俗,不应当被当作一种对真实的完美反映。
此外,根据自然法理论,“自然”可以为道德规范提供基础。尼采也拒斥这种自然法观念。仅就解释的方法而言,“自然”可用于证明专制与道德具有同样的正当性,“‘没有上帝,没有主人’——你们也有这样的愿望:因此,‘自然法则万岁’!——不是吗?但是,正如前面说过的,这是解释,不是原文;可能会出现某个人,他善于以相反的目的和解释技巧,从同一个自然之中,着眼于相同的现象,却恰恰理解到,诸种权力主张在霸道而无所顾虑地、毫不留情地贯彻着”(依据上下文语境,将原引文中的“规律”改为“法则”)[10]41。
为了支持他们特定的伦理与政治计划,自然法学者带着偏见解释自然。依据伦理信仰解读“自然”的错误,至少可以追溯至斯多噶派“适应自然生活”的告诫,在尼采看来,你们愿意“适应自然”而生活吗?哦,你们这些高贵的斯多亚主义者,耍这种言辞的花招!你们设想自然如一个造物,无限漫汗,无限淡漠,没有目标和顾虑,没有怜悯和公正,可怕、荒芜而又不确定,你们将这种无差别本身设想为权力——你们怎么能够适应这种无差别而生活[10]19-20?
一般而言,自然法学者会主张,自然可以为永恒不变的道德法典提供线索。然而,尼采却认为,这种主张根本不具有任何经验的基础,因为“他们通常自己服从一种道德的命令,他们所做的勾当说到底无非是进行道德宣传”[5]170。
对此,尼采提出警告,应当避免将某些人的理论模式具体化为它们是否属于先定秩序的组成部分。尼采所担忧的是,由于会将这种解释误认为原文本身,进而混同为文本,排除所有其他的解释。在尼采对法国革命的评论中,尤其突显了这样的忧虑,法国革命是一场“恐怖的、从近处评判又是多余的闹剧,从远处却有全欧洲高贵而痴狂的观众如此长久、如此激情洋溢地把他们自己的愤慨和激动阐释进去,直到文本消失在阐释之中”[10]65。
因此,如果自然法学者在智识上都是诚实的话,他们将不得不承认,对“不证自明的权利”和“自然法则”的诉求仅仅是一种“解释”,而不是“原文”。这些实际上是自然法学者假设的调整性观念,旨在证明他们既有的正义国家概念的正当性。也就是说,对于“自然”的解释是为了给他们的政治观念提供支持。此处,尼采的目的在于,揭示自然法理论的两面姿态:自然法理论打算将法律秩序建立在人性研究之上,然而,反之亦然,因为正是这种自然法理论确定了关于自然的观点。在公正发现权利的借口下,掩盖着探究此类权利的欲望,而这种欲望又塑造了对权利的探究。
事实上,人们做得很好(而且很聪明地),为了解释某派哲学中那些最冷僻的形而上学论题到底是如何形成的,他们总是首先问自己:它意愿(他意愿——)从哪一种道德出发[10]16。
所有哲学家都招来半是疑虑、半是嘲讽的目光,这并非因为人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发觉哲学家们多么无辜……而是因为他们不够正直:在刚要触及真诚问题的时候,便全体立即发出颇见美德的喧哗。他们全都在装模作样,仿佛他们是经过某种冷静、纯粹、神一般无忧远虑的辩证法揭示和达到自己的观点的(这区别于任何级别的神秘主义者,后者更实诚、更蠢,——他们还在谈论“灵感”——):归根结底却是,某条事先拟定的命题,某个念头,某次“灵光一闪”,大多数时候是某个被抽象地拟定和筛选出来的心愿,被他们用事后找到的根据加以辩护[10]15。
当人们认为有人发现了一种确定的、终极的解释——冰冷的、公正的理性的产物——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智识上的“不诚实”。然而,自然法学者错误地假定,可以一劳永逸地解析自然秩序,从而赋予一种对人类事务的终极的、权威性的解释。
尼采认为,实际上根本不存在法则,人只是不断地进行自我修复与自我重释。如果尼采是正确的,那么,基本人权就不可能建立在一种关于自然、理性或者上帝的静态概念之上。而且,只能将权利认定为一种人的创造,一种必要的确认生命的假定。因此,人们无法“发现”,而只能“创造”法律与道德。
正是人类创造了“自然权利”的概念,进而使这一概念呈现在世人面前,最后又宣称从自然中发现了这些权利。对于自然法的检验,不在于它是否真实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而在于它是否能通过道德推理加以理解。无疑,尼采认为,如果自然法学者宣称这样的观点——即自然法是规范性的而非描述性的,那就必须放弃下述观念——即自然法可以根植于对既有人类事件的解释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就自然法而言,根本不存在什么非常“自然的”东西。在西方自然法学者的想象中,理想化的国家首先是一个正义的国家,尼采却对此表示怀疑。
然而,尼采对自然法的批判比这些观点更为深入。例如,自然法理论认为,存在一种永恒不变的人的本质或者共同的人性,可以作为法律秩序的基础,但尼采却拒绝接受这样的观念,并且否认“人”是一种先于社会习俗而存在的自然事实。相反,伴随着不同的时代,人被创造和制造成一个理论上的构造物;根本不存在可用以创造一系列必要的道德法则的共同“主体”或“自我”。在这个意义上,人始终是“超越自我”的,因而不可能知道人将来会变成什么。就像闪电和闪电的照耀一样,“民众道德也把强势和强势之表现区分开来,仿佛在强势后面还有一个置身局外的基底,任由它随意表现出或者不表现出强势。可是没有这样一个基底;在行为、作用、生成后面没有‘存在’;‘行为者’仅仅是因为那个行为才被追加撰述出来的,——行为是一切”[11]353。代替自然法关于超验主体的观念,尼采试图将“法律秩序”建立在下述事实之上,即人始终在进行自我修复和自我超越。
为了概括尼采对自然法理论的第一个批判,无法设想在“自然”中存在或者依据理性可以推导出来道德法则。假设存在自然权利,就是“神话般地”构想,就是误解人们对永恒真理的偏见:哲学家们“全是不肯被叫作律师的律师,而且大多数甚至是在为自己的成见(他们将之施洗赐名为真理)狡辩”[10]15。或许,可以认为,尼采的主要敌人是智识上的不诚实——拒绝承认某人的假定可能会出错并且受到利益的驱动。而这恰恰是自然法理论无法承认的。
三、尼采的第二批判:人权与自然法的语言学错误
在尼采看来,根本不存在自然法和不可化约的人权。如果尼采是正确的,那么他就必须考虑下述事实,即人们将继续谈论这些好像实际存在的权利。可以在尼采的语言理论中找到对这一错误的解释。此处的基本观点是,关于权利的话题是语法上的和形而上学的错误在语言上沉淀的结果。权利的语言深陷在由糟糕的解释模式与形而上学的假定构成的泥潭之中,这至少可以追溯至基督教时代的初期。实际上,当前的权利话语让人们认为权利是发现之物,而不是暂时的假定——权利应被具体化。
尼采认为,日常的“真理”观念就是协议——在受厌烦和需要驱动的人之间订立的和平条约——的结果。这种语言上的立法创造了一种共享的真理观念,这种观念建立在一股由隐喻、转喻、拟人等修辞手法构成的潮流之上。这并不说根本不存在像真理这样的东西,或者真理是武断的。它仅仅意味着,人们必须记住真理不是一个人类可以一劳永逸地抵达的静态的终极状态,而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传统习俗,一种“保存生命的错误”。
对于尼采而言,在“词”与“物”之间不可能存在永久的联系,因而,除了暂时的假定,根本不存在固有的人权基础。人们绝不可能说,人权与自然法是人与生俱来的,因为有如此想法就是忘记了“自然法”这一术语隐喻般的起源。“自然的”这个词仅仅是一种语言习惯,而自然本身无法提供能够证明这种固有人权的主张的证据。也就是说,人们不应将权利话题的有用性与权利话题的真实性混为一谈。例如,从语源学的角度讲,“善”这个词从一开始就不是跟“非利己”行为必然联系在一起,因而,在尼采看来,将两者联系在一起,是“道德谱系学家们的迷信”,不仅“在历史学上是站不住脚的”,即便是作为一种关于“善”之价值判断的起源假说,也是一个“心理学的荒谬”[11]328-330。
即使有人(为了某些政治目的)需要声称存在人权,哪怕是基于不证自明的理由(例如《独立宣言》),但也无需坚持认为这种观点是永恒不变的真理:“谁如果敢诉诸某种认识直觉而对这些形而上学问题做出即刻的答复,像某人那样,说‘我在思考,我知道,至少这一点是真实的、确实的、肯定的’——则他今日在一位哲学家那里可要碰上一声嗤笑和两个问号。‘这位先生’,哲学家也许会提示他,‘您几乎不可能没弄错:不过,为什么非要真理不可呢?’”[10]32也就是说,直觉和语言仅仅是为思考权利问题提供了一个起点,但它们无法成为权利存在的首要和最终的权威。
诸多世纪以来,哲学家、神学家和政治家都在谈论自然法及其理论,因而,西方学者倾向于将自然法视为用以构建人类事务体系的组成部分之一。但从西方自然法的历史演进过程来看,这种自然法的立场实际上是一种以神学为基础的进路,从根本上讲源于下述错误的观点,即存在可以依据理性加以辨识的永恒不变的道德行为法则。在尼采看来,如果“按照科学的尺度来衡量,人对人所做的每一种道德价值判断,其价值是微不足道的:那是一种试探和摸索,每个词语都饱含幻想和不确定性”[5]19。
尼采所称的“上帝死了”[1]458使人们认识到人权是一种习惯,但此处所谓的“习惯”,不是任意指定的意义上的“纯粹习惯”,而是人类创造的意义上的习惯。如果忘记这一点的话,人们就会犯错误,就会将权利当作自然秩序的组成部分。
此外,智识上的诚实要求承认无法获得明确知识的理论,并且愿意改正或者放弃先前的研究进路。尼采认为,存在无数种可能的解释,因而解释的过程是无目的的,并且仅仅受制于人类的需要与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合时宜的法哲学都愿意依据新的解释和新的研究修正、改变或者放弃它的根基。
至此,可以将尼采对自然法理论的第二个批判概括为:西方自然法理论的危险之处在于,它对“自然的”这个词的理解和解释,实际上是模棱两可、含混不清的,从而使人们错误地相信可以从自然中发现权利,甚至可据以推导出基本人权或者对其加以论证。事实上,这会让人们误认为权利是一种可以发现的实体。显然,尼采拒绝接受这样的自然法观点和推论,以及由此而衍生的人权理论。
四、尼采的第三批判:对人权与自然法的谱系学解构
历史上,自然法理论声称,可以设想在公民社会出现之前便已存在一种自然状态。尽管自然法学者对于是否真正出现过这样一个历史状况仍然存在分歧,但他们都同意可以利用这种关于原初自然状态的观念判断现代国家是否具有正当性。自然法理论假定可能存在一个关于“正义”或者“自然权利”的前法律状态——先于实证法制定之前存在的状态,而尼采却在《论道德的谱系》中对这种假定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与洛克、卢梭以及康德的观点相对,尼采意欲表明,设想一种先于法律实施而存在的状态,是不可能的。尼采不仅反对必须依据当事人如何行为或者在一种原始自然状态下会如何行为来判定正义的观点,而且还反对公民社会起源于社会契约的主张,即所谓的“人类社会:它是一种试验,我如是教导,——一种长久的寻求:但它寻求的却是一个命令者!——一种试验,啊,我的弟兄们啊!而且不是什么‘契约’!为我粉碎吧,粉碎那些好心肠、半心半意的人们的此等辞藻”[1]341。在尼采看来,国家“是从一个‘契约’开始的迷狂已被破除了。谁若能够下命令,若天性即为‘主人’,若以暴力行事而成其作品和姿态,——他要用契约来干什么呢![11]405”尼采的观点不仅在于否认历史上社会契约的存在,还在于指出无法依据此类理想化的自然状态创造正义原则,因为只能将自然状态设想为法律的后果,而不是法律的缺失。
当人们普遍认为,人是因受过教养而信守承诺的动物时,尼采开始与这一观点展开争辩[11]368-370。但是,人实际上都是非常健忘的,而严厉的惩罚会使承诺得以记住与遵守。惩罚是由债权人施予债务人的;惩罚也是一种在债务人未履行债务的情况下施予债权人的救济。如果债务人忘记了他的债务,那么债权人的财产就会被剥夺,此时,债权人会将他的愤怒发泄在债务人身上。尽管债权人未能获得返还财产,但也可以从酷刑中获得愉悦,在这个特定的意义上,债务得到了履行[11]377-379。因此,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是首要的法律关系,所有其他的法律关系均建立在这一关系的基础上。这一结论符合尼采早期宣称的观点,也就是,权利源于缔约当事人之间相互冲突的权力主张。那么,正义始于追求相互贸易并以信守承诺实现自我保护的平等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正是平等当事人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本身既非善亦非恶,而仅仅是人性的)导致了法律的产生。尼采想要声称,刑罚中正义的原始基础不仅被遗忘,而且还被逆转:正义起初源于自私自利的目的,但后来又被用以实施非自私自利的行为(仁爱、宽容、公正)。
实际上,尼采认为,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存在两种法律范式。第一个法律时代建立在强者之间权力关系的释放的基础上[5]256-257。这实际上是原初的正义观念,即平等当事人相互之间的平衡,以及施予不平等当事人的刑罚与报应。第二个法律时代的到来伴随着以基督教为基础的怨恨的伦理规范,其中,弱者联合在一起反对在强者中盛行的原初的正义感。这种反应性进路强调对弱者或者不平等当事人的宽容、平等与公正。第一种范式大体上对应于尼采所谓的“主人道德”(master morality),而第二种范式则对应于“奴隶道德”(slave morality)。
这两种观点的斗争贯穿于整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过程中,而当前的司法制度是一种混合的类型学,包含了构成两种范式的诸多因素。对此,尼采的主要观点是,在没有任何种类的超越理由的情况下,原初的正义能够发挥作用,因为它是一种保存生命和确认生命的实践。尼采谱系学的核心目的是让人们记住,创造正义与法律是为了满足人的利益与需要,尽管基督教希望依赖上帝或自然为正义与法律提供正当性基础。
尼采认为,始终存在某种形式的法律,作为强大种族之间的交换关系与刑罚。因此,从起源上讲,法律不可能是因为对一系列先在的自然权利的侵犯而出现的,从历史学的角度看,大地上的法……恰恰是在进行对抗那些反应性感情的斗争,站在行动性、侵略性的权力一边对它们进行战争,这些权力把它们的强力部分地用于禁止和节制这种过分的反应性的感情用事,对之作出强行的调解。……针对那些对立性和后遗性的感情,最高暴力所实行和贯彻的最具决定性的举动——它一旦强得足够这么做便会这么做——是法律的建立,对于在它眼中究竟何者须视为允许与合法、何者为禁止与非法所做的律令性解释:法律建立之后,它把个人或整个群体的触犯和专断行动当作对法律的亵渎,当作对最高暴力的抗命不遵来自置,……自法律建立始乃有“法”与“非法”。……把某种法律秩序想成是绝对主导和普遍的,不是把它当作诸种权力复合物的斗争手段,而是当作根本上反对一切斗争的手段[11]391-392。
在这里,尼采的基本观点是,所有法律制度都必然可以化约为权力关系。古代的正义制度是一种很明显的由权力关系构成的制度,肯定有许多过度和残酷之处,但在很大程度上是确认生命的和“肯定的”。以基督教为基础的法律制度也是一种由权力关系构成的制度,但它是一种否定生命并以怨恨情绪为基础的制度,建立在神话、对变化的恐惧以及对生命的敌意的基础上。更为重要的是,以基督教为基础的制度谎称它不是由权力关系构成的制度,而仅仅旨在保护上帝赋予的自然权利的状态。实际上,这种基督教的理想是对整个自然的倒置,因而对生命怀有敌意。因此,尼采谱系学的观点在于,应当有理由怀疑基督教的正义制度是否表现出一种对古代制度的进步,当然,尼采肯定不至于倡导重返古代法。
尼采拒绝接受先在的自然状态,同时也反对无政府主义者所坚持的人是“天生自由的”观点。尼采声称,无政府主义者所谴责的“变化无常的法律”并没有不公平地强制先在的自由状态;相反,此类法律是自由存在的条件。自由不是一种初始状态,而是一种终极状,只有在权力关系稳定下来,以至于人们可以实施特定行为而不受惩罚时,自由才是可能的。也就是说,人并不是“天生自由的”,仅仅是发现自己受制于法律。相反,最早界定自由王国的正是法律的强制:
实际情况却很奇怪,大地上现有和曾有的一切跟自由、精细、胆量、舞蹈及大师才有的沉着相关的东西,不管是在思想自身,在执政时,在演说和游说时,在诸门艺术中,还是在诸般德教中,都是因为有“此类专断规则的霸道”才得以发展;最严肃地说,不无可能的是,恰恰这才是“自然”和“自然的”——而不是那种放任自流[10]136!换句话说,根本不存在所谓“自然的”状态,但假如存在这样的状态,它也将是诸多权力关系之一,而不是自由。
尼采的谱系学进路旨在揭示道德命令的历史基础,将诸多道德范畴视为创造物,而不是固定的、永恒不变的命令。他的目的是破坏人们从诸如“义务”和“良知”等“宏大语词”中获得的愉悦。如果尼采的谱系学是正确的,那么,自然法理论就是错误的。正是因为自然法理论仅仅是试图将法律建立在超人王国的基础上,而不是将法律建立在作为法律之起源的人类利益的基础上。
五、批判基础上的法哲学重构
然而,需要强调的是,尼采对自然法的批判只是部分获得了成功。自然法被写进道德生活的结构之中,并且可以通过对人性的反思发现自然法。尼采对这种古典自然法观念发起了猛烈的挑战。此外,尼采似乎还成功地挑战了诉诸不证自明的本能或者超验基础的自然法观点。但仍然存在其他一些潜在的问题,或许可以归因于尼采的谱系学进路。虽然无法详细探究这些问题,但还是值得提及,并予以简要论述。
第一个问题是,尼采仅仅提供了对自然法概念如何出现(作为一种以怨恨情绪为基础的、对古代正义制度的基督教回应)的一种解释,并没有明确指出是否可以将这种解释转化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理论。尼采认为,从历史上看,人权的观念是在更为原始的正义观念之后出现的。自然权利的辩护者会同意尼采的这个观点,或许也会承认无法将自然权利建立在自然或者上帝之上,但其仍然会坚持认为,自然权利是人类对协作、联合或者交流的需求中所固有的[14-15]。自然权利的辩护者也承认在人类文明的早期阶段并没有认识到自然权利,但即使未能认识到,自然权利仍然存在。作为自然法理论的倡导者,洛克或许早已预料到尼采的批判,故而指出,无论人们是否认识到,或者是否承认自然法的教义,都存在某种形式的自然法[16]。
第二个问题是,尼采未能充分认识到,那些秉持社会契约论传统的自然法学者并没有主张历史上存在某种“自然状态”,而是将“自然状态”视为一种可用以检验现代国家的正当性的假定条件。这种“自然状态”被当作一种理性的观念或者“思想的试验”,用以判定国家是否具有正当性。也正是由于这些社会契约理论不是建立在历史观点上的,所以,无法依据法律与道德起源的谱系学来直接否认或者质疑这些理论。
对尼采而言,这些都是涉及正当性的问题,或许尼采未能把握某些社会契约理论更为微妙的观点。尼采尽管未能充分理解,但仍然对下述观点——自然法可以建立在不证自明、理性、上帝或者自然之上——发起了猛烈的挑战。在这个意义上,他的批判对当时流行的社会契约论观念构成了挑战,尽管他的批判在几个重要问题上是不彻底的。对于尼采的批判,现代自然法学者或许会提出,如果尼采对自然法理论提出了批判,那么他就必须提出一个更可取的替代法律理论。也就是说,他必须提供某种确定的评判标准,据此,可以判断某项特定的法律制度或者法律优于另一项法律制度或者法律。
这种批判方法引起了所谓的“法律虚无主义”的问题,也就是,在竞争性法律编制之间根本不存在可供选择的正当性基础。于是,将再一次面临这样的问题:在尼采的哲学思考中,有可能构建出一种规范性的法律理论吗,或者他仅仅是提出了一种对法律的批判?如果想回答这样的问题,就不得不尝试提出一种可供评判的“尼采的法哲学”。
为了回答前面提出的问题,首先要找到将尼采碎片化的格言连缀起来的法哲学的基础。在尼采看来,一部法律或者一项法律制度,只要能确认生命和创造权力,就会被暂时接受。这种观点可被视为尼采法哲学的基石。这就意味着,必须进行先期研究,以确定一部供表决的法律是依据不被认同的理由(法律是由自然或上帝颁行的),还是依据公认的理由(法律是对我们是谁以及我们作为自由的、试验性的、自我超越的个体想要成为谁的公正反映)来寻求法律的正当性。关键在于,在自我克制、人类进步以及自我超越的意义上,最大限度地释放权力。一旦意识到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建立法律秩序,人们就要继续塑造法律,以使其适应不断变化的人类需求。尼采的研究进路不会建立在静态的形而上学的人性观念之上,而只是尊重这样一种意义,在这个意义上,人类持续不断地自我超越,并且尝试尽可能地为自我探索与自我克制开辟道路。
尼采提供了一种可据以在不同的法律制度之间做出选择的标准,因而他并不是一个法律虚无主义者。首先,他必然要拒斥受制于人性、不证自明、上帝等存在疑问的概念的所有法律或者法律制度。其次,对一部可接受的法律而言,它必然要根植于当前关于人类自身作为自由的且富于创造力的个体的观念之中,必然要为私人领域的权力创造与自我克制保留最大的余地。尼采认为不可能存在法律秩序的终极依据,在这个较弱的意义上,他算是一个法律虚无主义者;同时,尼采实际上为在不同法律之间做出选择提供了一个基准,在这个较强的意义上,他又不是一个法律虚无主义者。
尼采的法律理论并不要求法律制度立刻发生彻底的变化。同时,法律应当被视为获得解放的,因为它不断变化以适应“生命的法则”——人的自我超越或者“自身克服”。如果依循这样一条进路,“更高级的法律”就会忠实地确认,权利即是人类的传统习惯,可以基于保存生命的目的赋予正当性、废除或者修正之。之所以要遵循以权利为基础的法律制度,是因为在自我实现与自我超越的意义上,法律制度为控制、统治与权力提供了可能性最大的机会,“一切伟大事物皆通过自身而走向毁灭,通过一个自身扬弃的行动:这乃是生命的法则,生命本质中必然的‘自身克服’的法则,——最后总有召唤向立法者本身颁布:‘服从你自己拟定的法律’”[11]505。据此,尼采阐明了自己的立场,旨在使人们避免面临或者陷入基础性问题的困境。而基础性问题的缺失又为全新的法律方向铺平道路。
传统观点认为,尼采的道德与政治理论是建立在权力释放的基础之上的。对这种传统观点的解释是,尼采会高度赞扬授权最大限度地释放强力与原权力的政治与法律制度,从而可能导致形成一个由贵族精英治理的社会。这就将尼采视为一个反民主的偶像破坏者,他可以凭借“权力意志”的尺度评判所有的政治与法律安排。正是基于这样的解释,才有人在尼采的哲学命题与极权主义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进而主张尼采从不承认人权的存在。
这种传统的解释认为,尼采试图重归古希腊的“主人道德”,表现为贵族统治或者以身份与阶层为基础的政治制度。这种传统的解释得到了文本的支持,但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产生了误解,因为它未能说明,尼采所攻击的不是现代法律制度本身,而是可以将法律充分且最终建立在理性、人性或上帝等基础之上的谎言。他批判任何静态的法律研究进路,批判任何据以达到解释目的的方法。与其说尼采倡导回归古希腊法,还不如说尼采厌恶基督教从人类需求与人类意志之外寻找法律起源的观念趋势。这并不是古代法优于基督教法的本质,而是在古代法的支持中提供的面具与掩饰的缺失。
总体而言,在尼采看来,因为没有哪一项法律原则如此神圣,以至于即使在必要的情况下也不得予以废除,故而,尼采的法哲学是非基础性的;同时,因为可能会采用与废除新法,以满足不断变化的关于人类自身的概念,因而,尼采的法哲学又是试验性的。实际上,这是一种怀疑任何静态的正义概念的碎片化的法哲学。
结语
综上所述,尼采并不必然是一个法律虚无主义者,准确地讲,他更像是一个法律上的非基础主义者。实际上,尼采法哲学的真正危险不在于它导向虚无主义,而在于它否认存在永恒不变的基本人权与正义概念。原因在于,“人”的自我概念的变化,也就是,关于“权力”或“统治”的毁灭性的全新概念,可能将法律引入无法预料的、令人讨厌的路向。对于尼采而言,不可能通过诉诸某种基于上帝赋予的或者不证自明的自主权的基本权利来破坏某种预期的后果。在这个意义上,尼采根本不需要承受世人对他的“法律虚无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的指控。
基于尼采对诸多基本法律与政治理念所持的嘲讽态度,或许可以认为,尼采并没有提出一种肯定的、积极的政治法律理论,并且也不可能提出一项连贯的政治法律的研究议程。由此可见,从其哲学的基底上讲,在尼采的血液里隐约流淌着欧洲古典的贵族气质,对政治法律问题兴味索然。
为了建构连贯的尼采的法律观,必须越过那些过于尖刻的段落,从而阐释一种与尼采整体哲学事业相契合的法律理论。众所周知,这种努力缺乏充足的文本支持。然而,我们或许可以将尼采关于法律以及与法律相关的主题评论加以整合,在其挑战西方传统的语境下,梳理出一种对西方自然法传统的批判。无疑,在清理尼采法律理论的细节问题时,会面临许多无法想象的困境。实际上,沿着这条道路展开的深入研究会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尼采虽然未能建构出一套逻辑一致的法律理论,但却提出了一种“姿态”与“进路”,因而可能使关于“尼采与法律”的研究通往一条极富创造性与挑战性的道路。JS
参考文献:
[1]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323.
[2]西塞罗.国家篇·法律篇[M].沈叔平,苏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01.
[3]阿奎那.阿奎那政治著作选[M].马清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112-117.
[4]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49-150.
[5]尼采.1885-1887年遗稿(《权力意志》上卷)[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49.
[6]霍布斯.利维坦[M].黎思复,黎廷弼,译.杨昌裕,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131-132.
[7]洛克.政府论(下篇)[M].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59-62.
[8]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8-20.
[9]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M].沈叔平,译.林荣远,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143.
[10]尼采.善恶的彼岸[M].赵千帆,译.孙周兴,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65.
[11]尼采.论道德的谱系[M].赵千帆,译.孙周兴,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405.
[12]约阿斯.人之神圣性:一部新的人权谱系学[M].高桦,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4,19.
[13]耶里内克.《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现代宪法史论[M].李锦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14]哈特.法律的概念[M].许家馨,李冠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180~185.
[15]富勒.法律的道德性[M].郑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13-114,215.
[16] John Locke. Essays on the Law of Nature[M]. W. Leyden, e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4: 113-115.